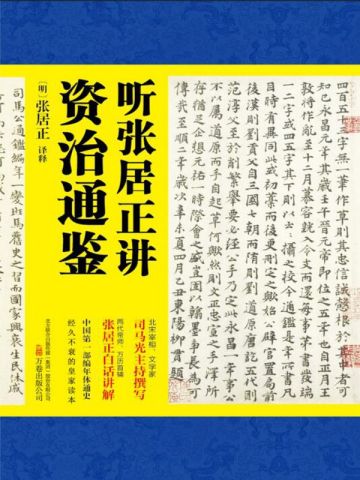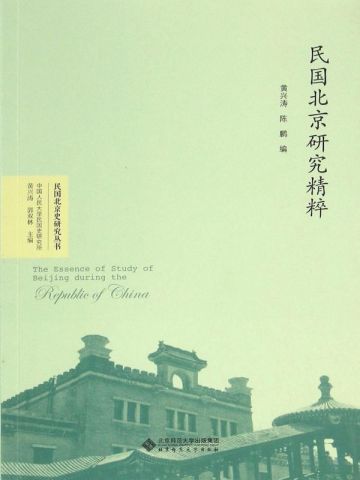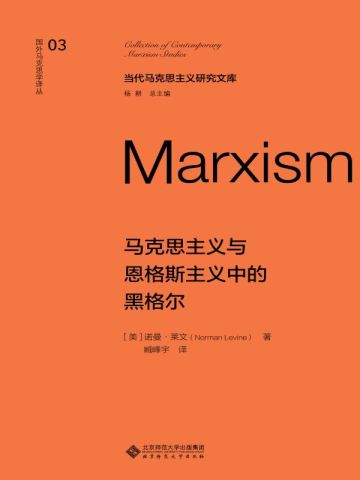礼教下延,色情上升:中国文化的分层互动
一
儒家伦理是一种生殖中心伦理。
近年来中国内地赞扬传统文化形成潮流,有一种说法,“先秦儒家创建文明社会新文化的过程,就是努力建设新的人性,彻底唾弃旧的兽性的过程。”从孔子起就强调“只有礼(男女有别)才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标志”。这种老生常谈经不起推敲。人兽之一大别的确是社会人不得不遵从一系列性禁限,但兽只有性(性冲动、性行为),色情化的性却是人类特有的。正是人的仁义良知等社会意识,把生物式的性冲动变为一个人独有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关系的混合体——色情。
生物的性严格局限于生殖繁衍所需,超出这需要就成为累赘,成为生存竞争中可能导致淘汰灭种的因素,因此“兽性”的“性”实在是相当有限。进化使人不仅成为唯一有智慧的动物,也使人成为唯一的性欲远超出生殖需要的动物。知识之昌明,医学之发达,使种族繁衍得到保障,从而使人的性欲富余量越来越大,远远超出生殖需要。
因此,人离兽性越远,文明越进步,超出性活动本来意义的色情就越发展。正是在这意义上,色情(Eros)不仅是人的本性中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是人作为社会的人,文化的立足点之一。
二
色情是一种文化现象。
色情的主导意识,是反生殖的。在色情想象与色情表现中(例如“黄色小说”中),与生殖有关的性特征都消失了,没有月经,没有怀孕,没有生育,没有子嗣。这是非生殖的“纯粹性”,色情是高级人类文明从生物性基础上剥离下来的纯粹性意识。
《肉蒲团》开场所谓“睁眼看乾坤复载,一幅大春宫”,又解释说,性是为了愉悦娱乐:
人生在世,朝朝劳苦,事事愁烦,没有一毫受用处。还亏那太古之世,开天辟地的圣人,制一件男女交媾之情,与人息息劳苦,解解愁烦。
这与《易》中关于阴阳乾坤万物生息的“性宇宙观”相去不可道里计,而恰恰是文明进步的结果。
色情想象与色情描写中一切“出格”、“性变态”不管如何花样翻新,其共同特征是不可能导致生育,令人怀疑恐怕不能导致生育的性活动,都可具有色情意味。
在色情小说中,主人公即使有后代,也得残酷地加以消除,以维护色情的反生殖性。《金瓶梅》中西门庆留下一个“孽根”,即吴月娘生的遗腹子孝哥儿。第一百回吴月娘让孝哥儿出家,被普静老师“度托”了去,“化阵清风不见了”。《肉蒲团》中,未央生与妾艳芳生有二女,未央生出家悔罪后还想去把她们杀了,说是免得让她们替父亲“还淫债”。后得二女夭折消息,竟然抚掌大喜,说是因为“一心向善,感动天心,把还债女儿收回去”。这种今天看来过于残酷的“报应”逻辑,其实是色情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中国文化的核心线索(“合二性之好,以上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色情的绝育狂最不可容忍,它不管用什么形式出现,都直接冲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基石。
三
任何社会,任何文明,都以控制性行为和色情表现为最基本的出发点,“《六经》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妇,《诗》首‘关雎’,《书》序嫔虞之文,《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岂非以情始于男女?”与“情”有关的一切,都必须控制。
控制(禁止或限制)有两种方式,一是所谓禁忌(taboo),它是在一个文化中界限明确,已成为社会成员共有的心理限制;另一个方式是查禁(广义的censorship),它是社会中用法律、行政或用舆论实行的外加控制。
无论禁忌还是查禁,都是双刃剑。弗洛伊德在其名著《图腾与禁忌》(Totern and Taboo)中指出禁忌有两面性:爱与恨,吸引与反感。任何禁限,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正是为人所向往才必须禁限,而禁限则向往必然更强。列维斯特劳斯也指出正因为禁限,被禁行为往往会出现于梦中,作为一种象征满足,“它们并不是作为实际行为的记忆,而是对于扰乱秩序、反秩序的向往”。
某些社会学家认为被禁限的色情表现,正是一个社会的负像,禁限不全是压制性的,实际上,没有一个文化中相当大一部分人的自觉配合,即理性上赞同,任何禁限无法有效实行。被禁限的内容,往往在梦、白日梦、谵妄,最后在文艺作品的虚构故事中表现出来。
梦、幻想、谵妄等色情想象领域都无法禁限,而且禁限反而使它们更为“猖獗”。色情表现的对象就是这类象征满足(而不是一般性行为),它实际上是一种所谓“二度符号体系”,即象征的象征,而社会对色情表现的禁限则是二度禁限,即禁止表现已禁限实践的事。
四
“二程先生一日同赴士夫家令饮,座中有二红裙侑觞。伊川见妓,即拂衣起去;明道同他客尽欢而罢。次早明道至伊川斋头,语及昨事,伊川犹有怒色,明道笑曰:‘某当时在彼与饮,座中有妓,心中原无妓。吾弟今日处斋头,斋中本无妓,心中却还有妓。’伊川不觉愧服。”
我怀疑王阳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名句可能就来自“避座中妓易,避心中妓难”。
“心中妓”确是一个叫道学家头痛的事,程颢是对的,无“心中妓”,座中妓就不再为妓。社会可禁限座中妓,却无法禁止“心中妓”。色情与否,是以反应为判别的。一般认为“思无邪”的读物,从未接触过的人可以觉得很色情。反过来,一般认为很色情的表现,“见怪不惊”的人可能觉得毫无刺激。就这一点也可造成是否出现“心中妓”的区分。
过强的禁限也造成过强的打破禁限的欲望;过严的社会禁限既能使社会成长自觉谨守严规,同时使他们对极低量的色情表现产生强烈反应。1979年中国内地对日本电影《望乡》演了禁、禁了演,无所适从,即一佳例。此电影写东南亚某地流落的日本妓女一生辛酸,其中接客镜头极短,但足以使在“文革”高压禁限中长大的青少年蠢蠢心动,据说甚至有女中学生学样开妓院的例子。它也使负有社会道德责任的人忧心忡忡,但几年后,各种电影放得多了,正反两种反应都不再冲着《望乡》这样无邪的电影而来。
由此可知,“心中妓”的出现及驱赶,并非单靠禁限就可办到。实际上,对色情表现不禁不成文明社会,严禁全禁会引起异常的色情心理,反而使非色情表现也“色情化”。“彻底”的性禁限非但不可能,而且有反作用。如何寻找这平衡点是难事。
五
色情并非无代价。当人们发现其色情想象太狂乱,超出社会及心理禁限过远时,就会有罪孽感。违禁虽属本能,守禁也是自觉的,二者在内心中总在演出戏剧性冲突。
内心禁限划出了一大片危险的、黑暗的,又是充满诱惑的领域,侵入这领域的行为、表现,甚至想象,都会引起内心警察的干预。
在此,我们可以看看中国文化在色情问题上一些特殊处理方式。
例如血亲(母子、兄妹等)乱伦之禁忌,本是任何文明社会之必须。当乱伦性禁忌已成为人的“自然本性”以至犯禁几不可能时,乱伦色情想象却很难禁绝。思与行的冲突,给很多民族的集体潜意识造成深巨的伤痕,于是古希腊悲剧最动人的几出都与血亲恋有关,而今影视中此类题材愈演愈烈。
血亲乱伦是不能做,却能用曲折方式(误会、命运的作弄)表现的事,此类主题之一再出现反映了人们努力压制想象与文明冲突的苦恼。
而在中国,宫廷中“蒸”、“因”、“报”之类血亲乱伦记载,先秦不断出现。后世记载却大都限于蛮夷王朝。证明至秦时,血亲乱伦禁忌已有效施行。但它却似乎没有在巨量的中国文学作品中留下任何印迹,甚至17世纪近百部色情小说中也没有。一直要到1933年曹禺的《雷雨》,血亲乱伦禁忌的心理紧张才第一次得到表现。曹禺此剧常被人说“太希腊”,却是中国现代最受欢迎的剧本。
如何解释《雷雨》的成功?中国人天性是道德民族,家庭异性成员的亲密不可能造成色情想象?这当然是欺人之谈。不能做是各文明民族相同的,无法不想也是相同的。只是别的民族能说,中国不让说,中国人也习惯了不说。对色情表现的压制,实际上是中国伦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或云血亲乱伦这问题过于极端,不能概而论及整个文化。但不少人类学者认为,孩提时代俄狄浦斯情结的化解方式,是成人性心理形成之基础;文明早期血亲关系的化解方式,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性伦理形成之基础。巴尔特甚至提出人类发现俄狄浦斯情结之同时,也发明了叙述艺术。
六
禁欲本是东西许多宗教实践的中心环节,自我克制清心寡欲,也是许多宗教思想的核心。为此,基督教承认信徒有色情想象犯禁的可能,甚至有此权利,只是事后须忏悔。儒家伦理一方面很人道,承认食色性也,对性活动加以规范,却从未重视色情想象与色情表现问题,似乎中国人无此问题。
于是中国人的色情想象与表现换成扭转的形式。
在中国通俗小说中,大部分英雄人物不近女色。性要求低(不是克制能力强)不仅是英雄本色而且是成功之原因。只有反面人物才落入女色陷阱,例如曹操败于张绣,西门庆死于非命。甚至有色情意味的政治笑话,例如曹操下江东乃为取二乔之类,也必落在反面人物头上。这种“坏人性专利”,被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全套继承。《子夜》中只有一个女共产党员突然有了性要求,我们发现其原因是她那时已变成“托派取消派”。
文学作品中,色情载体(具有色情想象,甚至付诸实行的人)都必须“边缘化”。
著名的淫猥小说《金虏海陵王荒淫》,有文学史家说是宋人所作,根据是因为有国仇,故“虏中书”,“骚挞子”骂不绝口。但就此断定为宋人所著,似为武断,酣畅淋漓地写异族之禽兽行,加以咒骂,既过瘾,又有安全距离。
《新儿女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等“坏人带黄”的革命小说,是50年代少年的政治教科书,兼性启蒙读物。坏人才能做色情载体,而色情教师须是异己者,无法让人认同的人物。不然学的时候让人无法心安理得。这种可笑的虚伪可能各民族皆有(例如《旧约》中对淫乱坏人的指责可能是几千年来西方少年的性“自学教材”),但中国文学更甚。
七
说文化对色情表现唯一要做的事是禁限,未免太简单了一些.没有一个文化能对色情全不禁限,也没有一个能全禁限。每个文化的特殊点表现在禁限什么、容忍什么;执行禁限或容忍的方法;以及不同集团阶层不同容忍度造
成的非均质。
无论哪种文化,在现代都要遇到一些相同的色情控制问题。首先,现代社会是大众传播爆炸的社会。大众传播形成后,以前可以轻易限制色情表现流通范围,在现代社会已不可能,甚至敏感集团,例如青少年,也很难阻挡在流通范围之外。
第二,现代社会是个图像社会,网络传播主要是图像,而图像的直观性,使以前靠文字和绘画难以取得的“色情现实主义”,惊人地容易。
第三,现代社会又是一个闲暇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假期越来越长,正在向工作时间的一半推进,从前只为少数人享受的余暇渐渐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所有这些原因,使过去的各种禁限方式不起作用了,使不少人惊呼“色情泛滥”。用不让接触的方式保持社会一部分人的“心灵纯洁”已经不可能,所以现代社会不得不变更控制方式。
容忍度提高视为不得不为之,“两恶相较取其轻”。旧的禁限方式无济于事,反而引出人心本有之禁限即诱惑悖论取得负效果。采用新的方式,完全可以导引出另一悖论,即越禁造成罪孽感,使人们有距离化需要。西方社会的“色情爆炸”、“性解放”,并没有引起60年代不少人担心或希望出现的社会崩溃局面,自80年代中期起,西方各大城市的色情表演与出版行业急剧衰落,即是第二悖论起作用的结果。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禁限方式越来越趋向界限明确的法律方式,而少采取公众舆论、道德法庭等边际模糊、易于宁紧勿松的方式。
八
上文中已经提到色情禁限的两种社会机制。
一种机制是体制式,它以法律为标准,强制施行。因为惩罚方式严厉缺少灵活度,所以禁的内容很有限,以保证立法的有效施行,不至于弄成法不责众。
另一种机制是舆论式,它以情理为标准,其施行可能具有灵活度,其控制面松而广。它很可能超越应有的限度,造成过分的人身伤害(例如霍桑《红字》中的故事)。一般说来,由于其惩罚似乎很轻,所以往往滥用。
两种机制,其道德标准是同一的,只是方式不同。体制式(法律式)往往只能处理明确的犯禁,不太可能过多地进入个人生活。而舆论禁限,其执行者与被惩对象可以是社会的每一个人,而且可以进入人的内心,使人对完全属于个人隐私的犯禁产生自惩的念头。舆论禁限是一张无形的网,罩住每个人的网。
任何社会都同时使用这两种禁限机制,偏重不同,却可造成极大的差别。上面我们已提到过现代社会共同趋向是渐渐偏重体制法律式,以给社会成员较大的个人生活方式选择余地。
九
任何文化,不可能绝对均质,不可能对社会每个成员使用同样的规范,施加同样的道德要求。
大部分社会有一个控制文化诠释规范的“意义上层”(meaningélite),有控制政治力量的“权力上层”(powerélite),许多社会有控制经济活动的“经济上层”(moneyélite),这三者可以互相渗透互相叠合一部分。例如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大夫阶层,既是意义上层,又是权力上层;在政教合一国家中,教会作为意义上层与权力上层重合;在经济国有化社会中,权力上层亦即经济上层。可是在大部分现代社会中,三者职司不同,成员叠合相兼不多。
而不管何种情况,社会大部分成员,在文化上接受现成的诠释规范,在政治上被控制,在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
不同社会集团、阶层,对文化规范的尊崇态度异中有同,其共有的部分是一个文化的基础。一般说来,意义上层与一个文化的规范价值之认同几乎是绝对的,这个集团必须控制规范的解释,并作出对规范的适应性调整。对权力上层与经济上层,尊崇规范的压力也比对社会其他部分大。虽然相对于意义上层来说,比较松一些。只有这些上层的违禁,才构成“丑闻”。丑闻具有新闻价值,就证明是例外。
中国历史上几个著名的道德家皇帝,其严厉诏令主要针对意义与权力上层,即士大夫官吏。朱元璋洪武二十二年著名的“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者卸脚”酷令,是针对“在京军官军人”,不是针对小民的。玄烨登基不久,康熙二年即发禁令“嗣后如有私刻琐语淫词,有乖风化者,内而科道,外而督抚,访实何书系何人编造,指名题参,交与该部议罪”,既是“题参”、“部议”处理,当非小民。
十
并不是说中国传统社会中对社会下层并没有施加禁限,只是禁限方法不同,宽严程度不同。区分君子与小人,是儒家伦理哲学的最基本环节之一。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说明了道德的社会分层的施行机制。
关于这点,二程很有理解。
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圣人不使知之耶?是民自不可知也?曰:圣人非不欲民知之也,盖圣人设教,非不欲家喻户晓,比屋皆可封也,盖圣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尽知之?是圣人不能。
把孔子说成是“愚民政策”的始作俑者,恐怕把文化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汉儒写定的五本仪礼书,是社会上层的行为规定。试问《礼记》这段规定如何施行于小民之家?
“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
“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
社会上层,尤其是意义上层,权力上层,众目睽睽,众言纷纷,这些阶层想维持其控制权力,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道德辩护,而这规范必须是整个社会普遍接受的规范。
至于社会下层,尤其是政权和主流文化难以触及的下层,不得不找行为根据时,也必须求诸这套仪礼规范,能变通时就变通。这些变通对于整个文化秩序并不起根本性的威胁,因为下层并不试图设立独立的规范。欲有所依时,必求于礼,上层社会必须有所依据的场合多一些。沈从文《萧萧》写下层童养媳通奸,若惩办则有所据,不惩办则无所据,无所据谓之变通。变通是社会下层享受的特权。“这事既经说明白,照乡下规矩倒又像不怎么要紧,只等待处分,大家反而释然了。”
上紧下松、下层变通,实际上并不是对下层人民“宽大”,而是一种文化规范得以维持有效的必要方式。文化规范只有靠示范,才能维持其有效性;只有靠适当变通,才能延展铺盖到整个社会,为“全社会”认同。
十一
上紧下松,在性与色情问题上,与其他道德问题上一样,也是由于上层的活动更具有公开性,使原可属于个人问题的事变成公众“性”。“万恶之首,实唯邪淫,况居高位,式化匪轻。”
下层在禁限上较为松弛,变通较多,可以形成一种“亚文化”色彩。亚文化是在主流文化之外局部超越禁限的意义活动集合。这种活动即使发展成很大规模,也不至于影响主流文化,因为它并没有规范依据。相反,允许下层适度违规犯禁反而是规范体系得以维持的安全阀。
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九记录他读到《金瓶梅》,是文学史上有名的第一次主流文人记及此书,下面还有一段:
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之者,非人之力所能清除。
这是明末一部分士大夫对亚文化文本所达到的高度理解。对亚文化表现不禁不崇,即允许存在,却不允许成为规范,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般方式。
关于文化的分层控制机制,很多学者都搞不清楚。范文澜的力作《中国通史简编》,从历代正史稗史上拣出无数例子,证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之荒淫无耻”。殊不知这种记载本身,就证明规范在上层一般说来尚在遵行。
江晓原先生近年出版观点大胆的著作《性在古代中国—— 一种文化现象的探索》,此书辟有专章,题为“上层社会一贯置礼教于不顾”。材料自然很丰富,史籍中此类记载数量极大,只需重抄旧书而已。奇怪的是,江晓原似乎明白这标题之无稽。他在某一处说:“防淫的需求一开始就只是针对贵族提出的,因为只有贵族们的淫乱才有可能危及封建社会秩序。”“男女大防之礼教对下层群众没有多少束缚作用。”(第141页)
江晓原的两个声明互相矛盾,而且都绝对化了。中国上层社会并非“一贯”置礼教于不顾,礼教对下层社会也并非“没有多少束缚作用”。不然传统中国社会将不成其一个文明社会。但是,一旦这个禁限紧宽颠倒过来,这个社会就有点问题了。中国当官多情妇,百姓反而谨守道德,这个社会在伦理上就不正常。
十二
于是我们碰到了本文将讨论的关键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把传统中国称为“礼教社会”。
一般的看法是:宋以后理学兴起,礼教窒息了中国社会。
理学没有新创一套礼教,理学只是给儒家礼教一套新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辩护,它实际上是一种原教旨主义,使儒家控制力量下移,尊崇礼教的范围渐渐扩大。
在作详细讨论之前,我们可以指出两个相关现象。一是理学重新确立孟子学派的优势。孟子学派与荀子学派的对比,很有点类似新教与天主教的对比。天主教仪式要求严格,牧师不准结婚,对离婚、堕胎等不予变通。这样一来,天主教民族(南欧、南美等)反而性关系最松宽。新教讲变通,重心诚,减仪式,牧师可结婚,近来英国让女性成为牧师。但新教民族(西欧北欧、美国东部)却是西方性关系较严谨的国家。原因上面已经说过:体制禁限,似严实松;道德禁限,似松实严。
孟子多次谈到男女之大防,但注重的是道德禁限。著名的《梁惠王篇》,对梁惠王的劝诫,是“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与淳于髡的辩论,孟子强调“权”(权变)与“礼”的关系。孟子强调的是修身养性,而不是外加的束缚。
与之相反,荀子对礼教的要求是外加的、规范的,“风俗之美,男女自不娶于涂”(《正论》),“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乐论》)。
在南宋之前,荀子的地位一直高于孟子,一直到朱熹定四书,才把《孟子》提到经典地位,孟子才成为“亚圣”,荀子的影响才渐渐式微。而这过程——从体制禁限转向道德禁限——与中国社会礼教控制之严格化正好相合。
十三
如何解释这个悖论?荀子之严,是针对社会上层的(“君子”),借控制上层来规范整个社会。孟子之宽,实际上是把下层的变通纳入规范范围。荀子基于人性恶,偏向体制式禁限;孟子基于人性善,偏向舆论式(包括人本身的良知)禁限。这就是为什么孟子学说正好适应了宋明后全社会礼教化的需要。
第二个可注意的问题,是理学兴起,正与中国俗文学兴起的过程重合。以变通为特权的亚文化,一直是没有书面文本的,做固然要有依据,“写”更得有依据,必须更履从规范,才能为俗文学争得立足点。这样,亚文化意义活动进入书面,反而减少了亚文化变通的自由度。俗文学的兴起,加速了礼教规范下延的速度。早期俗文学(平话、讲史、杂剧、南曲等)中对礼教之严格尊崇处处可见。
俗文学,实际上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礼教国家的强大动力。用“小人”的口语,来陈述儒家礼仪教义。现在草根村社民不仅可以“使由之”,而且可以“使知之”。
宋时理学大兴,俗文学未成势头,没有看到这情况,所以二程坚持“圣人不能”,无法作全民教育;周敦颐“文以载道”之论并不包括俗文学。要等到朱元璋用政治力量,高则诚用《琵琶记》的词曲,理学家们才看到他们点起的儒学原教旨主义,正朝社会下层烧一片燎原。
十四
说宋代礼教下移尚是不自觉的,而且被元朝一百年的异族统治基本打断,从社会下层造反起家的明朝廷,就以明确而直接的政权干预来推行礼教下移。明初颁定政策:孝子、贤孙、节妇、烈女等褒奖,只给布衣百姓家,不给有功名的士子官吏及其家属,士大夫奉行礼教是教礼本意,布衣百姓才需教化。
这种政策不久就造成中国历史上空前数量的烈女。民间苦行节烈以求褒奖的热情过于强烈,使官方不得不改动政策,把审批过程复杂化,尽量使求褒奖糜时糜资。福建莆田县志载某布衣捐尽家财,奋斗三年,终于为长期守寡之母争得节烈褒奖,得礼部准许在莆田镇闹市为母树立牌坊。“莆田百姓争相效尤,地方风气得以一变”。又泉州志载,某布衣奋斗三十一年为其母争褒奖,以致双目失明。求褒奖的男人用尽心力财力,以此为毕生奋斗目标,被褒奖的女人玩出各种花样地守节竞争,甚至为未过门的丈夫自杀殉节。1460年(天顺四年)的《大明一统志》“节烈”栏大部分还只是终身守寡者与抗强奸被杀者,明中叶之后各地方志的节烈栏就开始惨不忍睹。待到下层妇女如此热狂地追求礼教的精神满足,这个社会的性禁限控制方式就起了质的变化。如果说“礼教吃人”,吃上层是应该的,维护礼教是上层的责任,这本是文化游戏规则的一部分;吃到下层,就搞错了对象,因为下层并无意义权力,并无破坏礼教规则的可能,原本应享受变通。一旦礼教主要用来拘束社会下层,这个社会就病态了。
允许亚文化变通到何种地步,是需要斟酌的事,但亚文化变通是任何意识形态维持长期有效的条件。下层宽松能督励上层洁身自好。一旦“六亿神州尽舜尧”,原本该做尧舜的人就不想再做君子,因为太俗了。
十五
礼教下延必然使礼教虚伪化,过去是上层,尤其本是士大夫特权的风教,变得俗不可耐。礼教“全面覆盖”使意识形态遭受过大张力反使应负维持礼教责任的意义上层产生反礼教精神,意义上层与权力上层开始分化。从李贽到袁枚,从冯梦龙到李渔,从《金瓶梅》作者到《肉蒲团》作者。整个17世纪,士大夫阶层成批出现礼教叛逆。原先属于亚文化变动范围的色情,在上层文化中得到令人瞩目的表现。
应当说,这不是一件坏事。当意义上层开始重新思考礼教的意义,当士大夫阶层中出现了反文化潮流,试图重新估价对包括性和色情的诠释标准时,这个文化就开始出现了转型的希望。这时,色情表现的意义超越了本身,成为质疑社会规范的手段。乡村烈女节妇骤增,与书坊淫书春画骤增这两个相反的趋势,是晚明中国文化急剧变化的两个互为因果的征兆。
可惜,这个过程被过于迅速发展的政权法统变化所打断。晚明农民军过于急促地摧毁了正在解体过程中的政权结构,却无法重建社会秩序。清人入关填补了权力空白,立即着手重建中国传统意识形态,非但没有改造之,反而由于为了给外族统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而变本加厉地推行礼教。这个努力到康熙朝已完全奏效,意义上层与权力上层重新复合,一度“泛滥”的色情文学不仅创作完全消失,其流通也渐渐被控制。
而且,清人承继了明代礼教下延的成果,并继续加强这趋势,终于在17世纪中叶成功地把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道德规范控制上下相当均质的“礼教社会”。
如果在明代尚有意义上层之反叛,整个社会对礼教下延运动缺乏共识,那么在清代,意义上层的反叛完全消失。这种万马齐喑的道德一统,仅一百多年,到19世纪,就使中国传统文化筋疲力尽,生硬僵化,不得不靠外来力量“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