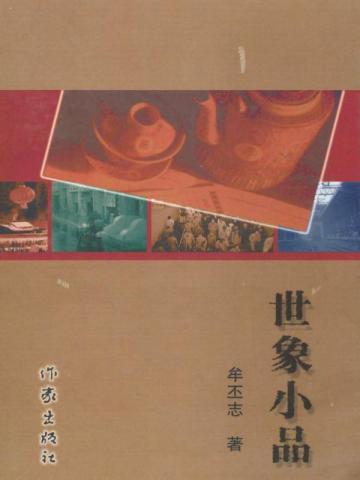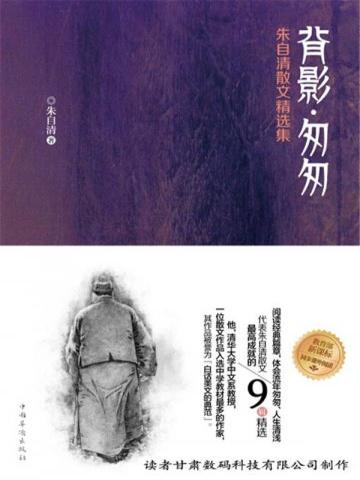第一节1910年前美国诗歌中的中国
1.两种不同的中国兴趣
19世纪中叶之前,美国诗坛对中国的兴趣大都是应和西欧,是回声之更遥远的回声。文献中有一些零星散乱的提及,甚至有一些中国题材诗歌,很难说构成了一种文学现象。比较文学工作者对此只能做一些搜奇探幽的工作。
当时中国和美国直接交往几等于零。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事(1851-1864)与美国的南北战争(1861-1865)几乎重叠。两个民族都忙于内争而无暇他顾,刚半开启的窗户被冷落。
另一个原因更重要:真正的美国民族文学,在此时很难说已经成熟。要到19世纪下半期,惠特曼和狄金森才开启了真正的美国诗风,马克·吐温等人才开拓了真正的美国小说。在那之前,美国文学只是欧洲文学的一个卫星,一个不情愿脱离母体的抛出物,而美国文人似乎也满足于文化殖民地地位,即使标志着美国文化开始成熟的新英格兰人文主义(霍桑、梭罗、爱默生),也只是欧洲思想逸出的旁枝。19世纪末之前美国文学各种体裁,提到中国,多半也是学舌欧洲。
这两个文化要正面直接碰撞,才有可能产生更切实的文学影响。
第一次亲密接触,以相当奇特的方式出现:19世纪中期,美国中西部开拓热潮,大中西铁路和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加上突发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而中国内战迫使南方沿海诸省居民大量外迁,中国移民浪潮卷入美国,使基本欧裔的美国人突然面对一个全新的文化现实。
从这个时期开始,美国文化人才开始直接注视中国。某些英国人所著关于中国的书开始成为文化圈中的热门读物。而美国诗人也开始“翻译”中国诗。最早有卡鲁斯(Paul Carus)和斯托达德(Richard Henry Stoddard)的译本。他们的“翻译”大都是法德两国汉学家译文的转译,很难说有多少中国味保留下来。当时欧洲译者倾向于把中国诗译出色彩浓艳的异国浪漫情调,让“文化贫乏”的美国人惊喜。
与之正相反的是,当时进入美国西部并渐渐向中部东部迁移的中国劳工移民,却让美国人觉得“色彩灰暗”:诚实,勤劳,狡黠,迷信,他们带来妓院和鸦片馆,怪异的“唐人街”文化。
因此,这时期的中国题材诗,几乎被撕成互不相关的两半:一半是“现实主义”的,以中国移民为题材,大量刊印于当时涌现的地方报刊,多半是拿中国人开心的所谓幽默作品,也有侮辱移民的种族主义打油诗,成为当时美国俗文学一个特殊景观。另一半则是抽象的,书上读来的中国,用绮丽文字写入华美诗章,作者多半是“主流文人”,理想主义自由主义色彩比较浓。
悖论的是,前一种“俗诗”,粗鲁,劣陋,鄙俗,充满“草根层”偏见,却是真正的美国本土文学,可称为“现实主义”;后一种是知识分子的诗,精雅但无生气,是欧洲传统的呼应。
有相当多的研究者,以是否“反华人”作为诗的价值判断标准,就是自找难题做了。
要等到20世纪初“诗歌文艺复兴运动”,美国诗歌主流拥抱东方诗学时,才开出一个新局面。
2.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74)
19世纪文坛领袖之一霍尔姆斯,他的一首诗至今常被人引用。1868年美国传教士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带领第一个中国使团游历西方,两个中国官员蟒袍红顶,带了30名随从,第一次出现于西方官式宴席,轰动可想而知。霍尔姆斯特别擅长命题作诗应酬。1868年8月他在为使团举行的宴会上朗诵诗。
霍尔姆斯的这首诗格调传统,押韵守律,但字顺句畅读来朗朗上口。其主题是两大民族理想主义式的拥抱——互相开门:
大开吧,你,黄金的门,
向那卷起来的龙旗!
宏伟长城的建造者,
开启你们的高山防线!
让太阳的腰带
把东西方裹成一体。
直到夏斯塔山的轻风
吹动大雪山皎白的峰巅——
直到伊利湖。把蓝色的水
融汇入洞庭湖的波澜——
直到深邃的密苏里湖
把水灌入奔腾的黄河——
第一段诗化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第二段颇有一些“殖民输出”的味道,可能是霍尔姆斯只是个诗人,或可原谅。但下面这两行名句,还是相当真诚的:
我们,夜晚的最后出生者
欢迎你们,曙光的孩子!
可能是为了押韵,谦词有点过分。不过,他把欧洲文明称作夜晚,把美国这欧洲文明的最后产物称为“夜晚的最后出生者”(the evening's latest born),而称中国人为“曙光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the morn),不仅诗句漂亮,而且识见过人。
这两行诗,表明的“地理文化”意识,却是此后一个半世纪的绝妙预言,而且透露了美国与欧洲传统(“夜晚”)久合欲分的模糊愿望。
3.朗费罗(Henry Wadworth Longfellow,1807-1882)
19世纪最受读者欢迎的美国诗人是朗费罗。朗费罗擅长叙事长诗,几部名作至今脍炙人口,是美国文学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
朗费罗有好几首中国题材诗。他的诗集《各地方之诗》(Poems of Places)有一组专门写中国。其中第一首《罕巴鲁》(Kambalu,1864)写的是蒙古军队征服中亚,很难说与中国有什么关系;第二篇《人民的声音》(Vox populi,1870)其中国背景几乎没有仔细构筑,只是借用西欧关于神州(Cathay)的种种浪漫传说。
第三篇《瓷器》(China Ware,1877),写的是景德镇,其中很难说有多少故事情节,却把制瓷器的工艺过程描写得很仔细。另一首关于中国的诗《瓷塔》(The Porcelain Tower)写的据说是南京的一个著名景色,下文将谈到。这两首诗原是长诗《卡拉莫斯》(Karamos)的一部分,朗费罗自己很喜欢,因此重印在《各地方之诗》之中。
4.斯托达德(Richard Henry Stoddard,1825-1903)
朗费罗对中国题材兴趣强烈,他竟然在自己的诗集中重印了另一个诗人斯托达德的十首“译中国诗”。上文已说过此人是美国首先介绍中国诗的翻译者之一,但他的翻译几近再创作。他的“原文”大都是西方汉学家翻译中国经典的散文,有的来源更奇特,例如《好逑传》中的《以诗为证》。写中国这样遥远陌生的国家,他有权学术上不严密。
斯托达德关于中国的作品之多,可以说是19世纪美国诗人之最。1851年出版的《诗集》(Poems)中有《汉浦》(Kam Pou),《露露》(Lu Lu)等诗;1857年的《夏日之歌》(Songs of Summer)中有《马汉山小夜曲》(Serenade of Ma HanShan);1871年他出版了诗集《东方书》(The Book of the East);1876年出版的《美国的客人》一书中有专门一章诗写“中国来客”。1880年版《诗集》(Poems)则换了一个方式写中国题材。《他看到自己的家》(He Saw in Sight of His House)和《大师,我们能否》(Shall We,O Master),显然都是理雅各所译《论语》的某些章节写成诗,读来很有趣。
他的一部分“翻译诗”,用的是三音步抑扬括体,四行一节隔行押韵,颇为勉强;另一部分“译诗”用的是素体诗(blank verse),就较为流畅,自由,没有过分刻意的涂抹,保存了一部分中国古典诗的清淡风味。
斯托达德的诗歌成就不高,若不是朗费罗倾全力推荐,他很可能被文学史忘却。在当时纽约文学圈中,他却是一位大名人,主要是由于他的评论与编辑工作,以及他家的文学沙龙(其妻是当时著名的小说家)。作为活动家,他对中国的兴趣渐渐感染了美国文学圈子。
5.政论诗
在19世纪的西方,诗常被用作时评政论。“诗歌议政”(不是鼓动)是一种并不顺手的政治宣传方式,但19世纪诗歌读者的“阅读期盼”,与20世纪读者很不相同。政论性诗作,被看成是很严肃的写作方式。
政论诗歌涉及中美关系的,在19世纪的美国数量还相当多,大部分不值得在这里讨论了。我们要指出的只是诗人一般比较倾向于理想主义,因此对帝国主义行径大多持激烈反对的态度。上世纪有些文名的诗人尤金·费尔德(Eugene Field)写中法战争的诗《法国佬滚回去》(The French Must Go)作于1883年,是19世纪少见的谴责帝国主义的作品。这位诗人对中国所知极少,诗中的中国士兵都以洗衣为业,中国军官爱开鼠肉宴,但诗对中国军队大捷作了狂欢节式的描写。
美国对列强侵华,似乎置身事外,可以指指点点。19世纪末美国最重要诗人威廉·伏恩·慕迪(William Vaughn Moody,1869-1910)的《猎物》(The Quarry)一诗,指责列强,支持麦金利总统宣布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个政策一方面是美国要求在列强所强取的特权中分一杯羹,另一方面也向企图独占中国的欧洲国家提出了阻吓。慕迪显然把“门户开放”看得太理想化了。
另一位诗人罗依德·米夫林(Lloyd Mifflin)的十四行诗《1900年之征服》(Conquest-1900)批评英国想沦中国为殖民地,也批评了美国也手脚不干净,参加掠夺。慕迪和米夫林的诗是针对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事件而作。义和团事件及东交民巷之围攻,给了美国(及西方其他国家)文人一个发挥想象的好机会。一时中国题材大行其道,指责中国暴民,赞扬东交民巷守卫者之英勇之类的诗比比皆是。在这个背景上,慕迪和米夫林的作品难能可贵。
6.哈特(Bret Hart,1836-1902)的《阿新》
中国劳工潮进入美国,美国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增加引起反华浪潮,美国政府最后颁布遏止中国人进入美国的《排华法案》。美国诗歌中,对华人劳工的态度问题,也有所表现。
当时大量出现的侮辱华人的打油诗,本来就毫无文学价值,现在不值得一提,并不完全是因为对华人的种族主义态度。
某些侮辱华人劳工的诗,采用中西部民歌的叙事风格,不能说没有西部式的幽默。有一首称作《高个儿约翰·中国佬》,说一个在犹他州筑铁路的中国劳工,带了辛苦钱远道回旧金山去看他的中国姑娘,却在半路上被印第安人劫杀,剥去了头皮。他还站着,但当他发现自己辫子也丢了,才吓死倒下。
仇华浪潮受到自由派文人的愤怒指责,马克·吐温,乔昆·米勒(Jouquin Miller),安勃鲁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等著名文化人,都有作品参与到这场争论中来。反华工的小报常用打油诗作讽嘲甚至谩骂,自由派文人有时也用诗参加辩论,例如比尔斯就写了一些诗,直接攻击社会党政客用华工问题骗取选票,甚至不惜煽动反华工浪潮。
以“自由派”、“反华工派”之类的标签来审视诗歌,总不免要出错的。真正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往往很难用“态度”分类,哪怕19世纪也是如此。
一个佳例是布勒特·哈特。哈特以其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与马克·吐温共同创造了现代美国小说。但哈特与吐温一样极为多产,各种文体都写。哈特在加州过了一段经历奇特的生活后,成为旧金山《远地月刊》(Overland Monthly)主编,在上面发表了一系列使他成为名作家的西部短篇小说。1870年他忽又转向写幽默诗,其中最早的一首,也是最有名的一首《异教徒中国佬》(The Heathen Chinee,1870年),使哈特突然全国闻名。
此诗最早发表于1870年,其诗行式节奏,戏仿盛名一时的英国诗人斯温朋(Algernon Charles Swinbume,1837-1909)节奏铿锵的名诗《卡里东的阿特兰达》(Atlanta in Calydon)。全诗不长,主人公是西部流浪冒险者詹姆士和比尔·奈依,这二人打牌赌钱,三缺一,拉中国工人阿新。凑一桌。阿新“脸上堆满孩童般的笑容”,说他不会打这种牌,被强拉入局。惯赌比尔·奈依袖里暗藏了王牌,不料阿新手中王牌比他还多。自然,两个白人全输了:
然后我抬头看奈依,
而他两眼朝我发怔。
他站起来,叹一口气,
说道:“这难道是真?
中国下贱工人毁了我们。”——
于是他扑向异教徒中国佬。
此后发生的各种事件
我袖手旁观决不参与。
整个地板飞落纸牌,
像河滨满地是树叶——
都是阿新藏起来的牌
来玩这“他不会的游戏”。
阿新的中国衣服袖子长,藏牌多;指甲长,手法灵活。由此可证明:
各种阴险古怪的方式,
各种愚蠢的把戏诡计,
异教徒中国佬真是特别。
哈特这首诗情节幽默,语言流畅俏皮,刊出来后人人诵读。据说当时全美国很少有杂志没有引用或重印过这首诗,或对之作俏皮评论,哈特名声甚至传遍英国。1871年1月7日出版的《纽约环球》(New York Globe)说,“本刊应广大读者强烈要求,不得不再次刊印此诗。”在19世纪,幽默诗之广受欢迎,可与现在的大众歌曲媲美。
哈特的“忠实的詹姆士”幽默诗系列以阿新开场之后,题材就转开去。他后来写的诗中,中国人形象再次出现于《最近的异教徒暴乱》(The Latest Heathen Outrage)和《天使岛上的自铸银币》(The Free Silver of Angel's)等诗中。后一首诗中阿新重新出现,当他听说这些银币是“free”(自铸,白拿),就囊括一空。鬼机灵阿新的形象最后于1877年集大成于哈特与吐温合写的剧本《阿新》之中。
关于哈特的“阿新”作品,至今文学史家争论不休,尤其是近年亚美文学批评兴起,对哈特的批评就比以前更严厉了。哈特的诗一出,群起效尤,大多沦为嘲弄华工的打油诗。实际上哈特本人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他的其他作品也证明他并没有种族歧视的意图。他笔下的阿新自然不是道德完人,只不过比狡猾的西部白人冒险家们更狡狯一筹,哈特的轻松的揶揄甚至可视为嘉许。
上引诗中美国赌徒奈依的咆哮“中国下贱工人毁了我们”,是照录当时加州社会党排华政客的煽动口号“中国廉价劳力毁了我们”,“下贱工人”(cheap labor),与“廉价劳力”英文相同,明显在讽刺社会党政客。
7.欧文(Wallace lrwin,1875-1959)的《唐人街谣曲》
唐人街作为华人聚居区,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半中半西的文化群体。而唐人街本身也在美国文学中形成一个特殊题材。下文将谈到这个题材在美国文学中——在诗歌、小说、戏剧和电影中——绵延流长,延续至今而不衰。
最早集中写唐人街题材的诗人可能是华莱士·欧文。此人于1896年至1903年就读于旧金山之南的斯坦福大学,后在旧金山新闻界工作。1906年出版诗集《唐人街谣曲》(Chinatown Ballads)。他笔下的唐人街充满堂会械斗、妓院鸦窟、戏院庙宇,确是多色多彩。
此集共七首长叙事诗,韵律熟练甚至流于油滑,全书有不少词故意拼成中国人的误读式(如yeller=yellow,is=his等),但读来依然顺畅,是典型的轻松读物。
这些诗的故事,据作者说是很“现实”的。例如其中的中国义仆故事,读来非常老套,但欧文说是他亲历的真事:他们全家先是看不起这个中国劳工,但在1906年几乎毁灭了整个旧金山的大地震中,是这个中国仆人救出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其他诗比较凄惨。《叶和》(Yut Ho,译音)一诗写一个中国三邑(Sam Yup)老板关某,在番摊上赌光了家产,自杀身亡,留下母女二人。母亲为借钱葬夫,把女儿叶和卖给奴隶贩子。叶和听闻此事,潜逃至一基督教堂避难,在里面躲了两年。后有一白人理发师向教堂提出娶此女,教堂审核认为合格,符合教堂的全部要求,就让他带走此女。不料这白人是奴隶贩子的帮凶。叶和被绑走,关入一鸦片馆待售。最后她自杀,其鬼魂使唐人街夜夜不安。
另一首诗《严少爷》(Young Mr.Yan),其表现的中国人性格比较复杂一些。严少爷是唐人街新一代年轻人,读的是教会学院,穿的是西服,吃的是面包,早就剪掉了辫子。他的父亲却是老辈“唐人”,开餐馆兼赌场。父亲包办儿子婚姻买了一个媳妇,儿子却不同意,因为他爱一个摩登女郎。一天父亲在堂会冲突中被暗杀,儿子不愿报仇,因为他已是基督徒,要原谅仇人。实际上他只是麻痹仇家,暗等时机。最后他“按中国规矩”杀了仇家,从唐人街消失。不管信什么教,中国人还是中国人。
这几首早期诗,故事比许多后来的唐人街小说更加凄婉,更加精彩。
8.利兰(Charles Godfred Leland,1824-1903)的《洋泾浜小调》
19世纪中国题材幽默诗中,有很大一类,用一种特殊的中国式英语写成,称为Pidgin English,中文译作“洋泾浜英语”。
洋泾浜英语诗作者很多,大都是业余投稿写些幽默小诗,以博一笑。19世纪70年代初起这种诗大量冒出来,甚至“专业”的洋泾浜诗人也出现了,利兰是其中最著名者。他出版于1876年的诗集《洋泾浜英语小调》(Pidgin English Sing Song)。此书自称为给美国商人和旅行者提供语言学的方便,书后附有详尽的“洋泾浜词典”,因此利兰被语言学界公认为这种特殊方言的专家。
该诗集实际上是用幽默语调写的远东风俗指南,而且每首诗后有一个叫作阿中(Ah Chung)的人物从中国人的观点评介这些故事。自然,中西善恶标准不同。其中一首诗写一西方商人给一个中国人一把放大镜,使他能在指甲上写小字夹带作弊,此人中举做官后给此西人大笔承包合同;另一首写一中国人到伦敦,伪装成中国官员,以中国戏单顶替官书文件,伦敦社交界为之倾倒。
此书中尚有不少纯中国题材,诸如“昭君思汉”,“孔子遇老子”之类,一旦用洋泾浜英语写出,再严肃的题材也流于滑稽可笑。下面这一段,从利兰的书引出,以给读者一个洋泾浜诗的样本。
My flin,supposey you hab leed he book of kungfoutsze,
You larn that allo gleatest man he most polite man be,
An on politepidgin Chinese beat allo,up on down-
This is he molalpidgin of he song of Captan Blown.
我的朋友,假如你读过孔夫子的书,
你就明白他是伟人中最有礼貌的人,
用文雅的洋泾浜中文诗,抑扬顿挫,
他给布朗船长唱出洋泾浜道理。
我的“翻译”,录于此以俟高明教正。
本书关于19世纪美国诗所受中国影响,就结束于此。读者可以看到这部分之零散,与全书的讨论不甚相称。但不久之后美国诗人就不得不严肃地面对这三千年诗歌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