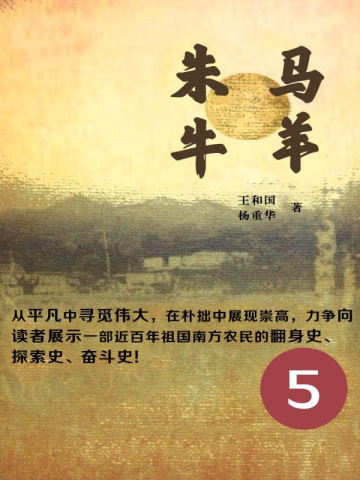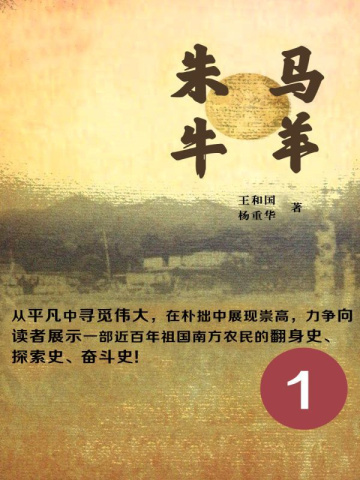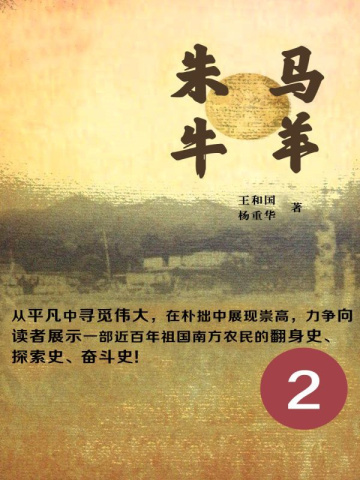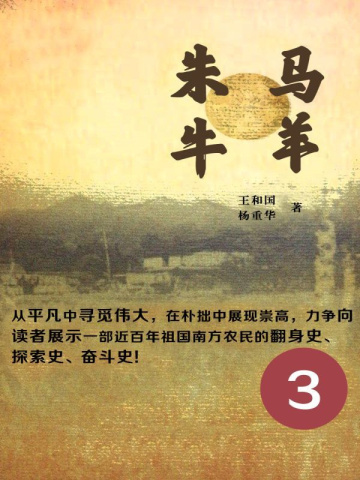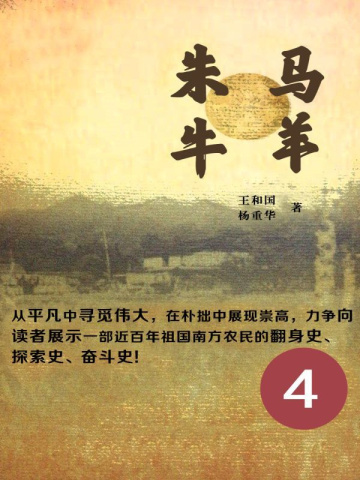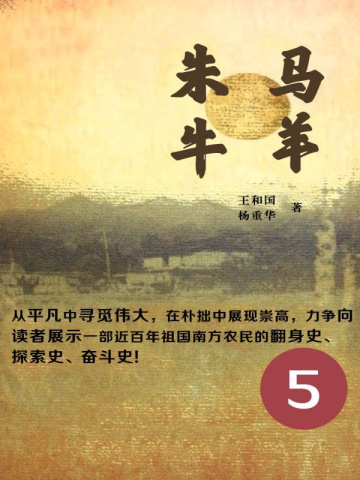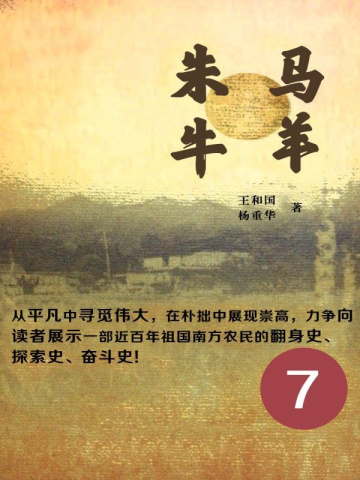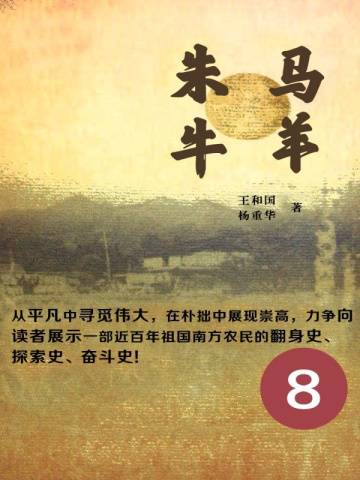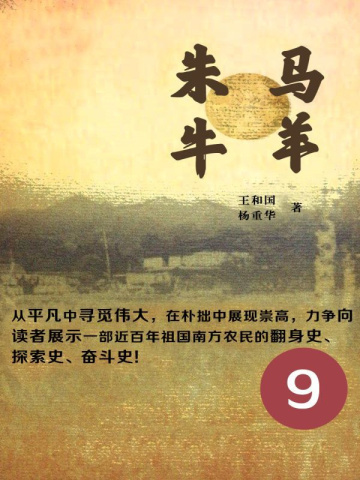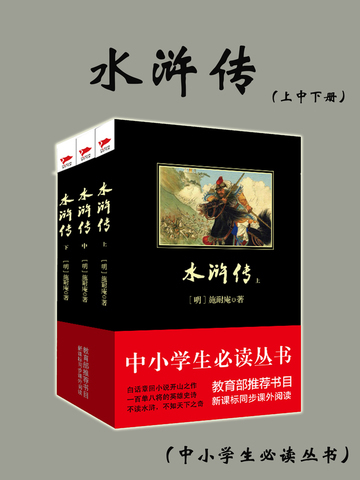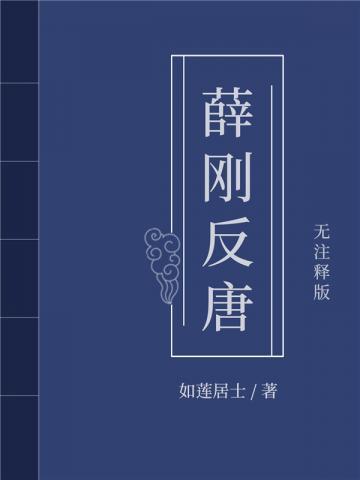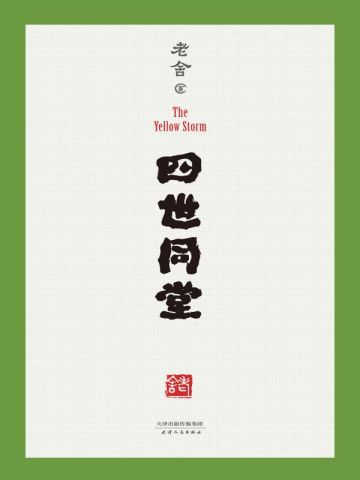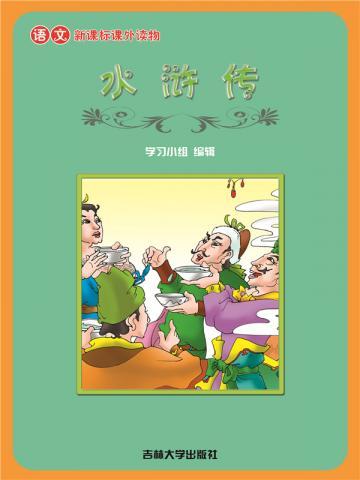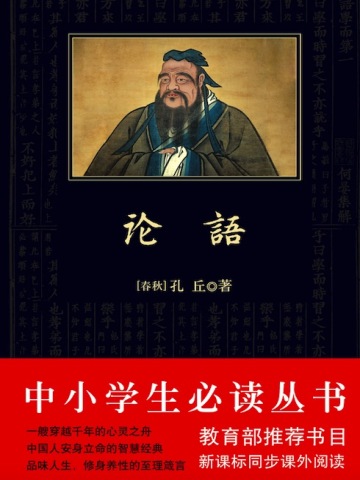进入腊月,家家户户忙着杀年猪,空气里弥漫着燃柏桠熏腊肉的芳香。亲朋好友之间,相互请吃庖汤。满院子都有股猪油香味儿。
工作队撤离的日子一天天近了。真要走,又还舍不得。只要有人当面提起“老梁”, 牛道荣总是眼泪汪汪的:“唉,天天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出工,一起开会,大半年了。一下子说起要走,哪个不心欠欠的嘛。”
工作组有规定:离开之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也不准接受群众吃请!特别强调:“坚决不准吃转转儿会”。
突然不开会了,人们一下子觉得闲来很无聊。羊登山而今一个人住牛家大院,三顿饭回羊子沟老屋场去吃。这些天老下雨,稀泥烂坎,田野不见一人,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讥诮调侃,阴阳怪气地说:“这老天爷和人一样,也有气血虚的时候啊。”
院子里年轻人听了,多不知所云,问他,啥意思?他幽幽地补一句:“月经不调嘛。”
恰好“舅母子”马德春从他面前路过。知道妹夫又在旁敲侧击“烧烤”人,笑眯眯地反唇相讥道:“人家月经不调,咋回事你个大男人,那张嘴巴总难得干净呢?要不要也整块勒胯片儿(月经带)蒙着?”
正坐在堂屋门口的矮子幺爷听了,拍着巴掌笑,幸灾乐祸对羊登山说:“气包卵呢,我给你娃娃说,今天‘门枋枋上头刷面羹儿(糨糊),遭到对子了’。格老子,一物降一物!安逸!来,又来,接着来。”
在葫芦尾河,舅子舅母子和姐夫妹夫之间说笑,只要不伤着姐姐妹妹,随便乱说,玩笑开得野都不会生气,女人挖苦男人可以狠,男人挖苦女人就要注意点分寸了。羊登山听矮子幺爷喊“又来”,随口真还又来了几句押韵的:“矮子心多,瘦狗筋多。遇到气包卵,往一边梭,老子难得和你们说。”快板儿味儿,一炮三响。把自己,矮子幺爷和“干筋瘦壳”的舅母子马德春,都捎带进去了。
家门口,岳父野牦牛也忍不住笑,责骂女婿道:“你日妈一天到晚就没正经过,衣禄话格外多。这回儿运动,你狗日的还没吃够?你认为你就过了关了嗦?工作组还没走,小心涮烦!”
马德春正在找话回击羊登山,听公公搭腔,不好再说什么,右手几根指头做成“磕钻儿”模样,向羊登山敲敲:“小心老娘收拾你。”笑着走开了。
各生产队都已经十多天没喊出工了。田里,土里的农活早就干净了。对乡亲们来说,四清运动最大功劳,是带来一个空前好收成。连最“不管罕事”的朱光恩、朱发富这些人也都突然发觉,眼下集体这点儿农活,大家一齐心,才是“真他妈的莫球得做头。”马德忠说:“说起来这么宽的田地——随便啥子农活,扯起场子,甩开膀子,能干几天?一窝蜂,就搞整完了。还全都平窍落板儿,没得人敢放点儿烂药踩点儿假水!你看今年这收成,哪家哪户不是柜柜箱箱装满,屋头还东堆一堆西堆一堆的?可惜哟,老子屋头苕窖挖慢了,烂他妈好多红苕哟。”
饭桌上,牛道荣忍不住对梁新眉叹道:“你看嘛,农民,好对付得很。下力人啦,都披张‘贱皮子’。平时生产队做点活路,怄死个人!松胯儿呀牛老大呀,嗓子喊哑了,卵子气爆了,莫球得人当回事。现在好了。你们工作组一进村,嗨呀,你看,一个二个沟子(屁股)一下子就夹紧了,没得人喊,没得人催,跑得飞叉叉的!积极得皮爆!平时起码要做一两天的农活,眼下半天保证搞归一,还巴适得很!说去说来,还是工作组狠点儿,镇得住邪!狗日的些,啥子都不怕,就是怕运动。运动一来,工作组一进村,一个二个全都乖完了!”
梁新眉听这老伙计一说话就走火,笑。连忙岔开。尽量用平白的话给他解释:“话不是那样说,还是个群众积极性的问题。生命在于运动啊,这运动期间嘛,大家都当积极分子就对了。不然,这运动怎么运动得起来?”
牛道松点头认可:“那是,运动一下是好呢。要是工作组不做那些搞整人的鸡巴事,就更好了,其实经常运动运动,都要得。愿意。”
吃过饭,牛道耕院子里溜达,恰好听到两人的议论。想起前些日子梁新眉读领袖著作,有句话他至今没搞懂。想问梁新眉,“留到不煮不如喂猪(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啥意思?正要开口,听老梁对牛道荣说“运动期间嘛,大家都当积极分子就对了。不然,这运动怎么运动得起来?”牛道耕若有所悟,这好像还真不是假话。解放这些年,运动一个接一个,追得大家屁滚尿流。你看,即便那些平时偷奸耍滑惯了的人,只要运动一来,不是脱产干部进村,就是工作组下乡。普通百姓都怕把自己整来“笼起”,一下子“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大跃进,亩产万斤,稻谷搬家;大炼钢铁,砸锅炼铁。明明是假的搞来耍的,也全都舍死忘生地劳民伤财,清醒白醒地做白日梦,一个个还可以几天几夜不合眼——干劲冲天!这种干劲,如果拿来认认真真做点好事、正经事,就对完了!大跃进搞得凶但不搞整人。而今这个四清运动,就更可怕了,喊醒了,就是专门搞整人的运动!几个月下来,整得鸡飞狗跳,又搞整出来了点儿什么名堂呢?哪有那么多莫桂仁、罗麻壳儿嘛。话说回来,只要齐心,干部带头,集体不是一样能搞好吗?如果集体真能搞好,又哪点儿要不得?哪里一定非要单干不可嘛!眼下的红奎村,如果真的扯开单干,日子不如眼前的,难道只是一户两户?
牛道耕心目中,只要不是坏了良心,喜欢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站在神螺山上放眼看看这葫芦尾河,就不难知道:一家一户单干时候,有多少人能在“寒露”前后把小春作物抢季节全部种下去?那些劳弱户,哪家不是拖到霜降前后?有的甚至拖拢立冬,麦种还没下地。“种在寒露口,一捧收一斗”,话都会说,做起来就力不从心了。宁耍三天也不愿劳累一早晨的“农民”,也不是没有。这两年,自己当大队长,手下几个生产队长,都容不得有人在庄稼活路上作假。惹火了,日娘捣皮一通乱骂,让他龟儿三五几天无脸见人。平心而论,劳弱户和那些庄稼手艺不过火、不靠实,只有点“三脚猫功夫”的人,他们那点农活,看着就让人心焦,挖土猫儿盖屎,刨一条地沟出来,“蛐蟮滚沙”拉不直。这些人家,最典型就是幺弟矮子幺爷一家,他们而今的日子,不比单干时候轻松?吴省长说的人均口粮六百斤,今年分粮分草,工作组全看到了,哪里才六百斤啊。干谷子也不只这个数!小麦豌豆胡豆大豆玉米,特别是红苕,人均千多斤,好些人家根本没地方堆了。牛道耕只认准一条道理:随便你咋整,老百姓有饭吃,有钱花,才是正经!
“集体也好,单干也好,都必须要有人认认真真去做,才有收获。不晓得高头那些当官的,成天球吃多了一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折腾过去,折腾过来,不晓得咋想的!”
晌午时分,公社新社长周也巡来了,带着马礼堂和工作队那个姓洪的“叫兽”,专程来葫芦尾河宣布:牛道耕还是大队长。会只开了不到半小时。周也巡一行还要急急忙忙赶到湾滩大队,宣布雷太平的事情。听梁新眉说,湾滩雷大队长遭降了半格,副大队长主持大队工作。不知内情的认为:“县官不如现管”,只要“主持工作”,“正”的“副”的当球疼?朱光明解释:“外行话吧?大队长工分补贴每月两百分,副大队长一百五。同样的担子、活路没少一点儿,他龟儿子五十分飞了。值不值嘛!”
周社长他们走后,谷栅安排朱光明带几个人,张贴出来几张大白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末尾还盖了个大红公章:
“葫芦底河公社红奎大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划分的阶级成分榜”。
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朱光兵那小学刚毕业的儿子朱正明,前些日子曾帮助牛道耕写交代,此时正好站在大队长旁边,就念给他听。第一,雇农,十二户;第二,贫农,八十八户;第三,下中农,五十二户;第四,中农,八十户;最后,第五,地主,一户——马德齐。牛道耕叫他把“中农”再念一遍。没错,八十户。中农最后一户是朱发丰。倒数第二是户牛道耕。——牛道耕觉得,这还有点儿奇奇怪怪的。自己和岳父朱发丰,家庭成分过去是“上中农”,每次上榜,都和中农隔开的。这次,咋会归到“中农”里去了?
安逸,还要得。感觉赚了。宣布了“还是大队长”,听了“阶级成分榜”,牛道耕全身轻松,和朱光明开玩笑:“如果不搞大四清,我可能当他妈一辈子的大队长,也不晓得我们这红奎大队有二百三十三户人家。有时候,‘运动’一下,还是有他妈点儿益处。”
办完这最后一件事,工作组才真是要走了。
牛道耕觉得,其他人不敢奢望,无论如何该请住在牛家大院的梁新眉喝杯酒吃个饭。无亲无故,千里迢迢,七八个月中,天天和乡亲们一起,风里雨里的,不容易哟。更重要的,这个老梁不拿大,心肠好。牛道耕找牛道荣商量是不是悄悄请,牛道荣的婆娘龚庆碧点拨牛道耕:“大哥你才蠢。他本来就住在我们家,顿顿都是要吃饭的,和他一起吃个饭会犯什么规矩?也不说请不请的话,更不用你来出面,都睁着眼睛盯到的,说得那么严,犯纪律的事,老梁是傻瓜?”她说得有道理。牛道耕说,“那就说好了:我们两家,再加上牛道松,矮子幺爷,四家人,每家整一两个好菜。我家里还有马常山牛天香小两口孝敬的三瓶葫芦特曲。够得喝。”
矮子幺爷说,两瓶就够了,别喝醉。
牛道松说:要得。晚上悄悄地干。
牛道荣编了个理由,对老梁说,晚上牛道耕、矮子幺爷、牛道松,“我们一起吃个便饭”。葫芦河规矩,女人即使贵为奶奶了,人来客往,依然没有资格上桌子。所以,朱光兰、牛羊氏、马德春她们,就免了。
一张八仙桌,五个大男人。无论如何推、劝、哄,还有“盛情难却”一说,梁新眉坚决不坐上席。没办法,主随客便。“牛老大”坐了。刚坐下,老梁立规矩:运动结束,没有工作组老百姓这一说了,我们大家是朋友。所以,运动中的事情,过都过去了,凡是和运动搭界的龙门阵,特别是和工作组相关的龙门阵,今晚就不摆了。不准犯规!除此之外,随便吹。
大家心领神会。也对。要得!
但,总不能都闷起脑壳只喝酒、光夹菜吧?还得找话说呀!“三个先生见面说书,三个屠夫见面说猪。”眼下,几个农民陪一位作家喝酒,不准谈运动,又谈不来文章,就只好谈天气,说地里的庄稼。今年秋冬两季这雨水——来得匀均,来得柔和,先前干泡了的田土,慢慢浸,透了,看样子准能蓄得住水。今冬明春,小春粮食对了。秋雨足,下得透,年尾巴上多会“干(旱)冬”。俗话说,“头干压断仓,尾干断种粮”。明年大春也有望头。于是说到犁田,说到今年的头遍板田——建社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八月完板田犁完了头遍的。牛道耕说:“八月犁田一碗油,九月犁田半碗油,十月犁田光骨头。乡下人都晓得。说去说来,还是要感谢你们,工作组来了,社员觉悟一下子就上去了。来来来喝酒,面前的,先干了。”
牛道松说:“今年搞得快,那肯定是工作组面子大啊。不过,大哥你今年那个建议,也还是有点儿作用。把使牛匠每天的十二分,调高两分,到十四分。对的。犁板田比犁水田,考手艺得多,也费力得多,加点儿分,和做旱地农活比较起来,使牛匠占不到啥子便宜。这规矩兴起了,今后,也要按照这个办法。对的。”
牛道耕说:“你没想想,过去犁板田,哪年不是我和使牛匠羊登贵犁得最多?我加分,不挨日卷才怪。羊登贵而今是军属,觉悟高,争表现,吃亏还说不出符,搭着我倒霉。”
牛道荣说:“今天当着老梁,别说我不给你面子。大哥你那脾气还是要改:你吃得亏,顾集体不自私,大家服你。牛道松他们四个生产队长,还有像我们这些作业组长,像羊登贵这些平头儿百姓,都是老庄稼,农活没做归一,你吼一下,大家从不放心里。其他社员,有些人本来就做不来庄稼,自己那点儿自留地,做来都茅荒草岭的。对这种人,惹毛了,你日娘捣皮乱骂就不对了。其实,老梁在这里,工作组最明白,这回四清,大多数社员,还是护着你的。朱、马、牛、羊,四大姓人,讲良心的,还是多数。好多时候,大哥你犯不着发那么大的火”
牛道耕已经喝得眼睛有点发红,端起酒杯和老梁一碰,径直一仰脖子,干了。“道荣兄弟呀,你说得太对了。为这事,我婆娘几乎天天和我唠叨。我这一辈子,球本事莫得。你们看到的,七八岁就跟着老爷子下水田。种庄稼,啥都见得,就见不得人做‘猫儿盖屎’的活路!我老汉儿屎观音在世,差不多天天都要念那句话:‘人哄地皮,地就要哄人肚皮!’从我掌得稳犁头开始,跟他老人家学犁田:横着一小步,顺着犁三犁,入土五寸厚。少了,薄了,老爷子手里的使牛条子,就打过来了!”
矮子幺爷和牛道荣有同感,想起不久前的事:“你那猫儿疯发了,哪个都劝不住!那天公社罗队长他们来,专门为弄你来下楼,给你好大的面子哟!你在上面,说些啥子嘛。头天晚上,一家人是怎么劝你的?你答应得口死眼闭,上了台子,羊连金一现怪相,你当着那么多人扯横筋。我们硬是为你担心完了!你自己说,这回儿,听说如果不是吴省长发话,你这大队长帽儿,还戴得成啊?”
牛道耕也笑,对老梁说:“那天,天理良心,事先,谷组长和罗组长都找我说了的,叫我顺着说,免得别人生气出难题。我吗,过都过了,也给大家说实话,老梁你别见气,日妈真的是不想当这个鸡巴大队长了。我不稀罕这两百分啊!你们算算嘛,真的,日妈当起球意思莫得。本来就一肚子火,恰恰狗日的羊连金老粪船装怪,老子实在——”
老梁一听他们的话题“违规”了,招呼道:“好好好,不说这个了。喝酒喝酒。”边说话边自己先干了。
好家伙,老梁酒量了得!
听老梁打住话题,矮子幺爷心领神会。笑大哥道:“大哥你就忘了?格老子昨天晚上,才学了自由主义的嘟嘛,领袖说了的,当一天和尚就要念一天经。”
牛道荣听了哈哈大笑,“矮子兄弟,你一天日疯倒颠的。啥子哟,老梁读那文章,明明是说的反对自己煮鱼,当一天和尚就整他妈一条。”
梁新眉忍俊不禁大笑起来。“好好好。不争了不争了。整一条就整一条。我告诉你们——正确的说法,领袖那篇文章,题目是《反对自由主义》,里面有话,意思是干革命就要自觉,要主动。批评有些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就是嘛。怎样?革命搞起来了,你格老子睡下头的,就是要自己脱(自觉),自己动(主动),不然,就是不得行!”矮子幺爷喝得二麻二麻的了,玩笑骚话跟着就来。
牛道耕责备幺弟:“你呀,啥时候能正经点儿,一天到晚骚话多,说不上三句,你就要扯到床上的活路去。亏你还当那么多年村长!”
矮子幺爷酒壮人胆,顶嘴:“嗨呀,我当村长又咋了嘛?我晓得,把你弄成富农了嘛——这未必是我的错哟?那个时候,哪个晓得当他妈个地主、富农要倒这么大的霉哟?实话说,开始评成分那时候,我真还有点儿眼红当地主当富农呢 。以为当地主富农光彩呢。从古至今,哪个舅子不想发财?不想当有钱人?”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梁新眉听矮子幺爷说到地主富农的话题,顿时神情忧郁,仰起头,闭着双眼,自言自语地:“好、好、好,到此为止,到此为止吧——不说这些不说这些——”
牛道耕酒醉心明白。最先发现梁新眉眼眶里噙着泪水,一下子想起他对自己说过,家庭成分不好,运动中很担心哥哥嫂嫂的事,想劝他,又找不到话,也不愿让旁人知道这个话题。于是站起身,端着酒杯,趁着酒兴,说:“老梁啊,好兄弟!什么都不说了。喝了这杯酒,今晚,我们就散了。明天,你一回京城,这辈子也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只想说两句话:第一句是,我谢谢你。”牛道耕也是泪流满面了,边说边向梁新眉弯腰,低头,像是鞠躬。“这第二句话,我老爷子常常挂在嘴边:‘离地三尺有神灵。好人终得好报’。愿你的哥嫂他们,平安。”
牛道耕自己说不下去了,一仰脖子,把杯中酒干了。拉开凳子,有点儿摇晃。定了定神,高一脚低一步地,走了。
矮子幺爷跟了出来:“大哥,你慢点儿。小心——”
工作组离开之前最后一次社员大会上,责成牛道耕带头,大队干部、四个生产队长、还有贫协代表,社员代表,全都一一表态:运动中的事,管你是干部也好社员也好,过了就过了,谁也不准再提起。“沙坝里写字,抹了重来。”社员坚决不准不听指挥,干部坚决不准打击报复。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不信就试试!——话是这么说,运动中编着故事整人的和被整的,那心里的疙瘩,不是几句好话说解就能解开的。这些年来,越是“运动”,人们越是学会了使阴招,说两面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差不多每 “运动”一回,人与人之间结怨就加深一回。这一次运动吃了亏,下次运动“赚回来”。“你做得初一,我就做得十五。”你琢磨我,我琢磨你,一报还一报,毫厘不爽。
牛道耕不怕丢官还真没丢。羊颈子、疯儿洞都想当又没当成。牛道耕自己笑自己:老实巴交的牛道荣都懂得,要“反对自己煮鱼,当一天和尚就整他妈一条。”这大队长帽儿没遭整脱,事情就得搞整起走。女儿女婿回家劝老爷子,到镇上粮站住些日子,大队里的事情让朱光明和羊绍银他们几爷子去搞整。 牛道耕瞪着一对牛眼,一阵冒火:“说得轻巧,挑根灯草!哪里去学你妈些混账话!这葫芦尾河,千多张嘴巴要吃饭,小孩子办家家嗦,闹着玩儿的嗦?”
运动也好不运动也好,牛道耕为人的原则是不做假。他的道理从来都简练实用:“管球你几十爷子怎么搞整怎么算计,老子摸着良心当这个大队长,不偷懒,带头做活路,问心无愧!”乡下,“门看门户看户,社员看干部”这是真话。牛道耕自己不偷懒,他的两个儿子媳妇不敢偷懒,牛家大院子的人,历来就对“牛老大”敬畏三分。牛道松而今也卖力气。葫芦尾河的社员也算齐心,劳动也算自觉,相互处得基本融洽。
腊月十五,倒衙的前一天,欢送四清工作组。
过完年,社长周也巡带队,全公社的大队长,正月十六出发,外出参观一个叫啥子“大寨”的地方。去来都在县里集中学习,讨论,前前后后,耽搁十来天。回到家中,一个正月马上就要完了。
自从葫芦口河牛老五家“躲灾”之后,牛道耕这是这辈子第一次出远门。好兴奋。回来后向朱光兰形容道:“格老子,开了盘洋荤,坐火车。啥子都好,吃球不惯,还吃球不饱。发些饼干,咸菜,只有早晨才有一个煮鸡蛋。那都抵得住饿呀?多数人早晨一顿,就把全天的饼干吃完了。不过也好,反正就是睡觉。那火车上,也不晓得是啥子鸡巴一天到晚都在响——吭咚咚,吭咚咚,吭咚咚,吭咚咚——过一会儿还扯起嗓子——呜——呜地叫。刚上车,兴奋咯,一个二个皮夸夸的,摆不完的龙门阵,嗨,没好一会儿,那车摇摇摆摆,摇摇摆摆,人像是坐在娃儿的箩篼窝里,摇哇摇的,摇着摇着,就睡着球了——最不安逸的,是屙屎屙尿要站轮子。火车上那茅厕的门,才鸡巴怪得很,要抓到门上的圆坨坨,揪一下,才推得开。起头那天,半夜三更,老子屎胀了,还好,门开启的,一个人也没有,不站轮子。高兴。进去,关了门,屙完屎,狗日的,拐了,怎么拉也拉不开。冷得老子打抖抖,喊也不好喊。吃奶的力都用完了,还是拉不开。——幸好,列车员听到茅厕里有响动,过来拍门,问咋回事——我说,咋回事?老子出不来了。”一席话把个朱光兰笑得在床上打滚儿,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指着牛道耕,回不过气来说话——
向社员群众传达“学习大寨精神”的时候,当然不能说自己如何在火车上,自己把自己关进茅厕里出不来,差点儿冷死的故事。不过,他的话依然实打实:“大寨那地方,冷球得不得了。吐泡口水在地上马上用脚去擦——你们猜怎么样——结凌冰了!那里的人,日妈才叫苦啊。漫山遍野,莫球得一块水田,全是土。还爬坡上坎的。一眼看过去,要么是雪,要么是黄泥巴。给我们介绍,说是坡上种点儿包谷、高粱,搞整点儿洋芋(土豆),没听清楚,不晓得出不出红苕,估计也出吧?”他谈他的感受,全都是老打老实的实在话,“大寨那些人干的那些活,哪里是人干出来的哟!你我去累都要累死!那些个老头儿,还有那些个姑娘,给我们介绍经验的时候,老子细细地看了一下,大姑娘家家的,一双手伸出来,全是松树皮那样,老茧半分厚。我估计,任随哪个人,不怕你的老脸再厚,这姑娘上来捧着你的脸搓一把,试试看,不把肉搓出来也要脱层皮。”大队部走马转阁楼一地坝的社员,男女老少听得哄堂大笑。有平辈人在笑朱光兰:“他回来的时候,你检没检查一下?你那牛老大这回儿肯定遭搓落皮了的。”
牛道耕没理会别人的玩笑话,正儿八经说:“那雪一落,啥子都盖完了。按说来,人总该耍了歇下来了吧?他们不,把雪刨开来继续干。改田改土,搞整啥子说是能旱涝保收的‘海绵田’。说实话,我牛道耕牛老大做农活,不是吹牛皮,还是个不偷懒的人。这回儿在大寨才算开眼界了——人家过的啥子日子?用的啥子干劲啊?比较起来,我说句落后话,和他们比,我们这葫芦尾河比洪布尔说的那个鸡巴共产主义还要共产主义得多!说是说,笑是笑,格老子人嘛,要知趣,知足,晓得享福。生在我们这葫芦河边,走步路,喝口水,也比那些山旮旯里头,强他妈好远哟!”
按照上级的要求,牛道耕也提出了自己“学大寨”的长远规划:“我在大寨回来的路上想了一路。大家还记不记得,公社彭高贵主任死的事情?那年抗旱,上百架水车,车水上神螺山,支援鸡公岭那边。这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现在,外头在搞机械化了,我们也来一盘儿机械化,就在当年车水的那个位置,修他妈个抽水站(提灌站),安一台抽水机,开一条渠道,遇到天干,神螺山上那股泉水不够用的时候,把机器一开,抽水上山,自流灌溉,从羊子沟,劈头盖脸,把这葫芦尾河淋透。你们说,安逸不安逸呢?”
“要得。安逸!”
“嗨,别说,这主意还硬是好呢!”
“神螺山那么球高,机器能把水抽得上去?牛老大发高烧了,打胡乱说的吧?”
村里没了工作组,人们又懒散多了。日子过得像要慢些。
一天,机动船载着一大船人,敲锣打鼓在葫芦尾河红豆林码头靠岸。公社马礼堂主任带队,上岸就直奔牛家大院。有人认得,跟来的还有个《葫芦日报》的记者。肩上斜挎着皮盒子。早听说过,那里头装的是个小机器。喜欢上谁了,对着你,按一下小机器上面的小泡泡儿,咔嚓,就把人的魂儿勾进去盒子里去了!
现在的牛家大院和前几年大伙食团时候比,不一样了。如果和土地改革分果实那个时候比,更是面目全非了。而今人们吃得饱,穿得暖了,身体恢复得快。又不懂得什么避孕之类,有生育能力的自然就生娃儿。也不全是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问题是两口子干了那事,婆娘就要怀上;怀都怀上了,那就继续干吧。管他是儿是女。好些家都是婆婆和媳妇依轮子“坐月子”,家里的箩篼窝窝坐着两代人。老奶奶一手摇一个,哄睡了叔叔,侄儿又尿胀醒了。添人进口是好事,问题是房子相对就变得越来越狭窄了。不得已就胡乱地搭些偏偏房子。
马礼堂到牛家大院时,这院子里就有六个人坐月子。牛道耕家就有两个,两个儿媳妇相继都生第二胎了。李明霞头一胎是个儿子,这胎生个女儿。三儿媳妇李明芳头胎也生了个带把儿的,这胎又生个儿子,却强忍着喜悦,假惺惺地对李明霞说:“姐姐呀,我硬是眼红你昏了,你这下子儿女双全。”
当然,马礼堂他们敲锣打鼓来,不是来祝贺这些人坐月子的,他们是来给牛道耕报喜戴大红花的。
牛道耕被评为“全国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