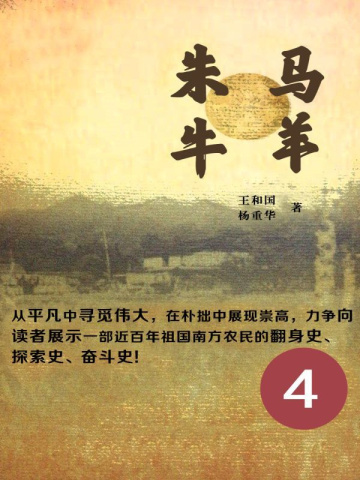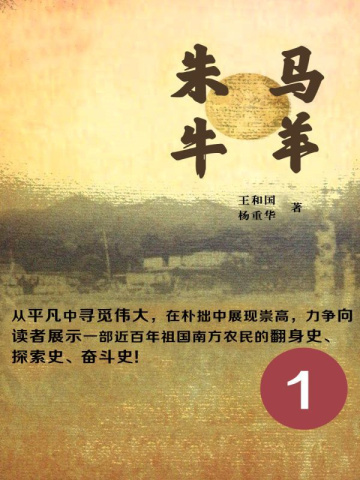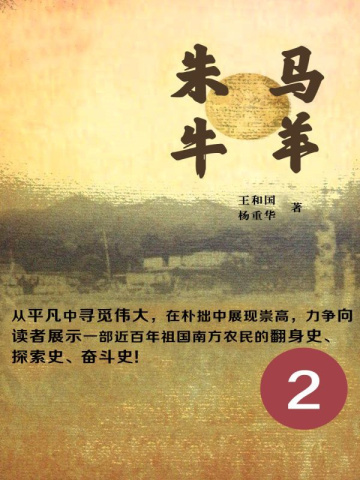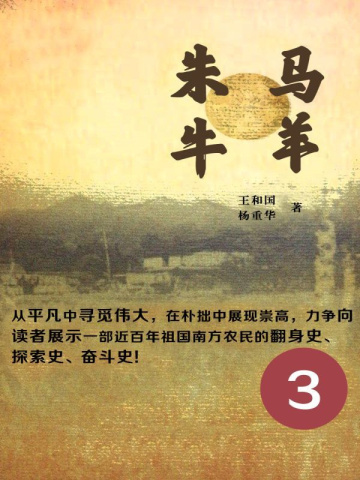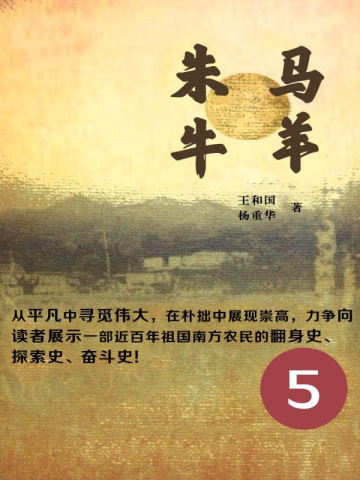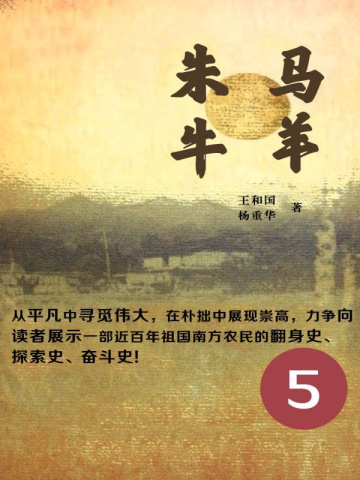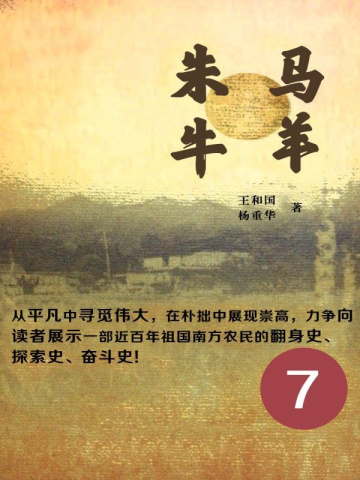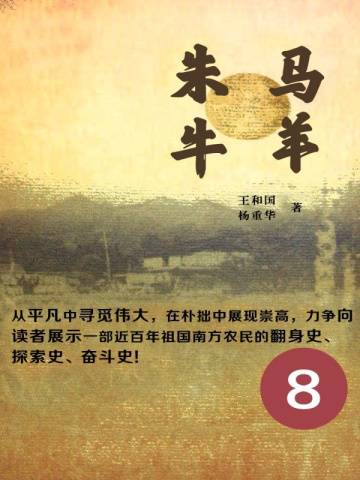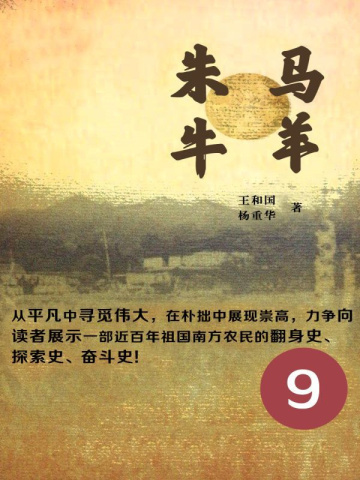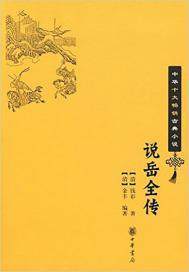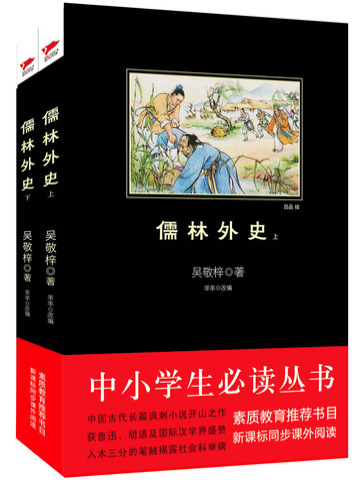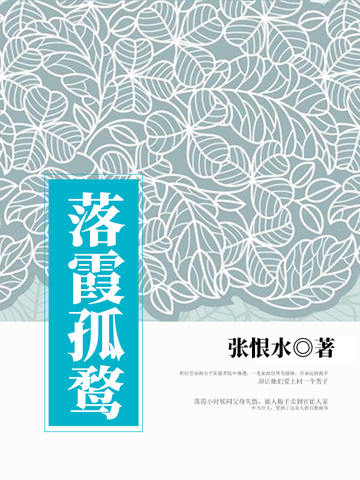牛家长房儿女都孝顺。岁月疯狂,也难免不受“时代潮流”的裹挟。先分过家,后来儿子媳妇们又吵着要合在一起。眼看这一大家子,特别是建功、建业两个孙儿营养不良,瘦得干筋吊肚;小儿子牛天宝在街上读书,姐姐牛天香长期把自己的一份饭多半给了弟弟,致使牛天香自己严重营养不良,至今没有孩子。牛道耕、朱光兰两口子心如刀绞。人人都在饥饿中煎熬,最可怕的是看不到来春有什么希望。长期被压着的怒火,开始燃烧起来。牛道耕的怪话、“反动话”又多起来了。他非常清醒,就幺婆太去世这么一件事,简简单单办个丧事“打包子”,只不过亲戚朋友来喝了几顿稀饭,这么点儿小风浪,牛家人居然就差点儿过不了这道坎儿!简直滑天下之大稽!朱跛子弄来那点儿来路不明的粮食,可救命却不可养人!牛道耕的心灵深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真理就一条:庄稼人的希望在土地里——牛家的根子在玉扇坝!农民自己不种出粮食,观音菩萨显灵也救不了你!他把两个儿子叫到面前,问:“未必我们这些庄稼人,大脚大手的,就这样蜷着双脚饿死球了不成?”
无路可走,逼得人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绝处逢生”。牛天宁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父亲的观点。是呀,“既然没有活路,就朝死路走!死在路上比死在床上强!”胞弟牛天宇两口子,堂弟牛天安、牛天泰和厢房、厅房的牛家人都觉得,再不自己想办法,真的就“死无葬身之地”了。问题是,到哪里去想办法呢?
这些年,牛天宁一直觉得窝囊。本来,长房的传统,父母亲顶着,儿子媳妇再多,也“大树下面好乘凉”,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之后,主要任务就是为父母亲多添几个孙儿孙女。没想到,妻子李明霞头胎生下牛建功之后,这日子会如此越过越艰难、紧巴。后来李明霞得了水肿病。如果不是妹妹牛天香及时伸手帮助,她母子差点都丧了命。明摆着,眼下什么路都堵死了,农民只有自己向土地要吃的,除此没有别的出路!父亲有一顶富农帽子戴着,被称作“阶级敌人”,再不能出头露面了。幺叔牛道奎半个残废。大哥在朝鲜用命挣回来的金字招牌,没挂几天就被下令收回,大哥从此音信全无,看来凶多吉少。这种情况下,作为牛家长房,自己不站出来,就只有如父亲所说,大家“蜷着双脚饿死”幺台!
牛天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李明霞。这位被牛家大院上下称为“霞姑”的李明霞读过初中,娘家是月山乡的大地主。牛家姑姑牛道梅到月山那边走亲戚,认识了这个“霞姑”,从中撮合,马白莲帮着“打了些圆场”,“富农”儿子配“地主”女儿,这姻缘也算门当户对。李明霞嫁到牛家后,深感这家人的和睦亲热,又将自己的堂妹李明芳介绍给了牛天宁的胞弟牛天宇。又是一次亲上加亲。葫芦尾河人都知道牛道耕“狗日的命好,接了两个乖媳妇”。后来,牛建功牛建业两弟兄相差七个月先后出世,把个牛家长房欢喜得几里路外都能听到他们的哈哈声。——谁也没想到,后来的日子会走到眼下这一步。听丈夫如此说,霞姑也慷慨激昂起来,“大不了,你也像爹那样,再为牛家人弄顶帽子戴上!放心,你坐牢,我和建功儿讨口,也要给你送饭!”
牛天宇和李明芳两口子听哥哥嫂嫂说要搞整田地来种,也坚决支持。牛天宇说:“大家都穷得只剩下一副肝肠一张嘴了,我们这些地富子女,更低人一等。再不想办法,饿死了,埋都没人敢拖你去埋呢!”
牛天宁向牛家人宣布,无论羊颈子他们怎么搞整,我们都去把玉扇坝被大炼钢铁毁了的田土复耕出来。那些田现在是荒起的,白天装太阳,晚上载月亮,我们去挖出来,种上粮食。要杀要剐,随他们!不能再这样等下去、饿下去了。再这样搞半年,老子牛家大院就找不到人种了!
同样饿得眼睛血红的堂叔、堂兄弟们都认可了牛天宁的说法,矮子幺爷和牛羊氏也积极支持。大家发誓:这回,管他哪个狗日的来干涉,哪怕把刀架在他们的颈子上,他们也不听。农民,有泥巴就有饭吃!只要玉扇坝种上粮食,再熬几个月,这葫芦尾河就没有人会饿饭。大家还建议,由矮子幺爷出面,去找找大姐夫朱跛子朱光富,帮忙借种粮。牛道耕知道朱跛子这条路再不能走了,搞不好就会毁了朱正才,今后连个“打圆场”的人都没有。绝了退路的事不能干,要不得。牛天宁立即想到这葫芦尾河鬼点子最多的“狗头军师”朱光明,他老婆钱耀梅而今是公社妇女主任,脱产干部。路子宽。找他们想办法,准行。
果然,李明霞话还没说完,朱光明满口应承:种子的事情,他想办法,但绝对不要走漏风声。他只提了一条建议,劝牛天宁,“最好还是主动和大队长羊颈子谈谈,探探他的口气,争取得到他的支持。”
牛道耕却不这样看,他告诉儿子:“羊颈子这种人。成天只是巴不得天上掉馅饼。想的是上级调大米调肥猪肉来。靠不住。你们先干起来,看他狗日的要咋子?”
自建钢厂以来,玉扇坝就荒在那里,快两年了。牛道宽不辞而别后。火烧钢厂,有许多木头没烧着,伙食团就弄去做柴了。马白莲运回来的硫铁矿,早被人们当作“稀奇玩意儿”拿光了。那堆钢锭没人管也没人要,就一层层生了锈。夏天涨水淹没过,泥沙凸成一个小丘,在平坝中突起,到处野草丛生,这里像长了癞疤,成了玉扇坝的一个新景点,而且还看不出什么人造痕迹来。那石碾砣也被淤泥埋了大半截。两座高大的土高炉在那里静默着,似乎想对过往行人诉说点什么。
在牛天宁带领下,牛家大院和朱家塘的人,纷纷去玉扇坝开荒。都指天发誓:第一是不说出去;第二是谁来阻止他们都不怕,他们也不种多了,只种土改时候司马大奎分的那一份儿。非偷非抢,那是政府分的!马家大院和羊子沟的人家,看到牛家、朱家的人在开玉扇坝,也闻风而动。意见空前统一:谁来都和他干,叫他狗日的拿饭来吃。不准农民种田,这是哪朝哪代的规矩?
玉扇坝的四十八大块,几乎都在开耕。
同住牛家大院,更何况这又是天坝坝里的事,当然瞒不过羊绍章,真让他头痛!
复耕玉扇坝是牛天宁带的头。分家之后,他们的家庭成分虽然仍然是富农,但这两口子都不是“分子”,“地富子女”属于“可以教育好”之列。灾荒年代,人们很难把“阶级斗争”落实到对具体人的待遇上,每个人关心的,都是自己的肚子。真正有实在意义的身份,仅仅是自己的那一份口粮。在这一点上,当时的政策倒还没有像若干年之后这样,明确要实行“优胜劣汰”,没有规定不同阶级肠胃的消化质量和水平应当有所不同。所以,只要没有来“运动”,“地富子女”的日子也并不比贫下中农差多少。即使真来“阶级斗争”了,他们也只能属于候补而不能等同于“阶级敌人”。
羊绍章找到牛天宁,开门见山地说:“你狗日的,你认为是解放前么?玉扇坝还是你牛家的呀?”朱光明早就料到有这一盘棋,点拨过牛天宁,叫他不要硬顶。牛天宁笑眯眯地回答说:“解放前又咋子了嘛?解放前,未必然我们牛家,还做了啥子对不起你的事情呀?”
一句话顶得羊绍章差点背过气去。羊颈子他娘是牛家女儿,他羊绍章理当有“五十根搭毛(头发)”姓牛。此其一。解放前,他家羊子沟的老房子被羊绍雄勾结鸡公岭的土匪放火烧了,是牛家人收留了他们。这期间,牛家没有少资助他们父子。此其二。羊绍章站在那里,一张脸皮紧了又松,松了又紧。笑不起来,又垮不下去。声音稍低了些:“日妈弄来种,也该由集体来种,啷个能私人来干呢?”牛天宁还是笑眯眯的,很随和地说,“没有私人干啊,你看,这不是大家都在干吗?”羊颈子开始鬼火起了:“日妈哪个安排你们来干的?”牛天宁还是不生气:“公社社员,劳动不该自觉?还要人安排干才干呐?把我们觉悟说得那么低?大队长放心,我们会认真干的。一定要把这玉扇坝重新种上庄稼!”
羊颈子觉得自己在被人戏耍,强按下的怒火又烧起来了,跳着骂道:“你给老子少日鬼!你们明明是在种土改时候分给各家的田嘛,还锤子个公社社员啊!”
牛天宁直摇手,说:“大队长,你快别那么说啊,我们没有往那里想啊。只是看着这样好的田土,荒起来可惜。挖来种点粮食。管他是哪个的哟,土里有粮食总比荒起好嘛。”
这些话,基本都是事先牛天宁、李明霞两口子和朱光明他们谋划好了的。按照朱光明的观点,挖田挖土种庄稼永远不会错,只有当粮食收获的时候,才搭得上是不是“倒退”之类话题。当前只是各做各的活路,整死也不能承认这是“单干”,看他羊颈子怎么说。
羊颈子直奔主题:“日妈你狗日的不要给老子绕弯弯。日妈这就是在搞倒退!”
上面开会时,羊绍章记住了“倒退”这个词,而且理解也是破天荒的透彻。大家都只开挖各自土改分得的那一块田,这明摆着就是“倒退”嘛。他知道牛天宁带这个头,背后还是他老子牛道耕在拿主意。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牛天宁比他老汉儿油,会给你绕过来绕过去。而且他不是“阶级敌人”,搞整他没有多少道理,于是他就直接找牛道耕“说聊斋”。
朱光明说过,“开始的时候,叫大姐哥牛道耕不要到玉扇坝干活,他身份不同,等事情有了定准再说。”牛道耕这人就是这些地方转不过弯,不懂什么策略不策略。还是那句老话:“庄稼人种庄稼不犯法。”固执地也参加了开挖的行列。
羊颈子走到牛道耕面前说:“日妈你是富农,你带头搞倒退!到时候上头来人,开你的斗争大会,你就晓得厉害了。”
牛道耕不回话,不理他。按说,羊颈子历来对牛道耕敬畏三分,但今天不同,事关“倒退”“复辟”,和“革命”搭界了,他不虚。见牛道耕不搭理他,感觉很没面子,窝火。转过身,又去吼其他的人,希望大家停下来。其他人更不搭理他。
羊绍章气得暴跳:“狗日的些,日妈造反了啊?”
任凭羊绍章如何骂、跳,大家装着没看见,不搭理他。放眼看去,整个玉扇坝上,除了极少数几家人之外,多数田里都有人在搞整了。看来,这些人早就背着他谋划好了!当了这几年干部,捡到不少大道理,他意识到这是个非常了不得的事,必须马上赶到公社去报告。
走到公社,太阳快落坡了。社长们都不在。灾荒年成,公社的脱产干部日子也艰难。粮食定量是每月十八斤,月小三十天,平均每天才有六两,还不全是白米白面,每月都要“搭配”些杂粮。都是有家有口的,负担重。道理都懂:走动要消耗体能。为了保持体力,上班尽量窝在办公室,下班就躲在寝室或者家里。走动少,稍微要饿得慢些。谁都可以躲,唯有一个人躲不脱——办公室主任。原来的主任彭高贵,抗旱车水累饿而死。在黄大峰社长的力荐下,上级批准了原属“借用”的办公室秘书马礼堂,暂时“代理”办公室主任一职。马礼堂做梦都在“挣表现”,争取尽快成为正式的“脱产干部”,所以,他“阶级斗争”的警惕性和阶级觉悟都特别高。听羊颈子说了一半,就当着羊颈子的面,马上打电话向县政府报告情况。
县政府接电话的人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定把带头的那个富农阶级敌人弄来斗争。决不能让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建立起来的美好社会主义大厦,毁在这些阶级敌人的手上。
放下电话,马礼堂非常严肃地告诉羊颈子,先要认清这个问题的“性质”。——羊颈子不懂什么“性质”,听成了土话“性子”——脾气性格。马上接口吼道:“那个狗日的富农子女,性子好得很。尽和老子两个噔儿呐哐地往一边说。你说坝里栽秧,他说胯下生疮。狡猾得很!”马礼堂噗地一声笑了,只好通俗易懂地要求羊颈子:你立即回到葫芦尾河,先将开耕的人无条件地阻止下来。这是个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必要时可以动用民兵,先把那个富农抓来关起!
羊绍章被上级的表态激动得热血沸腾,兴冲冲地从公社回到葫芦尾河。天已经很晚了,想通知开会,估计没有多少人会来,只好作罢,等第二天再说。自从公共食堂解散之后,干部手中的杀手锏——“不给他狗日的开饭”——没有了;“劳动工分”更是毫无诱惑力,既不分粮也不值钱,所以,开社员大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回到家,天早已黑尽。羊颈子饿惨了,到灶房,锅盘碗盏都是冷的。顺手在水缸舀了点冷水,颈子一伸灌下肚,气呼呼地问大女儿羊长芳:“你妈呢?狗日的疯婆娘,管他妈的啥子东西,还是要煮点来吃嘛!跑哪里去了?”
羊长芳没好气地说:“吃吃吃。看这屋里还有啥子吃的嘛!本来,给你留了点吃的,大傻和二傻趁妈没看见,悄悄分着吃得干干净净。——给你说,外公死了,妈和大傻赶过去了!妈说的,你一拢屋,无论多晚,也要连夜赶去,妈说,爷爷、我还有二傻看家。”羊颈子想把二傻叫来问,为啥把给他留的东西吃了,屋里屋外看,不见二傻人影,也不好发作,叹口气:“狗日的,一个二个全是五孽不孝的家伙。”到正屋里问父亲。羊登山证实。“他姨爹专门派人来放的信,说你老丈人死了”。
周金花娘家没有兄弟,就两姊妹。周金花是老大,理当为父亲送老归终。羊绍章对岳父是有感情的。当年一起讨饭,两家很顾及。周家两个女婿中,他现在是大队长,算得台面上的人物了,所以理当尽快赶到岳父家。临走之前,羊绍章专程绕到朱家塘,在朱光明家后面的山林里,喊应了朱光明,传达了公社马礼堂主任和县上关于牛天宁他们开挖玉扇坝问题的指示,要他明天去找羊绍银商量,坚决要出面制止。并强调这是个立场问题。朱光明在家中乐呵呵地连连大声答应:“你放心,我一定尽快告诉大家”。——马晓梅现在实际上除了享受妇女主任的工分补助,以及每月到公社开半天会,中午吃一顿免费伙食之外,其余什么公事都不过问,所以他没有去告诉她。
羊绍章连更连夜赶到了岳父家。灾荒年月,到处都在死人。虽然各级都在“破除封建迷信”,但一般说来,老人去世,作为“白喜事”,还是各自悄悄“循规蹈矩”的。
羊绍章一去就是七天。这七天,岳父家里里外外都要照应,天天熬夜,羊颈子周金花两口子累得够呛。只有随行的大傻天天跟着清风道长和那班做道场的人瞎念什么 “日嘣哝怂,猫钻灶孔”,学着大人咿咿呀呀唱孝歌、哭灵位。回来的路上,一个人还在念。羊颈子听来鬼火起,差点就打他的耳光。等父亲发火发过了,他还是念,声音小点而已。
“头七”一过,羊颈子就急匆匆地赶回葫芦尾河。到玉扇坝一看,连羊子沟那几家前几天没有来开挖的人,也参加开挖了。整个玉扇坝,只剩下自己家中那一块小“豆腐干”田没有动。他异常愤怒,到处找副大队长朱光明和民兵连长羊绍银。不见人影,越加怒火中烧。
他羊颈子自认是得了尚方宝剑的,而且立场问题谁都知道是个了不得不得了的问题。这几天在岳父家办丧事,也一直惦记着这事。连两个“伪甲长”——老粪船羊连金和野牦牛牛敬义也来开挖了,这“阶级斗争”就更明显了!“狗日的些胆子越来越大了!”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七天前,县政府和公社马主任通电话的时候,他“听蹼”听了个大概。 “——新洞样(动向),——带头的富农——弄来斗争——决不能让——果实大耍——毁——”他一抬眼,刚好看见牛道耕——“带头的富农”,正挖得起劲。马主任有言在先:“必要时,可以动用民兵,先把那个富农抓来关起!”羊绍银不在,来不及叫民兵,羊颈子直奔牛道耕挖田的地方,高声对牛道耕宣布:“日妈富农牛道耕,我叫你马上停下来,县政府的人在电话里说的,这是阶级斗争,是新洞样,一定要把你这个带头的富农弄来斗争。你要知道你的成分,你现在就格老子停下来,日妈我就不开你的斗争大会!”
开斗争大会是很恐惧的,但比起饥饿来,这种恐惧就算不了什么。淡了。牛道耕停下锄头,看了他一眼,向自己的手心里啐了点口水,继续挥锄挖他的田。
牛道耕不想发火。一家大小饿怕了。特别是看到那两个因为没有吃的,长得瘦弱不堪,鼓眼瓜瓜的小孙子,牛道耕心子肝子全牵着痛!
不能不承认,在所有人中,羊绍章是少有的真心诚意怕“倒退”的人。“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按照羊绍章的理解,就意味着他一家老小又要再当“叫花子”,连箫、金钱板、莲花落,流落他乡。现在已经这样了,这“一遍苦”“ 一茬罪”,就已经把人搞整得生不如死,还要再来“二遍”“二茬”,怎么得了?
羊绍章找不到副大队长朱光明。民兵连长疯儿洞羊绍银,过去“十处打锣九处在”,今天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他只好掏出已经很久没有吹响了的口哨,亲自吹,集合民兵。吹了半天,一个人也没看见来。在玉扇坝挖田的民兵,都装着不认识他一样,看也懒得看他一眼,谁也不理他。羊绍章恼羞成怒,自嘲地骂道:“日妈我才鸡巴蠢,狗日的些,都在搞整自己的田了啊!”羊颈子下不了台,便自己冲上前去,抓牛道耕的锄把,声称要把他抓到公社去,“叫你给老子倒退!我两个到公社,说清楚!”他想,别人我惹不起,你牛道耕是富农,阶级敌人那一头的,我羊颈子是雇农,大队长,惹你我绰绰有余。羊颈子气力大,牛道耕也不弱,势均力敌。羊颈子是大队长,牛道耕多少有点儿顾忌,不敢全力以赴。接连退了十来步。
羊颈子把牛道耕手中的锄头夺过来了,甩在一边,又上前抓住牛道耕的衣领说:“走哇,日妈我们到公社去,说得脱走得脱!”
牛道耕一直让着、忍着,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在看来,他羊颈子是想要绝了大家的活路,才甘心么?“来真的?你不要把人往绝路上逼!”牛道耕心里想,没有开口。
牛道耕虽然年龄比羊颈子大得多,但毕竟殷实人家长大,身体底子羊颈子望尘莫及,加之常年锄头犁耙不离手,有的是力气,手脚也重,气急而怒。三五两下,牛道耕就把羊绍章拉倒在田里。刚挖松了的田,昨晚下了雨,脚坑里积了些水,羊绍章滚了一身稀泥。不知道怎么搞的,额头让田里的石子儿刮了条口子。鲜血顺着脸颊,流到了下巴上。
这可是“数九”天啊。羊绍章从地上爬起来,两只棉裤裤脚被泥浆浆成了稀泥裤脚。人在气头上,并不觉得冷,也不觉得痛。伸长颈子高声叫道:“日妈富农搞倒退,还敢打人,老子今天,非要把你抓来斗争不可!”
一看四周,玉扇坝挖田的人全都围过来了。人们全都用冰冷的目光看着他。没有一个人吭一声,更没有人上来劝架,大家都像是在围场子看猴戏。牛天宁、牛天宇两弟兄平握着锄把,怒目圆睁,像是恨不能咬人。羊颈子虚了。再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鞋早已陷进泥里,双腿的泥浆,突然感觉冷气逼人。一摸额头,脸,一巴掌的血。“日妈”都说不出来了。连忙弯腰抠出了他的那双“解放”胶鞋,和着泥水穿上。“你格老子等到,你好功夫,格老子——倒退,狗日的——复辟,还打革命干部。狗日的富农——还敢翻了天了!”
骂骂咧咧,几步一回头,跑了。
他没朝家里跑,还真朝公社大院跑去了。
看羊颈子去了公社,大家都为牛道耕一家捏了一把汗,都好言相劝,叫他们去追羊绍章,给他认个错。人家羊绍章是革命干部,“民不与官斗”嘛。什么书都没读过的农民,像记偏方一样,就记得住这些所谓的“古训”。确实,农民怕官,尤其是牛家的人。野牦牛说:“无论哪朝哪代,都是官官相护。这人呀,一当了官,就会变,自己是哪个料搞整出来的,也弄不清楚了,简直就不是人了。你看看马德齐那个白鹏嘛。为了当官,连老子都不认,马都不姓了。这人当了官,你就把他摸不清,猜不透了。更别说朱大了,说起朱大,我们牛家人谁不寒心?”
牛道松接过父亲的话,也说:“现在的官,只要一听到‘阶级斗争’,就两眼发红放凶光,一副巴不得找人打架的样子!道耕大哥不是已经被朱大斗了好些回儿了吗?你可别忘了,头上这顶‘富农’帽子是怎么来的哟!”
牛天宁有点埋怨父亲“太冲动”。富农分子把集体的土地抢来自己种,还把前来制止的大队长打伤了,这性质就严重了。他对父亲说:“明知道他要找你的麻烦,你偏要牛。你看,人家马德齐表叔,就不出面,羊颈子能把他咋的?”牛道耕不这样看,“种庄稼,不是可以在袖子里干的事情,光天化日,躲脱不是祸,是祸躲不脱!”他说他是铁了心的,不怕羊绍章,公社来人就来人,看他们咋办都可以,看样子反正死路一条,要枪毙要劳改都无所谓,比自己圈着脚饿死强!那太窝囊了!
羊绍章穿着泥泞的棉裤,去了镇上罗公馆的公社大院。头上那条口子没有流血了,但额上却冒出个大青包来。血迹和稀泥糊了一脸,像舞台上的戏子。
一进公社大门,他就甩开喉咙大叫,要政府为他做主。他说他被阶级敌人打了,要求把牛道耕抓起来,开斗争会。这些话是他一路想好要说的。他说完后才发现,罗公馆前院的几间屋里,一个人都没有。只好大步穿过小戏楼,进到里院坝,向公社办公室冲。马礼堂主任从外面进来,羊绍章于是就向马主任诉说。七天前就是请示的他,他做了回答,还向县政府打了电话,还强调了是立场问题的。所以他羊颈子今天才敢去抓牛道耕的。“你喊我立即回去,先将开挖的人阻止下来,还说可以动用民兵!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还说一定把带头的那个富农阶级敌人弄来斗争。马主任啊,现在,我就是被这个狗日的富农打了!”
不知道为什么,马主任的态度和前些天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对羊绍章的诉说不置可否,只是莫名其妙地来了一句:“哎呀,很不巧,社长们都到县里开会去了。”
“日妈你们不快点去把牛道耕抓起来,他跑了怎么办?”羊绍章很着急。
马主任说:“前两天上面发了话,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随便抓人。”
羊绍章气急败坏,大吼起来:“日妈好哇,前几天你怎么说的?日妈未必然把革命干部,打成这样了,还不该抓起来?”
马主任耐心解释说:“昨天上面开了电话会,你说这种情况,现在到处都有了,被打的可能也不只你羊大队长一个人了。缓一缓吧。赵连根县长打了招呼的,没有他亲笔签字,不管哪个区哪个公社,任何人不准随便抓人。包括派出所。”
羊绍章这下真急了,扯着裤腿,指着头,让马主任看:“日妈你们这不是在支持倒退吗?这是在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嘛!”
羊绍章咆哮起来,声音又尖又利。院子里的公社干部,担心马主任受到攻击,从各自的办公室走了进来,站在马主任身边,都不说话。看到来了这么多人,羊绍章亢奋起来,绘声绘色地诉说了一遍事情的经过。又大声吼叫要把凶手抓起来。也许真如马主任说的那样,这类滑稽剧其实眼下到处都在表演,公社干部们见多了,都晓得。于是有人附和着说该抓凶手;也有人说老百姓饿红了眼,当干部的要多担待些才好;更多的人是在欣赏羊绍章的精彩表演,看笑话。
无论羊绍章怎样大吵大闹,马主任始终和颜悦色:“你去卫生所搽点药,先回去。等公社领导黄社长他们开会回来,我请示了黄社长之后,再回答你提的要求。好不好?”
当了这么多年大队长,官场的话羊绍章还是听得懂几句的。当官的问你“好不好”,不是真的要和你商量叫你选择,而是明确告诉你“就这样”!马主任的话中话,分明是在下逐客令。羊绍章横了,一屁股坐在办公室的地上。“日妈我今天就不走了!”
马主任说:“羊大队长,你就不要难为我们嘛。你知道,领导不在家,抓人这样的事情,我们这里的人谁做得了主?”看羊绍章没有站起来的意思,他就对其他人说:“大家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忙自己的事情去吧。羊大队长累了,坐一会儿,有啥子好看的?”
大家便笑着,知趣地走开了。
站了一会,马主任说:“羊大队长,我急着要找个材料,你还是坐凳子嘛,地上冷。”说着也走开了。
羊绍章一个人坐在地上,实在没意思,双脚冷得钻心钻骨的痛,站了起来,在公社办公室桌上一拍。
“日妈这个大队长老子不当了!”
说完,便扯着泥泞的棉裤,气冲冲原路回家。一路上他边走边骂:
“狗日的牛道耕,我日你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