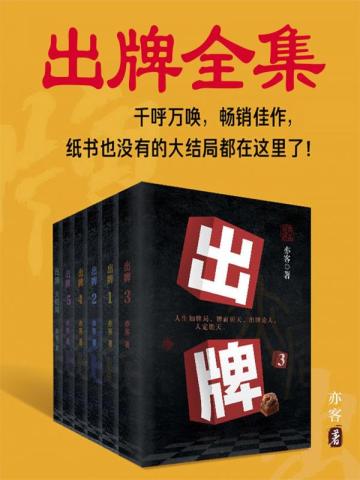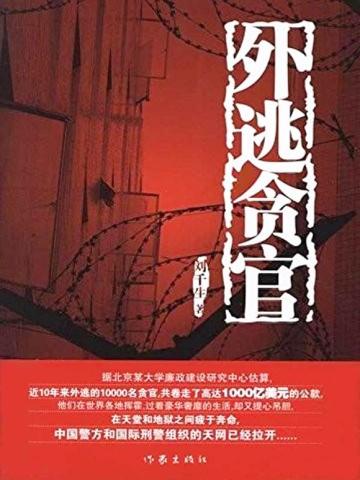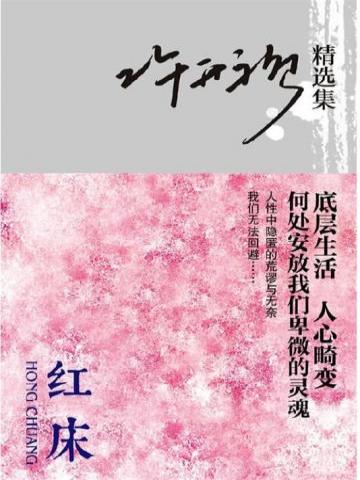上海的夜,是从曹家渡开始醒过来的。
白闪闪的晨光,掉落到曹家渡,紧密地散扎在曹家渡一带的低矮小屋,开始歪歪斜斜地显露了。在苍茫的空间,这就像一大群疲懒的黑猪。
没些儿声息。连矮屋下黑煤渣似的生命,也停息了粗鲁的鼻息声。时间像一匹白布,给裂成两半。中间开了一段空白。——冷铁一般地静寂。
于是有床板的嘎格声,睡眠不足的呵欠声,疲乏的带有晕色的黄色的叹息声……从矮屋下透泄出来。
声音越来越复杂。相互的问答,叫唤;没来由的叫骂,像绳索似的纠缠不清的咒诅;床板跟屋子破裂似的震动,——浪潮般地掀动起来。
屋子里可还不很亮,屋外苍茫的晨光,衬出它们陷在泥沼里的命运的黑暗。光明与太阳,永远不会降临到它们。它们前后的屋檐紧紧地密扎在一起,只给看到柳叶似的一鞭青天。它们的各个房间,大都紧窄地挤住,没让三个人站在一起打个旋身的空隙;可是那床铺、灶头、椅子、板凳、桌子等等杂物,却又占去一大半地面,每个矮屋里的人,都只能扁着屁股,小心地挤着走路。
四方八面的工厂,吹出了有力的惊心动魄的汽笛声,一阵阵地向这些矮屋子迫来。像敌人的号角,叫这矮屋子发抖。矮屋里开始吐出寒冷的一星两星的颤震的灵魂似的灯光。那灯光极其微弱,一流到矮屋子外,就消融在灰白的晨光里,再也找不到它的痕迹。还让那些小屋子疲懒地在暗沉沉的天底下喘气。
矮屋下开始有更大的躁动声:沙沙的像落叶扫过沙土似的泼水声,睁睁琮琮的碗碟的相互碰击声,象把一桶污水泼上马路似的咒骂声,直送到天空云端的尖利的孩子的哭叫声,拖鞋击地的噼啪声……以及每一个焦躁的灵魂的筋骨紧张时的轧砾声……轰动了整个的曹家渡。
晨光终于白荡荡地毫无偏袒地展开了。矮屋子吐出了没生命的黑影子。纷纷地在屋外、弄头、路上流窜。饭盒子锵哪锵哪地响着。拖鞋、皮鞋、胶鞋,噼啪咕咕地押着拍。这些黑影子像给魔法师摄去魂魄的鬼魂似的,向那发出汽笛声的工厂,昏昏梦梦地各自走去。而第三次放夜工的汽笛可又像抽尽人们所有的筋络似的叫起来了。
“嘟~~~~”
是早晨五点钟。
曹家渡的五角场上,人就像崩溃的洪流,纷纷乱乱交织地来去着。在那些人的洪流中,有一大股,是向东流去的——向那横拖在曹家渡东面像一条灰白的癫蛇似的族榔路那日本帝国主义者开着的太阳丝厂,像一头巨熊,横伏在萧瑟而寥落的像条灰白的癫蛇似的族榔路上。它每天早晚吞吐着成千的工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高的、矮的,肥的、瘦的,漂亮的、村俗的……杂色的成千的工人,成千的次殖民地的中国人的生命,帝国主义者用以肥壮自己的成块的黑煤,烧烂的煤渣……工厂灰白色的围墙,像座堂皇的城堡,高昂地耸立着。它的四周,全是些没有建筑的泥沼与污地。中间笔矗地耸起漆黑的烟囱,像一座铁骨架成的瞭望台。烟囱终年不息地吐着煤烟,发着烧焦头发一般的臭气,是一切生命煎成膏油化为焦炭的臭气。
工厂的门面,全用水泥结成。约莫有十来丈高。中间开了个大铁门,显着大肚子的帝国主义者眼珠子那样的威严的黑光。两旁又各开着一扇小门,可又窄得像一条缝,只容一个人钻狗洞般地进出。那大门是不轻易开放的,除非有搬运汽车进出,及早晚放工。就是早晚放工,有时碰到施行人身检查,就不开这大门。开放的时候,也还只开一扇,仅够工人们组成长蛇似的一队.流了出来。仿佛这巨熊的肚里,藏着极其隐秘的计谋,怕被一旦泄露。
工厂对面是一座泥土剥落的古旧的洋式“里屋”。沿路一行房屋,有几家小杂货店。那些小杂货店全用黑木板构成个棚架,放上些香烟、纸头、洋火以及花生、糖果之类。灰沙与尘穗子挂满了角角落落。烧饭的煤烟,终日缭绕在屋子里。屋里人影就像黑云块在暗空中浮动。但其间却有一进屋子,粉刷得簇新雪亮,显出一派傲视世界的神气。那是一个警察派出所。屋子里门槛、板壁都是蓝的。后壁上交叉地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和蓝地白星的两面旗子。旗下是一幅画像,上有蓝底白字的遗嘱。黄色制服的警察们,一早就在这里恍恍惚惚地浮动着。
上工的工人们,一连串地往边门挤着进去。待他们慢慢儿快走完了,警察派出所里就马上吐出几个武装的精神煊赫的黄色制服们,往那框榔路跟康脑脱路接界处,又往那康脑脱路跟极司非而路接界处,一对对地站起岗来。看他们那种荷枪实弹的情形,就像猎人们预防被追逐的野兽脱逃似的。他们在警戒着。他们在弹压这些放工的工人。他们无疑地是中国人。而工人们却始终是帝国主义者用以肥壮自己的煤渣。
这时候,有一个青年,枯发,瘦脸,白花条子的短衫裤,像觅食的小鸟似的,怯瘦伶仃地在这条路上来回地踱着。
他从康脑脱路踱到栎榔路去。他夹在上工的工人群中。他踱过厂门前,慢慢儿踱向东边去。他恍恍惚惚地踱着,他踉踉跄跄地踱着。他直踱到胶州路近边。他突然听到美国兵房里传出来的雄壮而骄傲的军号声。他马上觉得心头有块大石压住、感到了像处女被暴徒强奸似的侮辱。他愤怒地咬住牙关,铁青着脸,低下头去。——低下头去,他又瞧见一路上都是些为美国兵房里高大的骏马所践踏的马蹄痕迹与狼藉的黄色的马粪。他顿时感到这栎榔路就如他的肢体,一个个的马蹄痕迹,一堆堆的马粪,就是他身上被蹂躏的伤痕与被耻辱的标志。他于是愤然地折回了头,又向太阳工厂那边踱去。
终于他在太阳工厂前那座破旧的里屋旁边,一个空地上蹲下了。像撒野矢的人似的蹲着。他失落在茫然里,掐着沿路沟上带露的小草。
“唔喷——”
像从半空中掉下这么一声叫。巨熊的口霍然张开了。张开了一半。接着,就有五六个青年工人,像被撞的台球似的霍落落地弹了出来。这被弹出的他们,却偏又装作个老鹘扑地似的姿势,显得十分自主的快乐。
毕竟他们是年轻的。年轻而且活泼。生气蓬勃。一脸的笑容,一腔子的笑声。他们仿佛有无限胜利的光荣。
有一个,穿着黑皮鞋。走起路来,春春作声。方黑脸,大黑浓眉,鹘碌碌旋转的眼珠子。然而他的存在却显示在春著的皮鞋声里。他是黑皮鞋另一个,一身黑拷衫裤,架空的支住,准叫摸不出他骨柚在哪里。脸是酱黑色的,像个干枣子。然而他的活泼与精锐,却显在他那一对老鼠似的尖利的眼光里。还有一个是短短的两腿,一副猴子脸,衣服坎肩上,准破有十七、八个大小窟窿,也算是披了件灰布小褂儿,没敢犯“违警法”。此外,又有个长划脸的,文弱的像个缝衣匠,一切风度,皆显出善与女子接近的那种细腻与贴己。又有个像白开水似的掺在任何药水里都显不出它的特点的普通家伙,但此刻却因掺在几个比较活泼的工人,他也就显得活泼了……“不要走哪!不要走哪!站着看呀!”
开始是那黑皮鞋的说话声。
“是哪一个呢?”
有一句问话,却找不出是谁说的。
“看着,不就会知道了吗?——等会儿,我指点给你看。”
黑皮鞋站了下来。这一群也就着魔似的各各站下。短腿子破褂儿的蹲在路沟边,恰巧跟那个最先站在空地上那个怯瘦伶仃的青年并在一边。白短裤毛腿子的缝衣匠似的那一个,站在工厂围墙下,那水泥结成的人行道上。黑皮鞋拉住黑拷衫右手,黑拷衫扳住黑皮鞋左肩头,把下巴搁在右肩上,站在路中间。其余的,也各随自己习惯,站呀蹲地等在一边。可是那些人,都把一对尖眼珠,集中厂门口,往里窥探。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有人那么问。
“就是那个——那个‘所话’呀!……”黑皮鞋伸伸手指儿。
“是个小姑娘呢。”矮腿子破褂儿的仿佛有个数儿。
“乡下大姐。”
“乡下大姐?”是白短裤毛腿子的惊奇的语调。“倒亏她有胆量拨开两脚来哪。”
“总是那么一回事,还有什么拨不开的?”有人老下脸,仿佛他全是一本经手的。
“快乐哪!有趣哪!……”
于是一阵高呼,夹着一阵冷笑。这声音就如锉锯子,叫人汗毛根根倒竖。
但大多数放工的工人,全象没有这回事。脸色死板板的,眼光淡幽幽的,心像不放在腔子里,脚像踩在云块里,身子的移动,像是有别的活动的机械在推进,自己全作不得主。而那活动的机械,又仿佛跟路子极其熟习,知道从厂到家需要走几步,也知道哪块路子上,有个洼孔,哪块路子上,有块绊脚石。他们大都是提着饭盒子,锵啷锵哪响着,像故意在刺激自己的神经,可是老刺激不醒来。
但也有些女工们,带着另一副神态和气概。撅着个嘴巴,足足有半天高,像谁欠了她三百年冤债。老是一个劲儿赌着气,一步一转屁股。步子越开越快,屁股越转越高,上衣角就像鸟翅拍风似的,在屁股高峰上起劲地扇动。
“不要脸的烂腐货,臭×!”
“好骚不骚,怎么骚到那个人身上去了。”
骂着,咒着,全不当一回事,却又全当作是自己事似的。仿佛厂里头发生了这件事,就叫她们转屁股也有点不自由。
“哈哈!哈哈!”
“呵呵!呵呵!”
路边那一团,可把泼水似的笑声,将她们的咒骂声掩没了。
咒骂声中马上转出个带麻的方脸孔。她顾盼自若地送出蓝蓝的烟似的眼光。一步一转屁股,于是向四边瞧了瞧,再来一手骂:“要是轮到老娘呢,准叫他吃口×水去,不让他碰根毛。——怎么,一条烂黄鱼,偏有人爱吃呀!”
“爱吃!爱吃!”忽然她自个儿沉住。烟似的眼光发了毛。
她马上感到自己毕竟有缺点。每个麻点上,涨上一点红。
前面走着的男子,像给她突然戳上一针子,回过头来瞧了瞧她,她马上低微地嬉笑一下,和善地投了一个疲懒的色情的眼光,可是眼光所到处,那男子却早已哼了声,仿佛醒过来的人又睡去似的别转了头.理也不理她。
别的女工们却尽在路两边吐射唾沫子。在她们仿佛这种事连咒骂也是脏嘴的。于是她们和他们就各自带着不同的微弱的心的反应。在灰白色的癞蛇似的路身上走着过去。
“呵!哈哈!来了!”
路旁的一团,齐齐地站拢来。刚才走出工厂的男女工人,都回过头来。循着黑皮鞋手指处,向厂里面看去。
院子里走着三五个女工。
于是路上开始有不少男工们停下来。
消息仿佛是阵秋风,谁身上都感到有点毛毛的冷。但谁都有点不很了然。知道是有这么一回事。但不知道怎么会有这回事。那女主角的名字,可也有点知道的.但是个什么样的人,可又谁都不曾瞻仰过。
“就是开房间吧,那也不算什么一回出奇的事!”
有的人,这么一回想过来,好奇心也就有点坦然了。
“有什么可看呢——人总还是个人。”
接着这坦然的,似乎又瞧到了自己所处的命运。全都是一样。谁也没有嘲笑谁的权利,想拉着另一个走。但自己却还无意于走,又悄悄地兀自站住了。
“看一看,那又何妨呢。”
于是又倒回转想过来。觉得在自己的被损害与被侮辱的心里,唯有去损害别人或侮辱别人,才能取得快乐。
“嘘——”嘲笑声也轻狂起来了。
在这混乱中,早已推来一辆空空的小车。
像条着地生根的干萝卜。这小车夫终年是束着条破麻袋,在敲着他的旱烟袋。他是茫然的。但他也了然的。他想,这该是那些男工们想吃女工们的豆腐吧。吃豆腐,那是男子们对女子们一份应有的权利。这倒也满有意思。蛮有情趣的。小车夫敲完了一袋烟,于是傻里傻气地咧开嘴,笑了起来。
小车上,已经陆陆续续地坐上了三五个小姑娘。大都是红颧骨,浓眉,粗粗的睫毛,盖住了眼光,眼皮向下,眼光落在地上,落在自己挂在车座上的脚上,落在用自己的手揉弄着的衣角上——是抬不起头来的羞怯。但也有烂漫地一脸呆笑,圆着眼往四下里瞧,瞧不清趁热闹的傻子们的心思,终于又皱皱眉头,呆住了。
“呵哈哈!呵哈哈!”
一大阵群众的喝彩声,迎来了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女工。那女工从厂里出来,傲慢地走上马路。她平着脸,正看前方,那辽远的前方,她不顾一切,旁若无人地走着。
“呵哈!呵哈!”
喝彩声顶上天,天那么高。整个天地要给喝塌了!真相马路起了裂。仿佛一群疯狂的群众,欢迎一个名女伶出台演奏。
她是圆脸儿;白净的皮肤。身材适中。淡黄的单旗袍,适身地披着。她剪发。肩膀圆浑而结实。眼大而圆,黑亮的眼珠子,藏得下一万个人的面影。嘴原是红的,此刻却微露苍白。像淡水褪的牡丹花。这时,她仔细瞧去,像一个小清水池,映着岸上稚松的松针。她咬住两唇,仿佛在嚼牡丹花片。她走向小车去,坐上小车的左角,那唯一让出来空着的座位上。她漫然地伸过一只象用大理石雕出来的女神似的有力而可爱的手臂,挽住小车的背脊。低低地然而却像主将的命令似的说了声:“去!”小车夫就马上挂上肩带,摆开两脚把舵似的搭定屁股,两手挽住车柄,咕喳一声,就一路发响着,推着小车前去。
“呵哈!呵哈!”
于是像送行人似的,喝彩声更大也更高了——而且更复杂了。
而且时时发出咒骂:
“前夜快活不快活?”
“来过几次呢?——该不像咱们那么粗吧!”
“当然是,又白嫩,又软熟。像吞糯米汤糊似的!”
“不,是骚鸭子吞黄鳝哪!”
“哈哈!——呵嗬!哈哈……”
庞杂的嘲骂.庞杂的笑声。
“真是一只骚鸭子呀!一天到晚,呷呷呷地叫过去。吞到一条黄鳝,可就不让走了。还不如到马路上当野鸡去,拉人好啦!”
这是一个女人的尖锐的声音。就像一条无形的钢丝,贯穿了每一个人的耳朵。
于是这些跟在小车后面送着的人们,就一齐回过脸来,找这发话的主人。却原来是个中年妇人。看她那酱油色的瘦脖子上放着张灰黄色的脸,胖大的奶子发松似的在抖,至少是养过六个的孩子的。
她实实在在感叹她的黄金时代的消失!
黑皮鞋,短腿子,黑衬衫……这一团人,也还混在大群的人里。
车上人每一个都像坐在针尖上,感到了不安。连那个十三、四岁的大眼睛,也开始吃惊地闭下眼来了。她们全都想在这污蔑的袭击中,装出一副坦然的样子,表示自己没有可被嘲弄的污点。带着像一切卑劣者赶紧剃净自己的胡子来的心情。可是越想装坦然,越觉得不自在,连嘴角的苦笑,唇边的微颤也各自感到了。最后,各人且在各自永不会被发现的,连自己也早已忘得干干净净的隐秘处,找回了自己的羞耻,仿佛自己真的犯过了罪,真的给公开到公众面前去……于是也就在各人的眼上漾出似哭非哭的吃惊的泪光;狡猾者则用打呵欠掩饰过去,笨拙者可真的想哭了。
小车呜呜地转着。她们的心也呜呜地转着。她们又时不时的转着屁股,转着身子。竟弄得小车夫把不住车柄,就把屁股当作定向的舵子,摆东扭西地尽摆着扭着。
只有她却还泰然,淡然。无视一切。虽然心里是在一溜溜发酸。
她需要强!在一切的欺凌、侮辱、磨难中,她要强!强硬起来吧!然而她偏偏在软弱里失了足。失了足,她也还不懊悔。谁爱把自己青春如何出卖,谁就可如何做。没有人可以干涉她。她唾弃他们这些欺凌、侮辱与磨难……她终于痛苦地失笑了。
“嘻……呼……”
“呵呵!还笑呢!还笑呢!”
立刻有人像偷去她灵魂似的给发现了她的干笑声。
“这真是不要脸的!”
恶骂却也跟着泼过来。
“不要脸!哼!自己可别馋痨哪!”
但还有半句怜悯的袒护。
“准是你自己馋痨哪!咱老子可不吃臭咸鱼。——咸得淌白花!”
飞来的又是一句奚落。
男子们就都是这么推推撞撞的,边说边笑,边指着她瞧。女子们都吐给她一口唾沫。虽然这唾沫未必真的吐在她身上,而是吐在地上的,但她正是一块土地呀,正让千千万万人在那上边践踏。
然而也还有些出格的呼声:
“这个怎么奚落得人家呢,瞧住自己的妹妹好啦!”
“别太叫人受不下去哪!”
“唔!是的!总也该自己回头想一想谁能准没个错儿呢!”
黑皮鞋回过头来瞧瞧这说最后一句话的人,是个黑瘦脸,花白条子短裤,一头黝黑发,一个文弱的青年——一个全不像自己一帮里的人。
终于在这象纠结的长绳怎么也分不开来的情形下,这小车推上了康脑脱路,于是长绳在武装的中国同胞的警士的弹压下,渐渐松散了,渐渐疏稀了。小车又推上五角场。
一切的男女工人,脸上全收住快乐的笑影。一下子,这为了自己经常被损害与被侮辱因而想从损害别人与侮辱别人中取回快乐的心,就在武装的警士的弹压下冰住了!冰住了,换回的,仍是颗被损害的与被侮辱的心。他们和她们全都放低脚步,各自走向自己的家去!
家呵!一个怎样黑暗,怎样泥泞的家呵!一条黑色的死亡线横拦住在他们的门前!
小车又推向白利南路而去。
空气突然来了一下扫荡,车上人全都感到了一阵轻松,个个吐了口长气。然而这轻松,却给她一个反省。她反而感到心的沉重了。她又软弱下来。她想哭。然而她又要强硬,她把泪珠逆流到肚子里去!她只能听到小车轮子粗重的辗转声:“鸣呜呜呜……”
天哪!……她的前途呢?
远了!
黑皮鞋、黑衬衫、矮腿子、白短褂……这一团人,就茫然地站了下来,在五角场上,在泗阳茶楼面前。
“朋友,是怎么一回事呢?”
突然,一只瘦小的手,落在黑皮鞋的肩膀上,一个软和的声擦过这一群人的耳边。谁都回过头来瞧:是一个枯瘦文弱的青年。
黑皮鞋觉得有点面善。然而马上想起是刚才见过的。
黑拷衫给投了一个怀疑的眼光;矮腿子皱着扁脑壳,掀了掀线似的眼,发出一声笑,白短褂却安闲地踱起步来。
“没什么。”黑皮鞋回说着。“那个小姑娘跟咱们厂里帐房先生开房间哪。”
说着,他那脸上显出对于什么事都很平常的坦然的神色。那种近乎咸鸭蛋那样的通体灰蓝的平常的神色。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可不太难为她了吗?”
于是那瘦棱棱的差不多要给风吹倒的青年,以极其怜悯的语调,说了出来。在他那波谲云诡的脑子上,勾出了种种的映象。仿佛他和那被侮辱的女工,有种密接的线索,而且这线索,也拴在一切中国民众的身上。这是被压迫的命运的线索。他又更进一步唤回了过去的回忆,在这女人的面影上,看出他从小就耳鬓厮磨的一个童养媳:她那坚决倔强处,更像那童养媳反抗丈夫的侵害.花烛之夜就不让丈夫进房的顽强。然而不同的,那童养媳对他自己一切的柔和与软弱处,却不能在那个女人身上找到。……在一九二七年三月的某一天的深夜,这不为女人所齿的老实的丈夫,是如何赶了一匹马来,叫自己骑上把自己带出了火坑呵!而自己却终于没有见一见她……她一样是个灵魂被损害者呢。
“可不是吗?”于是这青年又说下去。也许她是个穷苦的家庭唯一的生产者呢。也许她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娘,她有三两个未成年的兄弟:也许兄弟是成年了,现在因为工厂合理化,多用起女工和童工来,也像你们一样在时时担心失业中,而终于失业了。现在你们那么的奚落她,弄得她没好意思上厂来,那么她的一家,不就要饿死了吗?
“哦!”于是这一群青年工人,全都肃然站停,睁着对瞠然的眼。“那一着咱们可没有想到呢。”接着,这几乎不能闻见的低低的声音,也通过各人的心头。
那瘦削的青年,知道自己的话,已发生些微的效力,他想征服这一群青年工人。用他那从历史的烘炉里锻炼出来的真理的宝刀,剖割他们古旧的为一切腐败的传统与恶俗的环境所凝住的脑子。他继续说下去:“而且,你们应该知道,咱们中国是次殖民地的国家;咱们工人所受的苦难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外国老的剥削,一方面是中国大肚子人们的欺骗与压迫。而做女工的却又是三重的了。她们在必要时,是得出卖她们的贞操。我想,在你们厂里,那样的人正多呢……”
“啊!那可真多啦!”矮腿子说。
“那多啦!那多啦!有的还争风吃醋呢。”别的人又那么说。
“那么你们又为什么奚落她呢?……”青年说了句沉默下来。
他仿佛在耳边听到一阵凄凉的歌声。
——买去了我的劳力,该也把我的贞操收买了呵!
——你好心的老爷,你好心的先生呀!
——从岩间带来的幽兰,已经不是为了自己而芬芳了!……“……而且单是奚落她呢?”那青年又说下去。“你们可真能体谅她的苦衷吗?再说到底,你们把自己的血汗,出卖给帝国主义者,出卖给资本家,跟她把贞操出卖给他们的走狗,又有什么不同呢?……”
“哪有不同的!哪有不同的!”
一致的反对声。每一个人的脸上,显着被侮辱了的怒容。那缝衣匠似的白短褂以稳健的语句,回答了那青年。
“咱们是用力气赚饭吃。这是自从盘古以来,就是这么的。是正当的。而她这种出卖,却是不正当的。吃这口饭,可是脏嘴的。”
“但是,你们吃的一口饭,却是苦的。开厂的人,一点不用力气,他们可吃得多么舒服惬意哪!……”
“那不,那不,他们放着本钱呀!”黑拷衫带着恶意的笑。
只有黑皮鞋沉默着。矮腿子像只松鼠似的跳踉起来。瘦青年知道征服他们需要用更大的力量,他回头望一望泗阳茶楼,很亲和地笑了一笑,说:“朋友,这就有话可谈了。道理说来长呢。咱们到那茶楼上喝杯茶,仔细谈一谈怎么样?”
“得咯!”黑皮鞋叫了起来。“咱们上茶楼去。”
于是这一群在警察的眼里已经觉得讨厌了的人们,就仿佛躲避老花猫的追袭的小老鼠似的,一个个窜上灰尘扑落的漆黑的泗阳茶楼上去。
楼上是水汽,烟雾,灰沙,黑的脸,茫然的眼光,混杂的浮在破黑桌上的说话声……这时候的曹家渡,已经成为小贩叫卖的世界。西瓜摊,牛肉铺,鱼贩,菜贩,酸梅汤担,包子店,烧饼店,……个个用着惯熟的叫唤声,兜揽着顾客。而在这些庞杂的声音中,十六路无轨电车的铁镫声,八路公共汽车的喇叭声,像跟包子店里击釜声争个响亮似的,更觉得显出特别。
工厂的汽笛声在阳光下绝灭了。——太阳下的上午的曹家渡,是灰黑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