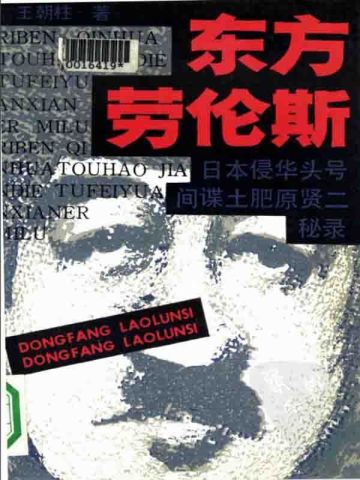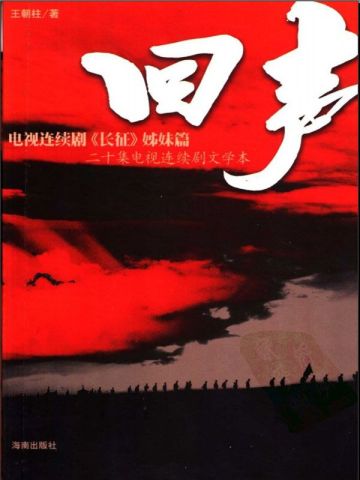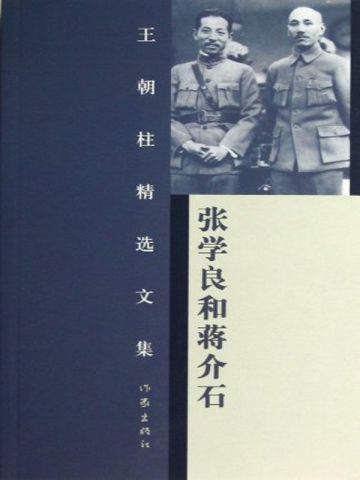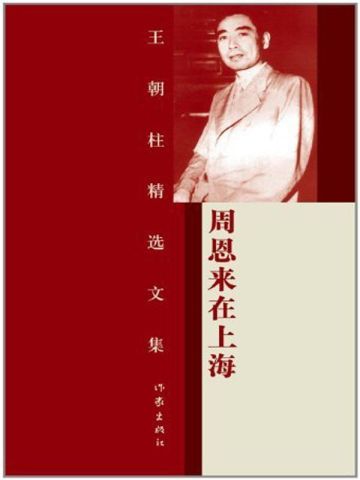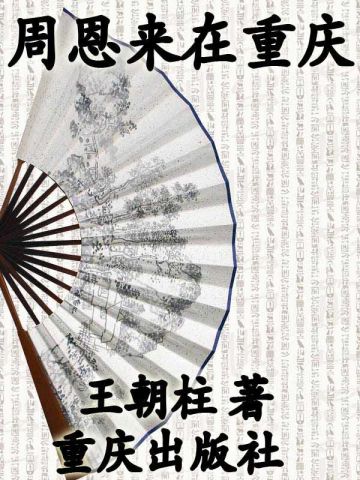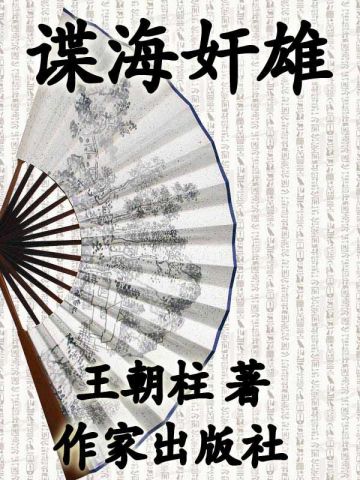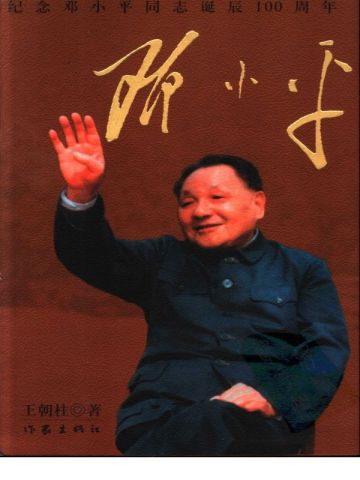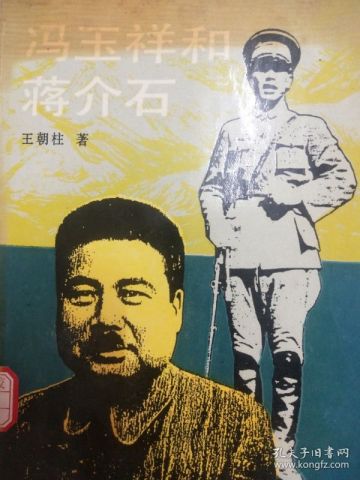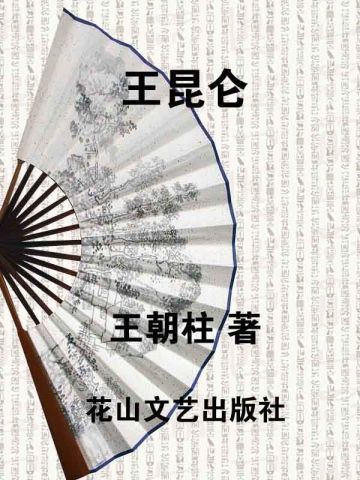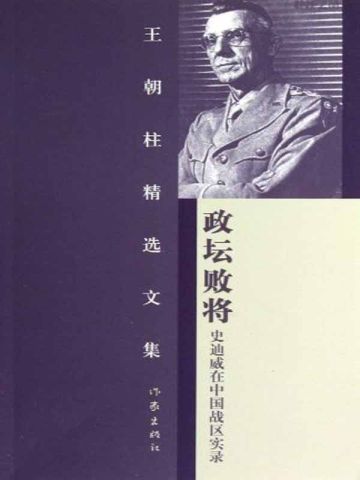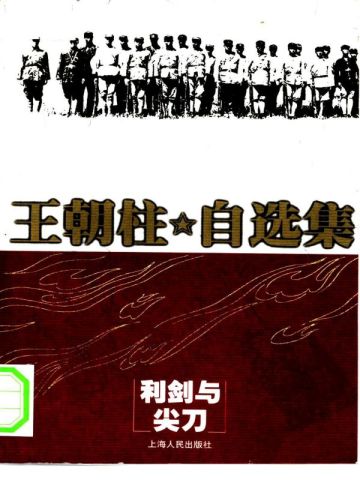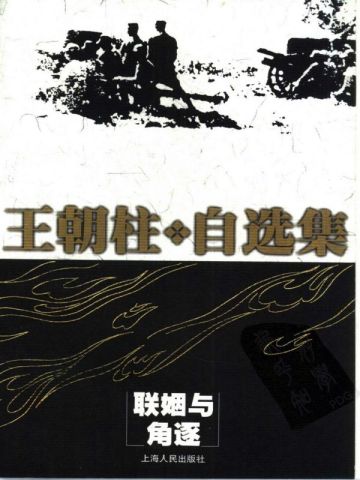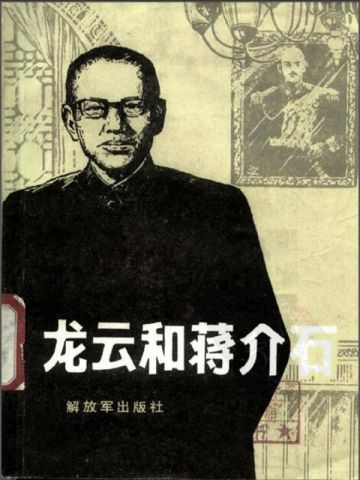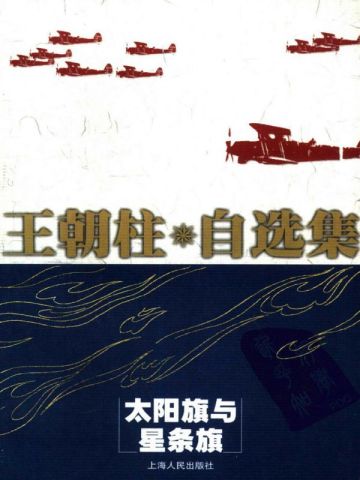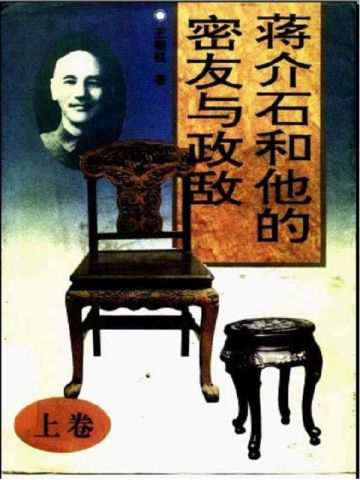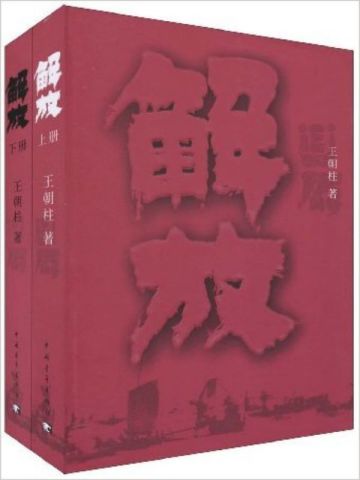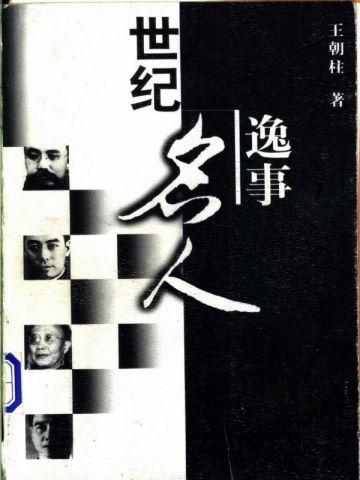偌大的上海,浓云密布,烟雾缭绕,压得人们几乎透不过气来。
二十年代末的一天,黄浦江上,停泊着一艘艘外国巨轮。码头上摆满了标有不同国籍的货箱, 由中国的“苦力”们卸船,装车,或卸车,装船。持枪的外国巡捕,大腹便便的船主,抡鞭抽打码头工人的洋奴……构成了一幅典型殖民地的悲惨景象。
江边的客运码头,是我国近代的志士仁人出国求学、寻觅解救中国之路的起点。 自然,它也是迎接远航归来的儿女们的门户。今天,停泊在码头上的客船,是法国的邮轮《昂达利.雷本》号。手持船票的各国旅客,排着整齐的队伍,踏着舷梯,登上客轮。有的人匆忙地进入船舱去找铺位,还有多数人站在甲板上,挥动着双手向岸边送行的亲友告别。
邮轮就要起航了。从码头上大步走来一位体格魁梧,身着海魂衫的外国人,只见他深陷的蓝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他就是这个船上的海员古久里。和他同行的是一位体格矫比,中等身材,工人装束的中国年轻人,他叫夏童。负责检票的那位海关官员,一看夏童和古久里那份亲热劲,不但没敢查看夏童的船票,还躬身让路,皮笑肉不笑地伸出右手向邮轮一指:
“请,请里就要开船了……”
“呜!呜―……”
《昂达利.雷本》号邮轮19L叫了儿声,夏童协助古久里收好船梯。站在甲板上的各国旅客,码头上送行的男女顿时挥动双手,操着不同的语言高声喊着“再见!一帆风顺!……”邮轮缓缓地驶离了码头,船上、岸边的减声汇集一起,完全分不出词意。有的旅客脸上泛起了欢欣的微笑,有的旅客脸上挂满了斑斑的泪迹……只有夏童神色肃穆地望着烟雾迷漫的上海,陷入了难以言状的沉思之中。古久里轻轻地打了夏童一拳,不大高兴地说:
“夏童旦你每次告别上海,脸上的表情就不大好看。说得准确些,这次还有些令人可伯的神色!”
夏童唱然摇头:“咳!讨饭的孩子,离开挨饿、生病的母亲远游异乡,脸上是露不出笑容来的!更何况……”
“这次一去就是五年,对吧?”古久里十分幽默地说:“看吧!尽情地和你这位挨饿、生病的母亲话别吧!可就是不准落泪、痛哭。”
夏童深沉地点了点头。稍顷,他抓住要离去的古久里的手,叮嘱说:
“你可不要忘了!船上还有一位不能和祖国告别的乘客呢。”
古久里耸了耸肩膀:“我会利用职权关照他的, 虽然我和他还没见过一面。”
邮轮的底舱是既脏、又窄小的锅炉房。飞舞的煤屑,熊熊的护火散出的高温,使人时时都有窒息的危险。几个汗流侠背的火夫,赤裸着上身向炉中轮番铲煤。只有一个身材偏高的小伙子,痴然伫立在船帮那口牛眼大的小窗前,透过满是污垢的玻璃,望着缓慢远去的上海。他长叹了一口气,又哀伤地摇了摇头,随即绰起一把大铁锨,俯身铲煤,不大熟练地向炉中扔去。他挂在腰间的那支竹箫,随着铲煤的动作在不停地摆动着。
“开饭了!开饭了……快洗洗测捌,到甲板上透透气,凉快凉快!”
随着话声,一位年长的中国火夫顺着船舱的梯子走下来。那些劳累了大半天的小伙子们一听,高兴地把铁锹一扔,几乎是小跑似地顺着通向甲板的梯子“哦瞪……”地离开这底舱锅护房。最后,只剩下了那位腰间挂着竹箫的小伙子,仍然机械地铲着煤,一下一下地送往妒中。老火夫趋步近前,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深倩地说:
“星海!你也上去吧。”
冼星海闻声转过身来,他满脸是煤灰,汗水津津,冲得脸色有浅有深,一双眼睛闪炼着价强、聪慧的光芒。他伸出右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张着嘴喘着粗气,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双手拄着那把大铁锨,望着慈善的老火夫为难地摇了摇头说:
“我……没买船票,伯……”
“这、我知道!”者火夫爱怜地说:“锅炉房的气温有四五十度,老是闷在这底下,你会晕过去的!”
冼星海放下铁锨,迟疑地呆了一会,拖着酸懒的双腿,跟着老火夫摇摇晃晃地登上了船梯,来到舱外一问洗漱室,把脑袋伸到水龙头的下边,让清凉的淡水冲个痛快。然后,他简单地擦了擦身子,换上一件半新不旧的学生服装,独自登上甲板。他先伸了伸嫩腰,活动一下四肢,旋又远眺那将要沉入大海的夕阳和金色。的晚霞,他顿感心旷神怡。他长长地叹口气,又情不自禁地吐出一个“啊”字来……
失然传来一阵笑声,把冼星海的视线引向前甲板上。原来是几个午国“放洋”的学生聚在一起在说笑。一位鼓着博士眼镜、颇有几分学究气的青年大发感慨地说:“咳!我们总算从那孤陋寡闻、闭关自守的小天地里闯出来了……,他转身看见了风姿英俊、在欣赏落日狂涛的夏童,恳切地请求说:
“夏童,你把那首诗再大声地朗诵一遍吧!”
夏童笑了笑,欣然应命。随即铿锵有力、富有表情地朗诵起来:
出国去
走东海、 南海、红海、地中海;
一处处的浪卷涛涌,
奔腾浩瀚,
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到那里,
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炼你的才干;
保你的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
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
推翻旧理论,
全凭你这心头一念……
站在夏童旁边的是一位窈窕女郎,穿着西方流行的时装,黑黑的发丝烫得一个波浪接着一个波浪,朱唇小口,人工描绘的弯弯的柳叶眉,再配上系在胸前的那副绿宝石项链,真可谓是时髦的摩登小姐。她瞪着两只水灵灵的、俊俏且又有点风搔的大眼睛,在静静地听着夏童那富有抑扬顿挫的咏诗声。朗诵结束了,她不由自主地赞赏道:
“您朗诵得真好旦但不知您是……”
“他是我们岭南大学的高材生,是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那位戴眼镜的学究青年忙介绍说。
“请问这首气势磅礴的诗是您写的吗?”窈窕女郎操着敬慕的口气问。
夏童微笑着摇摇头,郑重地说:“不!我可没有这样激昂的才思。这首诗,是出自九年前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之路的一位志士的笔下。”
“柳莺!柳莺……”
循着喊声,只见一位穿着褐色西服,系着紫红色的领带,鼻梁上架着一副方型墨镜,拄着一根绛紫色的文明手杖,说话很注意声音共鸣的青年快步走来。他叫杨德烈,是一位师承意大利美声学派的二流歌唱家。他冲着那位极其风流的妙龄女郎生气地说:
“柳莺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害得我到处找你。”
柳莺却不以为然地说:“这里多好!一等舱那个小房间闷死了……德烈,快来欣赏一下大海之上的落日吧,”
“查票了!查票了!
“冼星海闻声惊得一征,急忙回身就跑。事有凑巧,和从船舷的另一侧走来的查票船警碰了个对面,他惶然掉头又跑。富有经验的船警大吼一声“站住!”,冼星海就心慌意乱地落到船警的手里。顷刻之间, 围观的各国旅客拥了过来,把船警和冼星海圈在中间。顿时,甲板上一片嘈杂的喧哗声。
夏童机警地挤进围观的人群,猛然抬头,和被船警扭着手的
冼星海的目光相遇。他坚毅地点了点头, 匆忙分开围观的人群,大步踉跄地离去。
一个大块头的船警辱怒地问: “喂!快把船票拿出来!”
冼星海惶然地不知该如何回答。
另一个年长的船警轻蔑地说:“投有船票,一定是混上船的小偷!”
冼星海被小偷二字激怒了,他昂起头,大声抗辩说:“我不是小偷,我是船上烧锅炉的火夫!”
那个大块头的船警声色俱厉地斥责说:“胡说!伙夫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这是你该呆的地方吗?”
一个围观的绅士打扮的旅客说;“我看他不是个小偷,根据我多次乘船的经验,他是个没买票混二房来的穷学生。”
一个年过半百,却打扮得异常沃艳的外国女人,赶忙掏出一洁白的手帕捂住鼻子,装做很有身份的样子说:“船警,快把他弄走吧,免得这个东亚房夫把传染病带上船生”。
柳莺趋步上前,不知轰耻地凑热闹说:“德烈里您送给我的那串宝石项链,上船以后就丢掉了,说不定就是让他偷去的,快搜搜他!”
杨德烈欲要动身搜冼星海的衣身,古久里昂首阔步地走到跟前,拨开围观的旅客,神态很是严肃地问:“喂!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年长的船警指着冼星海:“古久里,你来得正好,这个人是你们锅炉房的火夫吗?”
此刻,冼星海的心里扑通扑通地活象是敲着大鼓,暗自说
着“完了!全完了……”懊丧地低下头,有意避开古久里那双熠熠闪光的蓝眼睛。古久里没有立即回答,他只是皱着眉头打量着冼星海。当他发现了冼星海挂在腰间的竹箫之后,语气肯定地说:
“是的!是我新雇上船来的火夫。
冼星海惊喜地拾起了头,带着愕然而又感激的目光望着古久里,眼眶里滚动着晶莹的泪水。 当他那模糊的视线依稀看见站在古久里背后的夏童,在冲着他顽皮地崛嗽嘴,得忘地眨眨眼睛后,他才从五里雾中走出,恍然明白了这一切。
古久里拍了泊冼星海的肩膀,充满着热情地说了句“开饭啦!吃完饭快去干活吧。”随即吹着口哨信步走去。
查票的船警,不同国籍的旅客茫然地看着离去的冼星海,一时显得是那样的静寂。
夜深了,皓月的银辉洒向万里大海,映起碎镜般的银光。邮轮《昂达利.雷本》号随着大海的自然呼吸,忽而沉下,忽而浮上,很有节奏地向前驶去。邮轮的船尾犁开了一道扇形的海沟,并击起无数朵海浪花。冼星海随着夏童、古久里来到甲板上,迎着徐徐拂面的海风, 自由地呼吸着湿润、并且含有腥味的空气,欣赏着风平浪静的海上月夜,真是有着一种说不出的神秘之感。他们三人随意地坐在甲板上, 夏童深情地说:
“古久里!感谢您保护了我的同学……”
古久里摆了摆右手,爽朗地说:“保护一位到我国寻找真理的穷学生,这是我应该做的事。”他凭借月光,又看见了系在冼星海腰间的竹箫,颇感兴趣地问:‘这是一件东方的乐器吧?叫什么名字?”
冼星海解下竹箫,顺手递给古久里,有些拘谨地说:“是的里它名叫箫……”
“萧?……”古久里翻来复去地摆弄着,似乎想从箫的形体上找到和欧洲的单簧管、双簧管、英国管一类竖着吹的木管乐器所共同的东西,然而他却大失所望地摇了摇头。他带着好奇的心理又问:“冼!你一定会吹箫吧?”
冼星海深沉地点了点头。
夏童急忙插嘴补充说:‘当然会吹了!星海是我们岭南大学有名的‘南国箫手’。”
古久里十分快活地问:“冼生能吹支好听的曲子吗?噢!噢……换句话说,能吹一支表达你的情感的曲子吗?”
冼星海双手接过竹箫,朝着古久里笑了笑,示意说“可以!”然后转过脸去,凝视泛着银光的平静的海面,沉思了片刻,把竹箫一端缓缓地举到唇边,顷刻呜咽的箫声悠然而起,送出一首富有南国特色的渔家情歌《咸水歌》。这动情的萧声发自星海的肺腑,打动着夏童、古久里的心弦;它还穿透了海上的静夜,带着冼星海的情思传得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