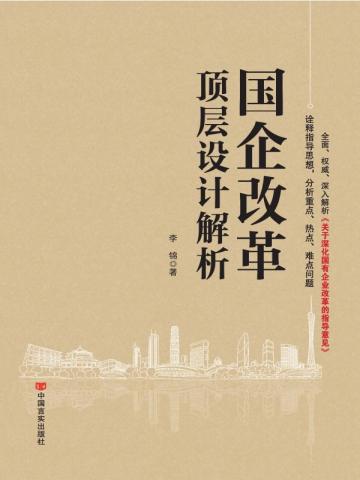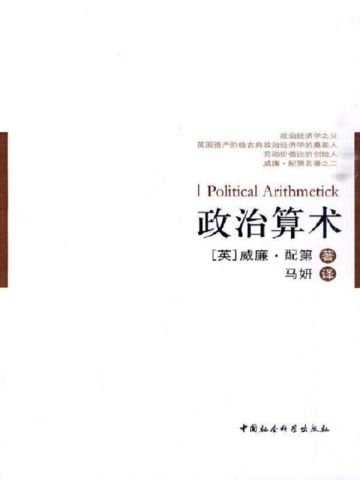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政治的历史向度 / 李里峰著. 南京 : 南京
大学出版社, 2018.6
(学人文丛)
ISBN9787305203954
Ⅰ. ①中… Ⅱ. ①李… Ⅲ. ①政治制度史-中国-文
集 Ⅳ. ①D6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3821号
出版发行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汉口路22号邮编210093
出版人金鑫荣
丛书名学人文丛
书名中国政治的历史向度
著者李里峰
责任编辑焦腊文官欣欣编辑热线02583593947
照排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35×9651/16印张 2625字数 324千
版次2018年6月第1版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305203954
定价10800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南大亚太论丛》
主办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列)
蔡佳禾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蔡永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洪银兴南京大学商学院
孔繁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石斌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孙江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王月清南京大学哲学系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张凤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朱庆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委员会
主编石斌
副主编李里峰毛维准
成员祁玲玲舒建中赵光锐
姚远吴小康宋文志
《学人文丛》编辑组
石斌蔡佳禾李里峰
毛维准舒建中李恭忠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得于2016年夏初创设并渐次成长,“南京大学郑钢亚太发展研究基金”之专项全额资助,实乃一大助缘、大善举;众多师友、同道的鼓励、扶持乃至躬身力行,同样厥功至伟。
此一学术平台之构建,旨在通过机制创新与成果导向,以国际性、跨国性与全球性议题为枢纽,将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具有内在关联之学科方向、研究内容与学术人才,集成为国际关系、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群”,对大亚太地区展开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并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
所谓“亚太”,取其广义,乃整个亚洲与环太平洋地区之谓。不特如此,对于相关全球性问题的关切,亦属题中之义。盖因世界虽大,却紧密相连。值此全球相互依存时代,人类命运实为一荣损相俦、进退同步之共同体,断难截然分割。面对日益泛滥的全球性难题,东西南北,左邻右舍,各国各族,除了风雨同舟,合作共赢,又岂能独善其身,偷安苟且?所谓“发展”,固然有“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多重意蕴,亦当有“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之价值取向,其理亦然。
吾侪身为黉门中人,对于大学之使命,学人之天职,理当有所思虑。故欲旧话重提,在此重申:育人与问学,乃高等教育之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大学之本是育人,育人之旨,在“养成人格”,非徒灌输知识、传授技能;大学之根是学问,学问之道,在“善疑、求真、创获”。二者之上,更需有一灵魂,是为大学之魂。大学之魂乃文化,文化之内核,即人文价值与“大学精神”:独立、开放、理性、包容、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与信念。大学之大,盖因有此三者矣!
南京大学乃享誉中外之百年老校,不独底蕴深厚、人文荟萃,且英才辈出、薪火相续。于此时代交替、万象更新之际,为开掘利用本校各相关领域之丰厚学术资源,凝聚研究团队,加强对外交流,促进学术发展,展示亚太中心学术同仁之研究成果与学术思想,彰显南京大学之研究水平与学术风格,我们在《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集刊已相继问世的基础上,决定再做努力,编辑出版《南大亚太论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设门户、画地为牢,绝非智者所为。所谓“智者融会,尽有阶差,譬如群流,归于大海”,对于任何社会政治现象,惟有将各种研究途径所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方能得到系统透彻的理解,否则便如朱子所言,“见一个事是一个理”,难入融会贯通之境。办教育、兴学术,蔡元培先生主张“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论丛》的编纂,亦将遵循此种方针。
故此,《论丛》之内容,并不限于一般所谓国际问题论著。全球、区域、次区域及国家诸层面,内政外交、政治经济、典章制度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重要议题,都在讨论范围之内。举凡个人专著、合作成果、优秀论文、会议文集,乃至特色鲜明、裨利教学的精品教材,海外名家、学术前沿的迻译之作,只要主题切合,立意新颖,言之有物,均在“网罗”、刊行之列。此外我们还将组织撰写或译介各种专题系列丛书,以便集中、深入探讨某些重要议题,推动相关研究进程,昭明自身学术特色。
要而言之,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所执守之学术立场,亦即《论丛》之编辑旨趣:一曰“本土关怀,世界眼光”;再曰“秉持严谨求实之学风,倡导清新自然之文风”;三曰“科学与人文并举,学术与思想共生,求真与致用平衡”。
一事之成,端赖众力。冀望学界同仁、海内贤达继续鼎力支持、共襄此举,以嘉惠学林,服务社会。值出版前夕,爰申数语,以志缘起。
石斌
2018年元旦于南京
中国政治的历史向度
目录
目录
上篇视野与方法1
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3
一、历史学与社会科学4
二、历史学的学科特质8
三、三部影片中的历史哲学14
四、结语18
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20
一、从《历史研究》两组义和团研究论文说起20
二、事件作为研究对象抑或研究路径23
三、“事件路径”的历史何以可为28
四、“事件路径”的历史与社会史、总体史32
五、“事件路径”的历史与“叙事的复兴”35
新政治史的视野与方法39
一、从政治史到新政治史40
二、政治事件的方法论意义43
三、政治行为从精英到大众48
四、政治制度及其运作之道51
五、政治文化的多重维度55
六、结语59
个体记忆何以可能:建构论之反思61
一、实存的个体记忆与隐喻的集体记忆62
二、时间、空间与记忆的质感64
三、日常生活实践与记忆的消费68
四、结语71
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73
一、自西徂东:概念史之译介74
二、多源交汇:概念史之方法78
三、循名责实:概念史之实践83
四、共筑平台:概念史之展望91
孙中山形象建构与政治文化史研究95
一、孙中山研究:旧与新97
二、政治文化史:实与虚102
暴力是恒久的吗?111
一、暴力的社会生态112
二、小地方、大历史、长时段116
三、社会史与新文化史之间121
四、重新检视“国家与社会”125
五、暴力是恒久的吗?130
中篇知识与制度133
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以汪康年为例的思想史阐释
135
一、作为思想史文本的汪康年135
二、“慢慢走”:变革道路的重新选择137
三、“往回走”:回归中国传统文化143
四、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149
“东方主义”与自我认同——梁启超中西文化观的再阐释154
一、“保教”之说:一个两难的文本155
二、人我之间:“东方主义”的文化认知158
三、不变之征:自我认同的寻求和困境165
翻译的政治:严复译著与近代东亚知识传播173
一、“达旨”之术:思想挪用的政治174
二、“求其尔雅”:语言归化的政治179
三、政治的翻译与翻译的政治186
在民族与阶级之间:中共早期的“国耻”论述
——以《向导》周报(1922—1927)为中心188
一、国耻之纪念:从“九七”到“五卅”190
二、国耻之根源:敌人与朋友的谱系197
三、国耻之洗雪: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205
四、结语:从“国耻”到“唤醒”213
民国文官考试制度的运作成效216
一、应考和录取人数217
二、任用资格和途径223
三、及格人员的任职情形226
四、小结229
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试制度的若干问题231
一、名目:文官考试还是公务员考试231
二、性质:资格考试还是任用考试234
三、原则:考试党化还是人才主义237
四、限度:公职候选人考试应否举行240
五、录取:凭文录取还是分区定额243
六、方法:论文考试还是新式测验245
下篇革命与治理249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抗战时期的山东共产党251
一、党组织的规模和构成252
二、新党员的吸纳机制256
三、党员的入党动机263
四、对党员的审查和清洗267
五、结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270
革命中的乡村——土地改革运动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274
一、基层组织网络的建构275
二、国家功能边界的扩张280
三、村庄权力结构的重塑287
运动中的理性人——华北土改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
293
一、地富:合作或抗拒的艰难博弈294
二、贫雇:理性农民抑或道义农民305
三、中农:利益与安全的双重考量314
四、结语:运动中的理性人323
中国革命中的乡村动员:一项政治史的考察327
一、抗战:民族话语下的乡村动员330
二、内战:阶级话语下的乡村动员338
三、中共乡村动员的变与常348
群众运动与乡村治理——1945—1976年中国基层政治的一个解释框架354
一、群众运动与运动群众357
二、群众运动中的行动逻辑364
三、群众运动与乡村治理373
集体化时代的农民意愿表达与党的农村政策调整380
一、“生产力起来暴动”与集体化步伐的放缓381
二、从“退社闹社”到公社化运动387
三、“瞒产私分”与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391
四、结语395
后记399
上篇
视野与方法
中国政治的历史向度
上篇视野与方法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14年第6期,第158165页。
①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
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历史学不断面临挑战和危机,又不断自我调适以应对挑战、摆脱危机的过程。除了社会政治变迁的时代大背景之外,近百年来历史学所遭遇的挑战主要来自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后来又加上了文学理论及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性别研究等跨学科研究领域),吊诡的是,它借以应对挑战的学理资源也大多来自这些学科。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曾撰写《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一书,在美国的汉学界影响甚大,其所谓“拯救历史”,是要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边缘立场出发,冀望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宏大叙述中发现多元、复线的历史脉络。①
笔者不敏,也想借用这一说法,简要辨析历史学的学科特质及其与社会科学的异同和交融,进而对历史学重新找回自我的可能性略作反思。
一、历史学与社会科学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传统历史学皆以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及重要历史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注重描述事件的起因、过程、后果,刻画历史人物的成长背景、言行举止和性格特征,并对特定民族、国家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以资后人借鉴。19世纪,以实证主义为旨趣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学派兴起,强调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对史料进行甄别批判、去伪存真,在此基础上据事直书,不偏不倚,从而让历史学摆脱哲学和神学的桎梏,开始向科学的行列迈进。和传统史学相比,兰克学派重政治、外交而轻经济、社会,重事件描述而轻理论分析的取向愈演愈烈,在他们看来,研读原始资料是最根本的史学研究方法,而只有政府文件和军事、外交档案等才算得上真正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界对传统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不满日益强烈。德国历史学家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站在批判历史哲学的立场上,斥责德国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社会心理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汲取概念和理论资源,甚而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Karl Lamprecht, What is History? Five Lectures on the Modern Science of History, Biblio Life, 2009.法国历史学家贝尔(Henri Berr)倡导打破过分专门化造成的狭隘局面,拓宽历史研究的领域,运用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解释历史,并创办《历史综合评论》杂志来实践这些主张。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James H. Robinson)则明确祭起“新史学”的大旗,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强调历史学家应该吸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的成果,用综合的观点、进化的眼光来解释和分析历史事实。[美]鲁滨逊:《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
1929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两位教授布洛赫(Marc Bloch)和费弗尔(Lucien Febvre)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揭开了20世纪影响最深远的史学流派——年鉴派的序幕。顾名思义,这份刊物是要以经济史、社会史去挑战和取代传统的政治、军事、外交史。进而言之,年鉴派主张一种“更全面、更贴近人的历史”,一种涵盖全部人类活动、重结构分析甚于事件叙述的历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极力倡导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借鉴。该刊编辑部成员除了历史学家外,还包括政治地理学家西格弗里德(Andre Siegfried)、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等人,即是明证。第二代年鉴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其史学理论文集中明确声称,贯穿全书的“一个固执的想法”,就是要看其他学科能给历史学提供些什么启示,以及历史学家反过来能给邻居们提供些什么。[法]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前言”。他承认,“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永远会在死的文献和太活泼的证据之间、在遥远的过去和太贴近的现实之间各执一端”,但他仍坚信“过去和现在是互惠地照亮着对方”。他对历史时段所作的著名区分则似乎表明,至少在他所处的时代,向社会科学借鉴“长时段”的“结构”分析乃是历史学家的当务之急,其重要性超过了历史学能够给社会科学带来的启示。[法]布罗代尔:《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收入《论历史》,刘北成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自此以降,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借鉴和交叉融合愈益频繁,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借用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方法,社会科学家也越来越注重将历史向度引入自己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交叉学科。发展到今天,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和渗透已经如此之深,以至于如果把来自社会科学的概念一律弃置不用,历史学家将不仅无法很好地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看法,甚至也难以对历史进行认真的思考。对此,英国历史学家伯克(Peter Burke)在《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书中作了至为透彻的阐述。在他看来,如今历史学家频繁使用的许多概念,诸如社会角色、性和性别、家庭和亲缘关系、社区和认同、阶级、身份、社会流动、炫耀性消费、象征资本、互惠、庇护和腐败、权力、中心和边缘、霸权和反抗、社会运动、心态、意识形态、交流与接受、口述和书写、神话等等,其实都是从社会科学借用而来的,离开了这些概念,历史学家将会面临失语的危险。参见[英]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三章。
需要强调的是,概念借鉴绝不是词汇挪用那么简单,而是把概念中所蕴藏的丰富意涵和理论前提融入史学研究,甚至内化为历史学家观察、分析、解释历史现象的一种“前知识”(preknowledge)。举例言之,如果历史学家要分析一位历史人物的“角色”,难免会想到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甚至下意识地把这位人物想象成历史舞台上的演员,看他(她)是如何进行自我呈现(presentation of self)和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如何在前台(front region)和后台(back region)之间进行转换的。如果要研究某一时期普通民众的“认同”问题,这位史家的脑海里也很可能立刻涌现出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关于“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的论述,借以考察这些民众是如何把自己与素不相识的其他人想象成同一个国家、民族或阶级之一员的。
对于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对历史学的影响,伯克书中提到了比较研究、计量研究、类型分析、微观分析(所谓“社会显微镜”)等。以比较研究为例,历史学家关注的是特殊、唯一和不可重复的事物,所以往往倾向于拒绝比较方法;而以探寻社会现象本质和规律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则始终把比较方法作为研究的利器。[英]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33页。韦伯(Max Weber)对世界各主要宗教及其与现代资本主义之关系的研究,桑巴特(Werner Sombart)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设问的回答,直至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对法国、俄国、中国革命之背景和后果的分析,都是堪称经典的比较研究范例。如今历史比较方法(包括求同的比较、求异的比较、影响的比较等)越来越有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拜社会科学所赐。
今天的历史学家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假设和分析模式(model)。例如“共识”(consensual)模式和“冲突”(conflictual)模式,前者为涂尔干所倡导,强调社会关联、社会一致和社会内聚力的重要性;后者为马克思所倡导,强调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无处不在。[英]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页。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时,我们还会用到精英主义(elitism)模式和多元主义(pluralism)模式,在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等精英主义者看来,少数精英(统治者)对多数非精英(被统治者)的控制和支配是不可更改的“铁律”(iron law);而在达尔(Robert A. Dahl)等多元主义者看来,竞争性选举和多元精英之间的制衡仍足以奠定现代民主的基石。
如果把上述概念、方法、模式全部抛开,像传统史学或实证主义史学所主张的那样完全让史料和史实本身来说话,历史学的洞察力和解释力无疑会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这些概念和模式早已潜移默化地融汇在绝大多数历史学者的脑海中,成了他们随时取用而习焉不察的“工具箱”的一部分,事实上已经无法从他们的心智中移除了。
二、历史学的学科特质
经过一个世纪的相互借鉴和交叉融合,配备社会科学工具的历史学和引入历时性维度的社会科学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越来越成为诸多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共识。然而,每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旨趣,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并不意味着取消各学科的独立存在。不幸的是,如今历史学对社会科学的摄取(或者说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殖民”)似乎有些走过头了,以致于历史学还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本文斗胆提出“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正是想对历史学的学科特质略作反思。在笔者看来,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相比,历史学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实质性的差异。
首先,历史学是一门时间之学。法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曾言,“历史学是时间的科学”。一语道出了历史学的真谛。有论者对这一经典命题作过如下阐释:社会中的任何存在都是历史的存在,这为历史研究规定了时间界限;历史时间(年代和时期)因与具体的历史事件相关而承载了特殊的意义;历史演变的轨迹体现了历史学家的时间观(如循环时间和线性时间);时间是理解历史和进行历史评判的重要因素;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争取时间的历史。参见俞金尧:《历史学:时间的科学》,《江海学刊》2013年第1期。不过,在许多受“后”学影响的学者看来,将历史学当作一门“科学”本身就是很值得怀疑的,所以称之为“时间之学”似乎更妥当些。笔者宁愿从一种更质朴的角度来理解勒高夫的命题,即历史学和其他学科门类相比,本质特征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已经逝去了的事物,历史学家无法亲身观察和感受它们,而只能依靠留存下来的文献和实物来进行研究。换言之,历史学家需要穿越时间进入另一个时代,可他们不能真的穿越,只能以一种“不在场的在场”的方式去接近自己的研究对象。
有一本非常简短的历史学导论,提到了两位英国作家对于历史的有趣看法——过去是一个异邦(foreign country)。就是说,历史学研究的并非自己的国度,而是异国他乡,只不过它是时间意义而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异邦。但是如何看待这个异邦,两位作家的看法正好相反。哈特利(L. P. Hartley)说,过去是一个异邦,在那里人们的行为方式全然不同;亚当斯(Douglas Adams)则说,过去的确是一个异邦,在那里人们的行为方式就像我们一样。参见[英]阿诺德:《历史之源》,李里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7页。人们去往另一个国度,可能会看到和本国大不相同的社会景象和风俗民情,也可能感觉到他们有着和自己相似的日常生活和七情六欲。历史学家要去研究、再现过去这个异邦,同样会有类似的体验。20世纪80年代一部很有影响的西方社会史论文选编以“再现过去”作为标题,是很有道理的。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尽管深受社会科学影响的社会史在理论和方法上与传统史学差别甚大,但作为一门时间之学,历史学无论新旧,都要把再现过去当作自己的基本任务,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历史学家看来,“再现”(representation)一词的具体内涵是不一样的。
将研究对象设定为时间维度上的异邦,就可以很自然地推导出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设身处地”,也就是要借助历史资料以及史学家的合理推测甚至想象,回到过去的场景中去。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对此作了至为精辟的论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所谓真了解者,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或者如狄尔泰所说,真正的历史知识乃是对过去的一种内在体验,历史学家就活在他的对象之中,或者是使他的对象活在他的心中。参见[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7页。历史学者往往会有一种冲动,以所谓“后见之明”对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制度、观念等加以评骘,仿佛上帝注视芸芸众生一般居高临下地看待过去。但是,如果没有设身处地的“移情”(empathy)能力,没有对历史研究之限度的自我反省,这种后见之明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上焉者不过是毫无意义的“马后炮”,下焉者则成为阻碍我们探寻历史真相的“后见之蔽”。
其次,历史学是一门叙事之学。传统历史学始终把政治、军事、外交等作为研究重点,相应地,叙事也就成了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手段。中国古代的编年体、纪传体、大事本末体史书,西方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直到兰克的诸多史家,都把讲故事作为第一要务。及至20世纪初“新史学”兴起,特别是年鉴学派创立之后,传统史学的“事件主义”(布罗代尔语)或“事件偶像”(西米昂语)遭到严厉批判。在布罗代尔构筑的历史时段等级体系中,事件虽能用“迷人烟雾”占据当代人的心灵,却不可能持久,人们只能短暂地瞥见它的光亮。相对于结构变动的“长时段”和局势演变的“中时段”,以事件为中心的“短时段”不过是历史河流中泛起来的小小泡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法]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尽管如此,事件和叙事并没有,也不可能从历史学家的视线中消失。这不仅是因为历史本就是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事件所构成的,还在于事件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方法论意义。我们(无论从历史学还是社会科学的角度)去考察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时,应该从何处入手呢?毕竟,所谓制度,所谓结构,都不是直观可见的事物。当然可以依据制度文本(法规、文件、档案之类)来研究,但规则是一回事,实践又是一回事,二者之间时常是相互背离的。要想克服制度和结构的“不可见性”,揭示其实际运行状态,就需要借助特定的事件为中介。如果把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比作大海里的冰山,事件就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虽然不能从中看到冰山的全貌,但若无视它们,就更难猜测水面以下的部分是什么模样。因此,历史研究绝不能放弃对事件的关注,而应把短时段的事件作为研究中时段、长时段的有效窗口。当然,这里对事件的理解应该是广义的,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将其等同于重大历史事件,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很重要,“五四”运动、抗日战争也很重要,但并非只有它们才算事件,才值得研究。许多看来很琐碎的小事件,如果能借以探讨其所折射出来的制度、结构、关系和行动逻辑,它们同样应该成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
说历史学是叙事之学还有另一层含义。如今写作历史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供选择,可以用传统的讲故事的方法去写,可以用分析的方法去写,还有的历史著作充斥着数据、图表甚至回归分析。每一种写作方式都有其独特的价值,都能给读者带来不同的启示,但笔者所期待于历史学的,是让它回归到最古典、最本真的形态——讲故事。像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萧邦齐(Keith Schoppa)的《血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及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一系列著作,带给读者的愉悦是其他许多史著难以企及的。西方史学界从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斯通(Lawrence Stone)所谓“叙事的复兴”,许多现代叙事史著经典,如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马丁·盖尔归来》、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近年来也都有了中译本。不过,在全球化和后现代的语境下,讲故事其实并不容易,要讲男人的故事(his story)、女人的故事(her story),还要讲无名者的故事(their story);要讲大写的、单数的故事(History),还要讲小写的、复数的故事(histories)。要把这些故事都讲好,洵非易事。
最后,历史学是一门人文之学。首先体现在,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个别的,而不是抽象的、普遍的。历史哲学家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指出,形成科学概念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一种是把现实的异质的间断性改造为同质的连续性,这是自然科学的方法;一种是把现实的连续性改造为异质的间断性,这是历史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兴趣在于发现对事物和现象普遍有效的联系和规律,所以要采用普遍化的方法;历史科学的目的则不是提出自然规律,甚至也不是要形成普遍概念,它“不想缝制一套对保罗和彼得都同样适合的标准服装”,而是要“从现实的个别性方面去说明现实,这种现实决不是普遍的,而始终是个别的”。[德]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0页。伯克则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差异提出了如下看法:社会科学是对单数的人类社会(human society)的研究,侧重对其结构和发展的归纳;历史学是对复数的人类社会(human societies in the plural)的研究,侧重于研究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各个社会内部基于时间的变化。社会科学家被训练成着重留意并概括一般规则,因而时常删除例外的东西;历史学家则学习如何以牺牲一般模式为代价去关注具体细节。[英]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页。研究对象的个体性特征,不仅使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划清了界限,也在很大程度上把它与其他人文学科(如哲学)区别开来。
英国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曾经提出,科学是由种种猜想和假说构成的,科学的增长也是通过不断的猜想和反驳来实现的,由经验研究而来的主张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即是否容许逻辑上的反例存在)是判断科学与否的基本依据。参见[英]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可同样是波普尔,在另一本书中却明确宣称:“我愿意维护被历史决定论攻击为陈旧的这个观点,即认为历史的特点在于它关注实际的独特的或特定的事件,而不关注规律或概括。”[英]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14页。许多历史学家不甘止步于简单地“再现过去”,而以探寻历史规律为己任,这样的学术追求当然值得称道,可不同的历史学家总能概括出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抵牾的历史规律,很难说清孰对孰错、孰优孰劣。换言之,作为一门研究过去的(而非当下的)、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个别的(而非普遍的)事物的学问,历史学难以归入科学之列,其研究结论往往是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的。
说历史学是人文之学,还意味着它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具有独特的价值关怀和价值判断,而无法做到“价值无涉”(value free)。自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详加阐述之后,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逐渐成为社会学、经济学乃至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要义。按照这一原则,“实然”(to be)与“应然”(ought to be)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研究者应该无条件地坚持把经验事实的确定同他自己的判断和评价区别开来,否则其研究的合法性和可信性就会遭到质疑。参见[德]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杨富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价值无涉原则的确立,无疑对20世纪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但对于人文学科来说,价值无涉可能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空想。正如李凯尔特所说,自然科学是对规律或普遍概念的联系进行研究,它不必关心文化价值或自己的对象与文化价值的关系;历史学则只有借助价值的观点,才能把文化事件和自然区别开,历史的方法只能是与价值相联系的方法,“没有价值,也就没有任何历史科学”。[德]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6页。或者说,人文学科要像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那样去追求价值无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现代科学话语霸权过度膨胀的一种表征。
三、三部影片中的历史哲学
为了更好地揭示历史学的学科特质,不妨以几部流传甚广的影片为例,对其中蕴涵的历史观念略作分析。透过这些影片,或许可以更生动地理解历史学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和科学不一样的东西。
第一部是日本导演黑泽明于1950年拍摄的《罗生门》(Rashōmon)。影片改编自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罗生门》和《竹林中》,从不同视角讲述了日本平安朝的一起强奸杀人案。武士金泽武弘的妻子真砂被强盗多襄丸强暴,武士也死在丛林中,但关于武士的死因却出现了四个不同的版本。强盗说,他和武士进行决斗,在激战数十个回合后杀死了武士;武士的妻子说,她被强盗蹂躏后又遭到丈夫的鄙薄,在绝望之下用随身匕首刺死了丈夫;武士的鬼魂说,妻子受辱后竟让强盗杀死自己,他心灰意冷,捡起妻子丢下的匕首自杀身亡。目击者樵夫的版本则是:女人让丈夫和强盗决斗,不料两人都武艺平平、胆小怕死,决斗变成了毫无章法的扭打,最后强盗碰巧拔出地上的长刀,刺死了武士。樵夫作为旁观者,他的描述似乎最接近真相,可武士和妻子都说他是死于匕首,樵夫却说强盗是用长刀刺死了武士。在旁人的追问下,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从尚未断气的武士身上拔走了那把值钱的匕首。
从这部影片中,我们可以得到关于历史的若干启示。首先,历史真实总是相对的、暧昧不明的,总是跟权力和利益纠缠在一起的,绝对的历史真实其实很难找寻。影片中关于武士死因的不同版本,都是既揭示又掩盖了部分真相,致使完整的事实难以大白。如今,“罗生门”已经成为一个代名词,指那些当事人按照各自的利益和立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事实真相始终无法水落石出的事件或状态。这正是历史学作为一门关于过去的学问的典型形象。其次,历史学要研究人、研究人类社会,但人与人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信赖也不可预知的,所以很难根据抽象、普遍的人性去猜测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许多影评从抽象人性的角度去分析这部影片,有人说它表达了人性之恶和对人类的悲观,有人却说它宣扬了永恒的人道主义理念,恐怕都过于简单了。再次,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会有不同的心态和思维方式,需要设身处地方能相互理解。观众在欣赏电影之余,也许会对强盗、武士、武士妻子都争相承认自己是凶手感到有些奇怪,如果发生在今天,这些人可能都会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开脱,以免受到法律的惩罚;只有对平安时代的日本社会略有所知,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为掩盖耻辱而篡改事实的心理动机。
第二部是德国电影《罗拉快跑》(Lola rennt,或译《疾走罗拉》),由汤姆·蒂克(Tom Tykwer)导演,1998年出品。这部电影的剧情很有趣。德国姑娘罗拉接到男友曼尼的电话,说他弄丢了黑帮老大的10万马克,如果不能在20分钟内把钱还回去,老大就会杀了他。为了弄到钱营救男友,罗拉开始拼命地奔跑,曼尼则在电话亭不停地打电话借钱。接下来影片分成了三段,每一段展现一种可能的过程和结果。过程一:罗拉向在银行任经理的父亲借钱,但没有借到,她在协助曼尼抢劫商店时被警察开枪打死。过程二:罗拉从父亲的银行抢到了钱,想去阻止曼尼抢劫商店,这时曼尼横遭车祸。过程三:罗拉在赌场赢了10万马克,曼尼也找回了丢失的钱,还掉黑帮老大的钱后,他们自己也成了有钱人。
我们知道,这三个过程当然不会同时发生,最终的结果也只会有一种。导演将三个过程、三种结果同时呈现给我们,用的是时下颇为盛行的电影叙事手法。这部影片告诉我们,在时间长河中沉淀下来的历史无法更改,但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随时都会面临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走向。历史不是一个封闭的王国,在过去真实发生的事情往往并非必然发生或者必然如此发生,而是由众多因素共同型塑而成的。当历史学者被探寻因果关系和历史规律的冲动所主宰时,很容易陷入历史目的论或历史决定论的幻象,认为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固定的目标,相应历史阶段的所有历史现象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发生的,而这些现象的发生又必定会将历史发展的道路引向这一目标。《罗拉快跑》的片头有这样一段字幕:“我们不放弃探索,探索的终点将是它的起点,让我们重新认识探索吧。”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或许不仅要探索历史的因果规律,也应该探索历史的多种可能性。这部影片似乎也为波普尔的前述看法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注脚。
第三部是中国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导演,1995年出品,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影片以“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为背景,讲述某部队大院里一群十多岁孩子们的故事。男主角马小军热衷于用自制的万能钥匙偷开别人家的锁,一天他在一户人家看到一张女孩子的泳装照片,从此迷恋上了她。后来这个叫米兰的女孩真的走进了这群孩子的生活,可她喜欢的是成熟帅气的刘忆苦,马小军既享受和她在一起的时光,又因嫉妒而心烦意乱。马小军找茬和刘忆苦打了一架,又想对米兰做出不轨之事,却未能得逞。后来大家各奔前程,多年后再次相聚,儿时的经历已恍如隔世。
对于历史学者来说,这部电影的独特之处在于,故事分明发生在备受世人瞩目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可男女主角们似乎和这场政治运动没有什么关系。“继续革命”、“斗私批修”、“走资派”、“红卫兵”、“大串联”、“破四旧”……都只是作为背景隐隐约约地出现在影片中,观众们看到的是嘲弄老师、抽烟喝酒、打架闹事、追逐异性,感受到的是青春的朦胧和躁动、暗恋的甜蜜和忧伤、成长的喜悦和烦恼。正如电影海报上所写:“那年夏天,对千千万万个中国人来说,是生命当中最黑暗的时期,但是对这群孩子来说,却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对于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时期,人们往往习惯于接受一种单数的、大写的历史叙述(History),可一旦回到历史场景,我们会发现很多个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普通人的小历史与宏大历史叙述可能是一致的,可能是冲突的,也可能是不相关的。
这三部影片内容迥异、风格有别,却以各自的方式向观众们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历史学的学科特质:它是一门时间之学,引领我们前往过去这个异邦,体察时人的言行举止、思想心态和喜怒哀乐;它是一门叙事之学,用一支生花妙笔,把过去那些形形色色的大事件和小故事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它是一门人文之学,既注重因果关系和历史规律,又尊重每一个时代、国家、群体乃至个人的独特价值。
四、结语
由此反观一百多年来的西方史学历程,可以看到传统史学、新史学、后新史学的发展脉络,也可以看到一条历史学自身特质从“离异”到“回归”的变化轨迹。传统史学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绵延数千年之久,至19世纪的兰克学派发展到顶峰,其特征是以政治史(包括军事史和外交史)为主要内容,以实证主义为导向,以事件为中心,以叙事为表述手段,以线性的、进步的历史时间为坐标。进入20世纪,传统史学遭受重创,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横空出世,以囊括人类各个活动领域的“总体史”为目标,以(广义的)社会史为主要内容,以科学主义为导向(尤其注重对社会科学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以问题为中心,重结构、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以相对静止的长时段、中时段历史时间为坐标。历史学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超乎人们想象的巨大成就,其代价则是历史学的学科特质日渐淡化,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日渐模糊。
最近三四十年来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史学的大旗屹立未倒,社会史的潮流仍在继续,可是一种新的史学流派——文化史(或者为了与过去的文化史相区别而称“新文化史”)——已经异军突起,大有取代社会史成为史学主潮之势。新文化史家从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和种种“后”学(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处汲取灵感,把历史材料视为承载着意义的文本(而不是客观事实的再现),注重通过“深描”(thick description)进行意义的理解和文化的阐释,事件和叙事也从新史学的垃圾箱里重新登上了大雅之堂。参见[英]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这股潮流可以看作新史学的一种自我更新,因为新文化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么是第三、第四代年鉴派史学家,要么曾深受年鉴派的影响;也可以看作对新史学过分社会科学化的一种反动(在此意义上或许可以称之为“后新史学”),因为它处处表现出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让历史学回归人文之学的坚韧努力。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洗礼,历史学已无法返回质朴无华的古典形态。但是作为最古老的一门学问,历史学能否以及如何既借鉴其他学科的优长之处,又保持自身的学科特质和独立品格,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本文原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44153页。
①2001年第1期各文为程歗《社区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对梨园屯一段口述史料的解说》、[美]柯文《义和团、基督徒和神——从宗教战争角度看1900年的义和团斗争》、[法]巴斯蒂《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省的天主教教民》,均为提交于(转下页)
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
一、从《历史研究》两组义和团研究论文说起
当代史学研究队伍的日益扩大和研究成果的迅速累积,使某些研究领域开始呈现“饱和”状态,那些长期为史学界所关注的课题,更因其浩如烟海的文献而让研究者视为畏途。记得很多年前准备本科毕业论文时,指导老师就告诫我们一定要避开诸如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样的选题,因为与之相关的问题要么早被“研究透了”,要么是我们尚无力涉足的。近年来的研究状况似乎印证了这种说法,以《历史研究》为例,据笔者粗略查阅,在2001年之前的十年间几乎没有发表一篇专门探讨义和团运动的论文。当该刊于2001年第1期和2002年第5期接连推出两组质量上乘的义和团研究论文时,的确有些令人惊讶。①
(接上页)2000年10月在山东大学举办的“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另有刘天路、苏位智撰写的会议综述。2002年第5期各文为路遥《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中的民间秘密教门》、[美]何伟亚《道德话语:1900—1901年对北京的劫掠》、[德]狄德满《义和团民与天主教徒在华北的武装冲突》、王如绘《冠、威义和拳举事口号考证》,其中前三篇为提交于2001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举办的“1900年:义和团、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①柯文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著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充分表明他早已超越了传统“事件史”的研究取向。这里的分析仅针对《历史研究》所刊载的论文而言。
两期刊物发表的七篇论文都建立在充分占有和理解史料的基础之上,这是其共同的优点,但它们所体现出的研究视野、方法、取向又分明大相径庭。从其与中国学界以往研究的关系来看,这些论文具有各不相同的特点。路遥和王如绘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传统义和团研究路径所取得的新进展,其特点有二:一是关注义和团运动的过程本身甚于运动背后的社会结构;二是关注本土因素甚于外来因素。与此相比,四位西方学者的研究都对义和团运动中的外来因素表现出更强的兴趣。其中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对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省天主教民的考察、狄德满(Rolf G. Tiedemann)对华北义和团民与天主教徒之间武装冲突的考察都是对事件本身的研究,只是将目光转向了对立两极中的另一极。在关注运动当事人即拳民和教民对事件的理解这一点上,柯文(Paul A. Cohen)的研究颇具新意,但它仍属对事件本身的探讨和再评价。①何伟亚(James L. Hevia)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义和团事件期间西方在中国的劫掠活动及由此引发的西方文明内部的道德反省,不再以事件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而将其作为对西方文明特质进行考察的切入点。程歗对义和团运动所反映出的本土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动态考察,一方面注重本土因素,另一方面着力探究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依据关注本土因素还是外来因素、把事件作为研究对象还是作为研究社会结构的视角两个维度,这七篇论文构成了不同的类型。
表1论文类型
以事件为研究对象以事件为研究视角
关注本土因素路遥文、王如绘文程歗文
关注外来因素柯文文、巴斯蒂文、狄德满文何伟亚文
这两个维度中,前者取决于对历史过程中不同因素的关注,研究者的选择与他们自身对各种因素的熟悉程度密切相关,所以毫不奇怪,三位中国学者都采取了本土视角,而四名西方学者正好相反(因主题和篇幅所限,本文不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论述)。后者则因为对历史事件的不同定位,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研究取向。一种把事件本身当作研究对象、研究实体、研究领域,力求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作出真实的描述,可以称之为“事件史”;另一种则把事件视为历史上社会结构的动态反映,试图挖掘出事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事件成了研究者透视历史的一种视角、一条路径,可以称之为“事件路径”的历史。这里所说的“结构”,正是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长时段”历史的核心问题,它指的是“社会上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固定的关系”[法]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4页。。对于史学家而言,它“也许是一种组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对它的推动也非常缓慢。一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它们迟滞着历史,阻碍着、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进程”。[法]布罗代尔:《论史学》,转引自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20页。打个比方,“事件史”把事件视为一幅画,研究者对它详加探讨,作出种种描述和评论;“事件路径”的历史则把事件当作一扇窗,研究者希望透过它看清窗外的世界。
关注本土因素的“事件史”作为中国史学研究的老传统,曾经产生过许多优秀成果,奠定了义和团研究的坚实基础,但是很难否认,这样的研究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境,尤其是大量的成果积累和相对不足的资料发掘导致了研究空间的日益狭窄。关注外来因素的“事件史”为传统的义和团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但既然仍以事件本身为关注对象,可以设想它或迟或早也会面临类似的困境,因为在把眼光转向西方因素之后,相关的资料不断被发掘,相关的史实不断被澄清,最后也会走到这一步。在笔者看来,只有在研究取向上做出根本性的转变,将关注点从事件本身投向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从“事件史”走向“事件路径”的历史,义和团史这样的传统研究领域才可能真正长久地保持活力、焕发生机。当然,从操作的角度来看,中国学者对于本土因素的理解具有先天的优势,探究外来因素则较多地受到语言、资料、环境等方面的限制,所以立足于本土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程歗所作的本土取向、“事件路径”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启示(因此以下的分析主要以此文为中心,对另外六篇论文暂不置评)。
二、事件作为研究对象抑或研究路径
在史学研究中,事件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最广义的事件可以指历史上的一切活动和现象,但这种含义过于宽泛,难以落实到实际研究中去;如果稍加限制,事件应该具备相对的完整性和独立性,按照通常的说法,应该具备时间、地点、人物、起因、过程、结果等要素;而史学研究通常所称的事件范围更窄,只有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影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者方可成为历史事件,正如辞书中的定义,事件是“历史上或社会上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在年鉴学派史学家的笔下,事件“是短促的时间,是个人接触的日常生活和经历的迷惘和醒悟,是报刊记者报道的新闻”,总之是与他们力图超越的“短时段”密切相联的[法]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1页。。“事件史”所要研究的,正是这些短促的重大事件。
一切过去的活动和现象都是历史,都可以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在平静的历史河流中掀起波澜的“事件”,自然会首先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从中国近现代史的情形来看,重大历史事件长期占据史学界的中心位置,以至于越出通常的史学分支学科(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之外,形成了像太平天国史、义和团史、辛亥革命史、五四运动史这样的独立研究领域。但是仔细探究,事件史其实并不具备学科建制的意义,不足以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分支学科。虽然中国当前的史学学科建制在二级学科(例如中国近现代史)之下将特定事件的历史(例如义和团史)与侧重不同历史面相的专门史(例如政治史)相提并论(称之为“研究方向”),但这些领域是基于不同的标准形成的。以义和团史研究为例,它要考察清政府的政策及其与义和团的关系,这属于政治史的范畴;要探讨义和团、清兵和八国联军之间的武装冲突,这属于军事史的范畴;要研究义和团兴起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这属于经济史的范畴;要关注义和团的降神附体、刀枪不入仪式,这属于文化史的范畴……将事件史与各种专门史混杂起来,容易造成学科体系上的混乱。
更重要的是,把历史事件视为独立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事件史”,极易形成一种封闭态势,从而束缚史学研究的视野。最常见的情形是,事件史的研究对象往往从历史事件缩减为“重大事件”,又进一步化约为政治事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事件史蜕化成了政治史或者政治事件史。布罗代尔即曾指出,虽然把事件史和政治史的名称混用并不恰当,但“事实上,近百年来的史学,除人为的断代史和个别的长时段解释外,几乎都是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法]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2页。事件史与政治史相同构的原因在于,首先,作为研究对象的事件必须具备清晰的边界,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加以研究,政治事件最能符合这种要求。其次,事件中心的研究取向极易导致这样的意识,即事件研究价值的大小是由事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决定的,按照通常的观念,政治事件正是左右历史发展方向的重大事件。再次,政治史是“最古的、最明显的和最容易写的一种历史”转引自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在“新史学”兴起之前,它本就是在中外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事件史对政治事件的极度关注也就很自然了。最后,中国史学界长期受到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支配的现象,也导致了政治事件的重要性远甚于其他事件,事件的政治意义远甚于其他方面的意义(例如“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文化事件的启蒙意义,即长期为它作为一个政治事件的反帝爱国性质所遮蔽)。
相比之下,“事件路径”的历史具有明显的开放性。既然关注的对象从事件本身转向了事件背后的社会制度、关系和结构,事件就势必是一种敞开的事件,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既然事件被定位为一种研究视角、切入点,那么事件本身的范围也必定会极大地扩展,在历史中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只要具有足够的可操作性,都可以作为事件来考察其背后的历史真实,而无须它自身具有多么深远的历史意义(当然,本身具有较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由于在卷入历史进程的程度、反映社会结构的深度、留存资料的丰富度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被纳入研究视野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事实上,20世纪以来政治史本身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再局限于重大政治事件的历史和精英政治人物的传记。60年代兴起的西方新政治史已经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范围,政治的概念被平民化了,凡公共领域皆有政治,甚至家庭和私人领域也事关权力的运用。由于政治和权力内容的扩大,以往被遗忘的民众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等日常生活有了政治意义,并由此进入史册。刘军:《现代西方政治史学的发展与展望》,《光明日报》2001年1月23日。在这样的背景下,事件作为传统政治史的研究对象已经失去了神圣的光环,转而向社会底层和日常生活敞开,这也进一步促使事件在史学研究中的位置发生转变。
就义和团运动这样已经被充分甚至“过度”研究的事件而言,在没有更多资料被发掘出来的情况下,研究中的每一个新进展都必定伴随着研究视域在某种程度上的敞开,而这也就意味着对作为“事件史”研究对象的事件概念的偏离。近年来西方学者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两部力作,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柯文的《历史三调》,都表明了这一点。周锡瑞声称自己所做的是关于义和团起源的研究,试图“尽量客观地理解运动的源流、时代背景、发生的原因以及运动发展的逻辑性”,这与中国学者以往的研究别无二致。但是他放弃了过去从组织源流入手的研究方法,转而考察义和团的仪式以及蕴育它的华北农村的文化习俗、社会经济环境、自然生态以及政治背景,这就在研究视角和思维方法上与传统研究大异其趣,义和团运动不仅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存在,而且作为探究历史社会深层结构的一个透视点支撑着整个研究。柯文的著作具有更强烈的理论震撼力,针对以往的义和团研究,他提出既要关注历史对于当事人的真实意味(“作为经历的义和团”),又要对历史神话化的倾向保持清醒的认识(“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从而突破了把历史事件仅仅当作事件来加以研究的“事件史”的局限性。事实上,即便是最表层的“作为事件的义和团”,柯文的描述也已经超出了传统事件史的范畴,因为义和团所反映的深层社会结构已被纳入其间,成了故事讲述的一部分。
前述程歗的论文也是如此。作为全文论述线索的那段梨园屯口述史料早在1982年已为义和团研究者们记录下来,却并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在作为“事件史”的义和团研究中,它只是教、民冲突导致村民反抗的众多记载之一,一来有助于澄清梨园屯玉皇庙事件的具体史实,二来不过是印证了关于义和团起源的“教逼民反”、“官逼民反”的简单说法。但是在将目光从事件本身(无论是义和团这一大事件,还是发生在梨园屯的小事件)转向作为义和团运动背景的乡村社会结构之后,作者注意到了这段史料所反映出的社区精英的行动逻辑,通过对这种逻辑的追根溯源,他找到了历史悠久的民间组织与突发性的义和团运动之间的重要中介,即“那些在变动了的晚清政治秩序中参与反洋教的乡土社会的精英群”,其联合和行动重塑了各自主导的那部分组织和文化,最终通向了义和团的起源并规定了运动自身的逻辑。和周锡瑞一样,程歗也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为对义和团运动之起源的探讨,却在研究过程中揭示出动态社会结构的深层真相,从而超越了传统“事件史”的研究范畴。
从“事件史”转向“事件路径”的历史,还意味着看待“时间”的不同方式。只有时间的推移才能使过去发生的事件成为历史,而事件本身又只有在时间之流中才能成为事件。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兴起之后,尤其是来自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结构主义对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古老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些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分野,例如历史学关注过去而社会科学关注现在,历史学探究过程而社会科学探究结构,历史学是历时性的研究而社会科学是共时性的研究,历史学重描述而社会科学重解释,等等。传统的“事件史”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源流考释、过程描述、影响分析,时间是一种线性的流动,历史事件就在这种流动中得以发生。在布罗代尔眼中,传统史学的历史时间观是单一的、表层化的,事件史所拥有的不过是短促而快速的时间,在他创设的以长时段为中心的历史时间等级体系中是微不足道的。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18页。但“事件路径”的历史则是社会科学介入历史学的直接后果,它不再把历史事件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在历时性的事件过程考察之外,将相对而言更具稳定性的共时性社会结构(这也正是年鉴学派所追求的长时段历史的主要内容)纳入研究视野,事件本身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其意义更多地在于对深层、隐蔽的社会历史真相的反映。时间不仅以其绵延之维使事件得以发生,其意义更在于为社会结构在事件中展现自身提供了可能性。这样,“事件路径”的历史就可以有效地将历史学的历时性研究取向与社会科学的共时性研究取向结合起来,时间既是流动的(就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而言),又是相对凝固的(就结构在事件过程中的展示而言)。
三、“事件路径”的历史何以可为
在引入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将研究旨趣从事件转向结构之后,为什么还必须对事件予以关注呢?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结构自身不会说话,只是静静地躺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之流中,各种各样的事件则是促使结构显露自身的重要契机。任何事件都受到各种制度、关系和结构因素的或明或暗的制约,绝不是凭空发生和任意发展的,即便是极具偶然性的事件,偶然性本身也只能促发事件,而不能决定事件发生的方式、发展的走向和最终的结局,这些仍要受制于制度和结构因素。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各种力量、各种因素纷纷登台亮相展示自己,从而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关于社会结构的动态图景(柯文对“作为神话的义和团”的研究还表明,事件不仅是事件发生之时社会结构的表演舞台,甚至可以为事件结束多年以后的社会结构提供展示自己的空间)。所谓“事件路径”,其意义首先就体现于此。
其次,事件本身就是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人们常将社会结构比作一座建筑,但这种建筑必须在人们持续不断的社会行动中才得以存在,正是一个个事件(最通常意义上的事件,而不是传统事件史以历史意义作为识别标志的“历史事件”)的动态过程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相对稳定和静止的社会结构。事件既促使深层的历史事实浮出水面,其本身又参与历史事实的建构。例如1905年废科举这一事件,就在这双重意义上成为极好的研究视角:一方面使传统社会结构得以显现(传统社会结构中不同阶层之间的制度化流动、知识者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化关联,恰恰是在科举制废除之后才被人们充分认识到的);另一方面又促成了这一结构的瓦解和向新结构的转型。“事件路径”的历史,就是要把历史事实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透过对事件的深入考察揭示历史事实的深层真相,即历史河流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程歗在论文中指出:“我们过去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地考察了以特定区域为依托的各种民间组织,是怎样从历史的深处‘走’出来的;现在,我们则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些组织是怎样在变化了的区域格局中‘动’起来的。换言之,需要在‘区域’和‘组织’之间寻找新的可以涵盖和沟通两者的研究角度,更具体地说,是要找出一股对特定区域的多层组织及其所属民众进行社会动员的力量。”这就清楚地体现出将历史事实、社会结构视为一个动态过程加以探讨的理论自觉。民间组织和蕴藏在它背后的民间文化(与义和团运动这一突发的、短时段的事件相比,它们正是稳定的、长时段的结构性因素)都不是静止不动的,通过“社区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这样的动态过程,它们一方面向史学研究者们显露出自己的真实面貌,另一方面引领着自己的发展变化,导向了似乎是突如其来的义和团运动。
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叫魂》一书[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堪称这种“事件路径”的历史研究的典范之作。作为叙述主线的叫魂事件,最终证明不过是一连串子虚乌有的妖术指控,是“一出追求幻觉的历史闹剧”杨念群:《在神秘叫魂案的背后》,《读书》1996年第8期。,然而在作者笔下,它却成了帝制中国官僚君主制中两种权力角逐的舞台,来自皇帝的专制权力与来自官僚的常规权力既密切关联又彼此冲突,它们在对叫魂事件的处理过程中纤毫毕现地展示出各自的利益、能量和特征,从而使官僚君主制中最深刻的内涵大白于天下。从动态而不是静态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通过事件过程来透视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实际运作,“事件路径”的历史的这一本质特征在孔飞力的著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实际上,在历史学借鉴社会科学概念、理论、方法的同时,社会科学也正努力引入历时性的研究视角。在社会学、政治学等关注制度和结构甚于事件过程的学科领域,事件既作为动态的社会事实又作为透视社会结构的切入点,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学家孙立平在考察国家与农民关系时提出的“过程—事件分析”策略,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他注意到在当前农村中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事实,一方面是国家权力在农村的弱化和撤退,农村基层组织陷于涣散与瘫痪;但另一方面,国家的意志在农村仍能得到贯彻执行,主要体现在征收定购粮、落实计划生育等棘手的行政任务仍能较好地完成。这种矛盾反映出静态的结构研究存在的局限,孙立平敏锐地称之为“结构上的不可见性”,即在静态的结构中,事物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事物在遭遇不同情境时可能发生的种种变化,都并不是潜在地存在于既有的结构之中。相反,只有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这些东西才可能逐步展示出来。所以他尝试从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事实,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并将过程看作是一种独立的解释变项或解释源泉”,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视为一种动态的实践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态的结构,从而对他观察到的矛盾现象作出了成功的解释。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载《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1),福州:鹭江出版社,2000年。之所以不避繁复地详细介绍一位社会学家的论述,是因为这段话完全可以用来说明通过“事件路径”进行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区别仅在于研究者所关注的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社会结构。
又如,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问题近来成为政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村民自治这种新制度(具体到每一个村庄则以村委会选举这一事件的面目出现)为研究者提供了深入观察农村政治结构的机会。在村庄这样的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中,政治结构、政治关系往往为农民的日常生活、日常社会关系所掩盖,而以村委会选举为核心环节的村民自治,则使村民或主动或被动地直接卷入国家政治生活,从而使隐蔽的乡村政治结构、政治关系在研究者面前显现出来。从当前村民自治研究的大量实例来看,这正是一种“事件路径”的研究,村委会选举这样的事件成了农村基层政治研究行之有效的视角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