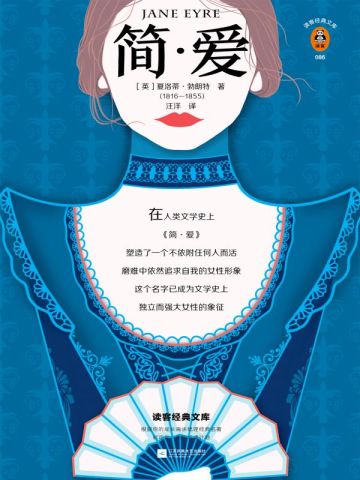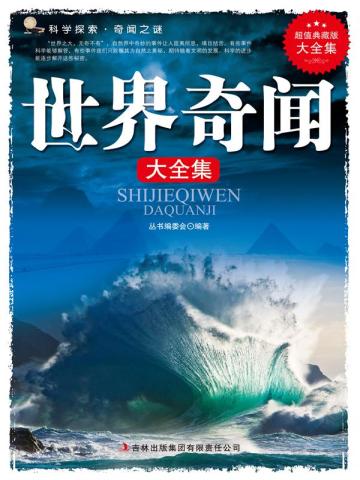战争与和平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丛书名: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书名:战争与和平作者:(俄)列夫·托尔斯泰出版社: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版次:2001年月第版印次:2001年月第次印刷开本:字数:千字书号:ISBN7-5312-1364-8/I11定价:00:00元
第一部
1
“好啊,公爵,热那亚和卢加成为波拿巴家的地盘了。不过我要告诉您,如果您还对我说我们没有战争,如果您还袒护这个敌人的任何卑劣行为和他造成的惨祸,那么我就不再理您了,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了。我把您吓坏了,是吧?好了,我们坐下来谈谈吧。”
1805年7月,非常出名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她是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后的女官和亲信,在迎接第一个来赴晚会的达官要人瓦西里公爵时说了这些话。安娜·帕夫洛夫娜咳嗽了好几天,她自己说她患的是流行性感冒。请贴是当天早晨由穿红制服的听差送出的,内容全都一个样:
“伯爵(或公爵),如果您没有其他更好的消遣,您如果不在意与我这个可怜的病人共度一个晚间,请于今晚七至十时惠临舍下,将非常欢迎。安娜·舍列尔。”
“我的天!”进来的公爵答道,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他身穿绣花朝服,脚穿长统袜和半高统鞋,胸前戴着几枚明星勋章,扁平的脸上带着喜悦的表情。
他法语说得很漂亮,语调既文静,又很具长者之风,那是
只有长期混迹于上流社会和宫廷的重要人物才会有的腔调。他
走到安娜·帕夫洛夫娜面前,俯下他那洒了香水的光光的秃头,
吻了吻她的手,就轻松自得地坐到沙发上。
“您先告诉我,您好吗?亲爱的朋友。好让我放心。”他没
有改变腔调。但是从他彬彬有礼、体贴关怀的腔调中,透露出
淡漠甚至嘲笑的意味。
“精神受折磨,身体怎么会好呢?..我们这年头,稍有
感情的人,又怎能心安理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你整个
晚上都待在我这里,好吗?”
“那英国公使馆的招待会呢?今天是星期三。我得到那里
去一下,”公爵说,“我女儿就要来接我,和我一同去。”
“我还以为今天的招待会取消了呢。说实在的,这些招待
会啦,焰火啦,都烦死人了。”
“要是他们知道了您的心意,招待会就会取消的。”公爵
说,他像一挂上足了弦的钟,习惯地说出连他自己也不希望别
人相信的话。
“不要折磨我了。告诉我,对于诺沃西利采夫的紧急报告作了什么决定?您都知道的。”“怎么对您说呢?”公爵说,他的语调冷冰冰的毫无趣味,“作了什么决定?他们决定:波拿巴既然破釜沉舟,看来我们也只得背水一战了。”
瓦西里老公爵说起话来总是懒洋洋的,像演员背旧台词似
的。而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则相反,别看她已经是四十岁
的人,却生气勃勃,好激动。
她为人热情。她有时甚至不愿这样做,但为了不让熟人失
望,她还是做了热心人。安娜·帕夫洛夫娜脸上经常含着微笑,
这虽然和她那姿色已衰的面容不相称,但就像娇惯的孩子一样,表示她经常意识到自己小小的缺点,可是她不愿,也不能,而且认为没有必要去改正。
在谈论政治事件时,安娜·帕夫洛夫娜激动起来。
“哎呀,再别对我提奥地利了!也许我什么都不懂,但是奥地利从来不愿意打仗。它把我们出卖了。只有俄罗斯才是欧洲的救星。我们的上帝知道他的崇高使命,并且忠于他的使命。这是我唯一相信的东西。我们至善至美的皇帝将担负起世界上最伟大的任务,他是那么受人欢迎,那么仁慈,上帝是不会见弃这样的人的,他一定能完成他的使命———镇压革命这个丑东西,现在有这个刽子手做革命的代表,革命就变得更加可怕了。只有我们才应当讨还殉难者的血债。我们还能指靠谁呢,我问您?..满身铜臭的英国不能理解亚历山大皇帝的精神是多么伟大。他们不能理解我们皇上的自我牺牲精神,我们皇上一点不为自己着想,他只想为全世界谋福利。可是他们答应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答应。就是答应了什么,也不会说话算话的。普鲁士已经公开说,波拿巴是不可战胜的,全欧洲都没办法对付他..不论是谁的话,我都不相信。普鲁士中立,是为了骗人。我只相信上帝和我们的君主。他一定能拯救欧洲!..”她突然停住了,对自己的急躁感到不好意思。
“我想,”公爵笑着说,“如果不是派温岑格罗德去,而是派您去,您一定会强迫普鲁士国王同意的。您的口才太好了。给我来一杯茶,好吗?”
“马上就来。随便说一下,”她平静下来了,“今天我这里要来两位非常有趣的人物,一位是莫特马尔子爵,法国最显赫的名门望族之一。他是一个很好的流亡者,真正名副其实的流亡者,另一位是莫里约神甫;您认识这位聪明绝顶的人物吗?皇帝已经接见过他了。您听说了吗?”
“啊!能见到他们,我太高兴了,”公爵说,“请您告诉我,”他接着说,好像偶然想起一件事,并且漫不经心地说起来,而实际上这正是他这次来访的主要目的,“听说守寡的太后想委任丰克男爵担任驻维也纳使馆的一等秘书,是真的吗?这人可不行。”
瓦西里公爵想给他的儿子谋到这个差事,可是别人却想通过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替男爵弄到这个位置。
安娜·帕夫洛夫娜几乎闭上了眼睛,意思是说,任何人都不能评论太后愿意做的或者喜欢做的事。“这可是太后的妹妹举荐的,”她说话时,声调既哀愁又淡漠。安娜·帕夫洛夫娜一提起太后,脸上就忽然现出无限的忠诚和由衷的敬意,同时还伴着淡淡的哀愁。她说,太后陛下对丰克男爵很器重,于是她的眼中又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
公爵沉默着。安娜·帕夫洛夫娜凭她特有的宫廷的和女人的圆滑和灵通,想一面指责公爵,因为他竟敢批评那个被举荐给太后的人,一面又安慰他。
“顺便聊聊您的事吧,”她说,“您可知道,自从您的女儿露面以来,人们全被她迷住了,大家都认为她是位大美人。”公爵鞠了一躬,表示敬意和感激。
“我常想,”安娜·帕夫洛夫娜沉默了一会儿后接着说,并且向公爵跟前凑了凑,对他亲切地微笑着,意思是说政治和社交的谈话已经结束,现在可以谈心了,“我常常想,生活中幸福常常分配得不公平。凭什么您命中就该有这么两个好孩子(除去您的小儿子阿纳托利,我讨厌他),”她把眉毛一挑,不
容置辩地插了一句,“为什么赐给您这么可爱的两个孩子呢?可是您却不赏识他们,所以您不配有这样的子女。”于是她兴致很高地微微一笑。“有什么办法呢?别人肯定会说我不是做好父亲的料。”公爵说。
“别开玩笑。我想和您说正经的。我对您的小儿子不大满意。这话只可在您我之间说说(她脸上又露出哀愁的表情),有人在太后面前提到他,并且为您惋惜..”
公爵没有回答,她也不说话,意味深长地望着他,等着回答。瓦西里公爵皱了皱眉头。
“我有什么办法呢?”他终于说道,“您是知道的,为了让他们受教育,我做了当父亲的所能做的一切,可是结果却培养了一对傻瓜。伊波利特这个傻瓜多少还算安分,而阿纳托利可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小子了。这就是他们唯一不同的地方。”他比平时更不自然,更兴奋地微笑说,笑得嘴边打成皱纹,既俗气又让人生厌。
“为什么这些孩子偏偏赐给您这样的人家?如果您不做父亲,我就没有什么可责备您的了。”安娜·帕夫洛夫娜说,她抬起眼来,露出沉思的样子。
“我是您的忠实奴仆,我的孩子是我的负担。该我负担的事,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不言语了,摆出一切都愿意听从于命运的摆布的样子。
安娜·帕夫洛夫娜也沉默不语。
“您不想给您那放荡的儿子阿纳托利娶亲吗?据说,”她说,“老姑娘都有说媒的习惯。我还没有觉得自己有这个毛病,但有一个姑娘..,她陪伴老父亲,生活很不幸,名叫博尔孔斯卡娅。”瓦西里公爵虽然具有上流社会人士特有的敏捷的悟性和记性,但对她的话只是晃晃脑袋,表示可以考虑,却没有回答。
“您可知道,这个阿纳托利每年要花掉我四万卢布。”他说,他无法克制他那忧愁的思绪。他沉默了一会儿。
“照这样下去,五年后会怎么样啊?这就是父亲的好处。您那位公爵小姐,她有钱吗?”
“她父亲很有钱,但非常吝啬。他住在乡下。您知道,这位有名的博尔孔斯基公爵在先帝在世时就退伍了,绰号叫‘普鲁士王’。他人聪明极了,就是乖僻,而且难处。小姐非常不幸。她有个哥哥,是库图佐夫的副官,不久前刚娶了丽莎·梅南,他今天要到我这里来。”
“听我说,亲爱的安内特,”公爵说,他忽然抓住对方的手,并且不知为什么向下拉了拉,“请多帮忙,我永远是您的最忠实的奴仆。她门第好,又有钱。这就是我所需要的。”
于是,他拿起女官的手吻了吻,接着,他靠到圈椅上握着女官的手,而眼睛却看着别的地方。
“等一下,”安娜·帕夫洛夫娜沉吟着说,“我今天和丽莎(博尔孔斯基的妻子)谈谈。也许事情会成功的。我也做起媒来了。”
2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客厅里渐渐挤满了客人。来赴会的全是彼得堡的达官要人,这些人尽管在年龄和性格上各不相同,但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却是一样的;瓦西里的女儿———美丽的海伦来了,她是来接父亲一起去赴领事馆的招待会的。她佩戴着成绩优秀的女中学生所特有的那种奖章,穿着赴舞会的服装。年轻、有名、小巧玲珑的公爵夫人博尔孔斯卡娅,据说是彼得堡最迷人的女人,也来了,她是去年冬天出嫁的,因为怀孕,已经不在盛大的交际场所露面,但是小的招待会还是参加的。瓦西里公爵的儿子伊波利特带来由他引见的莫特马尔;来赴会的还有莫里约神甫以及其他许多人。
“您还没见过我的姑母吧?”安娜·帕夫洛夫娜对每一位来客说,然后郑重地领着客人去见一位头上扎着高高的花结的小老太太;安娜·帕夫洛夫娜一边介绍客人的姓名,一边把视线缓缓地从客人移向姑母,然后就走开了。
每个客人都向这位谁也不认识、谁也不感兴趣的姑母行礼问候一番。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他们的问候露出哀愁的、庄重的神情,默默地赞许。姑母对每位客人全说一样的话,谈到他们的健康,谈到自己的和太后的健康,“谢天谢地,太后今天好些了。”每位前来请安的人,为了表示礼貌,都不露出着急的样子,但却怀着履行沉重的义务之后的轻松之感离开老太婆,整个晚上再也不到她跟前去了。
年轻的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带着一个丝绒绣金的手提包,里面放着她的针线活儿。正像非常惹人喜爱的女人常有的那样,她的缺点———翘嘴唇和半张开的嘴———仿佛成为她的独特的美。不管谁看到这个精神饱满、活泼可爱、虽然怀孕然而轻松愉快的少妇,都感到快乐。老年人和抑郁苦闷的年轻人,只要和她在一起待一会儿,谈几句话,就好像觉得他们也变得和她一样了。凡是和她说过话、看见她一说话就露出妩媚的微笑,看见她经常雪白闪亮的牙齿的人,就会觉得他那一天受到格外的宠幸。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娇小的公爵夫人提着针线包,迈着急促的小步,一摇一摆
地绕过桌子,快活地整了整衣裳,就在银茶炊旁的沙发上坐下
来,仿佛不管做什么,对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是一种娱乐。
“我把针线活儿带来了。”她一面打开手提包,一面对大家说。“您瞧,安内特您真是会开玩笑,”她转身对女主人说话,“您说是一个小小的晚会。我穿得太不合适了。”她伸开两臂,让大家看她那件镶花边的雅致的灰色衣裳,胸口以下系着一条宽宽的缎带。“放心吧,丽莎,您仍旧是最漂亮的,”安娜·帕夫洛夫娜回答说。
“您可知道,我的丈夫,”她继续用同样的腔调对一位将军
说,“就要离开我了,战争到底有什么意思?让他去送死。”她
对瓦西里公爵说,不等回答,又转身和公爵的女儿———美丽的
海伦说话。
“公爵夫人是多么可爱呀!”瓦西里公爵低声对安娜·帕夫
洛夫娜说。
小公爵夫人刚到不久,进来了一个肥肥胖胖的魁伟青年,
他戴着眼镜,头发剪得短短的,穿着时髦的浅色裤子,领子是
折角的,又高又硬,礼服是咖啡色的。这个肥胖的年轻人是叶
卡捷琳娜女皇时代赫赫有名的大官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他
还没有供过职,才从国外留学回来,这是他初次涉足社交界。
安娜·帕夫洛夫娜像对待客厅里最低一级的客人那样,对他点
点头。虽然这是最低一级的礼节,可是当皮埃尔刚一进门,安
娜·帕夫洛夫娜就露出惊慌不安的神色,仿佛看见一个不该在
那个地方出现的庞然大物似的。皮埃尔的确比客厅里其他男人都高大些,但这种惊慌不安却来自他那既聪明而又羞怯、既敏锐而又自若、不同于客厅中其他人的眼神。
“皮埃尔先生,谢谢您的光临。”
安娜·帕夫洛夫娜领他去见姑母时,边说边惶恐地向姑母递了个眼色。皮埃尔含混不清地嘟囔了一句,一直用眼睛搜寻什么。他兴致勃勃,满面春风,微微含笑,像对一个熟朋友似的向矮小的公爵夫人鞠了躬,随后走到姑母跟前。安娜·帕夫洛夫娜的不安并不是没理由的,因为皮埃尔没有听姑母讲完太后的健康情况,就离开了她。安娜·帕夫洛夫娜连忙用话拦住他。
“您认识莫里约神甫吗?他这个人,很有趣..”她说。
“是的,我听说过他那个谋求永久和平的计划,非常有趣,但不大可能实现。”
“您是这样想的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她本想应酬几句,就去尽她做女主人的职责,可是皮埃尔又做出一个不礼貌的举动。刚才他没有听完姑母的话就走开了,现在他又用话缠住想离开他的对谈者。他低着头,叉着腿,开始向安娜·帕夫洛夫娜证明,他为什么认为神甫的计划是空中楼阁。
“咱们以后再谈吧。”安娜·帕夫洛夫娜微笑着说。
她摆脱了这个不经世事的年轻人,又去履行她女主人的职责,继续东听听西望望,哪里不起劲,就到哪里鼓动一下。安娜·帕夫洛夫娜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时常走到发生冷场或者谈得太多的人堆跟前,插进三言两语或者把客人调动一下,于是谈话机器又节奏均匀、彬彬有礼地开动起来。但在她这样照料的时候,仍旧可以看出她特别不放心皮埃尔。皮埃尔不论是在听莫特马尔周围的人们谈话,或者走到有神甫在场的那一堆人里,她都关切地看着他。安娜·帕夫洛夫娜的这次晚会,对于一向在国外留学的皮埃尔说来,是第一次在俄罗斯见到的晚会,他知道整个彼得堡知识界的人才都聚集在这里,他像孩子走进玩具店一样,左顾右盼,目不暇给。他一面望着人们的面孔,一面盼望听到奇谈高论。最后,他走到莫里约跟前,他觉得这里谈得很有意思就停下来,像一般年轻人喜欢做的那样,等待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
3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很成功。只有老姑母和坐在她身旁的一位老妇人显得不大谐调。客人们分成三组。在男人占多数的一组里,神甫是中心人物。年轻人那一组的中心人物是瓦西里公爵的女儿———美人海伦公爵小姐和小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第三组是以莫特马尔子爵和安娜·帕夫洛夫娜为中心。
子爵眉清目秀,很有礼貌,是个可爱的年轻人。不论什么场合他都十分谦让,俯首听命。安娜·帕夫洛夫娜显然是要利用他来款待客人。莫特马尔那一组立刻谈起昂吉安公爵被害的经过。子爵说,昂吉安公爵死于自己的宽宏大量,而波拿巴的怨恨是别有原因的。
“真是这样吗?子爵,给我们讲讲吧。”安娜·帕夫洛夫娜说。子爵鞠躬表示服从,并且谦恭有礼地微微一笑。安娜·帕夫洛夫娜让客人把子爵围在中间,来听他讲故事。“子爵本人就认识那位公爵。”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一位客
人低声说。“子爵特别会讲故事。”她对另一个人说。“他出身高贵。”她对第三个人说。子爵嘴角含着机智的微笑,就要开始讲故事了。“到这里来,亲爱的海伦。”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坐在稍远的另一组的中心人物,美丽的公爵小姐海伦说。
海伦公爵小姐微微含笑;她站起来,脸上自始至终带着一种绝代佳人似的微笑。当她走过时,她那有常春藤和青苔花边的素白礼服发出的声音,白净的肩膀、光泽的头发和璀璨的钻石都光彩夺目,她一直朝安娜·帕夫洛夫娜走去,眼睛不看什么人,可对所有的人都笑容可掬,好像她把欣赏她的身材、丰腴的双肩和装束入时的十分裸露的胸脯和背脊的美的权利慷慨大方地赐与每个人,好像给舞会带来全部光彩的也是她。海伦的确是太漂亮了,她身上不但没有卖弄风情的意味,而且相反,仿佛她为自己无可置疑的、其魅力之大足以征服任何美貌,感到不好意思。好像她宁愿减少自己的美的魅力,可就是办不到。
“太漂亮了!”看见她的人都这么说。当她在子爵对面坐下,仍然带着始终不变的微笑注视着他的时候,子爵仿佛被一件不平凡的东西所惊倒,他耸了耸肩,垂下眼睛。
“夫人,当着这么多人,我会出丑的。”他低下头,微笑着说。
公爵小姐把裸露的丰满的臂靠在小桌上,含笑等待着。在讲故事的全部时间,她直挺挺地坐着,时而看一眼轻轻地倚在桌边的丰满的美丽的手臂,时而整整钻石项链,看看更加美丽的胸脯;她不时地整理衣服的皱褶,当故事讲到动听的时候,她回头望望安娜·帕夫洛夫娜,马上露出和女官一致的表情,然后又安闲自在地浮出容光焕发的微笑。娇小的公爵夫人也跟着海伦从茶桌旁过来了。
“我要干活了。”她说。“怎么了,您在想什么?”她转身对伊波利特公爵说,“帮下忙,请把我的手提包拿来。”
公爵夫人微笑着跟大家说话,人们给她腾出位子,她坐了下来。“现在我坐好了,”她说了一句,就请求开始讲故事,另外还一边做着针线活。
伊波利特公爵把手提包递给他,跟着她走过去,把圈椅移得离她更近一些,在她身旁坐下。
让人吃惊的是,这位可爱的伊波利特和他美丽的妹妹长得非常相像,而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尽管相像,但他却丑得出奇。他的脸型和妹妹的一样,可妹妹那种乐天的、自满自足、洋溢着青春活力、永驻不变的微笑和体态非凡的古典美,使她光艳逼人;相反,哥哥那副面容却呆滞阴沉,总有一种自以为是和不满的表情,身子又瘦又弱。眼睛、鼻子、嘴巴挤在一起,变成一副莫名其妙、枯燥无味的鬼脸,而手脚永远摆不出自然的姿势来。
“讲鬼的故事吗?”他说。他在公爵夫人身边坐下,连忙戴上长柄眼镜,仿佛没有眼镜他就不能说话似的。
“不是,不是。”讲故事的人吃了一惊耸耸肩说道。
“我最讨厌有关鬼的故事了。”伊波利特公爵说。
伊波利特说话非常自以为是,叫人弄不清他的话是非常聪明呢,还是非常愚蠢。他穿一件深绿色的礼服,还有长统袜和半高统皮鞋。
子爵讲得很不错:昂吉安公爵秘密到巴黎去会乔治小姐,当场碰上也受到这位女演员垂青的波拿巴;拿破仑在遇见公爵的时候忽然犯昏厥症晕倒了,于是他就落入公爵手中,公爵并没有把波拿巴怎么样,可后来波拿巴却将公爵处死来报答公爵的宽宏大量。
故事很动听而有趣,尤其是讲到两个情敌忽然彼此认出对方的时候。女士们个个都很激动。“真妙!”安娜·帕夫洛夫娜说,一面回头用探询的目光望了望娇小的公爵夫人。
“真是好极了!”娇小的公爵夫人低声说道。同时,把针插在手工上好像是表示故事太有趣,太美妙,听得她连活都做不下去了。
子爵非常欣赏这无言的赞许,感激地微微一笑,又接着讲下去;可是,安娜·帕夫洛夫娜总在留意使她担心的那个年轻人,她忽然发现不知为什么他和神甫谈得太热烈,声音太高了,于是她连忙前去援救。果然不错,皮埃尔竟然和神甫谈起政治均势问题,神甫显然对这个年轻人的天真热情很感兴趣,就对他大谈起他那套得意的理论。两个人都很兴奋,旁若无人,这使安娜·帕夫洛夫娜不高兴。
“办法是欧洲的均势和民权。”神甫说,“只要有俄国这样以野蛮落后闻名于世的强国,大公无私地出来领导以谋求欧洲均势为宗旨的联盟,全世界就有救了!”
“那么您怎样得到这种均势呢?”皮埃尔刚想说话,安娜·帕夫洛夫娜恰好走过来,严肃地瞅了皮埃尔一眼,问那位意大利人可受得了本地的气候。意大利人突然改变了脸色,虚假地应酬起来。
“能参加你们的社交活动,我很荣幸。现在还没有工夫想到气候呢。”他说。
安娜·帕夫洛夫娜为了便于监视,让他们加入人多的那一组。
这时客厅里又来了一位客人。这位新来的客人就是年轻的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也就是小公爵夫人的丈夫。博尔孔斯基公爵中等身材,是一个非常英俊潇洒的青年,面目清秀,神色严峻。他浑身上下,从倦怠烦闷的眼神到从容不迫的步履,和他娇小活泼的妻子正好形成尖锐的对比。看来,客厅里所有的人他全认识,而且使他感到厌烦。尤其厌烦他的妻子。他做了一个鬼脸,向她背过身去。他吻了吻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手,接着眯起眼睛朝在场的人扫视了一下。
“您要去打仗吗?公爵。”安娜·帕夫洛夫娜说。
“库图佐夫将军希望我做他的侍从官。”
“您的太太丽莎怎么办?”
“她到乡下去。”
“您怎么好把您那可爱的夫人从我们身边带走呢?”
“安德烈,”他的妻子说,她对丈夫说话和对其他男人说话一样都用那种娇滴滴的腔调。“子爵给我们讲了一段乔治小姐和波拿巴的故事,真是好极了!”
安德烈公爵眯起眼睛,转过身去。安德烈公爵一进客厅,皮埃尔就一直十分关注他,这时他走上前去拉住他的手。安德烈公爵头也不回,皱起眉头,露出一副怪相,表示对碰到他的手的人不耐烦,但是当他一回头看见是皮埃尔,脸上立即露出了和蔼而愉快的笑容。
“嗬,想不到!..连你也到上流社会的交际场里来了!”他对皮埃尔说。
“我知道您会来。”皮埃尔答道,“我到您府上吃晚饭,”为了不致打扰子爵讲故事,他低声补充说,“可以吗?”
“不,不行,”安德烈公爵笑着说,同时紧握对方的手,表
示不必多问。他还想说些什么,可这时瓦西里公爵和他的女儿
起身告辞,男客们全都起身给他们让路。
“请您原谅我,亲爱的子爵。”瓦西里公爵对那个法国人
说,亲热地拉住他的袖口往椅子上按了按,叫他不要起来。“叫人头痛的领事馆的招待会毁掉了我在这里的快乐,并且打
断了您的故事。离开您这美妙的晚会,太遗憾了。”他对安娜·
帕夫洛夫娜说。
他的女儿海伦公爵小姐,轻轻提着衣裙褶,从椅子中间走
过,她笑得更加妩媚了。当她从皮埃尔身旁经过时,皮埃尔差
不多是用惊奇的、狂喜的目光注视着这位美人。
“好漂亮。”安德烈公爵说。
“真漂亮。”皮埃尔说。
瓦西里公爵走过时,抓着皮埃尔的手,转身对安娜·帕夫
洛夫娜说话。
“请您开导开导这只熊吧,”他说,“他在舍下住了一个月,
我这是第一次在交际场中看见他。年轻人是很需要聪明女士们
的社交界的。
4
安娜·帕夫洛夫娜微微一笑,答应照管皮埃尔,她知道皮埃尔的父亲和瓦西里公爵是亲戚。那个原先坐在老姑母身旁的老妇人,赶忙站起来,在前厅赶上瓦西里公爵。刚才装出来的兴致从她脸上消失了。她眼睛里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和善的眼睛里满含着眼泪。
“公爵,关于小儿鲍里斯的事,您办得怎么样了?”她在前厅边追边问道,“我在彼得堡不能再住下去了。请您告诉我,有什么消息可以带给我那可怜的儿子吗?”
瓦西里公爵不愿搭理她,但她却微笑着,抓住他的手不让他走掉。“您只要向皇上说一句,他就可以调到近卫军去了,这在您算不了什么。”她请求道。
“请您相信,我一定会尽力,公爵夫人。”瓦西里公爵答道,“但是求皇上我有困难。我劝您最好还是通过戈利岑公爵去找鲁缅采夫,这么办比较明智。”
老妇人名叫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出身于俄国最显贵的家族之一,但现在已经落魄。她这次来是想为她的独生子在近卫军中谋个差事。她来参加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是为了见瓦西里公爵。瓦西里公爵的话使她吃了一惊,她有点怨恨,但很快她又露出微笑,把瓦西里公爵的手抓得更紧了。
“公爵,”她说,“我恳求您看在上帝的份上,为小儿办妥这件事吧,我会永远把您当作恩人。”“请您不要生气,您答应我吧。我求过戈利岑,他拒绝了。请您发发慈善心吧。”她说,极力陪着笑脸,但是她的眼睛里却含着泪水。
“爸爸,我们要晚了,”等在门口的海伦公爵小姐转过头来说道。
瓦西里公爵知道权势不能随便使用,如果有求必应,那么很快他就无法为自己而向别人求情了。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再三恳求,使得他觉得仿佛受到良心的责备。她提醒他一个事实:当初走上仕途的时候,他曾受过她父亲的提携。而且,这位母亲,为了孩子,不达目的会决不罢休的。
“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他用亲昵而枯燥的腔调说道,“您所希望的,我几乎不可能办到;但我要办到这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您的儿子会调到近卫军里去的,我向您保证。您满意了吧?”
“我亲爱的,您太好了!您是多么仁慈的人啊!”他要走开。
“等一等,还有两句话。等他调到近卫军以后..”她犹豫起来。“您和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库图佐夫很要好,请您把鲍里斯举荐给他当副官。那时,我也就放心了。”
瓦西里公爵微微一笑。“这个我可不能答应。自从库图佐夫被任命为总司令以后,
求他的人太多了。”“不,大好人,请您一定答应我。”“爸爸,”那位美人又用同样的声调说,“我们要晚了。”“好,再见,再见啦。您听见她说什么了吧?”“那么您明天就奏明皇上?”“一定的,可是向库图佐夫求情,我不能答应。”“不行,一定答应,一定答应,瓦西里,”安娜·米哈伊洛
夫娜紧接着说,露出卖弄风情的年轻少妇的媚笑,但现在却很不相称。为了儿子,她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她仍回来听子爵讲故事,实际想等待时机离开,因为她的事已经办完了。
“最近,《米兰的加冕礼》那幕喜剧,您觉得怎么样?”安娜·帕夫洛夫娜说。“还有新的喜剧呢!热那亚和卢加各族人民向波拿巴先生请愿。”
安德烈公爵直瞅着安娜·帕夫洛夫娜的脸,冷冷一笑。
“‘上帝赐我王冠’。”他引了一句波拿巴在加冕时说的话。
安娜·帕夫洛夫娜接着说:“波拿巴已恶贯满盈。”
子爵仍然说自己的话。他轻蔑地叹了口气,换了个姿势。伊波利特不屑一顾,画徽章给娇小的公爵夫人看,并滔滔不绝地向她解释。“阿弥陀佛。”他说。公爵夫人面带笑容听着。
“如果波拿巴再在法国的王位待上一年,”子爵仍顾自己发挥,“事情就越发不可收拾了。阴谋、暴力、放逐、死刑将要永远把法国社会,我指的是法国上流社会,断送掉,那时..”
他耸耸肩,摊开两手。皮埃尔想说什么:子爵的话使他感到兴趣,可是监视他的安娜·帕夫洛夫娜把话接了过去。
“亚历山大皇帝宣布,”她带着一提起皇家就露出的哀愁,说,“他要让法国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政体。毫无疑问,一旦摆脱掉篡位的奸贼,全国上下都会争先恐后归顺合法的国王。”安娜·帕夫洛夫娜说,竭力讨好这个亡命的保皇党。
“难说,”安德烈公爵说,“子爵言之有理,事情现在很糟糕。但是我相信,走回头路是困难的。”皮埃尔红着脸说道:“据我所知,贵族都已经投向波拿巴了。”“这是波拿巴派的言论,”子爵对此不屑一顾,“现在很难知道法国怎样。”“这是波拿巴说的。”安德烈公爵冷笑着说。他虽然不喜欢子爵。
他引用了一大段波拿巴的话。“得了。”子爵反驳说,“在杀害了公爵之后,甚至最偏激的人也不再把他看作英雄了。”
站在旁边的皮埃尔又插嘴了。“处死昂吉安公爵,”皮埃尔说,“对国家有其必要性。拿破仑不怕由他一个人负全责,我认为这正是他精神伟大之处。”
“天哪!我的天哪!”安娜·帕夫洛夫娜害怕地低声说。小公爵夫人一面说,一面微笑。“皮埃尔先生,谋杀就是伟大吗?”
“哇!哇!”
几个人同时惊叹起来。
“妙极了!”伊波利特公爵拍着大腿嚷道。子爵只是耸了耸肩。
皮埃尔洋洋自得地从眼镜上方端详着听众。
他不顾一切地说道:“波旁王朝逃避革命,使人民陷于无政府状态。只有拿破仑善于理解革命,战胜革命,因此,不能为了一个人而坏了全体。”
“您到那边去,好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可是皮埃尔不答理,仍旧讲他的话。
“不,”他越讲越兴奋,“拿破仑伟大,因为他站在革命之上,他扬弃了革命的弊端,保留了所有好的东西———公民的平等权利啦,言论出版自由啦,等等,因此他才取得了政权。”
“是的,要是他取得政权以后,不是利用政权来屠杀,而是把政权交给合法的国王,”子爵说,“那么,我就会称他作伟人了。”
“他无法这样做。人民把政权交给他,正是因为他使人民摆脱了波旁王朝,而且是因为这个原因,人民才把他看作伟
人。革命是伟大的事业。”皮埃尔先生不顾一切地继续说道。“革命和弑君都是伟大的事业吗?..您还是到那边一桌去吧?”安娜·帕夫洛夫娜又说了一遍。大家又谈了一通弑君,理想等等,争论不休。
“自由平等,”子爵轻蔑地说,仿佛为了证明人们的愚蠢似的,“这都是高调,早就名誉扫地了。谁不爱自由平等?我们的救主早就宣讲过自由平等。难道革命以后人们过得更幸福吗?恰恰相反。我们希望自由,而波拿巴却消灭自由。”
安德烈公爵时而笑着看看皮埃尔,时而看看子爵,时而看看女主人。安娜·帕夫洛夫娜虽然精通上流社会的世故,却被皮埃尔的狂妄无礼吓坏了。但是后来她看到,皮埃尔尽管说了些亵渎神圣的话,但并没有惹恼子爵,她就和子爵联合起来,集中力量攻击这位演说家。
“可是,皮埃尔先生,”安娜·帕夫洛夫娜说,“一个伟大人物可以处死公爵,他甚至可以随便处死任何无辜的人,您对此怎么解释呢?”
“请问,”子爵说,“您怎样解释雾月十八日呢?难道这不是一个骗局吗?”
“他杀死了全部非洲俘虏,”娇小的公爵夫人说。“这太可怕了!”她耸了耸肩。
“无论如何,他是一个暴发户。”伊波利特公爵说。
皮埃尔先生不知道回答谁好,他看了一下所有的人,笑了笑。脸上露出一副稚气、善良、甚至有点拙笨的表情,仿佛在请求饶恕。
子爵虽然和他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已经看出,这个雅各宾党人完全不像他的话那样可怕。大家全沉默了。
“你们要他一下子回答所有的人,那怎么行呢?”安德烈公爵说。“再说,对于一位政治家,我们应当分清,哪些是他的私人行为,哪些是统帅的或者皇帝的行为。”
“是的,是的,自然是这样。”皮埃尔接过去说,看到有人帮他的忙,他很高兴。
“必须承认,”安德烈公爵继续说,“在阿尔科拉桥上的拿破仑是个伟人,在雅法医院里向鼠疫患者伸出手来的拿破仑也是个伟人,但是..但是有些事他也做得不对。”
安德烈公爵想和缓一下皮埃尔的失言;他欠起身来准备走,并且向妻子暗示了一下。忽然,伊波利特公爵站了起来,示意大家留下,让大家坐下,他开始说:“我想让你们听一个从莫斯科听来的笑话,我用俄语讲,因为用法语讲就没有味道了。请原谅。”伊波利特公爵开始用俄语讲,俄语说得很差。大家都留了下来,因为伊波利特公爵非常希望大家听他的故事。
“莫斯科有位太太,她很吝啬。她需要两个跟车的仆役。要非常高大的。这是她的爱好。她有一个侍女,也是个大个子。她说..”
说到这里,伊波利特公爵停了下来,用力思索。“她说..对了,她说:‘丫头(alafemmedechambre),穿上制服,站在马车后面,跟我们一道去串门。’”说到这里,没等听众笑,伊波利特公爵噗哧一声笑起来。那位老太太和安娜·帕夫洛夫娜,还有另外一些人,都笑了笑。“她坐上车走了。忽然来了一阵大风。侍女的帽子刮跑了,长长的头发披散下来..”
他说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边断断续续地说:“于是整个社交界都知道了..”
笑话就这样结束了。这个笑话虽然不是什么精彩的笑话,但是却愉快地结束了皮埃尔先生令人不快的、无礼的谈话。随后,大家就一起谈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5
客人们谢过安娜·帕夫洛夫娜,开始告辞了。
皮埃尔笨头笨脑。他长得肥肥胖胖,个子比一般人高,他不懂礼貌,没有道谢就离开了。而且还心不在焉,临走时拿错了帽子。不过他心不在焉、不懂进客厅的礼节,不善于在客厅里说话,所有这些都被他的温厚、纯朴、谦恭的表情补偿了。安娜·帕夫洛夫娜向他转过身来,怀着基督徒的温和,并没有怪罪他那不得体的谈吐,向他点了点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