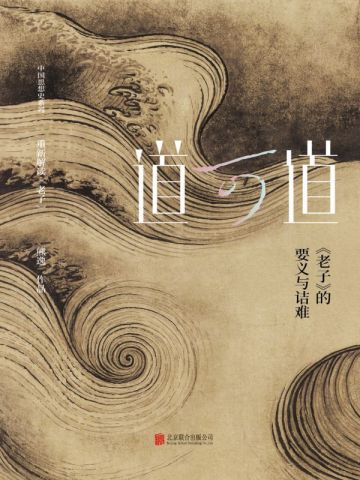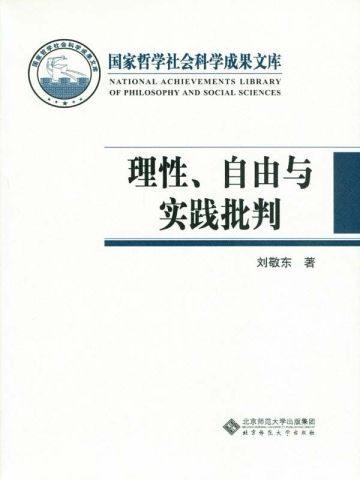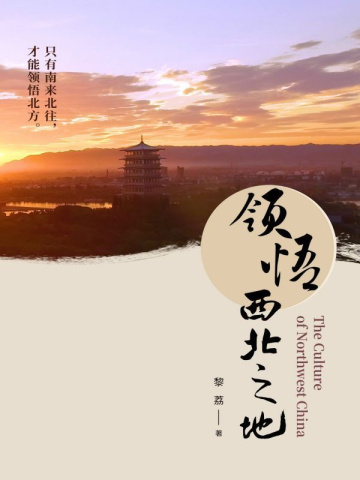避难经过
“七七事变”,卢沟桥的炮火一响,我就对朋友说这件事情要扩大。朋友说,北平以东方为缓冲地带,塘沽是有条约的,日本一时不会再有举动,恐怕此事是误会。我说《塘沽条约》(即《塘沽协定》)乃受日本人欺骗,日本侵略,绝无止境,此次恐怕我们政府不能容忍了,而宋哲元他们还抱着讲和的希望。过了两天日本军队进了北平,我就把我所有国剧学会的东西安排装箱,把它保藏起来。事还未起手,一日在东交民巷散步,遇到友人余天休君,他坐着汽车,看到我赶紧跳下车来,背人问我:“有一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我问:“何事?”他说他才由日本使馆出来,见抗日人员单上有我的名字。我问:“我向来与政治无关,何以有我的名字呢?”他说:“我也知道你向来不搞政治,但是单子上确有你的名字,你得预备。”我听到这话,自己寻思,总是半信半疑。晚间与家兄竺山讨论此事,家兄云:“我们虽然不搞政治,但日本欺侮我们,我们心中当然是极愤恨的,我们又爱随便说话,平常谈话中,常常露出这种论调来,有时且至大骂,由这种地方得罪了日本人或汉奸们,也是有的事情。我认识人少,得罪人也少,你认识人多,当然得罪的人也多。此事不可疏忽,应该早些预备,倘被他们抓进去,虽然不敢说一定要命,但他收拾的罪过就受不了。”
我想这话很有道理,当即说:“我们反对日本人侵略我们,这是人情之常,是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如此,但我们并没有做过抗日的工作,这正是我们应该惭愧的地方。他虽说我们是抗日分子,但他绝对不会有什么凭据,我也不会有什么罪过的,可是倘抓了我去一审问,我可就有罪了,因为我虽没做过抗日的工作,但这‘不抗日’三字,我一定不肯说,安能没有罪呢?”当即想托东方文化会理事长桥川代为一询,又一想,我同他虽极熟,但此时亲身去问,有点不妥。乃托与他相熟之友人代问,旋即得到回话,说他往使馆去查过,确有我名,并云至晚三两日内,必要前来逮捕,嘱我早为躲避要紧。当天我就躲到亲戚家去,家兄舍弟,也都暂且躲避。次日夜间果然来了,而且是五个人,两个巡警,两个便衣,一个刑警,这足见很严重了,叫门时家中只剩妇女,当然受惊不小。叫开门后,在门洞中问了许多话,问这是齐如山家不是,又问有几人同居等这些话,问了十几分钟,才进内检查。检查得倒很严重,查完后走的时候,一个穿便衣的人说:“我从前在富连成,我认识齐先生。”家人等一夜当然都未睡好,第二天一早家人来告知此事,家兄亦到,我们听到这些情形,以为很奇怪:叫开门先问话,有一刻钟之久,才进内检查,这明明是有放人越墙逃走之意,暗思何以这样紧的逮捕,又放人逃走呢?过后托人探听,才知道彼时日本虽已进城,但他们的特务、宪兵及警察等,还未行使职权,一切案件,先嘱中国旧警察局办理。承办此案者,为余友人蒲子雅君。蒲为福建人,正在警局任司法处长之职,他派人办此案之时,对五人说明此案,并问:“你们知道齐某人吗?细瘦高身材,常穿一蓝布大褂,他与前任白朵乡处长认识,所以我见过他。”白为蒲之老师,十余年前,曾任警局司法处长,亦余好友。他说这套,是明明有放走之意,常办案的警察,对此还有不在行的吗?一听就明白,所以此案便缓和了许多。
以上乃是后来才知,当时仍不敢回家,乃搬到法国医院,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才知道前边说的蒲子雅这件事情,以为既是缓和了下来,似乎可以回家了,又一想,中国方面的警局虽然缓和,日本方面是否缓和,尚不得知,仍以暂躲为是。果然过了四五天,又有便衣警察来了,问人上什么地方去了,家人告以早已离开北平,至于目下在何处,也实在不知。他们说如果在北平可以出来,不会有什么罪过的,麻烦了有半个钟头就走了。有周大文者,亦余熟人,当了日本人广播电台的台长,台中我的熟人很多,其中有代我求桥川之人,他们明知我在北平,辗转找到法国医院,跟我商量,请我出去广播,并言明只广播戏剧,并且特别优待。我问第一二次只播戏剧,以后呢?他们说他们敢担保,不会广播别的事情。我自己心中说,你们保我,谁保你们呢?但在那个时期,我只可心中这样想,绝对不敢说出口来,又麻烦了会子,一位旗门中的朋友说:“最要紧的,不过是让你骂骂中央,还有比这个厉害的吗?中央并非不可骂,且离这样远,就是骂了,中央也怎么样不了呢不是?”我说:“做一件事情,但问应该做不应该做,不应该管‘怎么样的了’‘怎么样不了’。我们中央政府未尝没有该骂的地方,但我要骂,我往四川重庆去骂,我不能在此地骂。”他们听了我这话很动容,我请他们吃了一顿点心,并告诉他们,我再考虑考虑,他们才走了。他们所以能来法国医院者,是因为家兄抹不开面子,才带他们来的,当然预先跟我说好喽的。
他们走后,我同家兄说:“他们来的四个人之中,有三个满洲人。按满洲人不同蒙回藏三族,那三族都另有宗教,有地盘;地盘还是小事,宗教团结力最大。满洲人无宗教,现在完全汉化,我们一毫不应该歧视。但他们虽然汉化,有些人心中总有点不舒服,本来把他们皇帝给赶掉,全族全家,失业没有饭吃的人很多,则他们心中不舒服,也是人情之常。如今日本人一抬举宣统,他们精神为之一振,请看这几个人脸上,都有兴奋的神气,所以说了许多得意的话。我很想抢白他们几句,转而一想,此时岂可再得罪人呢?所以才说了那几句话,然这几句,他们已经很不爱听。这个法国医院,怕又住不成了,倘他们再来时,一定就不好应付了。然仍不敢回家。”家兄很以为然,出去替我安排一切,当晚又搬到亲戚家。后王叔鲁到北平,亦系老朋友,他手下我的熟人也不少,又来找。我一概未见,此后便无人再来,过了两个月,仍然搬回家去。此次回家,决定一人不见,因为我向来认识人多,倘若有人见到,则难免有人提起来,无意中便可出乱子,所以至亲本家都不见。东单牌楼裱褙胡同舍下之房,南北短而东西宽,共四个院,最东边一院,为客厅院,客厅为三间北屋,我就住在里边,把门一锁,到晚间无客来之时,方与家人相见。白天偶遇阴雨,客人来得当然少,也偶尔在廊下或院中散散步,可以换换空气,然仍嘱咐家中,倘有人叫门,必须先来告我,然后再开。如是者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过了八年之久,虽夜间也没有在大门口望过一次,这可以算一种很特别的生活。在这样长久的时期中,当然也很经过些次麻烦或危险,兹在下边,大致谈几件,也算是我一生可纪念的事情。
第一先说国剧陈列馆。我既为逃亡之人,不敢出面,则这陈列馆,当然是非停办不可,乃同家兄商议,把所有物品装在箱中,觅一妥当地方暂且保存。次日带人去装,装了不多,一位傅君提出异议,说这些东西,以不收为是,倘若一收,则怕惹起日本人的注意及干涉。傅君为国剧学会帮忙之人,而且同日本人来往很多,或者他另有所闻,也或者别有用意。无论如何,先装起来再说,没等装完,又有其他中国人及日本人说来要这个房子开一俱乐部,是某一机关的俱乐部,看到这些东西,他们也不让装了,他们说他们用不了这许多房,以一半仍归国剧学会用,仍然把这些物品陈列出来,于本俱乐部也好看,于国剧学会也无损,岂非一举两得?也未答应他。此时大致已经装完,尚未能运走,又有人来说,某机关想借去陈列,并云管保代为保存,亦未应允。总之以上这几次交涉,意思虽不善,而态度尚不十分强横,倘他们强横地抢夺,彼时也无法抵抗。最末前边所说的傅君来云,他在电台做事,这项物品,可以存在电台,并可陈列,一定可以保存,两天就派车来运。此时外边的闲话已经很多,朋友都来说,姓傅的没安着好心,尤其沈兼士先生更注意此事,连来了几次,说外边人都如此说法。但彼时就是确知其如此,身后有日本人,也无法抵抗。后他果然运到西长安街旧交通部内广播电台,也陈列了一部分,只有铜的乐器等,其余均未开,想因地方不够之故耳。沈兼士兄又来云,他果然抢走了。
此时北平学界人大多数人都已知道,南边袁守和诸君也得到此消息,大为不平。盖傅君在学界向不利于众口,尤其是北大、孔德、清华、辅仁、燕京等大学及国立北平图书馆这些地方,他想进门都进不去。他运走后,家兄大为难过,且很生气。我对家兄云:“不必生气,此事我已想到,这背景确有日本人。年余以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组一班学生毕业后旅行,共五十余人,先到上海,后到北平,参观的地方当然不少,最注意的是图书文物。他们来国剧学会参观的工夫很长,且有一班人又来过一次。他们回到东京,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此次到北平,所看到的东西,自以国立北平图书馆存书为最多,‘但其中除四库全书外,其余我们国中都有,且都看见过。唯独国剧陈列馆所陈列的物品,大多数都是我们没看见过的’。以上这段报,我虽未亲眼得见,但告诉我的是很靠得住的人,则此事不至假。如此是他们早就注意到这些东西了。此次他们抢这项东西,是奉机关之命抢?抑系他们私人抢了去预备将来卖出发财?则不得而知。但他们想要这项东西,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不过此事可以放心,无论他搬到什么地方去,将来我们一定还能要得回来。因为此次战事与从前不同,从前友邦也未尝不想帮忙,但因自己不争气,友邦无从帮起,所谓有力使不上;倘自己不要强,专靠别人替出力,那是永远没有希望的。要抗战到底,则友邦自然帮助,因为我们果然败了,他们也受不了,所以知其必帮,如此则我们焉有不胜之理?此时只管任其所为,胜利之后,他运到什么地方,都能找得回来。”
一次沈兼士兄来谈(此时我已不见人,他来时总是与舍弟寿山谈天),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从前总是不赞成你们把国剧学会的东西让别人拿去,现在却明白了。”舍弟问何以明白,他说:“现在傅某之兄,已进国立北平图书馆了。我问馆中为什么要他,他们说,背后有日本人,敢不要吗?国剧学会当然也是如此。”后来屡有朋友来信问及此事,由中央来的信也很多,有的只是不平,有的因为认识日本人,想替挽回此事。我对家兄说:“这件事情最好不提,倘再翻腾起来,难保不另生枝节。”对友人热心,一一婉谢才罢。这票东西,在西长安街电台存了一年有余,又搬至东城南小街禄米仓左右一所房中,在此处并未打开,存放而已。后来美国出来,日本渐渐不支,家兄向他要过几次,总不肯交还,又托几位友人代为说项,亦未交还。按他们已经抢去几年了,何必此时这样着急呢?实因珍珠港事已起,则美国定有时要轰炸日本,倘他们运到东京,则难免被炸,我们这些东西,倘被炸毁,实在有些冤枉。然要不回来,也是无法的事情。在日本投降之前两个月,又找人去问,他们说可以运回来,大概他们也是看日本快支持不住了,所以才肯交回。于是雇车运到顺治门外自己的栈房中保存,此事才算告一段落,然其中要紧的物品,则已丢了几件,只好将来再说了。
以上乃是第一件麻烦的事情。第二件则是普查户口,我想这件事情,真不容易应付了,听说是家家要查,且须全家站齐,一个个点名验看。在这期间,跑到谁家去也不成,不用说人家不敢留,就是敢留,也难免连累人家,自己也不肯。自己正在想法子的时候,忽然有一友人来了,一进门就大哭,哭完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前几天就听说要查户口,以前他检查就检查,没什么关系,我们也不是搞政治的人,家中更不会有违禁的物品,任凭他检查,没什么可怕的。昨天果然来了,来了两个日本人,两个中国巡警。这两个日本人,不但不够尺寸,且长得不像个人,一进门就嚷:‘都出来。’当然就都出来了,他又说:‘站齐喽!’我说:‘你们要检查谁就检查好了,何必站齐喽呢?’他一句话没说,就给了我一个嘴巴,巡警也喊:‘快站好喽!’家人害怕,都赶紧站齐,且劝我赶紧也站好。他点了一次名,都细看了一看,倒没有搜检身上,各屋中都看了一看,也大致检查了检查就走了。我们堂堂华胄,黄帝的子孙,就让他们这样侮辱吗,这以后还怎么活着呢?”说罢又大哭。家人说:“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劝了好久才罢,晚上家人把此事告诉我,我听到这话,又添了许多烦恼,固然可以说是“素夷狄行乎夷狄”,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倘挨一嘴巴,乃是终身之辱。而且我的事情,还不在站齐不站齐,而是可以出面或不能出面,岂不更多一层难处?于是想届时伏在房顶上,或藏在一木箱中,或装病。房顶地方,已经看好,并在一间破屋中,放上一个大木箱,都预备妥当,等他来时,再随机应变。过了不到两天,有人来送信,说某友人去世了。问他什么病?他说因为日本人检查户口,命其站班,他受刺激太厉害,登时脑充血,就躺在地下,当晚即去世。我听到这话,更是难过,心中说:此公比我有血性,然仍应留有用之身,做将来的事业,故仍以躲避为是。
又有人来谈,某人因恨日本人,随手写了“小日本”三字,即掷于字纸篓中,日本人去检查,看见有此三字,便打了某人两个嘴巴,并命他说“大日本”,他无法,说了三声“大日本”才饶了他。家人听此,就想把家中旧纸都烧了。又有人说,都烧了不成,字纸篓中无纸,他说你有了预备,他倒疑惑你,最好还是设法写上一点恭维日本的话,放在字纸篓里,还得让他看着像无意中写的,倘若他看着你是故意写的,也许出麻烦。家人说,反对日本的话,固然是不敢写,恭维日本人的话,也不甘写,只好听其自然吧。然而终归把各字纸篓,详细检查了一次。以后听到的这种事情很多,不必尽述,也无法可想,只好到时候随机应变了。幸而舍下住的裱褙胡同,前后左右都是日本人,二十余年以来,就是如此,谁家是怎么回事,彼此也都知道,而且住的日本人极多,于是他对这一带的住户,注意力较小,检查的比别的地方松得多。他来检查的那一天,家人也没有站齐,我在床上躺了一个钟头,也没有问,含含糊糊就过去了,这总算不幸中的一个大幸,以后虽然仍不断有这种麻烦,但因日期长了,尤其东单牌楼一带,几乎都是日本人,就是检查也容易应付了。
还有麻烦的就是租房,舍下之房,在裱褙胡同,是日本人最多的地带。前边已经说过,当然有许多人想占此房,最初是天天有人来看房,当时我正在医院,都经家人应付过去,也是因为我们房虽多,但住的人也太多,无一间空房,所以容易应付。只有两次较难:一次是一女子来租房,面貌相当漂亮,她说她奉某机关命令,来租此房,倘租不成,她回去不但受申饬,恐怕饭碗就得丢了,“至少也得租给我一两间”,说罢大哭。其实这话一听就是假的,一个机关,倘若要占,至少也要占一整所,岂有只用一两间之理。说了许久,她不应允,看情形光说好话是无济于事,后来对她说起大道理来,问她你们是什么机关,可以随便就用人家的房,你们政府有这种命令吗?倘乎我们这房是空闲着,还可商量,现在我们每一间屋都有人住着,你让我们搬到什么地方去?你说一两间都可以,请问一个大机关,在此要两间房,有什么用处?你让我们把两间中之人搬到什么地方去?你机关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同你去见你们长官,我们可以央告他,也要跟他讲讲理;我想你们政府,也不能允许这样做法。一套话说得她闭口无言,又说了一会儿,她才说她回去商量商量,就走了,以后没有再来。
一次又来两个日本人看房,不敢阻拦,只好让他看,亡国之惨,以至于此。各屋都看完后,说某机关须用此房,问租价若干。答以人太多无处可搬,不能出租。他说话之神气,相当客气,笑笑说不租怕是不成的,你们先打算打算,我们明天再来,说罢就走了。大家以为此二人说话虽然相当和气,但来头似乎很凶,很难应付,但也无法可想,只好应付到哪儿算哪儿。按从前与日本人,直接或间接,认的人也不少,当时北平政府的汉奸,也多系熟人。再者我被逮捕及逃亡的这个消息,大家早已知道,有许多通日本文的朋友,及与日本人有关系的朋友,前来舍下安慰,说倘有危险,务必告诉他们,定可挽回,就是现在回来,也敢保无事,就是以后倘有为难的事情,只管告诉他们,必能尽力云云。我们果然去求求他们,或能得到其帮助,斟酌了许久,我说:“这些人的好意实在可感,在我遭难的时候,还肯前来安慰,这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并且我也真知道,有几个人说话,不是假的,果真求他,他必能出力无疑。但私交是私交,现在他们都是汉奸,以堂堂男子去求汉奸,心中有所不甘,不必说我去求北平政府,就是去求他日本使馆的人,也尽有熟人。我最初求桥川,是求他给探询探询,是否果有我的名,并未求他设法帮助,倘若肯求他,我此时想已早平安无事了。最初还不求他们,现在更不必了。”家兄也说:“可以不去求他们,因为倘去求人,则房子或者可以保住,但又恐怕把你的事情翻腾起来,更要多事,更要麻烦。”家人都以为然,遂决定不去求人,倘日本人来了再说。次日果然又来,因为昨日各房都已看过,只未到客厅,一进大门,就直到客厅来。我向来由里边锁上门,我一看不好,倘他们看到由里边锁着门,就更要当心有别的事情了,赶紧把门锁开好,自己假装伏在书桌上写字。幸而我早有安排,在日本进城之后,约半个月之久,并无逮捕我的消息,所以我还常到各朋友家去走走。一次到观音寺胡同友人施秉之家中,正谈时事,忽有两日本人进来,说话很不客气,东翻西看,后见到两个日本人的名片,此名片上的两个日本人,都是日本使馆的高级职员,亦都是施君的好友。他们看到这两张名片,脸神登时改为笑容,问认识这两位吗?施君答,都是我的好朋友,并给述说了认识的经过,此两人赶紧拉手,又说了些客气话就走了。施君说:“哎呀可怕呀,幸而有这两张名片,中了大用了,否则不晓得出什么麻烦呢。”我看到这件事情,心中很有感触,以为这却是一种办法,回家来,把从前所有朋友来往的名片都找出来,共有四百多张,其中有日本人有三十几张,我把它摆在一玻璃盆内,放在条案一头很容易看到的地方,并且挑拣了几个跟日本人来往最多的中国人,摆在大面上,又把饭岛(是否名曰饭岛,记不清了)的名片放在极容易翻到的地方。饭岛者,为吾从前中央政府之顾问,自然有强迫性了,而他又是此时日本北平居留民会的会长,也与我极熟,此人是一中将,又为日本贵族,日本人之在北平者,第一必须先认识他,所以把他放在容易看到之处。
我又佯为与两三日本人写信,一为好友龙居枯山,乃大文学家龙居濑三之子,亦一大文学家;另一人为长泽规矩也,乃一汉学家,对于中国书之版本极有研究,专买中国旧书,北平之古物保存会最注意他,每逢他到北平,总有人跟着他。这些人平常就不断通信,每逢年节,必有贺年片寄来。在日本军到北平之后,龙居来过一信问候,长泽则在前十几天中,来过两信,彼时我固然不能给他们写回信,而且也不愿写,此时不得不利用他们了,也可以说是借重他们,我先写了一个信封,放在旁边,便接着写信。在这个时间,这两个日本人进来了,我立身一招呼,他便看到这个写好了的信封,他脸神为之一变,便问认识此人吗,我说是老朋友,便随手把长泽来信给他看。他便说:“我同他也是好朋友。”正说之间,那一位果然检出饭岛的名片来,手拿着来问我:“认识此人吗?”我说:“也是老朋友,我认识他,已经十几年了。”有这两段情节,就完全缓和了。一位说他也认识长泽,他来北平,永远住他的旅馆,又谈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并说打搅对不起。他们走后,家人初则害怕,后则高兴极了,说怎么这样凑巧,他们就看到这些名片,我说这不是偶然的,都是预先安排布置好了的。我就把在施秉之先生家中遇到之事说了一遍,并且说这一着总算是用上了,效力还是很大,不过幸而是他们不知道我是何人,更不知我是抗日单上的人,倘若知道,则此事怕不能这样容易就会过去。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商人,想占我们的房开旅馆。
当我在法国医院住着的时候,同住者有李君润章,名书华,表弟段子君二人,都是避难,白天都藏在房中,不敢见人,晚间三人谈天,都是想设法逃走,几乎天天所谈的都是此事。但各人地位情形不同,只好自己想自己的法子。过了二十几天,润章居然走了,都是法国人帮助保护。子君劝我也照他的法子去办,我是不能出面,家兄为此事也跑了几天,说:“事情可以办到,但须慎重,听说逃走的人很多,抓回来的也不少,应该暂看看风头,再打主意。”我说:“此话极对,而且我不同润章,润章认识人较少,他所认识的,只有政学两界,我则不然,五行八作,我都认识的人很多。常说笑谈,我到戏馆去看戏,观客中,我总认识百分之三十,其余我虽不认识他们,而他们认识我的人也很多。还有到公园散步,举目一看,有百分之七十的茶桌上都有熟人,当然不会全桌都认识,但总有熟人在里头。倘在火车上,有人一招呼,就许出麻烦,还是看看情形再规定为是。”后来听到,有两个熟人逃走,都被抓回。一位是赵君,他化装为工人,穿的工人衣服,脸上抹了些黑烟子等,没想到在天津车站,一下车就被日本人扣下了。天津车站的检查站,是预备一盆水,其中有一块布,日本人提起这块布来,在你脸上擦,黑颜色自然就掉了,他便扣下问话。赵君在天津被扣了两天,又押回北平,幸亏没有什么大罪过,只若能同他合作,肯帮他忙,也就可以饶了呢。家兄听到这些话,来同我述说。我听过之后,便说:“照这情形,现在万不可走,别的事不必说,就他用那一块布在我脸上抹一下,我就受不了。”另一位就是管翼贤,他也是佯为工人逃走,也是被人用布一抹,脸上颜色被人抹去,被扣留在天津,幸亏把守门口的是中国人,他花了几百元钱,就放了他。他逃到中央,因为不能如自己之意,又逃回北平,经日本人盘问了几次,他说的都是赞成日本人的话,日本才放了他。他当然得做几件投降日本人的事情,北平有句话说得“卖几手”,方能得日本人的信用,于是他便干脆做起汉奸来。他到处对人说,中央对不起他;也有人帮他说话,说北方逃去的人,中央应该特别优待,不应该不理。有人对家兄谈,说:“中央这种情形,令弟也不必往南逃走了。”家兄听到这话,很不以为然,来对我谈及。我说:“他这话自己以为很是,大家也有赞成的,但是这种思想,是整个的错了。请问他,中央是该他的,或是欠他的呢?自己逃走,是凭自己的思想,即是自己的良心,想做汉奸,就可以不逃,不甘做汉奸,就得逃走。逃走不了,是没法子的事情,不必于逃回去之后,便趾高气扬,以为大家对我都得另眼看待,中央也必须奖励我,给我好的事情。果真这样想法,那就完全错了。总之逃回去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自己做了,这岂非平常事体呢?大家为什么要恭维你呢?在中央一方面说,由北边回去的人,自然应该帮助或安插,但能帮助,自己应该感激,不能帮助,也是平常的事体,自己可不应该抱怨。再说中央处的是什么景况,所谓军书旁午,一日万机的时候,怎么能顾到一两个人呢?若因为中央没有优待,自己就逃回来,这天然是汉奸的思想,就让他当汉奸吧。”不过因为他们都说天津查得很严,其办法很多,不只用布擦脸,我当然就不敢逃走了。
虽然不敢轻易说走,但无时不想走,不过在北平无法可想。想求人,就得把我的名字说出去,倘说出去,就难免又生枝节;若用假名逃走,倘被查出,更是不了。北平既无法可想了,只好另想法子,彼时小儿煐在香港,舍侄焌、熨弟兄都在重庆,用别人的名义,给他们去信,问他们有法可想没有,并嘱其如“无法不必写回信”。过了一年多的工夫,焌侄来信云,已与德国顾问团及大使馆说妥,国剧学会所有的物品,一切可以交德国使馆,代为运到重庆,我本人亦可由德使馆人员保护南去。接到此信,与家兄斟酌,焌与德国顾问团中人都熟,与团长塞将军尤靠得住。家兄住德国多年,我与德使馆汉文参赞斐色耳君,也是好友,此事办成与否,或不至于有意外不幸的事件出来,不管能成功不能成功,总可前去接洽。次日家兄即到德使馆,说明来意。使馆人员却非常客气,他说他们也已经接到来信,问共有多少件。告诉他们宽高各三尺,长约四尺之箱,共三十余只。他听到此数,已经皱眉。问有多重,答以尚不能详知,但每一个空箱,总有七十余斤,因为都为寸板,且都是榆木制成,所以分量相当重。他此时已有为难之色,他问:“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吗?”答以当然可以,但其中稍有为难的地方。便将此事之经过,详详细细告诉了他。他听完后说:“哎呀,这里头还有坏人哪!”他想了一想说:“这样吧,我再调查调查,你再计划计划,我们后天再斟酌吧。”家兄回来告知此事,大家斟酌:这票物品,在汉奸手中已经存了一年有余,探听着并未损坏,亦未偷走(最初偷走几种重要物品,后来未偷),已往算是安定下去,此时再一交涉运走,恐又惹出许多是非来,《易经》上云“吉凶悔吝生乎动”,还是不去交涉的好。再说以往看到日本人的行为,凡他们抢到东西,大致都未运走,又相传日本人有命令不许运走,窥其意是将来战胜,得了中国,物品存在什么地方,也是他们的;倘战败,虽然把东西运到东京,也得给人家运回来,而且运往东京,则比北平危险得多,所以一切东西都不运走。以上乃是朋友们揣度之词,但也确极有理,如此则这票东西仍以不动为是。至于我个人,也已经平静了一年多了,或者不至于再发生任何危险,亦以不动为是。家兄又到德使馆,使馆人员又非常客气,他先说,这件事情,我们得详细谈谈,问家兄有工夫吗,家兄答以有工夫,遂拿定主意,自己先不说,光听他的。他说:“府上与敝使馆的关系与他人不同,自一九○○年,府上就与敝使馆有来往,到现在令弟之名,使馆中人无不知者,府上的少爷、小姐、姑爷等在德国留学者,有十几位,都与敝国感情很好,有几位少爷小姐,到我们国防部去过,经部长给大家介绍,都很钦佩,都很融洽。齐焌与吾赛将军,又系好友。照以往的关系说,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是应该尽力的。但有三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详细斟酌,从长的商量商量再定行止。第一个问题是,不知这票东西是他官场需要,或是私人抢去,无论哪一种,总是其中有坏人,现在以德国同日本国交的情形来看,我们要这票东西,或者要得出来,但其中既有坏人,则难保他们不另鼓动风波,由此闹得令弟也走不成,或另有事故,都不敢预定;第二个问题,这票东西相当多,运到半途,不敢保不出危险,被日本飞机炸毁,已不敢保,沿途土匪更多,也难保不出意外,再者日本小鬼,诡计多端,他虽然跟我们说得很好,但若非情之所甘,他们便可能另想坏主意;第三个问题是,以目下的战况来看,这票东西,在北平存着,似较重庆为安全。因为日本不时有飞机去炸重庆,而中国倘有一线之路,则必不肯来炸北平,这是很明显的事情。”他说完问家兄:“您以为我说的这话有理没有,我绝不是推诿,至于令弟个人走,那是没有问题的。”家兄说:“您这话极对,我们回去商议了商议,也以为是不动的好,否则又恐生出别的枝节来,就是舍弟个人,也是暂以不动为是。舍侄焌所以来此信者,他实不知此地目下之情形,我们分头各去一回信好了。”他说如此甚好。这票东西先不往回要,我自己暂且也先不走,经此次斟酌之后,才算告一段落,以后就没有人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