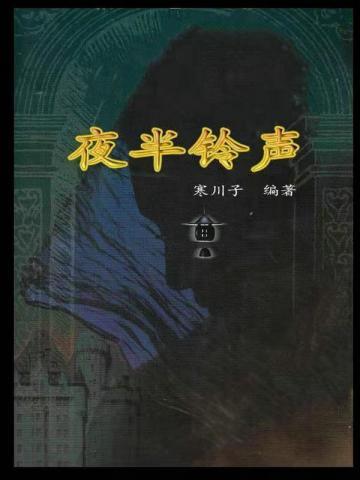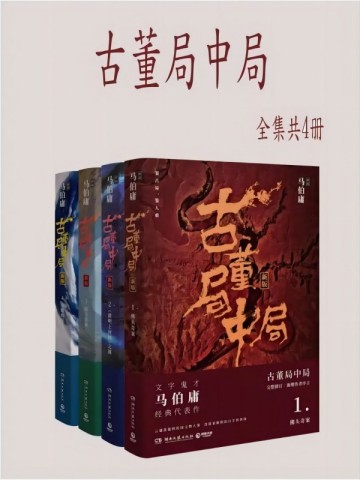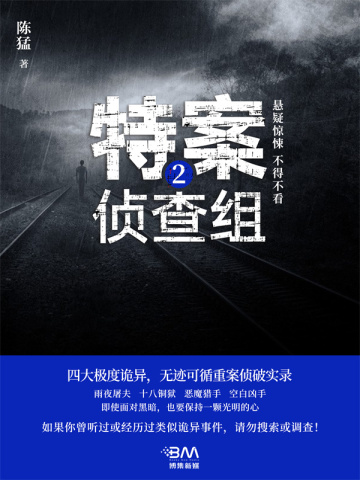故事发生一个秋天。那时我刚患过伤寒,在医院里整整躺有三个月,出院时弱不禁风,想找个工作,可连找几家,没有人愿意雇我。两个多月里,我每天都等在职业介绍所里,任何一个看起来像样的招工广告都能使我空欢喜一场。我已囊中空空,对生活几乎丧失了信心。四处奔波使我更加瘦弱,我真不知道何时才能时来运转。然而运气真的转了——至少当时我这么想。一天,一个叫瑞尔顿夫人的,她也是带我到美国来的女士的朋友,看到我后,停下来与我说话。她总是那么友好。她问我是否病了,为什么看起来脸色苍白。我把遭遇讲给她听,她说:“哦,哈特利,我想我手头有个工作再合适你不过。明天到我家里吧,咱们详谈。”
第二天我去拜访她,她告诉我,她想到的人是侄女布莱姆普顿夫人。她虽然年纪轻轻,却一副病焉焉的样子,许是过不惯城镇生活吧,一年四季都居住在哈得逊河畔的乡间别墅里。
“哈特利,”瑞尔顿夫人说着,乐观的态度让我觉得前途一片光明,“你听我说,我让你去的地方气氛并不活跃。房子虽然宽敞,但有些沉闷。我侄女还多少有些神经质,性格郁闷。她的丈夫——嗯,基本上不在家;有两个孩子,只可惜都死了。要在一年前,我根本不会把你这样一个活泼好动的女孩介绍到那个阴郁如牢笼的地方,可现在,你自己的身体也不怎么好,安静的环境,再加上清新的乡间空气、有益健康的食物和早睡早起的习惯,对你的身体可能有些好处。
“你别误会,”可能因为我看上去有些沮丧的缘故,她补充说,“你也许会觉得生活单调,但你一定能过得开心。我侄女像天使一样善良可爱。她的贴身侍女曾服侍她二十多年,直到去年春天才死。她一直喜欢自己的庄园,对仆人很好。你知道,但凡女主人和蔼可亲的家庭,仆人们大都脾气祥和,所以你一定能跟其它仆人们友好相处。把你介绍给我侄女再恰当不过了:你话语不多,行为端庄,还受过高于你本人地位的教育。我想你朗诵得不错,是吧?这样更好。我侄女喜欢听别人朗读,还想找一个侍女做伴儿。她原先的侍女是个好伴儿,我知道她多么怀念她。这样的生活有些孤单……你下定决心了吗?”
“夫人,为什么说我下不定决心呢?”我回答,“我并不害怕孤独。”
“那就去吧。有我推荐,我侄女肯定会雇你的。我马上给她发电报,你可以赶下午的火车。目前她身边没有人服侍,我不想让你浪费时间。”
我早已做好出发的准备,但有件事儿让我犹豫不决。为节省时间,我问道:“夫人,请问这家的男主人――”
“男主人几乎常年在外,我可以肯定。”瑞尔顿夫人急道。“不过,他在的时候,”她又补充一句,“你只要离他远点儿就行。”
我乘下午的火车,大约四点赶到车站。一个车夫和一架轻便四轮马车正在等我。马儿踏着轻快的脚步离开车站。时值金秋十月,天空灰蒙蒙的,头顶上阴雨绵绵。我们进入布莱姆普顿地区的树林时,白昼的光亮看不见了。马车在树林里蜿蜒行驶二里地后,到达一处宅第,四面环绕着高大的黑呼呼的灌木。窗户里没有亮灯,整幢房子看起来灰蒙蒙的。
我什么也没有问过马夫,因为我不习惯于向别的仆人打听新主人的消息。我喜欢自己总结对新主人的感觉。但从外观上看,我似乎到了一个适合我的地方,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一个面容亲切的厨师在后门迎接我,并叫女佣将我领到楼上我住的房间。
“过一会儿你去见布莱姆普顿夫人,”她说,“现在夫人有客人。”
我没有想到布莱姆普顿夫人会有客人来访,因而,这个消息让我高兴。我跟在女佣身后上楼,透过楼梯顶部的小门,我看到房子里装饰豪华,深色镶饰,还挂着从前的肖像。另外一段台阶通向仆人们住的侧厅。四周很暗,女佣抱歉说没有带灯过来。“不过,你的房间里有火柴,”她补充说,“如果走路当心的话,不会有问题。注意走廊尽头的台阶。你的房间就在旁边。”
我朝前看一眼,见走廊中间站着一个女人。我们走过时,她退到门道里了。女佣似乎没有注意到她,旁若无人地走了过去。她体态消瘦,脸色苍白,身穿一件深色罩衣和围裙。我以为她是管家,又见她不做一声,只在我们经过时久久地盯着我。我觉得奇怪。我的房门在走廊的尽头,位于一个方形的大厅里面。对着我房门的是另外一间屋子,门大开着。女佣看到门在开着,大叫道:“瞧瞧瞧——布兰德太太又忘记把那扇门锁上!”说着话,她已把门关上。
“布兰德太太是管家吗?”
“这里没有管家:布兰德太太是厨师。”
“那是她的房间?”
“噢,当然不是,”女佣有些生气,“谁的房间也不是。我是说,那间屋子空着,房门不应该开的。布莱姆普顿夫人希望把房门锁上。”
她带我走进一间整洁的屋子,装饰得极为精巧,墙上挂着壁画。女佣点燃蜡烛后就离开了。她告诉我六点在仆人用的侧厅进茶点,又说布莱姆普顿夫人可能在此之后约见我。
在侧厅里,我发现几个仆人谈吐风趣活泼。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我可以得出,一切正如瑞尔顿夫人所讲,布莱姆普顿夫人是天下心眼最好的女主人。我没有注意听他们的谈话,一直留心着那个穿深色罩衣、脸色苍白的女人。可她始终没有露面。我很纳闷儿,不知她是不是另外用餐。如果她不是管家,为什么可以单独用餐呢?我突然想到,她可能是个受过训练的特别看护,那样的话,她当然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餐。既然布莱姆普顿夫人是个病人,可能就有特别看护。我承认,这一点使我气恼,因为这样的人不好相处,早知如此,我就不会来了。既然来了,也没有必要为此愁眉苦脸。我这个人不适合提问,只好等着看有什么事儿。
用过茶后,女佣问男仆:“兰福德先生离开了吗?”男仆说走了,女佣叫我跟她去见布莱姆普顿夫人。
布莱姆普顿夫人在卧室里躺着休息。她的躺椅靠近壁火,旁边是个有罩的台灯。她看起来非常纤弱,但当微笑时,我觉得愿意去为她做任何事。她讲起话来令人舒服,低声问着我的名字、年龄等,又问我是否缺少什么,怕不怕乡间生活孤寂。
“跟您在一起我肯定不会寂寞的,夫人,”我说道。这句话让我自己都有些吃惊,因为我并不是个容易冲动的人,但不怎么的,我竟脱口而出。
她听到后似乎很高兴,轻声说希望我以后也这么想。然后她给我介绍盥洗室,说她的女佣艾格尼丝第二天早上会带我看东西都放在什么位置。
“今天晚上我有点儿累了,想在楼上用餐,”她说道,“艾格尼丝会把我的托盘端上来,你也整理一下行李,好好准备一下,晚一点儿就过来为我更衣。”
“好的,夫人,”我说,“我想您会按铃?”
“我不会按铃的——艾格尼丝会带你过来,”她说着,又拿起书来读,模样怪怪的。
是有点怪:我是她的贴身侍女,夫人需要我时却叫另外的女佣来喊!我怀疑这幢房子是否有铃。但第二天我就满意地发现每间屋子都安有响铃,还有一只特别的铃从夫人的房间直通我的房间。这使我更加奇怪,因为布莱姆普顿夫人想要什么时就按铃叫艾格尼丝,艾格尼丝再穿过仆人侧厅叫我。
奇怪的事情远不止此。就在第二天,我发现布莱姆普顿夫人并没有特别看护,于是向艾格尼丝打听昨天下午在走廊上看到的那个女人。艾格尼丝说她谁也没有看见,我看得出她以为我在说梦话。毫无疑问,我们是在傍晚时通过走廊,当时她抱歉说没有带火,但我确实看到有那么个女人,只要碰见她我肯定认得出来。我突然想到,她可能是厨师的朋友,或其它女佣的朋友,许是刚从乡下来,仆人们不想张扬。有些女主人很看重仆人的朋友在家里过夜。总而言之,我决定不再追问这件事。
两天后又发生一件奇怪事情。这天下午,我和布兰德太太聊天。她为人友好,一直在这幢房子里当仆人。她问我住得好不好,缺什么没有。我说,这个地方和女主人都无可挑剔,只是若大一幢房子没有缝纫房让人想不通。
“你怎么会这样想?”她说,“这儿有间缝纫室,就是你的房间。”
“噢,”我说,“那么夫人以前的侍女住在哪里?”
听到这里,她显得慌乱,匆忙说道,去年仆人们的住所都变过了,她有些记不起来。
我觉得不大对劲儿,但装着什么也没在意,接着说道:“这么说,我对面的房间是空着的。我打算问问布莱姆普顿夫人,看是否可以用那间屋子做缝纫室。”
让我惊奇的是,布兰德太太脸色刹时变得惨白,紧紧抓着我的手说:“千万别问,宝贝儿。”她的声音有些发颤,“实话告诉你吧,那是爱玛·萨克森的房间。自她死后,女主人一直锁着那间屋子。”
“爱玛· 萨克森是谁?”
“布莱姆普顿夫人从前的侍女。”
“是那个陪伴她多年的侍女?”我想起来瑞尔顿夫人给我讲的故事。
布兰德太太点点头。
“她是怎样的人?”
“没有人比她更好了,”布兰德太太说道,“夫人对她就像对待自己的姐妹一样。”
“可我指的是——她长得怎样?”
布兰德太太站起身,不高兴地瞪我一眼。“我不擅长描述,”她说,“我想我要烘烤的面团已经发酵了。”她走进厨房,把门关上。
二
到布莱姆普顿庄园一周后我才看到男主人。一天下午,有消息说他要到了,全家上上下下全都忙碌起来。很明显,仆人们不喜欢他。布兰德太太正在精心准备晚餐,说话粗气粗气,跟平时大不一样;男管家威司先生一向不苟言笑,讲话慢吞吞的,做事就像准备参加葬礼似的,动不动就引用几句《圣经》,可那天他引用的词汇令人恐怖,吓得我打算离开饭桌。他向我保证说,引用的句子全都来自《以赛亚书》。后来我发现,只要男主人回来,威司先生总喜欢引用《圣经》里的恐怖词句。
大约七点,艾格尼丝把我叫到女主人屋里,在那儿我看到了布莱姆普顿先生。他站在壁炉前面,身材高大,白肤金发,粗短脖子,红红的脸膛上一双蓝色的、易怒的小眼睛。年幼无知的小傻瓜可能认为他英俊潇洒,并愿意为他付出昂贵代价。
我进屋时他突然转过身,上下扫视我一番。我知道扫视意味着什么,我曾经有过一两次这样的经历。之后他转过身背对着我,继续跟妻子讲话。这意味着什么我也知道。我不是他心目中的女子,看来那场伤寒对我多少有些好处:可以让这样的绅士保持距离。
“这是我新来的侍女,哈特利,”布莱姆普顿夫人柔声讲道。他点点头,继续着自己的话题。
一两分钟后他离开屋子让女主人更衣用餐。我注意到,伺候她更衣时,她脸色苍白,手一接触,她就打起冷颤。
第二天一大早布莱姆普顿先生就动身离开。他的车走远后,大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女主人也戴上帽子,穿上毛皮大衣到花园中散步(因为那天早晨天气很好)。她回来时精神饱满,脸色红润。好一会儿,她脸庞的红润还未消褪,我可以想象,她从前,或许就在不久以前,应该多么可爱迷人!
她在庭院中遇见兰福德先生,两个人就一起回来了。我记得他们经过我窗下的露台时谈笑风生。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兰福德先生,尽管已经不仅一次听到别人提及他的名字。看来他是这儿的邻居,住在离布莱姆普顿庄园很近的地方。他习惯在乡下过冬,在这个季节几乎是我家女主人唯一的访友。他身材消瘦,个头高大,大约三十岁左右。我一直觉得他面色忧郁,很少见他露出微笑。这一天,他的笑容简直出乎意料,就像春天里第一个暖洋洋的日子。据说他象我家女主人一样博览群书,两个人总是相互把书借来借去。冬天的下午布莱姆普顿夫人就坐在那间宽敞、灰暗的书房里,(威司先生告诉我)成小时地听他朗读。仆人们都喜欢他,这恐怕是对他最好的赞扬。他对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很友好。我们也很高兴男主人在外时布莱姆普顿夫人能有这样一位讨人喜欢的绅士做伴儿。兰福德先生似乎跟布莱姆普顿先生相处也很融洽,这令我感到惊诧,很想知道两个性格如此迥异的人怎么可能成为朋友。后来我终于明白,真正有品质的人大都不露声色。
提到布莱姆普顿先生,他去去来来,在家里呆的时间从不超过两天,总是诅咒这里乏味单调,偏僻荒凉。不久我发现他还酗酒。布莱姆普顿夫人离开餐桌后,他总要在那里坐到半夜,喝布莱姆普顿家收藏的葡萄酒。有一次,我离开女主人的房间稍迟一些,正碰上他喝得醉醺醺地爬上楼梯。一想到夫人不得不忍受他这样的人,我就恶心。
仆人们很少提及男主人,但从他们的言谈中我可以看出,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不幸福,因为布莱姆普顿先生为人粗俗,爱出风头,且喜欢寻欢作乐;而我家女主人却生性孤独,喜欢安静,甚至有些冷若冰霜。这并不是说她对他不好:我认为女主人已经非常有耐心了,但对象布莱姆普顿先生这样无拘无束、大手大脚的绅士来说,我家女主人显得确实有些离群索居。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一切平静如初。我家女主人很和蔼,我的工作也挺轻松,而且我和其它仆人相处得很好:简而言之,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但不知怎的,我总觉得心里象压着块石头。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但知道决不是因为寂寞。我很快就习惯了:那次伤寒后我一直虚弱无力,乡间的宁静和新鲜空气对我再合适不过;可我内心无法平静下来。女主人知道我大病初愈后,坚持要我四处走走,所以她时不时就给我安排些跑腿的差事儿,比如说到村子里去买一条缎带,寄一封信什么的,或还书给兰福德先生。一走出门,我的心情就舒畅起来。我期待着漫步于充满露水味的树林中。然而,只要看到布莱姆普顿庄园,我的心就开始下沉。从良心上说,这幢宅子并不阴暗抑郁,只是我一走进来觉得沮丧而已。
布莱姆普顿夫人冬天不常外出,只在天气很好时才会在午后到南面的草坪上散步一小时。除兰福德先生外,来客还有医生,他一星期从城里过来一次。有一次他喊我过去,说一些与女主人病情相关的注意事项儿。尽管他没有告诉我她患的是什么病,但从她早晨上妆前蜡黄的脸色看,我想她可能心脏不好。这个季节天气潮湿,对健康并非有益。一月下过一段时间雨,这对我来说简直是痛苦的折磨,整天守在屋子里做针线活儿,听屋檐下雨水下落的滴哒声。我变得极度紧张,一丁点儿声响都会吓我一跳。不知怎么的,想到走廊对面那间锁着的门,就像有东西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一样。在漫长的雨天晚上,有几次我感觉自己听到那边竟有声响。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天一亮,这种念头就会从我的脑海消失。有一天早晨,布莱姆普顿夫人给我一个惊喜,她要我到城里去买些东西。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当时的情绪多么低落。我兴高采烈地出了大门。一看到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以及令人振奋的商店,我有些情不自禁。可到下午时,街道和人群的喧闹拥挤开始让我烦心,我开始期待布莱姆普顿的静谧,想象回家穿过黑暗的树林时自己该有多么高兴。路上碰见一个姑娘,她与我在一块儿工作过,我们已好几年没有见面了,所以就停下来说话。我告诉她这些年的境遇,当提到现在时,她抬起眼睛,板起面孔说:“你说什么?布莱姆普顿夫人!一年四季都住在哈得逊河边乡间别墅的那一家?亲爱的,你不会在那儿呆满三个月的。”
“可我不在乎呆在乡下,”我说,她的语调让我生气,“自从伤寒之后,我喜欢安静的环境。”
她摇摇头说:“我不是指乡下不乡下。就我所知,过去四个月中她已换过四个侍女。最后一个是我的朋友,她告诉我没有人可以呆在那幢房子里。”
“她有没有告诉你原因?”我问道。
“没有——她不肯告诉我原因。但她讲道:‘安塞,如果你认识的姑娘想去那儿的话,告诉她不值得。’”
“她是不是年轻貌美?” 我想到了布莱姆普顿先生。
“年轻貌美?不。只有那些孩子去读大学的母亲们才会雇佣她这样的人。”
哦,尽管我知道这位朋友平时爱说长道短,她的话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黄昏时分,在回布莱姆普顿庄园的路上,我的心情比以往更加低沉。我敢肯定——那幢宅子一定有问题……
我进去喝茶时知道布莱姆普顿先生又回来了,因为一眼看去,所有人都跟平时不一样。布兰德太太的手不停地抖动着,几乎没法倒茶。威司先生引用了可怕且与地狱有关的《圣经》句子。没有人同我讲话,可当我去女主人房间时,布兰德太太跟在我身后。
“哦,亲爱的,”她抓住我的手说,“看到你回到我们身边,我真高兴!”
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么惊奇。
“为什么?”我问,“你认为我不回来了?”
“哦,当然不。”她急忙说道,“我只是不想让夫人独处,哪怕只一天。”
她紧紧地握一下我的手,继续说道:“哈特利姑娘,你是个基督徒,对女主人好一点吧。”说完这些话,她匆匆离开了……
不一会儿,艾格尼丝来叫我去布莱姆普顿夫人的房间。听到男主人的声音,我就从梳妆室转过去,心想在他进屋之前应先把女主人晚餐时穿的衣服准备好。梳妆室是一间很大的屋子,柱廊上有扇窗子对着花园。布莱姆普顿先生的套房就在那边。我走进梳妆室时,看到夫人卧室的门虚掩着,听见布莱姆普顿先生正气呼呼地说道:“别人还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才配跟你讲话呢!”
“冬天这里冷清得很。”布莱姆普顿夫人轻声说道。
“可你有我呢!”他讥讽道。
“你很少回来。”她说。
“那怪谁?你把这里搞得像坟墓一样没有生气。”
听到这些,我乒乒乓乓地拨弄着洗漱用具以提醒女主人。她起身喊我进去。
他们两人像往常一样单独用餐。从吃晚饭时威司先生的举止来看,我就知道情况不妙,因为他引用的是《圣经》中最恐怖的词句。这些话吓得布兰德太太魂不守舍,宣布她不会独自一人下楼把冻肉放在冰箱里。我也有点紧张。伺候女主人休息后,我鼓起勇气下楼想劝布兰德太太陪我打牌,但却听到她关门的声音,于是只好蜇回自己房间。雨又开始了,滴嗒滴嗒的声音不知不觉地直往我的脑海里灌。我没敢睡着,躺在床上听着落雨声,辗转回想着城里朋友所讲的话。令我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每次离开的只是夫人的侍女…..
过一会儿我就睡着了。突然,一阵巨大的声响把我惊醒,是我屋里的铃声在响。我坐起来,被不寻常的声响吓坏了,因为它听起来似乎丁丁当当地在黑暗中响个不停。我的手颤抖着,可找不到火柴。最后我终于点上灯,跳下床。我开始觉得自己是否做梦。看看挂在墙上的铃声,里面的小锤仍在摆动。
我匆忙穿衣服时又听到另外一种声音。是我对面锁着的房间房门开关的声音。我听得很清楚,吓得站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接下来,我听见有脚步声匆匆穿过走廊朝主厅方向走去。因为地板铺着地毯,所以声音很轻,但我敢肯定是女人的脚步声。想到这个我就浑身发冷,好一阵儿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然后我恢复了理智。
“爱丽丝 • 哈特利,”我对自己说,“刚才有人从那间屋子出来在你之前跑过走廊。这想法并不令人愉快,但你必须面对现实。女主人摇铃喊你,要你去她那里,你必须沿着刚才那个人走过的路走过去。”
嗯——我就这样做了。我从来都没有走得这么快过,可觉得似乎永远也走不到走廊的尽头或者说布莱姆普顿夫人的房间。路上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一切就像坟墓一样黑呼呼、静悄悄的。到女主人房门口时,四周如此安静,我开始怀疑自己一定是在做梦。我几乎想转身回去。就在这时,我突然一阵恐慌,于是我敲敲房门。
没有应答,我又大敲几下。让我吃惊的是,开门的竟是布莱姆普顿先生。看到是我,他后退几步。透过手中蜡烛的光芒我看到他面红耳赤、恶狠狠的。
“是你?”他怪声怪气地说,“上帝啊,你们到底有几个人?”
听到这个,我觉得脚下的土地要塌陷下去,但我对自己说,他喝多了,于是语气坚定地说:“先生,请让我进去。布莱姆普顿夫人按铃让我过来。”
“你进来吧,我才懒得管呢,”他说。我推着他穿过大厅回到他自己的卧室。让我惊奇的是,他走得笔直笔直,像一个没有喝过酒的人。
我发现女主人很虚弱,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看到是我,她勉强露出笑容,做手势让我给她倒水。然后,她躺在那儿不说话了。她喘着气,闭上眼睛。突然,她伸出手四处摸索,轻声说道:“爱玛!”
“夫人,我是哈特利。”我说,“您需要什么?”
她睁大眼睛,惊诧地望着我。
“我在做梦,”她说,“你可以离开了,哈特利。非常感谢你。你瞧,这会儿我好多了。”她转过头背对着我。
三
那天晚上我吓得不敢再睡,直到天大亮后才感觉略好一些。
刚起来不久,艾格尼丝就把我叫到布莱姆普顿夫人的房间。我担心她是不是又病了,因为她九点之前很少派人叫我。可我发现,尽管她脸色苍白,面容憔悴,似乎并没什么不舒服。
“哈特利,”她飞快地说,“你能不能马上穿好外套去村子里走一趟?我想让你为我抓药——”说到这儿,她犹豫一下,脸红着说,“——我希望先生起床前你能赶回来。”
“好的,夫人。”我答道。
“还有——等一下——”她把我喊回来,好像突然又想起什么,“配药时,你可以顺便把这张便条带给兰福德先生。”
到村子里要走两里地,所以在路上我可以好好思考这件事。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我家女主人想瞒着先生配这副药。回忆一下昨天晚上的场景,再加上我所看到和猜测到的种种迹象,我开始怀疑可怜的女主人是否厌倦了生活,绝望之极,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念头深深地揪住我的心,我几乎是跑向村子,上气不接下气地一下子坐到药店柜台前的椅子里。那个好心的人刚刚开始营业,直直地盯着我,我恢复了常态。
“理摩尔先生,”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您能不能看看这个药方,告诉我是否有问题?”
他戴上眼镜,仔细阅读那张药方。
“有什么问题?这是沃尔顿医生开的药方,”他说,“能有什么问题呢?”
“吃下去有危险吗?”
“危险——你是什么意思?”
这个人真蠢,我真想打他一下让他清醒清醒。
“我是说——如果有人喝过量的话——会不会出现意外——”我说这话时,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上帝保佑,不会有任何问题。只是酸橙水而已,即使你一勺勺地喂小孩子也不会有事。”
我如释重负,急匆匆赶往兰福德先生家里。路上又闪现出另一个念头。如果到药店取药没什么好隐瞒的话,那么女主人想让我为另一件差事保密。不知怎的,这个念头比前一个更让我恐慌。可兰福德先生看起来似乎是我家男主人的忠实朋友,而且我对女主人的人品深信不疑。我为产生这样的猜疑感到羞愧,最后得出结论是,可能是那天晚上发生的怪事困扰着我。我把便条留在兰福德先生家里,匆忙地赶回布莱姆普顿庄园。我悄悄地从边门溜进来,以为没有人看见。
然而一小时后,我正要把早餐送往女主人房间,布莱姆普顿先生在大厅叫我停下。
“一大早你干什么去了?”他紧盯着我说。
“一大早?你在说我,先生?”我说着,有些发颤。
“别装了,”他说,额头上因生气而红涨起来,“难道一个多小时前我看到从灌木丛中急匆匆溜进来的不是你?”
本质上讲我很诚实,但当时谎话竟然顺口而出。“是的,不是我。”我盯着他回答。
他耸耸肩,冷笑着说,“你以为我喝多了?”他突然问我。
“没有,先生。” 我回答,这一句倒是实心话。
他又耸一下肩,转过身去。“仆人对我的绝妙看法!”我听见他喃喃自语着走开了。
直到下午静心做针线时,我才意识到那天晚上发生的怪事对我的影响之大。每当经过那扇锁着的门时我都会发抖。我知道自己曾经听到有人出来,并在我之前穿过走廊。我想和布兰德太太或威司先生谈谈这件事,似乎这幢房子里只有他们两人对发生的事情略知一二。可我隐约觉得,如果我问他们的话,他们肯定会否认一切。我要是保持沉默,留心观察,可能会知道得更多。想到要在那间锁着的房间对面再呆上一夜我就不舒服,有时我甚至想打行李赶第一班火车回到城里。但我不忍心就这么抛开心地仁慈的女主人,于是我假装无事,继续做我的针线活儿。我刚刚做有十分钟,缝纫机就发生故障。这台机器是我在房子里找到的,尽管很好用,却总出问题:布兰德太太说爱玛·萨克森死后没有人用过它。我停下来检查机器时,一个从未打开过的抽屉滑到地上,从中掉出一张照片。我拣起照片,惊异地坐在那儿盯视着它。照片上是一个女人——我觉得似曾相识——她的眼睛似乎在问我什么。突然,我想起走廊里那个面色苍白的女人。
我站起来,浑身冰冷地跑出房间。我的心仿佛在头顶砰砰直跳,觉得自己好像永远也无法摆脱那双眼睛的目光。我直奔布兰德太太,她正在午休。我进去时她猛地一惊坐了起来。
“布兰德太太,”我说,“她是谁?”我举起照片。
她揉揉眼睛盯着照片。
“她是爱玛·萨克森。”她说,“你在哪儿找到这张照片的?”
我盯着她足足一分钟说:“布兰德太太,我以前在哪儿见过她。”
布兰德太太站起身,走到镜子前面。“天哪!我刚才肯定睡着了,”她叫道,“我什么也没有听见。现在得快点儿,哈特利姑娘,亲爱的,我听见钟敲了四下。这会儿我必须为布莱姆普顿先生准备晚餐,把他的弗吉尼亚熏腿烤上。”
四
表面上看,两个星期以来,一切还跟以往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布莱姆普顿先生没像往常那样很快离开,而是住了下来。兰福德先生没再露面。一天晚餐前我听到布莱姆普顿先生在夫人的房间里说起这件事。
“兰福德哪儿去了?”他说,“他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来过这儿。是不是因为我在,所以他就躲开了?”
布莱姆普顿夫人的声音很低,我听不见她的回答。
“啊,”他接着说,“两个人做伴,三个人就多余了。我很抱歉妨碍兰福德了。我想一两天后我又该告别,给他一次出现的机会。”他因自己的玩笑大笑起来。
就在第二天,碰巧兰福德先生来访。马夫说他们三个在书房喝茶时很开心,兰福德先生离开时布莱姆普顿先生把他送到大门口。
我说过,一切都跟往常一样,家中的其它人也跟往常一样。但就我而言,自从那天晚上我的铃响过以后,一切都变了。每到晚上我总是似睡非睡,等待铃声再次响起,等待那扇锁着的门再悄悄打开。但铃声再没响过,且我也再没听到走廊里有声音。然而,正是这种无声无息比那种神秘的声音更让我恐怖。我觉得有人缩在那扇锁着的房门后面,我观望和倾听时她也在观望倾听,我几乎想喊出声来:“不管你是谁,快站出来吧!我们面对面地说说清楚,不要老躲在那儿,躲在黑暗中!”
尽管我有这样的感觉,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并没有离开主人。有一次我几乎这么做了,可最后关头又犹豫下来。我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可能是对女主人的怜惜,因为她越来越依赖我,也可能是我不愿再换新的工作,或是种不可名状的什么,总而言之,我像着迷似的迟迟未曾离去,尽管每天晚上我都觉得可怕,白天也好不到哪儿去。
再有一件事,我越来越不喜欢布莱姆普顿夫人的外貌。自从那天晚上起她开始变了,变得像我一样。我本以为布莱姆普顿先生走后她会快活起来,可尽管她心态平静,精神状态和精力却再也恢复不起来。她越来越依赖我,似乎很喜欢我呆在她的身边。有一天,艾格尼丝告诉我,自从爱玛·萨克森死后,我是女主人喜欢的唯一侍女。这让我对可怜的夫人又产生一丝怜惜之情,尽管我几乎帮不了她。
布莱姆普顿先生离开后,兰福德先生常来造访,不过没有以前频繁。我在庄园和村子里看到过他一二次,感觉他也在变化。但我把这些都归结为自己的胡思乱想。
几个星期过去了,布莱姆普顿先生离开已一月有余。听说他和朋友乘船到西印度群岛去了。威司先生说那里离这儿很远,然而,即使你有鸽子的翅膀,不管走到地球的哪个角落,都无法逃脱万能的上帝的制裁。艾格尼丝说,只要他离布莱姆普顿庄园远远的,万能的上帝便会接待并保佑他。她的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听说西印度群岛很远我们都非常高兴。我记得,尽管威司先生看起来有些严肃,那天我们在侧厅里特别高兴地吃了一顿晚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心情好的缘故,我觉得布莱姆普顿夫人看起来气色很好,似乎也很开心。早晨时她在散步,吃过午饭,她就躺在房间里听我读东西。我离开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感觉特别轻松愉快。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经过那扇锁着的房门时没有多想。我坐下来工作,向外一望,看见飘起了雪花。这景色比那连绵的淫雨悦目多了。我想象光秃秃的花园披上一层洁白的罩衣该有多么漂亮。在我看来,这场大雪可以掩盖所有的沉闷,不论是屋外的还是屋内的。
这个念头刚刚划过脑海我就听见身边有脚步声。我抬起头来,以为是艾格尼丝。
“哦,艾格尼丝——”我说,我的话像冻结在舌头上一样,因为门边站着的是爱玛.萨克森!
我不知道她在那儿站了多久,只知道自己动弹不得,也拿眼睛死盯着她。之后我惊恐不已,但当时感觉到的并不是害怕,而是比之更神秘、更静寂的东西……她久久地、紧紧地盯着我,就像不会讲话的祈祷者——但我究竟能帮她做些什么呢?突然,她转过身,我听见她的脚步声穿过走廊。这一次我没有害怕,决定跟着她——我觉得我必须弄清楚她想要什么。我跳起来跑出去。她站在走廊的另一端。我期待着她转向女主人的房间,但她没有这么做,而是推开通向后面楼梯的门。我跟着她走下楼梯,穿过通道,来到后门。在那个时辰,厨房和大厅都没有人,因为仆人已经收工了,只有马夫还呆在配餐室里。走到门边,她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又望我一眼。然后她转动门的拉手,走了出去。我迟疑一会儿。她要把我带到哪儿去?门在她的身后轻轻关上,我打开门,向外望去,几乎希望她已经消失。可我看到几码之外,她正匆匆穿过庭院,朝树林方向走去。在雪地里,她的身影漆黑孤寂。好一会儿,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想要转身回去,但她始终牵引着我。
爱玛.萨克森已经走在树林里。她稳步前行,我以相同的步伐跟着她,直到走出大门,来到大路上。然后,她穿过田野朝村子走去。地上白茫茫一片。她翻过一座光秃秃的山坡时,我注意到她身后没有留下任何脚印。我的心一阵紧缩,两腿发软。不管怎么说,这儿完比不得房间。她使得整个村庄都像坟墓一样荒凉。除我们两个之外,这儿再无他人。广袤的天地里我显得孤立无助。
我想回去,但她转过身来望着我,仿佛用绳子拖着我一般。此后,我就像一条听话的狗一样跟在她的后面。我们来到村子旁,穿过教堂和铁匠铺子,顺着小巷来到兰福德先生的家里。兰福德先生的宅子靠近路边,是一座朴实的老式住宅,一条石板小路通向花坛中间的小门。小巷空寂无人,我拐进去时看到爱玛·萨克森在大门旁的榆树下停住脚步。现在我感到的是另外一种恐惧。我们已经到达这次旅程的尽头,我觉得该做点什么。从布莱姆普顿庄园到这里,我一路上都在问自己,她到底想要我做什么,但可以说,我一直都恍恍惚惚地跟着她,直到看见她停在兰福德先生的家门口时我的头脑才开始清醒。我站在雪地里,离她仅几步远,心脏跳动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双脚快要冻僵在雪地上。她就站在榆树下注视着我。
我很清楚,如果没事,她不会带我来到这里。我觉得必须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但又实在猜不出该做什么。我从来都相信布莱姆普顿夫人和兰福德先生没有恶意,然而现在,从种种现象上看,我敢肯定,有些恐怖的事情在困扰着他们,而爱玛· 萨克森知道这一点,如果可以的话,她会告诉我的。
想到要和她谈话我的头都发晕,但我还是鼓起勇气,拖着自己靠近她。往前走的时候我听见大门打开,然后看到兰福德先生走了出来。他看起来英俊潇洒、兴高采烈,就像那天早晨我家女主人一样精神焕发。看到他,我血管中的血液又开始流动了。
“哈特利,怎么是你?”他说,“出了什么事?刚才我看见有人顺着小巷走来,就出来看看是不是你在这雪地上。”
他停下来注视着我说:“你在看什么?”
我正望着那棵榆树。他的眼光顺着我的视线望去,小巷里空无一人。
我觉得孤立无助。她已经走了,而我还猜不出她想要我做什么。她最后一眼似乎要看穿我,然而并没有告诉我。突然间,我觉得比她站在那里注视着我更孤独凄凉,仿佛是她把我抛弃在这里,承受这个猜不出来的秘密。雪开始在我的周围打旋,田野消失了……
一杯白兰地外加兰福德先生家的炉火使我恢复了知觉。我坚持要求立刻送我回布莱姆普顿庄园,因为天要黑了,我担心女主人需要我。我向兰福德先生解释说,自己刚才在散步,经过他家门口时突然一阵眩晕。这是真话;但说出来时我却有种撒谎的感觉。
为布莱姆普顿夫人更衣用餐时,她说我脸色苍白,问我哪里不舒服。我告诉她自己有点头疼,她说晚上就不要我过去了,并建议我上床休息。
我确实头重脚轻,但我不喜欢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只要头还能抬起来,我就坐在楼下的大厅里。九点种时,我累极了,只想把头放在枕头上。我爬上楼,再没时间考虑其它事情。家里的其他人不久也都休息了。男主人不在家时他们喜欢早起早睡,十点以前,我听见布兰德太太关门的声音,不久,威司先生也把门带上了。
那天晚上很寂静,大地和空气全都裹在雪中。躺到床上就感觉舒服多了,我静静地倾听着黑暗中传出的任何声响。我仿佛听到楼下有开门关门的声音:可能是通向花园的玻璃门。然而除去打在窗玻璃上的雪花,外面什么也看不见。
我回到床上,刚迷乎一会儿,突然给吵闹的铃声惊醒。头脑还未清醒,我已跳下床来,匆匆忙忙披上衣服。她又来了,我自言自语道,但并不知道自己指的是什么。我的双手像粘满胶似的,我觉得自己可能永远穿不上衣服了。最后,我打开房门,凝视着走廊。顺着蜡烛的光亮一眼望去,我看到前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加快脚步,气喘吁吁。但当我推开通向大厅的大门时,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因为爱玛.萨克森就在楼梯的尽头,目光可怕地凝视着黑暗。
好一会儿我动也没动,但我的手却从门上滑落,门关上时人影就消失了。同时楼下传来另外一种声音——鬼鬼祟祟,神神密密,有点像弹簧锁钥匙转动房门的声音。我跑到布莱姆普顿夫人的门前,敲敲房门。
没有动静,我又敲门。这一次我听见屋里有人走动,门闩滑开,女主人站在我的面前。让我吃惊的是她还没有更衣休息。她诧异地望了我一眼。
“什么事,哈特利?”她低声说,“你病了吗?这么晚来这儿做什么?”
“夫人,我没生病,但我的铃响了。”
听到这个,她的脸色变得惨白,仿佛要摔倒的样子。
“你听错了,”她厉声说,“我没有摇铃,你一定在做梦。”我从来都没有听到过她用这种声调说话。“回去休息吧。”她说着把房门关上。
就在这时我又听到楼下大厅里有声响传来。一个男人的脚步声,我开始明白事情的真相了。
“夫人,”我轻轻说道,“有人来了——”
“有人?”
“布莱姆普顿先生,我想——我听见楼下有他的脚步声——”
她的脸上一阵恐惧,没讲一句话就瘫倒在我的脚下。我双膝跪下,想把她扶起来。看她呼吸的架势,我知道这次昏厥非同小可。我刚托起她的头,就听见大厅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门猛地一下子打开了。布莱姆普顿先生站在门口,身上穿着旅行服,雪在往下掉落。看到我跪在女主人旁边,他吃了一惊。
“什么事?”他大叫道。
“夫人晕倒了,先生。”
他颤抖着冷笑一声,一把将我推开说道:“真遗憾,她晕倒的不是时候。我很抱歉打扰她,可——”
我站起身来,他的行为让我惊骇万分。
“先生,”我说,“你疯了吗?你要做什么?”
“会见一个朋友,”他说着,看起来好像要去梳妆室。
我内心一阵惊悸,也不知道当时都想了些什么或担心些什么,只一下子跳起来抓牢他的衣袖。
“先生,先生,”我说,“出于仁慈之心,看看你的妻子吧!”
他发狂似地把我甩开。
“看来得有个说法了,”他说着,一把抓住梳妆室的门。
就在那一刻,我听到里面有微弱的声响。尽管声音很微弱,但他也听到了。他猛地把门打开,紧接着退后一步,因为爱玛·萨克森站在门口,她的身后一片漆黑;但我清楚地看到是她,布莱姆普顿先生也看到了。他猛地举起双手,仿佛不想让她看见自己的脸。我再抬眼望去时,她已经走了。
他站在那儿,一动也没有动,好像全身力气都没有了似的。悄无声息中,女主人突然苏醒过来。她睁开眼睛注视着他,然后向后一仰。我看到死神从她的脸上滑过……
第三天我们安葬了女主人。那天下着大雪,教堂里人少得可怜,可能是天气不好的缘故,城里的人不方便过来。再说,女主人生前似乎并没有多少朋友。兰福德先生最后才到,此时他们正要将女主人的尸体抬向过道。作为主人家的老朋友,他当然穿一身黑孝。我从未见过男人的脸色这么苍白。他经过我的身边,我注意到他将身体的重量都倾斜在那根拐杖上。我想,布莱姆普顿先生肯定也注意到了,因为他的额头又涨成了紫红色。整个葬礼过程中,他没有象其他人那样祈祷,而是站在教堂的一边冷冷地注视着兰福德先生。
仪式结束后我们赶到墓地,兰福德先生不见了。可怜的女主人刚一入土,布莱姆普顿先生就跳上教堂门口最近的一驾马车,没对我们说一句话就一走了之。我听见他大声命令车夫:“去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