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花姨五十多岁,看起来却像六十多岁的人。郊县野村的农人们,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
早春,乍暖还寒。看起来像六十多岁的春花姨感叹着,公公怎么突然就去世了,真是人活一世,草木一秋。
就在大前天,春花姨的公公还和农人们一起,下田插秧呢。南国的早春,虽然乍暖还寒,但三月份已经开始播种了。农人们把冬天的菜梗子拔除,把春水放入田垄,水牛驾着犁车便将泥土的芬芳搅拌而挥洒至田间地头,空气中弥漫着春的气息。
对于公公的下田干活,春花姨是反对的,“阿爸,家里也不差吃穿,就在家待着吧。”
春花姨的公公虽然八十多岁了,已是满头白发和皱纹,但他坚持认为自己还能干农活,拔草、犁田、插秧,都还行。而且忙活了一辈子,闲不下来,何况是春耕季节呢。
结果就出事了。在一垄长田忙活好之后,春花姨的公公对春花姨说,“先歇会儿,我边上草堆里躺会儿先啊”,十几分钟后,春花姨再叫他,已经没有反应。在农村,无疾而终是一种福气,对他的后辈们来说,更是一种福气。本应高兴才对。但是春花姨的公公死在野外,和一般的无疾而终不一样,“八十多岁的人还被子孙赶去干活,累死在田野里”,族人们私下的议论不好听。
当天,春花姨就哭得双眼通红、涕泪满脸:“阿爸,阿爸啊,你咋不听我的话,偏要去田里呢……”
春花姨虽然没有听到族人的议论,但是第六感告诉她,议论肯定有。因为村里其他族人家一有风吹草动,春花姨也是这般对待的。
春花姨和他丈夫把他父亲弄回老宅、向亲朋好友们报丧后,马上就叫村里管事的老人联系唱经班和吹打班前来唱经、吹打。一共叫了两班人马,早晚轮流,热热闹闹的,用于超度老人,也用于平息议论。
春花姨的丈夫觉得花钱心疼,一亩地一年收成只有几千元,而唱经班和吹打班一天就要花费4000多元,按照当地的习俗是要唱七天的,单单唱经、吹打这一块就要三万来块钱了,还有其他林林总总呢,难。
“春花,要不就叫一班吹打的吧,晚上太热闹也影响隔壁邻居休息。”
“你就一个阿爸,影响就影响了,一定要热热闹闹的。”
于是唱经班和吹打班马上请过来,灵堂也布置起来。白色的纱幕和经幡挂满了堂屋,纸人纸马整齐有序待在一边,唱经班和吹打班二十几号人在灵堂外面羌笛唢呐、吟咏低唱,不知道是佛经还是道经,总之是幽怨绵长、如泣如诉,用于超度亡魂。
等春花姨把这一切都安排妥当,黑夜已开始笼罩野村,除了办白喜事的地方,整个乡野安静而冷清。
等唱经班停下歇息时,灵堂也很安静,淡黄色的灯光在春风中摇曳着,经幡和纸马明暗交替变化,阴森森的。春花姨不知道生死的意义,但对于死亡还是恐惧的,八十多岁的人,你看说没就没了,无常啊。
春花姨看着纸马和经幡被冷风吹动,想起大前天公公还争执着一定要去干活,如今却安安静静地躺着。春花姨瞄了一眼棺材,冷不丁哆嗦一下。
这时,远处一个光点晃动着,慢慢朝着灵堂这边走来。春花姨正疑惑大半夜的谁来了,只见两个人已到眼前,一个是村长,还有一个是村长助理。春花姨正想开口,村长助理先说话了,“阿姨,阿公的死亡证明办了吗?你抽空得去办下。还有,按照县里的要求,三天内都要火化的,你们定个时间,村里帮你约火葬场那边。”春花姨忙着办丧事,没想到火化这一层,被村里这么一说,一时回答不上来,就推说时间还没定,等明天定了再说。
野村的传统是土葬,几千年以来一直如此,虽然野村的历史也才几百年。但是,火化是最近几个月才说起的事,野村这么小,最近几个月并没有人去世,春花姨的公公便成了第一个。第一个是最难的。春花姨的丈夫觉得不行,老祖宗传下来的惯例,怎么可以改,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能用火烧掉?春花姨也觉得不行,第一个火葬,会被族人说一辈子的,但春花姨也忧虑,县里有要求,村长也来说了,能怎么办?
一家子为火化这事忙得团团转。最后决定,管他火化不火化,明天先入土为安,土葬完成了,县里还能怎样?而且,因为火化的事把丧事时间减短,也省些钱,族人也不会议论。
次日早上,春花姨的公公就入土为安了。村长着急却无可奈何,“春花,镇里问起来,这个怎么办,你们怎么自作主张呢?”春花姨表示歉意,“道士先生说今日时辰最好,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火化来不及,只好土葬了。”
村长叹了口气走了。
村长走了,春花姨一家都舒了口气。
然而,下午镇里工作队就过来了,浩浩荡荡几十号人,先是到春花姨家质问,为什么不火化,知不知道这是违法行为?春花姨一家人都说不知道。再问,人葬在哪里了?春花姨一家人也都说不知道。带队的放下狠话:“你们等着吃牢饭吧。”然后率队去村委会,要求村里把坟墓找到,“县里三申五令,要求火葬,村干部如果阳奉阴违的话,马上就地免职!”村长没有办法,把位置说了下,但是不当向导,打死都不当向导,要不就不当村长算了。带队的没有办法,就按照村长讲的地址去找——在一个山坳里,花圈都还摆放在坟墓边上,工作队很容易找到。
春花姨家人闻讯赶来,“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拉去火化。县里有文件的,你们自己不火化,还要麻烦我们帮你。”
“皇天哪,你们太缺德了,连下葬了都要火化,怎么下得了手啊。”
“有文件在,依法办事,你们不要在边上胡搅蛮缠。”
工作队开始动手挖坟,春花姨家人扑上去阻止。工作队就按照三比一的比例,逐个把春花姨的家人架到一边,然后农民工开始挖坟,“哐当”一声,墓门就被敲开了,接着,棺材被竹竿顺出墓穴,再接着,尸体被移出棺材,装入裹尸袋——春花姨家人哭得死去活来,特别是春花姨,先是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等她公公的尸体被拉出来时,不止是悲痛,她看到盖在尸体上的红色绸被在眼前一亮,像满天血色,被风吹动,像是公公的亡魂在哭泣,春花姨感到心被捏了一下,而脑袋被棉絮蒙住了,浑身难受而挣脱不了。
深夜,工作队把骨灰盒送到春花姨家,在没有灵堂的堂屋里放着。葬礼已经举行一次,不能再举行一次,春花姨一家人就等着天亮时把骨灰盒再次送入坟墓。
事件宣告一个段落,野村的稻子和春草依然生长,村民也依旧生活,但春花姨却好像疯了,神神叨叨,说她公公每天晚上在梦里找她,指责她没有保护好阴宅,被火烧得好痛。
刚开始,春花姨的家人觉得可能是惊吓过度,过几天就能好的。结果越来越严重,有时候春花姨白天打个盹,她公公也入梦来指责她,被火烧得好痛啊,好痛啊。春花姨吓得哭出声来,“阿爸,我们也没有办法啊,镇里来这么多人,我们挡不住啊。”春花姨的家人知道她做恶梦了,过来安慰,“没事的,没事的,阿爸不会埋怨你的。”但是春花姨还是惊魂未定、满脸恐惧。
春花姨家人叫村卫生室的大夫看看春花姨怎么了,大夫给了一些安定药,却是服药有效,不服又疯。春花姨家人叫道士先生帮忙看看,道士先生说可能是被脏东西粘上了,去找十几公里外的娘娘宫庙祝何大师看看,把脏东西赶走即可。
春花姨家人就带着春花姨去找何大师,何大师摆祝招魂,令春花姨公公前来对质,春花姨公公在了解了当时的情况之后,就和春花姨冰释前嫌了。此后,春花姨就恢复了正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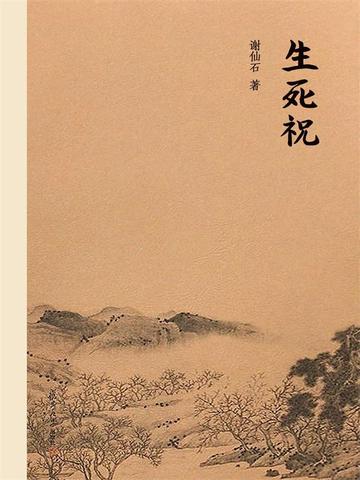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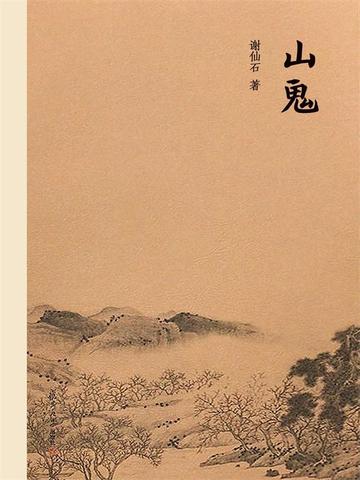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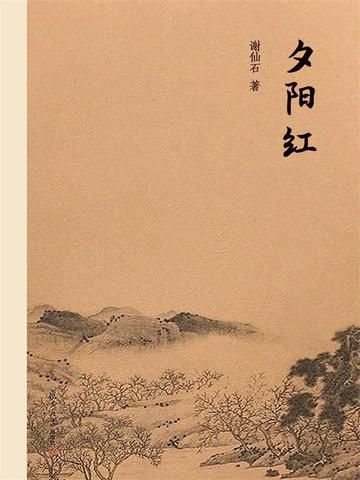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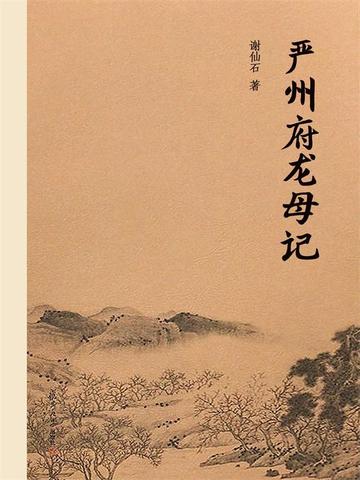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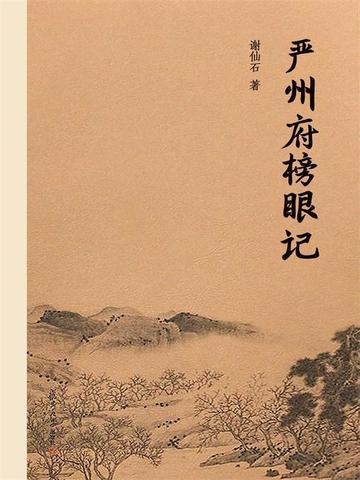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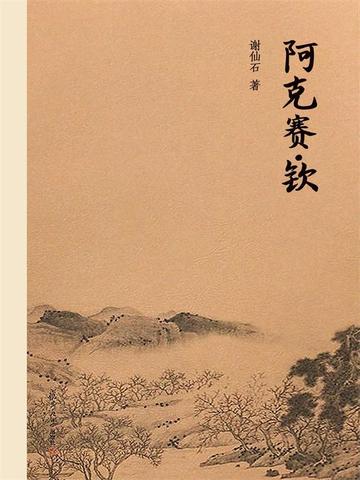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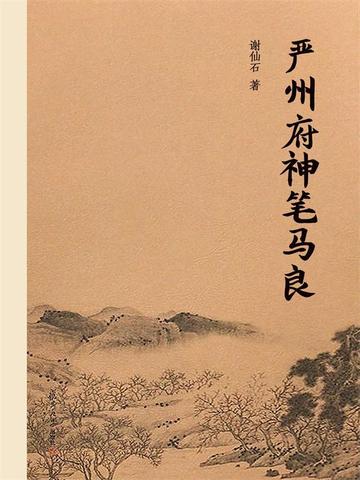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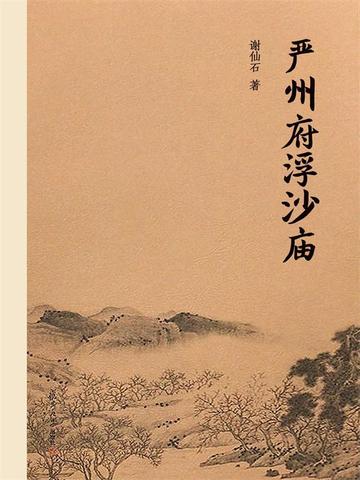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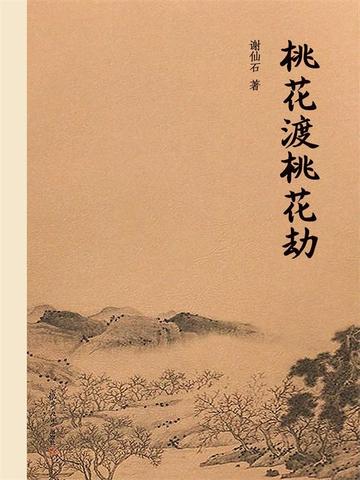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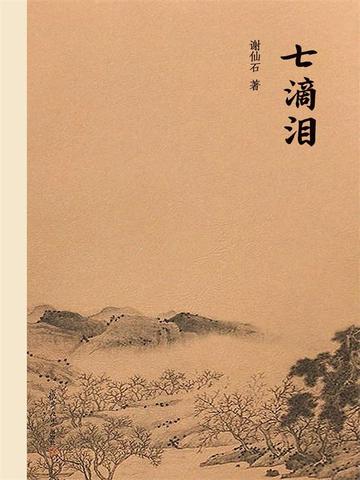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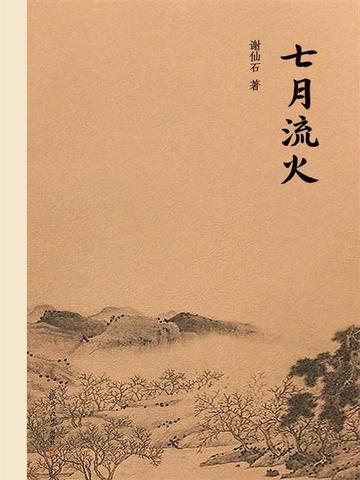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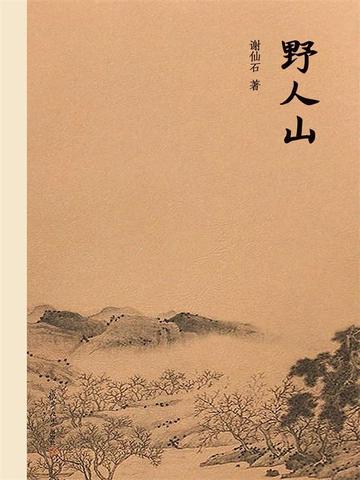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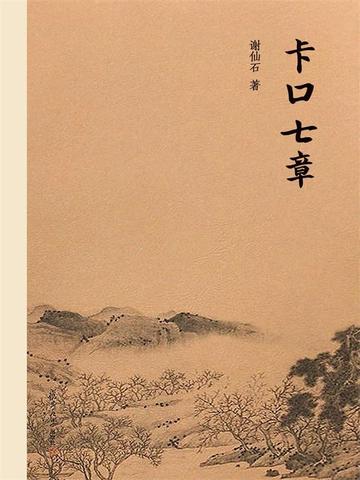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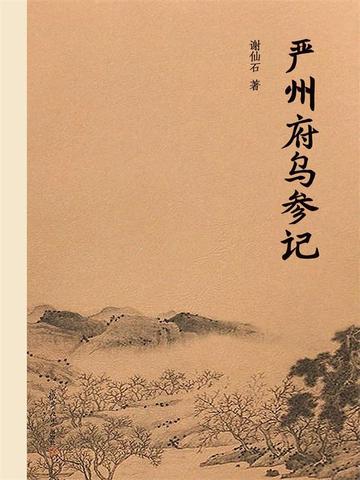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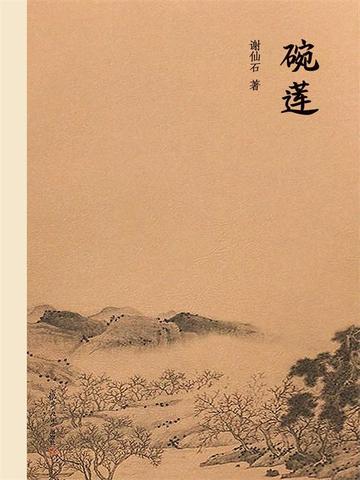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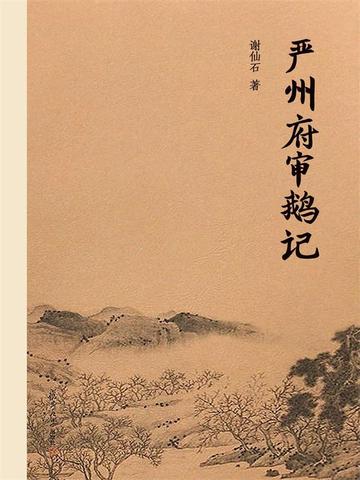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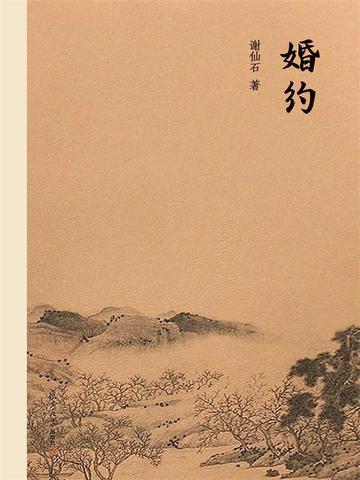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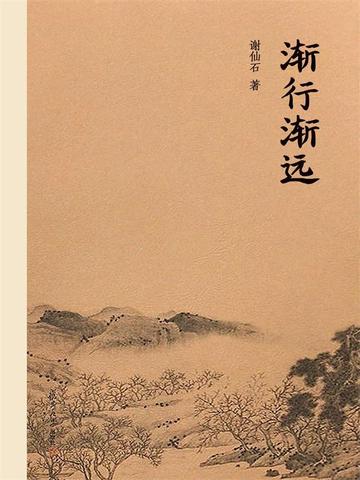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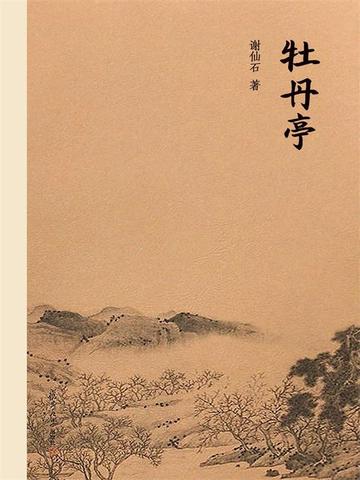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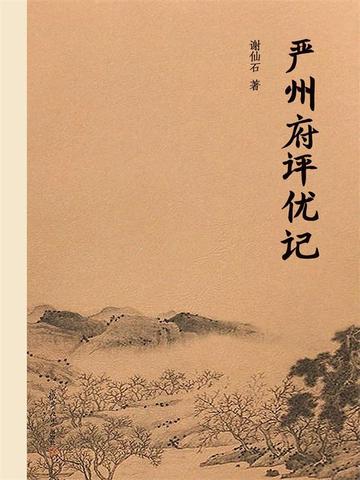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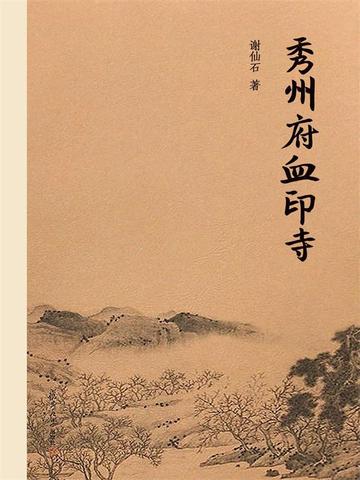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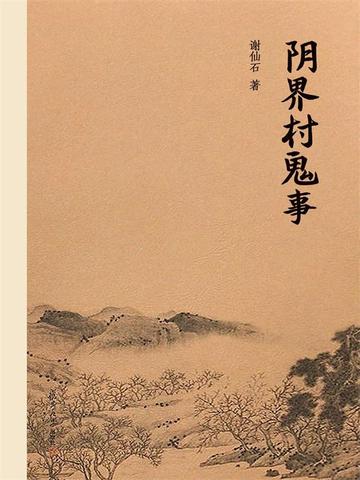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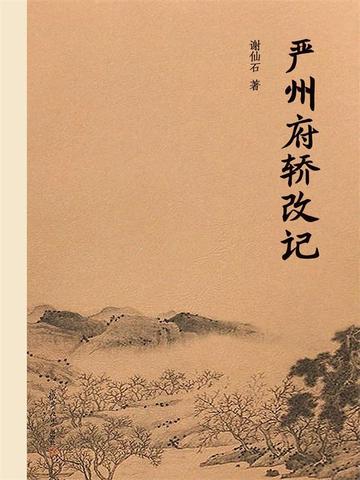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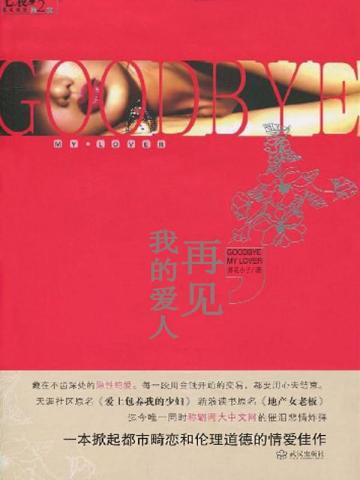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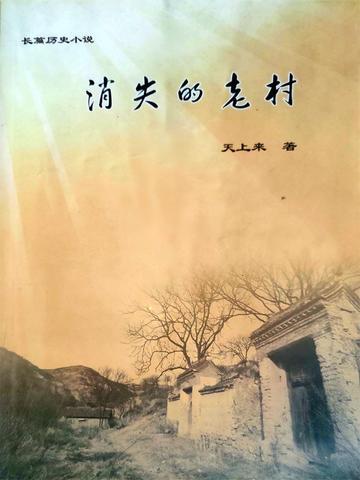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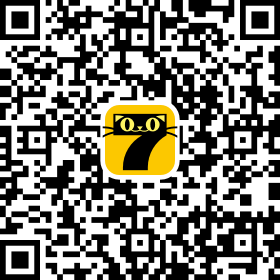 下载七猫免费小说APP
下载七猫免费小说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