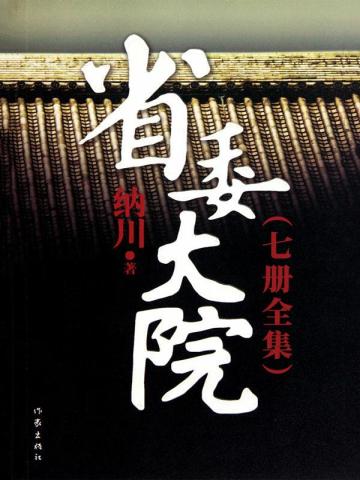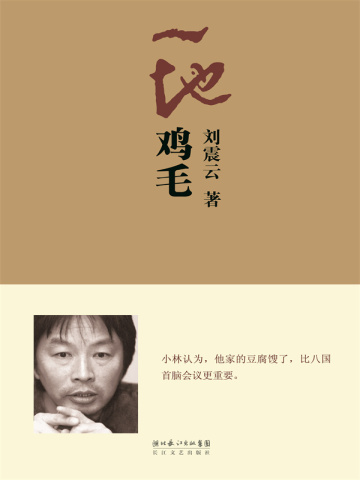这次到益州,已经待了半个多月了。
凌宜生第一次感觉自己闲得有点发慌,很想去找点事做,充实一下过于空虚的日子。上街时,他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发现胡子已经很长了。他想,等下应该去理个发,不然让房东看到这副模样,会觉得他不像个正经人。
凌宜生是昨天在墙上一张小广告上看到一条出租的信息,他记下了电话号码。此时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说,她女儿还没有回来,不过她已经跟女儿说了出租的事,估计没什么问题。
凌宜生说,我想下午就搬过去。
中午,凌宜生没有回叔叔家,他在一家小馆里随便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去河边看景色。他信步走上一座桥的中央,见很多人在围观。他斜眼过去,但见一个女子扶着桥栏,眼睛望着河面,身子向前倾出。
桥上的风很大,女子的头发被吹得很乱。凌宜生感觉这女子有些不对劲,心想,她不会是要自杀吧?近来,新闻上有很多自杀之类的消息。其中有失恋的,破产的,心理扭曲的,神经不正常的。他用力从人群里挤到女子的身后,正要说话时,那女子却突然转过身来,用奇怪的眼神盯着他。
凌宜生脸一下燥热,说,你,你不会是想不开,要跳河吧?女子看一眼围观的人,脸上一红,说什么呀,我不跳河,只是看看船。看热闹的人嗡嗡笑起,有个人说,看船!益州人还没有看过船吗?这女人也太有闲情了吧。凌宜生暗暗笑了笑,也转身走开了。
女子叫高音,跟丈夫离婚已两年,现在带着一个六岁的儿子住在娘家。
日头从桥的西面落下时,高音觉得有几分困了,她拖着倦倦的步子,慢慢离开了大桥。市区内一条街道里,她走进一条宽巷子,到了家门口,听到里面传来儿子和母亲的嬉笑声,其中,还夹杂着一个陌生人的声音。
高音有些诧异,推门进了院子,见客厅里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瘦瘦的脸颊,似乎有一些面熟。那人看到她,投过来一丝微笑的目光。
高音突然觉得一阵莫名的慌乱。高母向高音介绍说,这是家里新来的房客,他可是个画家。男人起身,将手伸向高音说,你好,我叫凌宜生。高音发现他就是刚才在桥上以为自己要跳河的男子,不由笑了,伸手与他相握一下,说怎么是你啊?凌宜生也认出了她,说这么巧啊。
高母愕然,说道,原来你们认得啊。
凌宜生笑了,说是巧合,刚才在桥上见过一次。
高母对这个房客显然满意,说要跟他学画画,说以前租房的人,十个有九个是做生意的,都不太跟她多说话。高音也觉得这男人很不错,声音沙沙的,很有滋味。聊了一会,高音精神好了许多,等高母走开去拿画稿给凌宜生指点时,高音取了十块钱,叫过儿子去买烟,她对凌宜生说,家里也没个男人,没什么好招待的。凌宜生“哦”了一声,心想,难道男主人出远门了吗?没有问出口,只推辞说,不用不用,我有烟。掏出一只烟盒,捏了捏,只剩下一支。
高音笑说,别客气,虽然你是来租房子的,但大家还是可以成为朋友的。我妈不是还想跟你学画吗。指着那个烟盒,叫儿子赶紧去烟摊上买。等烟买回,高音已与凌宜生说了许多话,知道他是省城人,刚过三十岁年龄,在一家杂志社作美术编辑,有个叔叔在益州。
两人聊到天黑,高音去做饭,凌宜生说要出去一下,高音说,今晚就和我们一起吃吧,省得另做了。凌宜生说,不了,我约了几个朋友去外面吃,他们还不知道我在这里租了房子呢,我得跟他们说一声。高音“嗯”了一声,心里突然觉得几分空落落的。
临近中秋,风凉凉地吹过,院子里的几棵大树哗哗地响着叶子。院子是高家最宽敞的地方,其中放着许多把椅子,老人孩子都喜欢在树下玩耍。一架秋千吊在树干上,摇摇晃晃的。望着树顶上的天空,月亮有影子依稀能看得见,也许它也有些怕凉,不一会儿,又躲进了云层间不再出来。
高音先出了客厅的门,指着斜对面靠院门的一间小屋说,我一个人在那间屋子睡,孩子跟着外婆睡,你要是有事的话,就招呼一声。凌宜生抬头看了看,说好的。回头正对上高音的眼睛,又说,改天,我给你画一张像吧。高音掠了掠头发说,那怎么好意思,我长得这么难看,年龄也上来了,不入画的。凌宜生说,你真会说趣话,你怎么会难看呢。拾了桌上那包烟,告辞而去。
高音脸上热热的,倚在门口望着凌宜生远去的方向出神。关了院门,靠着树待了有片刻,心里回想着这个男人的声音。他说自己长得不难看,那意思就是她长得好看了!高音胡思乱想着,这个人他还说要给自己画画,那他就真的是个画家了。想到这里,她不由进了凌宜生睡的那间屋子。
左右看了一番,里面的摆设她都是熟悉的。但因为有个男人来住,感觉那气味就有些异样了。床上搁了一只大挎包,是他的全部行礼。高音好奇心上来,去打开包来看,见里面是一些日用品,还有几卷纸,猜想是画。取一卷展开,果然是一幅涂得稀奇古怪的画,颜色很灿烂,心想,这个人还真是个画画的。
这一夜高音翻来覆去睡不着,一张大床显得空荡荡,空得她心里毫无着落。很久以来,她枕头旁边的另一只枕头都毫无用处,有时成了她架脚用的工具。耳边听到凌宜生回来的声音,看了看表,已是凌晨两点多钟。
第二日一大早,有人在使劲敲门,敲得“咚咚”响。高母在内屋絮絮叨叨地说着,谁这么早就敲门啊!高音也听到,她的屋子离得近,便起来穿了拖鞋,踢踢踏踏去开了院子的大门,一个剪着碎碎短头发的女孩探进一颗脑袋,问凌宜生在不在。
凌宜生在屋子里听到了动静,从房间出来。女孩上去,在他胸上就捶了一拳说,你还睡啊,不是要去见我爸吗?凌宜生打着哈欠说,你还真找到了这里啊。女孩神气地扬了扬头,说你还瞒得过我吗,我爸让我来兴师问罪。凌宜生扶着女孩的肩膀进了屋子,笑声不断里面传出来。
高音苦笑一下,心里怅然若失,觉得昨晚的那场失眠有些不值得。梦都还没来得及做,就已经破碎了。她进卫生间洗了脸,对着镜子揉揉眼睛,脑子里浮现出以前的丈夫来。
转眼到了中秋,院子里的那棵最大的树上,叶子也开始往下掉了。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高母每天都要扫一遍,但扫完后,又掉了一地,于是她便总会嘟嘟喃喃地埋怨。
这天,高音正要陪母亲去看一位亲戚,凌宜生过来说,他想请几位朋友来这里聚会。高音掏出一串钥匙,递过去说,我也正要和妈出去串门,大概五六天时间,这几天家里就交给你了。凌宜生接过钥匙,不停地道谢。
高音突然问,你不是说要给我画像吗?画得怎样了?凌宜生一摸头,说我都忘了,过些日子一定画好。高音说,我没有你女朋友漂亮,你当然要忘了。凌宜生诧异,说你什么时候见我女朋友了?高音说出那天清早找来的女孩子,凌宜生“哎”了一声,说你听错了,那是我叔叔的女儿。高音快乐地笑了,说我还以为是你女朋友呢。
凌宜生每次来益州都要出去租房。叔叔的家是一套两室一厅的小房子,不足四十平方米,几口人窝在一块十分的拥挤。凌宜生这次来益州,其实是为了逃避一宗官司,那家杂志社由他经手的一单广告业务出了点问题,单位上有个早要排挤他的人将他告上了法院。凌宜生自小到大都没见过这种场面,几番折腾后被弄得焦头烂额,只好躲到益州来散心。
这里夜里,凌宜生要请的人来到高家。分别是李景卫,陈章,王隆才和堂妹凌燕花。李景卫是凌宜生中学时的同学,在一个事业单位混了一个小职位,陈章则是凌宜生在厦门当兵时的战友,在一家小公司里做事,嫌钱不够花,自己又开了一家小店,生意也算不得景气。李景卫这几年胖得惊人,下巴颏儿的肉堆出了两层,只见几条深痕,不见脖子。用陈章的话说,李景卫身上的每一块肉都是用钞票贴出来的,属于国宝级的人物。
李景卫坐的那张宽大的太师椅上,是高母每天必坐的位置,此时,也正适合李景卫的体积。凌宜生望着李景卫,满怀同情地说,景卫,看着你就心酸,你真也该去减减肥了。陈章笑道,现在减肥药满世界飞,也不知哪种牌子对他有用?凌燕花端上茶,给众人分发,说,景卫哥不能减肥,他是要升官做的,可比不得我们这些寻常老百姓,什么药对他也无济于事,心宽体胖嘛。李景卫皱皱脸,露出痛苦状,用肥肥的手指敲着脸皮说,这是个学术性很强的问题,有的人该胖的时候就会胖,该瘦的时候自然会瘦,不是谁能决定的。我老婆就不想做官,还不是和我一样胖。陈章打趣地说,你老婆和你联在一起,都变成了一座城市。凌燕花不解地问,城市?什么意思?陈章说,合肥,不是一座城市吗?
众人都笑起来,说这个比喻好俗,好像是从哪个相声节目里剽窃过来的。陈章也不解释,唤各人拿出各自从超市买来的现成的熟食,凑在了一起。大家热热闹闹地吃完了饭,便支好了桌子,打起了麻将。
四个男人中,王隆才最年轻,二十五岁,在当律师,也没结婚。他不玩牌,退在凌燕花后面替她当参谋,俩人时不时斗些俏皮话,一旦出错,就相互埋怨。陈章在桌底下踢李景卫一脚,说我们加点惩罚吧,输了的,在脸上挂一张纸条。李景卫说不太高雅,还是输了打一下脸吧。凌宜生看出意图,说燕花是我妹子,你们可别动歪心思。凌燕花嘻嘻笑,一脸的无所谓,说我后面这位脸皮不薄,由他替我抵挡。王隆才叹息说,和女人在一起,男人总要吃亏的。
玩到深夜,大家散去,凌宜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数着墙挂钟的敲击声,朦朦胧胧正要睡去时,听到院子的门吱呀地打开了。凌宜生警觉地起来,拉亮了灯,外面有人说了声,是我。凌宜生听出是高音的声音,披上衣服出来,说怎么你一个人,你妈呢?高音说,还在亲戚家,我想起单位一份材料没写好,特地赶回来。
凌宜生见高音的脸赶得通红,像喝了酒一样,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话说,那张画,抽时间一定给你画好。高音愣了一下,随即省悟说,又不是马上要走,哪天画好了给我就是。凌宜生郑重地说,一定画好。
次日,睡到九点多钟凌宜生才起床,见客厅桌上摆着一碗面,一碟荷包蛋,另有一张纸条,写着:你的早餐。
凌宜生心里升起些异样,猜测是高音留下的,端起来风卷残云吃下肚。吃完去菜场买菜,到一鱼摊前,挑了两条肥大的鱼。走到半路,提鱼的绳子松脱,两条鱼掉在地上乱蹦。凌宜生手忙脚乱捉住一条,另一条蹦到一辆车下,被车轮压扁鱼头。凌宜生暗叫一声晦气,提了那条死里逃生的鱼往叔叔家去。
到叔叔家门口,敲了许久的门,慢慢地传来一阵脚步声,然后门缝闪开一条线,冒出凌燕花的半颗头,她说,哥,原来是你呀。凌宜生把鱼递给她,说就你一个人在家啊,你爸呢?凌燕花脸窘迫起来,说我爸去玩了,根正在我屋里玩。凌宜生不知根正是谁,心想可能是凌燕花的那一位。见她头发散乱,身上罩着一件男式的短衫,便说,我去找个人,晚上过来吃饭。
凌宜生去了陈章家。因是周末,陈章不用上班,也没去他那家店,正在玩电脑上玩游戏,玩得不亦乐乎。玩的时候,又担心单位裁员的事。凌宜生安慰说,你又年轻,又勤快,怎么也轮不到你啊。陈章说,现在的事谁说不准,前些天我们的头儿就下去了,听说新来的比我还小五岁。想一想,我可是脸盆里的鱼,转不了几个圈,如果被裁掉,就是死鱼一条了。凌宜生说,那是解放了你,你更可以大展手脚了。
去翻陈章书架上的书,竟翻出一本色情画刊来。凌宜生笑着说,你也爱看这个啊?陈章说,别人丢我这儿的,这算什么,我这儿还有碟子呢。凌宜生掀了几页,扔回书架上,说不怕你老婆发现?陈章嘿嘿笑了,说我俩还一起看呢。凌宜生“哟呵”一声,说她还蛮够劲的。陈章摆摆手,说别谈这个,早两年我还能把她治得服服帖帖,现在她常骂我无能。凌宜生说,青出于蓝胜于蓝,这都是你调教出来的。陈章感慨地说,女人啊,到了这个年龄,可就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了,你没办法制服的。男人呢,如同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发不了多少光了。问凌宜生要不要一块看看那片子,凌宜生摇头,说我现在哪有这个心思啊,我都为生计的事愁死了。陈章把电脑关了,丢给凌宜生一根烟,骂道,愁个屁,我还不知道你,就喜欢现实主义!
凌宜生到柜子里取了一块月饼吃,吃到半块,发现馅里夹了一小块指甲,抠出来叫陈章看。陈章大喊假货,把那一盒月饼全部掰开来。凌宜生喊着,这有什么看的,指甲还算是干净的东西,还有那看不见的东西!
想一想刚才吃到肚里的饼,凌宜生觉得一阵恐惧,跑到卫生间干呕,呕不出来,倒弄出一身汗,发誓从此再不吃月饼。陈章感到过意不去,说过阵子去野外玩,叫把房东的女儿带上,说那女人长得不错,很有些少妇的味道。凌宜生没吱声,两人商定好郊游的具体时间,凌宜生告辞出来。
暮色落下,月亮还没瞧见,街上的风从四面袭入汗毛孔,凉爽无比。晚上,凌宜生留在叔叔家吃饭,吃着吃着,问凌燕花,你那位叫根正的,怎么没留下吃饭?凌燕花一脸不自然,拿眼使劲白凌宜生,夹一块大鱼放在凌宜生碗里说,吃你买的鱼吧。凌宜生闭上口,把鱼夹给了叔叔,叔叔嘟囔道,又不是没有了,都自己吃吧,我最不喜欢夹来夹去。
饭毕,凌宜生帮凌燕花洗碗,问她去不去郊游,凌燕花兴奋说,去去去,当然去啊,上班上得人都麻木了。凌宜生说,你要上班怎么去,你可比不得我这个无业游民。凌燕花说,找熟人到医院开张病假条就是。继而一脸思索状,埋怨自己没什么好看的衣服。凌宜生说,那就别去了,下次吧。凌燕花说,那可不行,机会难得,你真以为一个女人会没有一两套像样的衣服?脸露得意之色,要去穿了给凌宜生看。凌宜生忙说天色已晚,要回去睡觉了。跟叔叔说了一声,往高家而去。
到了高家,见高音还没睡,正偎了儿子小迟在客厅里看电视。高音起身,将切好的月饼端给凌宜生。凌宜生将那月饼接过放回桌上,现在他已见着月饼就害怕。他说,就你和儿子在家也怪寂寞的,应该去你亲戚家才热闹。高音说,我本来就不太喜欢热闹。凌宜生轻轻地“哦”了一声,把要邀请她去郊游的话压在了肚里。高音见凌宜生不吃月饼,说你嫌我家的月饼不好吃吗?凌宜生忙说,不是不是,我是才吃饱。见盛情难却,便取了一块最小的,放在嘴边轻轻咬一口,用舌头压住,生怕会吐出来。
趁高音去剥柚子,凌宜生赶快将月饼吐出门外,指着柚子说,有一次我叔叔带了几个去北方,那边的人问,这个东西怎么吃啊,叔叔说,这个就跟吃橘子一样啊。他们便剖开来,掰了一瓣就咬,真像吃橘子那样吃下去。
高音捂着嘴吃吃地笑了,说这么有趣吗!
看到高音的笑,凌宜生感觉到像看到一朵火红的花,绽放着一种灿烂的温暖。在这一片刻,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一只飞累的鸟,很想找一根枝头休息停留。
高音休息那天,叫凌宜生把不穿的脏衣物拿给她洗。凌宜生不住道谢,抱了一堆给了高音,然后去了一趟李景卫家,通知郊游的事,赶回来帮高音洗衣服。高音已洗到最后一件,凌宜生捋了袖子去帮忙,高音说,不用,不用。弯腰去桶里取,衬衫的领口低低地垂下来,凌宜生眼睛一抬,见那领口深处,有两个硕大半遮的乳房露出,不由一呆,全身被震住。高音直起身来,凌宜生忙把目光转向别处,心思早乱了,只觉得体内有一股巨大的火焰要喷出,万分难受。
难受足足持续了一整天。黄昏后,高音取了院内的衣服去洗澡,凌宜生忍受不住,悄悄站到洗澡间的门口,听到哗哗的水声,脑中幻觉出女人赤身的样子。听着听着,突发奇想要在门上找出一条缝。瞧了一遍仔细,真得找到一条细缝,只是太细,什么也看不清。直到水声止住时,凌宜生已是疲惫万分,回到房间掀起被子蒙头大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