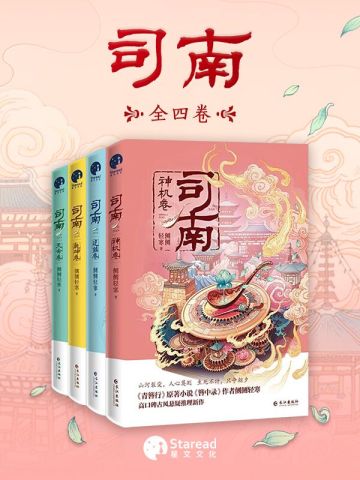清晨。
她起床穿衣。衣服是青灰色的,陈旧而单薄,领口磨脱了线,袖子明显短一截,而裤子又过于肥大,裤腿处不得不紧紧缠上几圈,才好干活。
她从没穿过新衣服,只有婆婆不要的旧衣服,才会轮到她穿。
她看了一眼床上熟睡的男人,沉默起身去洗漱。
水缸里的水不多,用冷水快速洗了把脸,然后把梳子略微沾湿,开始梳辫子。
前些日子,婆婆叫她把辫子盘起来,梳妇人头,她借口说自己不会,仍梳着姑娘家的辫子。可能是忙着秋收,加上一直没圆房,婆婆最近没再提这事了。
天色蒙蒙亮,她已经收拾好了自己,接下来是烧水做饭。村里的早饭无非米粥大饼之类,婆婆爱喝杂粮粥,喜欢往粥里放陈年的豆子,用不了多少米就能煮一大锅,再配上几张大饼,很能填肚子。
但是她不喜欢。她想煮一锅白白糯糯的大米粥,配一小碗醋腌青瓜,或者脆萝卜干儿,吃起来一定有滋有味。
也只是想想罢了。
“阿萝!”
婆婆的声音传来,尖锐而急躁。
“瞎眼的东西!水缸里快没水了,你看不见吗?!快去挑水!”
她伸手往脸上抹了把炉灰,小跑来到厨房外,对院子里的妇人道:“我做好早饭就去。”
“早饭还没做好?!”妇人拔高了嗓门,一面用力舀出缸底最后的水,一面恼怒的骂道,“谁家儿媳睡到现在才起?懒不死你!赶紧做好饭去挑水!我和志贵他爹要去地里了!”
她没做声,默默回到厨房,往灶里又添了几根柴,然后摆碗摆筷。
其实她起得不算晚,即便起晚了,也是因为夜里被志贵闹醒了两回,帮他换尿湿的裤子,所以没有睡好。
志贵是她的丈夫,比她大两岁,但言行举止与三五岁的小孩无异,甚至比孩子更孩子,屎尿总是憋不住,无论她再如何勤洗裤子,屋里头也总有股尿骚味儿。
她想从野地里挖些花草回来种,熏一熏家里的臭气,最好能像村里的大夫家里那样——在院子里种满了白芷、丁香、野菊,还有金银花,又香又好看。
也只是想想罢了。
院子被婆婆分割成鸡舍和菜地,哪还有余地让她种花?
早上的时间过得飞快,她把早饭端上桌,然后拿起墙根下的扁担和水桶,去河边挑水,也躲个清静,呆在家里难免又要挨骂。
话说回来,那地方哪里是她的家呢?……那是婆婆的家,是公公的家,是志贵的家。唯独,不是她的家。
挑水的时候,遇到同村的女人,她们在抱怨又征兵丁了,又加赋税了,家里没有男人,日子快要过不下去。
战事蔓延,村里不少人搬走了,更多的人留了下来,田在地在,哪里走得了呢?何况这天下,本就没有太平的地方,不是战火连天,便是洪涝虫灾,她会在这里生活,也是因为小时候家乡遭难,家里卖儿卖女,后来几番周转,婆婆把她买下来,当童养媳养大。
有时候觉得自己命苦,活了快二十年也没一个自己的家。
有时候又觉得自己的命还算不错,隔壁的阿晓也是被买来的,她男人是个暴脾气,因为瘸了一条腿逃过了征兵,每天在家打阿晓。
志贵虽然傻,但至少不会打她。
她应该知足。
应该知足……
水桶在身体两侧晃荡,肩膀火辣辣的疼,她低头走路,汗水流进眼睛,视野里她看见自己的影子单薄而模糊。她不禁问自己:这样的生活,还要过多久?
远远的,听见婆婆在喊她:“阿萝!阿萝!……”
她走近了,应了一声。
婆婆骂道:“挑水挑到龙王庙去了?!臭丫头现在才回来!志贵醒了,快去给他穿衣!我们要去地里了!”
她闷不吭声,挑着水从婆婆面前走过。
婆婆看见水桶里的水只有一半,眉头皱起,再次骂道:“每天好米好面养着你,倒不如养头驴!这么点力气,农活干不了,挑水也做不得,几年不知下一个蛋,吃的倒是比猪还多!养你有什么用?!”
公公走到前头,不耐烦的催促:“走吧,要不天黑前别想干完活了。”
地里的活重,婆婆没有骂太久,狠狠盯她一眼后,背起农具离开了家。
阿萝放下扁担,把水桶提到水缸边,将水倒进去,估摸着还得往返两趟,才能把水缸填满。
但她现在不能去河边,因为志贵醒了。
阿萝回到房间,志贵正在咬自己的裤腰带,一边咬,一边含糊发着音,口水浸湿了布头,他像在玩一种自己跟自己拔河的游戏。
阿萝把腰带从他嘴里扯出来,帮他穿衣穿裤,擦洗头脸,然后领他去小解。
尽管从小就知道这人是自己的丈夫,她还是迷茫得很,觉得志贵更像自己的弟弟。又因为常常为他的事挨骂,所以她对这个“弟弟”也喜爱不起来,只觉得烦,无穷无尽的厌烦……
志贵朝她傻笑,下身懒散的摆动,她按住他,告诉他:“不要乱动。”
他通常是不听的,乐呵呵的手舞足蹈。
所以尿液洒了满地,也浇湿了她半截裤腿。
腥臊的气息让阿萝沉沉的心,一直往下坠去……
这样的生活,究竟还要过多久?
她觉得自己活得不像一个人。
她觉得自己像头驴,或者……一条狗,畜生似的被这人间的磨砺来回磋磨,哭不出,笑不出,连脾气也没了,日复一日忍着受着,直到死了,才是解脱。
不是没想过逃。
可这世道竟是不给女人活路——朝廷规定,只有男人才能立户。置办田地家业或是招募劳工苦役,也只有男人才行。若她逃走,便只会有两个下场:变成流民乞丐;被拐子卖进风尘地。
阿萝为志贵换了一身衣裤,然后喂他吃饭,他的嘴总是含含糊糊说着话,米粥喂进去,又顺着嘴角流出来,阿萝时不时用帕子擦拭,用尽了耐心。喂饱志贵,她草草喝了半碗稀粥,然后收拾碗筷,接着舀水浇过菜地,打扫鸡舍,同时没忘记清洗自己的裤子。
水缸里的水又快见底了,她哄着志贵到树下看蚂蚁,自己拿起扁担和水桶,抓紧时间出门挑水,要马不停蹄的做午饭。
这次挑水,她遇到了冯婆。
冯婆是村里的老寡妇,无儿无女,不知什么时候起做起了皮肉生意,后来年纪大了,便找些年轻的媳妇去家里过夜,所以名声不大好,村里人对她避之不及,仿佛跟她说一句话,就会被人误会自己不干净。
冯婆扶着树干休息,裤腿上沾了泥,木桶倒在地上,里面的水早已流尽。
阿萝走过去,帮她把桶扶起来,见四下无人,轻声问冯婆:“上次跟您说的事,您想好了吗?”
冯婆看着她摇头:“这不是条好路,我不能害你。好孩子,你还年轻,熬一熬,总会熬过去的,只要熬死了你的公婆,那小子又是个傻的,家里的田地房子都会是你的。”
“若他们都是长寿的命呢?”阿萝低下头,盯着脚尖喃喃,“冯婆,我想要个孩子,我只求您这一次……”
阿萝想要一个孩子。
她已经设想过许多次,女人虽然不能立户,但也有例外——若是怀有身孕的寡妇,便能以腹中骨肉的名义立户。当然,需得男胎才行,若是女胎,只能由娘家领回去,或者借住在亲戚家里。
多么荒唐,她明明是一个完好无损的人,却得靠未成形的胎儿,才能在这片土地站住脚跟。
“冯婆……”阿萝再次缓缓开口,“只要怀了孩子,我就会离开这里,谁也不会知道,也不会怪到您身上,您答应我吧。”
冯婆说:“好孩子,你帮过我,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如今世道这样乱,你无父无母,又没有兄弟姐妹帮扶,若是真怀了身孕,又能去哪里落脚?听冯婆的话,再熬几年,日子会好起来的。”
阿萝轻轻摇头:“我会织布,能裁衣,药材也识得几样,有手有脚总不会饿死。冯婆,您帮我这一次,将来我的孩子便认您做祖母,等您故去了,我和孩子年年给您烧纸。”
老人最怕身后事凄凉,话说到这份上,冯婆已经心动,只是想到阿萝离开村子后会怎样颠沛流离,实在不忍,长长叹了口气后,说:“阿萝,你再让老婆子我想想……”
阿萝不再多劝,去河边帮冯婆打了一桶水,而后自己也打好水,挑着扁担回去了。
中午。
中午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尽管她已经忙了一整个早上,可是每每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会累得不堪重负。
她在厨房里为公婆准备午饭,志贵在院子里吱哇乱叫,他从灶里拿了烧火的柴去捅蚂蚁窝,却点燃了院子里堆放的柴火,火势一大,他便害怕的叫起来,阿萝出来瞧见,吓出一身冷汗,她立刻舀水灭火,又夺了他手里烧到半截的柴。
刚才一直在厨房里忙活,实在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拿的。
家里有个傻小子,再平常的环境也变得处处危险,阿萝只好把志贵关进屋子里,任凭他大哭大闹也不开门。
她把做好的面条和菜卤子用罐子温着,放进菜篮,匆匆往田地里去。
地里不少人在树下休息,隔壁大婶正聊起自己孙子——
“儿子去打仗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这家里头没个男人怎么过?幸好我那儿媳肚子争气,一连生了两个小子,以后啊,我就指着这两小子长大孝敬我咯……”
阿萝一面将罐子里的面条盛出来,一面默默听着,心想这世道实在荒唐,男人都去打仗了,留下一群老人女人,每天互相争着比着,儿子,孙子……儿子,孙子……家里没个男人,就仿佛低人一等。
愿老天保佑,一定要让她怀上儿子。
“傻愣在这里做什么?!”婆婆突然发怒,“还不赶紧给我回去?!留志贵一个人在家里,要出什么好歹,看我不打死你!”
阿萝愣了愣,看着菜篮和罐子,“那罐子……”
“我和志贵他爹会带回去!你回去看着志贵!”婆婆骂道,“呆蠢的猪样儿,白吃家里的米粮!养了几年不下一个蛋,送个饭也拖拖拉拉!老娘真是上辈子倒了血霉才娶你这扫把星回来!赶紧给我滚回去!志贵在家要是有什么差错,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她低着头起身,也不辩驳什么,默默往回走。
她知道,是隔壁大婶的话刺痛婆婆了。志贵没被抓去当兵丁,是因为他是个傻子,婆婆永远等不到儿孙孝敬自己的那一天。
阿萝回到家时,志贵已经没再喊叫了。
她饥肠辘辘,又渴又累,打算先用锅里剩下的面条填饱肚子,再单独给志贵烙两张饼吃。
可是一进屋,便闻到难以忽略的粪臭,她心知不好,竟也没感觉多少意外,打开上锁的房门,看见志贵拉了满地水粪,地上,床上,桌椅柜子,全被糊上了粪便痕迹,而志贵正躺在沾满脏污的被单上呼呼大睡。
阿萝定定站在房门口,心中忽生一股悲凉。
愤怒吗?委屈吗?……恨吗?若日复一日这样的生活,便什么情绪都是徒劳。
她转身,关门,去厨房盛了一碗已然冷掉的面条,端起来,一边吃着面,一边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而后连同面条一起吃进嘴里,用力吞咽。
填饱了肚子,才有力气干活。
她收拾好厨房,拿上水盆和抹布,再次返回房间,认命一般开始打扫,打扫,打扫……
打扫。
……
公婆今天回来得尤其晚,两个人的神情都有些古怪。
婆婆看见院子里堆着没来得及洗净的被单,竟没骂她,只冷淡瞟她一眼,说道:“你是志贵的媳妇,照顾他是你的本分,等以后生了孩子,爹娘都不会亏待你的。”
阿萝坐在院子里,搓洗着手里的衣物,听见婆婆的话,有些莫名。
平日里对她从来没个好脸色,今天这是怎么了?
婆婆见她木讷的样子,脸上显出几分厌烦,又道:“行了,去做饭吧。这些我来洗,就你那磨蹭性子,洗到天亮也别想洗完。”
阿萝犹豫的起身,往厨房去。
脚刚迈进厨房,又听见婆婆在院子里吩咐:“把梁上那半斤熏肉切了蒸熟,再炒几个鸡蛋。”
家里并不富裕,如今又不是逢年过节的日子,为何要吃肉?阿萝心中不解,但还是乖觉的应了一声。
等晚饭备好,一家四口聚在桌边吃饭,婆婆不停的把鸡蛋和肉往儿子碗里夹,语气亲热:“志贵乖,多吃点,身体长壮壮……”
志贵好久没沾肉腥,吃得狼吞虎咽,下巴到胸襟全是口水与菜汤。
公公在一旁抽着土烟,一言不发。
“阿萝,吃完没有?”婆婆说道,“吃完了就快回屋去洗澡,水已经烧好了。”
阿萝愣愣看向婆婆。平日里洗衣做饭烧水,哪一样不是自己干?今天婆婆这么多异常举动,难道……
她心底咯噔了一下。
脸色随之变白。
婆婆却已然不耐烦,厉声喝道:“你是哑了还是聋了?我叫你回屋洗澡!”
阿萝赶紧起身,埋着头回屋去。
——屋里有一盆热水,桌上点着两根红烛,床上还铺着一张白色帕子。阿萝心如明镜,知道婆婆不能等了,无论如何,也想要志贵和她圆房。
可是志贵懵懂如孩童,这圆房,到底要怎样圆?
阿萝对这事全然不懂,平时去河边打水时,偶尔会听见村里的女人说些荤话,也将将听个一知半解,只知道男人女人做了那事,就能怀上孩子。
可她不想怀志贵的孩子。
志贵是个傻子,万一生下的孩子是个小傻子,她该怎么办?
事到如今,她如何想已经不重要了。他们要她圆房,她根本拒绝不了。
阿萝默默擦洗身体,换了一套干净衣服,坐在床上等。
外面很快传来动静。
婆婆哄着志贵开了门,说道:“乖宝,按你爹教的法子做,做好了,娘明天给你炖鸡汤补身子。”
志贵看着床上的阿萝,眉开眼笑:“生娃娃,我和媳妇生娃娃……”
房门关上,哐当一声,随后又有金属磕碰的声响。阿萝听得出,是公婆在屋外落了锁。
她轻轻抿唇,往床里挪了挪。她不怕志贵,只是对那即将发生的事,心底到底有些畏惧。
志贵显然被公公教导过,嬉笑着过来,扒拉阿萝的裤子。他太孩子气,扯了几下也没能解开阿萝的腰带,嘴里嘟嘟囔囔:“不好玩……不好玩……”
外头传来婆婆的声音:“志贵乖啊!等志贵当了爹,就有小娃娃陪你玩了!”
“小娃娃,我要小娃娃陪我玩!”志贵眉开眼笑,更使劲的拽阿萝的腰带。
阿萝被他拽得有些吃不消,知道自己今晚逃不掉,索性配合他,轻轻柔柔按住志贵的手,说:“你别扯了,我来吧。”
平日里多是她照顾志贵,志贵不胡闹时还算听话,当下松了手,憨笑着盯着阿萝的裤裆。
眼下也无所谓什么羞耻心了,只当他是个不懂事的孩子,阿萝默默脱下自己的裤子,然后去解志贵的裤子。
志贵的身体算得上细皮嫩肉,家里好吃好喝供着他,也不需他干活,肚子上还养出了几两赘肉,白白软软的,再往下,是稀拉拉几根毛,两腿间坠着一团肉,混着一股尿腥味,宛如阴沟里不见天日的鼻涕虫。
哪怕阿萝毫无经验,也从村里那些妇人口中得知,想要生娃娃,必须得让男人那物,放进女人里面才行。
公公大约也是这样教志贵的,志贵傻乎乎的凑到近前,他一贴过来,阿萝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下意识就想将他推开,却不得不暗暗忍耐。
她的丈夫一时傻笑,一时大叫,贴着她蹭了又蹭,“进不去!娃娃在里面,我要进去玩娃娃!”
阿萝听了,既觉得可笑,又觉得自己悲凉,她躺在床上,只想这一切尽快结束。
这时,志贵突然撤身离开。阿萝愣了愣,撑着手肘起身,便见志贵抱着尿壶过来,朝她咧着嘴笑,“给娃娃玩大宝贝,让娃娃出来玩……”
他抱着尿壶上床,阿萝吓一跳,几乎是本能的并拢了腿!侧身躲开,壶里的尿液洒了满床!
阿萝狼狈的爬下床道:“志贵,志贵快住手!别这样!”
可志贵认定了她那里头有娃娃,抱着尿壶又追过来,大喊大叫:“娃娃!我要娃娃!娃娃出不来!”
“志贵!……”阿萝从床边抓起自己的裤子,一边遮掩,一边着急道,“志贵,你放下……你别乱来……”
阿萝逃得太快,志贵没扑到她,反而捧着尿壶摔了一跤,他咧嘴正要哭,看见柜子上的针线篓子,不知想到什么,又笑起来,欢天喜地跑过去,一把拿起针线篓里的剪刀,转身看向阿萝:“剪开,剪开娃娃就能出来了!阿萝剪开!”
“志贵!”阿萝脸色全白,步步往后退,直退到门板。
眼看志贵举着剪刀扑来,她惊恐的大叫:“爹!娘!——啊!!!”
门外无声无息,听不到半点动静,她仓惶躲着逃着,逼仄的一间小屋,竟成了她的地狱!志贵追不上她,急了,手里的剪刀直直扔过来!那尖头刺在她肩上,惊恐下阿萝尖声喊道:“救命啊!”
呼救声太过凄厉,使得外面一下子嘈杂起来,邻居家的狗狂吠不止,陆续有人从自家出来,站在院外好奇的张望。
外面发生了什么阿萝浑然不知,只觉得伤口剧痛难忍,身后的志贵也被吓到,他看见阿萝身上鲜血汩汩涌出,瞬间染红了大片衣裳。
“血啊,血……要死了,要死人了!”志贵吓得大哭,“哇啊啊啊!……”
阿萝艰难穿上裤子,还要安抚志贵:“志贵,别哭了,别哭……”
房门哐哐作响,公婆终于把门打开,看见屋内一片狼藉,不等阿萝出声解释,婆婆举起一根秃头扫帚狠狠打过来!
“没用的东西!养了你十年连颗蛋也不会下!养你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骂一句,打一下!
打一下,骂一句!
“每日米面养着你,光长一身白肉!连蛋也不下!你怎么不投身个猪胎去!猪都知道下崽!你连猪也不如!挨千刀的丧门星!”
阿萝浑身痛,那扫帚劈头盖脸往身上砸,她抱住自己闷头承受,眼泪大颗往外涌。
志贵的哭声渐远,似是被公公拉出去了,又过一会儿,婆婆终于打累了,扔了扫帚,指着她骂道:“把屋子给我收拾干净!再把衣服洗了!干不完活明天就滚去睡猪圈!”
阿萝蜷缩在地上,瑟瑟点了下头。
婆婆转身出去,步子带着火气,又急又重。
四周慢慢安静下来……
隔着屋门,能听见志贵断断续续的哭声,婆婆耐着性子哄他,公公时不时叹气……外面的狗吠声平息了。
阿萝扶着墙,小心翼翼站起来,她浑身疼,肩上的伤口仍在流血,只能用手勉强捂住,目光扫过室内,桌椅凳子倒在地上,尿壶洒了一地尿渍,床褥也被浸湿,满屋狼藉。
阿萝垂下眼帘,不知该作何想,在这片杂乱中静默站了片刻,开始慢慢收拾屋子。
扶起桌椅板凳,捡起剪刀,尿壶拿去外面涮洗干净,然后回屋撤掉床褥,最后将床单卷成一圈,背在肩上,走出门外。
她在院子里拿了木盆与捣衣槌,慢慢往河边走……
院子外的村人早已散了,只零星几个,还在自家门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张望。
阿萝隐约看见了冯婆,没有在意,目视前方,安安静静往前走。
阿萝一直走,一直走……
脚下的路渐渐湿润,河水浸润了脚底,她放下木盆与棒槌,眼前黑沉沉的河水,一如抬头望不到一丝光亮的夜空。
鬼使神差的,她继续往前迈了一步。
夜里的河水冰凉刺骨,浸没了她的脚踝,接着是小腿,膝盖,大腿……阿萝心中萌生一个念头:不如,就这么走下去吧?
不如,去另一个世界。
若有下辈子,想做不知疾苦的虫蚁,想做青天作伴的飞鸟,想做水底畅游的河鱼,想做一棵树,一樽石,一株草……总归是,不想做人了。
冰凉的水浸没胸口,一颗心仿佛也跟着凉掉,她闭上眼,想要一了百了,身后却忽然有股力拽住她!
“阿萝!你何苦想不开啊!”冯婆死死抱住她的腰,老迈沙哑的声音充满悲怆,“好死不如赖活!熬过这一劫,以后必将有大把好日子等着你!听老婆子的话,快回家去,最多等三日,我一定想法子叫你怀上孩子!”
阿萝如梦初醒,转身怔怔看向冯婆。
冯婆紧握她的双臂,字字恳切:“好阿萝,听冯婆的话,不要再寻短见!外头见天的打仗,即便你逃了,你公婆也绝不可能扔下傻儿子去寻你,你只管揣好肚子里的娃娃,安安生生往那不打仗的地方去!等孩子养大,你会有儿媳,有孙子,有子子孙孙供养,不会像冯婆这般孤苦伶仃!”
阿萝哭起来:“冯婆……”
冯婆把她拽上岸,再次催促:“快回去吧!”
阿萝哭着点头,抱起洗衣物什回去了。
冯婆做的生意,不太干净,叫暗娼,村里人也叫暗门子。
以前冯婆自己做,后来年纪大了,加上年年打仗,村里许多人家都过不下去,便有些女人来冯婆这里“做工”,每做一次,冯婆收取一些住宿钱。
因为男人都被朝廷征兵走了,故而光顾冯婆这里的客人,大多来自附近驻扎的一个兵营。
这些大头兵手里有钱,却无处消遣,每日除了操练还是操练,日子过得苦闷,偶尔遛出兵营厮混,只要不惹出大事,他们的长官也会睁只眼闭只眼。
冯婆为阿萝挑中的人,正是这些大头兵之一。
此人叫杨骁,生得人高马大,样貌俊朗,冯婆第一眼见到,便觉得合眼缘,若能和阿萝生下孩子,那孩子定然也俊秀可爱。
跟杨骁一起来的,是冯婆的熟客,叫张成海。
张成海揽着杨骁的肩,熟门熟路往冯婆屋里走,边走边道:“天天在那营帐里闷着,人都给闷臭了,今天哥们给你介绍个好地儿,保管你睡一个好觉!总不能哪日去战场上送了命,连女人滋味也没尝过几次!亏不亏?!”
杨骁懒洋洋的,“营里有女人,何必绕这么远的路。”
张成海大嗓门的道:“统共就那么十几个,看都看腻了!也就那个叫萍儿的不错,可她是百长看中的女人,谁敢沾身?”
说完话,张成海冲守在门口的冯婆嘻嘻一笑,问:“冯婆,阿惠在不在?”
冯婆笑道:“在、在,一直等着您呢!”
“冯婆,也给我这小兄弟安排个小嫂子呗!”张成海嬉笑道。
来冯婆这里做工的,都是村里的媳妇嫂子,家里没有男人,又要养老人孩子,不得不委身出来赚活命钱。
冯婆笑眯眯的说:“不巧,现在屋里只有阿惠一个人,要不您先过去?老婆子给两位烧点热水,等晚些了,多来几个媳妇嫂子,再看您这位兄弟喜欢什么样的……”
“成,再给整些酒菜来!”张成海摸出一枚碎银,出手很是阔绰。
他拍拍杨骁的肩,给兄弟一个嘚瑟眼神,说:“哥们,我先去了~”
杨骁:“…………”
“小军爷,您这边请。”
冯婆弓着身子,将杨骁领去院子里另一间房。
屋门打开,里头昏黑一片,不知是不是杂物房改的,连扇窗子也没有,不过床褥卧具全齐,有桌有椅,冯婆点燃烛火,又端来茶水,哪怕没窗子,也比兵营不知好了多少倍。
至少没有某些人的臭脚丫子味儿。
杨骁直接在床上卧倒,抻了抻胳膊,甭管今晚有没有女人来,就这么睡一觉也舒服。最近操练得紧,据传齐国马上就要打过来了,这样的安稳觉以后会越来越少。且睡且珍惜吧。
“听军爷口音,像是渝北人?”冯婆问。
杨骁微愣,笑着坐起身,“瞧您一把年纪了,耳朵还挺尖,我家是渝北的,岚山村,您知道吗?”
冯婆回道:“我夫家一个妹妹嫁去渝北,不过去的是兰坡村。”
“兰坡村……”杨骁回忆片刻,轻轻摇头,“没听说过。”
说完一笑,自嘲道:“我出来时才十二岁,半大小子,周边几个村子也没混熟,一转眼都快十年了,也不知家里的老娘怎么样了……”
冯婆试着套话:“家里没有兄弟姐妹照顾吗?”
“四个哥哥被抓去当兵丁,音讯全无,我走的时候,家里只剩老母亲一个。”杨骁苦笑,他平日里寡言少语,看到冯婆难免想起自己的母亲,多说了几句。
冯婆又问:“即便兄弟不在,那叔叔伯伯……”
“我父亲,连同五个叔伯,一起被皇帝抓去修皇陵,死在半路上了。”杨骁淡淡回道。
冯婆心中惊叹,真真了不得,家里连他一共五个男丁,再往上父辈又有六个男丁,阿萝若想一举得男,运道可不就在应这男人身上?
杨骁察觉到冯婆的目光异样,狐疑的看她一眼。
冯婆忙道:“您先歇着,我去外面招呼。”
说完话,小心翼翼关上门,便马不停蹄往阿萝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