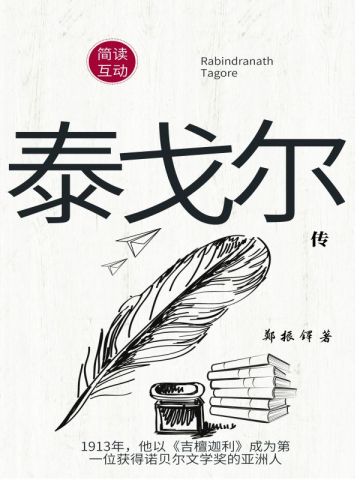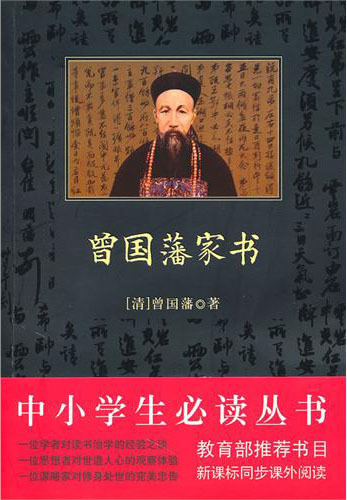天地虽寬靡所容!长淮誰是主人翁?
江南父老还相念,只欠一帆东海风。
——文天祥:《旅怀》
一
他們是十二个。杜滸,那精悍的中年人,叹了一口气,如释重負似的,不择地的坐了下去。刚坐下,立刻跳了起来,叫道:
“慢着!地上太潮湿。”他的下衣已經沾得淤湿了。
疲倦得快要瘫化了的几个人,听了这叫声,勉强的掙扎的站着,背靠在土墙上。
一地的湿泥,还杂着一堆堆的牛粪,狗粪。这土围至少有十丈見方,本是一个牛栏。在这兵荒馬乱的时候,不知那些牛只是被兵士們牵去了呢,还是已經逃避到深山里去,这里只剩下空空的一个大牛栏。湿泥里吐射出很浓厚的腥騷气。周遭的粪堆,那臭恶的气味,更陣陣的扑鼻而来。他們站定了时,在靜寂清鮮的夜間的空气里,这气味兒益发重,益发难聞,随了一陣陣的晚风直冲扑而来。个个人都要呕吐似的,长袖的袖口連忙紧掩了鼻孔。
“今夜就歇在这土围里?”杜滸无可奈何的問道。
“这周围的几十里內,不会有一个比这个土围更机密隐秘的地方。我們以快些走离这危险的地带为上策,怎么敢到民家里去叩門呢?冷不防那宅里住的是韃子兵呢。”那作为向导的本地人余元庆又仔細的叮囑道。
十丈見方的一个土围上面,沒有任何的蔽盖。天色蓝得可爱。晶亮的小星点兒,此明彼灭的似在打着灯語。苗条的一弯新月,正走在中天。四围靜悄悄的,偶然在很远的东方,有几声犬吠,其声凄惨的象在哭。
露天的憇息是这几天便过慣了的,倒沒有什么。天气是那末好。沒有一点下雨的征兆。季春的气候,夜間是不凉不暖。睡在沒有蔽盖的地方倒不是什么难堪的事。所难堪的只是那一陣陣的腥騷气,就从立足的地面蒸騰上来,更有那一陣陣的难堪的粪臭气浓烈的夹杂在空中,熏冲得人站立不住。
“在这个齷齪的地方,丞相怎么能睡呢?”杜滸躊躇道。
文丞相,一位文弱的書生,如今是改扮着一个商人,穿着蓝布衣褲,腰系布条,足登草鞋。虽在流离顛沛之中,他的高华的气度,渊雅的局量,还不曾改变。他忧戚,但不失望。他的清秀的中年的脸,好几天不曾洗了,但还是那末光潤。他微微的有些愁容。眉际聚集了几条皺紋,表示他是在深思焦虑。他疲倦得快要躺下,但还勉强的站立着。他的手扶在一个侍从的肩上,足底板是又痠痛,又湿热;过多的汗水把袜子都浸得湿了,有点怪难受的苦楚。但他不說什么,他能够吃苦。他已經历过千辛万苦;他还准备着要經历千百倍于此的苦楚。
他的头微微的仰向天空。清丽的夜色仿佛使他沉醉。凉颸吹得他疲劳的神色有些苏复——虽然腿的小肚和脚底是仍然在痠痛。
“我們怎么好呢?这个地方沒法睡,总得想个法子。至少,丞相得憇息一下!”杜滸热心地焦急着說道。
文丞相不說什么,依然昂首向天。誰也猜不出他是在思索什么或是在領略这夜天的星空。
“丞相又在想詩句呢!”年輕的金应悄悄的对邻近他身旁的一个侍从說。
“我們得想个法子!”杜滸又焦急的喚起大家的注意。
向导的余元庆說道:“沒有别的法子,只能勉强的打扫出一片干凈土出来再說。”
“那末,大家就动手打扫,”杜滸立刻下命令似的說。
他首先寻到一条树枝,枝头綠叶紛披的,当作了扫帚,开始在地上扫括去腥湿的秽土。
个个人都照他的榜样做。
“你的泥水濺在我的脸上了!”
“小心点,我的衣服被你的树枝扫了一下,沾了不少泥浆呢。”
大家似乎互相在咆吼,在責駡,然而一团的高兴,几乎把刚才的过分的疲倦忘記了。他們孩子們似的在打閙。
不知扫折了多少树枝,落下了多少的綠叶,他們面前的一片泥地方才显得干凈些。
“就是这样了罢,”杜滸叹了一口气,放下了他的打扫的工作,不顧一切的首先坐了下去。
一个侍从,打开了文丞相的衣包,取出了一件破衣衫,把它鋪在地上。
“丞相也該息息了,”他怜惜的說道。
“諸位都坐下了罢,”文丞相藹然和气的招呼道。
陆陆續續的都围住了文丞相而坐下。他們是十二个。
年輕的金应道:“我覚得有点冷,該生个火才好。”
“刚才走得热了,倒不覚什么。現在坐定了下来,倒眞覚得有些冷抖抖的了。”杜滸道。
“得生个火,我去找干树枝去。”好动的金应說着,便跳了起来。
向导,那个瘦削的終年象有深忧似的余元庆,立刻也跳起身来,挡住了金应的去路,严峻的說道:“你干什么去!要送死便去生火!誰知道附近不埋伏着韃子兵呢?生火招他們来么?”
金应一肚子的高兴,橫被打断了,咕嘟着嘴,自言自語道:“老是韃子兵韃子兵的吓唬人!老子一个打得他媽的十个!”然而他終于仍然坐了下去。
“韃子兵不是在午前才出来巡邏的么?到正午便都归了队,夜間是不会来的。”杜滸自己寬慰的說道。
“那也說不定。这里离瓜州揚子桥不远,大軍营在那边,时时有征調,总得格外小心些好。”余元庆的瘦削見骨的脸上露出深謀远虑的神色。
文丞相只是默默的不响,眼睛还是望着夜天。
鐮刀似的新月已經斜挂在偏西的一方了;东边的天上略显得阴暗。有些烏云在聚集。中天也有几朵大的云块,横亘在那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出現的。
晚风漸漸的大了起来。土围外的树林在簌簌的微語,在凄楚的呻吟。
二
沉默了好久。有几个年輕人打熬不住,已經横躺在地上睡熟了;呼呼的发出鼾声来。金应是其一,他呼嚕呼嚕的在打鼾,仿佛忘記了睡在什么地方。
文丞相耿耿的光着双眼,一点睡意也沒有。他的腿和脚經了好一会的休息,已不怎么痠楚了。
他低了眼光望望杜滸——那位死生与共,为了国家,为了他,而牺牲了一切的义士。杜滸的眼光恰恰也正凝望着他。杜滸哪一刻曾把眼光离开了他所敬爱的这位忠貞的大臣呢!
“丞相,”杜滸低声的喚道;“不躺下息息么?”他爱惜的提議道。
“杜架閣,不,我閉不上眼,还是坐坐好。你太疲乏了,也該好好的睡一会兒。”
“不,丞相,我也睡不着。”
文丞相从都城里带出来的門客們已都逃得干干凈凈了;只剩下杜架閣是忠心耿耿的自誓不离开他。
他們只是新的相識。然而这若干日的出死入生,患难与共,使得彼此的肺腑都照得雪亮。他們俩几成了一体。文丞相几乎沒有一件事不是依靠架閣的。而杜架閣也尝对丞相吐露其心腑道:
“大事是不可为的了!吳坚伴食中書,家鉉翁衰老无用,賈余庆卑鄙无耻;这一批官僚們是絕对的不能担負得起国家大事的。只有丞相,你,是奋发有为的。他們妒忌得要死,我們都很明白。所以,特意的設計要把你送到韃子的大营里去講和。这魔穴得离开,我們該創出一个新的有作为的局面出来,才抵抗得了那韃子的侵略。这局面的中心人物,非你老不成。我們只有一腔的热血,一双有力的手腕。拥护你,也便是为国家的复兴运动而努力。”
丞相不好說什么,他明白这一切。他时刻的在罗致才士俊俠們。他有自己的一支子弟兵,訓練得很精銳;可惜粮餉不够——他是毁家勤王的——正和杜滸相同。人数不能多。他想先把握住朝廷的实权,然后徐图展布,彻底的来一次扫蕩澄清的工作。然而那些把国家当作了私家的产业,把国事当作了家事的老官僚們,怎肯容他展布一切呢!妒忌使他們盲了目。“宁願送給外賊,不願送給家人”,他們是抱着这样的不可告人的隐衷的。文天祥拜左丞相的諭旨刚刚下来,他們便設下了一个毒計。
蒙古帅伯顏遣人来邀請宋邦負責的大臣到他軍营里开談判。
这难題困住了一班的朝士們,議論紛紛的沒有一毫的定見。誰都沒有勇气去和伯顏談判。家鉉翁是太老了,吳坚是右丞相,政府的重鎮,又多病,也不能去。这难題便落在文天祥的身上。他是刚拜命的左丞相,年刚气銳,足以当此大任。大家把这使命,这重責,都想往他身上推。
“誰去最能胜任愉快呢?”吳坚道。
“这是我們做臣子的最好的一个效力于君国的机会,我倒想請命去,只可惜我是太老了,太老了,沒有用。”家鉉翁喘息的說道,全身安頓在东边的一张太师椅上。
“国家兴亡,在此一举,非精明强干,有大勇大謀的不足以当此重任,”賈余庆献諛似的說,两眼老望着文天祥。他是别有心事的:文天祥走了,左丞相的肥缺兒便要順推給他享受了,所以他慫恿得最有力。
朝臣們紛紛的你一言我一語的,都互相在推諉,其意却常在“沛公”。
那紛紛营营的靑蝇似的声响,都不足以打动文天祥的心。在他的心里正有两个矛盾的覌念在作战。
他不曾預备着要去。幷不是退縮怕事。他早已是准备着为国家而牺牲了一切的。但他恐怕,到了蒙古軍营里会被扣留。一身不足惜,但此身却不欲便这样沒有作用的給糟蹋掉。
当陈宜中为丞相的时候,伯顏也遣人来要宜中去面講和款,那时天祥在他的幕下,再三的諍諫道:
“相公該为国家自重。蒙古人不可信,虎狼之区万不宜入。若有些許差池,国家将何所賴乎?”
宜中相信了他的話,不曾去。
如今这重担是要挑在他自己的身上了。他要为国家惜此身。他要做的事比这重要得多。他不願便这样輕忽的牺牲了。他还有千万件的大事要做。
他明白自己地位的重要,責任的重大。他一去,国家将何所賴乎?杜滸,他的新相識的一位俠士,也极力的阻止他去;劝他不要以身入虎口。杜滸集合了四千个子弟兵,还有一腔的热血,要和他合作,同負起救国的責任。也有别的門客們,紛紛扰扰的在发揮种种不同的意見。但他相信,純出于热情而为远大的前途作打算者,只有一个杜滸。
然而,文天祥在右丞相吳坚府第里議事时,看見众官們的互相推諉,看見那种卑鄙齷齪的态度,临难退縮,見危求脫的那副怯懦的神气,他不禁覚得有些冒火。他的双眼如銅鈴似的发着侃侃的恳摯的光亮。他很想大叫道:
“你們这批卑鄙齷齪的懦夫們呀,走开;讓我前去吧!”
然一想到有一个更大的救国的使命在着,便勉强的把那股憤气倒咽了下去。他板着脸,好久不开口。
但狡猾如狐的賈余庆,却老把眼珠子溜到他身上来,慢条斯理的說道:
“要說呢,文丞相去是最足以摧折强虏的銳鋒——不过文丞相是国家的柱石——”
他很想叫道:“不錯,假如我不自信有更重要的使命的話,我便去了!”
然終于也把这句不客气的話强咽了下去。
“文丞相論理是不該冒这大险。不过……国家在危急存亡之候,他老人家……是最适宜于担着这大任的。”吳坚也吞吞吐吐的应和着說道。
一个丑眉怪目的小人,刘岊,他是永远逢迎着吳坚、賈余庆之流的老官僚的,他挤着眼,怪惹人討厌的尖声說道:
“文丞相耿耿忠心,天日可鉴;当此大任,必不致貽国家以忧戚。昔者,富郑公折辱辽寇……”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方张的寇势,能以一二語折之使退么?这非有心雄万夫的勇敢的大臣,比之富郑公更……”賈余庆的眼鋒又溜到文天祥的身上,故意的要激动他。
对于这一批老奸巨猾們的心理,他是洞若覌火的。他实在有些忍不住,几乎不顧一切的叫道:
“我便去!”
他究竟有素养,还是沉默着,只是用威严有棱的眼光,来回的扫在賈余庆和刘岊們的身上。
一时敞亮的大厅上,鴉雀无声的悄靜了下来,虽然在那里聚集了不下百余个貴官大僚。
空气石块似的僵硬,个个人呼吸都艰难异样。一分一秒鐘,比一年一紀还难度过。
还是昏庸异常的右丞相吳坚打破了这个难堪的局面:
“文丞相的高見怎样呢?以丞相的大才,当此重任,自能綽有余裕,国家实利賴之。”
他不能不表示什么了。鋒棱的眼光横扫过一堂,那一堂是行尸走肉的世界;个个人都低下了眼,望着地,仿佛內疚于心,不敢和他的銳利如刀的眼光相接触。他在心底深喟了一声,沉痛的說道:
“如果实在沒有人肯去,而諸位老先生們的意見,都以为非天祥去不可的时候,天祥願为国家粉碎此无用之身。惟恐囂张万状的强虏,未必片言可折耳。”
如护国的大神似的,他坐在西向一张太师椅上。西斜的太阳光,正照在他的身上,投影于壁,碩大无朋,正足以于影中籠罩此群懦夫万輩!
个个人都象从危难中逃出了似的,松了一口气。
文天祥轉了一个念,覚得毅然前去,也未尝不是一条活路。中国虽曾扣留了北使郝經到十几年之久——那是賈似道的荒唐的挑衅的盲举,但北廷却从不曾扣留过宋使。奉使講和的人,从不曾受过无礼的待遇。恃着他自己的耿耿忠心,不惧艰危,也許可以說服伯顏,保全宋室,使它在不至过分难堪的条件之下,偷生苟活了若干时,然后再徐图恢复、中兴。这未必較之提万千壮丁和北虏作孤注一擲的办法便有逊。这也是一个办法。即使冒触虏帅而被羈,甚至被杀,还不是和战死在战場上一样的么?人生总有一个死,随时随处无非可死之时地,为国家,个个人都該貢献了他的生命,而如何死法,却不是自己所能自主的。为政治活动者,正象入伍当一个小小的兵丁,自己是早已丧失了自由的——自己絕对沒有选择死的时和地的自由。
况且北虏的虛实,久已传聞异辞,究竟他們的軍队是怎样的勇猛,其各軍的組織是怎样的,他們用什么方法訓練这长胜之軍,一切都該自己去仔細的考察一下,作为将来的准备。那末,这一行,其意义正是至重且大。
这样一想,他便心平气和起来,随即站起身来,說道:
“諸位老先生,事机危矣,天祥明天一早便行;現在还要和北使面談一切。失陪了。”
头也不回的,刚毅有若一个鉄鑄的人,踏着坚定的足步离开大厅而去。
三
想不到北虏居然出乎例外的会把他羈留着。
杜滸听見了他出使的消息,焦急的只頓足。見了他,只是茫然若有所失;也更說不出什么刺激或劝阻的話来。他覚得,这里面显有极大的阴謀。他不相信文丞相不明白。他奇怪的是,丞相为什么毅然肯去。
“难道我們的計划便通盘打消了么?”他輕喟的对天祥說道。
“不过,这一着也是不得已的冒险的举动——战爭还不象賭博,每一次都在冒险么?我們天天都要准备站在最前綫。又何妨冒这一次险。其实,我的目的还在覌北虏的虛实——你明白我的心事,我去了,你要加紧的訓練着軍士。更艰危的責任,是在你們的身上!”天祥說着,有些黯然,他实在莫測自己此行的前途。
杜滸瞿然的跳叫道:“不然,不然!丞相在,国便在!丞相去了,国事将靠誰支持?吳坚、賈余庆……不,不,他們岂是可以共事的人!丞相旣然决心要出使,那末我也随去,也許有万一的帮助。假如北虏有万一不測的举动,我們得設法躱逃。丞相以一身担国家大事,为責甚重。决不可視自身过輕。要知道我們的身体,已許于国,便是国家的,而不是自己的了!……至于我的子弟兵,那很容易措置,还不是有我的族弟杜渚在統率着么?他是不会誤事的。”
天祥热切的握住了杜滸的手,感动得說不出話来,良久,才道:
“杜义士,我是国之大臣,应該为国牺牲。义士何必也随我冒这大险呢?”
“不,不,我此身是屬于国的,也是屬于丞相的。丞相的安危,便是国家的安危!我要追随着丞相的左右,万死无悔!”他的眼眶有些泪点在轉动。
天祥很兴奋,知道宋朝还不是完全无人!天下的壮士們是尽可以赤誠热血相号召的。同时奋然自拔,願和他同去的,又有門客們十余人,随从們十余人。
想不到一到北营便失了自由,一切計划,全盘的被推翻。北虏防御得那末周密,他們的軍士們是那末守口如瓶。天祥們决无探訪一切的可能。他們的虛实是不易知的。但所可知的是,他們已下了一个大决心,要掠夺南朝的整个江山,决不是空言所能折服的。
他对伯顏說了上千上万的話;話中带刺,話里有深意。說得是那末恳切,那末痛切,說得是那末慷慨激昂,不亢不卑,指陈利害是那末切当;听得北虏的大将們,个个人都为之愕然惊叹。他們从不曾遇到那末漂亮而刚毅的使臣。
他們在中央亚細亚,在波斯,在印度,灭人国,墟人城,屠毁人的宗社,視为慣常不足奇的事。求和的,投降的使臣們不知見了千千万万,只有哀恳的,訴苦的,卑躬屈节的,却从来不曾見过象这位蛮子般的那末侃侃而談,旁若无人的气槪。
出于天然的,他們都咬指在口,嘖嘖的叹道:
“好男子,好男子!”
伯顏沉下了脸,想发作,終于默默无言。几次的爭辯的結果,伯顏是一味敷衍,一味推托;总說沒有推翻南朝社稷之心,总說絕不会伤害百姓,总說要听命于大皇帝。但文天祥現在是洞若覌火的明白蒙古人的野心;他們不象过去时代的辽、金,以获得一部分的土地和多量的岁币与賄賂为滿足的。挡在蒙古人鉄蹄之前的,决不会有完整的苟全的一片土。他們扫蕩,排除,屠杀一切的障碍,毫不容情,毫不客气。在他們的字典里沒有“怜恤”这一个名辞。
文天祥警覚到自己这趟的劳而无功;也警覚到自身的危险。然而他幷不气餒。条件总是談判不下,蒙古兵不肯退,也不叫文天祥回去,只是一天天的敷衍推托着。派他們二个貴族的将官們,天天同天祥作館伴,和他上天下地的瞎聊天。趁着这个机会,文天祥恳切的把能說的,該說的話都說尽了;說到了南朝的历代深仁厚澤,說到了南方人民們的不易統治,說到了蒙古人之必不能适宜于南部的生活,說到了几代以来南朝与蒙古皇帝的眞誠的合作,說到了南北二朝有共存共荣的必要。他几乎天天都在热烈的游說、辯难着。
那两位貴酋,也高高兴兴的和天祥折难,攻駁,但一到了紧要关头,便連忙顧左右而言他,一点兒眞实的意見也不肯表示。蒙古人集重兵于临安城下,究竟其意何居呢?講和或要求投降?誰都沒有明白的表示。
然而在那若明若昧,閃閃爍爍的鬼祟态度之下,文天祥早看穿了他們的肺腑。他們压根兒便沒有講和的誠意。已經快到口的一块肥肉,他們舍得輕易放弃了么?
捉一个空,天祥对杜滸低声的叹息道:“北虏此来,志不在小。只有拚个你死我活的分兒;决沒有可以苟全之理!饒你退讓到絕壁,他們也还是要追迫上来的。講和,只是一句門面話。我懊悔此行。以急速脫出为上策。此事只可和君說!走!除了用全力整軍經武和他們周旋之外,沒有第二条路可走!”
杜滸慷慨的說道:“一切都会在意,我早就看穿了那些狼子們的野心了!”
坚定的眼光互相凝望着。他們的前途明明白白的摆放在那里;沒有躊躇、徘徊、退縮、躱避的可能。
四
从降臣呂师孟叔侄到了軍中,北虏的情形益加叵測。大营里天天有窃窃私語声,不知講論些什么。一見到文天祥走近,便都緘口不言。天祥好几次求見伯顏,欲告辞归之意,只是托辞不見,故意拖延了下去。告二貴酋,要求其轉达,也只是唯唯諾諾的,不置可否。而防卫加严,夜間門外有了好几重的守卫。鉄甲和兵器的鏗鏗相触声,听得很清楚。
終于見到了伯顏。天祥直前詬斥其失信:“說是送我归朝,为何还迟延了下去呢?有百端的事待理。便講和未成,也該归朝和諸公卿商議,明奏皇上,别定他計。为什么明以館伴相礼,而实阴加监視呢?”
伯顏只以虛言相慰。天祥声色俱厉在呵責,求归至切。呂文煥适在旁坐,便劝道:
“丞相且請寬心住下;朝事更有他人可理会。南朝也将更有大臣来請和。”
天祥睜目大怒,神光睦睦可畏,駡道:“你这卖国的乱賊,有何面目在此間胡言乱語!恨不族灭你!只怪朝廷失刑!更敢有面皮来做朝士?汝叔侄能杀我,我为大宋忠臣,正是汝叔侄周全我。我又不怕!”
北酋們个个都动容,私語道:“文丞相是心直口快男子心!”
文煥覚得沒趣,半晌不响。然天祥却因此益不得归。
文煥輩私語伯顏道:“只有文某是有兵权在手的,人也精明强干;羈留住了他这人,他們都不足畏了。南朝可传檄而定。”伯顏也以为然。
五
那一夜,天容黑得如墨,浓云重重叠叠的堆拥在天上。有三五点豆大的雨点,陆陆續續的落下。窗外芭蕉上漸有淅瀝之声,风吹得檐鈴間歇的在作响。
窗內是两支大画烛在放射不同圈影的紅光。文天祥坐在書桌前,黯然无欢,紧蹙着双眉,在深思。
唆都,那二貴酋之一,也坐在旁边,在翻閱他的带来的几本詩集,有意无意的說道:
“大元将兴学校,立科举。耶律大丞相是最爱重讀書人的。丞相,您在大宋为状元宰相,将来必为大元宰相无疑!不象我們南征北討的粗魯人……”
“住口!”天祥跳起来叫道:“你們要明白,我是大宋的使臣!国存与存,国亡与亡!我心如鉄如石,再休說这般的話!”他的声音因憤激之极而有些哽咽。
“这是男子心,我們拜服之至!只是天下一統,四海同家,做大元宰相,也不亏丞相您十年窗下的苦功。国亡与亡四个字且休道!我們大元朝有多少异族的公卿。”
天祥坚定的站在烛影之下,侃侃的說道:“我和你們說过多少次了,我是大宋的使臣,我的任务是来講和!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再休提那混賬的話。人生只有一个死;我随地随时都准备着死。迫紧了我,不过是一死。北廷岂負杀戮使臣之名!”
忙右歹連忙解围道:“我們且不談那些話。請問大宋度宗皇帝有几子?”
天祥复坐了下来,答道:“有三子。今上皇帝是嫡子。一为吉王,一为信王。”
“吉王,信王,今何在呢?”
“不在这都城之內。”
忙右歹愕然道:“到那里去了呢?”
“大臣們早已护送他們出这危城去了!”
唆都連忙問道:“到底到了那里?”
“不是福建,便是广东。大宋国疆土万里,尽有世界在!”
“如今天下一家,何必远去!”
“什么話!我們不知道什么叫做降伏;即使攻破了临安,我們的世界还有在!今上皇帝如有什么不測,二王便都已准备好,将别立个朝廷。打到最后一人,我們还是不降伏的!还是講和了好,免得两敗俱伤。貴国孤軍深入,安見不会遇到精兵勇将們呢?南人們是随地都有准备的。”
唆都不好再說下去,只是微笑着。
門外画角声嗚嗚的吹起,不时有得得的馬蹄声經过。紅烛的光焰在一抖一抖的,仿佛应和着这寒夜的角声的哀号。
六
接連的几天,北营里紛紛扰扰,仿佛有什么大事发生。杜滸和小番将們是很接近的,但也打听不出什么。
天祥隐約的听到入城的話,但問起唆都們时,他們便都緘口不言。
伯顏是更不容易見到了。連唆都、忙右歹也忙碌起来,有时半天不見面,好象到什么地方。归来总是一身汗,象騎馬走了远路似的。
天祥知道一定有什么变故。他心里很不安,夜間,眼光灼灼的睜着,有一点声响便側耳細听。
有一夜,他已經睡了,唆都、忙右歹方才走了进来,脫了靴。仿佛是忙右歹,低語道:“文丞相已經熟睡了罢?这事,大家瞞得他好。呂家叔侄也說,万不可讓他知道。”
“如今大事已定,还怕他知道做什么!”唆都粗声的說。
天祥霍地坐起身来,心脏蓬蓬的象在打鼓,喉头里象有什么东西塞住,一股冷气透过全身,整个人象跌落在冰窖里。
“什么!你們瞞的是什么事?”
忙右歹連忙向唆都做眉眼,但唆都不顧的說道:
“我告訴您丞相了罢,如今大事已定,天下一統了!我大元軍已經进了貴国都城。貴皇上拜表献土,幷詔書布告天下州郡,各使归附。我大皇帝和大元帅寬厚仁慈,百姓們絲毫不扰,社稷宗庙可以无虞。不过納降大事,大元帅已請貴国吳相,賈相,謝枢密,家参政,刘同知五人,为祈請使奉表大都,恳請大皇帝恩恤保存!”
“这話眞的么?”天祥有些暈乱,勉强的問道。
“那有假的!我們北人从来說一是一。”
天祥象在云端跌到深渊之下;身体有些飘忽,心头是欲呕不呕,手足都战抖着,面色蒼白得可怕。掙扎得很久,突伏在桌上大哭起来。
血与泪的交流;希望与光明之途,一时都塞絕。他不知道怎么办好!此身如浮萍似的无依。只欠一死,别无他途。
那哭声打动得唆都們都有些凄然。但誰都不敢劝。紅烛光下,透吐出一声的哀号,在靜夜,凄厉之至!
門外守卫的甲士們,偶然轉动着刀矛上的鉄环,发出丁丁之声。
唆都防卫得更严,寸步都不敢离开,怕天祥会有什么意外。
七
杜滸凑一个空,来見天祥。天祥的双眼是紅肿着,清秀的脸上浮現着焦苦絕望的神色。
杜滸的头发蓬乱得象一堆茅草,他从早起便不曾梳洗。
低声的談着。
“我們的子弟兵听說已經从富春退到婺、处二州去了;实力都还不曾損。”杜滸道。
天祥只点点头,万事无所容心的。
“吳坚、賈余庆輩为祈請使北上,不知还能为国家延一綫之脉否?最可怜的是,那末頽老的家参政,也迫他同行。丞相明天也許可以見到他們。”
天祥默然的,不知在打什么主意。他的心是空虛的。一个亡国的被羈的使臣,所求的是什么呢?
“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消息:虽詔書布告天下州郡,各使归附北廷。但听說,肯奉詔的很少。忠于国的人很多。两淮、浙东、閩、广諸守将都有抗战到底的准备,国家还可为!”
天祥象从死亡里逃出来一样,心里漸有了生机;眼光从死色而漸恢复了坚定的严肃。
“那末,我們也該有个打算。”
“不錯,我們几个人正在請示丞相,要設法逃出这北营,回到我們的軍队里去。”
“好吧,我們便作这打算。不过,要机密。如今,他們是更不会放我归去的了;除了逃亡,沒有其他的办法。”
杜滸道:“我去通知随从們随时准备着。”
“得小心在意!”
“知道的。”
就在这一天下午,伯顏使天祥和吳坚、賈余庆輩一見。
“国家大事难道竟糟到这样地步了么?”天祥一見面便哭起来。
相对泫然。誰也不敢說話。
“老夫不难引决;惟有一个最后的希望,为国家祈請北主,留一綫命脉。故尔偷生到此。”家鉉翁啜泣道。
“北廷大皇帝也許可以陈說;伯顏輩的气焰不可向邇,沒有什么办法。所以,为社稷宗庙的保全計,也只有北上祈請的一途。”賈余庆道。
天祥不說什么。沉默了一会。
唆都跑了来,传达伯顏的話道:“大元帅請文丞相也偕同諸位老先生一同北上。”
天祥明白这是驅逐他北去的表示。在这里,他們实在沒有法子安置他。但这个侮辱是太大!伯顏可以命令他!他不在祈請使之列,为何要偕同北上呢?
他想立刻起来呵責一頓;他决不为不义屈!他又有了死的决心。北人如果强迫他去,他便引决,不为偷生。
但这时是勉强的忍受住了,装作不理会的样子。
那一夜,他們都同在天祥所住的館驛里。天祥作家書,仔細的处分着家事。
那五位,都沒有殉国的决心。家鉉翁以为死伤勇;祈而未許,死还未晚。吳坚則唯唯諾諾,一点主見也沒有。賈余庆、謝堂、刘岊輩口气是那末圓滑,仿佛已有弃此仕彼的心意,只是不好說出口。
杜滸,在深夜里,匆匆的到了天祥寝处,面有喜色的耳語道:“国事大有可为!傍晚时,听說陈丞相、张枢密已有在永嘉别立朝廷的准备了;这是北兵的飞探报告的。伯顏很恐慌。”
“如天之褔!”天祥仰天祷道。
他的死志又因之而徘徊隐忍的延下来。而逃亡之念更坚。
“有希望逃出么?”
杜滸搖搖头。“門外是三四重的守卫。大营的巡哨极严,行人盘查得极紧密。徒死无益。再等一二天看。”
“名誉的死”与“隐忍以謀大事”的两条路,在天祥心里交战了一夜。
“我們須为国家而存在,任何艰危屈辱所不辞!”他喃喃的梦語似的自誓道。
第三天,他們走了,簡直沒有一綫的机会給天祥逃走。他只好隐忍的負辱同行。他的同来的門客都陆續的星散了。会弹古琴的周英,最早的悄悄的溜走。相从兵間的参謀顧守执也就不告而别。大多数的人,都是天祥在临行之前遣散了的。他們知道这一去大都,凶多吉少,便也各自打算,揮泪而别。不走的門客和随从們是十一个。杜滸自然是不走。他对同伴們說道:
“丞相到那里去,我也要追随在他的左右。我們还有更艰巨的工作在后面。”
一个路分,金应,从小便跟在天祥身边的,他也不願走。他是刚过二十的少年,意气壮盛,有些膂力。
“我們該追随丞相出死入生,为国尽力!”他叫道。
十一个人高声的举手自誓,永不相离。天祥凄然的微笑着;方棱的眼角有些泪珠兒在聚集,連忙强忍住了。
“那末,我們得随时准备着。說不定什么时候有事,我們应該尽全力保护丞相!”杜滸道。
仗节辞王室,悠悠万里轅!
諸君皆兩别,一士独星言!
啼鳥乱人意,落花銷客魂。
东坡爱巢谷,頗恨晚登門。
杜滸悄悄的对天祥道:“我們等机会;一有机会,我們便走;疾趋軍中,徐图恢复!路上的机会最多;請丞相覚醒些。一見到我的暗号,便当疾起疾走!”
“知道,我也刻刻小心留意。”
那一夜,船泊在謝村。他們上岸,住在农家。防御得稍疏。到了北营之后,永不曾听見鷄啼。这半夜里,却听得窗外有雄鷄长啼着。覚得有些异样,也有些兴奋。
他們都在灯下整理应用的杂物;該抛的抛下,該带的带着,总以便于奔跑为第一件事。灯下照着憧憧往来的忙乱的人影,这是一个頗好的机会。
杜滸吩咐金应道:“到門外看看有什么巡邏的哨卒沒有?”
金应刚一动足,突聞門外有一大队人馬走过,至門而停步。把破門打得嘭嘭的响。
吃了一惊,那主人战抖的跑去开門。一位中年的北方人,刘百户奉了命令来請天祥立刻下船。同来的有二三十个兵卒,左右的监护着。那逃走的計划只好打消。
但刘百户究竟是中国人,听了婉曲的告訴之后,便不十分的迫逼,竟大胆的允許到第二天同走。然防卫是加严了。
不料到了第二天清晨,大酋鉄木兒却亲駕一只船,令一个回回人命里,那多毛的丑番,立刻擒捉天祥上船。那种凶凶的气势,竟使人有莫測其意的惶惑。杜滸、金应都哭了。他們想扑向前去救护。
天祥道:“沒有什么,該鎮定些。他們决不敢拿我怎样的。此刻万事且須容忍。以蛋碰石,必然无幸!”
他們个个人憤怒得目眦欲裂。可惜是沒有武器在手,否則,說不定会有什么流血的事发生。
且拖且拉的把天祥导上了船,杜滸們也荷着行李,跟了上去。在船上倒沒有什么。只是防备甚严。为祈請諸使乘坐的几只船都另有小舟在防守着;随从們上下进出,都得仔細的盘查,搜检。他們成为失了自由的人了!
听說刘百户为了沒有遵守上令,曾受到很重的处分。几个色目人乘机进讒,說是中国人居心莫測,該好好的防备着。所以重要的兵目、首領,都另換了色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