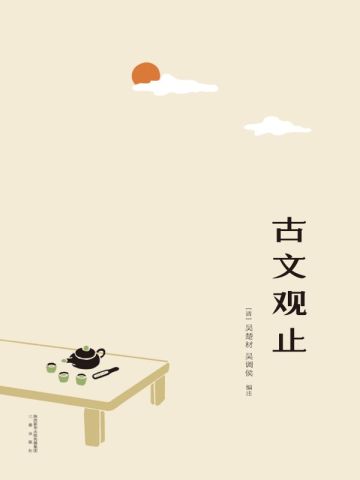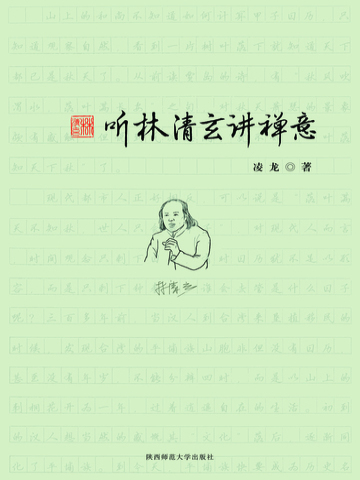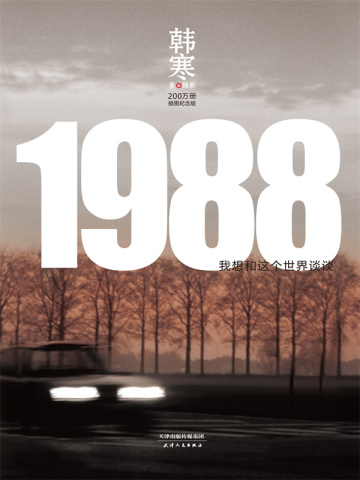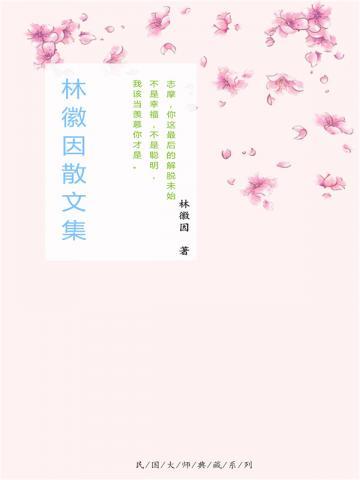吴继文
结束印度一个多月的旅行,午夜离开加尔各答,在新加坡樟宜机场中转,“亮度”就告诉你这是两个世界,好像两地的距离,不是公定时差两个半小时,也不是飞行时间的三个多小时,而是,也许三十年!所以当香港朋友来台北,你听到的第一印象竟然是“台北好暗”,心里还是小小受了点伤。
明或暗,其实是相对的。在尚未通电的婆罗洲内陆雨林夜晚,一只萤火虫的光足以燃亮编竹长屋的一角;当你换上油灯,萤虫只能勉强点亮自身。
本书开篇之作《阴翳礼赞》从电器用品进入日式建筑所带来的美学尴尬谈起:前所未有的明亮,无所不在的电线,和木构建筑格格不入的瓷砖……然后又说关于厕所,日本人无疑富于诗意的想象力,由于小屋“一定建在离主屋有一段距离之处,四周绿荫森幽”,蹲在被纸窗滤过的幽光中,不但可以沐浴芬多精,还可以一边办事一边聆听风声、雨声、鸟叫虫鸣(包括蚊子、苍蝇吗?),于是,住宅中最不洁的场所一变而成为最雅致的地方。
从题名到如是的开场铺叙,不免让人顺当地以为这是以耽美闻名的作者对幽冥晦涩空间的偏执之爱,也是对“日本之美”国粹或民粹主义式的回归;依评论家、著名读书网页“千夜千册”主人松冈正刚(Matsuoka Seigou)的看法,谷崎氏一点都不是日本民族美意识的理想代言人。松冈氏很喜欢谷崎润一郎,却无法消受比方“在幽暗中追求美的倾向,为何独有东方人特别强烈”,然后扯到“日本的鬼是没有脚的,但西方的鬼不仅有脚,而且全身透明”,所以说“我们的幻想与漆黑的幽暗密不可分,而西方人甚至连幽灵也如玻璃般透明”之类的二分法夸言。
因为幽黯、暗沉并非日本所独有,那是所有前现代世界的共相;东方既有谷崎所谓由“幽暗所堆栈而成”的漆器,但不也有釉色斑斓、闪闪发光的瓷器?谷崎固然以《刺青》、《春琴抄》、《痴人之爱》、《卍》、《疯癫老人日记》、《少将滋干之母》诸作建立他耽美的系谱以及文坛至高的地位,作品多以强势女性为主体,正面歌颂女性,描写男性受虐的色情想象、乱伦、恋足癖等,展现他独特的偏执美学,似乎他会有同样偏执的日本论毋宁是合情合理。然而出身东京大商人家族(虽然到他父亲那一代已经中落),自小被视为神童长大的他,对生活、人情皆有过人的感受性(否则也不会写出让一代代读者惊叹、动容的故事),对浮世悲欢自有一种凌厉的眼光,对虚伪的流俗更是不假辞色(想想他创作全盛期是什么时代:主旋律无非讴歌男性、灭私奉公、富国强兵),这样一个人,会卤莽地卖弄“东方文明优越论”或是厚古薄今的美学观吗?
何况将谷崎作品浏览一过,就会发现即使他驱使极为典雅的日文、展现一个充满古代风情的世界,但他创作者的自觉是非常强烈的:他无法满足于平庸、模拟(即使是高明的模拟)之作,于是毫不迟疑地运用许多实验性技巧。比方《少将滋干之母》(1949)多重视点的叙述游移,《键》(1956)交叉呈现一对夫妇的日记,丈夫的部分一律用片假名,妻子的自白则是平假名;最特别的是描绘一个年轻音乐家对年长女琴师惊世苦恋的《春琴抄》(1933),全书极少使用分段、句读,除了在绵延数页的两个大段落之间空个一行,有时甚至连续十几行不加任何标点(但《春琴抄》可不是教人消化不良的痴人呓语,它的故事迷人至极)。这样说来,同年发表的《阴翳礼赞》也是好几页才分段空行一次,但至少该有的标点一个没少,还算是温和的。
和他同时代文人一样,谷崎有着深厚的古典底子,他当然深知他的美学观不过是常识,无非承袭古人遗韵:中世歌人吉田兼好(Yoshida Kenkou,1283-1350)《徒然草》写道,教养出色者幽居的场所,月光落入的风情沁人心脾,“群树古驳,无人工斧凿的庭草也心趣在现”,“家中的器具古调凝重,呈现出深沉的美”,相反,众多工匠尽心营造的豪邸“连庭院里植栽的草木也不能随顺自然生长”,被人为地修饰,“看起来别扭心里更悲戚”;或是七夕祭时节“渐次感到了夜里的寒冷,大雁鸣叫着飞来,秋蒿根部的叶子黄枯起来,收割晾晒早稻等,一时间多种事情接踵而至,真可谓多事之秋”,却一切显得极雅致,连“台风离去的翌日清晨的景象也颇有意思”。这不就是谷崎《阴翳礼赞》篇的旨趣吗?歌人鸭长明(Kamono Choumei,1155-1216)《方丈记》里面的“随意休息,随意怠惰”、“胜地无主,可无拘无束地了却闲情”,不也可以在《说懒惰》和《旅行的种种》两篇发现镜像语句?
所以要真正理解谷崎润一郎这样一位作者,或许不是在他的作品中孜孜于寻迹索隐,甚至落入偏狭的诠释,这只会是对作者很抱歉的误读;反而是作为读者的我们,需要驱使想象力与同理心,一窥他内在的幽微,进而隔空对话,才是进入谷崎文学世界的王道。
小说,是作者的独角戏,不管喜不喜欢,你只能端坐台下,或悻悻离去;阅读随笔,则好像你公园闲步,突然一个陌生人过来搭讪,对方话多,但因为说得极有意思,你偶也附和几句,不觉边走边聊了起来。随笔的趣味,或就在于书写者和阅读者之间一种内在、私密(因为超越时空以至于也有些神秘)的互动与对话。
“即使我魂不守舍,也总游荡在很近的地方……凡人所能接受的宗教,只是一些凡人的宗教……因为没有勇气不信而相信的信仰又是多么轻松的信仰!”这是老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来自十六世纪微颤的声音,那时他独居的塔楼除了晚风偶尔吹动书页此外一片静寂,你对他的小窗招手,他视而不见(也许是因为肾结石又发作了)。
“有一件事情绝不允许再去弥补:错过从父母身边逃走的机会……幸福就是能够认识自己而不感到惊恐。”慧黠,同时带点恶作剧叛逆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你仿佛看到他最后一次走过巴黎街头一排枯黄欧洲七叶树时同样萧瑟的侧影,那时纳粹追捕的机器正在收网,你很想劝他走另一个方向,但你知道他已经预见了结局,哪里都一样。
“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人类并不存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人类也不会存在。”我喜欢如此这般看待(其实没那么灵光的)所谓万物之灵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明明是神却总是站在人的高度说话,注视人的超越,以及不可超越的边界。每每看到形容忧郁的他,你多希望他知道,即使只到过很少地方,即使那些地方多半只探访一次,即使非常痛恨旅行,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
要与谷崎润一郎对话,首先必须观想他所属的年代(1886-1965),也就是明治末叶,直到二次战后日本经济起飞初期,然后设身处地。在他出生前三十年,日本这个因地理位置而自然闭锁、内造了数千年的国度才正式对外开放;前二十年,幕府奉还王政,明治厉行维新,强国之梦沸沸汤汤;青少年时期,日本连续打赢了和清朝、帝俄的战争,俨然新兴大国,脱亚入欧之说无须辩证,举世滔滔,大量引进西欧文明,现代化之路一往无前。
所以谷崎的心性,借用卡内蒂(Elias Canetti)的说法,有一段时期他住的房子每一扇窗都是开向欧洲的,作风相当洋化(在《说懒惰》篇中他也坦承不喜欢“乡土味”),时代的大气候使然;昭和初期(1926年起)的现代主义风潮也明显影响了他。1918、1926年两次中国之旅,也让他发过一阵中国热。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后,他移居关西地区凡二十一年,辗转于大阪、神户之间,并迷上文乐(净瑠璃偶戏),于是又回头关注日本的传统事物。他在关西总共搬过十三次家,多是赁屋而居,只有一个住所是自己的,而且是依自己的理想设计而成,即神户市东滩区的锁澜阁。评论家奥野健男(Okuno Takeo)对这栋位于山坡上、展望良好的房子印象是“非常奇妙:日本、西洋、中国的元素各自强烈展现,却又硬是被揉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而独特的宇宙”。
生活在大量引进外来事物,而且以洋为尚的时代,社会上总是漂漾着一种暧昧的空气,好像先进国的文明体系、包括美的概念一律是理想的、优越的,于是竞相抛弃本土既有的一切,以显示自己的进步。于生活有敏锐感受性的人,包括本书作者,恐怕很难不产生抵抗感。这便成为与谷崎同时代的许多峥嵘的文化人必然要面对,并寻求纾解之道的天命。
一个社会,当它有意识地进行典范或体系的转移,比方政权的递嬗,政制的改革,文化的输入,或整个由封闭而开放,所要付出的代价,常超乎想象,尤其,这种移转通常没有足够的缓冲时间。革命成功,统治者换班,但民众还是原来那些人,没办法即刻换一个脑袋来适应新的秩序(如果有秩序的话)。如果你只以先进国的尺度作为唯一的、普遍的尺度来测量你的社会,如果你不能理解、尊重民众原有的思维与感情,那么任何新秩序的建立,都将伴随着暴力(为了排除旧秩序),而且基本上就是国家的暴力。
当一个城市的统治者宣称要整顿市容(而且也取得法律的正当性并具有多数民意基础),于是警察就可以对相对弱势的边缘族群(比方摊贩)采取驱离、取缔(或索取放水费、保护费),并不管这些人是否将失去仅有的生存空间;或为了国家的一时性庆典(比方举办奥运或博览会)而强迫大量民众永久搬迁(完全不需征求同意),统治机器都会反复强调: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没有建设就没有未来。谁的未来?
所以本雅明提醒我们,一切法律或秩序的根源,总是包藏着暴力。从暴力而来的法律体系,必然也同时种下暴力的种子。不同国家、种族、宗教之间的倾轧,更是教那暴力的种子随时发芽、随处开花结果。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年深日久,无时或已,就是最显著的例子;而所谓全球化的趋势,直接压迫、挑衅许多封闭的体系,所引发的暴力更是触目惊心。
文化人类学者中泽新一(Nakazawa Shinichi)对“911”攻击的响应可以给我们足够的警醒:“以压倒性的非对称所构筑而成的现今的文明,由于拥抱着潜在的恐怖暴力威胁而享受繁荣,因此文明最深远的后台不断上演的,正是残酷的弹压与杀戮的戏码。”以暴易暴,只是先进国的暴力一向披着人道、理性、正义的外衣(所以多数人不知道美国才是世界头号恐怖主义国家),而面对全球化威胁进退失据的伊斯兰社群,其只能以最原始也最野蛮方式响应的人民,则被妖魔化为凶残暴徒,世界公敌。
谷崎之辈的文化人,包括不世出的大学问家南方熊楠(Minakata Kumagusu)、民俗学者柳田国男(Yanagita Kunio)与折口信夫(Orikuchi Shinobu)所致力的,正是力抗那一味取法欧美、忽视本土的倾斜风潮,只有本于日本民族的思维,用日本的方法,建立属于日本的学问,始有可能真正了解日本,或者那个有别于诸外国的日本的特殊性,进而调和日本与外来文明的扞格。这项行动,正是在源头上摘除暴力种子的尝试。
所以谷崎润一郎《阴翳礼赞》通篇要抒发的,不是“日本虽然没有欧美现代化,可是日本的美(或日本人的美意识)却胜过一切”或“外来的新生事物粗暴地破坏了古老的日本的美”之类的牢骚,而是,我认为,意在言外的、不带排他性的朴素问句:“当我们义无反顾地追求进步时,能否冷静自省,我们的一切行为,是否同时也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生活质量变得更好?”并宣示重新取回几乎要让渡给他者的、对于美的诠释权。
当然,对许多只知道要当下的新、快、大、多的人而言,他们的美好,并不是其他人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