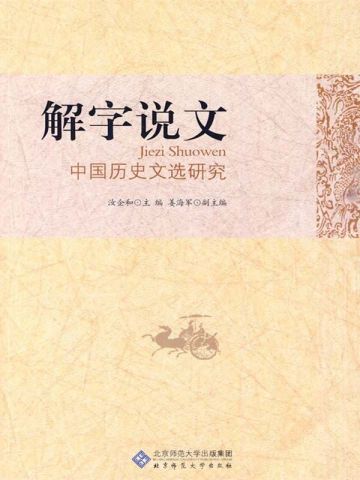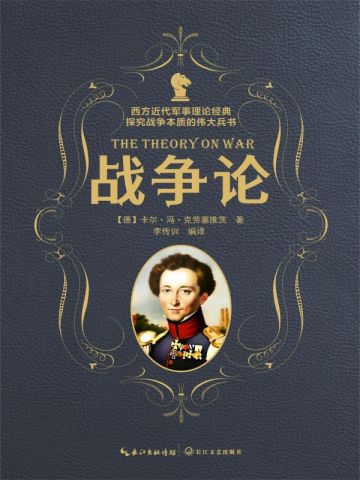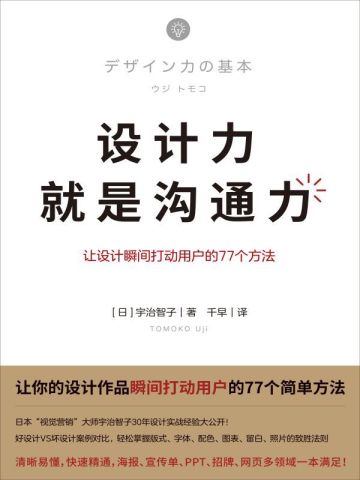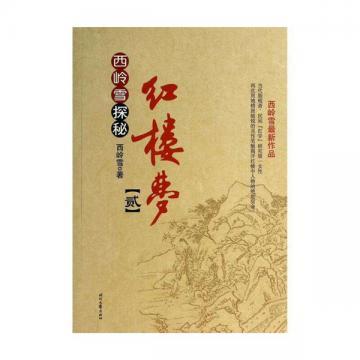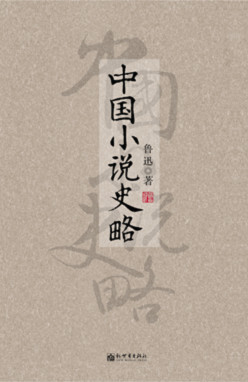北京师范大学 汝企和
研讨陈老学术成就的论文已有许多篇,然对陈老在教育方面的建树,尚鲜见有专文论述。刘乃和先生曾指出:“我们的陈垣老校长,从事教育工作达70年,在我校担任校长前后47年,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极少见的。他一生为医学教育、工读教育、平民教育、师范教育、大中小学教育等多方面都作出过不少贡献。不少史学界著名学者都出自他的门下,多少优秀人才都曾得到过他亲手培育和指导,他在我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1]然而近年出版的多部颇为优秀的教育史专著中,均未见有论述陈老的教育成就或教育思想的专门章节,更未见有研究陈老对于中国历史文选课之贡献的文章,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对老校长教育成就研究甚为匮乏这一现状。本文试图通过剖析陈老创设史学名著选读和历史名著评论这两门课(以下略作“两课”)之事例,来揭示陈老在历史教育方面的一项成果,以及他对中国历史文选课之巨大贡献,并由此管窥其部分教育思想与教学特点,以期借鉴陈老的经验,进一步深化历史文选课的教学改革。
全文分三大部分:一、创设“两课”的时代背景与陈老的主观因素;二、“两课”的内容、授课方法以及对老校长教育思想与教学特点之管窥;三、两课与陈老思想的深远影响。
一
对于“两课”产生的时代背景,刘乃和先生回忆道:“20世纪20年代初期……过去青年作文写稿都用文言文,五四运动后中等学堂也改为白话课本,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在这种局势下,“陈垣……认为历史系今后更应有专门讲提高阅读文言文能力的课程。因此就提出设置这门新课,他起名为‘史学名著选读’。”“他还认为……历史系学生必须有目录学的知识,因此,不久他又提出设置另一门新课——‘历史名著评论’。”[2]
从主观方面讲,为何不是别人,而是陈老创设了“两课”呢?笔者以为至少有三点原因。其一即刘先生所指出的:“陈垣作为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师,逐渐感到青年们对读古书有了困难。”[3]许多回忆文章都指出:陈老是极富责任心的教师,因此他在当时众多的中国史教师中,敏锐地感觉到历史系学生的文言文需要加强这个问题。
原因之二是陈老具备深厚的国学功底。陈老5岁时就“苦读经文”,很早便以《书目答问》为向导遍览群籍[4],13岁时,“更进而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5]。他从1915年开始研究《四库全书》,“前后断断续续用了十年时间”。[6]因此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陈老在国学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从而深知掌握文言文对历史研究之重要意义;而他自己的学术奠基,就是从目录学开始的,故由他提出开设“两课”绝非偶然。
原因之三是陈老特别重视基础知识的传授,这方面例证甚多,本文仅择其二。例证之一为陈老对当时大学一年级的国文课(以下略作“大一国文”)的重视。赵守俨先生指出:在“辅仁(大学)……‘大一国文’是各系一年级学生的主课,这门基础课是由陈校长亲自主持的,自己还教了一班,并为这门课程编选了《论孟一脔》等教材。教授‘大一国文’的教师也是由陈校长自己选定的……年终考试,由陈校长亲自出题……由于老校长抓得紧……效果显著。”这段文字说明:当时身为辅仁校长的陈老,不但将“大一国文”指定为“文理各系共同的必修课程”,而且亲自主持、亲自编教材、亲自教课、亲自选定教师、亲自出考题。上述五个“亲自”及其他方面生动体现出老校长对基础知识教学的高度重视。
例证之二为陈老所撰的四种“关于基础知识的介绍和历史学基本建设的工具书”,“这就是《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赵先生最后还特别指出:“这虽是历史学的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建设工程,而有些学者却是不愿意作的。”
陈老正是如此重视基础知识,在教学中以身作则,从而带动师生都重视基础知识;在研究中编写“有些学者不愿意做的”工具书。两课的内容都是基础知识,由此可见,当年是陈老而不是别人创设“两课”,也是颇耐人寻味的。
二
对史学名著选读课,刘乃和先生追述了其目的、内容、注释、选篇的排序及深远影响等情况,兹将与本文关系最密切者简述如下:
第一,设置此课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历史系学生的古文阅读能力。”现在在历史文选学界对今天开设历史文选课的目的仍有不同看法,而老校长当年的开课宗旨对这些分歧意见应是有借鉴意义的。
第二,从“本课内容”可见其选篇之原则:A.以史学名著名篇为主;B.选篇上限为三传;C.对了解某一特定历史事件有助益的篇章。
第三,授课方法:“他在有的学校(有条件的)开辟了实习室,在实习室里从图书馆调来必要的工具书、参考书,同学到实习室自己动手,标点、分段、注释。同学自己准备,自己查书,印象深,也能提出问题……”[7]
上述大部分内容,对今天的历史文选课仍具有现实意义。
对历史名著评论课,杨殿珣先生的叙述涉及:
1.教材:“是由先生选定史学著述若干种,每书逐一评论;”
2.授课方法(讲特点、讲心得、启发式等);
3.讲治学方法:A.如何收集资料;B.如何鉴别与审定资料,“实际就是资料考证问题”;C.如何安排资料;D.读书的路径:“教师应当把自己走过的路径……一一讲授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走自己的路径”;E.“要勤于做笔记,勤于写作,但不要急于发表”;F.戒浮夸风:“当时的青年喜欢把‘研究’两个字作口头禅,先生却不以为然。先生说研究工作首先要打好基础……再好好读上十年书,研究也不为迟吧?”[8]
“两课”的创建与授课内容等情况,反映出陈老的部分教育思想与教学特点。
其一为重视基础教育。这是老校长的一贯思想:“陈老在担任辅仁大学校长的几十年中……一直非常重视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前文所述之两则例证说明:这一思想是陈老创设“两课”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两课”的实施,又是这一思想的突出体现。
一个人学术基础的深厚与否决定着他今后可能达到之学术水平的高下。这恰如古人所言:“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9]人们常用地基与大厦之间的关系作比喻,来说明基础的重要性。事实也正是如此。
这一原理不仅适用于学术界,还适用于任何一种内涵丰富的人类活动,如武术、京剧、舞蹈、乐器演奏等,无一不强调扎扎实实的基本功训练,舍此则不可能达到高水平。
陈老重视基础教育,创立“两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史学家。“早年他的学生中,有很多都认为这两个课对他们后来的研究有很大好处,主要是打的基础扎实,我就听到过他的学生方田瑜(师大)、史念海(辅大)、朱士嘉(北大)、柴德赓、余逊等著名学者和我提过他们受益不少,这都是几十年后他们说的……都认为这两门基础课还是十分重要的。”[10]
陈老的这一思想对今天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在人们已跨入21世纪,学生面临的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其结果必然是:传统知识—如国学—在一般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中所占比重日趋减少。然而艰深的史学研究对每一位研究者学术基础的要求却绝不会因此而有丝毫的降低。所以在新世纪里,打好基础的问题比80年前就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天某些人忽视乃至削弱基础课教学的做法,短时间内很可能看不出有什么影响,然而绝大部分人在参加工作后,很难再有几年时间静下心来学习,因此在大学期间基础知识掌握得好坏,必然对绝大部分人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正如上文所引刘先生文章中讲的:几十年后才能深刻体会出当年基础打得扎实的益处一样,打不好基础的恶果,同样也会在几十年中逐渐显现,而到那时却只能是悔之晚矣了!由此更可见陈老重视基础教育思想的深邃!
其二为重视能力的培养。这句话近年来几乎凡言教改者必言之,然能真正做到却绝非易事。而陈老在几十年前不但已具备这种思想,而且还将其成功地付诸实践,其典型事例即前所述之历史名著评论课中的“讲治学方法”。
按一般人理解,历史名著评论课不过是介绍和评价史书而已,而陈老讲授的内容却远不止于此。上引杨先生的回忆中,仅关于资料者就占三条之多。历史研究的基础就是资料工作,陈老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不遗余力地反复解说,从资料搜集到考证真伪,再到资料编排,讲授这些治学方法,就可切切实实地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
陈老讲读书的路径,其实质则是引导学生找到适合自己走的治学门径。这更是一项提高能力的有效措施。治学门径是治学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若只知埋头读书,而找不到正确的门径,其结果只能是事倍而功半,甚至是一事无成。
笔者认为,大学教学与中学教学的最本质区别之一即在于:中学是以传授知识为主,而大学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教会学习方法,解决本专业中难题的方法,以及其他治学方法。这点在陈老的教学中非常突出:他不但教给学生读书的方法,而且引导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读书路径和治学门径。这对于今天的教学仍是颇具启迪意义的。
其三为特别强调实践在教育中的作用。这点在陈老七十年的教学中尤为突出。在早年的医学教学中,他为了让学生对人体骨骼有生动的感性认识,就“曾带着学生到郊外乱坟堆中挖掘尸体,寻找核对骨骼,观察人体骨骼结构。”[11]为了让学生学会诊病治病,他自己首先“为群众诊病”,“积累了实际诊断经验,写出心得运用到课堂教学”,从而达到“丰富提高了教课内容,增加了同学学习兴趣”的效果。[12]又如创设史源学实习课,也是颇为典型的事例。该课“是以一种史学名著为底本,追寻其史源,考订其讹误,以练习同学的读史能力。鼓励同学自己动手查书、找材料、做文章,隔周做练习一次”。其效果亦颇显著:“经过这样的严格训练,同学进步提高很快,而且对读书、查书、考证、写作都发生了兴趣。”[13]
在“两课”中,建立实习室是陈老的一大发明。与历史系其他课程相比,“名著选读”课的突出特点就是实践性强,许多内容,如对古文的标点、注释等,若只是由教师在课堂上讲解,学生不亲手实践,终有隔靴搔痒之感,很难切实掌握。陈老不但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且想出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即建立实习室。通过实习,许多课堂上难以讲清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
有些事情在今天看来似乎很简单,然而在当时情况下,敢为天下先者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对这一事物的深刻了解。老校长若非多年钻研国学、多年潜心教学,若非一贯重视实践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可能想出如此切实可行而又效果甚佳的办法的。
其四为自觉地将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创设“两课”本身,即是这种结合的产物——前述开设“两课”的主观原因之二、之三,皆源于老校长自身的科研:他在科研中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功底,从而才能深切体会到掌握文言文与目录学知识对中国史研究至关重要;同样也是在他自己的学习与治学过程中,深感基础知识对于学术向高层次发展不可或缺,他才会如此重视基础课教学。
科研与教学的结合贯穿于老校长的各种教学活动中,如前述“两课”中的“讲治学方法”与“史源学实习”课的创立,皆源于他自己科研中的心得和体会。
陈老的教学“是异乎常人的……好像授业者所要知道的,他都能随时讲授出来……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会讲授的先生。”[14]达到这种教学效果的最大“秘诀”恰在于:他的教学是以其广袤而深邃的科研为基础的,因此无论在教学内容上,还是在教学方法上,他都能“异乎常人”。而这种将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的思想与实践,无疑是我们的最佳典范。
其五为富于创新精神。“两课”的设立,既是课程设置的创新,又是教学内容的更新;而实习室的建立,更是教学方法上大胆的革新。这种精神在老校长70年的教育生涯中处处闪现:开设“史源学实习”课;将“大一国文”课作为“文理各系共同的必修课程”;教国文的教师“在老校长的领导下……每周聚会一次,交换学习心得”;将学生作文中的佳作在“校内开辟墙报专栏,分期张贴发表,以收观摩之效”等,他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上几乎都有创新。
更为重要的是:老校长在教学中的种种创新,都是建立在深厚的科研基础之上的,因此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两课”于八十余年后的今天在九州遍地硕果累累,就是最具说服力的铁证(详后)。这种具高度科学性的创新精神,在今天仍是极为宝贵的。
其六为注重思想教育。前述“勤于写作”与“戒浮夸风”即是生动例证。牟润孙先生回忆道:“先师教导学生……主要是使学生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用功读书。”足见今日常讲的“教书育人”,老校长也早已付诸实践了。
这点在今天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在距创立“两课”之时已过了八十余载,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商品经济大潮对社会各个领域都有很大冲击,学校亦不能幸免,不少学生读书期间就开始经商,有些学生做学问也是急功近利,总想少耕耘,多收获。在这种形势下,学风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要想做好学问,首先就要做好人。古人常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意固然是要治国平天下,然而研究学问也是同样道理:不能正心修身,总想投机取巧的人,是作不好学问的。因此,陈老这种既教书、又教做人的思想和做法,正是今天为人师者应大力发扬的。
三
老校长创设的“两课”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前,“每年他自己为一二年级讲授这门课,并在师大、辅仁、燕京各大学都曾讲授”。聆听过“两课”的许多学者都感到受益匪浅(见前文)。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师范教育会议讨论课程设置时”,“肯定了这两门课作为历史系的必修课,改名‘历史文选’和‘历史要籍介绍’”。
由于两门课被确定为必修课,因此受到各高校历史系的普遍重视。
其中中国历史文选课仅教材一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迄今就已出版了60余种。许多未出教材的历史系也已开设此课多年。老校长当年开设的这门课,而今已在全国各地结出了硕果。
60余种教材中,自1949年10月至1962年12月的13年里,仅有12种付梓;而1980年至今,29年间就出版了38部。从这些数字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后全国拨乱反正,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有了正确认识,这门课随之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从教材内容上看,随着近年来历史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历史文选教材的选篇范围也从以经部、史部为主,扩展到经史子集四部兼收,其中史部选篇也从以正史为主而逐渐深入到史部的各门类。尽管如此,老校长当年的选篇原则之一“以名著名篇为主”,仍是所有教材的共同特点,由此亦可见陈老的选篇原则具有深刻的合理性。
此外,这种内容上的发展,恰是老校长将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思想的生动体现——“文化大革命”后,史学界也敞开大门,吸收西方先进的史学思想,历史研究的领域从单一的政治史、阶级斗争史拓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正是基于这一科研上的重大发展,历史文选的选篇范围随之逐渐扩大,教学内容也随着科研的深入而不断深化。
教材选篇的编排从初期按时间顺序的单一体例发展为多种体例并存的局势。教材里的辅助内容与初期相比也大大增加,如古文化常识,工具书介绍,旧注选篇,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常识及选篇等,都分别出现于一些新教材中。这些发展正是老校长创新精神发扬光大的结果。
这门课受到重视,还表现在已召开了全国性的研讨会六次,且都得到教育部领导的大力支持——像这样专门讨论一门课教学的全国性会议尚不多见。六次会议对这门课的性质、目的、任务、地位、教材编写、教学方法、教学改革、该课与相关课程的关系,等等,几乎与之相关的所有问题,都进行了畅所欲言的讨论,讨论的成果集结为五部论文集出版。老校长重视培养学生能力与注重思想教育的思想,成为贯穿五部文集的一条红线。
陈老在我校担任校长达47年之久,师大人继承老校长的事业是义不容辞的。历史文选课在历史系一贯受到重视:“陈垣之后,柴德赓、白寿彝、何兹全、赵光贤、尹敬坊几位老先生都教过历史文选,我也教过,李秋媛、杨燕起老师都教过或正在教。”此后这门课一直由历史文献教研室的教师承担。1994年我系被评为历史学教学基地后,系领导特为我室开辟了实习室,内容为标点、注释、工具书、文字学等——陈老强调实践在教育中的作用的思想与实践,在这里得以继承和发展。同时我系还专为本课设立过关考试,不过关者则不授予学士学位。这项措施在几次全国历史文选教学改革研讨会上均受到同行们的好评。
1996年我室承担了国家教委“高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立项项目,于1999年6月出版了新教材,并提前完成项目。新教材从指导思想到选篇等都多有创新,是努力发扬老校长创新精神的结果。2001年我室获北京市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02年我们的《中国历史文选》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008年我们又对该教材进行了精心修订,并被批准成为北京市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至于历史名著评论课,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历史要籍介绍”后亦在许多院校开设,如柴德赓先生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要籍介绍”,“若干年后他出版的《史籍举要》,即在陈老讲稿的基础上增补而成。”
在陈老历史名著评论课影响下,还产生了其他专著:“(我)讲此课时……就是依据陈老讲法。长期积累的讲稿,后来压缩成为一本《史部要籍解题》,与《廿二史札记校》都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两书中实际上都渗透着援老的思想和看法。”足见这门课的影响是何其深远。
“援庵师是一位著名的超卓的史学家和教育家”,“称得起是一代宗师”,其学问博大精深,其教育思想亦深邃广袤,其教学更是异彩纷呈。本文仅就他创设“两课”一事来揭示其对“历史文选”课的巨大贡献,并进一步管窥其教育思想与教学特色,而这些教育思想与教学特色对我们今天应如何进行“历史文选”课教学改革,仍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迪意义。
笔者毕业于历史系,未受过教育学的系统传授,故文中评论难免有失当之处,诚望教育学家和研究陈老的专家,以及广大同行们不吝赐教。
[1] 《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编者的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 刘乃和:《历史文选课设置的回顾》,《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一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3] 同上。
[4] 刘乃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载《励耘书屋问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82。
[5] 陈智超:《史学家陈垣传略》,载《晋阳学刊》,1980(2)。
[6] 王明泽:《陈垣事迹著作编年》,载《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7] 刘乃和:《历史文选课设置的回顾》,《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一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8] 杨殿珣:《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载《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9] 《礼记》,《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 刘乃和:《历史文选课设置的回顾》,《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一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11] 刘乃和:《陈垣老师勤奋的一生》,载《励耘承学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12] 同上。
[13] 刘乃和:《陈援庵老师的教学、治学及其他》,载《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14] 史念海:《忆先师陈援庵先生》,载《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