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女奴
- 书名:
- 侠女奴
- 作者:
- 周作人 译
- 本章字数:
- 16225
- 更新时间:
- 2021-04-12 14:32:22
前十世纪之时,波斯某街有兄弟二人。一名慨星(Cassim),一名埃梨醅伯(Alibaba)。其父在时,家仅小康。死后平分以给二人,其所得产业各相等,析居而处,尚可拮据以度日。及后景遇不同,而二人生计上之状态,遂亦各异。
慨星娶一少妇,当未结婚之前,为一富贾之继女,承袭其产,有土地上之不动产甚多,且有仓库一所,满贮商品,其值不赀。及归慨,携之与俱。慨星以妻之花荫,一洗昔日穷愁之景况,突然一跃而为富家儿,财名甲于一镇。
埃梨则不然。其妻之境遇,不能少优于彼。一家聚居一破屋中,家无长物,惟藉营业所得,以养赡其妻子。日至邻近丛林中伐木为薪,以三驴负之,售于市场以为常。
一日埃梨至林中采薪。日已旁午,所得颇多,三驴之载已满。方将驱驴就归路,就食于家,忽举首见前山尘埃障天,如半天浓密乱云,蓬蓬然直薄霄汉。细察其起处,自右方向之地而前进,其势甚疾,如暴风云。
埃梨甚骇,注目凝视,烟尘历乱之中,有多数人队,据马背而疾驰。此地固久不闻有盗害,然见此情状,不能无疑。此时埃梨不暇顾及其驴,攀登一大树以自匿。树乃生于一峻峭之岩石上。石之高过于树,颇险阻不易上。树枝去地不及数尺,而绿阴浓密蔓延四垂,恍如一座之碧幔。埃踞其中,颇安适,人不能窥见己,而己可探视其外之动静。
埃梨方登树,此跨马之群亦风驰电掣而俱至,刹那间已渐近岩下。视其状貌,皆壮健而狞武,且善骑。数之得四十人。睹其装束形式,其为盗确然无疑,因思前此推测之不谬。盖彼等实为一群之盗,惟其组织之方法,不施掠夺于邻近之村落,由远处劫得财帛,而仅以此处为集合所,故人皆不知。盗既驻马,各下骑,去其络,并捆于背间之袋,其中似满实以粟类,并各携其旅行之革鞄,其量似甚沉重者。埃梨自思此革鞄中,必为金货无疑也。
众盗系马于小树,盗魁乃取革鞄置于肩,负之为诸人导,取径于灌木丛莽中。直行至峭壁下,拨荆棘得一户,向之大声而呼曰,“西剡姆(意译为胡麻)启户。”……语未竟,石壁之门,呀然而启。于是各人皆鱼贯而入。门亦砰然遂阖。其处与埃梨所匿之树,距离不远,盗魁之语,埃梨闻之极清晰,心窃志之。盗入穴良久不出。埃梨伏树上不敢下,因恐一离其所处之地而他逸,或为彼所见,故忍耐以俟其离去。未几门复启,众盗俱出,相率加马之辔首,且系其革囊。盗魁乃复呼曰,“西剡姆闭户。”门即闭。于是跨马俱去。
埃梨见盗已去,不敢遽下,惧彼或有遗忘物而复返。及其行已远,竭目力之所及,不复见一点之人影。空山寂寂,四顾无人,乃逡巡下树。忽忆及盗魁之口号,知“西剡姆”一语,为其启户之机关。不觉陡然激起好奇心,思仿其音入穴,一穷其境。于是乃披草而至其门大呼如盗魁声,门果辟如前。
埃梨入门。初以为其内不过一黑暗阴晦之地穴,及渐进,则见一拱状之窖室,系凿岩石为之,高一人有半。岩顶开一孔以受光线,广大而光明。埃不胜惊讶,复细视其中,无物不备。粮食山积。金银之货币,堆累于地,若小阜然。并有皮袋累累,满贮一种之小金钱名西坤者。四壁之隅,叠置多捆之美好商品。其外复有生丝之织物,及贵重之罽毯,并花缎锦绣绸帛之属,不可胜计。其中积蓄,殆足支数世纪之用。若众盗以此处为隐避之所,以一丸泥封穴口,闭关自守,不求取于人,如是亦足以供给四十人一生之用而有余。
埃梨入此富丽之窟室,恍游天上,傍徨良久,莫知所为。既而思得一法,乃取一袋实以金货而不取其银,竭其力之所能,运之出穴。往复数次,所得已甚多。出寻其驴则迷道不返,埃梨一一引之归。至穴口,以袋置其背,复以所采之薪覆之,不使袋有少露,以避人耳目。诸事已毕,乃复呼如前,门即闭。遂驱驴疾行,取道归镇。埃梨既至其家,推户而入,引驴至一小天井中,郑重着意而闭其户。遂取去覆袋之薪,而携其袋至内室,置于其妻之前。
其妻方倚睡椅而坐,见此袋不知何物,起视之,见累累皆金钱,心疑其夫窃诸他人者,不胜惊异之色,曰,“埃梨。此何来者?予思汝必……”埃梨不俟其言竟,即慰之曰,“勿恐,予之爱妻乎,汝勿疑讶。予不为盗,此物乃取之于盗者。汝当去其疑虑,予将告汝以予之奇遇。”言毕倾出袋中之金钱,如一小山,光焰夺目,目光为眩。埃梨乃坐而为其妻述冒险之始末。
其妻睹此多金,且闻埃梨之语,惊惧之心尽灭。不觉欢喜无量,不知所为,乃取金钱一一数之。埃梨见之,笑曰,“汝何愚也。真可谓贪儿暴富者矣。予将掘地为坎而埋之,则永远可不失。数之何为?”其妻曰,“然。然予欲知其约数。汝先掘坎。予将借升于邻家以量之。”埃梨曰,“汝欲何为?此无益之事也。汝幸听予之言,虽然汝必欲量之,亦无不可。惟当切忆勿泄此秘密事。”
其妻如教,径至慨星之家。二人虽析居,然相隔不远。斯时慨星方外出,埃梨之妻,因向其姒乞借升一用。其姒诺之,入室取量。惟素知埃梨贫困,今其妻忽需谷量,殆将以量粟,心以为异。因于升底涂以兽脂,俾还时可以察其曾量何物。诸事已竟,乃以升与埃梨之妻。并谢使之久待之罪。
埃梨之妻持升至,置于金侧,满入以金钱,复倾于睡椅。如是良久,金已量竟。尔时埃梨坎亦掘成。掩埋毕,其妻告以金货之约数,互相庆幸。而己则复至慨星家还量于姒,且谢其相假而归。
当埃梨之妻还量之时,匆遽不暇细视,遂致升底有金钱一枚,为兽脂所粘,附着其上。其姒受而视之,见金钱大讶,自语曰,“此何故!埃梨乃量其金货。此困苦者从何处得此多金?实令予不解。”言次,倚于卧椅,一种妒嫉愤懑之神情,不觉现于词色。
慨星每日必至工场及店铺,经理商务,薄暮始归,以为常。是日归少晚,其妻待之,恍若一小年之久。少顷,慨自外至。其妻一见即语之曰,“慨星。汝自思汝可为巨富乎?然汝弟埃梨之富,百倍于汝。彼不若汝之数金钱,彼乃以谷量量之。”慨星闻此隐语,茫然不解,诘问其故。其妻乃为之解说,告以始末,并自述其发见此事之诡计,而示以粘着于升底之金钱。
慨星视之,则乃古昔之金币,上镌古代帝王之名号,殆西坤之类。不觉对之艳羡,不以为埃梨得此,可以救其穷困,为埃梨喜,而惟觉歆羡妒忌之念交战于胸中,终此长夜未曾交睫。次日黎明日未出之先即起,往扣埃梨之门。尔时慨星之心,惟注意于金钱,不复待埃梨以兄弟之道。至即呼其名,厉声而言曰,“埃梨汝作事胡如是诡秘?汝诡为穷愁落魄之态,敝衣恶食如乞丐,而汝乃量汝之金货。”埃梨闻之愕然有间曰,“长兄,予甚不解汝所言之意旨。望勿为此谜语而解说之。”慨星以暴怒之音答之曰,“咄!汝欺何人,尚诡为不解耶。”因以其妻所寻得之金钱示之,且曰,“此量底之金货何来者?汝实告予。”埃梨闻此言,知此结果,原因于其妻之偏执。思饰词以弥补之,然事已发露,终觉无良策可以掩饰。不得已,因直陈颠末,不少露惊惧烦恼之状,而告以偶然得入盗穴,得此一袋之金,且指其所在,许以财富共之,并嘱秘其事。
慨星乃以倨傲之容而言曰,“是果汝兄之所确望。然予欲知此财物所藏之精确场所,有何符号,以为指导,汝应告予。如是则予可以自往。不然,汝拒绝予之命令,则予将告发汝于警察署。尔后汝非但不再有所得,即汝所已得之物,亦将因予告发而归于予。”
埃梨为此凶暴之兄所胁,其心已怯,经此逼迫威吓,不得不尽吐其实,告以彼所要求之各款,及出入之机关与口号。慨星觉其言皆实,无复可以进诘之事,遂舍之而归,而思运金之策。悬想将来,踌躇满志,妄念憧憧,往来胸际,不觉欣喜欲狂,预为次日之准备。而更漏迟迟,长夜不旦,通宵傍徨,不能成寐。伫俟东方希微,未黎明即起。择壮健十骡,负以大筐,驱之行。俾得畅所欲得,满载而归,且为二次远征计,当尽其力之所及,以运穴中之积蓄。
慨星驱骡向埃梨所指示之路而前。不久即至岩下,见一大树,大可蔽牛,窃念是殆即埃梨藏匿之处矣。因复拨荆榛进行,则地穴之户,已朗然在目。慨星趋近之,乃如埃梨之教呼曰,“西剡姆启户。”户果辟,遂入之,户亦随闭。
慨星既进窟室,觉其中之富丽,莫可言状。目中所见,无非金玉锦绣。历观各物,目眩神迷,真如行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埃梨所言,尚不足尽其万一,叹观止矣。叹美良久,乃取革囊数只,择最贵重之物品入之,携至穴口,将尽十骡所能负,运之归家。斯时其心中快乐无量,神魂飞越,而忘其最要之口号。不曰“西剡姆”,而误呼曰,“伯累(意即大麦)启户。”彼盖错记一种之谷名,以大麦为胡麻也。呼之良久,而门坚闭如故。
慨星见门闭不得出,大骇惧,竭力思索此启户之口号。而遇此危险之事,忧惧交并,记忆力顿失其用。虽绞尽脑汁,其脑中终无有此“西剡姆”之一字,一似当时未尝闻之者。盖彼实仅一贪婪之暴徒,无冒险之性质,无应变之急智,心为形役,遂不惜生命而为此。今户既闭,只能付之无可如何,因置袋于穴口。而己则绕穴而走,终无策以出户。
日将午,众盗皆返。行渐近,忽见有骡负大筐,鹄立于岩石之下。皆甚讶异。因即疾驰而前,逐去此十骡。慨星系骡时,本匆匆未尽绊,一逐即俱散窜林中。众盗既逐去十骡,其主要之目的,即在根求主有此骡之人。群议须大索穴中。于是盗魁即把剑为导,启户而入。
慨星在窖室内,遥闻马蹄蹴踏之声,自远而近,知必为众盗已返无疑。自思终不能免,竭力欲得一良法,俾得脱此危险。因匿于门后,思乘户启而逸。未几,彼所百思不得之“西剡姆”一字,倏已发声,石壁之户大辟。乃疾奔而出,以至猛之力,掠倒盗魁仆于地。方图他窜,而群盗之刃已交于胸,遂被杀于阶下。
盗既杀慨星,安然入户。见一满贮金银之袋,倚于户侧,即伊所欲携以去者。乃复挈之入,安置于旧处。然匆促间,竟不及察埃梨之已运去者。
众盗勘考此事而相评议,知慨星必初次入穴,不得出而被杀,但其以何方法而得入此门,则此问题终不能解决。此容受光线之石孔,如是其高,岩石之绝顶,又荦粗而难攀登,且其所用之规则,亦无与人以可根究之痕迹。觉此事真如天上飞来,出人意外,而不疑及彼之入户,或由于仿行窃闻之口号,因彼等深以此秘语为十分机密而必无失。故虽研究再三,终不料及有为埃梨侦知而仿行之奇事。
伊等遇此不意之异事,心滋疑惧,念此后将不能永远保有此财帛,必将为人窃尽而后止。因协议将慨星之尸,分为四片,投于穴内近门之处,分置两旁,以恐吓大胆之人,有仿之而为此危险事业者。且决议此数日间,暂为漂泊生涯,俟此死体之恶臭发尽,而后再归。遂封闭此穴,骑马俱去。而时以旅队游行于左近之地,以侦此事,且亦可乘此好机,以演习伊等劫掠之惯熟伎俩。
尔时慨星之妻,独处于家,见时已薄暮,而其夫尚不归,心甚恐怖。乃往见埃梨,似不胜警急者,急语之曰,“埃梨,予深信汝。汝引汝兄至林,断不为无见。然以何故,彼尚未返。暝色渐迫,吾恐彼有不意之变。”埃梨答曰,“否,彼必无不期之厄集其身,可无过虑。或彼故为慎重,俟日入始还,以免惹人耳目,亦未可知。”慨妻闻此语颇中理,遂亦不复疑虑,坦然归家,思此事之利害颇巨,慨之郑重乃尔,亦固其所。既归家,乃忍耐以俟。直至夜半,月黑星沉,残灯惨淡,然终无消息。忽忆及邻近之地,无可隐匿之所,慨将何以自卫。言念及此,不觉忧惧交集。草木皆兵,呼吁无门,涕泣何济,惟是自怨自艾,深悔恨己之贪婪,为妒羡心所煽动,而致酿此悲惨之境界。回肠九曲,徒唤奈何,通宵跼蹐,以泪洗面。迨天方黎明,即趋往埃梨之家而告警,且求援。
埃梨不俟其嫂之恳乞,即立时许可往寻其兄。因驱己之三驴,而向林中进发。及至岩下,则惟见碧血殷于草际,阶石尚濡,而不见其兄与其十骡之只影。心大鹘突,知非佳兆。呼门而入,则慨星之尸,赫然陈于户左。不觉战栗却步,肤粟股栗。然终以同气之感,自思当尽此最后之义务。于是不复踌躇,于穴中取二匣,以装此支解之碎肢体,如二小包状。令一驴负之,遮以柴薪覆。速运金货两袋,分载二驴背上,一如前次所为。既毕,闭门而去。惟鉴于其兄之覆辙,不敢即归,乃为预防之策,入林木深处自匿,待日入始驱驴取路而归镇。
既至家,即驱二驴入门。命卸其荷物,略述慨星之事。即引此负尸之驴,往见其嫂。叩门而入。应门者为一女奴,名曼绮那。其为人机警有智,富于进取力,能从事于至困难之冒险事业,而终达其目的。以此故,其品性非常人所可及,平日亦素为埃梨所器重。
迨入门,至庭中。埃梨取去覆匣之柴,置二匣于地,指之谓曼绮那曰,“此匣内乃汝主人之遗体。予有要事,汝为予达之。”言次曼为导进至内室。慨星之妻见之,自卧椅戚然而起,以至急迫之音问曰,“埃梨,汝良劳苦。寻汝兄之消息竟何若?彼竟何如?噫,予观汝面色,殆必已绝望。”埃梨曰,“汝言予实不知所对。幸少镇静,听予之述此事,而勿中断予之谈话。”因详述颠末,自出发以至发见尸体。述毕,复言曰,“予思此悲惨事,实出于不意。然已过去,如已逝之水,不复可挽。而祸患之来,方将未已。予等瘗此尸体,当加谨慎,一如死于天然之病者,勿与人以疑窦。予思此事惟曼绮那能任之,予亦就力之所及以相助。”即复建议同居之利便,而陈分立之不可。因同居则非但患难可以相顾,且亦可以慰离索之感。慨星之妻,念慨已死,此间之富有,已不啻薤露,而埃梨之家,则如日方中,日进未已,且转输所有,不忧匮乏。辗转思索,觉莫妙于准此义案,因不复犹豫而即许可。
埃梨乃辞别,驱驴归家,而奖励曼绮那,使之任所托之事。
时已将昏黑,曼急携数金而出。至邻近之药铺,叩其户而向之乞治危疾之一种锭剂。调剂师乃与以药,如其纳付之金资,且问以病者为伊主人眷属中之何人。曼太息曰,“嘻,病者即我主人慨星也。伊不能语,又不能饮食,无人知其为何疾。察其状,恐殆将不起矣。”
翌朝复至药铺,即泪承于睫,来求买一种之“安笙思”。此剂之性,系专用之于危险极端,已将绝望之病夫,而暂为孤注之一掷者。(殆参苓之类。)方其接自医师之手,面上若不胜悲戚之状,而言曰,“此药之效能,未知若何,吾恐未能胜于锭剂。噫,如是则终将无补,予将失吾之良主人矣。”
尔时邻近之人,皆已知慨星病且殆。是日日间,频见埃梨夫妇往来其家。迨入夜,闻其妻与曼绮那之哭声,知慨已死,人无以为异者。
次日清晨,日尚未出,曼绮那早起经营各事。谂知村尾有一老人,名麦斯塔夫,以补靴为业,设肆于镇有年,其为人诚朴而良善,且其每日开铺,亦较他家为早。于是往寻之。至则门已早启。入门以金钱一枚,置其手中,方有所言。麦视之,即言曰,“汝为此何意?”曼绮那曰,“予有求于汝。欲汝随予往缝纫一物,但必须以布带绷汝目。如是则予方可引汝至某处。”麦闻言有难色,既而曰,“呵呵,汝所言予知之矣。汝殆欲予为一违心之事,如是则必有关于予之良知与节操。”曼复以一金置其手曰,“上帝鉴之。予乞汝所作之事,实无污汝之高节。第随予往,请无恐。”
麦如其教,出门至一处,以一手巾缚脑际,遮其双目,始引导之至慨星家。既入室,先移置此四块之尸凑成之,乃去其遮目之巾,谓之曰,“予引汝至此。欲汝为我将此碎片,纫合为一。在汝所失之时无几,且若缝就,予将复酬汝以一金。”
麦如言,少顷工已毕。曼乃复以巾裹其首,引之至原处,如约与以金钱一枚。且嘱以勿泄此秘密事,始令之去。继复竭其视力,迨见其归铺始回。因恐彼以此奇异而返诘,或致露踪迹也。
曼绮那方回,埃梨亦至。乃取温水濯慨星之尸,又以香薰之缠以尸布,一切悉照通常之仪式。斯时埃梨已命工人数人,舁棺而至。曼令置之户外,如数偿以报酬而遣去之。己与埃梨合力放尸入棺内,加盖钉固。然后乃至墨斯克(回教徒之礼拜堂)布告此事,且告以葬仪之已预备。墨思克中之教徒,其行业在为死者洗濯尸体,斯时即欲往而尽其职务。但伊则告之以诸事俱备,且已完毕。
遂即举行葬式。少顷墨思克之祭司及僧侣已至。四邻人荷棺于肩,前行以至葬地。祭司随之口诵祷词,为死者忏悔。曼绮那从其后,涕泣而送葬。埃梨则与邻人之来送者,行列而诵经。
慨星之妻留于家中,与三五邻妇相向而哭。是盖彼时之习俗使然,遂致哭声不绝,一室中皆充满此悲哀之声音。
葬式已毕。慨星之末路如是,然人终无知颠末者。越三四日,埃梨乃于夜中,暗运其家之动产,至慨星之家,如金帛类之得之盗穴者。不数日已毕,遂宣告同居。弃其昔日之破屋,而迁居于美宅。牛马满野,金玉盈籝。埃梨此后遂享受此顺遂生涯矣。
当埃梨经营迁居之时,群盗前所议定旅行之日期已满,而相率皆归。逮入户,不觉愕然相顾,讶异不可名状。视解支之尸,已不知何往。而穴中之积贮,则又显然大加减少。盗魁乃曰,“予思此事甚不妙。如予等此后尚不思一良法以挽回,则患更无所底止。吾等历尽艰辛所得之财物,将拱手以入他人之囊中矣。予勘察此事,思彼等入穴,必已得吾侪之秘诀而仿行。且知此法者,当不止一二人。试观尸体已移,财帛日减,是其确证。此数人中已杀其一,其余者,予等亦必不能舍之。予之诸壮士,汝意云何?与予有同情否?”
其徒党闻此议,觉甚当而合于理。全群悉以为是,无异言者。因决定此数日间,当于全力从事于此,而暂停止别种运动之事业。
议既决,盗魁复曰,“予甚感谢诸君。以诸君之勇力,必能成就此事。今先办起始之事。需一胆敢豪勇之人,易名入城,以作侦探,易旅人或闲汉之衣装,用种种手段,以侦察各事。其主要之目的,则在访有无被杀而死之人。于通常谈话间,而详探其为如何人,并其居址,则予等方可以行事。但此事甚危险,非精细者莫办。倘或败露,实有关于吾全群之存亡。未知吾侪中有谁堪任此者?”
斯时即有一盗出而言曰,“某不才愿当斯任,当不致愤事,有负委托。即不然,使事不成,失予生命,为全群谋利益而死,死有余荣也。”盗魁奖励之,且告以机密。迨入夜,遂遣之行。乃伪为行人,乘天未明时,即入城。行至市场,则人声寂寂,尚无行道者。忽见左侧有一小店,户已大启,盗遂就之。斯盖即麦斯塔夫之居也。
麦坐于一斗椅,右手持一突锥,方将作工。盗近之,与行早礼。见其已老迈,因谓之曰,“翁起何早,天未明即工作。年高如此,安得有此眼力,而从事缝纫。予思日间当可为此,此时尚早,恐未能了然。”
麦闻言,摇首曰,“否,汝不知我。我虽老,然眼力尚佳。我尚忆数日前,有人招我至一处,缝合一破碎之死尸,其时天始破晓,昏暗等于此刻,顾我尚能为之。”曰死体,曰缝合,此奇异之语,入盗之耳,心怦然动,自思此与所探事,似甚有关系,或可藉此而得踪迹。因故为诧容,曰,“死体!何谓?汝何时缝一死体,予思汝必谬误。或汝为人缝一死者之缠布,因而误记。”麦曰,“否,否,予记之甚清。此事诚异,如汝欲知其原委,然汝勿得多言。”盗闻言,急以一金置几上曰,“汝幸告予。予当如教,不泄露于外人。此微物聊以酬相告者之高谊。或令予知其处,则更幸甚。”
麦闻言愕然曰,“承君厚贶。然予实无以答君命。”言次,举手作还金状。复续言曰,“实告汝,当前日去时,彼曾引余至一处,以巾蒙我眼,乃导之至其家。及予作工毕,复如是送予归。予虽往返二次而一无见闻。故不能以实告,深负君意。”盗曰,“虽然,但汝即蒙眼而行,而路之曲折及方向,当尚能记忆其彷彿。翁幸从予,当仍以帛蒙汝眼,偕予往循前日所由之路屈云屈止云止一,惟汝心内记忆以为主。如是则汝不啻告予以昔日之情事,而得达此目的。且汝身少劳苦而报偿亦不薄矣。此又一金也,聊酬高义。速偕予往,惟翁之惠。”言讫,乃复以一枚金钱置其掌中。
此两枚之金钱在麦手中,古色陆离,直触眼帘,不觉心为之动。注视踌躇,良久良久,不发一语,一似意不能决者。至终则自怀中取夹袋纳入之,顾谓盗曰,“我业告汝,知之不详。即使予往,所得恐亦不能如汝之望也。惟当日出门时之事,予尚记忆之,余则忘矣。去,去!我行将为汝思索之。”
盗意得甚,挈麦匆匆出,不及闭户而行。至一处曰,“此其地矣,即彼蒙我目之处也。”盗乃出帛一方,绷其额上,傍之行。彳亍于路上,或引之,或随之行。行重行行,踯躅良久,麦忽霍然止,嚄唶言曰,“予思当日所行,似不至更远于此。”盗闻言亦止,游目四瞩。噫,此何地?则此渠渠夏屋在于道左者,正昔日慨星之旧庐,而今日埃梨之新构也。
盗乃自衣袋中取所储之垩笔,疾行至门前,作一标识于其上。乃取去麦蒙目之物,询其为何人之居。麦则以己不居此村,莫知为谁氏。盗知麦所知者已尽此,无可进诘,遂遣之返店。而己则径回林中,以报告此事于其徒党。
当盗谍离去此村后,一刹那间,曼绮那适以事被遣归。举首忽见门上白垩之标识,不觉大诧,自忖曰,“此记号为何意?岂有人不慊于主人,而将施其狡狯欤?抑仅为儿童游戏所偶作乎?其将以何法对付之,以抵制此不意之祸害?”于是即取垩笔仿其式,作记号于上下两旁之邻屋,与埃梨之居相似者。既毕,乃入室操其业如恒,一若行所无事,不欲以此危险使主人惊扰,以败乃公事者。
其时盗返故巢,陈其旅行侦探之所获。盗首奖励其能,乃复对余众而发言曰,“火伴,汝等亦知此时机之不可失乎?吾党须即结束就道,潜行入城,相待于一僻静之地,以为聚集之场所。然须离散而行,勿滋人疑惑。予则偕侦获此消息之伴侣,往访其屋,既知确实之所在,而后可定进退之策。愿诸君鼓勇气以谋公益,成功在此一举也。”众盗闻之,无不拍手赞成。于是议遂决。即时预备出发。盗等二三为伍,参差而行,游行过市,一如常人,人无疑者。乃相与潜伏所约集合之地以待号令。
盗首则挟谍者越多数之街市以至埃梨所居之村,而探访所标志之室。行经第一家,即有曼绮那所仿为之记号者。盗指之曰,“此是也。”不意忽一举首,则见有物朗然入目,盖其第二家第三家,亦罔不有白垩标门,粉色如新,字形毕肖,一如第一家之所为。不觉大讶,指问谍者孰为所志。盗谍至是,亦迷惑不知所对。乃复往下视,则第四第五之家,亦莫不然。于是实告盗首,并立誓言,谓己所记者,实只一家。且曰,“此事实非予之所及料,予不解其何以模拟能如是之酷肖,盖至此予亦不能自认何者为予之所记矣。”
盗首既以此计画不成,遂返至盗众集合之场所。适遇一盗,告之以此次远征之失利,在此费业失时,无所事事,无宁归休。因命之传令于众盗,相与潜自引归,而至退隐之巢穴。
众盗既重集于林中,盗首宣告此事失败之原因。群盗莫不愠甚,众口一词,谓司其事者不得辞其咎,宜科以失误机密重事之罪。遂判定处以死刑。斯盖虽暴客之举动未脱野蛮之习俗,然欲保一群之安全与幸福,势不得不以严酷立法。彼有志复仇,而事机屡失,一误再误,因以偾事者,直盗道之不如矣。
处决既毕,乃有一盗忽发奇想,愿复任侦探之责。谓彼之秘计,其效果当百倍于前人。盗首许可。彼乃易服入城,一效前法, 麦斯塔夫引至其处,而作一红色小记号于埃梨门上。以为如是则不易辨认,且红色黯淡,不若白色之耀目,当不至再受敌人之愚。因自信为百无一失之良法,遂归而报命于其党。
斯时也,忽有一人自道旁蹀躞而来,止于门外。噫,此何人?盖曼绮那自外方归,一如前日。方欲举手推门,而门上之红色标志,迄不能避其明锐之双瞳,已灼然显露于眼帘。曼一见即推知其故。复仿其式,作记号于邻近之户,如前所为。而盗不知也,惘惘然归,自诩其计于众,以为此次于数十家之村中,访埃梨之户,不难一见立辨矣。
盗众信之,意皆得甚。于是整备入城,一如前计,以备实行平日之计画。盗首复偕谍者,先往探视。不意及至其处,则所见事,殊不可思议,实无异于前之所遇。盗首恚甚,几于发狂。而此偕行之盗谍,亦恐怖惊怚,深悲此一击不中,不免与前之谍者同其结果也。盗众不得已,乃相率复归,莫不懊丧失志。而此侦探失事之盗,其受罚自无待言矣。
盗首乃思出行不利,反丧党中之二勇士,如是以往,将必无成功之一日,而徒党且因以减少,可惧孰甚。因思同辈虽富于冒险之精神,而徒勇无成,所谋辄败,殆如人之臂力虽强,必以元首为之指挥焉。以是遂决意自任此事。微服潜行以入城,复以麦斯塔夫之借助,知埃梨之居。但彼不复另立记号,如前二人所为,惟十分留意其地址并方向,亦不斤斤注视,而仅于其前周行数过,至心内了然,即点首四顾,倏然飏去。
盗首既侦得此消息而返,不觉喜形于色。至林中,则其党已待之于石穴之前。盗首一见即言曰,“火伴,予以半日之旅行,已得达其目的。自今以往,无论何人,皆不能阻予等之报复。予顷已确知此罪人之居址,可即施以扫除。以后予等作事,必如是之严密,使无第二人能知予秘事者。而吾等之富有,乃可长保。惟此事志在必成,须以刚强不屈之精神对付之。如一不谨,非但所事无功,反增祸害。故予等对于此事,不得不商酌尽善而行。予今已筹得一方法,如诸君之策,更有妙于此者,则尤善矣。”伊既陈其计,即派众盗为数小队,分遣至邻近之村镇。令买骡十九头,皮制极大之油瓮三十八枚,其一满盛以油,而其余之三十七瓮,则皆空其中。
越二三日,众盗所购之物,俱已齐备。惟瓮之口甚窄,盗首乃设法扩大之。每一瓮中,令一盗入其中,封闭其口,一如贮油之法,而于其旁略开小孔,不纫合之,以为空气流通之路,得便其呼吸。复于贮油之瓮,取油少许,涂抹于各瓮之口。不知者视之,以为此累累者必为油瓮无疑矣。
各事配置已毕,乃取贮盗之瓮三十七,并一贮油者分载于十九骡之背上。盗首则为之导,伪为油商之状,取道入城。预算日入时当至其处,至则天已昏黑矣。盗首即直诣埃梨之家,以马鞭挝门,告以失路,且求许其寄宿。是时埃梨晚餐甫毕,方散步草地上吸受空气,闻声出应门。盗首对之一举手曰,“贵君,予适自远处贩油归,拟明日售之于市。不意至此已日暮,予不知何处可度夜。因不揣冒昧,叩贵君之门,乞假一席地。如贵君以予之请求,为无不便于贵君,则假予一宵,受惠多矣。”
埃梨虽曾在林中窥见盗首之状貌,且熟闻其声音,一见当不难即知。然时已昏黑,且断不料及此时之油商,由于盗首之假托,以是无所疑虑,即大开其户而曰,“请以让其入,并此十九头负瓮之骡,使之立于草地。”而己则肃客入室,殷勤备至。命其仆名蔼代拉者,代卸其骡之荷物,置之庭中,驱骡入屋后之皂枥饲食之。复呼曼绮那备晚餐一分,以供宾客。且又为之整治客舍,预备床席。所以待客之道,靡不周至。斯时之埃梨,正时而酬酢,时而指挥,奔走以尽地主之谊。而岂知此座上不速之客,即山中暴客之魁也。
埃梨待客,礼数甚周,视一切均整备,乃辞客而去,且谓之曰,“简亵勿罪,如有所需,可以相告。”盗首谦谢起,送之出户,而自至厨下。诡语曼绮那将至枥下视其骡。乞火径至庭中,扣瓮告众盗以机密事,每一瓮皆轻语之曰,“明日予当以小石投瓮为号。汝等闻声,可即以利刃剖瓮出。记之,记之。”告戒既毕,回至客舍,熄烛就枕。惟以要事萦心,恐误时机,乃和衣而睡,未几鼾声作矣。
于时埃梨亦召曼至,语之曰,“明日破晓,予即起沐浴。汝为予寻检浴巾,预交蔼代拉,且为予煮肉羹一瓯,俟予浴后早膳。汝勿忘也。”语毕,亦径归卧室。
曼不敢忘主人之命,为之预备浴巾,以与蔼代拉。又生火支锅,为煮肉羹。卒卒鲜暇,因不复就睡,倚窗而坐。未几夜阑灯灺,盏中之油已涸。寻思室中既无少许之油,又无蜡烛代之,不觉窘甚。因出房思取之他处,而重门已闭。蔼闻之,问以何为。告之故,蔼曰,“此细事耳,何必如是?庭中累累之瓮,注取少许,即足用矣。”曼闻其言即携一油注,径至中庭。乃将近瓮旁,忽闻其中有微弱之音发声曰,“此其时乎?”嘻,此何声也?盖瓮中之盗,闻履声橐橐,以为盗首之来,即举相问。绿林豪客真卤莽哉。
盗在瓮中,语虽甚轻,然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且其瓮口封皮,当卸装后已经盗首撕去,以为流通空气之路。坐是二故,故其声浪传递甚速,一种清朗之音,已径入于曼绮那之耳。
咄咄奇事,于油瓮中忽发人声,他人当之鲜不惊叫失措者,或因是而惊起群盗,陡起不测之祸。无能之人莫不坐此以致失败。然曼在当时,一闻此声,并不惊骇。盖曼之为人机警,有胆力与急智,其处事所以较他人占优胜者,正在此等处。伊乍闻之下,心中即了悟其故,自思此中以人代油,事出意外,必含有危险残害之事件无疑,此时若不思挽救,必将祸及埃梨全家。于是立定主意,不露仓皇之状,即假为盗首之音拊瓮答曰,“尚未。”及至次瓮。复问如前。曼均以此语答之。至终过三十七瓮,而至末贮油之一瓮,即由瓮中取油,贮入油注中,携之回厨下,加入灯盏内燃之。又取一大铁锅,复出至庭中,满盛以油。返取火炉一,中燃以木块,令焰极盛。置锅于其上,坐守之。伊独自寻思,埃梨偶留油商一宿,不意隐藏三十七瓮之盗,如此油速沸,则予之计画,不致失坠,而埃氏全家之幸福,亦可保全,因益加火力。少顷,油渐渐沸。未五分钟,大沸如潮涌。曼大喜,捧锅去,于每瓮中皆注入少许。瓮中盗跼蹐不得辗转,转瞬焦灼死。须臾,已沃了如许之盗,俱无复有生望。曼携空釜回厨下,窃喜目的之已达。
曼作此事,殊有价值。伊一人为此,不作一声,亦不惊扰众人。见盗均死,如无事然,回房闭户,将前煎油时所生烈火,以水沃熄,仅留少许于炉中,足煮埃梨之肉糜。息灯伏暗处静待,欲一见此事之究竟,以破宿惑,因不即就睡,伏窗下,由隙间以窥庭中。
曼窥伺约十五分钟,盗首醒由床上起,开窗四顾,寂无人声,天色沉暗,黑如漆。乃拾小白石数颗,投向瓮所在处,均中,铿然作小响,但无回音,亦无起而应其召唤者。盗首久俟,大不快,又掷石二次三次。终不应。始大惊异,思此事何以失误。亟跃下庭中,近第一盛盗之瓮询之,又不应。初以为熟睡,不疑其死。及探首瓮口,鼻观中忽触一种之油味,极热而枯焦,棘喉中甚猛烈欲呕。试第二三瓮亦如是。疑不决,至末,伊见一瓮之油,己所满贮者,已甚减少。推度其故,恍然明了。知此次图谋,又归失败,不胜悲愤。顾无他法,不得已,乃逾园与庭交界之墙,翻身至草地,又逾长短垣数重而逸。
曼待良久,寂无声息,盗首亦不返。料其必已逾垣去,因户间已加键二道之铁闩,颇不易出也。曼既得如此之结果,不胜自幸。思众盗已歼,虽盗魁漏网,然势孤易制,日后当不能大为害。心中不觉泰然,徐徐起立,倦而就卧,不少顷已熟睡矣。
日未出,埃梨即起赴浴所,其仆蔼代拉随之,茫然不知昨夜中有非常之事件,出于其家者。盖当时曼知惊醒若辈之无用,而或反以偾事。且其时已经营此冒险之事业,亦无时光可失。及危险之事已去,更不必惊扰全家,故埃梨等至此犹在梦中。
浴竟,日已出。埃回至庭中,始诧异此累累之瓮,何以尚堆积吾庭,彼油商又安往,胡为不驱骡适市以求售。疑不能决,问于曼。曼欲为之陈说其始末,乃先谓之曰,“上帝祐汝,及汝全家,祸患已去。汝今欲知此事,予当说明。汝第随予来,毋恐。”言次,引之至瓮旁,令俯首觇之。则一属目,即见有人伏其中,失色回首大叫。曼曰,“无妨,彼不能为汝害。彼当时潜入,本图不逞,然至此则已无能为。彼今者俨然成一死尸矣。”埃梨不解曰,“曼绮那,汝言何谓?汝可速述颠末,予甚欲知此奇事。”曼曰,“诺可。但祈汝勿惊扰,并勿惊动邻众。当思一极秘密之良法,以安顿此死尸之问题。汝今试再观其他瓮。”
埃梨依其言,则见每瓮中皆有人在,惟末一瓮则否,视其瓮上之油渍痕,其内容已较减少。心以为异,时以目视瓮,复以目视曼,嘿不一语,若有无限惊愕之情者。良久,忽自语曰,“但此油商为何如人乎?”曼曰,“其人诚酷似一商人。予今将告汝以实,且以何故而为此。但汝欲闻其详,汝可入室。予将为汝取肉糜来,食毕,再告可也。”言次,埃入室。曼为之取羹。至埃举匕未及食,即问曰,“其事究何如?汝速为予述之。”
曼如言,为述昨夜之事,既且曰,“此事之起端,已非止一日,予已早有所见于二三日前,顾当时不能确定其为汝害,今证以所遇。此事之忽然来袭,可决言其必为林中四十盗之阴谋,彼等之意旨皆欲置汝于死。今三十七人已死,余二人不知已于何日除去,今只剩一人,汝善自防,当不足惧。予亦当尽予之力,资汝臂助,以保阖家之安全焉。”
埃梨闻言,甚感动,答曰,“汝之恩没世不敢忘。予之余年,皆汝所赐,予必相报以明予志。自今以后,予当还汝自由,且将别有以酬汝。天诱汝衷,救予于难,脱此危险之关。吾望上帝助汝驱逐祸害,反殃其身,则予等当可终免其残害矣。但予等今须用何法,以埋此尸体乎?吾思此事最为紧要。顾何人能胜其任,无已,则惟吾与蔼代拉耳。”
埃梨之园,甚长而阔,满栽以大木。伊等主仆,乃合力于树林中掘一深坎,长广深浅,足容如许尸身之放入。其地土松且软,不久,坎已掘成。即将盗尸自瓮中取出,解下其所带之兵器,将尸放入坑内。少顷,三十七个焦烂之尸,一一入坑,加土筑好,将地面平治如常,令无破绽。又将众瓮及器械,一一藏置。而骡无所用,且无处可容匿。于是埃梨乃命仆将十九头之骡,分数次驱入市鬻之。
盗首当日既出险,即逸入林中。将近旧穴,觉一种阴森凄惨之气,竦人毛发。回想所遇之恶境,不觉悲从中来。入穴独坐,形影相吊,失声大恸曰,“予之勇士,予同患难之勇士,今乃何往?予失汝等之助,将何以成予事?以汝等之勇猛,乃丁于厄运,竟并命于俄顷,是诚为无价值。虽然,勇士不忘在沟壑,君等为一群之公益,执兵而死,死复何恨?顾此后予欲再求一良伴如君等者,何可得乎?如是则此复仇之事,殆只予一人任之矣。”心中默自思索。良久,计画已定。倦极曲肱少睡,过此残余之半夜甚速。
次日,天微明,盗首即起,照所定之计画而行,微服入城,僦居一旅馆中。自思昨宵之事,未知究竟如何。因诡辞向店主人,询以近处有无新闻。彼所对则与此事并无涉。心甚异之,思埃梨处事,何机密乃尔。盖彼不欲人知其隐,殆亦知此危险之事,于彼生命有关系也。以是知其防守必甚严密,急切必不能下手,因耐心静守,探埃梨之举动,以便进退行事。
盗住数日后,以种种秘密方法,或明或暗,或朝或暮,驾一马自穴中搬运许多美好之织物,如锦绣布帛之类,至旅店中,而转售之于一商店。久之,渐相稔熟。其店之主人,即埃梨之子,袭慨星之遗产者,年少好交游。盗时已变姓名为苛琪亚(Gogia),伪为诚恪,待商人礼数甚恭,一似后进之敬前辈。以是埃之子甚喜之,屡相过从,遂缔交为忘年友。盗初不知其为埃子。及后埃梨来,三四日辄至店一视其子以为常,盗见之,起一大注意。俟其去后,潜询之人,始知即店主人之父。心窃喜,思设计饵之。乃时邀埃子宴其寓,设筵备极丰美,款待之维至。
埃之子屡次受苛(即盗首假名)厚待,思不可不一报之。而其寓所又极湫隘,因归家以情告埃梨,思享之于家,以酬苛之厚谊。埃许可,且曰,“明日为礼拜五,汝可闭店,于午后偕苛君出游。不须告以此意,只引之至此,过门外时,即延之入,似较常例之请客少便利,且不迂拘。汝且往。予当于尔时令曼绮那预备晚餐,以俟其至也。”
其子如言,至明日下午约苛同出,至各处少一游览。及归时,于无意中故引之至埃梨所住之街。及至门首,即止而叩户,谓苛曰,“此吾父家中,可入少憩,且请君在此晚餐。予屡次受君之惠,今日聊以相答,望勿却也。”
盗闻此,思时机已至,不胜暗喜。顾欲掩饰,伪为谦逊不欲入。惟时埃之仆已出,启户以俟。埃子以手挽苛臂,牵之强入。埃自内出,降阶相迓,欢迎备至,且谢厚待其子之惠。苛以礼相接,就坐,即互相谈笑甚洽。少顷,苛忽起立告辞。
埃急止之曰,“苛君,君欲何往?予甚愿君且少住,饭后归去未晏,乞君嘉纳予意。如君必欲坚执此义,是殆以茅屋草具,不足以辱高贤也。”
苛曰,“否,君之盛意,予已敬领,君何谦逊乃尔。予之欲去,非由于此。但予自有予之隐情,以致重负君意,望君恕予。”
埃曰,“苛君,但君之隐情,可得闻乎?”苛曰,“予有癖,生平雅不愿食盐味之食品。”
埃曰,“君之言尽此乎?若别无他故,则事易办。就食品而论,其中 一物(即面包),各处皆无以盐制者。其他肉腊及肴品,则予当为君嘱庖人,令勿加盐料。君幸少待,予即往一视也。”言已,至中厨语曼绮那,令备肉脯,及他肴三四碟,皆勿入盐。
曼此时正调理肴馔,闻此新奇之命令,心滋不服,乃向埃梨问曰,“谁?!不食盐者,此乖戾之人!吾思汝之宴,若令予治之,必将不佳,不足以娱佳宾。”埃急曰,“汝勿尔。彼乃良善之人,癖如是耳。汝但作,勿违予意。”
曼如言而心甚奇异,思一见此怪人。不久料理已毕,蔼代拉来安置几案,曼助之运食品,至食堂见苛貌,心中忽骤悟。彼殆即前此之盗魁,今虽改装,而真相终不能掩。又加意侦察,则见其上衣中隐约藏一短剑。渠自思曰,“不食盐者,乃此恶徒乎?吾可无疑矣。彼为埃梨之仇,今日之来,必将肆其毒害。然予必当阻之于成事之先,决不使此残贼得志也。”
晚餐既备,蔼代拉又往整治果品。曼于此时间,独自措置一功,以备实行此冒险之事业。少顷,蔼来告,果实已备。曼乃往撤筵席,排列酒果,设一小几于埃梨之傍,置酒杯三盏于上,即偕蔼俱去。余埃氏父子,与其客对坐一室中,静饮一瓶之啤酒。
苛琪亚睹此,心潜喜,自思报复之好机会已至,埃梨之生命已不啻在其囊中。乃窃计曰,“吾为此事,必先令此二人痛饮,使之酩酊大醉。我乃剚刃于埃梨之胸,而无人得以阻我。其时庖人及其奴仆,或正就食,或已熟睡。我即乘其不知,仿前次逾垣出。计甚得。”
曼既出食堂,即回室,伪装如一舞女状。首带华美之冠,腰束镀银带,一锐利小匕首插其上,面上蒙以美丽之假面。装束既毕,乃命蔼代拉曰,“取汝小鼓,予等当入一舞蹈,以乐佳客。渠乃幼主之友,汝从予来,当为之演奏一奇剧焉。”
蔼从之,持小鼓随曼入,和容下声,请于埃梨,一演其技。埃曰,“善,汝等且试演。予将请苛君一评高下。”言已,又回向苛曰,“深夜寂饮,无以为欢,令奴辈舞蹈一回,以破岑寂。君勿疑予宴君多耗费,盖彼等皆予之家人,一女奴,一庖人,即君日中所见者也。”
苛虽雅不愿意于此宴会间,突添两人,顾亦无可推辞,不得已允之。于时主客无言。蔼挝小鼓,冬冬作细响,唱古曲,其音节与曼之舞蹈恰合,起落上下,靡不应节。歌舞数回,曼忽又变一种舞法,自腰间挈小匕首,执之而舞。其盘旋甚轻捷,其踊跃甚高。引刀四刺,或收或纵,飘忽迅速,寒光森森逼人。
既而急霍然止,取蔼所持小鼓,左手执鼓,右手执刃,径至座前,以鼓之反面空隙,引向埃梨。常例舞女每舞毕,辄如此以收观者之酬赏,故曼仿为之。埃乃取金一片,投入鼓中。曼即去而向埃之子,复如前。至终至苛前。苛见此状,思亦酬之以金,乃解胸前衣袋,方以手探入,曼忽猱进,左手持匕首,直揕其胸,深入数寸。刃出鲜血潺潺,随刃流溢,洒地毡上作胭脂色。
埃与其子见此,战栗失色。埃大呼曰,“杀人贼!汝何为如此?汝灭吾家矣。”曼从容拭刃答曰,“予何为乎?予之所为,福汝家,非祸汝家也。汝试观此。”言时启苛之上衣,出剑一柄,指之曰,“汝良友,乃潜藏此凶器。汝如细观其貌,与前此之油商无二,且其举动多可疑,吾一见即疑其为盗之魁。今乃除患尽,汝可高枕而卧矣。”
埃闻言,始恍然悟,此次生命复为曼所救,不觉感甚,呼曰,“曼绮那,汝于予恩亦厚矣。予前云将报汝惠,今时机至矣,予即许汝以自由,且将以汝为吾子妇。”曼夷然曰,“除患,吾分也,吾不敢邀非分之福。且予自行心之所安,富家妇何足算?吾勿愿也。”卒不许。
埃乃埋盗尸。顾心终惴惴,惧有伏莽未尽。待数月无事,心渐定。思一探林中踪迹,乘马而往。将至洞门,则见榛菅塞路,无人马行迹久矣。大喜,直造岩下呼门而入,又满载归。自此埃以此处为外府,时取用之,不忧匮乏,家道日以长。前此破屋卖薪之子,今俨然面团团作富家翁矣。
曼绮那其后不知所终。
已经读完最后一章啦!
90%的人强烈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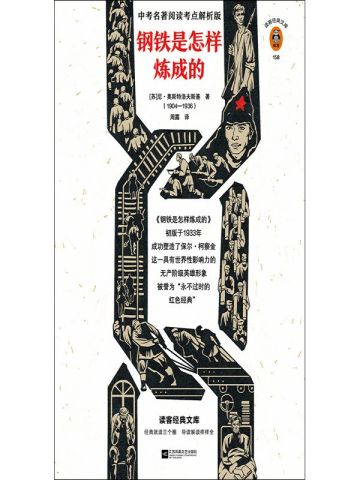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一部
- 书名: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作者:
- (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 本章字数:
- 74
保尔·柯察金从小饱受生活的苦难,目睹了很多底层人民的辛酸,在老布尔什维克朱赫来的指引下,保尔心中点燃了革命的星火,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