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关公
- 书名:
- 关公崇拜溯源
- 作者:
- 胡小伟
- 本章字数:
- 6403
- 更新时间:
- 2024-05-21 15:04:43
如果仅仅是佛教一宗一寺的“显圣”传说,所在多有。从桂林龙隐岩佛徒碑刻即以关公续接天台智(左岂右页),又加予“擎天得胜”称号来看,关公此时已经另有使命在身,这就是“战神”。另一通记述年代、地理相近的宋碑能够证实这个微妙而意义深远的变化,这就是至今犹存山西沁县博物馆的元丰三年(1080)《威胜军新建蜀荡寇将〔军汉寿亭〕关侯庙记》。雍正十三年《山西通志》概要介绍说:
沁州汉寿亭侯庙:宋仁宗时侬智高陷邕州,铜川神虎第七军以矫捷应募。行次荔浦,祷于祠下。广源以南地,多深林,蛮伐木塞路。忽大风卷卧木,军得并进。及战,有神兵旗帜戈甲,弥亘山野。敌顾望恇怯,军遂大克。归建庙。李汉杰撰记。[55]
其实不够确切。该碑全文甚长,为省篇幅,仅将有关文字抄录如下:
向也交(左阝右止)入寇廉、白,熙宁九年,今上矜恻下民,诏元戎举兵问罪。沁州铜川神虎第七军以(左走右乔)捷应募者,由任真而下,凡二百三十七人,隶于左第一军前锋之列。枞金伐鼓,行踰桂州,驻旌荔浦,遇将军之祠下。询其居民,对曰□其始,得□□□□。皇祐中,侬贼陷邕州,祷是庙,妄求福助,掷杯不应,怒而焚之。狄丞相破智高,乞再完。仁宗赐额,以旌灵贶。众骇其异,罗拜于庭,与神约曰:一军誓假威灵,平蛮得儁,长歌示喜,高蹑太行,而北归旧里,当为将军构饰祠宇。复请木(刀)绘马,执为前驱,入践贼界,士气骁锐,武威震叠,蛮将闻钲鼓,望风乞降,余众弃城而遁。进军临富良江,蛮酋遣将,乘蒙冲斗舰,举楫若飞,急趋争岸,迎官军陆战。江北神虎军鼓噪先登,强弩雨射,贼大奔(溃)自相腾轹,斩首及溺死者数万余人。既捷,荣雄受爵赏者二十六人。任真、贾信、董宁并指挥使,余以功之高下,递补有差。
山西沁县博物馆藏北宋元丰三年(1080)《威胜军新建蜀荡寇将军汉寿亭关侯庙记》,详尽叙述了他们奉命远驰广西抵御交阯军入侵,密林中遭遇伏击时,如何得到关公率阴兵救助,全军平安,回到驻地后集体立庙,酬谢关公的过程。
先是,我军之行也,广源以南地多深林,密于栉比。蛮人预伐,横绝其路。结营息众,势莫能前。夜有大风暴发,怒号之声,若挝万鼙。迟明视之,卧木飞尽,九军得以并进。我军之战也,众与敌均。俄有阴兵,旗帜戈甲,弥亘山野,敌人顾望,惴恐而败。精诚所召,助顺之灵。暴风夜至,阴兵昼见,神以符效,应人之祷。神虎军踊跃请行,深入万里,果立战功。归而建庙以享祀,荅神之休。庙制一新,高堂峻庑,雕焕森严。费逾千计,出于众心悦助,其赀成之不日,事有极异不著,于辞久则寂无所闻。乃(上龙下口)石镂记,永传嘉应,于神无愧负矣。[56]
碑文提到“迄今江淮之间,尊其庙像,尤以为神”,已与前引刘禹锡《自江陵沿流道公》诗句“行到南朝征战地,古来名将尽为神。”地域相关,时代踵继。可以见出,关公信仰在唐宋之际,已经开始从荆楚地区沿长江而下了。
请注意,这里实际上谈到在广西先后发生的两次战事,第一次是仁宗朝狄青为主帅征伐侬智高,第二次是神宗朝郭逵为主帅逐走交(左阝右止)(1076),《宋史》均有记载。也和北宋其他战事一样,这场战争依然是在“半人半神”的状态下进行的。《宋史·狄青传》说他“临敌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颇有几分天神鬼魅的模样:
皇祐中,广源州蛮侬智高反,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岛,围广州,岭外骚动……青明日乃整军骑,一昼夜绝昆仑关,出归仁铺为阵。贼既失险,悉出逆战。前锋孙节搏贼死山下,贼气锐甚,沔等惧失色。青执白旗麾骑兵,纵左右翼,出贼不意,大败之,追奔五十里,斩首数千级,其党黄师宓、侬建中、智中及伪官属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贼五百余人,智高夜纵火烧城遁去。
司马光言,侬智高攻广州,“使勇士数十人,以青黛涂面,跳跃上岸,广州兵皆奔溃。”[57]亦或双方都有“以傩制傩”的心理和威慑功用。又《宋史·郭逵传》:
交(左阝右止)李乾德陷邕管,召为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兼荆湖、广南宣抚使,请鄜延、河东旧吏士自随……至广西,讨拔广源州,降守将刘应纪;又拔决里隘,乘胜取桄榔、门州,大战富良江,斩伪王子洪真。乾德穷蹙,奉表归命。时兵夫三十万人,冒暑涉瘴地,死者过半。至是,与贼隔一水不得进,乃班师。[58]
请注意“时兵夫三十万人,冒暑涉瘴地,死者过半”句,即知立碑之官兵虽经密林中敌军设伏,仓促应战,犹能全身而还,立功受赏,所以要回乡为关公建庙,敬诚祈祷的心理了。
沁县关庙立碑人达到七百八十多位,包括两个属于北宋“禁军”编列的建制部队的官兵:一个是“先于熙宁九年五月内选募,往安南道战蛮”,参加了实际作战的神虎军,另一个是前来赞襄的宣毅第二十五指挥,都是戍守西夏前线的一线部队以及上下级其他相关人员,恐怕是现存关庙碑刻中人数最多的。宋代兵制承袭晚唐五代“募兵制”,保留了一部分职业军人,即“营伍子弟听从本军”。但是基本国策却是招募灾民,理由倒也简单:“不受为兵,则恐为盗。”[59]此外还有罪犯充军及抓丁两途。往往形同乌合,因此战斗力始终不振。[60]所以在一线军队中亟需树立榜样或以“神道设教”激励士卒奋勇之志,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率阴兵助阵”的说法,并非中土素有风俗。在道教前身的方士观念中,以“兵神”著称正是蚩尤。《史记·天官书》云:
蚩尤之旗,类彗而后曲,象旗,见者王者征伐四方。
《云笈七签》卷一百引唐人王瓘《轩辕本纪》:
蚩尤始作铠甲兜牟,时人不识,谓是铜头铁额。
于葛庐山发金作冶,制为铠甲及剑,造立兵仗、刀戟、大弩等,威震天下。
类似今日“兵工专家”。唐初儒家祀典则以谋略之相姜尚为“武成王”,与孔丘“文宣王”对举。
[1]《全唐文》卷六八四,中华书局影印本。
[2]《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大正藏》五十卷。
[3]《宋高僧传》卷十《唐荆州天皇寺道悟传》。
[4]《宋高僧传》卷十《唐荆州天皇寺道悟传》。
[5]《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载《大正藏》四六卷。
[6]参《大正藏》卷四六《修止观坐禅法要杂说》。
[7]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审查报告〉三》,载《金明馆丛稿二编》。
[8]《全唐诗》卷五二。
[9]《宋高僧传》,中华书局排印本第 225 页。据《三国志·魏书·张乐于张徐传》叙张辽征吴时死于扬州:“辽还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刘晔将太医视疾,虎贲问消息,道路相属。疾未瘳,帝迎辽就行在所,车驾亲临,执其手,赐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还屯。孙权复叛,帝遣辽乘舟,与曹休至海陵,临江。权甚惮焉,敕诸将:‘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是岁,辽与诸将破权将吕范。辽病笃,遂薨于江都。帝为流涕,谥曰‘刚侯’。”
[10]乾隆《解梁关帝志》。
[11]今存佛教典籍有《景德传灯录》《续传灯录》等几种,但笔者没有发现类似记载。
[12]敦煌写本《楞伽师资记》是唐朝开元年间净觉和尚根据其师玄赜《楞伽人法志》而作,其中叙及北禅法统八代,第七代迳言“唐朝荆州玉泉寺大师,讳秀”。宋代玉泉寺已为禅宗丛林,宋真宗命人编纂智(左岂右页)以后的诸僧语录,即《景德传灯录》。
[13]嘉靖壬午卷之十六,毛本作“普静”。“还我头来”是禅宗所谓迷失自我。宋末周密(1232 ~ 1298)《齐东野语》卷一“真西山”条谓:“有道人于山间结庵,炼丹将成。忽一日入定,语童子曰:‘我去后或十日、五日即还,谨无轻动我屋子。’后数日,忽有叩门者,童子语以‘师出未还’,其人曰:‘我知汝师久矣!今已为冥司所录,不可归,留之无益,徒腐臭耳!’童子村朴,不悟为魔,遂举而焚之。
道者旋归,已无及,绕庵呼号曰:‘我在何处?’如此月余不绝声,乡落为之不安。时有老僧闻其说,厉声答之曰:‘你说寻“我”,你却是谁?’于是其声乃绝。时真母方娠,忽见道者入室,遂产西山,幼聪颖绝人。”按真西山即南宋理学大家真德秀(1178 ~ 1235)。“关公索头”,老僧喝断,或为此时传说。
[14]据朝鲜金九经校敦煌唐写本。
[15]王维《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禅师塔铭》。
[16]《全唐文》卷三九○。
[17]《全唐诗》卷六七三。
[18]《全唐诗》卷六七三首载:“周朴,字太朴,吴兴人。避地福州,寄食乌石山僧寺。黄巢寇闽,欲降之,朴不从,遂见害。”他所见玉泉寺也当为唐末景象。
[19]《全唐诗》卷二四八。又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五作“唐郎士元《关某祠送高员外还荆州》”。《关帝志》此诗题《壮缪侯庙别友人》。《全唐诗》该卷首云:“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天宝十五载擢进士第……出为郢州刺史。与钱起齐名,自丞相以下,出使州牧,二君无诗祖饯,时论鄙之。故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
[20]此则材料承桂林市桂海碑林博物馆馆长刘玲双女士提供,谨此致谢。摩崖在龙隐岩。按《鞞婆沙论》卷十二言:“当言名缘耶。当言义缘耶。答曰:七解脱。当言名缘。当言义缘。”造像僧得名,当自此来。
[21]陈寅恪《韦庄〈秦妇吟〉校笺》,辑入《寒柳堂集》。又翟理斯(Herbert A. Giles,1845 ~ 1935)为英国汉学家。1897 年任剑桥大学中文教授 30 余年。毕生致力于介绍中华文明。其文原载《通报》第二十四卷第四、第五合期,译文载《燕京学报》第一卷第一期。
[22]康熙刻本《玉泉寺志·词翰补遗》,承当阳关陵文管会原主任姜耀南提供复印件,谨志谢意。又据张商英《荆门玉泉皓长老塔铭》,承皓示寂于元祐六年(1091)十二月十八日。
[23]据《玉泉寺志》,玉泉寺曾在南宋绍兴年间(1131 ~ 1162)、端平元年(1234)及元至正十七年(1357)三次毁于兵燹及火灾。玉泉寺志编纂委员会编(内部发行),2000 年 6 月印刷,第 36 页。承该书主编周天裕先生持赠,谨致谢忱。
[24]毛德《新建武安王殿记》,《解梁关帝志》卷三。
[25]《玉泉寺志》,第 156~157 页。
[26]《解梁关帝志》卷四《艺文下》辑录一组蒙汉官员在玉泉山的诗咏,其中有李俊民、刘纬、程严卿、何溟、周午、李鉴、乃贤等。《元史·刘伯林传》载
刘伯林济南人,与史天泽、严突、张柔同为汉军四大万户。其子刘马袭职万户,有子十二人,长子刘元振袭万户。元振卒,子刘纬袭万户职。或即其人。李鉴当为胡琦《关王实录》作序者。
[27]载《大正藏》(N0.1249)卷二一,第 227 ~ 230 页。台湾新文丰出版社
1983 年版。
[28]一行生平可参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24~245 页。
[29]毗沙门天王或实有其人。提云般若译《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卷上言:“惟有北方毗沙门子那履沙婆,曾于往昔造菩萨像,以斯福故,后得为王,名频婆沙罗,复因见我,今得生天,有大势力,永离恶道。”盖缘佛陀生于印度北方,毗沙门王可能是他早期有势力的施主。
[30]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序品第一》。
[31]北凉法众等译《大方等陀罗尼经》卷三。
[32]参《大唐西域记》卷一《缚喝国·纳缚僧伽蓝》。
[33]参《管锥编》第一册,第 320 页。
[34]周氏论文原系以英文刊载于《哈佛亚洲学报》第八卷(1945 年)第三、四号上。中译本题改作《唐代密宗(Tantrism in China)》,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7 月版。
[35]《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中华书局 1993 年 2 月校点本。
[36]《宋高僧传》卷二六《慧云传》。
[37]《全唐文》卷七三○。
[38]《金石粹编》卷一〇六,中国书店影印本第三册。
[39]段成式《酉阳杂俎》,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版。
[40]高彦休《唐阙史》卷下。
[41]李筌号少室山达观子,两《唐书》无传。大约生活在肃宗、代宗年间。乾元二年(759)《进太白阴经表》称“正议大夫持节幽州军州事幽州刺史并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臣李筌上表”,唐永泰四年(768)《序》署名“河东节度使都虞侯臣李筌撰”。可得时代之概。
[42]参敦煌研究院谢生保等编著《敦煌艺术之最》,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 年 6 月版。编者持赠,谨致谢意。
[43]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
[44]同上。卷第十七。薛居正《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上》亦言“新城北有毗沙天王祠,祠前井一日沸溢,武皇因持酒而奠曰:‘予有尊主济民之志,无何井溢,故未察其祸福,惟天王若有神奇,可与仆交卮谈。’奠酒未已,有神人被金甲持戈,隐然出于壁间,见者大惊走,惟武皇从容而退,由是益自负。”
[45]据《佛祖统纪》《释氏稽古略》:慧才俗姓王,浙江永嘉乐清人,宋真宗祥符初年(1008)获准剃度,年十三受具足戒,往四明山追随法智大师。因愚痴迟钝常持诵《大悲咒》,一夜忽梦身长数丈之清净僧人脱袈裟覆于其身,次日豁然开悟,所闻佛法,一时洞彻。后从慈云遵式大师,日夜精勤。宋英宗治平初年(1064),居于法慧宝阁,赐号“广慈”。不久隐退雷峰塔下,日诵《大悲咒》一百零八遍,又曾诵阿弥陀佛圣号翘足仰望一昼夜。一晚梦达极乐世界七宝楼阁清净宫殿,方知净土中品是其阶位。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春,为僧俗二众千人授菩萨大戒于雷峰塔,净慈守一禅师特作《受戒放光记》。元丰六年(1083)五月二十一日坐化,时年八十六岁。
[46]严耀中《试论汉传密教与天台宗的结合》,《汉传密教》第 69、67、77页。严著《汉传密教》一书另有《宋代的密教高潮》一章缕述此题,罗列多方证据,亦可一并合观。
[47]《中国密教史》,第 365~366 页。
[48]黑水城文献中亦发现有密宗文献,如ф221 + ф228 + ф266R《大乘入藏录》卷上;ф221 + ф228 + ф226V:1.八种粗重犯堕;2.常所作仪轨八种不恭;3.大乘秘密启发;4.咒惜财不布施者诗偈并画。参府宪展《敦煌文献辨疑录》,载《敦煌研究》1996 年第二期。
[49]白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宋代文献》,辑入《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人民出版社(北京)2003 年 9 月,第 398 页。
[50]《文物天地》杂志(北京)2004 年第二期 89 页。
[51]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序品第一》。
[52]北凉法众等译《大方等陀罗尼经》卷三。
[53]今泰山犹立有关帝庙一所,2003 年 1 月笔者应泰山风景区管委会李传旺主任之邀,由管委会张用衡先生陪同特意前往考察。据介绍,关帝庙位于泰山南麓,自此登山始有盘道。庙踞盘道西侧,原名关帝祠,又称山西会馆。相传山西商客建祠祀关羽,创建年代无考,明清拓修而成。建筑群分为东南、东北、西南三组。第一组由影壁、南山门(戏楼)、戏台、配殿、拜棚、正殿等组成,为祭祀区;第二组由东门、憩厅、东厢房、过厅、西厢房组成,为祭祀休息区;第三组原称山西会馆,
占整个建筑群的二分之一,大部分已改造,今存南山门、正殿和左右配殿,现为国家文物局培训中心。整个建筑规模宏敞,筑构精美,均饰彩绘交清式墨线小点金和墨线大点金。三组建筑年代各异。第一组较早,清初又建第二、三组。1983 年重修。
[54]辑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卷五,第 586 页。
[55]雍正《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六,第 41 页。
[56]原文载冯俊杰主编《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中华书局 2002 年 1 月出版,第 16 ~ 25 页,惟错讹漏失甚多,难以卒读。复查得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辑录乾隆《山西通志》卷二百〇一《艺文》亦载节本,题目作《汉寿亭侯庙记》,后蒙山西友人张小别、景晓雄提供碑拓及摄影照片,校定此文。
[57]《涑水记闻》,中华书局校点本,第 258 页。
[58]又《邵氏闻见录》卷八,亦以狄青、郭逵、杨遂、苗授“四人者,其功业、智勇、贫贱、遇合略相似,故并书之。”
[59]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五九。
[60]可参郭汝瑰《中国军事史》第三卷第五章第二节《(宋代)兵源及兵役制度》,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 327~33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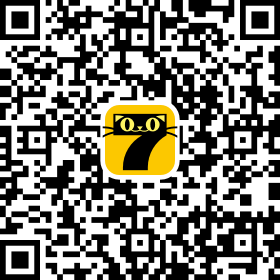 下载七猫免费小说APP
下载七猫免费小说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