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 牛天高遍撒大团结 羊绍银吊死包产田
- 书名:
- 朱马牛羊7
- 作者:
- 王和国、杨重华
- 本章字数:
- 11005
- 更新时间:
- 2024-04-30 11:58:51
众人簇拥着矮子幺爷一家,吹吹打打,向村公所走。一到村公所地坝边,又一连串的鞭炮炸响了。村会计朱正明问:“先在村公所坐一会儿吗?”
“这里?——村公所?咋会是这样子?不是好大一座——走马转阁楼房子吗?”
牛天才和牛羊氏的脸,一下子阴了下来。苦笑。矮子幺爷接过大儿子的话,“莫提这本经了。文化革命。你格老子倒跑球了。我们这葫芦尾河,遭那个马礼堂他们些狗日的,收拾惨了!这里那座房子,烧球了。还有,你五爷那儿子,牛天红,修公路,神螺山放炮,爆死球了——”
牛天高早已经知道母亲和弟弟的身世,无意中提到这个话题,很后悔。忙说:“就不进屋里坐了。”他回过身,向一直紧跟着他的那位姑娘单秘书,做了个手势。单秘书立即上前一步,打开提包,取出一捆“大团结”,递给牛天高。
村公所地坝里,立即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全都一下子集中在了那一大捆“大团结”上。
只见牛天高笑眯眯地举着那钱,轻轻撕掉拦腰捆钱的牛皮纸。——接下来的动作,就太让所有在场的人惊讶了。牛天高大声说:“这么多年没落屋了,这回儿,又走得急,没给大家买礼物,小意思,小意思,拿着拿着——”他从身边起,见人就发。
人们本能地一退,像是不相信牛天高这钱真是给自己的。都下意识地推辞:“要不得,要不得!你太客气了!要不得——”当看到前面的人真拿在手上了,而且牛天高那样儿真的是在“向大家表示心意”,后面的人,全都在裤腿、衣角上擦手,然后举双手,接下那见人就有一张的“大团结”!
一捆钱发完了,单秘书又递上来一捆……
眼下,葫芦尾河春节,至亲的亲戚,“打发”前来拜年的娃儿,给喜钱,多是一角,大方的两角。经济最活络的,也没人会超过五角。牛天高不分老的少的包括女人怀抱里还在吃奶的,出手就是每人十块!这太令人震撼了!
看儿子举着一捆大团结,见人就发,矮子幺爷和牛羊氏一时都惊呆了。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看两个儿子都满面春风高高兴兴的,估计是他们商量好了的。拿了钱的人都要过来谢声矮子幺爷和牛羊氏。牛羊氏也就顺势对他们说,“这些年啊,全靠大家帮衬哟——娃儿点小意思嘟嘛,莫那么客气哟——”
村里转了一圈儿。牛天高感慨良多。离开家乡这么多年,山河依旧。唯一的变化,就是长辈们更加苍老了。不通公路不通电。全村就一个小卖部。供销社代销员“水糖罐儿”两口子“撤离”后,骟匠朱发青瞅准这个空隙,开了个小卖部。为了让他驼背儿子朱光贵顶替自己的工作,朱发青提前办了病休,回葫芦尾河后,不想再干本行了,自己有退休费,就开小卖部卖百货,能赚点小钱,过得很滋润。现在的村公所、红豆林小学校,都是因为要欢迎牛天高“衣锦还乡”,才盖上瓦顶、换了木头桌凳,来证明家乡有变化。可墙还是土墙。没有任何现代设施,没有任何公众娱乐。多数人家的神龛上,伟大领袖和英明领袖也早已换了“天地君亲师位”。少数懒散的人家,神龛烟熏火燎,早已看不清原图。几大院子墙壁上,那些历次运动陆续写上去的红油漆、石灰水、墨汁的标语、口号,而今已经全成了黑色。作为后人,“先富起来”了。亲临父母亲的生存环境,牛天高多少有些内疚。
自己家人在一起,牛天高把早就准备好的一叠叠百元大钞,送给大伯大妈。意外的是,牛老大却坚决不收:“你拿这么多钱,我要起来,干啥子?这葫芦尾河,乡旮旯里,除了称盐打油,只要不生疮害病,拿着这钱,有球的个用头哇?”一旁的矮子幺爷,脸上挂不住,生气了。心里叽咕:“前次三姑姑补习读书没钱,我们打不出主意,你当伯伯立即站出来,把面子给我们撑起!那人情,我们两口子一直欠起的。今天,我儿子回来,送你几个钱,就算还你个人情嘛——你就做起那个样子,不要,不给脸,看不起么?”朱光兰心细,看矮子幺爷脸垮下来了,明白他的心思,赶快拉着牛羊氏的手,一把接过牛天高手中的钞票:“哎呀,我大侄儿孝敬的,凭啥子不要嘛。你大伯他,装得像多革命的样儿。狗屁!——儿子女儿给的钱,他一天数三遍。”
一句话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
钱耀梅让单秘书请示牛天高:建筑队“大名单”敲定之后,要不要牛总亲自对上了名单的人员,目测筛选过?还要不要召集大家,开个会什么的?牛总指示:带残疾的,有病的,就不要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了,其他人,都欢迎嘛。这不是去享福,是大家共同艰苦创业呢!
有了大儿子这句话,矮子幺爷和牛羊氏心里有底了。那些上了名单的人,生怕有变——想想吧,进了这建筑队,只要自己不偷奸耍滑,努力干活,就保证能吃饱肚子,还能够挣到现钱——这简直就是观音菩萨降世人间了。牛天高回家这几天,矮子幺爷的磨房,几乎是川流不息的人啊。都提着家里自认拿得出手的好东西,往矮子幺爷的磨房里送。都希望矮子幺爷或牛羊氏,“别忘了帮我家娃儿说句话哟。到了你家的工地上——嗨呀,随便喊他做啥子,都要得。不听话,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有口饭吃,还有几个零花钱,就是万福勒!”矮子幺爷和牛羊氏都是菩萨一样的心肠,“乡里乡亲,谁跟谁呢!——没问题,没问题,包了包了。”除了明知文革中落了残疾的羊绍银、羊绍铜之外,其余的,他们都满口答应:“要得要得,只要你屋头走得开——”
牛天才拜托二傻,到罗汉寺,请他哥长道子测了字,建筑队取名儿:“福禄威建筑工程队”——“福禄威”暗合“葫芦尾”。还算了一卦。清明过后的第三天,就是黄道吉日。上百人的队伍,背包捞伞。浩浩荡荡,喜气洋洋。乡政府包了四条船。县政府支援六辆卡车。多数人,第一次出远门,晕了船又晕车,吐得一塌糊涂——大煞风景。
“福禄威建筑工程队”全班人马,被直接运到葫芦口河市天高公司目前在建的建筑工地——由牛总他老丈人胡晋翎和婆娘胡洛萍父女两个“胡工”监督,“带岗培训”。 工地上,几乎都是体力活。力气好,人勤快,能吃苦,就是好样的。和“老工人”一吹牛,“待遇”很快就清楚了:一日三餐,保证吃饱,中午、晚上两餐,有肉食;住宿,睡大屋子,暖和。小灾小病自己负责。大灾大病,公司会适当帮助。——工钱计件制,按工程结算。平时,按月借款。实行“保底工资”。每人每天的收入,不会低于三块钱。
“嚯呀,如果是满勤,九十块了呢!这就等于,每个月都能搞整出大半条肥猪了呢!”这还只是保底——这账谁都会算。都说“整住了的!”
“福禄威建筑工程队”到达葫芦口河。第二天,《葫芦日报》用了一个整版,宣传新的“葫芦尾河经验”。通栏大标题是:《转变观念谋发展,劳务输出闯新路》。社评《榜样的力量》说:“近年来,在的农村政策指引下,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伴随着农业机械化以及现代农业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多。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做大做强农村劳务输出产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组织地转移就业,既是农民实现脱贫致富的有力之作,更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之举。面对这个具有时代挑战意义的重大改革难题,葫芦肚河县葫芦底河乡的葫芦尾河村,在先富起来的年轻村长,万元户牛天才,和他的明星企业家哥哥牛天高的带领下,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敢为人先,组建了我市第一支农民建筑工程队。在有组织的劳务输出这条大道上,走在了全市前面,树立了一个很值得我市各地农村借鉴学习的榜样……”
牛天高、牛天才兄弟俩的大照片,双双上了报纸。葫芦尾河村 “劳务输出”,“组织富余劳力外出打工”这颗卫星,放得并不比——“万斤粮”、“钢这个东西”、“包产到户”——任何一颗卫星小多少。
当年朱正才从外边带回来一支队伍,开辟了一个“翻身”的新时代。今天,“牛老板”“牛百万”,从村里带出去一支队伍,开辟了一个“发财”的新时代。报纸社评里说,“从此,葫芦尾河人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进了建筑队的人,都感激矮子幺爷家的“捡宝儿”。进城之后,才发觉,这世上,竟然还有这么神奇、这么好耍、这么安逸的地方。那街、那房、那车、那人——那穿戴、那步伐、那姿势,那腔调,那男人、女人身上的骚味儿——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令人震撼、令人神往!和老师傅们打过交代,才知道,无论冬热,在长裤子里面,还应该要穿条“豁腰裤儿”。把前羞后丑,都“兜住”,那叫“内裤”。操腰裤子再不能穿了。这种裤子拴的裤腰带儿。一用力,断了咋办?不丑死个人啦?太不保险。进城了,就该穿“西式”裤儿,就是裤腰有袢袢,拴皮带那种。工地上不能打赤脚,伤脚。穿鞋,就应当穿袜子。——城里女人那奶子看不到“米米(乳头)”,那是用“乳罩”把奶奶笼起来。——依然不解。到女人用品商店一看,哦——啥玩意儿,好稀奇呀?那样式,和乡下“笼子猪儿”嘴上的“笼子”,差球不多。不过,罩乳,棉的,罩猪儿嘴巴那种,竹编的。安逸,一定给婆娘买个回去,免得婆娘那奶成天甩过去甩过来的。
建筑队大锅大灶大碗,睡大屋。除了每个人枕头下面的衣服裤子,碗筷、洗漱工具,其他一切,都是“打官的(集体)”或者“老板儿的”。几乎每个人都不声不响地在裤子的内里胯间部位,缝上个小口袋,用来装钱。哪怕是一分、一角,也得收藏好,积攒起来。只有藏在这个小兜儿里,才踏实、保险。任何时候,一摸:卵子在,钱就在。睡觉前,还拿出来,躲在被窝里数数!白天的活,很苦很累,每月却能“借支”好几张“大团结”!天啦,“大团结”!捏在手里,比挑谷子进仓,牵猪儿上街,捡鸡蛋进篮子的感觉,好到天上去了。
寄钱回家——把钱送进邮局、拿给陌生人?——不放心。呕心沥血,省吃俭用挣来的钱,必须亲自拿回家。葫芦口河太远,逢年过节,才能回家。一,老人、婆娘娃儿团聚;二,送钱。后来一段儿,工地转移到葫芦肚河县城,就忍不住了。收了工,车、船早没有了。走几十里山路,赶回家。夜饭吃过了,娃儿们睡了。这才把钱,从胯间的小兜儿里拿出来,厚厚一卷儿,交到婆娘手里。婆娘高兴啊,抱着男人要亲热。两口子就开始折腾啊。——告一段落的时候,婆娘枕头边拿过那卷儿钱来,拉直,理伸展,数了又数。仍然卷回一卷。用纸包了。再用手帕包了。放进布袋子里,系紧。藏在柜子的最底层。婆娘再回到床上——男人已经呼呼大睡。他太累了。明天一早,还要赶回工地干活呢!——泪花在婆娘的眼中打转。挑亮灯光,听不够那匀匀的呼吸声,看不够那黑里透红的脸庞。夜深了,还想拿出钱来数一遍。金钱的传递,抹去了男人不在身边这些日子的思恋和忧伤……幻想着男人在城里的日子。肯定比在葫芦尾河家里,好多了。累是累,点电灯,乘汽车,看电视,安逸呢!
——留守农民心中,“进城打工”,简直就等于参加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两口子召开的蟠桃会,享受的是神仙待遇,过的天堂日子。
牛天高给建筑队人员立的标准是:没病,没残疾,力气好,人勤快,家里走得开。其中“没残疾”一条,本来不言而喻,是牛天才征得哥哥同意后,专门加进去的。一听就知道“有所指”。其实,牛天才这一招,多余。羊登亮一家,根本就没报名,也没想过进“牛天才家的那个建筑队”。那次周也巡带人,来宣布牛天才“代理村长”。当天夜里,羊登亮就喊着全家人,开了个家庭会,特别告诫儿子羊绍铜、孙子羊长文,侄儿羊绍银和侄孙羊长武,说是“我们这一家人,和气包卵羊登山那一篼子,虽然也是一个总老疙蔸发下来的,但几世的冤仇,一天两天,是解不了的。当年,牛天才他老汉儿羊绍雄,遭乡亲们吊在红豆树上打,就是我的老汉儿你们的爷爷祖祖放的信,团的人,动的手。这叫‘带死人过’,懂不懂?我们家的老房子,就是牛天才他老汉儿,放火烧了的!清匪反霸,狗日的狗子三‘挨了炮’的。而今,他那婆娘红樱桃就是牛羊氏——占着朱正才白鹏他们的势,儿子当村长了。——风水轮流转呢!你们都要给我记住:俗话说,你当三年官,老子三年不做贼,敢把我卵子咬了?关键就是,你自己做不做得到‘三年不做贼’啊!告诉你们,从古至今,如果仇家占官府,随便哪个,一旦落在他们手里——哼!不死,也得脱层皮!”
蛇有蛇道鼠有鼠道。羊登亮也不是没闯过江湖的人。村里的建筑队,前脚一走,羊登亮就拜托家住临葫县城边上的姨侄儿,在那边县城里,找到一份儿帮养猪场收泔水的苦力活。带着儿子羊绍铜,侄孙羊长武,三代人三个人,也出门“打工”,挣现钱去了。
城里留给农村人的“机遇”,实在太多了。一方面,改革开放,一些人先富起来。时下许多城里人已经不需要工作了;另一方面,城里的好多工作,眼下的城里人“打死也不愿干”!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正好!只要你给钱,我伺候你。不就是累点儿、苦点儿、脏点儿吗?这算个球哇?——累莫过于搞“大炼钢铁”,苦莫过于熬“三年灾害”,臭莫过于埋“武斗腐尸”——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这三样更加累、苦、脏的活?
城市就是一个硕大无比的胃,无论多么顽固的东西,一旦吞噬进去,很快就会被磨碎、溶解、消化、吸收。傻头傻脑的农民,就像鳄鱼嘴边戏水的小鱼儿,甘心情愿地作了城市的营养品。葫芦尾河进城的人,很快发现,即使最下层的城里人,那日子、那生活,拿到葫芦尾河村去,也算是人上人了。慢慢地,有人更进一步发现:这世上,还有更适合于自己这种人干的事业。于是,尴尴尬尬地,离开了建筑队,自己去独立门户,“赚大钱”。朱、马、牛、羊,都有人自己做起小买卖来。本钱不分大小,只要成了“周吴郑王”的“老板”,就行。三个人,一架板车,四个粪桶,也请人取个名儿:“葫芦环卫清洁有限公司”。还印一张名片:“羊经理”。
外出的人回家探亲,看到留在家乡的人,总有一种憋气、掉价的感觉。慢慢地,就“看不顺眼”了。时间一长,甚至开始有人不屑和那些仍在家乡,脸朝黄土背朝天,累死累活的农民兄弟们,走在一起了。“愚昧呀!”你一年到头累,能挣几张“大团结”呢?还不如我在城里掏一个月大粪。窝在这四面通风的烂茅草房子里,瞧你这出息!——说的是实话。
羊登亮六十几了,身子硬朗。一辆架架车,一个七尺长,两人合抱粗的木头卧式泔水桶。早晨,天一开亮口,祖孙三人,就拉着泔水桶满城吆喝:“收——泔(臊)——水——了喔!”不带孙子羊长文而带侄孙羊长武,是看羊长文这娃娃和镇上杀猪匠张世元好,看猪、买猪;杀猪、卖肉。都能上手。家里就疯儿洞、胡鸾香和熊桂花“守棚棚儿”“种庄稼”“看鸡鸭”。留个男娃儿离家近点儿,也好。
很快,村里的青壮年男劳力,几乎走光了。常年留在村里很少外出的,弯着指头就能数清:一个村长牛天才;一个会计朱正明;一个昔日的“狗崽子”,而今的县长他幺弟马白三;还有 “红苕人”马白俊;“半残废”疯儿洞羊绍银。村长、会计跑了?成何体统?其余几个,马白三不敢走——父亲马德齐、岳父羊颈子,还有哥哥白鹏嫂子朱正英,都严令马白三两口子,带好双胞胎马羊和羊马。疯儿洞不能走——肋骨上有钢筋,重活干不了,轻活不挣钱。亲叔叔外出打工,宁可带他刚满十七岁的儿子,也不愿带他走。——唯独只有“红苕人”马白俊“骚棒”,不愿意走!
老婆病死后,马白俊“逍遥自在”十来年了。饱一顿饿一顿,“不关事。”就图个“自在”“好耍”。“帮人打工?那不是又受剥削受压迫吗?他牛屎高又咋子嘛?资本家嘟嘛!哼,想让老子‘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门都没得!老子们贫下中农——”
能进城的进城了,不愿进城的,四面八方做上门手艺,“挖野斋”。村里的农活,全靠一帮妇孺老弱。农闲时候的田间管理,还能勉强支撑,到了农忙季节,特别是“双抢”时节,完全靠这些人,就太过艰难了。
农活若要论技术,使牛匠坐头把交椅,当之无愧。葫芦河流域,主产水稻。主要耕种面积是水田。常识,水田并非全部四季关水。正冲“水道”里的水田,旱涝保收。那叫“冬水田”。其余,浜上、山腰那些田。打完谷子收完大春,当年,就不再关水。这时候的田,叫“干田”。犁过来,寒露前,种一季麦子胡豆油菜——“小春”。犁干田讲究底平、道顺、能“利水”,作物不至于“坐蔸”、涝死。到第二年立夏前后,就进入“双抢”了——抢收小春作物,抢栽水稻。收完小春那田,关水就全靠老天爷“发雨”了。那雨,多是说来就来。来时雷鸣电闪,大雨滂沱,扯天扯地,干田都澎淹四海。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半天,雨过天晴,太阳又会晒得人皮爆。这“抢水”犁干田,揉田边,必须在雨停、田里水满的时候完成。慢了半拍,可能今年就再也没戏了!不仅时间分秒必争,而且犁来还不能漏水。二杆子农民,“牛上岸,田水干。”伪政府时候,到发财人家里“帮人”,万一“大意失荆州”,出了犁干田漏水这种洋相,工钱莫得、吃喝莫得,还要挨东家——轻则咒骂,重则拳脚相加!怎说呢?人家的一份良田,一年的主要收成,这关键的一买卖,全被你搞黄了哟!
集体时候,特别是“大寨式”年代,同样是出工,使牛匠每天都会多得几个工分。懂行的,口服心服。也有那种农活不精,自不量力,不虚火势的,自告奋勇,要当使牛匠,拿高工分。好吧,请,手上过。结果,多是为争几个工分,真还把田水犁漏了。——你算惹大祸了。须知,无论什么田,灌水泡软浸透之后,水漏了,就成了“夹板田”。一是田水再难“装起”,二是栽下的秧子,必然“箍蔸”,整块田就等于半荒废了。——你认为使牛匠那么好当?扣工分,罚款,事小。惹毛了,扣你一顶“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大帽儿,游乡示众。那就倒血霉,丢祖宗八代的脸了。
而今,包产到户,“各人的娃儿各人抱”。“使牛匠”立即成了金宝贝。农忙季节,从早到晚,都有人好酒好菜还出“劳务费”——“请”。麻烦在于,人家犁不犁你家那块田,喝不喝你桌上那杯酒,收不收你那皱巴巴的几块钱,还得看人家高兴不高兴!
葫芦尾河最权威的使牛匠羊登贵老了。儿子麻糖上街当了脱产干部,衣食无忧。要老太爷再“帮人”?免谈。牛道耕也老了。他家只留了点菜蔬地,农忙时节,最大限度帮矮子幺爷家犁两天,过把瘾儿,再没心劲帮别人。马德寿、朱光寿、牛道松、牛道荣这一帮“老农”,也“靠不实”。高兴了,请得动,不高兴,“哎呀。这两天我人不大舒服。”推了。——没办法,外出打工的人,只好匆匆忙忙回家,忙上几天。该收的收进屋,该栽的栽下田。也有正好工地上也赶活,忙,实在回来不了的,就给钱,让家里 “请人”——都知道,犁田技术勉强过关,又能随请随到的,全村而今只有“红苕人”马白俊“马骚棒”了。
马白俊父母早死。爷爷奶奶把他带大。早年,马先生马德高牛道梅夫妇在世,对他多有照看。马家人帮助下,他结过婚。老婆还没来得及为他生下小孩,居然一病不起,死了。于是,又请媒,说了好几个,姑娘、寡妇都有,总不成。最长的,在他家住三五几个月,整死也不回来了。后来,婆娘家之间在传说,这马白俊,简直天性畜生,“脚牛(公牛)”一条。据说只要床上有女人,一上床,他就会抱着不丢手,手脚都要来,想着法儿变着花样儿,极尽蹂躏折磨之能事。最可恶的,是女人的那几天,他也要强迫同房,还必须尽兴。不从,则拳脚相加,乃至捆绑强奸!狗日的“骚棒”——再没女人敢进他家门,更别说嫁给他了。他气力大,爱帮忙,吃顿饱饭就行。平时爱说骚话开“荤玩笑”,即使挨了臭骂,他也不生气,笑扯扯地望着,还挤眉弄眼。
知道自己名声不好,女人看不起他,着急也没用。干脆不急了。大集体时候,他犁田,有人亲眼看见他爬母牛背,去饲养场,搞整母猪——丧祖宗的德——下流啊!牛道耕听说,虽然恨得牙痒,却还拿他没法。眼下,“包产到户”,加之男劳力大多外出“打工挣钱”,马白俊那把力气和犁田技术,一下子就成了香馍馍。周围通公路的杨柳滩、望岭村、湾滩,请他“帮忙”还要排队。犁田、栽秧、打谷子,只要是下蛮力的,干啥子都行。有些家男人不在,婆娘半老不老,老人不管事,娃儿还小。他就说不在乎给不给钱,给多少钱。不在乎吃喝,只在乎“把你家那些大田犁完了,未必不让我搞整一下你那小田啦?”
正经女人以为他开骚玩笑,一笑了之。可是,吃过夜饭,当着一家人的面,把账结清,走了。——更深人静,女人发觉有人轻轻敲墙壁。悄声告诉你,他的汗帕子在桌环子上忘拿了,你开开门吧——才知道遇到癞皮狗了!也有——那些风骚的女人——才巴不得呢。“谁怕谁”?背着老人娃儿的眼睛,田边地头的竹林、树林里,双双干得神魂颠倒,脚趴手软。划算,干过这事,还好意思要工钱?——就省了。“马骚棒”干上瘾了,好些时候干脆不和人家说钱,田地里的活路和女人肚皮上的活路,都干得把心把肝的。
今年开春稍微有点儿旱。小春粮食熟得快。立夏刚过,羊登亮三爷子,就齐刷刷地赶回来,收粮食、准备“整干田”。收他们泔水的养猪场老板儿,也是乡下人。知道农时耽误不得,说好了,同意他们“最多耽误七八天”。
收完粮食,老天爷天天红花大太阳,根本就没有下雨的意思。公社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多是边看老天爷脸色,边做最坏打算——神螺山撇泉水进田,或者葫芦河里车水。
将神螺山上的那股泉水引过来,玉扇坝那一坝田,基本都能把秧子栽插下去。问题是,要盼望这股水,灌溉了玉扇坝,再从马家湾、毛狗湾、仙鹤岭一路干田,过到朱家浜一带的田地来,又还不是“添水”而是“整田”,就几乎不可能了。至于车水,眼下就不敢指望了。而今,除了沿河单架水车可车水进田的地段之外,其余地方,早已不谈“车水”二字了。真要把水车上朱家浜,十来架水车,鲢鱼咬尾排开。这还不说,水还要从一二十块田过路。包产到户了,“车水?你们车吧,浜上我的那块田,我没打算栽秧呢。”气死你。
听天由命吧。羊登亮在家里又守了几天,白天黑夜,都在抬头看天,眼巴巴望着,“行行好,赶快下雨吧。”已经第八天了,老天爷不乖,还是不下雨。看样子,这两家人的干田,就摆起了。
这一大家子,犁田技术过关的,就羊登亮。羊绍铜脚带残疾。疯儿洞肋骨上有钢筋,不能太过用力。羊长文勉强能犁冬水田,“整干田”没把握。羊长武今年刚满十七岁。 疯儿洞“坏分子”摘帽儿之后才结婚。快四十了,才生了这个儿子。属于文化莫得,农活不会那种“红小兵”。羊登亮想让羊绍铜先带侄儿回临葫县城,把收泔水那头“稳住”。转念一想,儿子那脚,本来就使不得大力,万一又整伤了咋办?“两害相权取其轻”。算了!——只好给疯儿洞胡鸾香两口子和儿媳妇熊桂花打招呼。“下了雨,就喊马白俊,先揉边,把水关起,羊长文你就学着,把田犁出来。耙平,再请几个人,帮着栽秧。两三天就完事了。”
羊登亮走后的第四天。葫芦肚河全县普降大到暴雨。雨是半下午落起来的。到“擦黑(黄昏)”时候,葫芦尾河所有田块,都封箱漫埂了,这是一场及时雨。
疯儿洞安排弟媳熊桂花,“你爹说的,请马白俊帮忙揉边。看你和你嫂子,哪个去跑一趟——还不晓得马白俊他狗日的,在不在家呢。先打个招呼,排个轮子。不然,外村人来,把他喊起走了,就麻烦了。”疯儿洞和马白俊是“拐的”,他知道,自己出面去请,马白俊多半不会买账。想支着熊桂花走一趟。
熊桂花讨厌马白俊。虽是石板大路,黑天黑地,不愿去。将就羊绍银的话,顺口对胡鸾香道,“嫂子,你去跑一趟嘛。下雨了,今晚上,文娃子说不定要从镇上回来呢。”意思是她还要给儿子准备夜饭。
胡鸾香不好推辞,“好嘛好嘛,我去我去。——就怕他狗日的不在家。”一边说,一边解下围腰,拍拍头上肩上的灰尘,顺手拿起根打狗的竹棍。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天黑净了。没见羊长文回家。
羊绍银阶沿上坐了好一阵,没见胡鸾香回来。就进屋点灯。就着油灯,抽了两杆叶子烟,还不见婆娘的人影子。出门,向葫芦尾河方向马家院子望过去。初夏雨后洁净的夜空,星光灿烂。被大雨洗得干干净净的石板路,隐隐约约,泛着白光。猛然间,一个念头在羊绍银脑海里闪过,他顿时有点儿慌乱起来——未必然,他狗日的马白俊“马骚棒”,敢打我疯儿洞老婆的歪主意?大院子人户,敢动手动脚?不会——吧?他找死!疯儿洞只觉得胸口一紧,头皮发麻。对熊桂花说,“把你家手电筒,拿给我用一下。我去接你嫂子。我的电筒没电了。”熊桂花拿出手电筒,还好,有点儿电。红杏杏的,有点亮。
刚走到地坝边,隐隐看见石板路上有个人影,喊道:“回来了?他来不来嘛。”
果然是胡鸾香。火渣渣地边说边骂:“嗨呀,他狗日的,十六两秤不要砣,翘起了。傲得很咯。我在院子外边喊半天,他听不见。进院子里找到他,才晓得,都有三拨人请过他了。罗玉儿跑最前面。他已经答应下来,明天一早,给羊绍青家揉边。然后,是羊绍宝家,马白贞家。——说了,实在搞不赢,我们两家,就要排到后面去了。唉,到那时候,恐怕田里的水早漏光了!不过,他还是留了话的,说是——如果还是要坚持请他,叫我明天去回他的话。”
“我晓得,这个狗日的想咋子——”后半句羊绍银没有说出来。他咬咬牙,“我不信,真的‘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事到如今。疯儿洞只好硬着头皮,麻着胆子,自己干了。——虽然没把握。但也没有别的办法。
第二天,两家人三个人,都起了个大早。吃过早饭,就兴致勃勃到朱家浜“整干田”。疯儿洞平生第一次独自牵牛,架犁,“揉田边”。胡鸾香、熊桂花,铲田壁,勾田埂。
黄昏时候,浜上的干田,田边揉完,田埂勾好。
停了犁。下了牛。站上田埂,看满田里黄澄澄红莹莹的泥水,羊绍银就像隐约看到了一挑挑黄谷,一担担白米。自豪感油然而生。对正在田缺边洗脚的胡鸾香说:“日妈的,拿给他几爷子,越说越神!不就是揉个田边,勾个田埂嘛,好稀奇呀?”转身,又对弟媳熊桂花说:“——这几块田,明天一早,我就来驾牛。顶多,喊长文也回来,帮一天。我们三个,加长文一个,四个人。后天,就能把秧子栽下去了。”
熊桂花也高兴。边擦手上的泥水,边笑盈盈地说:“那也要得。——他大伯,我晓得,你是第一回揉边关水,辛苦你,累了。待会儿,我炒两个菜。你兄弟那里,还藏得有一瓶葫芦二曲酒。今晚上我和嫂子陪你,喝二两!”
夜饭时候,一个男人,两个女人,都能喝酒。很快,酒瓶就底朝天了。劳作一天,虽然疲倦不堪。但也还多有成就感,欢天喜地的。
刚下了雨,初夏的早晨。分外凉爽。万里无云。远山近岭,都笼着薄薄的雾。那乳白色的雾气,贴着大地,慢慢浮动,飘逸。低低地,缓缓地和农家晨炊的烟,相互渗透,融合。像瀑布一样,向着葫芦河的河面,漫过去。
牛天才懒。但到底大院子,众目睽睽。而今,黄袍加身,当了村长。农忙季节,面子活路总得做起走。再说,这几天大伯牛道耕在帮他。农忙时节,大伯多是老早就堂屋阶沿上一站,半开玩笑半认真,骂道:“你些狗日的,一个二个懒得烧蛇吃——太阳晒屁股了!”他才不管你是啥子鸡巴村长呢。市长朱正才县长白鹏也怕他七分,虚你牛天才?麻姑勤快人,天天早起。心痛老公,多不忍心过早叫醒他。看大伯披衣出仓屋门槛了,这才三脚两步,进屋推醒牛天才:“还不快些——大伯都起来了。要遭骂!”
大忙季节。布谷鸟也赶早。兴致勃勃飞来,沿着葫芦河,一路欢叫,安排农活。“快收快割——快收快割”。
牛天才醒来。浑身酸痛。昨天勾了一整下午的田埂。虽然睡了一晚,但十根指头,还是硬翘翘的。掀开被子,刚要坐起来。“咚、咚、咚——”脚步声。麻姑急匆匆地门外就喊起来:
“快些!天才——出大事了!”
“咋子嘛。棒老二来了?”
“疯儿洞吊死球了!朱家浜。朱会计朱正明在喊啦——你快起来。”
“啥子呀?”牛天才翻身起床,“日疯颠倒的。无缘无故,吊死球了?遇到鬼了?”
牛天才出门。牛家大院得到这惊人消息的,都在呼朋邀伴,往朱家浜方向跑。
“是不是哟?这种玩笑开不得哟!”
“嗨呀,你听嘛。那边——都闹惊林了!”
“把个使牛匠羊登贵差点儿吓死!——就是他老人家,最先看到的。早晨,麻麻匝匝。田埂桐子树上,像是吊着个啥子,走拢一看,是个人。吓得羊登贵丢了犁头转身就跑——”
“啥子想不开嘛。日妈当坏分子,那么造孽,都过来了。”
“他那儿子羊长武,前几天看见还在屋里呢!未必,两爷子有啥子过节?”麻姑揣测。
“球扯,疯儿洞这种人。——死要面子活受罪。”
离朱家浜老远,牛天才就听到胡鸾香惊抓抓的哭喊声:“你狗日的死鬼呀——”
已经读完最后一章啦!
90%的人强烈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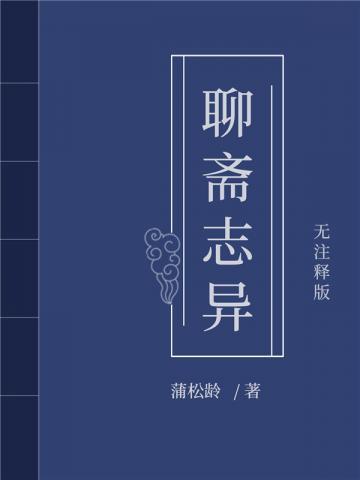
聊斋志异
卷一 □ 考城隍
- 书名:
- 聊斋志异
- 作者:
- 蒲松龄
- 本章字数:
- 587
宋公讳焘,邑庠生。一日,病卧,见吏人持牒,牵白颠马来,云:“请赴试。”公言:“文宗未临,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病乘马从去,路甚生疏。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时入府廨,宫室壮丽。上坐十余官,都不知何人,惟关壮缪可识。檐下设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与连肩。几上各有笔札。俄题纸飞下。视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无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诸神传赞不已。召公上,谕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称其职。”公方悟,顿首泣曰:“辱膺宠命,何敢多辞?但老母七旬,奉养无人,请得终其天年,惟听录用。”上一帝王像者,即命稽母寿籍。有长须吏,捧册翻阅一过,白:“有阳算九年。”共踌躇间,关帝曰:“不妨令张生摄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谓公:“应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给假九年。及期当复相召。”又勉励秀才数语。二公稽首并下。秀才握手,送诸郊野,自言长山张某。以诗赠别,都忘其词,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之句。公既骑,乃别而去。及抵里,豁若梦寤。时卒已三日,母闻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语。问之长山,果有张生,于是日死矣。后九年,母果卒,营葬既毕,浣濯入室而没。其岳家居城中西门里,忽见公镂膺朱幩,舆马甚众。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惊疑,不知其为神,奔询乡中,则已殁矣。公有自记小传,惜乱后无存,此其略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