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订戴
- 书名:
- 从宋明理学到阳明心学
- 作者:
- 吕思勉
- 本章字数:
- 3967
- 更新时间:
- 2023-11-27 11:58:58
戴东原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以攻宋儒。近人亟称之,谓其足救宋儒之失,而创一新哲学也。予谓戴氏之说,足正宋学末流之弊耳;至其攻宋学之言则多误。宋学末流之弊,亦有创始之人,有以召之者,戴氏又不足以知之也。宋学之弊,在于拘守古人之制度。制度不虚存,必有其所依之时与地。而各时各地,人心不同。行诸此时此地,而犁然有当于人心者,未必其行诸彼时彼地,而仍有当于人心也。欲求其有当于人心,则其制不可不改。是以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此犹夏葛而冬裘,其所行异,其所以求其当同也。宋之世,去古亦远矣,民情风俗,既大异于古矣,古代之制,安能行之而当于人心乎?宋儒不察,执古之制,以为天经地义,以为无论何时何地,此制皆当于理。略加改变,实与未改者等,而欲以施之当时。夫古之社会,其不平等固甚。宋时社会之等级,既不若古之严矣。在下者之尊其上,而自视以为不足与之并,并不若古之甚矣。宋儒执古之制而行之,遂使等级之焰复炽,与人心格不相入。戴氏之言曰:“今之治人者,视古圣贤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屑措诸意。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夫使尊者、长者、贵者,威权益增;而卑者、幼者、贱者,无以自处,是诚宋学之弊,势有所必至。由其尊古制、重等级,有以使之然也。(东原又谓:“今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曰理者。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辞者理屈。”此则由人类本有强弱之殊,理特其所借口耳。不能以此为提倡理者之罪也。)至于以理责天下之人,则非创宋学者之所为,而为宋学末流之失。戴氏又谓“理欲之说行,则谗说诬辞,得刻议君子而罪之,使君子无完行”。夫以宋儒克己之严,毫厘不容有歉,因推此绳君子而失之严,事诚有之。至于小人,则宋儒曷尝谓其欲可不遂,而不为之谋养生送死之道哉?横渠见饿殍,辄咨嗟,对案不食者经日。尝以为欲致太平,必正经界。欲与学者买田一方试之,未果而卒。程子提倡社会,朱子推行社会。凡宋儒,讲求农田、水利、赋役之法,勒有成书,欲行之当世者,盖数十百家。其志未尝行,其书亦不尽传,然其事不可诬也。乡曲陋儒,抱《性理大全》,侈然自谓已足;不复知世间有相生相养之道;徒欲以旷世之高节,责之人民,此乃宋学末流之失,安可以咎宋学乎?宋儒所谓理者,即天然至善之名,戴氏所谓必然之则也。戴氏称人之所能为者为“自然”,出于血气;其所当止者为“必然”,出于心知。与宋儒称人之所能为而不必当者为气质,为欲;所当善者为义理,为性,有以异乎?无以异乎?夫特异其名而已。戴氏则曰:“吾所谓欲者,出于血气;所谓理义者,出于心知。血气、心知,皆天之所以与我,是一本也。宋儒谓理出于天,附着凑泊于形体。形体者气质,适足为性之累。是二之也。”夫宋儒曷尝谓气质非出于天哉?谓“义理气质,同出于天,则气质不应为义理之累。宋儒谓气质为义理之累,是二之也。”然则戴氏所谓血气者,任其自然,遂不足为心知之累欤?谓任血气之自然,不足为心知之累,则戴氏所谓“耳目鼻口之欲,必以限制之命节之”之说,为不可通矣。谓性必限之以命;而声色臭味当然之则,必以心为之君;则宋儒之说,戴氏实未有以易之也。若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心知之自然能好懿德,犹耳目鼻口之自然能好声色臭味。以是见义理之具于吾心,与宋儒谓义理之性原于理,而理出于天者不同。”则宋儒固亦未尝不谓理具于吾心也,特本之于天耳。即戴氏谓义理之性天然具于吾之心知,而推厥由来,亦不能谓其不本之于天也。戴氏谓“饮食能为身之养者,以其所资以养之气,与所受之气同。问学之于德性亦然”是也。安得谓宋儒“更增一本”乎?
戴氏曰:“宋儒所谓理,即老氏所谓真宰,释氏所谓真空也。老释自私其身,欲使其身离形体而长存。乃就一身分为二,而以神识为本。推而上之,遂以神为有天地之本。以无形无迹者为有,而视有形有迹者为幻。宋儒以理当其无形无迹者,而以气当其形体。故曰心性之郛廓。”老氏、释氏是否自私其身?是否歧神与形而二之?今不暇及。宋儒之辟释氏也,曰:“释氏本心,吾儒本天。”其所谓理,与老释之所谓神识非同物,则彰彰明矣。宋儒盖病老释以万物为虚,独吾心所知见者为实,则一切皆无定理,猖狂妄行,无所不可,故欲以理正之。宋儒所谓理者,乃事物天然之则,即戴氏所谓“有物必有则”;而其所谓义理之性,则吾心之明,能得此天然之则者,即戴氏所谓“能知不易之则之神明”也。安得视为虚而无薄之物乎?
戴氏谓:“老释内其神而外形体。举凡血气之欲,悉起于有形体之后,而神至虚静,无欲无为。宋儒沿其说。故于民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甚轻。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故用之治人,则祸其人。夫人之生也,莫病于无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不仁也。不仁实始于欲遂其生之心。无此欲,必无不仁矣。然使无此欲,则于天下之人,生道穷促,亦将漠然视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无是情也。故欲不可无,节之而已。谓欲有邪正则可,以理为正,以欲为邪,则不可也。”此为戴氏主意所在,自比于孟子不得已而言者。吾闻朱子之言曰:“饮食,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则朱子所谓天理,亦即欲之出于正者。与戴氏谓“欲其物,理其则”同。未尝谓凡欲皆不当于理也。人之好生,乃其天然不自已之情。自有人类以来,未有能外之者也。世固有杀身以成仁,亦有以杀止杀者。彼以为不杀其身,不杀杀之可以止杀之人,则于生道为有害。其事虽出于杀,其心仍以求夫生也。自有人类以来,未有以死为可歆,生为可厌者。戴氏以为宋学者不欲遂其生为虑,可谓杞人忧天之队矣。若谓欲遂人之生者,先不能无自遂其生之心,则又有说。世无不肯舍其身而可以救人者。盖小我之与大我,其利害时有不同。于斯时也,而无舍己救人之心;亦如恒人,徒存一欲遂其生之念,则终必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顾。此成仁之所以必出于杀身;而行菩萨行者,所以必委身以饲饿虎也。彼行菩萨行者,宁不知论各当其分之义,固不当食肉以自养,亦不委身以饲虎哉?不有纯于仁之心,固无以行止于义之事。彼行止于义者,其心固纯于仁。所以止于义者,所能行之仁,止于如此;不如此,则转将成为不仁。故不得已而止于此,而非其心之遂尽于此也。心之量,适如其分而已;及其行之,未有能尽乎其分者,而戴氏所谓戕人之生以遂其生之祸作矣。故以纯乎理恒人,宋儒未尝有此;其有之,则宋学之末失也。至于以纯乎理自绳其身,则凡学问,未有不当如此者。抑天下之人,使皆进于高节则不能。诱掖天下之人,使同进于高节,则固讲学问者,所当同具之志愿。而非天下之人,真能同进于高节,天下亦决无真太平之望也。
戴氏谓“老释以其所谓真宰真空者为已足,故主去情欲勿害之,而不必问学以扩充之。宋儒之说,夫老释之说,故亦主静。以水之清喻性。以其受污浊喻气质。宋儒所谓气质,即老释所谓情欲也。水澄之清,故主静,而易其说为主敬存理”云云。主静之说,发自周子。其说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盖以人之所行,不越仁义。而二者名异而实同。义所以行仁,而仁则所以为义立之体。无义固无以行仁,无仁亦无所谓义。当仁而仁,正其所以为义;当义而义,亦所以全夫仁;所谓中也。止于中而不过,则所谓静也。何以能静,必有持守方焉,则程子所谓主敬也。主敬而事物至当不易之则(宋儒所谓理)存焉矣。宋儒所谓静,非寂然不动之谓也。戴氏之说,实属误会。
戴氏谓“宋儒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此亦宋学末流之生。若程朱,则“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两端固并重也。抑进学亦必心明而后能之,故反身自勘之学,终不能不稍重于内。戴氏曰:“圣人之言,无非使人求其至当,以见之行。求其至当,即先务于知也。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此说与程朱初无以异。又曰:“闻见不可不广,而务在能明于心。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知,则虽未学之事,岂足以穷其知哉?”此说亦与朱子一旦豁然贯通之说同。天下事物,穷之不可胜穷,论明与蔽者,终不得不反之于心也。然与戴氏力主事物在吾心之外,谓心知之资于事物以益其明,犹血气之资于饮食以益其养者,则未免自相矛盾矣。
戴氏谓“心之能悦懿德,犹耳目鼻口之能悦声色臭味。接于我之血气,辨之而悦之者,必其尤美者也。接于我之心知,辨之而悦之者,必其至是者也”。夫口之同嗜易牙,目之皆姣子都,耳之皆期师旷,亦以大致言之耳。鸱枭嗜鼠,即且甘带,人心之异,有不翅其若是者矣。谓义理之尤美者,必能为人所悦,其然,岂其然乎?乃戴氏又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者也。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责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责于我,能尽之乎?以我絜之人则理明。”故曰:“去私莫如强恕。”夫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固有此视为不能受,彼视为无难受;此视为不能尽,彼视为无难尽者矣。若曰:“公则一,私则万殊;人心不同如其面,只是私心。”则非待诸私欲尽去之后不可,因非凡人所能持以为是非之准也。凡人而度其所能受以施诸人,度其所能尽以责诸人,适见其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樊然淆乱而已矣。戴氏曰:“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谓之义。未至于同然者,存乎其人之意见,非理也,非义也。凡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谓同然。”此说安能见之于实。如戴氏之所云,亦适见其自渭义理,而终成其为意见而已矣。
已经读完最后一章啦!
90%的人强烈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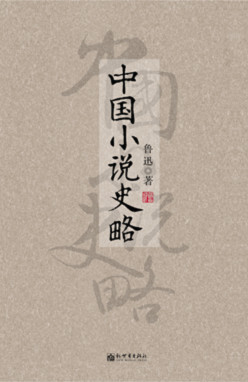
中国小说史略
题记
- 书名:
- 中国小说史略
- 作者:
- 鲁迅
- 本章字数:
- 503
回忆讲小说史时,距今已垂十载,即印此梗概,亦已在七年之前矣。尔后研治之风,颇益盛大,显幽烛隐,时亦有闻。如盐谷节山(1)教授之发见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即中国尝有论者(2),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之论也。此种要略,早成陈言,惟缘别无新书,遂使尚有读者,复将重印,义当更张,而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故仅能于第十四十五及二十一篇,稍施改订,余则以别无新意,大率仍为旧文。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
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夜,鲁迅记。
【注释】
1)盐谷节山(1878-1962) 盐谷温,字节山,日本汉学家。
着有《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等。他在所着《关于明的小说“三言”》一文中,介绍了新发现的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及“三言”(载一九二四年日本汉学杂志《斯文》第八编第六号)。“平话五种”及“三言”,分别参看本书第十四篇和第二十一篇。
2)论者指郑振铎。本篇手稿原作:“郑振铎教授之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之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