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 书名:
- 亚洲冷战与冷战后国际问题
- 作者:
- 蔡佳禾著
- 本章字数:
- 332833
- 更新时间:
- 2023-09-25 12:38:11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880.
NSC153号文件表明,保持大平衡,也就是说,兼顾美国经济承受能力和维护美国全球利益的要求是艾森豪威尔政府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发点。政府面临的问题是要找到一种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战略。
四、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新战略
修订国家安全战略早已排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日程表上,塔夫脱对NSC149号文件精神的批评促使这件事加速进行。1953年5月8日,艾森豪威尔和他四个得力下属在白宫的“日光浴室”举行了一次会议。这四个人是:战争时期曾担任过艾森豪威尔参谋长的副国务卿沃尔特·史密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克特勒,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心理作战局局长、总统特别助理C.D.杰克逊。会议决定成立三个工作小组,分别审查和研究三种可供选择的战略方案。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克特勒、史密斯和艾伦·杜勒斯三人组成“工作委员会”,对修订审查工作进行领导监督。会议决定这一计划应在7月1日前完成,并以此次会议的地点将此项工作定名为“日光浴室计划”。
在5月8日的会议上,克特勒提出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文件,它为三种选择方案提供了初步设想。方案A是继续执行经NSC149号文件修正过的既定政策,这种政策是“防御性的,它谋求在整个自由世界建立适当的实力地位,并以此遏制苏联力量,它相信通过力量显示能阻止苏联发动进攻,直至苏联因专制政府中的内部弱点而衰朽”。方案B要求明确“美国将不允许哪些地区被共产党得到,不管这是由于公开或秘密的侵略所造成,还是由于当地人的颠覆或别的原因所造成”。该方案要求明确告诉苏联,美国已在这些地区画了一条线,在此线内,任何国家倒向共产主义,美国都应采取相应措施,包括进攻性战争,但B方案仍属“防御性”的。方案C与前两方案的基本立场不同,它要求“采取行动,在一个或多个地区赢得成功,以此恢复西方的威望”。“这种积极的选择方案目的是要扰乱苏联和卫星国,鼓舞自由世界。C方案是一种进攻性的战略。”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325326.
“日光浴室计划”的临时指导小组由五人组成。小组主席为退役将军、壳牌石油公司副董事长姆斯·杜利特尔,小组成员有杜鲁门政府的助理国务卿、现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的迪安·腊斯克,中央情报局研究和报告部助理主任R.艾默里,陆军负责计划和研究的副参谋长莱姆尼策中将和海军的史蒂文斯上将。6月1日,这个指导小组完成了“日光浴室计划”的参考性文件,该文件就整个“日光浴室计划”的目的、范围、方法、应探讨的主要问题等事项提出了意见,并为将要研究的各种战略选择方案作了进一步的提示。
指导小组认为,“日光浴室计划”的目的是“制定和提出美国现在和将来可能采取的对付苏联集团行动的选择方案”。关于美国的政策目标,指导小组的文件要求各方案工作小组以NSC153号文件的提法为指导。
指导小组认为,A方案要提出的就是NSC153号文件确定的政策,为了便于分析,可以提出两种设想来解释它:第一,“时间是有利于自由世界的”,加果美国能长期坚持下去,苏联的情况会恶化;第二,这一政策包含着“甚至冒全面战争的严重风险,但尽可能使这种军事行动地方化”。关于B方案,指导小组提出了三条参考意见:一,“完成一条连接北约国家和西太平洋的线,以便形成一条连续不断的环绕苏联集团的防线”,超越此线意味着战争;二,以明确无误的方式通知苏联,美国将执行这一政策;三,“在当地共产党人夺取线内国家政权的情况下,保留行动自由,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重建符合美国及其盟国安全利益的局面”。指导小组要求考虑此线该如何划,范围多大,此线如被超越,美国应采取什么行动,等等。关于指导小组对C方案的意见,美国至今尚未公布这方面的档案材料。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364366.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日光浴室计划”的各个工作小组于7月16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了各自的研究结果。
A方案小组由“遏制战略”的创始人乔治·凯南担任主席。A方案认为,在NSC153号文件框架内,美国的战略政策还有许多地方可作重大修改。它指出,美国的对苏政策应是“在盟国的帮助下,通过逐步进展并且不冒过分的战争风险来阻止苏联的扩张。但也认识到,战争的威胁不能阻止我们进展中的行动路线”。这一政策的目标还包括“减少和压缩苏联对东欧卫星国及红色中国的控制”,瓦解苏联的“实力和意识形态”,“最大限度地增加苏联制度内部的紧张和冲突,最终迫使苏联……将其目标调整到与自由世界和平共处”。
在分析世界形势时,A方案认为有两种基本因素必须加以考虑。首先是亚洲等经济不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变革的要求,“被共产主义有效地利用了”。其次,“1945年以来支配世界局势的两极结构已在削弱,它表现为过去几年中美国威望和领导权的下降,其他自由国家独立行动的增多”。A方案认为在苏联方面也发生了相同的情况,它要求政府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政策来对付这两种因素,“利用而不是反对它们”。为此美国必须注意如下原则:“避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它追求的目的实质上是战时的目标,以及它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此外,“在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方面,美国应造成稳定和可靠的印象”。第二,应积极强调“美国的政策是建立在……实力地位之上的”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400403.。
A方案承认全面战争的风险不是很大,但不能因此削弱美国的军备建设,“军事计划应继续同苏联从事全面战争的能力相联系,而不能为苏联政治政策的摇摆所左右”。A方案还认为,美国在应付地区性侵略时,将“自由”使用原子武器,重新研究苏联大规模的毁灭能力在危机时对西欧有何种影响。A方案指出:“从今后五年或更长时间看,在特殊武器对我国安全计划的全面影响方面,应该有一个全新的面貌。”
A方案与NSC153号文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对经济能力的分析。A方案认为,美国的经济能力在较长时间里能提供“高水平的军备”,“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它指出:“关于国家债务,主要的问题是,它是否已高到威胁美国的实力的地步,而债务方面任何可能存在的威胁似乎不能同苏联的威胁相提并论。”A方案不理睬NSC153号文件关于必须平衡预算的理由,反而怀疑是否有“任何减少联邦税收的迫切的经济理由”,它建议进一步增加税收,并重新研究NSC153号文件的经济政策。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403405.
B方案小组主席是麦考马克将军。按照指示,B方案应划出一条线,如果苏联超越此线,美国可视其为发动战争的理由。但B方案报告说,“没有能找到一条令人满意的,只包括对美国安全所必需的最小范围地区的线”,“也不能找到一条可排除对美国安全有绝对重要意义的较大地区的线”。原因是美国必须使用分布于全世界的军事基地。因此B方案建议“沿着现在苏联集团的边界划线,填补中东和南亚地区尚未被北约和其他条约覆盖而留下的缺口”。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415.
海军军事学院院长R.康奈利上将领导了C方案小组。这个小组不仅提出了各种分析,而且还提供了近、中、长三个时期的不同行动路线。
C方案的第一个观点是,“时间不在美国一边”,“这种倾向将持续下去,除非美国采取积极行动来阻止和扭转它”。C方案声称接受NSC153号文件的目标,但要求把NSC153号文件关于“阻止苏联的重大扩张”的提法改成“阻止苏联的一切扩张”,它要求把“不过分冒全面战争的风险”的提法改成“不主动发动全面战争”。和A方案的观点相反,C方案要求在安全政策中加入美国的战时目标,“如结束苏联在边界以外的统治,摧毁自由世界中的共产党组织,剥夺苏联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削除‘铁幕’,消灭一切残剩的苏俄布尔什维克力量”。C方案认为,可以通过冷战来实现这种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和一切共产党力量的目标,虽然它承认这要冒“更大的全面战争的风险”。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416420.
由于“日光浴室计划”三个方案的前提几乎完全不同,最后决定把归纳工作交给安全委员会的政策设计部进行。7月30日,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克特勒向安委会157次会议提交了一份提纲,经过讨论与修改,艾森豪威尔同意把这一文件的内容作为制定新战略的指导性方针。提纲包括六点内容:
“1. 以最低的可行的代价,建立和维持一种强大的报复性进攻能力、动员基地和大陆防御体系;2. 建立对美国友好的、强大的、独立的和自给的,以西欧(包括德国)和远东(包括日本)为中心的国家集团,在中东地区建立实力地位;3. 明确今后的援助:在西欧自立的条件下,逐步减少对该地区集团的援助,在较长时间内援助远东地区集团的发展。支持中东地区加强实力地位。根据预测的美援对美国世界地位的作用,限制对其他自由国家的军事、技术和经济援助;4. 决定在哪些地区中,苏联集团军事力量的推进如被确认越过了现有边界,将被美国看作是它与苏联集团全面战争的开始;5. 即使全面战争的风险稍有增加,也要采取有选择的、范围有限的进攻性行动,消灭自由世界中苏联占支配地位的地区,削弱卫星国边缘地区的苏联势力;6. 采取非军事行动,削弱自由世界各国当地共产党力量。”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397398.
在六条指导性纲领外,克特勒还加上了关于对外政策的三点解释:“1. 估计现在的针对苏联集团的进取性行动所带来的全面战争风险,其严重性比A方案所提出的要低;2. 接受有限增加的全面战争的风险,这一风险是由C方案提出的针对卫星国的行动所带来的;3. 在最近的将来,目标是要创造一种‘胜利的气氛’,在迫使苏联集团采取守势的同时,加强自由世界的士气和力量。”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440441.
这六条提纲和三点解释表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安全战略将兼收并蓄“日光浴室计划”三种方案的基本思想,这个新战略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的战略目标或义务。但是,“日光浴室计划”仍没有找到一种可以满足“大平衡”要求的具体方案。
共和党保守势力多年来一直对以布莱德利上将为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满,认为这些军队领导人是杜鲁门政府扩军政策的工具。他们对布莱德利本人更为不满,因为他曾公开嘲笑过胡佛的战略思想,并作过不利于麦克阿瑟的证词,而且他是目前支持增加军费开支的中坚分子。按照美国的政治惯例,政府的更换并不影响军队领导人的进退。但这次情况却有所不同。布莱德利自己也知道,尽管他和艾森豪威尔是西点军校的老同学,但共和党政府不会再容得下他了。因此他在1952年12月陪艾森豪威尔去韩国视察时,就向艾森豪威尔建议,让现有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们继续工作到1953年8月,此后不再留任,以便共和党政府任命新人。艾森豪威尔接受了这个稳妥的办法。
由于塔夫脱在4月30日又一次严词指责布莱德利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艾森豪威尔加快了行动。在事先得到塔夫脱的认可后,艾森豪威尔在5月10日任命了新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由阿瑟·雷德福上将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修斯·李奇微上将任陆军参谋长,罗伯特·卡尼任海军作战部长,内森·特文宁上将任空军参谋长。任命下达后,艾森豪威尔要他们去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视察和了解情况。
7月1日,艾森豪威尔下达书面指示,要求新任参谋长在正式任职以前,首先对美国的军事战略重新进行审查和研究。艾森豪威尔指示说,他要的不是下级参谋人员式的详细报告,而是要提出个人看法,要求新观点。
7月14日,艾森豪威尔又在白宫召见了这几位新任参谋长,要求他们根据美国的全球义务,对美国的军事能力做出透彻的估价。他提醒他们要理解“大平衡”思想,在军事地位和国家破产风险之间保持平衡。艾森豪威尔要求他们说出“真诚和直率”的个人看法。后来他还告诉他们,他要的是“一致决定”,而不是一个“有分歧的文件”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894.。
由于削减军费将不可避免,各军种都竭力保全自己的利益,参谋长们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为了避免干扰,雷德福向海军部长借来了“巨杉号”游艇。8月6日四位参谋长来到了这艘船上,他们在美国东部海域的切萨皮克湾上转了两天,经过激烈的争论和讨价还价,最后做出了总统要求的“一致决定”。8月10日,经国防部长威尔逊同意,雷德福携带会议报告,乘飞机到丹佛面见艾森豪威尔。
参谋长们在“巨杉号”上做出的决议是一些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有:1. 美军的基本作用和使命不应改变;2. 美国面临的两个基本的军事问题是大陆防御和建立并维持迅速进行大规模报复的能力;3. 美军力量分布过散,一些驻扎海外的军队应撤回美国,现在应撤回在日本和朝鲜的美军,并撤回在中欧的部分美军;4. 地区性防御主要是当地军队的责任,美军可给予海空支持;5. 美军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动员;6. 不是以增加战斗人员数量,而是以效率和战备两个方面来增强美国的后备力量。李奇微和卡尼一开始不肯接受这些观点,在雷德福接受了他们提出的先决条件以后,他们才作了让步。他们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国际形势不再进一步恶化,韩国军队的扩充及重新武装西德将按计划进行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445; Snyder and others, Strategy, Politics and Defense Budgets, pp.414415.。
“巨杉号”会议报告正式把“大规模报复”概念引入军事战略考虑,这表明,美国在放慢常规武器装备速度的同时,将大力扩充其核报复能力,加快核军备速度。艾森豪威尔在初步了解了这一报告的内容后,认为可以把它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
在艾森豪威尔收到“巨杉号”报告两天后,发生了一件对美国军事战略有严重影响的事。1953年8月12日,苏联成功地试验了第一件热核武器。苏联的试验虽较美国第一次热核试验晚了十个月,但此时美国的热核武器的研发尚未进入实战要求阶段。这表明两国在核武器方面的差距已大大缩小。
苏联氢弹的影响很快就表现出来了。8月21日,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主席斯特林·科尔致函艾森豪威尔,说苏联热核武器的试验成功,使美国必须保持热核武器的领先地位,同时应重新探讨控制军备的途径。科尔保证国会将支持总统在这两方面的努力。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11861187.这预示着有关新战略的风向可能转变。
8月27日,副总统尼克松在华盛顿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巨杉号”会议报告。此时艾森豪威尔仍在丹佛休假。会议首先讨论了撤回美军问题。国务卿杜勒斯对报告要求马上撤出部分美军反应十分强烈,说他最担心的是外国政府和人民会从美国的这个行动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认为世界大战的威胁已经减小或消失。杜勒斯说,美国从中欧或其他有安全需要的地区完全撤退是异常危险的。总统特别助理、负责“心理战”的杰克逊也认为“重新部署”美军可能被欧洲舆论看作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立场上去。但尼克松和财政部长支持“巨杉号”报告的观点。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444448.
会议关心的另一问题是强调核武器的作用。尼克松问道:“在战略和战术两方面美国都可能使用原子武器吗?”雷德福作了肯定的回答。雷德福还要求公开宣称美国将使用核武器。他说在他看来,现行政策是一方面花大量的钱制造这些武器,另一方面却因为担心舆论反应而不做出可能使用的决定。李奇微则持异议,他怀疑能否靠一种军事武器的威慑效果来阻止战争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447448.。
由于“巨杉号”报告提出“重新部署”美军及突出原子武器的作用,而这两条又都被认为能减少军费开支,财政部长汉弗莱以异乎寻常的热情称赞这一报告“了不起”,“是1月20日以来最重要的事”。汉弗莱说,节约下来的钱可用于大陆防御建设。他甚至提出,有这一报告就可以“中止”对“日光浴室计划”作进一步研究了。杜勒斯认为,报告内容不错,但在实施时须十分小心,因为它的主要精神可能影响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他说,“破坏自由世界团结,或使美国单独承担防卫的任何措施都不是真正的节约”。杜勒斯非但不同意中止“日光浴室计划”的研究,而且不同意安委会就这一报告表示意见。他坚持要让国务院研究“巨杉号”报告的国际影响。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447451.
对杜勒斯来说,“巨杉号”报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新东西。突出核武器作用,强调大规模报复能力是他自己的观点,“重新部署”美军则是雷德福的一贯立场,两者都被认为是符合新政府的军事战略原则的。那么,为什么这次他变得如此谨慎小心?原因盖出于苏联氢弹试验成功。杜勒斯觉得有必要重新考虑前一时期确定的原则。他首先想到的是欧洲。过去欧洲把美国的核优势当作“保护伞”,而现在核力量则可能成了“避雷针”。欧洲会非常符合逻辑地认为,“如果欧洲首先遭到攻击,美国可能会因为自身的脆弱而置身事外,同样如果美国首先遭到攻击,欧洲也宁可置身事外”。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457459.因此,杜勒斯认为,在这新形势下,“巨杉号”报告和“日光浴室计划”可能在国外被看作孤立主义和采纳“美国堡垒”思想的证据。为了消除这种误解,杜勒斯担心,美国的军费开支将会急剧增加,经济会发生问题,“而实际上又得不到更大的安全”。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459.
于是杜勒斯盘算可否另辟蹊径,如提出限制军备和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美、苏撤出在国外的军队以“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方案。这既可增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不冒被孤立的风险,又能顺利解决纷争不已的削减军事预算这个实际问题。杜勒斯知道此事重大,必须先和艾森豪威尔商量,所以在会议结束后,带着写好的备忘录于9月6日抵达丹佛。9月7日他与艾森豪威尔长谈一天,当天下午飞返华盛顿。9月8日,艾森豪威尔根据前一天的谈话内容,也写下了一份备忘录,这是他对杜勒斯建议的正式答复。
艾森豪威尔首先表示,他在“总的方面同意”杜勒斯的观点,“特别同意重新做出努力,在全球范围内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以及把“共同撤军”作为缓和紧张局势的第一步。艾森豪威尔还表示应尽早开始这方面的行动。
但是,艾森豪威尔不同意杜勒斯大幅度修改美国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的提议。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三条理由。首先是经济方面的障碍,他指出,按杜勒斯的意见,美国必须做出更大努力来发展非常规武器,但“这涉及我们要大大增加开支”,而不是杜勒斯所打的如意算盘。其次,艾森豪威尔不认为杜勒斯的和平攻势能奏效,他说,“即使总统、内阁和国会领导人在一致意见的基础上采取经过重大修正的政策,这一局面仍不足以保证实现期望中的目标”。而且,美国老百姓会觉得这是政府无能。第三,艾森豪威尔怀疑杜勒斯关于对核武器进行国际控制的建议是否可行。他说苏联“一直拒绝依靠集体行动进行国际控制的任何真诚的努力”,美国的“每一个真诚的和平姿态或建议都被共产党人粗暴地拒绝了”。
至于苏联氢弹试验成功,艾森豪威尔要杜勒斯设想苏联领导人“可能考虑”“侵略性”地使用核武器,美国必须考虑改变战争准备政策,应作好长期准备,对敌人进行更大的报复性打击。因此,“为了下几代人的利益,我们的职责是要求我们在可安排的最适当的时间发动战争”
艾森豪威尔1958年9月8日备忘录,见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460463.。
杜勒斯另辟蹊径的方案没有被艾森豪威尔接受,这表明,在重大问题上,掌舵的还是总统艾森豪威尔。这同样表明,艾森豪威尔调整军事战略的余地是有限的,他既不能按塔夫脱等人的要求搞一套与杜鲁门政府截然不同的战略,也无法接受杜勒斯得知苏联氢弹爆炸成功之后,突然提出的新建议。
从丹佛回来10天之后,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美国已完全准备好探讨结束当前紧张局势的途径”,他要求苏联“对缓和这种紧张局势做出更大贡献”,并且保证美国政府“愿意表现出它要求别人表现的同样的精神”。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50—1955, pp.350359.不过,这只是对苏联氢弹试验成功所采取的一种姿态而已。
五、“新面貌”战略的面面观
在“日光浴室计划”和“巨杉号”会议报告等文件的基础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起草小组开始起草新的军事战略文件。他们从1953年8月初开始工作,到9月20日完成了编号为NSC162文件的第一稿。10月7日、13日、2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三次讨论了这份文件,决策者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再次进行了辩论。
引起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的对苏政策。NSC162号文件一稿中有一段国务院提出的文字:“不过,美国不应使用部队针对苏联集团领土发起进攻性的行动。在我们力所能及范围内的有限行动即使成功也不会实质性地减少苏联的威胁。这类行动反而会大大增加全面战争的风险,使西方联盟国家之间关系更加紧张,并可能在苏联威胁这个更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上毁掉同它们达成协议的机会。”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513514.这段文字比罗斯福时期承认东欧是苏联势力范围还要过头,遭到了威尔逊、史塔生和艾伦·杜勒斯的反对,艾森豪威尔也站在他们一边。杜勒斯不得不同意删除这一段文字。但在最后一次讨论中,杜勒斯重申,如果要采取进攻性行动,例如进攻阿尔巴尼亚或中国的海南岛,必须事先得到安全委员会的批准。
草稿中关于苏联的另一段话也引起了争论。国务院提出:“只有通过美苏两国接受他们认为符合自己利益的解决办法,苏联的威胁才能被实质性地减少。”由于其他人包括艾森豪威尔提出要删除这一段话,杜勒斯以强烈的语气为这一段话作了辩护。杜勒斯说:“如果我们指望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得到好处,而让苏联人什么也得不到,那么我们就无法减缓同苏联的紧张关系”,他说,“解决必须是双方可接受的。”杜勒斯指责国防部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似乎要改变政府的全部政策——这一情况从苏联拥有氢弹来看就更危险了”。杜勒斯坚持说:“如果你要让双方可接受的解决服从于增强美国对付苏联的实力地位,你就打消了解决朝鲜、奥地利、德国等问题的所有希望。”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512, 529, 530.最后安委会成员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妥协的提法。
争论的第二个问题仍然是“大平衡”观点。在文件起草小组中,国防部、国务院和共同安全署的代表认为,苏联是基本的威胁,他们也承认健全的美国经济是十分重要的,但美国必须首先满足必要的安全费用。而财政部、预算总署的代表则坚持“双重威胁”观点,认为必须在两种“威胁”之间保持平衡。在10月7日的讨论中,杜勒斯说:“如果采取这一方针意味着美国将要平衡预算、减少税收,一切事情都要给这一目标让路的话”,他就反对这一文件。国防部长威尔逊说,美国真正要做的事是,“明确和达到一个合理的长期防卫态势”,“如果我们能在平衡的预算下做到这一点就最好,如果不能做到,我们就不得不推迟实现平衡预算”。艾森豪威尔反驳了这两位部长的意见,他说国务院和国防部的观点似乎是“设想对国防所必需的任何东西都可能实现,而且不会严重损害经济”。他坚持这将影响美国的“生活方式”,他说,“如果我们愿意采取阿尔道夫·希特勒的制度,我们或许能战胜整个世界”。他告诫说:“你能使美国人民在一两年甚至三年时间内做出牺牲,但不能使美国人民无限期接受这种立场。”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517521.NSC162号文件最后表达的思想倾向于艾森豪威尔的观点。
引起争论的第三个问题是有关核武器的“常规化”,即改变使用原子武器的政策问题。军方对1950年底美英会谈公报中的一段话耿耿于怀,即美国总统将随时把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向英国首相通报。国防部长威尔逊咄咄逼人地问道,究竟要不要使用花了这么多钱制造出来的武器?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国如要从海外基地使用核武器就必须得到盟国的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随即追问道:“我们可以从不需得到外国政府同意的基地上使用这些武器吗?”艾森豪威尔回答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当指望在全面战争情况下使用这些特殊武器,但他们不应当在小事情上计划使用这些武器。”杜勒斯不同意这种区分,他认为“必须以某种方式破除对使用这些武器的忌讳”。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532533.
在决策层意见不一的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也在准备提出1955年度的国防经费预算。军方认为美国承担的海外军事义务没有减少,朝鲜战争还可能重新爆发,因此在10月13日会议上,军方提出了420亿美元的国防拨款,350亿美元新授权的要求。这使财政部长汉弗莱和预算署署长道奇大为吃惊。道奇指出,“由于减税,政府可能在1955年度面临54亿美元现款赤字和87亿美元拨款赤字”。汉弗莱愤怒地指责国防部和军队在做了种种研究之后,“连一文钱也省不下来”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543544;Snyder and others, Strategy, Politics and Defense Budgets, p.426.。艾森豪威尔对此也深为不满。
杜勒斯这时胸有成竹地问道:军方在估计预算时是否考虑到使用核武器?雷德福答道没有,因为使用原子武器的现有政策并无改变。他接着说,他希望改变。军方的态度显然是,如果政府不改变使用原子武器的政策,他们就不会真正同意削减军费。这时,刚刚指责过军方的汉弗莱立即开了窍,他说,“解决使用原子武器的问题是绝对重要的,只有在广泛情况下使用它们,才能真正改变国防部的计划,才能减少军事预算的费用”。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547.汉弗莱接着用塔夫脱的观点向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他说,1955年是关键的一年,必须维护公众对“经济健全和总统领导地位的信心”,如果美国人民认为政府仍然在走老路,美国经济就会垮台,共和党就会输掉下一场竞选。面对预算问题,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放弃了反对改变使用原子武器政策的立场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547.。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一个名为“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演讲。在这篇看起来是为了控制核军备的主旨演讲中,艾森豪威尔加进了十分重要的两句话:“在我国武装部队中,(原子武器的)发展已使得这些武器实际上具有了常规地位。在美国,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都能够把这些武器投入军事性使用。”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50—1955, p.2800.
1953年10月30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NSC162号文件——“国家安全基本政策”。这一文件取代了以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68、135、149、153号等文件,成为新政府指导美国安全和对外政策的基本文件。
所谓“新面貌”一词最初出现在“日光浴室计划”A方案中,但据雷德福回忆,人们把“巨杉号”会议报告称为“新面貌”文件。最终,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战略主要体现在NSC162号文件中。
S. Jurika, e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2800.
与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8号文件一样,NSC162号文件也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文件分析苏联对美国的威胁有三个方面,即“苏联对非共产主义世界,特别是对美国的根本性敌视”,“巨大的苏联军事力量”和“苏联对共产主义支持和对其他颠覆、分裂自由世界工具的控制”。文件认为苏联的政策是建立在这些威胁之上的,“苏联集团和非共产主义世界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冲突”以及苏联“对安全的忧虑”,“不信任美国的目的和意图”等。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578579.
与过去的安全战略文件不同的是,NSC162号文件没有一个专门论述美国战略目的的部分。文件只是在结尾处说到,“面对苏联日益加强的威胁,美国安全政策的宏大目标必须是创造某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美国和自由世界联盟决心准备好应付苏联的烕胁,并在适当的安全保证下,为缓和这一威胁而进行谈判”。文件在另一个部分谈到,“美国的政策是要防止苏联侵略和继续统治别的国家,并在适当保证下建立有效的军备控制,它并不是要支配苏联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制度”,但要“阻止世界局势发生基本的变化”。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594596.
“新面貌”战略坚持了艾森豪威尔的“大平衡”思想。NSC162号文件提出的两项基本任务是,“应付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在这样做的同时,避免严重削弱美国经济或损害我们的基本价值和制度”。它还要求“维持一个强大的、健全的和成长的经济”,通过“自由制度的运作”,具有在长期竞争中“提供必需的力量和迅速有效地转入全面动员的能力”。NSC162号文件在关于美国支持安全开支的能力这一部分说到,“不仅美国的世界地位,而且整个自由世界的安全均有赖于避免美国衰退,有赖于它的长期增长”。但“经济增长不是自动的,需要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政策支持而不是损害这种长期增长的潜力”。文件提醒说,“过分的政府开支会导致通货膨胀性赤字或压抑性税收”,“现有的高额政府债务将进一步使美国财政和经济问题复杂化。”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582, 588589.
NSC162号文件表明,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意识到了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它并没有也不愿意相应限制或者缩小它的战略利益,艾森豪威尔的“大平衡”实际上是希望以更低的代价来保住这些利益的“最佳方法”。由此就可以理解,艾森豪威尔政府先后提出的1954和1955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主要是根据财政部门的限额而不是根据军方的要求制定的。
政府对军方的要求还是必须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这表现在以原子武器为主要手段的“大规模报复”概念终于成为“新面貌”战略中的主要军事原则。NSC162号文件要求美国“发展和维持强大的军事地位”,并“强调以进攻性打击力量实施大规模报复性破坏的能力”。文件还要求美国在原子武器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保持优势地位”,因为在整个西方世界中,只有美国拥有能对抗苏联核武器的能力。因此,“充足的原子武器和有效的发射手段对美国的安全是不可缺少的”。NSC162号最终文件中还有一段第一稿所没有的文字:“在敌对状态下,美国将把核武器看作像其他军火一样能够使用的武器。”这段文字表明,在“新面貌”战略中核武器使用政策已正式改变,即所谓“非常规武器常规化”。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582583, p.593.
但是,NSC162号文件也包含了艾森豪威尔的观点,即如果要从盟国基地上发射核武器,事先还要得到这一盟国的同意。此外,这一战略也承认,在新的形势下,核武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该文件说,苏联核力量的增长可能“消除美国原子力量对苏联在边缘地区进行侵略的威慑效应”,它还可能使苏联对美国的某些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反应。“由于全面战争对任何一方都越来越成为灾难,把诉诸全面战争作为对地区性侵略的制裁也就越来越不可能。”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581583.由此可见,在“新面貌”战略中,虽然强调了核武器的作用,但它们主要是一种“威慑”手段。而“日光浴室计划”B方案的基本思想——以全面战争来“防止苏联扩张”——并未被采纳。
“新面貌”战略的另一新的内容是“重新部署”驻扎海外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虽然在“巨杉号”上同意了这一原则,但各军种对撤军的时机、地区、数量等问题有不同意见,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也意见不一。NSC162号文件只得这样写道:“美国武装部队现在的部署过于分散,影响了未来军事行动的机动性和主动性。但是,在现有条件下,从欧洲和远东地区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撤退都会被看作美国防卫这些地区的兴趣在减少,并会严重破坏联盟的力量和团结。”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593.怎么办?该文件要求“进行外交努力”,使盟国理解“重新部署”美军的意义,认识到“对自由世界最好的防卫有赖于带有主动性、机动性和支持能力的美军部署,有赖于我们的政治承诺,即我们将有力地、直接地回击任何进攻这些盟国的侵略者”。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593.
“重新部署”美军被看作最能节省军费的措施,因此,财政部长汉弗莱在10月召开的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呼吁“立即考虑重新部署大量的海外美军并彻底修改我们的军事战略”。但NSC162号文件没有做出这方面的安排。然而预算问题比任何理论更有权威。1953年11月18日,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威尔逊和汉弗莱举行了会议,再次讨论如何减少1955年度国防预算问题。杜勒斯这次同意撤军:“我们应当开始从朝鲜撤出地面部队,这样做的理由是我们应显示我们对空军和海军力量的信心,应当避免在亚洲部署地面部队。如果这样做了,我们就能对现役陆军进行实质性的削减。”会议还决定,对驻欧洲的部分美军实现“精干化”,如果形势没有大的变化,政府将不批准陆军要求在1955年拥有150万人的计划。这次会议同意,“我们对新武器的依赖使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常规力量作某些削减,这包括地面部队和海军的某些部分”。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备忘录上写到,这次会议意味着将削减美军人数,减少驻朝美军,并研究减少驻欧美军。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597598.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联盟政策在NSC162号文件也占有较大的篇幅,虽然这一政策在“新面貌”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很少引发争论。
NSC162号文件指出,自1950年以来,美国在“建设自由世界的力量、团结和决心”这三方面已取得了成功,“可能已阻止了自朝鲜战争发生以后的公开侵略”。文件在谈到盟国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意义时写道:“没有盟国的支持,即使美国付出昂贵的开支,仍无法满足国防需要”。文件还指出,“在这场世界斗争中,无论是在和平还是在战争情况下,美国都需要使主要的高度工业化的非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和经济资源及物资同美国站在一边。如果这些国家逐步丢失给苏联集团,将会使美国孤立,并危及美国赢得全面战争的能力”。“新面貌”战略中的联盟政策要求做到“真诚地使盟国相信,美国的安全战略是集体安全战略。联盟必须扎根于对利益共同体的强烈信念,并坚信美国领导的稳定性和明智性”。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583585.
NSC162号文件承认,美国的联盟政策面临着种种问题,如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西欧军事力量薄弱、某些盟国内部的动荡不稳,等等。但美国最为不安的是“西欧越来越不愿追随美国的领导。许多西欧国家担心美国的政策,尤其是远东政策,会把欧洲卷入全面战争或者会无限期地延长冷战的紧张状态”。文件还说到,西欧认为美国的政策太僵硬,太不灵活,也太不稳定,具有发动先发制人战争和“解放”,以及退回到孤立状态的种种风险,而且“表现得太过忙于反共”。文件因此提到,为了获得盟国的长期支持,美国应使盟国相信,它愿意同苏联谈判解决问题。文件还提出要求英、法、德三国加强合作,在这一基础上增强西欧的军事实力地位。西欧的自立程度已有加强,因此对欧洲的援助总量将要减少,但这一援助还会进行下去。文件表示支持建立一体化的西欧共同体,并要求西欧各国尽力建立防卫力量。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583586, p.592.
“新面貌”战略还专门制定了对不结盟国家的政策。NSC162号文件说,许多不发达国家由于紧迫的国内问题,“他们现在还不愿同美国及其盟国结盟”,虽然这些国家“大多是不发达的,但他们巨大的人力,他们的基本原料资源以及他们的增长潜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他们并入苏联体系就会大大地甚至是决定性地使世界局势变得不利于我们”。
文件承认,在许多不结盟国家中,动乱和敌视西方的力量很强,原因据说是多方面的,包括“种族情绪、反殖民主义、上升中的民族主义、公众对社会和经济迅速进步的要求、人口过多、停滞的社会模式崩溃,以及在很多情况下,是当地宗教、哲学与西方宗教、哲学的冲突”。文件还说到“不能单靠外部经济援助来解决它们的基本问题或赢得它们的合作与支持”。文件还提到,不结盟国家政治上的不稳定使西方加强与它们的联系、抵制中立主义等问题更加复杂了。文件建议采取积极措施使这些国家意识到“它们与自由世界有共同的利益,并抵制共产主义的吸引”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587588.。
美国的这一政策表明,它开始意识到不结盟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但美国既然反对这些国家奉行中立政策,就难以提出什么措施来吸引这些国家。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战略还突出了“心理战”和开展颠覆活动的作用。与民主党政府相比,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心理战”的重视,可谓情有独钟,它不仅设立了隶属白宫的心理作战局,还把颠覆手段引为“新面貌”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10月29日的讨论中,文件起草小组要求修改原稿中的一段话,即“为了扩大解决问题的机会,美国及其盟国应向苏联领导人和人民讲清楚,如果苏联放弃扩张和统治别国,他们准备接受一种解决办法,承认苏联领土完整和内部政治与经济制度”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513.。总统心理战特别助理杰克逊说,这段话如不修正,“可能被看作对目前存在的苏联制度的赞同”。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568569.起草小组说,他们希望说明这段话“是对外交领域的指示,并不打算以此来指导我们的情报和宣传机构”。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568569.这一说明作为注解被正式载入NSC162号文件。这个修改和注释表明,美国在宣传和情报活动中,仍将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指导方针。文件写道:“据此,美国应采取可行的政治、经济宣传和秘密措施,以便制造和利用对苏联有麻烦的问题,损害苏联同中国的关系,使它控制卫星国更加困难,并阻止苏联集团军事和经济能力的增长。”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595.
NSC162号文件还指出,对安全计划的支持“最终有赖于民族道德的健全和全国对政府的……政治意愿的支持”,文件要求把动员这类“精神资源”作为“心理战”的另一面。文件认为“美国应采取公开和秘密的手段诋毁作为苏联力量有效工具的苏联威望和意识形态,削弱各国共产党和各种亲苏分子的力量”。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595.
颠覆活动在“新面貌”战略中有更大的重要性。早在7月30日讨论“日光浴室计划”时,杰克逊就迫不及待地指出:“该计划包含了许多可取的行动计划”,“这些计划不应等到整个新政策文件全部完成后才进行,采取某些行动中的初步措施不会有坏处”。杰克逊建议国务院研究“离间某个卫星国的可能性,不必等待采取新政策”。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p.438440.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等人讨论了美国可能采取行动的地区,如危地马拉、阿尔巴尼亚、伊朗以及中国的海南岛等地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根据艾森豪威尔的指示,中央情报局成功地颠覆了伊朗的摩萨台政府。
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用于秘密活动的经费直线上升,即便如此,直到艾森豪威尔上台,秘密行动才真正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工具”。
John L. Gaddis,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57158.与杜鲁门政府的扩充军备、到处派兵相比,花钱不多但后果明显的“心理战”和颠覆活动,受到“新面貌”战略制定者们的重视,实是题中应有之义。
1953年12月22日,杜勒斯在华盛顿向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时,宣布了“新面貌”的一个重要军事战略原则——“大规模报复”理论,“新面貌”战略正式出台。
一个月以后,1954年1月22日杜勒斯在“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全面解释了这一战略。杜勒斯说,过去的外交政策诸如“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欧洲复兴计划”、“克服柏林封锁”、“回击共产主义对朝鲜的进击”等,有许多是成功的,这些“主要是在紧急情况下的行动,是我们的敌人加诸我们的”。但紧急措施“不一定能成为良好的长期政策,紧急措施是昂贵的、粗糙的,意味着敌人掌握主动权,不能指望它为我们的长远利益服务”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50—1955, pp.8085.。
杜勒斯分析了民主党政府战略理论。他说,“使美国地面部队长期在亚洲承担义务,以致我们没有战略后备力量,不是一种健全的战略”。他还指出,“永久地援助其他国家不是一种健全的经济学,或者说也不是一种好的对外政策”,因为,“长期承担如此巨大的军费开支,会导致实际上破产,这不是健全的政策”。
杜勒斯说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心改变这种情况。“我们需要盟国和集体安全,我们的目的是使这种关系更有效,而且花费更少。较多地依赖威慑力量,较少地依赖地区性防卫就能做到这一点。”杜勒斯犹恐听众印象不深,重复道:“新战略是要获得这样一种国际安全体系,它以可以承受得了的费用实现最大程度的威慑。”他解释道:“地区性防务仍然是重要的,但没有一种地区性防卫能单独遏制共产世界巨大的地面部队,地区性防务必须由大规模报复力量的进一步威慑来加强。”杜勒斯总结道:“对于自由社会来说,威慑战略的方法,是愿意而且能够在它自己选择的地点,以它选择的方法做出强有力的反应。”杜勒斯这篇阐发“新面貌”战略的演讲,以这句话给人们印象最为深刻,以致后来人们几乎认为“新面貌战略”就是“大规模报复”。
六、对美国“新面貌”战略的历史回顾
“新面貌”战略是战后美国军事和外交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在艾森豪威尔执政八年间,它是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在战后美国军事、外交政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自“新面貌”战略公布至今,美国朝野对该战略的成败得失一直议论纷纷,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它的评价也各有不同。
艾森豪威尔制定“新面貌”战略的指导思想就是搞所谓的“大平衡”,即平衡对待“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外部威胁和国内的经济危机威胁。为了维持美国世界领袖的地位,艾森豪威尔政府必须确保美国的海外利益及其盟国的安全,同时还要避免本国经济因“超负荷”而崩溃。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利用美国的核优势来达到上述目标。具体做法便是削减耗资巨大的常规军力,发展费用相对低廉的核打击力量。这必然要削弱当时美国陆海军的地位。因此,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争论中,对“新面貌”战略怨气最大的要数陆军将领。他们认为,该战略不足以保卫美国的利益,而且“战术核武器很可能需要较大的军队而不是较小的军队”。
马克·李奇微语,引自拉塞尔·F.格伟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498页。
五十年代中期,苏联的核武器以及运载能力有了迅速发展,特别是苏联先于美国拥有了洲际导弹,剥夺了美国本土不易受攻击的有利地位。这更使人们对作为“新面貌”战略核心的大规模报复的威慑效应产生了怀疑。1956年,刚卸任的陆军参谋长李奇微便在其回忆录《战士》一书中对核威慑的作用提出了质疑。他指出,相互的核威慑将使人们不愿意使用核武器,并使人们认识到,核战争会使世界上大部分人民、财产及制度都化为乌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否真可以放心大胆、毫无顾忌地依靠核武器来发挥军事威力是可以怀疑的”,这反而使苏联可以不动用核武器就实现其所要实现的目的。
拉塞尔·F.格韦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第498页。
接替李奇微任陆军参谋长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对大规模报复理论也大为不满,甚至认为它处一种荒谬的观点。1956年,他为《外交》杂志撰文抨击这一理论,但因受国务院阻止而未能发表。以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大规模报复政策的全盛时期,它只能使我们的领导人面临这样两种选择:发动核大战,或谋求妥协和退却。”“1945年以来的其他许多有限战争——中国的内战、希腊和马来亚的游击战、越南战争、台湾事件、匈牙利事件、中东战争、老挝战争,等等——也清楚地说明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可能阻止了大战,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却未能保持住‘小和平’,即没能清除局部地区的骚动。”
马克思韦尔·泰勒:《不定的号角》,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612页。
曾积极主张扩充常规军力以遏制苏联的保罗·尼采也于1956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原子弹、战略和政策”的文章,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普遍适用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政策很难在中东或亚洲奏效。他指出,如果核战争无法避免的话,西方的利益就是,在最小的地区针对尽可能有限的目标系统使用最小规模的原子武器,而且“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不应使用原子武器来对付侵略和恢复局势”。他仍希望加强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
Paul Nitze, “Atoms, Strategy and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34, No.2, pp.187198.
亨利·基辛格在这场辩论中初露头角。他在1957年发表的《核武器和美国对外政策》一书中指出,新战略并没有使美国得到主动权,因为我们只把核武器看作这样一种战争概念中的工具,即除了全面胜利以外不接受其他目的,除了全面战争以外不承认其他作战方式。基辛格肯定了核武器的作用,但否定了核大战,认为应当为核武器寻找中性的用途,因为“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与能够以人力代替科学技术的大国作战,有限核战争却是我们最有效的战略”
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第1819页,186页。。
显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人们着重分析的是“新面貌”战略中的“大规模报复”政策,因此“灵活反应”,“有限战争”等理论应运而生。进入六十年代后,随着美苏核僵持局面开始形成,“新面貌”战略在八年的实施过程中又累累受挫,尤其是该战略把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共产主义的“扩张”联系在一起,企图以“莫斯科本身当作人质来对付世界各地共产党侵略”
FRUS, 1952—1954, Vol.2, pt.1, p.494.的做法,不但未能有效对付世界各地的地区性冲突,反而使美国的威望大大下降,“新面貌”战略开始受到更严厉的抨击。在一些与民主党关系较深的学者眼里,艾森豪威尔执政的八年几乎是一部失败的记录,甚至有人对艾森豪威尔本人的领导能力提出了疑问。
W.W.罗斯托在1960年出版的《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一书中,全面抨击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外政策。他认为,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由于领导不力,美国在导弹方面已落后于苏联,美国在西方和不发达地区的领导权及影响力正在丧失。他还直接批评了“大平衡”思想,认为艾森豪威尔的基本政策是由中西部的共和党人制定的,这些人的思想“深深地带有从前孤立主义思想和概念的色彩,他们不是以同情的态度来接受现代历史所造成的后果,而这个后果已经使美国与整个欧亚大陆周围地区及欧洲大陆本身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罗斯托指出,在1953年,当武器技术和不发达地区的事态发展都需要美国花钱时,那些有意要削减联邦预算的强大舆论却左右了美国的政策。他还说,“新面貌”战略是一种“意在挫败共产主义直接军事侵略的短期军事和政治结盟政策……而当时,共产党的政策已转变成一种进行长期蚕食的策略”。罗斯托还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狭隘地根据从‘大平衡’中得出的军事政策对待不发达地区”。他把一切失败都归咎于艾森豪威尔个人领导不力。
W. W. Rostow,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Aren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Publishers, 1960, pp.302304, pp.325331, p.381.
六十年代初,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全面研究了“新面貌”战略。亨廷顿认为,新战略的变化主要在于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军事战略方面。他认为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是“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他指出,虽然新战略在提出的头两年里曾取得了一些成功,包括减少联邦政府支出近100亿美元,减少税收75亿美元,但这些成功是“短暂的”。当苏联实力的增长开始破坏“新面貌”战略的前提和目标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却未能及时调整其战略。亨廷顿指出,这一战略在国际政治方面是一个严重的失败。他说:“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安全只是一个小目标,在世界政治中,关系重大的恰恰不是安全,而是美国的威望、盟国的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前途。”他指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阻碍了美国扮演更活跃和更富创造性的角色。
S. P. Huntington, Common Defense, pp.8387, pp.440442.
曾专门研究“新面貌”战略产生过程的施奈德也对这一战略持批评态度。他认为,新战略的指导思想主要是从经济压力出发,服从于国内政治需要,它倾向于“使军事政策脱离外部政策和目标”,而由“内部目标”来作决定。他指出,就“新面貌”战略的整体和目标而言,是“国际主义”的,但是,其实现目标的方法却是孤立主义的。施奈德指的是美国削减驻外军队,减少对盟国的依赖,削减对外援助款项等问题。他认为这样做“将会冒在战争爆发后花更大代价的风险”
Warner R. Schilling and others, Strategy, Politics and Defense Budgets, pp.492498, pp.502504.。
六十年代后期,“新左派”在美国学术界异军突起。在J.科尔科和G.科尔科所著的《实力的限度》一书中,作者指责艾森豪威尔坚持反共冷战是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他们认为美国在五十年代试图寻找一种“便宜”的防卫姿态,同时却鼓励西欧盟国继续扩大军费开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急于维持那种应付全球危机和危险的动员意识”,以此避免削弱美同在北约中的霸主地位。作者认为美国是有意识地利用其他西方国家“对俄国的害怕”。科尔科揭示了“新面貌”战略的困境,即既要维持霸权,但又面临力量有限的局面。作者还批评美国对“亚洲、拉丁美洲及中东的不可避免的变革”采取敌对立场,而这一立场正是由“新面貌”战略造成的。
J. Kolk and G. Kolk, The Limit of Pow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p.695.
艾森豪威尔离职后,他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处于谷底。人们普遍认为艾森豪威尔缺乏活力、激情及应有的政治技巧,对事态的发展不能施加有效影响。甚至有人认为艾森豪威尔总是不务正业,只会谈谈西部小说,与他的百万富翁朋友们玩玩高尔夫球和桥牌,而听任杜勒斯等人操纵局势。
Thomas G. Paterson, 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Vol.Ⅱ, Washington D. C.: Health and Company, 1989, p.470.当时的民意测验显示,在历届美国总统中,艾森豪威尔名列第22位,被视为美国最差的十位总统之一。
Steve Neal, “Why We Are Right to like IKE”, in American Heritage, Vol.37,NO.1,p.50.
在七十年代,由于遭受了越南战争失败以及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打击,美国人开始怀念艾森豪威尔时代了。美国公众看到,自从1961年民主党人执政以来,由于扩充常规武装,美国的军费开支迅速上升,而民主党政府以“有限战争”和“灵活反应”等策略来防止核大战的战略理论又使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淖,最后不得不以认输告终。与此相比,艾森豪威尔在执政八年中却使美国安享和平与经济繁荣。在五十年代的各次危机中,他巧妙地避免了美国的军事介入;“体面”地结束了朝鲜战争;他顶住了强大的压力,没有在印度支那直接动用美军;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他勇敢地反对了“欧洲帝国主义”,同时又能成功地团结盟国一致对苏。
Paterson, 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Vol.Ⅱ, p.472.在一些美国评论家眼中,五十年代是一段美好时光,而这一切都归功于艾森豪威尔领导得力以及他的“克制”精神。
R. Melanson and D. Mayors, Revaluating Eisenhower,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7, pp.17.
赫伯特·帕麦特在《艾森豪威尔与美国十字军》一书中指出,艾森豪威尔当选时,整个美国面临着“严重的分裂”,他使国家重新团结起来了。没有艾森豪威尔,朝鲜战争可能不会在“三八线”附近停战。帕麦特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显示了力量”,但又能小心地避免卷入更大的风险。他使“北约保持活力,并维持相对和谐,这正是他一开始的主要目标”。帕麦特认为艾森豪威尔政策是“杜鲁门—艾奇逊政策的继续”。尽管人们批评“放蒋出笼”和“大规模报复”,但较前任的政策来说,新政策效果明显,流血较少。帕麦特还赞扬了“大平衡”思想,认为“使财政力量与国家生存相匹配”是一个“无可争辩的概念”。帕麦特还指出,艾森豪威尔的最大成就是“保持了和平”
Parmet, Eisenhower and American Crusade, pp.573575.。
艾森豪威尔的主要传记作者安布鲁斯也肯定了“大平衡”思想的经济后果。他认为,“新面貌”战略意味着巨大节约,这是艾森豪威尔对美国最大的贡献。因为这一战略为美国省下了数以百亿计的美元。当代评论家们在这一问题上观点趋于一致,他们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至少使美国避免了狂热的军备建设。
Ambroze, Eisenhower, Vol.2, pp.225, p.435; R. A. Aliano, American Defense Policy from Eisenhower to Kennedy, The Politics of Changing Military Requirements, 1957—1961,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5,p.60.实际上在“新面貌”战略指导下,美国武装部队的总人数由1953年的345万人减少到1957年的281万人,这种人力上的削减及五十年代中后期相对较低水平的军费开支,无疑有助于美国经济在相当时期内的稳定增长。
进入八十年代,对艾森豪威尔安全战略的研究达到了新水平。艾森豪威尔图书馆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解密文件,使学者们能够更详细更全面地评价“新面貌”战略以及艾森豪威尔本人的领导能力。
约翰·加迪斯在其重要著作《遏制战略》一书中指出“新面貌”战略的目标是要夺取东西方斗争的“主动权”,同时要降低美国的安全费用。加迪斯认为新战略的核心思想并不是“大规模报复”,而是“不对称反应”,也就是杜勒斯说的,在美国选择的地点,以美国选择的方式与苏联对抗。在加迪斯看来,这个战略“实现了以较低代价获得较大威慑的目的”,但他对这一阶段未发生较大规模的东西方冲突是否是这种威慑的结果表示怀疑,因为这需要了解“被威慑者”的意图。至于“新面貌”战略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加迪斯认为是失败的。他指出,由于杜勒斯把威胁看成是普遍的共产主义威胁而不仅仅是苏联的威胁,因此“政府集中力量反对共产主义而使共产主义采取了民族主义的形式”。由于对“非共民族主义的自立几乎没有信心”,美国在对待这类力量时,“违反了原想要维持的主权和自立原则”。但是加迪斯仍认为“新面貌”战略是“连贯的”、“小心的”,“在它的目的和手段方面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而不是有害的。”
Gaddis,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pp.147148, p.171, p.182, p.197.
另一位历史学家诺曼·格雷伯纳在1987年对“新面貌”战略仍持基本的否定态度。格雷伯纳认为,艾森豪威尔虽然控制了新战略的性质,“但似乎不能控制其规模”,理由是这一时期美国核武库发展速度过快。美国政府不能使别国人民,甚至不能使美国人民相信美国的安全利益是全球性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从开头起就如此广泛地界定美国的利益,以致美国人民不知道华盛顿到底要他们保卫什么”。格雷伯纳认为,美国所宣布的目的,不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道义上,是任何军事结构都不能获得的。
Norman Graebner,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80287.
随着研究的深入,历史学家们从大量资料中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艾森豪威尔并非他所表现的那么“懒散”。相反,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精于权术、善于伪装的老练政治家。
Paterson, 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Vol.2, p.470.他往往躲在幕后控制着局势的发展。因而,在他整个执政期间,正是艾森豪威尔本人,而不是国务卿杜勒斯,控制着美国的战略方向。于是,历史学家们把研究转向艾森豪威尔制定这一新战略的动机。理查德·梅兰森指出,要求对外政策的连贯性,重建国内的冷战共识,谋求国际合作,防止美国成为一个孤立主义的“堡垒国家”等因素是理解艾森豪威尔政策的关键。梅兰森说,艾森豪威尔“试图形成的安全战略,是在塔夫脱的美国堡垒孤立主义和杜鲁门的凯恩斯国际主义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梅兰森认为艾森豪威尔“维持了杜鲁门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艾森豪威尔不愿意重新确定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由于他坚持“反共信仰”。
Melanson and Meyers, Reevaluating Eisenhow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50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p.50 61.
肯尼思·汤普森看到了历史本身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限制。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坚持冷战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争夺全世界人民的忠诚”,“没有一个战后领导人成功地解决过顽固的冷战问题,这些问题的改进也许完全超过了人类的能力”
Melanson and Meyers, Reevaluating Eisenhower, p.26.。
不管历史学家们还有多大的分歧,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重新评价已使艾森豪威尔本人的历史地位上升。1982年《芝加哥论坛报》对一批学者作了民意测验。艾森豪威尔在40名总统中名列第九。公众对艾森豪威尔时代的这种新热情与八十年代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潮兴起有关。也许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诚实、公正、坚定而又灵活的艾森豪威尔正好与造成了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的那些人形成了强烈对比。
S. Neal, “Why We Are Right to like IKE”, American Heritage, Vol.87., NO.1, pp.6162.
“新面貌”战略提出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美国学术界对它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但它毕竟是进入核时代以后美国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军事外交战略。即便它在实施过程中屡受挫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其影响还是极为深远的。曾严厉批评过这一战略的基辛格也不得不承认,有限战争只能用来补充“新面貌”战略,而不是代替它。
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187页。在以后几届美国总统所制定的战略中,人们仍能看见“新面貌”的影子。
周恩来与1954年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
——从多边外交视角进行的研究
本文原发表于《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954年召开的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不仅有苏、美、英、法等世界大国的参加,也有中、越、老、柬等亚洲国家的参加。通过谈判,与会各方成功地解决了亚洲国际关系中一个事关和平与战争的重大问题,这两条都是史无先例的。同时,这次会议也是新中国建立后首次参加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多边外交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前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到日内瓦后开展了活跃的外交工作,对会议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的研究表明,这次外交活动是中国多边外交的成功典范。
一、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的基本进程
关于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是在亚洲国际关系处于关键时刻召开的。至1953年底,在中国的援助下,越南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取得了优势,在中部和南方也控制了一些地区,法国在印支三国的殖民统治难以维持。出于国内政治压力,1954年初,法国拉尼埃(Joseph Laniel)政府不得不要求召开国际会议,寻求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途径。此时,东西方正处于冷战对峙中。美国艾森豪威尔(D. D. Eisenhower)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建立“欧洲防务集团”,以此重新武装西德。为了争取法国议会批准“欧洲防务集团”计划,美国不得不同意法国的这一要求。
在亚洲地区,虽然朝鲜战争已经停火,但美国仍想在这里“推回”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国务卿杜勒斯(John Dulles)力图帮助法国赢得军事上的胜利,推翻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由于法军在奠边府陷于重围,从1954年3月起,杜勒斯不断向法英两国施加压力,要他们接受美国的条件,通过“共同行动”扩大印支战争,使这场战争“国际化”。出于维护在印支的利益的原因,法国的拉尼埃政府不愿冒扩大战争的风险,特别是在谈判解决的道路尚未堵死前法国更不愿这样做。因此,印度支那三国何去何从就成为当时国际关系中引人注目的焦点。
印支日内瓦会议开幕以后,谈判各方的要求相去甚远。法国由于在战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它一方面让尚未完全取得独立地位的老、柬两国要求“入侵”的越军撤退。另一方面,法国表示只谈判越南军事问题,不谈判越南的政治解决问题。它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保大政权巩固地位,阻止越南以后的民族统一。此外,与会各国在监督机构的组成以及国际保证等方面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英国保守党政府认为,西方的军事干预只会迫使中国做出同样反应,印支战争可能成为另一场朝鲜战争,并可能最终导致新的世界大战。因此,英国希望谈判能取得成功,亚洲地区的形势能有所缓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是会议的两主席之一,他在会上挡住了美国的一部分消极作用,但英国并不处于当事人的位置,对会议的直接影响也就很有限。
美国政府希望会议失败,国务卿杜勒斯在会前就确定了阻挠会议成功的方针。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软硬兼施,要求法、英及西贡的南越政权采取强硬立场。会议进行了一个来月,有关方面只在进行法越司令部会谈这一程序问题上达成谅解,在所有实质性问题上都没能取得进展。作为会议两主席之一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V.M. Molotov)态度也比较强硬,6月8日他发表了一通讲话,全面批评拉尼埃政府的谈判立场,而且没有作任何灵活的表示。艾登对此非常失望,他当天通知美方说,在日内瓦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应做出安排使会议在一周或十天内结束。6月12日拉尼埃政府垮台,法国陷于政治危机。苏联记者向西方透风说,在法国政府危机结束以前会议不会有进展。莫洛托夫还询问越南外长范文同:如果会议“暂缓”有什么意见?实际上,苏联已准备接受会议的失败。美国代表团负责人,副国务卿史密斯(Walter B. Smith)14日向杜勒斯报告说,印支问题没有进展只有倒退。杜勒斯回电说,会议的终止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次日,朝鲜问题日内瓦会议因美国的破坏而失败。16日,杜勒斯说,如果印支问题达不成协议,而法国又有一个得到议会信任的政府,并认为必须坚持斗争,美国准备迅速做出反应。
Department of State, U.S.A.: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52—1954, Vol.16, (以下简称 FRUS) p.1110, p.1117, pp.11461147,p.1167; James Cable, The Geneva Conference of 1954 on Indochina,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1986,p.93. 曲星:“试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研究周恩来》,第256页。艾登和史密斯还准备利用休会时间去美国参加两国首脑会谈,商讨有关亚洲问题的新对策。美国的打算是,利用会议的破裂,对印支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此时,印支日内瓦会议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在这关键时刻,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会议上发挥了主导性作用。13日晚他和莫洛托夫、范文同就形势及下一段谈判方针举行了商讨。14日,周恩来致电中央说,准备向对方指出,双方司令部代表会谈是初步成果,“应扩大此成果继续讨论下去,说失败是错误的。应该使我方这种坚持积极态度的精神给世界造成印象:我方一向是现在仍然是积极的希望迅速达成协议的,并且是主张根据已有的共同原则继续讨论求得协议的”。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力平和马芷荪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82页。
在征得苏越两国的同意后,周恩来在6月16日紧急会见了艾登,17日又会见了法国外长皮杜尔。周恩来向他们表示,中国不愿看到印支会议也发生破裂。“中国愿意看到老挝和柬埔寨成为像印度那样的东南亚型的国家,我们愿与之和平共处。”他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愿意尊重老挝和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统一。只要外国军队从印度支那撤出,越南军队就可以从这两国撤出。16日,周恩来在限制性会议上提出新建议,指出印支三国情况确有不同,应有不同方式处理。周还表示已经注意到柬老两国政府有着自卫的需求,对此可以适当考虑。周恩来的谈话实际上提出了老挝和柬埔寨中立化的新建议,这使艾登受到很大的鼓舞。18日法国方面表示,周的建议中包含着“可以接受的因素”。老挝代表认为,周的建议中有“进一步可以讨论的基础”。柬埔寨代表也“对中国人表现出的妥协精神感到满意”。就连史密斯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新建议是克制的和合理的。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85387页;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6567页;FRUS, 1952—1954, Vol.16, pp.11821183. p.1201, p.1207.老柬中立化方案创造了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新的谈判空间,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17日,法国议会选出了新总理孟戴斯弗朗斯(Piere MendesFrance),周恩来在6月23日赶到伯尔尼同他见面。除了老挝和柬埔寨中立化问题之外,周还提出了分两阶段处理越南军事与政治问题的建议,并表示可以考虑承认西贡政权。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法越双方开始高级别的秘密会谈。6月21日,周恩来宴请了柬埔寨和老挝代表团,要求他们同越南方面进行直接接触,老挝外长萨纳尼空对中国的调解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FRUS, 1952—1954, Vol.16, p.1234, p.1240, pp.12111212, p.1214.老柬两国的积极反应表明对方战线出现了松动,这对于谈判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但实质性的进展仍然有限。休会三周后,英、苏、中、法外长回到日内瓦。他们发现与他们离开时相比,局势没有显著的变化。7月13日,范文同在周恩来敦促下向法国表示,越方可以接受法方的建议在北纬16度线划界。
曲星:“试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研究周恩来》,第258页。但是法国坚持以北纬18度线划界。此外,在越南的大选问题上、在老挝的划界和老、柬两国的政治解决问题上,在国际监督委员会的组织问题上,与会各方的分歧仍然很大。
由于孟戴斯弗朗斯上任时曾向议会保证,7月20日以前如果达不成协议,他将辞职。7月11日,孟戴斯告诉美国驻法大使狄龙(C.Douglas Dillon),如果不能达成停战,法国可能反应强烈,唯一的出路就是战争的国际化,美军应迅速投入帮助法国。
FRUS, 1952—1954, Vol.16, p.1136.17日,艾登再次对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悲观。在会场外进行斡旋的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Krishna Menon)也开始感到悲观。同一天,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向国内报告说,“最近三四天共产党方面,特别是莫洛托夫的态度又强硬了许多”。18日下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电台和电视台在21日预留时间,以便在会议失败时“向公众解释局势的严重性”。同时,杜勒斯加紧策划建立军事同盟,试图在会议失败后扩大战争。
FRUS,1952—1954, Vol.16, p.1420, p.1436, pp.14381439.
会议又一次面临破裂的局面。为了将谈判重新引导到互动反应、相互让步的局面,周恩来全力投入更紧张的外交活动,13日他在会见孟戴斯弗朗斯时指出,有关分界线的分歧必须解决,他要求法方对越方的新建议做出反应,“如果法方肯在原有立场上前进一步,越方是愿意以更大的让步来迎接让步的”。在周恩来的调解下,法国迅速做出了反应,双方最后在19日晚就划界问题达成妥协。周还派李克农会见英国外交官,要英国向法国转告,协议中必须确定越南大选的时间表。法国后来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让步。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99页;FRUS,1952—1954,Vol.16, pp.13681369,pp.13731374.
7月13日,杜勒斯到达巴黎同艾登、孟戴斯弗朗斯商讨美国可能采取的政策。很快传出了西方要加快建立东南亚军事同盟的消息。由于这一问题涉及中、越未来的国家安全,17日,周恩来对艾登说,美国正在组织东南亚条约,中国愿意参加对柬、老和南越三方独立与自由的保证,但是如果这三国被列入该组织,那一切情况就改变了。艾登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经过与美国的协商,19日,他派英国外交官哈罗德·卡西亚米会见张闻天副外长,保证印支三国不会成为东南亚条约的成员。18日周恩来再次会见艾登,提出了国际监督委员会由印度、加拿大和波兰三国组成。这个建议突破了莫洛托夫原来拒绝让北约成员加入的设想,使美国不得不放弃它在该问题上阻挠达成协议的立场,解决了一个久拖不决的重大问题。17日周恩来还会见了柬埔寨外长泰普潘,要求柬埔寨政府接纳抵抗力量。周向他指出,如果让美国在柬建立军事基地或接受美国军事教官,其后果将非常严重。周的这些话使柬、老两国对会议破裂的局面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James Cable, The Geneva Conference of 1954 on Indochina, p.119; FRUS, 1952—1954, Vol.16, p.1420.
周恩来还积极介入了有关老挝问题的最后谈判。7月17日,越老双方就老挝的集积区问题进行最后谈判,但是未能取得成果。老挝方面抱怨越南想要得到半个老挝。18日周恩来再次同萨纳尼空会谈,提出老挝抵抗力量的集积区可在丰沙里、桑怒两省及伦不拉邦部分地区。这一建议是符合老挝抵抗部队现有力量的。19日周恩来会见孟戴斯弗朗斯,修改了我方有关行政权力的建议,并同意法国在老挝保留一个基地,条件是法国将这个基地移到南部地区。
FRUS,1952—1954, Vol.16, p.1405, p.1449, p.1466.周恩来的这些建议为老挝问题的解决扫除了障碍。
在印支日内瓦会议两次面临破裂的关键时刻,是周恩来积极主导了会议的进程。在多边谈判中,使冲突降级的主导作用必须通过实施正确的谈判战略表现出来。周恩来在采取行动的时机,挑选谈判的对象,选择可以突破的问题,促使对手做出反应的方式等方面表现得极其出色。正因如此,他才能力挽狂澜,解决了会议两主席艾登和莫洛托夫无法应付的难题。
二、周恩来对与会各方的主导与协调
印支日内瓦会议是一次非常独特的多边外交会议,参加会议的八国九方分成东西方两个集团,而在这两个集团中,各方的利益又有明显差异。多边外交的复杂性在于与会各国不仅要维护本国的利益,还要维护集团其他成员的利益和集团共同利益。当然,为了使合作具有空间,还要兼顾对立集团的利益。日内瓦会议的进程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多边外交的这种复杂性。
中、苏、越三国具有联盟关系,他们在会议上同处一个集团。三国虽然在缓和紧张局势,实现印支停火的基本目标方面有共同利益,但是,在实现停火的迫切性,老柬两国政治前途,以及一般目标的取舍等方面也有不同的利益。越南在日内瓦会议上的行为实际上表明,它最终将共同利益放在较优先的地位,并对自身利益进行了克制。它做出的这一正确选择,同周恩来引导越方认清全局,强调维护我方共同利益是分不开的。
中共中央对于日内瓦会议非常重视,书记处和政治局多次开会进行讨论。1954年3月初,中央原则批准了周恩来精心准备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要求利用这次会议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文件指出,即使美国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和平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协议,甚至是临时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中央强调“要力争不使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可以看出,中国对于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愿望是十分迫切的。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56页;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3月中旬,周恩来致电胡志明和越共中央,提出形势对越南进行外交斗争是有利的。关于具体方案,周恩来指出:“如果要停战,最好有一条比较固定的界限,能够保持一块比较完整的地区。”在划界问题上,周恩来说这条线越往南越好,但是“一方面要对越南有利,一方面要看敌方能否接受”。显然,中国是把争取停战和实现南北分界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上。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82页。
苏联希望印支战争不要扩大,但没有解决问题的紧迫感。赫鲁晓夫认为中、朝、越一起参加会议就是胜利,社会主义各国利用这次机会阐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和方针政策,“对有关事态作些声明、解释和澄清,就是一种政治收获。如果工作进行得顺利,能阐明和解决某些问题,那就算有益的收效了”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539页。。
苏联的低调表明,他们的主要利益和兴趣在欧洲。在印度支那,苏联并不面对冲突扩大的直接危险,所以它希望通过日内瓦会议影响法国政局,打击法国的主战派势力。谈判期间,莫洛托夫一直坚持一些并非很重要的条件,如越南军事与政治问题不可分阶段解决,国际监督委员会必须由东欧和亚洲中立国组成等。6月上旬,莫洛托夫在回了一趟苏联后立场更为强硬。史密斯认为,莫洛托夫想对法国的政治危机施加影响,苏联真正担心的是法国可能批准“欧洲防务集团”。莫洛托夫要让支持“欧洲防务集团”的拉尼埃政府倒台,“减轻苏联在欧洲受到的威胁”。由于轻视民族主义国家,莫洛托夫对柬埔寨和老挝两国在会议上的作用估计不足,对他们提出的意见不予理睬。在周恩来已就老挝、柬埔寨问题提出妥协方案之后,莫洛托夫还在坚持“不能同意越南的形势与老柬不同,后两国只是有些特殊性要考虑”。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53页;FRUS, 1952—1954,Vol.16, p.1160, p.1169, p.1193.苏方的这种民族利己主义态度无助于越南采取较为克制的立场,也使周恩来的处境更为艰难。
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利益最直接的一方。在3月底4月初,胡志明等人先后到北京和莫斯科,就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与中苏两国举行会谈。由于奠边府战斗进行得不顺利,越南领导人对于战争的结局没有把握,武元甲也信心不足,说:“损失太严重了。”胡志明向周恩来提出,如果越南最后抵挡不住法国的话,希望中国同意越军在必要时退入中国境内。他还希望中国能派出志愿军到越南同法军作战。越方的这种要求显然是中国难以接受的。而且,这也表明,越方对中国面临的困难缺乏认识,对于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没有足够的估计。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54页;Douglas Pike, Vietnam and the Soviet Union, Anatomy of an Alliance, Boulder and London, West View Press, 1987, pp.3940.
越共中央最初定下的方案是南北划界。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使越南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越南方面的要求也因此抬高,提出了法国撤出所有军队、通过选举实行国家统一等要求。越南认为,印支三国面临的问题“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类型上的不同”,他们希望让越军继续留驻在老挝和柬埔寨,以期建立受其支配的“印支联邦”。越方的一些人还低估了战争扩大化与国际化的风险,认为不必向法国做出大的让步。正如胡志明在1954年7月15日对越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说的那样:“一些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想不惜一切代价地打下去……他们赞成军事行动却忽视了外交行动……他们向敌人提出了不可接受的过分条件。”
罗纳德·基思:《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74页。
为了确保最重要的共同利益的实现,周恩来全力推动会谈向兼顾我方各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尽管周认为莫洛托夫态度比较僵硬,“对什么问题都用一个‘不’字来对付。美国人提一个方案,他说‘不’,英国人出来打圆场,他也说‘不’”。但周恩来还是与莫洛托夫耐心磋商,满足苏联的利益要求,在拉尼埃政府倒台后才提出了老、柬两国中立化的构想。中越柳州会议后,周恩来再次到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会谈。这时苏方才表示应迅速争取和平,实现停火,如果在划分集结区问题上坚持孟戴斯弗朗斯难以接受的条件,“则易为美国所乘,法国主战派势力又会得势,对解决印支问题不利,对越南不利”
夏衍:“永远难忘的教诲”,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22页;韩念龙、薛谋洪:《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出版社,1988年,第6667页。。当然,这对苏联也不利,因为这些主战派势力更倾向于接受西德的重新武装计划。
多边外交理论认为,一个有效的领导者必须具有卓越的分析能力,以便找到一种潜在的构想,同时也要有说服能力,使其他各方确信应当接受这一构想。
P. Terrence Hopmnn,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and re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6, p.266.周恩来在日内瓦充分表现出了这种高超的外交能力和艺术。首先,周恩来对越南的立场和要求总是表现出理解和同情,高度尊重他们要求统一的民族感情。他对越方的事务从不越俎代庖,从不代替他们同西方谈判具体问题。法国大使肖维尔指出,越南在会谈中有相当大的自由,只是在越方的要求超过了法国可能接受的限度,中国才会加以干预。
FRUS, 1952—1954, Vol.16, p.1322.
其次,周恩来是以对形势的准确分析和从越方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说服对方。在7月上旬举行的中越柳州会议上,他分析了美国害怕所谓中国的扩张,绝不会允许越南民主共和国取得大规模的胜利的想法。他指出:“如果我们要求过多,印度支那不能达成和平,美国必然干涉。”周恩来的论证使越共中央相信,越南已经到了十字路口,必须和法国搞好,争取和平,从而与中国达成了共识。
其三,对有些方针的调整主动承担责任。在柳州会议中,周恩来在老柬两国问题上表示,中方要对没有在事先搞清楚印度支那的组成情况负责。同时他也指出,印支是由三个国家组成的,实际上都是民族国家,几千年来都是这样。这样做既给了越方面子,又坚持了正确原则,越方也比较易于接受这一立场。
李海文:《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对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作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香港大学,1996年;《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94395页。
最后,在说服越南做出必要妥协的同时,周恩来也坚定地维护了越方的重大利益。他在会议期间多次强调不允许美国在印支建立军事基地、不得使用美军顾问,以及老、柬两国不得加入军事同盟等立场。这些问题事关停战后越中两国的基本安全利益,老挝和柬埔寨能否保持中立,以及越南以后的统一斗争。越战历史表明,老、柬两国的中立制约了美国的军事干涉,每当它破坏这两国的中立,它就会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
三、周恩来对舆论环境的高度重视
由于多边外交有较多国家参加,谈判进程比较公开。因此,它相对说来具有较高的透明度。这一特点使得参加国在谈判中要谨慎行事,但也可以利用新闻媒介、动员国际舆论及别的方式来形成公众压力,向其他与会国施加影响。
Winfried Lang, Lessons Drawn From Practice, Open Convenants, Openly Arrived, in International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 approaches to the management of complexity, ed. by I. William Zartman, San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4, pp.20202.与双边外交相比,多边外交可能更多地受到国际舆论环境的影响。
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非常重视舆论的作用,他不仅在中国代表团中专门安排了新闻发言人,而且还多次指示《人民日报》刊登配合会议的报道。6月上旬,周恩来批评了《人民日报》对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将访华的消息报道得不及时和不显著。他指示:“今后关于这类新闻以及日内瓦会议重要报道如何刊登问题,外交部与中宣部应经常联系与研究,以便密切地配合外交斗争。”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58页。
周恩来还积极地同各国媒体打交道,对他们施加影响。早在4月1日,周恩来在祝贺法国《人道报》创刊50年时致电该报主编时说:“我们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并主张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和法国人民在内,应该和平相处。”向法国公众表示了中国希望和平共处的愿望,他在日内瓦也多次发表声明,表达中国政府谋求和平的积极态度。在日内瓦会议处于关键时刻的6月22日,周恩来会见印度记者说:“希望在最近的三周内,印度支那交战的双方……达成光荣的停战协议,而与会的其他各国的责任,应该是推动和支持,而不是阻挠和破坏双方停战协议的达成,同时,我们对于会内、会外某种势力企图使印度支那战争化的阴谋,不能不提高警惕,而这种阴谋正是科伦坡会议所反对的。”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758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册,第18941895页。
6月下旬,周恩来在日内瓦进行了大量外交活动,还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对此,各国记者进行了跟踪报道。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正日益独立地发挥国际作用,中国要求和平的愿望是真诚的。法国的《世界报》说,周恩来访问印度是“亚洲日内瓦会议的延伸”。6月28日,周恩来在新德里召开记者招待会,强调了和平共处、各国人民有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以及革命是不能输出的等原则。这次招待会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广泛反响,使亚洲各国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配合了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推动老、柬两国走中立化道路的活动,加强了亚洲各国要求和平与中立的潮流。
FRUS, 1952—1954, Vol.16, p.1251;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71页。
7月18日,会谈进入最后阶段。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秘密约见美联社记者托平。黄华指出,美国应对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做出保证。同时,他也透露,西方国家如同意印支三国不参加军事集团,不在三国建立军事基地,会议就有可能达成协议。托平据此发出报道说,中国正在施加压力使美国赞同停战协议,英法两国已在原则上表示同意。美国作为会议成员,有义务签字并保证协议的贯彻,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与否有赖于美国的态度。托平特地指出,他的消息反映了周恩来的观点。托平的报道使公众了解了谈判最后阶段的情况。更重要的是,面对舆论压力,美国政府很难再阻碍协议的达成。史密斯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说,他感到如果达不成协议,盟国会让美国来承担失败的责任。
FRUS, 1952—1954, Vol.16, p.1428, pp.14381439.
周恩来还注重引导会场以外的舆论环境,以此增进各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在日内瓦,周恩来会见了许多欧洲国家的政治家,向他们阐述中国的立场。他与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谈判的紧张阶段,他们几乎天天见面。通过梅农,周恩来从英法两国得到保证,他们将阻止美国在老挝和柬埔寨建立军事基地的图谋。周恩来与艾登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工作关系,这也与周重视发挥英国的作用有关。美国人一直对艾登不满,认为他受到了尼赫鲁的影响,而尼赫鲁则受到周恩来的影响。非常有意思的是,美国代表团成员、一贯持反共亲蒋立场的助理国务卿罗伯森(Walter Robertson)认为,他的顶头上司副国务卿史密斯受到了艾登的影响。
B. R. Nanda, Indian Foreign Policy, the Nehru Year,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6, pp.8788; FRUS, 1952—1954, Vol. 16, p.1281
周恩来访问印度以后,两方新闻界纷纷猜测,中印之间可能达成了关于科伦坡国家不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谅解。《纽约时报》在7月2日说,中印之间的默契对建立东南条约组织的设想,以及对英国提出的对印支提供洛加诺公约式的保证来说都是“凶兆”。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兰德尔认为,周恩来在6月开展的一连串的外交活动,使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吸引力对亚洲各国大为下降。
Robert Randle, Geneva 1954, the Settlement of Indochina War,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309.
四、中国取得成功的几点经验
周恩来在印支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经验,无论是对于指导实际工作,还是对于研究多边外交的理论都有重大帮助。多边外交起源于近代欧洲,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们普遍认为,传统的多边外交虽然复杂,但由于与会国具有相同文化背景,它的成功可能性还相对大一些。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由于情况已发生巨大变化,多边外交的理论和实践面临更大的挑战。
Gordon A. Craig and Alexander L.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Diplomatic Problems of Our Ti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83, p.165.从周恩来的成功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在印支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与各国代表团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耐心倾听与会各方的意见,特别是老挝和柬埔寨两国的要求,从而发现各方的基本利益和西力集团中的分歧,寻找各国普遍可以接受的共同点。正是在这一系列行动的基础上,尽管回旋余地有限,周恩来仍然发挥了他的杰出才能,提出了老柬两国中立化这具一有创造性意义的新建议,从而打击了美国的干扰破坏,分化了西方集团,将会议从破裂的边缘导向成功,实现了中央的与会方针。与双边外交不同的是,多边外交中存在着主导权问题。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行动表明,多边外交中的主导地位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在关键时刻积极发挥主导作用是维护本国利益和集团共同利益的重要途径。
第二,在日内瓦会议中,中国、苏联和越南三国既有集团的共同利益,也有各自的国家利益。三国虽然在会议中密切地进行配合,但在确定各种利益的优先权方面也存在着矛盾。苏联的利己主义态度,越南在外交事务方面缺乏经验,这些因素使矛盾变得更加难以处理。周恩来对苏越两国意图和利益的透彻理解,是他能够说服集团成员转变立场,兼顾眼前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键。这也表明,在多边外交中,集团成员虽然应当密切配合,但在重大问题上也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并力争将这种立场转化为集团的共同认识。
第三,1954年的印支日内瓦会议对于缓和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强中国与亚洲各国的相互了解和建立睦邻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在会议期间重视舆论影响和媒体作用,使我方收到事半功倍之利,使对手受到舆论环境的制约。多边外交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对舆论的成功引导不仅有助于形成有利的谈判环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弥补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加强谈判各国的互信关系。这些经验对当代中国外交也具有一定意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
*此文原发表于由刘同舜和姚椿龄先生主编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3》,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14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亚非各国人民的民族主义独立运动,一批国家在战后终于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桎梏,重新获得了主权地位。民族独立运动极大地削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势力和影响,成为战后世界最有力量,也是最重要的历史潮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同样,中共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也是非常明确的。由于当时对亚非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认识不足,因此中共当时也就不可能针对这些国家制定专门的政策。
在1949年1月18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有这样的规定: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附属的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①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第56条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这是被称为“另起炉灶”的一种政策,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是相配合的。
对于苏联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中央的指示说: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根据这一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共决定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不经谈判即可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对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坚持了“谈判建交”、“另起炉灶”的方针,其主要目的在于促使各国尽快切断同国民党政权的联系,破除有些国家试图推行“两个中国”政策的幻想。但同时这一方针也表明,在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是根据社会制度的异同来确定标准的。尽管《共同纲领》明确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制度和反华阴谋,但此时中国政府对曾经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新独立的亚非国家也没有区别对待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第514页。。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各国历史背景的不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同,以及社会内部的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不同,亚非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色彩,它们在独立后大都采取了西方国家为他们设计的社会制度,奉行的是中立主义的对外政策。长期处于游击战争环境下的中共很难了解各国复杂的国内形势,因此也就很难把它们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分别开来。
其次,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坚持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并因此获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一理论强调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民族和民主革命取得成功。因此,中共本能地怀疑那些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
第三,在“两大阵营”的理论下,战后复杂的国际形势被苏共领导的“左”倾思想方针掩盖了。苏联对亚非国家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中国对它们的看法。
1947年欧洲九国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成立时,日丹诺夫在报告中曾表示,苏联有同不同制度的国家合作的意愿。他说到,有一些国家是“同情”和“靠近”社会主义阵营的。日丹诺夫还列举了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埃及和叙利亚作为例子。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加剧,以及一些亚非国家采取了某种程度的偏向西方的政策,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开始对亚非国家采取了“关门”的政策。从1948年起,苏共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公开文件总是以批判性的语言提到这些国家。“同情”与“靠近”苏联的国家仿佛已经不复存在。这类公开文件通常还把亚非国家内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当作政治呼吁的对象,甚至不顾一些国家的具体情况,要求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国内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
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总论部分》,第6689页;不破哲三:《斯大林与大国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560页。。
1949年7月,正在苏联进行秘密访问的刘少奇要求斯大林介绍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7月29日,斯大林在一次会谈中对刘少奇及中共代表团说,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共以后多负担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的经验会对这些国家产生较大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和吸取。斯大林认为苏联在这方面起不到像中国那样的影响和作用,
斯大林的这一想法不久后便得到了贯彻。1949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和澳洲工会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在报告中说,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该报告仍然把已经独立的亚非国家说成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并宣传中国革命所走过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可能成为情形相类似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06407页。
这种向亚非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宣传武装斗争经验的做法,必然削弱《共同纲领》所宣布的中国愿意“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呼吁。这种情况表明,对于如何团结最大多数的亚非国家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共在国际政治理论方面需要突破苏联的教条主义束缚。
但是,中国在政策执行方面仍然是谨慎的。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只向越南提供了军事援助,越南人民此时正在为反对法帝国主义恢复其殖民统治而斗争。中国的援助大大加快了越南人民争取独立与解放的进程。
一、中国谋求和平与合作的努力
1. 寻求与西方和平合作,争取和平共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这一原则下,中国为谋求国际和平与合作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中国政府反对西方国家干涉中国的内政,但是中国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同西方国家合作的希望与可能。
1949年9月和1950年9月,苏联政府曾经两次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在美、苏、中、英、法五大国之间缔结一项加强国际和平的公约的建议,对于这一既能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又能有助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建议,中国政府明确表示积极支持,并呼吁西方大国接受苏联的这一建议。
1950年10月美国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把朝鲜战争的战火烧到中国的国门口。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和巩固新生政权,中国政府决定出兵朝鲜,并动员全国人民投入抗美援朝运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张起来。为了尽早结束战争,恢复朝鲜半岛和远东地区的和平,中国政府还以更大的热情推动世界和平运动。
1951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人们知道,我国和苏联及美、英、法等五大国对世界和平是负有主要责任的,这是因为这五大国在国际关系中起着特别的作用。当然,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对和平负有责任,但是,必须是这五个大国维护和平,世界和平才有可靠的保证。”
一星期后,《人民日报》再次指出,“中、苏、美、英、法五大国的和平合作,是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的决定环节。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爱好和平人民在人类历史的错误中所寻找出来的巩固战后世界和平的重要原则。”“五大国之间有和平合作,对于世界和平的前途是异常重要的。”这篇社论还指出,中苏两国政府一贯地坚持奉行防止战争和维护和平的政策,并且两国政府“不止一次地表示了愿与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的愿望”。
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50—1953年》,下卷,人民教育出
版社,1960年,第12901297页。
通过《人民日报》社论,中国政府表达了它同西方和平合作的真诚意愿,以及对五大国合作维护世界和平这一机制的高度评价。
尽管中国政府希望与西方和平合作从而实现和平共处的局面,但是中国政府也完全清楚,在朝鲜战争尚在进行之时,要实现这一目标是困难的。因此中国政府也把世界和平运动看作揭露美国在亚洲的侵略政策,呼吁西方各国人民抵制战争的手段。3月4日的《人民日报》还指出,美帝国主义集团“敌视并一再拒绝缔结五大国公约的建议”,使得“美英集团的侵略意图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面前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
《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50—1953年》,下卷,第1296页。
1951年6月,朝鲜战争作战双方宣布准备进行停战谈判。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不能因为战争而延误国内的经济建设。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藕春斋举行的一次中共党内会议上指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阶段里,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说:“除开必要的国防外,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设均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刘少奇还提出了“今年解决朝鲜问题”的设想。
《党的文献》编辑部编:《共和国走过的道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编,1953—1955》,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012页。刘少奇的讲话说明中国政府对朝鲜战争的发展趋势已做出了基本判断,党的中心任务将从巩固新生政权向发展经济转移,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内外政策会发生重大变化。1953年10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说道:“谁都知道,中国人民在解放了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是受威胁的环境下来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谁也都知道,中国人民认为全世界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中国人民从来就不想威胁任何人,不想侵犯任何人。可是,我们决不能容忍别人所加于我们的威胁和侵略。”
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总论部分》,第180181页。从周恩来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认为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高潮对和平环境有强烈要求,还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对和平共处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中国的对外政策开始了调整过程,它已经把争取和平共处的对象从“各国人民”转变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这一变化的含意是非常深刻的。
但朝鲜停战谈判进展得相当缓慢。1952年夏,因为美国坚持所谓的“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谈判陷入了僵局。7月,毛泽东指示中方谈判代表拒绝接受美国的遣返方案,他认为这样做“等于是结城下之盟,对我不利”。他决定采取强硬立场,不向美国的压力让步。
徐焰:《第一次较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第285页。尽管停战谈判无法取得突破,中国政府仍然坚持争取和平共处的对外方针。1952年10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郭沫若在发言中指出:亚洲及太平洋各国人民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争取与保卫和平。苏联和中国在大力从事和平建设的事实更说明了他们不要战争,因为和平建设与准备战争是不能并立的。郭沫若还说,中苏两国“屡次提出和拥护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议,他们已经用行动证明了他们和其他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能够和平共处的”。
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50—1953年》,下卷,第1315页。
1953年春,由于中朝两国采取了主动措施,朝鲜停战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加强了同西方寻求和平合作与和平共处的外交努力。周恩来在4月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深信,只要具有真正谋取和平的诚意,世界各国间的一切争端,都应该而且可能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取得解决,中国政府已在这方面表现了真诚的愿望,并坚持以相互协商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崇高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二集,第135136页。。
但是,由于美国顽固地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以及它执意在亚洲地区进一步扩大势力和影响,中国在朝鲜战争时期同西方大国和平共处的政策没能取得明显的成果。但是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对和平共处的原则的认识已经逐渐加强,它已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维护和平方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同中国有着同样的意愿,中国对外政策具有取得进一步突破的可能。
2. 中印在西藏问题上的争执
1949年以前,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就很紧张。其原因是印度政府当时奉行了英国殖民主义的老政策,试图使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1947年,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国大党政府从英国当局手中和平接管了权力。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尼赫鲁曾表示过独立后印度要完全割断同英国的联系,他还多次拒绝使印度成为英联邦成员国的建议。但是,独立后的印度又宣布留在英联邦内。这种状况表明,在独立之初,印度在对外关系方面与西方有着密切的联系
B. R. Nanda, India Foreign Policy, The Nehru Years,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6,
pp.2441, pp.131149.。
1949年春夏,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地区挺进。帝国主义分子乘机鼓动西藏的分裂主义势力,试图趁国民党政权垮台的机会,搞分裂祖国的“西藏独立”活动。为了阻止解放军入藏,西藏地方当局于7月18日发动了“驱汉事件”,他们以遣走“可疑”的共产党员为借口,迫使国民党政权驻拉萨办事处的人员和其他汉族人全部离开西藏。
在这一事件发生以前,印度驻拉萨代表团团长、英国人理查逊对西藏“外交局”局长札萨柳霞·土登塔巴说:“拉萨有许多共产党人,留他们在这里,将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他建议西藏当局做出驱逐汉人的决定。“驱汉事件”发生后,印度和西方新闻机构纷纷为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行为喝彩叫好。7月18日印度新闻社还挑唆说:“西藏从未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廖祖桂:《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第1215页。
针对西藏局势的发展,新华社在1953年9月2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西藏。社论说“驱汉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英、美、印度反动派勾结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举行这个‘反共’事变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反而进一步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新华社社论还说:“英印反动派为了吞并西藏,竟敢妄想否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侵略者在白昼说梦话。”社论警告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和干涉。”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册,第706708页。
1949年12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致电周恩来,表示印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西方国家和印度没有停止对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支持。他们通过理查逊之手向西藏地方当局提供了“可装备一万多人”的枪支弹药,试图帮助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用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解放军在1949年秋已经受命准备进藏。1950年1月,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下令解放军用四个月的时间作准备,争取先占领入藏战略要地——昌都。显然中国政府担心外国侵略势力可能加紧活动,这将使西藏形势变得更为复杂。
1950年3月,西藏地方当局表示愿同中央政府进行“平等”谈判。为了使西藏解放得以和平实现,中央政府同意谈判,但是也坚定和明确拒绝了西藏当局的独立企图。然而,西藏地方当局派出的谈判代表却迟迟不到北京,滞留于新德里达数月之久。这种奇怪现象同印度及西方的干涉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它使中国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当局的谈判无法尽快进行。
1950年8月22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会见了周恩来总理。次日,毛泽东电告负责进军西藏的中共西南局说:“现印度政府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惟希望和平解决勿用武力。”毛泽东还说,英国原不许西藏代表来京,现已允许,中央“正采取西藏代表团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这份电报表明,在朝鲜战争发生后,英国和印度的态度有了一点变化。中国政府仍坚持自己既定的进军西藏的计划,毛泽东告诉西南局说,望于十月占领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8月29日,毛泽东指示中国外交部向印方透露,中国政府希望西藏代表团尽早到达北京谈判,因为人民解放军即将向西藏进军。10月11日,毛泽东再次让驻印大使袁仲贤转告印度,“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团九月来北京谈判;该团故意拖延……现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前进”。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475476页,第489页,第549页。
10月19日,解放军攻占昌都。21日印度政府照会中国,对中国的军事行动表示不满,并把这一问题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一事相联系,试图以此为条件,换得中国接受它对西藏事务的干涉。10月26日印度外交国务秘书梅农约见中国参赞申健,对中国进军西藏表示“遗憾”,甚至指责中国进行侵略。10月28日,印度再次照会中国政府,声称中国军队进军西藏的决定对印度是最为“惊异与遗憾的”。印度政府为西藏当局代表团迟迟不到北京辩护,并说“在目前的国际情势下,中国军队入侵西藏不得不被认为是可悲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册,第165167页。
印度政府的公然干涉激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他指示中国外交官对印度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他说,应告诉印度,“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627页。30日中国政府复照印度政府,重申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并重申了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疆的原则立场。照会也指出,中国政府并未放弃同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希望,“可是无论西藏当局愿否进行谈判及谈判得到如何结果,均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问题,不容任何外国干预”。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册,第164165页。
11月1日,印度政府再次照会中国,指责中国在西藏的行动大大增加了世界紧张局势和导向大战的趋势。照会在为印度干涉中国内政进行辩解的同时还表白说,印度对西藏没有政治和领土方面的野心。但实际上印度这时正在悄悄地支持西藏地方当局向联合国呼吁,要求联合国出面干涉西藏问题。11月16日中国政府又复照印度,严正指出印度政府企图影响和阻止中国政府在西藏行使国家主权,对此中国不能不感到惊异。照会说,印度曾屡次表示过它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与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中印友谊,以及制止世界走向战争的愿望。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正是为了保障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一切愿意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国家首先应该在这一问题上表示出他们对于中国的真正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册,第177179页;P. C. Chakravarti, India’s China Polic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3132.
中国政府坚定的立场及昌都战役的迅速结束,使英国和印度政府不能不意识到,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不会有什么结果。加之这一时候中国已经投入抗美援朝,出于对战争进一步扩大的担心,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11月下旬,英国和印度让联合国推迟了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虽然印度和西方的报刊仍在指责中国的西藏政策,要求其政府采取“有力”行动,但有关国家已开始转变方针。
1951年春,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韩德逊对西藏地方当局官员夏格巴说,同中国政府和平谈判是上策,如果采取战争的办法,现有的内部权力必将丧失。英国方面也表示,西藏当局想在独立问题上得到英国的援助是不实际的。西方国家一后退,印度也就自然跟着他们后退了。印度外交国务秘书梅农在会见夏格巴时说,西藏至少要在表面上承认是中国领土,在谈判中争取西藏内部有更多的权力,这样印度可以从各方面给予援助;如果一味强调独立,谈判一旦破裂,乃至发生武装冲突,印度就无法进行援助。梅农的这番话表明,尽管印度没有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图,但它已不得不改变公开干预的政策。
1951年3月21日,周恩来在会见印度大使潘尼迦时指出,中国对西藏的政策是和平解决,以便解放军和平入藏保卫边疆。周恩来提出,达赖已跑到中印边境地区的亚东,有人正引诱他去印度。如果达赖不走,经谈判解决,达赖的地位可以保持,中印关系可以进一步增进;如果达赖离藏去印度,就有损于中印关系。周恩来说,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对西藏的和平解放是有影响的。印度方面后来表示,印度不鼓励达赖离开西藏,可以劝他不去印度。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印度仍在搞两面态度,但中国政府的行动已经有力地减少了外部势力的影响。5月23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定在北京签字。8月,达赖从亚东返回拉萨。
廖祖桂:《西藏的和平解放》,第4950页,第7273页。
中国反对任何外国干涉自己内政的原则立场不仅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增进了同亚非民族国家的相互了解,为中国同这些国家进一步发展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3. 中印关系的改善
朝鲜战争发生后,亚洲地区的国际形势日益紧张。一些民族主义国家对战争有可能扩大十分不安。印度一开始在联合国表决时对谴责朝鲜“侵略”的提案投赞成票,但在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战争的行动后,印度开始担心中国的反应。1950年7月,印度大使会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时说,印度认为必须使朝鲜的冲突局部化,并把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解决。潘尼迦还指出,在处理朝鲜问题时,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应该恢复,这样苏联也可结束其对安理会的抵制。7月13日,尼赫鲁总理就这一想法向美苏发出呼吁,中国政府对印度的这一立场表示欣赏,但美英立即拒绝了印度的提议。
George N. Patterson, Peking Versus Delhi, New York: F. A. Praeger Publisher, 1964, pp.106109;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112页。
1950年10月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以后,印度加强了外交活动。12月初,在志愿军给予美军沉重打击、美军仓皇向“三八钱”以南撤退时,印度和阿富汗、缅甸、埃及、印度尼西亚等十三国向中国和朝鲜发出呼吁,要求中朝军队不进军“三八线”以南地区。12月6日尼赫鲁在议会中指出,在朝鲜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对中国人民都是有着极大意义的,印度政府的一贯态度是,朝鲜问题只有与中国人合作才能解决。
1951年1月11日,由印度、伊朗和加拿大三国代表组成的联大“朝鲜停火三人小组”提出了立即停火的建议。17日中国政府指出,先停火再谈判的建议只是为美国争取喘息时间。中国提出了自己的反方案,并要求召开由中、英、法、美、苏及印度和埃及参加的七国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由于西方舆论指责中国拒绝谈判,印度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指出,中国没有关上谈判大门。24日,印度、埃及等12个亚非国家提出建议,由美、苏、英、法、印度、埃及的代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会晤,以便进一步了解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并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其他远东问题做出进一步安排。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卷,第321322页,第373374页,第383389页。
1月30日,印度等12国的这一提案因美国的反对而遭到否决。印度代表在批评美国政府的态度时指出,美国拒绝该建议就意味着“不停火、不谈判,也不和平解决”。印度代表在辩论中还指出,中国对朝鲜战争的干预“并不是出于扩张中国的领土或势力的意图,而是出于害怕中国自己的领土完整受到损害”。完全可以看出,印度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抱有一定的同情和理解。美国在拒绝亚非国家提案之后,于1月30日及2月1日先后在联合国政治委员会及联合国大会上抛出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案,并操纵一些国家投票通过。印度两次都投了反对票,印度的这种立场有助于世界舆论了解朝鲜问题的真实情况。2月2日,周恩来对印度及其他一些亚非国家不顾美国压力投反对票和弃权票的行动给予了积极评价。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卷,第383页,第392394页。
印度在朝鲜问题上执行的是中立主义的方针,这一方针有助于防止战争扩大,有助于冲突各方谈判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印度的这一方针影响了一大批亚非国家奉行类似的中立主义政策,从而削弱了西方对中国封锁、孤立政策的影响。正因如此,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印关系的改善与发展。1951年1月26日,毛泽东出席了印度大使为印度国庆举行的招待会,并在招待会上发表了热情友好的祝酒词: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了和平而努力。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78页。毛泽东的这一行动表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为了使朝鲜问题得到和平解决,中国曾经多次通过印度向美国方面传递信息,并提议印度参加“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出席解决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等,这都表明中国对印度政府是非常信任的。
印度政府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上也起了积极作用。1950年9月19日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劳氏在发言中要求恢复中国的席位,他说联合国应当“容纳抱不同政策和理想的各种政府制度”。印度代表在联合国还指出:“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民众的一个国家不能加入世界组织,我们即不能认为该组织有代表性。一个自由独立的中国与印度并肩迈进,将成为亚洲最有力量的稳定因素。”1953年,印度代表再次呼吁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并强调说不让中国政府占有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实际上意味着剥夺五亿人口的权利。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卷,第11691171页,第13871388页。
此外,印度政府在缔结对日和约问题上的立场也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欢迎。1951年7月美国政府正式抛出了由它一手把持制定的结束对日战争的和平条约草案。这一草案既不接受苏联、中国等主要战胜国的原则性主张,也不接纳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修正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于1950年12月4日曾发表声明说,对日和约的准备和拟制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与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1951年1月,印度政府也曾表示它不能签订美国提出的对日和约草案,因此也不会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印度政府在给美国的照会中,还明确对美国声称的它有权控制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表示不满。印度指出,美国对这些群岛的继续控制“包含着远东未来纠纷和可能冲突的种子”,表示了它对美国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的反对态度。印度在这个照会中还指出条约草案在台湾问题上的规定“既不公正又非得策”。印度表示条约应该“将台湾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它也说,“这种归还的时间和方式或许可以是另外的谈判的题目”。
同上书,第316319,550557页。总之,印度政府的这些立场是对美国一手包办对日和约的企图的打击。作为当时一个有着重要影响的亚洲大国,印度的缺席无疑降低了旧金山和会的意义,削弱了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对于印度政府顶住美国压力,敢于拒绝参加旧金山和会的立场,中国政府予以高度的评价。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印度政府和缅甸政府拒绝签订对日和约,并拒绝出席旧金山和会的态度是“中国人民欢迎的”。社论指出印缅两国的“明智决定无疑反映在了亚洲人民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意见”,将受到亚洲各国人民的欢迎。社论还指出,印度和缅甸的行动跟苏联和中国的行动一样,证明帝国主义政府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卷,第562584页。正是印度政府这一系列坚持中立、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政策,使中国政府看到了民族独立国家在当代国际事务中的重大作用。
印度在亚洲国际关系中所遵循的和平与中立的对外政策使中印双边关系有了很大的改进。1950年和1951年,印度发生了粮荒,需要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但美国政府借此机会向印度施加压力,试图使印度放弃中立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先后6次同印度政府签订合同,向印度提供了66万吨粮食,帮助印度渡过了难关。中国的这一行动得到了印度各界人士的好评。在这一时期中,印度许多地方成立了印中友好协会,中印两国人员互访也逐渐增加。
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页。
4. 中缅关系的发展
缅甸是中国的另一个邻邦,它在1947年获得了独立。独立后的缅甸政府一度希望和西方国家尽可能地在政治、经济和防御等领域进行密切的合作。1947年缅甸和英国签订了防御协定,1949年由副总理奈温率领的代表团出访了英美两国。他们向华盛顿和伦敦表示,缅甸愿意加入拟议中的太平洋地区安全条约,并要求购买武器。但英美两国对缅甸的要求没有做出积极的反应。
F. N. Trager, Burma, From Kingdom to Republic, New York: A. Praeger Publisher, 1966, p.2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缅两国关系也是较为冷淡的。缅甸领导人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没有多少信任感。总理吴努在1949年10月说:“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不能是亲密的。新的中国政府似乎倾向于向我国的共产党人提供道义支持,并显然地把我们看成西方的走狗。”
Richard Butwell, U Nu of Burm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172174.另一方面,由于2000多名国民党残兵败将逃入缅甸境内,中国政府对缅甸是否会严格按国际法解除国民党军队的武器也有怀疑。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1949年11月29日发表声明说,国民党残部正逃向越南及其他和中国国境毗连的地方,准备把这些地方作为他们等待时机卷土重来的据点。声明向有关国家政府郑重指出,不管战败的国民党军队逃到什么地方,中国政府“都保有权利过问这一事实,而容留国民党反动政府武装力量的任何国家的政府必须对此事实负责,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集,第87页。
然而,缅甸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表示了积极的态度,吴努在1949年12月要求印度推迟行动,以便让缅甸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同月,吴努总理宣布缅甸将遵循一条独立的路线,不同任何实力集团结成联盟,不倾向英美,也不倾向中苏。
但是缅甸混乱的政治和经济局面迫使政府继续向西方寻求帮助。正如吴努自己说的那样:“理想的方针是保持严格的中立,但缅甸需要外国资本和技术援助来发展经济,把国家从因叛乱而产生的灾难中拔出来。”1950年3月,缅甸政府同美国签订了经济援助协定,美国同意向缅甸提供800万美元的援助。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缅甸在联合国投票赞成美国武装干涉朝鲜战争的提案。
Trager, Burma, From Kindom to Republic, p.219; Butwell, U Nu of Burma, pp.172177.
出于各种原因,缅甸对新中国抱有疑虑。1951年3月缅甸副总理吴觉迎说:“小国总是不信任大国,尤其是那些邻近的大国。很多年来,每个缅甸人都不信任中国,不管中国是在毛还是在蒋的统治下。”他说缅甸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但是承认在某一天中国有入侵我们的可能性”。
Trager, Burma, From Kingdom to Republic, p.232.
虽然缅甸政府存在这种心理,但中缅关系在1951年还是有了明显的发展。缅甸和印度一起提议联合国考虑中国的关于朝鲜停战的主张;缅甸政府拒绝投票支持污蔑中国“侵略”的决议,它还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此外,缅甸也拒绝了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缅甸政府的这些立场表明,中国投入抗美援朝战争以后,亚洲紧张的国际形势使缅甸进一步调整了对外政策。它的和平中立政策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评价。
更为重要的是,缅甸政府逐步改变了对进入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残部的默许和容忍态度。
当时,逃入缅甸的国民党军队在原第八军军长李弥的率领下在中国和泰缅边境地区活动。由于他们的活动得到美国的支持,加之缅甸军事力量的不足等原因,在一段时期里,缅甸政府对这一事态采取了保持沉默的方针。然而,这种状况不仅损害了缅甸的国家主权和边境地区的安定,也给中缅关系的改善造成了很大的困难。195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制订和执行了一个“纸行动”秘密计划,将大量武器装备从台北和冲绳美军基地经曼谷空运到李弥残部在缅甸北方的基地。到1951年底,李弥残部已扩充到6000余人。同年4月和7月,这支军队曾两度窜回中国境内进行武装袭击和骚扰活动,在遭到解放军回击后又逃入缅甸。
John Prados, President’s Secret Wars, CIA and Pentagon Covert Operations Since World War Ⅱ,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 1986, pp.7378.
1952年1月,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公开指责美国援助国民党残部。但中央情报局并未就此罢休。美国一面否认缅甸的指责,另一面以更大规模向李弥残部空运装备,并从台湾空运700名军官加强这支军队。通过强征缅甸当地少数民族入伍,李弥残部在1952年发展到了12000人。1952年夏,李弥指挥这支军队对云南省进行了第三次窜扰。在再次遭到云南解放军痛击以后,剩下的残兵败将又退入缅境。他们同缅甸叛乱武装勾结,于1952年秋同缅甸政府军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此外,李弥部队进行强征和抢劫,严重侵扰了缅甸当地人民的生活和生产。
Prados, President’s Secret Wars, CIA and Pentagon Covert Operations Since World War Ⅱ, p.76.
缅甸政府曾在私下多次要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残部,并将他们运出缅境。但美国一直采取拖延策略。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共同安全法”,实质上是把经济技术援助同军事援助绑在一起进行,试图以援助为手段,迫使受援国,尤其是一些实行中立主义政策的受援国接受美国的“集体安全”政策,同美国建立某种方式的军事联系,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义务”。根据这一立法,美国政府也向缅甸施加压力,要缅甸接受有关条件。这显然不符合吴努政府寻求援助的目的。因此缅甸政府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吴努说,缅甸愿意同所有国家建立良好关系,愿意接受来自外国的援助,但不能损害缅甸的主权。他指出缅甸要执行“严格的中立政策”。结果是美国减少了对缅甸的经济援助。
Trager, Burma, From Kingdom to Republic, pp.315317.
1953年初,缅甸政府忍无可忍,调集政府军进攻国民党残部。3月,缅甸政府在联合国公开谴责台湾国民党当局侵略缅甸。由于美国拒绝支持缅甸的有关要求,吴努宣布停止接受美国的援助,显示了缅甸政府决心独立自主的勇气。4月23日,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下,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向缅甸境内的“外国军队”提供援助、使这支军队能滞留在缅甸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决议还要求各国尊重缅甸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立即解除国民党残部的武装,使其从缅甸撤出。
《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发言集》(第五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278页。
联合国决议通过以后,美国不得不改变策略,着手把近6000名国民党军队运出缅甸。尽管在中缅边境地区还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残军赖着不走,但他们对中国的危害程度已大大降低。缅甸政府这一时期采取的行动客观上配合了中国政府对李弥残部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气氛和基础。
5. 中国对亚非民族国家的新认识
在朝鲜战争时期,中国同西方大国谋求和平合作及和平共处的政策没有取得进展,但同印度、缅甸等一些亚非民族国家的关系却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一现象向中国领导人揭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关键可能就在于如何同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关系。在这一方面,中国的认识同苏联的国际政治理论慢慢地拉开了距离。
1951年9月,周恩来在一次政协会议上指出:“现在还被帝国主义欺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府,我们应该争取他们反对战争,赞成和平,即使是暂时的朋友,我们也要争取。”周恩来认为:“一切国家,一切可以争取的政府,都应该争取,即使是中立,哪怕是暂时的,在一个问题上的中立,对于人民来说也有好处。”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9页。
周恩来的这番话表明,随着朝鲜战争向持久作战转变,中国政府更加注重外交活动,并开始奉行更为灵活与现实的方针。同时它也表明,中国领导人正开始重新使用自己熟悉的统一战线方法来观察、分析及解决自身面临的国际问题。
1952年4月,周恩来在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了一些有重大意义的看法,他的这些思想为完善中国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周恩来的观点包括:第一,当前的国际问题“不是两大阵营的简单对立”。周恩来在会议上指出:新中国的外交“要分清敌我友,具体地分析一下,朋友方面以国家来分有两种:第一种是基本的朋友,第二种是一时的朋友,这后一种朋友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只能在某一时期成为朋友,有的可以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朋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
关于“第二种朋友”,周恩来说:“从国家性质来说,他们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但对战争他们不参加,表示中立,这是可能的。”周恩来认为,中国对这些国家不能采取敢对态度,“不要把他们挤到敌人的营垒里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253页。这里,周恩来说的“基本的朋友”显然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朋友的国家则是指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在周恩来看来,这些国家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它们并不在“敌人的营垒”里面。这一看法已经部分地突破过去那种认为在两大阵营之间不能保持中立的观点,间接地承认了在两大阵营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中立的国际力量。
第二,“资本主义世界不是铁板一块,我们要区别对待”。周恩来在会议上指出,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国家毕竟是少数。他以朝鲜战场的情况为例指出,“敢于坚决和中国敌对并走上战场的究竟还是少数”。他具体分析说:“同我国未建交,关系又较坏的国家,不能把它们看成同美帝一样。它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354页。
周恩来认为中国应该采取“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的方针来对待资本主义国家。从理论角度看,社会主义国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间存在矛盾并不困难,关键是面对复杂多样的国际矛盾采取什么政策。中国的“区别对待”政策同苏联此时的政策已有重要的不同。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在1952年10月召开的苏共19次代表大会上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但是他的报告只字未提要争取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在等待这些矛盾“不可避免地”导致它们之间的冲突。
第三,新中国要团结争取“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周恩来在会议上说:“同中国已建交的东南亚国家,过去是殖民地,现在不仅形式已经改变,有自己的国会与政府,同时人民的觉醒也使得帝国主义不能不改变过去对殖民地的一套办法,而由当地资产阶级来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有人说他们是殖民地,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他补充说,由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才是殖民地。周恩来此时的观点比他自己半年前在政协会议上的提法又进了一步。这一观点的提出,为一大批新独立的亚非民族主义国家摘掉了“殖民地”的“帽子”。
而马林科夫半年后在苏共的19大报告中仍把越南、缅甸、马来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伊朗、埃及、摩洛哥、叙利亚、突尼斯等情况完全不一样的国家纳入殖民地和附属国范围。这种现象表明,苏共在关于殖民地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方面的理论是相当混乱的。在他们看来,国家是否已经独立,殖民主义统治是否已经结束,并未改变问题的性质。
第四,周恩来说,外交工作“是以国家和国家关系为对象的”。周恩来在大使会议上特别向大家提出了两个问题,即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周恩来指出,中国要团结世界人民,但外交是“以国家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354页;《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总论部分》,第223224页。周恩来的这一思想为新中国的外交活动提出了一项基本原则,为中国外交严格按照国际法准则行事提供了保证。这一原则的提出为以后区别外交活动与支持革命者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的这些观点表明,中国领导人通过三年的外交实践,已经清楚地看到,亚非地区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虽然对中国有怀疑,甚至有时还有些敌意,但总的说来它们希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希望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反对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在这些方面,中国同他们有共同语言,有进一步发展关系、团结和争取它们的基础。同时,周恩来的观点也表明,中共在国际政治理论上已开始突破苏联的教条主义束缚,试图更多地以自己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为依据来制定对外政策。
1952年9月,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报告说,印度和缅甸间接表示了愿同中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并表示希望周恩来访问印、缅两国。据姚仲明分析,印度总理尼赫鲁本人也有意访问中国。毛泽东对这一信息持积极态度,他认为印、缅两国如正式提出要求,中国不大好拒绝。他要求正在苏联访问的周恩来与苏联领导人协商,征求苏联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看法。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544545页。
但苏联对发展同中立主义国家的关系并不感兴趣。斯大林实际上要强化“两大阵营”的理论,而且力图从经济基础角度解释这一理论。斯大林在1952年秋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的经济后果是,出现了“两个并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根据这一提法,马杯科夫在苏共19大报告中说,资本主义市场与社会主义市场是“没有联系的”,“这两个市场向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
斯大林和苏共的这种看法和估计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它加强了苏联对外方针中的“左”倾“关门”倾向。马林科夫的报告几乎点了欧洲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名,认为他们受美帝国主义的驱使,放弃了本国的独立外交政策。这一报告根本没有提到对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应如何区别对待。
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总论部分》,第214236页。
苏联的这种“关门”倾向也表现在具体政策和对外宣传方面。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在批评印度政府1952年11月提出的朝鲜战争停火方案时说:“说得好一点,你们印度人是梦想者和理想主义者,说得糟些的话,你们是讨厌透了的美国政策的工具。”而中国并没有对这个方案持这种苛刻的态度。1953年1月出版的苏联《真理报》和工人党“情报局”的《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杂志把缅甸政府说成是“仰光右翼社会主义者的乌合之众”,是“社会主义叛徒”。苏联对印、缅两国的这种态度显然不利于中国提出自己独立的对亚非国家的政策。加上朝鲜战争此时尚在进行,中苏两国之间如产生分歧会带来严重后果,因此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没有进行大的调整,同印、缅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事也就搁置下来了。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过程
1. 有利于中国调整政策的国际形势
从1953年春季起,国际形势中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为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国调整对外政策创造了条件。
首先,西方国家之间在亚洲政策及对华政策上的矛盾有所加剧。中国为结束朝鲜战争所作的重大努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中国政府认为朝鲜停战的实现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提供了可能,它证明一切国际争端可以用和平协商方法求得解决。亚洲各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也希望远东地区的国际关系能进一步改善。这些国家认为,没有中国的参加,要解决亚洲重大国际问题是不现实的。但是1953年1月上台的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却推行一种更为僵硬的和更为敌视中国的政策,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在朝鲜停战后坚持继续执行对华禁运和经济封锁政策,并且加紧支持法国,策划在印度支那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美国还在台湾海峡制造新的紧张形势。杜勒斯的这种政策在一些西方国家引起了不满。
5月12日,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在英国下院发言时说,他不相信中国只是俄国人手中的傀儡。艾德礼说,当初中国在蒋介石的统治下,是个“摇摇欲坠的国家,然而它却被放在安全理事会的位子上。但是现在,在一个不同的政府之下,它正在发展成一个很有力的国家,它有权利列为五大国之一”。艾德礼认为,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应该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他强调说:“我们常常被迫不和中国进行贸易,即使是和战争没什么关系的货物。如果我们被限制起来,不能有效地和中国进行贸易,同中国断绝关系,再加上铁幕的种种困难,我们就不能生存。因此中国问题的解决对我们有不亚于任何人的切身的利害关系。”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卷,第11481149页。
艾德礼的话表明一些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中国今后在国际事务上将起重要作用,它们愿与中国开展经济政治方面的合作。7月30日英国议会再次辩论中国问题。代理首相、财政大臣巴特勒表示不赞成美国阻止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政策。他说,联合国是“一个各国的大家庭,而不是一个反共联盟”。外交副大臣劳埃德也明确表示,“相信中央人民政府应当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唯一有争执的是时间问题’”。英国的立场得到了加拿大、印度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但是,由于美国的坚决反对,联合国又推迟了对这一问题的决定。10月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阻挠行为,并指出,许多重大问题,首先是亚洲问题,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是不能解决的。对此,英、法两国是十分清楚的。在1954年2月召开的四大国柏林会议上,英法两国坚持要求让中国参加关于印支问题的国际会议。英法的这一立场使中国清楚看到了“区别对待”政策产生的效果。
其次,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亚非民族独立国家与美国的矛盾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发展。朝鲜停战只是亚洲地区形势缓和的第一步,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和平协商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印度支那问题以及台湾问题。但是美国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在亚洲的势力和影响,顽固推行军事遏制政策和对抗政策,这不能不引起奉行中立主义政策的亚洲民族独立国家的不满。
1953年8月,苏联政府建议让印度参加有关朝鲜问题政治解决的国际会议。但是美国强烈反对印度与会。美国以朝鲜停战协定的有关条款为由,一方面在联合国竭力阻止印度出席会议,另一方面又通过外交途径向印度施加压力,要它“自愿撤销提名”。中国政府积极支持印度参加国际会议,9月13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批评联合国不让印度出席会议的决议。周恩来指出,其他亚洲国家参加有关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可使会议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从而使会议有成功的可能。周恩来强调,印度的与会对于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都将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周恩来再次提议邀请印度、印尼、缅甸和巴基斯坦等中立国参加会议。
FRUS, 1952—1954, Vol.11, pt. 2, Africa and South Asia, G.P.O.,Washington, D.C., 1983, pp.1496, 1500150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卷,第13561361页。
印度当然希望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但由于美国的阻拦,它得不到联合国成员国三分之二多数的赞成票。尼赫鲁愤怒地指出:“这是一种藐视亚洲的意志。”9月17日,尼赫鲁在印度国会中说:“尽管在过去几年中世界有了重大发展,世界上许多大国不知怎的还没有理会到:亚洲国家不论是怎样弱小,并不愿被人忽视,也不愿被人弃之不理,更不愿受人欺压。”他强调指出,世界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旧的压迫时代已经过去,而某种新的事物正在取而代之。“无论如何,这时的帝国主义除了零零落落地还在苟延片刻外,已成为过去了。”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卷,第13701372页。尼赫鲁的这番话反映了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反对帝国主义霸权政治的勇气和决心,反映了这些国家维护本国民族权利、争取更公正的国际秩序的愿望。1953年秋,印度和缅甸还共同展开了反对美国在亚洲扩大军事同盟、试图同巴基斯坦签订军事合作协定的斗争。中国政府对印缅两国的这一中立主义立场表示坚决支持。
朝鲜停战后亚洲民族独立国家的中立主义倾向的加强说明,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平共处及发展长期合作关系的可能性正在增长。
其三,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外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苏共新领导人以极为明确的态度强调对外政策中的和平与合作愿望。1953年8月8日,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苏联争取和平的斗争已经取得了成就,“在长期不断增长的紧张局势以后,国际气氛在战后年代初次有了一些缓和”。马林科夫还指出,苏联与芬兰、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等邻近国家的睦邻关系有所发展。他还表示愿意同阿拉伯国家继续加强友好合作。他还特意提到印度对朝鲜停战的贡献,说“像印度这样一个大国的立场对巩固东方和平有着巨大意义”。
马林科夫甚至还对一些西方大国的对外政策表示赞扬,他提出苏联要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关系。他说苏联“一贯执行着与外国扩展经济联系的政策”。马林科夫的这些观点同他本人10个月前在苏共19大所作的报告相比,可谓是面目一新,判若两人了。更值得重视的是8月13日《真理报》对马林科夫讲话的评价。这张报纸称这一讲话是苏联“对外政策方面的总路线”。
《现代国家关系史参考资料,总论部分》,第239270,271274页。
苏共和苏联政府放弃苏共19大报告中的一些极端观点,重新认识和积极评价民族独立国家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变化显然大大有利于中国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并且更坚定了中国领导人独立自主地形成和决定中国对外政策的决心。
2. 中印关于中国西藏与印度通商贸易问题的谈判
朝鲜停战前夕,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对国际政治中各种矛盾的性质与特点已经有了更清晰更准确的判断。1953年6月5日,周恩来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究竟世界主要矛盾是什么?两大阵营的对立当然是基本的,但是究竟具体表现在什么问题上?美苏之间的对立已经是剑拔弩张了吗?不是的。当前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战争与和平、民主与反民主、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四个方面。”他明确地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国人民以及反对美国战争叫嚣的人,都是和平的力量,都包括在和平统一阵线之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862页。周恩来的这些观点表明,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将利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多种矛盾,打破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
在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以后,中国政府把调整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作为对外工作中的主要任务。此时中印两国在国际关系方面有不少相同的主张和要求。两国在国际事务中进一步相互合作与配合的潜力很大。但是中印两国在双边关系方面还有一些重大的问题尚待解决。因此,如何改进同印度的关系,对于中国形成中的对民族独立国家的新政策也是一种挑战。
在中印双边关系中,双方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印度在中国西藏的一些特权问题。1952的年印度政府曾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关于印度在西藏利益现状》的备忘录,列举了印度的七项“权利”。它们是:1. 在拉萨驻有使团;2. 在江孜和亚东设有商务代表处;3. 在噶大克设有商务代表处;4. 在商业市场以外的地方从事贸易的权利;5. 通往江孜的商路上的邮政及电讯机关;6. 在江孜驻有军事卫队;7. 朝圣的权利。备忘录说这些特权是“由于惯例和协定而产生的”。
同年6月,周恩来在会见印度大使时表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和步骤,中印在西藏的关系要通过协商重新建立。同时,周恩来还明确指出:“英国政府与旧中国基于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了。”中国同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的现存情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周恩来在这里已经把问题点得十分清楚,对于那些因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产生的、损害中国国家主权的特权,中国将不能允许它们继续存在下去。在表明这一原则性立场的同时,周恩来也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暂时解决方案。印度对中国的这一立场没有做出直接反应。
由于根本性问题未能解决,不久之后中印两国又在印军人员进入西藏等事上发生争执。1953年9月尼赫鲁致电周恩来,建议两国尽早就在西藏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显然,印度政府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了更充分的了解。10月5日,周恩来复信尼赫鲁接受这一建议,并提议谈判于12月在北京开始。
韩念龙、薛谋洪:《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75177页。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了以赖嘉文为团长的印度代表团。周恩来对印度方面说:“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63页。
经过双方的努力,中印两国于1954年4月29日在北京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该协定规定,为了促进通商贸易、文化交流、互相朝圣和往来,两国政府“同意基于(一)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二) 互不侵犯,(三) 互不干涉内政,(四) 平等互惠,(五) 和平共处的原则,缔造本协定”。周恩来四个月前提出的五项原则成了该协定的指导原则,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被载入一项国际文件中。在中印两国的这项新协定中,印度放弃了那些有损中国主权的政治和军事特权,中国为两国正常的通商贸易及文化宗教往来提供了必要的便利。该协定成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共在对外交往方面多年的经验总结,也是1949年以后进行外交活动的经验总结。在五项原则中,“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在毛泽东为“紫石英号事件”起草的声明中已经提出。和平共处的思想最早是由列宁提出,中国在朝鲜战争发生后已多次提到这一思想。“互不侵犯”原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贯立场,中国曾多次表示自己“不侵犯任何人”。印度和缅甸两国对这一原则非常重视,曾经表示要同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周恩来把它纳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民族独立国家的和平中立的对外政策的尊重和重视。“不干涉内政”这一条原则的纳入也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人对外部力量干涉中国内政早就有着痛苦和深刻的经验教训。1949年后,又发生了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从这一角度看,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要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实现长期和平共处,就必须打消它们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的意图。在五项原则中纳入这一条也有利于消除印缅等国对中国会“输出革命”的担心。
总之,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外交活动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道路,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从此有了很坚实的基础,它预示中国将更现实地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并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进行更广泛的合作。
3. 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
进入1954年春季,国际形势继续显示出缓和的势头。在亚洲地区,法国在印度支那从事的殖民战争已经陷入困境。尽管美国政府为扭转印支战争局势出谋划策,并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但越南人民军在中国顾问的帮助下在奠边府包围了法军主力。这一局面迫使法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印支问题。在英法两国的要求下,美国不得不同意原定讨论朝鲜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也讨论印支问题,并同意中国参加有美、苏、英、法及印支交战各方出席的这次会议。中国的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实际上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中国政府寻求的与西方大国和平合作的机会已经出现。
但由于美国的阻碍,日内瓦会议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也陷入了僵局。东南亚地区和平前景正面临考验。周恩来对印度、缅甸两国的访问正是在各方同意暂时休会的期间进行的,这次访问对亚洲国际形势的发展具有微妙的影响。
6月17日,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见《印度教徒报》记者时指出,把亚洲国家分裂为互相敌对的军事集团的侵略政策正日益威胁着亚洲各国的和平和安全。这是亚洲各国人民当前面对着的主要问题。周恩来强调指出,中国政府认为,为了保障亚洲的和平,为了维护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权利和自主权利,亚洲国家彼此之间应该进行协商,以互相承担相应义务的方法,共同努力,来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3集,第107108页。
周恩来的这番话表明了他此时出访印度和缅甸的主要目的之一,即积极地支持亚洲民族国家的和平与中立的立场,揭露美国在亚洲的侵略性政策,使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和平共处对外政策,争取有利于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
6月25日,周恩来到达新德里。在同尼赫鲁的会谈中,周恩来向尼赫鲁通报了日内瓦会议的进展情况,双方讨论了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和平前途。在讨论双边关系时,两国总理对双方最近达成的有关中国西藏与印度通商交通协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26日,周恩来在尼赫鲁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这个协定进一步加强了中印之间的友谊,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供了国际间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的一个良好的范例”。尼赫鲁也高度评价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说:“这些原则如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被承认,那么,对战争的恐惧就可能消失,而合作的精神就可以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3集,第109113页。显然,尼赫鲁希望中国进一步澄清立场,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做出更广泛的承诺,推动东西方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缓和。
6月27日,周恩来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个书面讲话。对印度的试探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周恩来在这个讲话中明确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对中印两国适用,而且对亚洲的其他国家以及对世界上一切国家都能适用。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周恩来还强调:“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是可能和平共处的。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自主权利是必须得到尊重的。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针对一些亚洲民族国家的担心。”周恩来还说:“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同时一个国家内人民表现出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容许外来干涉。”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3集,第109113页。周恩来的这些解释进一步表明了中国愿同亚非民族国家长期友好合作的立场,并且再次表达了中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愿望。
6月28日,中印双方发表了“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两国总理在这个文件中重申了互相尊重领上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基本原则。声明说,两国总理感到,在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应该适用这些原则。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而现时存在的恐惧和疑虑,则将为信任感所代替。
这一“联合声明”还指出,在亚洲及世界各地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然而,如果接受上述各项原则并按照这些原则办事,任何一国又都不干涉另一国,这些差别就不应成为和平的障碍或造成冲突。“联合声明”的这些内容表明,中印两国都希望并且提倡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这一行动对于世界和平事业和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做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
结束对印度的访问后周恩来到达缅甸访问。尽管中缅关系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缅甸政府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仍有不少的疑虑。1954年4月缅甸总理吴努在一次中立国家首脑会议上还说,亚洲国家应把共产主义危险视为同殖民主义危险具有一样的威胁性。吴努还写信给尼赫鲁,说他十分关注中国军队在中缅边界地区的活动,以及中国对越南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军事活动的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三册,第113115页。。吴努的这些态度表明,使缅甸政府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很有必要的。
在同周恩来的会谈中,吴努坦率承认说,缅甸人口只及中国的云南省,缅甸一直怀疑中国对缅甸有领土野心,因此甚感恐惧。他还说到缅甸政府对缅甸共产党的看法,并表示说这些话只是一种“友好的埋怨”。周恩来向缅方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和平政策,中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世界上的一切国家友好相处,何况中缅两国是有亲戚关系的国家。中国的立国政策就是把自己的国家搞好,中国没有领土野心。针对缅甸政府对中国可能支持缅甸共产党的担心,周恩来说,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经验,革命是最不能输出的,输出必败。今后如果两国关系发生什么困难,马上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
FRUS, 1952—1954. Vol.11, pt. 2, Africa and South Asia, p.1134.。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向缅方表示,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需要时间进行调查,可以在以后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以解决。吴努对中国的立场很感满意,认为周恩来的访问起了很好的作用,消除了缅甸人很大一部分恐惧
转引自金畅如:《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弟342346页。。
6月29日,中缅两国总理也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再次提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指出:“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和对于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恐惧就将为安全感和互信所代替。”声明还特别强调:“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同时,一个国家内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容许外来干涉。”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三集,第115116页。
周恩来对印、缅两国的访问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这次访问表明,中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对外政策是深受亚洲民族国家欢迎的,它为中国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打开了道路。这次访问还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成为中国同一切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发展关系的基本方针。更重要的是,通过两个联合声明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倡,这些原则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周恩来对印缅两国的成功访问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对亚洲地区的形势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表明,中国的对外政策已经完成调整并且日趋成熟完善,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也已开始走出“两大阵营”理论的框架。1954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国际形势作了分析。这些分析可概括为三点。第一,现在总的形势是美国相当孤立。东南亚、印度支那的问题解决之后,美国的孤立要继续发展。第二,整个形势比过去大为好转。缓和紧张局势,不同制度可以和平共处,这些原本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原则,已逐步被一些西方国家所接受。第三,“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那里的国家被整得哇哇叫”。
转引自迟爱萍:《毛泽东对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战略指导》,《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第213页。
此时,毛泽东又回到了他过去所提过的“中间地带”理论上来了,这一变化的意义无疑是相当深远的。毛泽东还提出了广交朋友的方针,除了要继续加强同苏联的合作外,毛泽东也明确指出:要把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三大洲的国家。这些国家与中国有着共同的特点:在历史上都遭受过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经济落后,受帝国主义歧视。独立后仍有被帝国主义颠覆的危险。中国必须和这些国家联合起来,维护自己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并相互支持,共同发展。
毛泽东还要求积极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他强调了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应该把思想体系上的分歧和政治上的合作分别开来。他认为对美国也要争取主动,公开地主张同他们和平共处,建立外交关系,解决台湾问题,欢迎他们来中国。在原则问题上要寸步不让,坚持斗争。
转引自迟爱萍:《毛泽东对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战略指导》,《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第213页。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的外交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中国的对外政策已为更多的国家和人士所了解,国际威望迅速提高。亚洲地区的和平中立主义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54年8月,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等国反对美国的军事同盟政策,拒绝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并且提出了建立亚洲和平区域的设想。他们的这一行动对中国国际环境的改善有积极意义。尼赫鲁和吴努在1954年秋冬还先后访华,中国领导人在会见他们时都强调,“和平共处原则”适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长期方针。
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后,中国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取得了进一步改善。1954年6月,中英两国决定正式互换代办。不久后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访问了北京。中日关系在1954年也冲破美国的重重阻挠,双方在经济和人员交往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
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在继续加强。1954年10月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高级领导人访问了中国,双方签署了联合宣言、经济协议等重要文件,中苏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得到了全面发展。这一切都表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对外政策的指导下,中国的对外交往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探析*
(1954.11—1955.8)
*本文原发表于由刘同舜、姚椿龄先生主编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5年》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原文标题因体例需要为“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现增加“探析”二字。
①中英两国决定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于1954年6月17日日内瓦会议期间达成协议。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1954年日内瓦会议闭幕后,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紧张局势出现了缓和的趋势。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中国对外政策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了解,印度、缅甸等国奉行的和平与中立的方针在亚洲地区扩大了影响。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英法两国也希望亚洲局势能有所稳定,这便带来了日内瓦会议后中英双边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①
然而,美国共和党政府却认为这一缓和趋势不利于西方。华盛顿把印度支那战争的结束看作其东南亚政策的“重大失败”,是西方世界的“严重损失”,这一失败的心理后果与政治后果将影响“整个远东和世界”。由于美国把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等地遭到的这一系列的挫败都归咎于中国的崛起,共和党政府遂对中国采取了更加敌视和更为僵硬的政策,这一政策导致了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发生,中美两国走到了发生大规模军事对抗的边缘。
一、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到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基本将大陆上的国民党军事力量肃清,蒋介石将所剩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部署于台湾及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的沿海岛屿地区,试图利用海洋屏障苟延一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在1949年夏季已开始筹备攻打台湾的战役。由于台湾海峡宽达一百多公里,中共中央决定迅速发展海空军力量,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施解放台湾的战役,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宏伟目标。
此时的杜鲁门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必将获得内战的全面胜利,退缩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力量已毫无出路。为了阻止中苏两国的接近,杜鲁门于1950年1月表示,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得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他也不打算使用美国武装力量干预目前的局势。杜鲁门的这一立场表明,美国政府的基本政策仍然是从中国内战脱身。
但是华盛顿也有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认为,台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不应让中国共产党政权控制台湾。他们大肆制造“台湾地位未定”的舆论,甚至还提议由美国军队直接控制台湾。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甚至说:“我们会给占领台湾找到一种方式的。”1950年5月中旬,共和党人、国务院特别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提出了“台湾中立化”建议,试图促使美国政府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进入1950年,美国保守势力对杜鲁门政府的对外政策展开了更多的抨击。民主党的对华政策尤其被指责为对共产主义“软弱”的标志。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则耸人听闻地叫嚷政府中有“大批共产党人”。这一切都对杜鲁门政府构成了强大的压力。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即改变对华政策。6月27日,杜鲁门以防止朝鲜战争扩大为借口,宣布将第七舰队派往台湾海峡地区,任务是阻止共产党进攻台湾及国民党进攻大陆,实行所谓的“中立化”政策。杜鲁门的这一方针完全推翻了他自己做出的“不奉行一条将导致(美国)卷入中国内部冲突的路线”的承诺,公然干预中国内政,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力图使台湾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的岛屿链中的重要一环。
对于杜鲁门政府的这一行动,中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指出这是美国对中国的公然侵略,并且表示不管帝国主义如何阻挠,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但考虑到朝鲜战争带来的形势变化及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构成的新的安全威胁,中央军委在1950年6月底做出决定,在加强海、空军建设的同时,将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在中国投入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中央又决定将东南沿海的渡海作战全部中止。
萧劲光:《萧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26页。
为了替陷于僵局的朝鲜战争寻找出路,1953年1月上台的艾森豪威尔加强了对中国的战争恫吓政策。入驻白宫不久,他就宣布停止执行杜鲁门政府的“中立化”方针,声称不再用美国舰队“屏护”中共不受进攻。这一加剧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行动被称为“放蒋出笼”。国民党这时虽然没有大规模进攻大陆的行动自由,但他们对大陆沿海地区的骚扰和破坏却进一步升级了。
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了打击国民党对大陆沿海地区军事袭击和破坏活动,人民解放军逐渐加强了针对国民党所占岛屿的军事行动,不过,中国政府并未改变暂不攻打台湾的政策。然而,对美国来说,朝鲜战争的结束使美国失去了让第七舰队继续留驻台湾海峡的借口,美国遂同台湾当局讨论签订双边“防务条约”。这理所当然地使中国领导人警觉到美国军事力量有可能长期赖在台湾地区,并使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合法化”。
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签字之后,毛泽东致电尚在日内瓦的周恩来:“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错误。”1954年7月2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也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1954年8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的联合宣言》。1954年8月11日,针对美国方面的言论,周恩来在政府外交工作报告中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他国干涉。”1954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对金门进行了大规模的炮击,以军事斗争的方式显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4045页。
中国政府从1954年夏季起重新强调台湾问题具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在战略角度上,中国政府早就认为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三条战线,在朝鲜和印支问题基本解决后,中国也有可能争取台湾问题的解决。8月12日,周恩来在外交部工作会议上说:“远东有三个战争,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还有台湾战争。”他指出:“朝鲜战争停了,印度支那战争也停了,剩下来就是美国加紧援助台湾进行骚扰性的战争。”周恩来说,中国现在提出解放台湾是“适时的”,他要求各方面要进行工作,“等待胜利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8485页。显然,中国领导人不愿意无限期地“等待”下去,他们希望通过一些行动,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第二,在外交上,中国政府努力要阻止美国方面使大陆与台湾分裂长期化的企图,尤其是要阻止美国与台湾签订军事性质的同盟条约。在朝鲜与印度支那出现分裂局面后,西方也试图把中国的分裂局面固定化。此时,美国正在加紧策划建立针对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并且试图把台湾纳入这一由“美日条约”、“美韩条约”、“美菲条约”、“美澳新条约”及“东南亚条约组织”构成的反华军事同盟体系中去,这种局面也是中国政府不能接受的。
尽管这一时期中国政府重提“解放台湾”的口号,并且对金门展开了大规模的炮击,但中国这时并没有改变暂不发动大规模渡海作战的计划。中国的行动主要在于达到政治上的目的:了解美国的意图,排除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预,显示解放台湾的决心。美国是中国解决统一问题的主要障碍,但当时中美两国没有正常的外交联系渠道,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有限的军事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政治试探,即摸清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底牌。就全局而言,中国领导人这一时期希望通过同西方国家的协商谈判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同他们建立正常的国际交往关系。
1950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发动过大规模渡海作战,解放了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不久,又以强大的军事优势迫使国民党军队撤出舟山群岛。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国民党在大陆沿海地区只占有福建省沿海的马祖岛和金门岛,以及浙江省沿海的以大陈岛为中心的一些小岛。
朝鲜战争开始之后,中国军事力量的重心北移,暂停了大规模渡海作战。然而内战并没有完全停止,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怂恿和援助下,乘机向大陆沿海地区发动中小规模的军事袭击。国民党先后组织了“福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大陆游击总指挥部”等机构,训练和装备了数万名游击武装,在东南沿海数千公里地区进行骚扰破坏活动,严重威胁这一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民党当局还利用海军力量对东南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运输进行破坏,搜检过往的外国商船,甚至多次攻击和扣押过往的苏联和东欧船只。国民党军队还破坏大陆渔民的生产,从1950年至1953年先后劫走渔船2000余艘,抓走渔民10000多人。
徐焰:《金门之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171页。
尽管美国政府宣布了所谓的“中立化”政策,但美国私下里一直鼓励国民党当局的军事袭击活动,试图以此牵制一部分中国兵力,这种活动在1952年之后还有扩大的趋势。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了打击国民党的破坏活动,华东军区准备于1953年秋季发动一次攻击金门的大规模作战。此前,1949年秋,人民解放军曾经发起过一次金门战役,但因准备不当而失败,损失9000余人。攻击金门的新作战计划一度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但考虑到缓和国际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很快又改变决定,要求华东军区暂缓进攻金门,首先解放浙江沿海岛屿。中央军委还确定了“从小到大、逐岛进攻、由北向南”的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方针。
叶飞:《征战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636页。根据中央的指示,华东军区准备先攻打国民党所占领的浙江沿海岛屿,再根据形势发展,攻打福建沿海的马祖和金门等岛屿。
从1954年3月起,解放军加强了在浙江地区的军事行动,先后攻占了东矶列岛等岛屿。通过多次海空作战,解放军基本获得了浙江沿海地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从1954年夏季开始,又开始在福建抢修军用机场,准备夺取福建沿海地区的制空权。这些行动为解放东南沿海诸岛创造了条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军事行动是对国民党骚扰与破坏行为的反击,也是中国内战的继续,完全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与其他国家本无关系。而美国政府却要以此为借口,加剧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甚至不惜冒战争风险。他们这样做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
二、第一次台海危机前夕的美国对华政策
艾森豪威尔政府虽然结束了朝鲜战争,但出于在西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的需要,他们很快又把眼光投向东南亚,并把支持法国打赢印度支那战争作为美国亚洲政策的一个重点。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还调整了对华政策,使这一政策更明确地为其在亚洲地区的整体战略服务。
1953年11月,艾森豪威尔批准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NSC166/1文件“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这一文件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崛起已经改变了远东地区的力量结构,西方的影响已经完全被挤出中国大陆,而苏联的影响已经扩展到长城以南,甚至到达东南亚地区。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对付已经变化了的力量结构,而这种变化是由于“强大而敌对的共产党中国的存在”,以及中国与苏联结盟所产生的。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简称FRUS), 1952—1954,Vol.14,Part.1, GPO, Washington, D.C.,1985,pp.278279.
NSC166/1文件为美国对华政策规定了基本指导方针,这些方针能够为政府处理有关中国的问题提供长期指导。这一文件提出的第一项方针是,美国不能接受“使用美国武装部队推翻或替代中共政权的政策”;该文件的第二项方针是,美国也不能接受使用美国武装力量“帮助台湾国民党势力推翻中国政权”的政策。这两条方针基本上是民主党政府政策的延续,即排除美国以推翻中国政权为目的,主动向中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NSC166/1文件分析说,美国不能采取这些政策的理由是,一旦同中国发生全面冲突,美国付出的物质与人员代价过高,西方联盟必然因此发生分裂,以及存在着苏联干预并发生世界战争的高度风险。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281.
NSC166/1文件第三项方针认为,美国不能接受的另一种政策是,“为了克服这个共产党政权对西方的根本敌对而向该政权让步”。文件无视中国政府多次表示过愿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的愿望,主观武断地判断说,美国的让步“不一定能改变中国对美国深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敌视,也没有证据表明,较小的经济和威望上的让步会使中国同意美国可接受的解决重大突出问题的方案”。文件没有根据地宣称:“远东的一些特殊问题即使以满足北平的方式解决,中共作为共产党人仍将保持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的根本性敌对。”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p.282283.
艾森豪威尔政府此时制定的对华政策的新内容主要就体现为这种“不让步”的方针。这一方针几乎完全排除了中美两国在朝鲜停战后改善关系的可能,对两国关系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NSC166/1文件提出的这些方针极大地限制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选择范围,使美国政府实际上只能僵硬地继续推行对中国“遏制”、封锁和孤立的消极政策,而这种政策只会使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长期维持下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一文件还提出:“使中共政权改变方向,或者使它最终被一个不敌视美国的政权所替代,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这表明,艾森豪威尔政府把推翻或改变中国政权和分裂中苏同盟看作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长期目标。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p.270,280.
NSC166/1文件的这一倾向反映了美国右翼保守势力的观点。美国的右翼势力虽然不愿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但同时坚决反对同中国改善关系。为了迎合右翼势力的这种观点,已出任国务卿的杜勒斯认为,推翻中共政权和分裂中苏同盟并不像民主党政府设想的那样是一种两难选择。在他看来,美国如能长期地在各个方面向中国施加强大的压力,上述两项目标就都可能实现。
杜勒斯的这一看法反映在1953年3月国务院起草的《美国对中共基本目标研究报告》之中,见FRUS, 1952—1954, Vol.12, pt.1, GPO, Washington, D.C., 1984, pp.287289,294298.NSC166/1文件表明,美国对华政策正在向这种毫无灵活性的方向发展。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54年4月,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战场上遭到了严重失败。艾森豪威尔政府一度准备进行军事干预,但因为担心不能得到公众和盟国的支持而不得不放弃这一打算。尽管中国政府为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谋求和平的诚意得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公认,但美国政府更加敌视中国,并把法国殖民统治在印度支那的失败看作中共“扩张主义”的胜利。
随着印度支那战争的结束,艾森豪威尔政府加紧制定新的远东政策。在美国军方看来,中国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一切问题的核心,政府首先必须在“想要一个友好但非共产党的中国”,或者“在相当长时间里容忍共产党中国”这两种目标中进行选择。五角大楼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副总统尼克松等高级官员的支持,他们都认为,“中国是亚洲的关键”,要提出和形成一种可行的亚洲政策,首先必须对华政策的基本方向做出进一步的研究和决定。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p.750751,752753.
1954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对华政策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研究班子提出了四种对华政策的方案供决策者们选择。被认为是一种“软政策”的A方案认为:“为了巩固西方的团结,消除盟国对美国发动战争的忧虑,美国应尽快把它同中国的关系建立在它同苏联关系的同样的基础上。”A方案建议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中国进入联合国、减少贸易限制等措施。A方案的这些建议实际上只是把中美关系放在正常的国际关系基础上,但是它遭到国家安全委员会许多成员的反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上将8月18日在安委会的会议上夸张地说,该方案是要让“整个亚洲共产化”。尼克松也赞同地说,这个方案提出的是“英国人的立场,虽然也有一些美国人持这种观点”,但是,“一种软政策将导致中共对亚洲的完全统治”,是一种“绥靖政策”,意味着向敌人“张开双臂并拥抱他们”。共同安全署署长史塔生说,这一方案的基本错误是反映了那种想“通过向中国人求爱的方式,把它从苏联人那儿分开的观点”。艾森豪威尔也不相信美国能使中苏分裂,他说:“除非发生某种重大的社会变动,设想能够把中国从苏联集团中分离出来是不可能的。”决策者们认为,A方案代表着一种“共处”的政策。尼克松说:“我们当然拒绝这种意义上的共处。”艾森豪威尔甚至表示,“共处”一词含意不清,他打算制止使用这个词。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p.701702,741, 751754.
研究班子提出的四种方案中最强硬的选择是D方案。该方案提出说,如果中国“不改变对共产主义扩张给予支持”的政策,就必须使中国面临一种“美国对中国本土采取军事行动的明确可能性”。方案还提出了一系列如何将政治冲突转化成军事冲突的措施。按照陆军参谋长李奇微上将的看法,这个方案意味着美国将很快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它实际上是一个“摧毁”共产党中国的方案。除了雷德福含蓄地暗示他欣赏这个方案外,这种发动战争的设想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支持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p.703, 722723,751.。
此时执行的对华政策被归纳为B方案,但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现行政策不够强硬,因此安委会倾向于采纳C方案。这一方案的基本思路是,“即使冒发生全面战争的风险,也要削减共产党中国在亚洲的实力,但美国不故意挑起战争”。这一方案把削弱中国的力量看作美国亚洲政策的主要目标,甚至不惜冒全面战争的风险来达到这一目标。虽然方案表示美国不故意挑起战争,但整个态度比NSC166/1文件的立场又明确和强硬了一层。按照杜勒斯的解释,美国的政策要避免使美国卷入一场世界舆论认为美国是错误地卷入的战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在任何一件有可能使我们卷入同共产党中国发生战争的事情上都避而远之”。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p.702703, 747,753,756.共和党政府对C方案的选择倾向表明,美国此时具有十分强烈的敌视中国的态度,共和党政府非但没有缓和亚洲局势的愿望,相反,只要具有一定的条件,他们乐意以军事手段达到削弱中国实力的目的。这一政策倾向在1954年底批准的NSC5429文件中得到了肯定。它不仅对美国对华政策提供了长期性的指导,而且还为这一时期美国处理台湾海峡危机提供了政策依据。
三、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国际背景
进入1954年夏,共和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打击中国的威望,加剧台湾地区的紧张形势,企图以此改变因印支战争失败而造成的对美国不利的发展趋势。5月下旬,针对浙江地区解放军军事活动的增加,艾森豪威尔下令第七舰队部分舰只到大陈岛周围活动,“显示可以威慑中共进攻该岛的力量”。6月下旬,美国指使国民党当局劫持苏联油轮“图埃普斯”号。7月下旬,一架英国小型客机被解放军误以为是国民党轰炸机而被击落。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向英国进行了道歉,并表示愿意赔偿一切损失。尽管英国政府已打算低调处理此事,但杜勒斯却表示,“不能降低此事的重要性”。他和雷德福协商后向出事地区附近派出航空母舰,企图制造事端。7月26日,美军战斗机向一艘开往中国的波兰货船扫射挑衅,随后又击落两架前来护航的中国战斗机。美国的这些行动大大加剧了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增加了中美两国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p.428434,444,518519.
1954年8月17日,针对中国重新强调“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如果中国进攻台湾,将会迎头遭遇美国第七舰队。
《纽约时报》,1954年8月17日。8月24日,杜勒斯也公开以战争对中国进行威胁。
1954年9月3日,解放军驻福建炮兵部队奉命对金门岛实施大规模炮击。美军太平洋总部立刻再次下令航空母舰开往台湾海峡地区显示实力,试图威慑中国。但是,此时华盛顿的决策者对于美国应该在中国沿海岛屿问题上具体采取什么方针却举棋不定。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在8月份提出,从心理上及其他方面看,美国“不能容许远东的任何地方再落入共产党中国的控制之中”。炮击金门之后,雷德福和军方的多数领导人要求政府立即明确政策,允许使用美国的海空力量帮助国民党防守沿海岛屿。他们强调,这些沿海岛屿的丢失会对美国的远东战略产生严重后果。但是陆军参谋长李奇微认为,这些岛屿对防守台湾并无多少重要的军事意义,不至于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他一针见血地提出,军方不应从政治角度评价这些小岛丢失的后果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p.598610,617619; FRUS, 1952—1954, Vol.12, pt.1, p.755.。
炮击发生时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不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去了西部的丹佛度假,杜勒斯则去了远东出席“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立会议。在致国务院和总统的电报中,杜勒斯流露出明显的想帮助国民党守住这些小岛的倾向。他指出,沿海岛屿的失去将对国民党产生巨大的心理和威望上的打击。如果华盛顿的判断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能守住这些岛屿,美国就应该帮助国民党防守。杜勒斯指出,如果守住了金门,“共产党从奠边府获取的威望就会被消除”。这表明,杜勒斯从一开始就是把中国沿海岛屿问题放在美国整个亚洲战略的大背景下来看待,他有着一种在沿海岛屿问题上为印度支那失败报“一箭之仇”的心理。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p.560572.
艾森豪威尔最初的反应是,“除非我们能守住它(指沿海岛屿),否则就不应该去”。而且他也担心,美国在沿海岛屿的军事卷入可能对美国同西欧盟国的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他不愿匆忙做出决定。
1954年9月1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们赶到总统度假地丹佛出席紧急会议,专门讨论美国在台湾海峡及沿海岛屿问题上的对策。尼克松、雷德福、史塔生等人在会上强调,美国不能容许丢失金门等沿海岛屿,因为那会对国民党和整个远东地区的反共士气产生严重影响。国防部长威尔逊则认为,美国在沿海岛屿的军事卷入势必会导致同中国的全面战争。美国既然在朝鲜和印度支那没有这样做,现在也不必为了这些“该死的”小岛而这样做。威尔逊指出,美国应区分台湾、澎湖与沿海岛屿之间的不同形势。
此时,美国情报机构对于局势的发展也有一定分歧。1954年9月6日的一份“国家情报特别估计”认为,由于中共不了解美国的意图,它会在沿海地区不断采取行动以试探美国的动机和可能的行动反应。如果这些试探没有遭到预计中的美国的反击,中共就可能扩大进攻规模,并可能夺取国民党占据的岛屿。大多数情报机构认为,如果中国确信美国的反击是全面攻击大陆的军事基地,“他们就可能被威慑住而不致发动一场夺取沿海岛屿的全面进攻”。但是陆军情报机构G2却认为,即使美国宣布防卫沿海岛屿,中国也不一定会被威慑住而不敢发动进攻,“他们可能不相信美国会采取反击行动”。显然,双方争论的焦点是,美国的威慑能否阻止中国发起进攻沿海岛屿的行动,这里也涉及对中美发生全面战争可能性的估计。
FRUS, 1952—1954, Vol.14, pt.1,p.597.
艾森豪威尔在丹佛会议上明确表示,美国不能为了这些沿海小岛同中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他向与会者说:“除了心理上的意义,金门并不真正重要”,但他也承认,“心理上的意义已经构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尽管如此,他要求与会者从全局考虑问题。他说,共产党可以在世界各地牵制美国的力量,因此他反对美国做出对世界上所有地方都要守住的承诺。他认为如果真要打一场全面战争,他宁可同苏联打而不是同中国打,因为苏联才是“蛇头”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p.615617.
杜勒斯显然事先已知道了艾森豪威尔的想法。他在会上指出,美国正面临着可怕的困境。一方面,如果不同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沿海岛屿就无法永远守住。但是同中国打全面战争不仅会使美国与盟国产生严重分歧,而且国内舆论和国会也会发生分歧。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不采取制止中国的措施,中国也许会发起强有力的行动。国民党军队如从沿海岛屿撤退,对日本、韩国、“台湾”和菲律宾会有灾难性的后果。杜勒斯提议,为了避免在全面战争与丢失沿海岛屿的两者间做选择,美国可以采取两项措施:第一,考虑同国民党当局签订正式的条约,美国正式承担防卫台湾和澎湖的义务;第二,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并安排沿海岛屿的“停火”。他说,由于有朝鲜的先例,“这个问题也不会被看作内战”
FRUS, 1952—1954, Vol.14, pt.1,pp.616618.。
最后,丹佛会议做出决定,美国不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去防守金门等沿海岛屿,但可以向国民党军队提供物资上的援助。但是,美国不公开宣布它的这一政策,使中国无法了解美国的真正意图,从而阻止中国可能对沿海岛屿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会议还同意了杜勒斯提出的上述两条措施,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干预披上“合法”外衣,并使沿海岛屿问题“国际化”。按杜勒斯的设想,如果中国拒绝联合国的“停火”努力,美国与世界的舆论就会发生变化,届时美国政府就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而采取新的措施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p.617619.。
四、“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
随着朝鲜战争走向结束,台湾国民党当局意识到,经过与美军交战的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将更加强大,第七舰队在朝鲜战争之后是否还会留在台湾则有很大的疑问,没有美国的军事保护,国民党在台湾的生存是无法维持的。因此,在1953年3月国民党当局就向美国共和党政府提出签订军事防务条约的要求,以达到长期拴住美国的目的。但当时杜勒斯认为,国民党的这一计划有可能把美国卷入“反攻大陆”的企图中去,所以美国不能同意签订这样的条约。同年12月,国民党重提此事,并且还拿出了条约草案,但共和党政府仍未予以肯定答复。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367.
但国民党当局的缔约要求在美国保守势力中不乏同情者,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沃尔特·饶伯森就多次敦促杜勒斯考虑此事。杜勒斯除了不愿意美国被卷入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活动中去,而且从整个亚洲战略的角度上看,他一直把台湾看作对中国的潜在的进攻力量,尤其是在印度支那战争的局势没有明朗以前,他并不愿意让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被防守性的条约束缚。1954年5月,杜勒斯在会见国民党驻美国“大使”顾维钧时说:目前国共之间存在着公认的战争状态,如果美国同“台湾”签订一个条约的话,其后果不是阻止了国民党对大陆的军事行动,就是使美国有可能直接卷入国共军事冲突。杜勒斯明确地指出,美国政府现在既不想阻止国民党对大陆的军事行动,“冻结”台湾海峡的形势,也不想承担有可能使自己卷入国共冲突的条约义务。杜勒斯告诫顾维钧说,当缔约一方“实际上在进行一场进攻性行动时”,那就很难说得通所订条约是一个“防御性”的条约。杜勒斯说,美国国会肯定不会批准一项允许缔约另一方发动军事进攻的条约。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p.339340,422424.
显然,艾森豪威尔政府既想利用国民党军队在东南沿海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又不愿让国民党当局发动大规模反攻,从而使自己面临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可能。蒋介石虽然屡屡碰壁,但他并不就此罢休。对于每一个到台湾访问的美国军政要人,他都一再提出签订条约的要求,力图促使美国政府改变政策。
随着日内瓦会议成功地结束了印度支那战争,以及中国重新强调解放台湾,杜勒斯意识到,美国已不再需要台湾作为一种潜在的战略进攻力量,美国有必要改变对台湾的政策。8月底杜勒斯开始谈论“美国可能最终需要同国民党人谈判一个条约”。但是,由于国民党还占据着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岛屿,杜勒斯认为,“美台条约”如何确定其涵盖的地域范围是十分麻烦和复杂的。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p.548549,555.
杜勒斯的设想是,美国的军事保护将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和澎湖地区,从而使台湾长期成为它西太平洋岛屿链中的重要一环。但是,杜勒斯认为,“美台条约”很难回避国民党军队占领的沿海岛屿问题。这些岛屿从地理上说是大陆的一部分,把它们包括在条约涵盖范围内,不仅会大大增加被国民党当局拖入中国内战的风险,而且还会引起西方盟国的反对。如果把这些岛屿排除在条约范围之外,这又可能导致中国很快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没有美国的支持显然不可能守住这些岛屿。面对这一难题,杜勒斯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给他时间进行研究,然后再作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之后,杜勒斯曾于9月8日到达台北,与蒋介石进行了半天会谈,即使在那时,杜勒斯仍然没有在签约问题上松口,他对蒋介石说,总统的行政命令仍是保护国民党当局的很有效的方法。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p.581582.
丹佛会议上的有关决定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处理沿海岛屿问题提供了方针,同时它也清除了缔结“美台条约”的一个技术性障碍。10月6日,杜勒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说,国务院即将和国民党当局谈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在谈到缔约的目的时,杜勒斯说,朝鲜停战状态的持续使美国不再有使用武力“保卫台湾的自由”,因此美国必须同“台湾”签订一个“防御”条约。但由于国民党当局需要的不只是一项单纯的防御条约,美国必须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他接受这种“单纯的防御性条约”。杜勒斯强调,有关“防御性条约的想法完全是同目前变化了的环境相一致的”。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p.619,756.
“美台”双方就这个条约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谈判。双方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条约涵盖的地理范围。11月2日,在同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进行第一次谈判时,杜勒斯就明确说,美国不打算把国民党占据的沿海岛屿包括在条约里,但这些岛屿的地位也不会“变化”。他说美国军方认为,如不攻击大陆,这些小岛是守不住的,而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有可能导致全面战争。尽管叶公超竭力要求条约包含“所有中国领土”,但在美国方面的强硬姿态下,他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意见,同意条约适用的领土范围只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但双方为了确保国民党军队占有的沿海岛屿不至于立即丧失,又宣称这项条约也“适用于经共同协商后确定的其他领土”。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p.845846,860.这一解释为美国后来改变相关政策留下了余地。
谈判中“美台”双方有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坚持台湾国民党当局必须事先同美国协商,并在美国同意之后才能采取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杜勒斯坚持这条内容的理由是十分简单的,即防止美国被蒋介石拖入“反攻大陆”的行动中去。美国的这种“否决权”实际上在1953年初已经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默认,但是蒋介石认为,他不能在条约中公开接受这一内容,因为这将严重影响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和“反攻大陆”的基本目标。最后双方达成妥协,以秘密换文的方式规定国民党当局接受美国的“否决权”。这一换文不仅剥夺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行动自由,甚至剥夺了蒋介石调动团以上兵力的自由。1954年12月2日,“美台”双方代表签订了这个“共同防御条约”。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p.870880,982.
中国领导人对“美台条约”签订的反应十分强烈。1954年12月5日,周恩来在同缅甸总理吴努会谈时指出:“这个条约名为共同防御条约,实际上是为了正式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岛。”他说,“从这一条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人民不得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澎湖列岛和沿海岛屿,国民党可以自由进攻大陆,而美国则对台湾和澎湖列岛进行军事占领,以便将来扩大战争。”周恩来指出,美国试图“以美蒋条约来吓倒我们,但是我们是吓不倒的”。他说,中国热望和平,“但是不会拿我们的主权和利益去乞求和平”。中国政府还正式发表声明,表示决不承认这项非法条约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9293页。。
在1954年9月12日的丹佛会议上,杜勒斯曾提出将沿海岛屿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试图以此达到阻止中国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目的。杜勒斯在会上说,在将要求“停火”的决议草案提交安理会之后,不管苏联对这一草案是否投否决票,美国都能从中获利。杜勒斯分析说,如果苏联否决“停火”决议,那时共产党的行动就违背了大多数国家要求和平的意愿,西方盟国和美国人民对此事就会有新的看法。如果苏联对决议投赞成票,美国就可以采取使形势稳定的其他措施,因此也不会有丢失金门等沿海岛屿的危险。杜勒斯后来还说过,他并不期望苏联的支持,他认为安理会的行动很可能在中苏两国之间引起分歧。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p.619620.
1954年9月17日,杜勒斯抵达伦敦出席北约的有关会议。他向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透露了这一设想。为了获得英国的支持,杜勒斯一方面以美国在金门等沿海岛屿问题上面临和平与战争的选择来吓唬艾登;另一方面,他又表示,如果安理会的这一行动能得到支持,就可能开始进行范围更广泛的谈判,“从而使目前动荡的远东局势得到部分解决”。他还指出,这样做能使英美两国在外交方面的分歧得到弥合。对于英国方面提出的这样做是否会导致国民党军队最终撤出沿海岛屿的问题,杜勒斯也含糊其词地表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651.。
英国政府此时奉行的是一种“遏制”加“缓和”的远东政策,对于杜勒斯的这一方案,艾登决定予以支持。双方商定,让此时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新西兰出面提出决议案,草案的内容将由三国协商确定。不久,英国为这一外交行动取了一个名为“神谕行动”的代号,以达到保密的目的。
在美英就决议草案协商时,英国方面发现美方草案只提到金门等岛屿的停火问题,于是英国代表提出异议,认为决议草案也应提“更广泛的解决”,因为艾登认为实现亚洲问题更广泛的解决是进行这一行动最主要的起因。但美国代表表示,现在并没有这种解决的可能,因此决议草案只能限制在有关金门等沿海岛屿问题上。英国认为,这样的决议草案可能使蒋介石更有恃无恐地向大陆挑衅,英国认为决议至少可以提一下未来更广泛的解决,否则地区形势无法得到缓和。最后杜勒斯只能向英方透露,国民党已经口头承诺不经美国同意不对大陆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英国这才放弃了他们的要求。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p.710713,724.
杜勒斯让安理会讨论沿海岛屿“停火”问题的主要目的是,让世界舆论认为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是希望和平的。他预期中共会反对这种干预中国内政的“停火”安排,这样,到时候美国政府采取别的政策就会得到西方舆论的支持。在杜勒斯看来,如果“停火”安排能够实现,它可能导致台湾最终从中国分离出去,这种局面在他们看来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然而,蒋介石对杜勒斯的这一想法多少也估计到一些,在知道美国要把金门等沿海岛屿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后,国民党当局立即向华盛顿表示强烈反对。蒋介石认为,这一方案就像当年的马歇尔使华一样,将导致国民党的利益被出卖。沿海岛屿的“停火”将导致国共之间的全面停火,进一步的发展就可能是由联合国托管台湾,并让中共政权取代国民党当局获得在联合国的席位。蒋介石的反对表明,他意识到把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交由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不仅影响到国民党当局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还可能影响到它最终的生存问题。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p.732735,740748..
为了说服蒋介石默认拟议中的“神谕行动”,艾森豪威尔政府特地派出深得蒋信任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去台北。饶伯森对蒋说,苏联和中共多半是会拒绝这个决议草案的,届时美国在帮助他防守沿海岛屿时就能得到盟国和舆论的支持。万一共产党方面接受这一方案,国民党当局自然就不会有失去沿海岛屿的风险。蒋介石对于后一点并不相信,但是饶伯森带来了他最想要的东西,即美国正式同意签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在美国的压力和诱惑的双重作用下,蒋介石只好同意美国的意见,对即将提出的金门岛的“停火”决议不公开表示反对。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p.734737.
1954年12月初,由于中国审判美国间谍案引起美国舆论的强烈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认为,此时在联合国采取“神谕行动”不仅不能使形势缓和,而且还可能使形势更加紧张,因此,艾登提出推迟进行行动。杜勒斯被迫同意了英国的意见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p.961965.。
五、美国的政策变化与台海危机的发生
1954年春夏以后,尽管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军事冲突有所增加,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不少加剧紧张气氛的行动,但是中美之间在12月以前并没有爆发战争的风险或气氛。
1954年11月24日,中国政府宣布了对两起美国间谍案的审判结果。一起是以美国空军上尉阿诺德为首的11人案件。他们在1953年1月驾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侦察,因飞机被击落而跳伞被捕。另一起是两名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非法进入中国,试图接走另一名间谍的案件。这13名美国人分别被中国法庭判处有期和无期徒刑。案件公布之后,美国舆论反应强烈,报纸、电台掀起了新的一轮反华浪潮。他们认为阿诺德等11人是朝鲜战争时的战俘,应根据停战协议予以遣返。11月24日,美国军方提出封锁中国海岸、进行空中袭击、劫持中国船舶和船员作为人质,以及支持和配合国民党军队占领一些中国岛屿等方案,试图以武力迫使中国释放被监禁的美国人。11月29日亲台湾当局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威廉·诺兰公开宣称,政府应当立即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的操纵下,通过了指责中国违反停战协议的决议。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948.
美国舆论和右翼保守势力的这些反应表明,在经历了朝鲜与印度支那战争的失败后,在麦卡锡主义的歇斯底里的反共气氛中,美国社会中弥漫着强烈的敌视中国的情绪,右翼势力和亲国民党的政治力量则利用这种情绪向政府施加压力,希望政府利用美国的海空优势对中国进行打击,即使冒战争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世界舆论对美国的战争叫嚣很快就感到不安,艾森豪威尔也认为诺兰的讲话给政府制造了麻烦。他不得不公开讲话说,美国不会允许其公民被中国扣留,为此将做出强烈反应。但是艾森豪威尔也表示,“封锁是一种战争行动”,美国不能轻易做出这一决定,必须先以和平手段争取被扣人员的释放。尽管如此,中美之间的战争危机气氛已经出现了。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No.807, Dec.13., 1954, pp.887889.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在1954年8月已受命攻占浙江沿海地区的大陈诸岛,11月20日解放军总参谋部批准了在12月20日进攻大陈外围一江山岛的作战方案,命令强调这场战斗是要打击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卖国行径,迫使美蒋炮制的“共同防御条约”不包括金门、马祖和大陈等沿海岛屿。12月2日,由于美台双方已宣布签署“共同防御条约”,为了摸清这一条约的底牌,中共中央军委下令推迟进攻大陈岛。不久,中央军委做出了判断,认为“美台条约”签订并没有改变美国的态度,美国不会为几个小岛再同中国打一仗。同时,对于美国炫耀武力的行为中国也不能示弱。
徐焰:《金门之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180页。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在浙江沿海发起联合登陆作战,激战数小时后占领了大陈外围的一江山岛。此战使国民党当局在浙江沿海的主要据点大陈岛的门户洞开。更重要的是,它显示解放军的登陆作战与三军协同能力有了质的提高,意味着中国在解放这些沿海小岛时已不再有技术上的障碍。
美国东部时间1955年1月18日上午,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通了电话。艾森豪威尔指出,一江山岛离台湾很远,因此没有多大的重要性。他要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该岛被中共占领“不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不会影响台湾和我们自己的重大利益”。杜勒斯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也的确按此口径作了解释。
FRUS, 1955—1957, Vol.2, GPO,Washington, D.C., 1988, p.37.
但美国的立场第二天就起了变化。19日一早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匆匆赶到华盛顿,他告诉杜勒斯说,无论美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国民党军队这次要“死守”大陈岛。
FRUS, 1955—1957, Vol.2, pp.3841.蒋介石采取这种态度并不难理解:倘若没有美军的直接帮助,国民党军队肯定是守不住大陈岛的。但问题是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刚刚签字不久,如果美国在沿海岛屿问题上仍旧态度暧昧,那么国民党迟早会失去所有这些岛屿。因此,蒋介石认为他只有以“死”相逼,才能迫使华盛顿改变立场。
杜勒斯在丹佛会议上虽然接受了艾森豪威尔的观点,同意不使用美军帮助国民党防守沿海岛屿,但他内心并没有排除一旦形势有变美国改变政策的可能。他当时在会上就说过,形势当然会发生变化,那时美国就可能会有不同的立场。他要求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准备应付种种不测事件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266.。
对于蒋介石的“死守”方针,杜勒斯即刻做出了反应。他对叶公超说,美国不能在沿海岛屿问题上草率行事,但可以作这样的设想:从军事角度看大陈岛的确是难以防守的,因此应当主动撤退,但是美国对金门岛则可能采取新的方针。
同叶公超的会谈只进行了半个小时,杜勒斯就赶往白宫,在那里他同力主帮助国民党防守沿海岛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一起会见了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对艾森豪威尔说,基于共产党对一江山岛的成功进攻,他对远东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不安。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是守不住沿海岛屿的,因此美国必须明确立场。杜勒斯又说,“对美国意图的怀疑正在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威望产生恶劣影响”,因为“很多方面认为美国会保卫这些小岛”,“如果美国不这样做的话,就会显得是当真正的危险到来时,我们就逃避责任”。他对艾森豪威尔建议说:“现在也许应当考虑修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杜勒斯的具体计划是,鼓励和帮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同时表明美国将帮助国民党防守金门的态度。雷德福表示他完全赞同杜勒斯的意见。艾森豪威尔仍然不很积极,但也表示“大致上同意”杜勒斯的思路。美国对中国大陆沿海岛屿的方针就在他们三人短短的午餐工作会议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FRUS, 1955—1957, Vol.2, pp.4143.
当天下午,杜勒斯把美国的新政策通知叶公超,他甚至不等蒋介石的同意就开始贯彻这一政策。在向一批负责安全事务的高级官员通报美国政策变化的决定时,杜勒斯谈到了两点理由:第一,中国对一江山岛的进攻是要表明“解放台湾的决心”,美国必须对此做出反应;第二,如果这些岛屿被攻占,而美国在一边坐视不管就会引起震动,这不仅会影响国民党当局的士气,而且对美国在远东所有的朋友都会造成“损害性的影响”。
FRUS, 1955—1957, Vol.2, p.51.
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对沿海岛屿的新政策。杜勒斯强调,美国如果不加以干涉,局势的发展将对“整个自由亚洲的所有国家产生严重影响”。但安委会成员们仍对新政策感到不安。财政部长汉弗莱、国防部长威尔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卡特勒都认为,这一新政策有引起战争的风险,美国不应为了这些小岛而卷入战争。但艾森豪威尔此时似乎决心已定,他说,除非美国打算完全抛弃台湾,进一步的耽误会导致局势严重和迅速地恶化。他告诉与会者,在新的政策下,同中国发生战争的机会可能比现在的“危险趋势”还小一些。
FRUS, 1955—1957, Vol.2,pp.6979.
1955年1月22日,艾森豪威尔下令向第七舰队增派3艘航空母舰,此时大批美国舰只和飞机已云集台湾海峡。24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了一份“特别咨文”,要求国会授权他使用美国军队“保卫”台湾、澎湖列岛和其他“有关地区”。艾森豪威尔在咨文中强词夺理地说,中国在浙江沿海岛屿采取的军事行动威胁了“美国的安全”,“威胁了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和平”。他硬将中国的行动与“进攻台湾”相联系,并称美国的措施是为了“保卫台湾和澎湖”。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No.815., Feb.7, 1955, pp.211213.经过几天讨论,国会两院在28日以绝大多数赞成票通过了总统的授权请求。美国采取的这些军事和政治措施导致了中美战争危机的形成,西方报刊纷纷报道可能发生战争的预测,台湾海峡局势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美国右翼保守势力对政府的这一政策变化纷纷叫好,一位来自俄勒冈州的参议员甚至叫嚷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
FRUS, 1955—1957, Vol.2, p.141.
但是,美国的西欧盟国对于美国为了几个小岛而不惜冒全面战争风险的政策大惑不解。英国在1月19日已知道美国要改变政策,当时杜勒斯说,“这是一种临时性的保证”,但艾登这次不打算再轻信杜勒斯。1月20日,英国向美国表示,首先美国的新方针会使各方面都产生混乱,而且会使国民党军队长期留在沿海岛屿不走,从而使形势不能缓和,因此英国反对美国公开宣布防守金门。其次,英国认为,在联合国采取“神谕行动”需要共产党方面最低程度的合作,而国民党军队长期留在沿海岛屿使得西方获得这样的合作成为不可能。英国建议,除非美国推迟执行其关于沿海岛屿的新政策,否则“神谕行动”的整个基础就发生了变化,有关这一行动的整个问题必须重新考虑。
FRUS, 1955—1957, Vol.2, pp.86,97.
艾森豪威尔政府当然不愿让国民党军队撤出沿海岛屿,但为了得到盟国的支持,他们也不得不作一点妥协。1月30日,艾森豪威尔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明确指示,“美国不公开宣布保卫金门”,他的理由是,那样做会“吓坏欧洲”。但美国的这一变化又引起了蒋介石的疑虑,他认为美国又从1月19日的立场上退了回去。当天蒋即表示,如果美国不愿公开防守金门的政策,他宁愿不要美国帮助撤退国民党在大陈岛的守军,直到美国方面澄清他们有关金门的立场。面对蒋的要挟,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得不于次日私下向蒋介石保证,美国并没有改变关于防守金门的立场,这才换得蒋介石同意宣布“邀请美军”协助撤出在大陈岛的军队
FRUS, 1955—1957, Vol.2, pp.166168,172174.。
六、美国促发台海危机的原因分析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危机期间多次声称,美国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是要确保台湾安全,因为中国大陆在沿海岛屿采取的军事行动不仅是针对这些岛屿本身的,而且也是针对台湾的。然而美国政府此时完全清楚,中国大陆此时并没有进攻台湾的军事准备。1954年11月下旬的“国家情报估计”报告说:“只要美国在台湾地区派驻足够的空海军力量,中共就不会试图对台湾及澎湖地区发动全面进攻。”美国情报机构的这一估计即使在危机达到顶点时也没有发生变化。
FRUS, 1952—1954, Vol.14, pt.1, p.931;FRUS, 1955—1957, Vol.2, p.377.因此,可以说艾森豪威尔政府促发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原因主要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
首先,从美国国内政治来看,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态度一直有增无减。美国的右翼保守势力对于政府花大量金钱援助西欧盟国持批评甚至反对态度,但是他们对于支持亚洲的反共势力却一直非常积极。他们对于民主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尤其不满,不断攻击艾奇逊等人对中国“软弱”。为了避免走民主党政府的老路,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等人在1952年大选中一再保证要结束过去“对亚洲的忽视”,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方针,以此争取右翼保守势力的支持。
然而,右翼保守势力要求“在远东不再丢失任何土地”,他们对共和党政府上台两年来的亚洲政策并不满意。在他们看来,朝鲜战争在“三八线”附近的停战,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和结果都是美国的失败。他们尤为痛恨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威望的增长。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共和党参院领袖诺兰一贯以亲蒋而闻名。1954年夏,当英国出现让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言论后,诺兰对政府威胁说,如果政府不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他将辞去公职,领导一场让美国退出联合国的运动。诺兰的这一立场还得到了民主党国会领袖林登·约翰逊的支持。
S. D. Bachrach, 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 China Lobby Politics, 1953—197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8296.1954年国会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在国会中成了少数党,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政治上更加依赖右翼保守势力的支持,而台湾国民党当局却与右翼势力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他们可以利用与右翼保守势力的种种关系抨击艾森豪威尔政府。助理国务卿沃尔特·饶伯森就曾提醒过杜勒斯,如果美国不采取支持国民党的方针,“对我们来说,国内的政治反应将比英国的不赞成更难对付”
M. Dockrill, M and J. W. Young,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45—1956,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p.191.。
1954年,也是麦卡锡主义影响达到顶点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政府一方面必须同这位把攻击矛头对准军队和政府机构的右翼参议员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为这位参议员掀起的反共浪潮推波助澜,以便取得政治上的平衡。尽管如此,右翼势力仍然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不满意。1月22日《时代》和《生活》杂志老板、亲国民党势力代表人物亨利·卢斯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说:“作为亚洲反共力量最坚强的盟友,美国立场和态度的最轻微的软化,也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他反对政府只是让联合国干预的方针(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尚未宣布改变政策),并声称他的立场是对近来美国出现的“绥靖与自满”倾向的“小小反击”。
Bachrach, 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 pp.105107.总之,取悦和迎合右翼保守势力的政治要求,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惜冒战争风险而促发危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从国际政治方面来看,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改变政策的另一重要原因是,1954年下半年以来,亚洲出现了强大的中立主义潮流。在朝鲜停战以及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上,一些中立主义国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进一步鼓励了这些国家执行和平与中立的对外方针,他们希望避免冷战的扩大并推动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的缓和。特别是在1954年12月,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锡兰和巴基斯坦五国在印尼茂物举行了首脑会议,决定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亚非国家会议,并邀请中国参加。中立主义国家的国际活动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严重冲击了美国在亚洲构筑反华军事同盟体系的政策。共和党政府面对这种国际政治的压力,转而决定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他们希望通过显示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决心”来加强美国的亚洲“盟友”对其政策的信心,从而稳定亚洲盟国的军心,扭转亚洲国际局势中不利于美国的倾向。
七、共和党政府的新分歧与政策再度调整
从1955年1月下旬起,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军事和政治行动来加剧台湾海峡危机。这些行动得到了国会的支持,也得到了新闻媒介的喝彩。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也多次发表强硬讲话,甚至公开对中国发出核威胁。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华盛顿对于这场危机该如何收场却有深刻的分歧。
美国政府的危机政策刺激了一些好战势力的情绪,一些官员认为,“中国在短时期内不一定会进攻,”但是美国“可能需要一些军事交火来使得他们相信我们坚定的意愿”。美国驻台“大使”蓝金建议,美国可以帮助国民党守住南齐岛,该岛是“交火”的“好地点”。五角大楼也以中国在加强军事准备为由,要求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国民党军队对大陆的机场和公路进行先发制人的轰炸。杜勒斯也支持这种意见。1955年2月21日他在马尼拉致电艾森豪威尔说,美国应当考虑允许国民党对大陆的军事设施“进行空中攻击”。显然华盛顿是有一些势力想看到军事冲突变成现实。
FRUS, 1955—1957, Vol.2, pp.269,300.
然而,美国公众并不支持政府的战争危机政策。在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授权使用武力的请求后,白宫三天内收到了561封有关台湾海峡局势的信件和电报,其中反对美国干涉,要求维持和平的为375封,占66.8%,支持总统政策的为122封,只占21.8%;要求将该问题交给联合国处理的为64封,占11.4%。
“Hopkins to Wilitmali”, Jan.27, 1955 DDE Papers as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Series, Box 9, Eisenhower Library.这一统计表明大部分公众是反对政府的冒险政策的。
美国公众的这一态度很快在政府内部表现出来。2月7曰,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鲍伊向杜勒斯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说,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国对台湾和沿海岛屿都明确地做出了区分,它们都认为,沿海岛屿只有在国民党“反攻大陆”时才有意义。它们还认为美国保卫这些岛屿的方针增加了战争风险,因而危及了它们自身的安全。鲍伊评论说,盟国的这些担心将使美国与其盟国关系紧张,并产生限制美国的压力。这位国务院高级官员认为,现在美国的政策取向应是在不损害美国威望、不动摇对美国防守台湾能力与意愿的信任的条件下,从沿海岛屿问题上脱身。
FRUS, 1955—1957, Vol.2, pp.238240.
艾森豪威尔本人在2月中旬也开始对台海危机的持续感到不安。接到杜勒斯21日的电报后,艾森豪威尔召集负责安全事务的高级官员开会,试图寻找走出危机的出路。他在会上一方面表示同意杜勒斯的看法,认为美国不能长期阻止国民党空袭大陆,并以此作为向英国施加压力的手段。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又说到,国民党自己从沿海岛屿撤出“是一种更明智的选择”。2月底,艾森豪威尔甚至想通过一名美国报界的高级人士悄悄传话给台湾,试图说服蒋介石主动从金门撤出。他也向国务院的官员指出,美国应该设法使蒋介石改变思想,从沿海岛屿撤退,巩固台湾的地位是符合国民党利益的
FRUS, 1955—1957, Vol.2, pp.277,301301,305307.。
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台湾海峡危机政策的不满反应是艾森豪威尔想从金门脱身的重要原因,他担心一旦同中国发生大规模冲突,美国可能得不到欧洲盟国的有力支持。而且亚洲的紧张局势也可能增加西欧国家对美国政策的疑虑,担心美国的右翼势力会把欧洲拖入亚洲的战争中去。3月11日,艾森豪威尔做出决定,在即将成立西欧联盟的情况下,美国应当避免直接卷入沿海岛屿冲突。如果美国不得不进行干涉,美国也应避免使用原子武器。艾森豪威尔的这些想法和决定抑制了军队中好战派力量的进一步上升。
FRUS, 1955—1957, Vol.2, pp.354357.
杜勒斯在3月中旬开始跟上艾森豪威尔的步伐,他也开始谈论说,“如果有时间的话”,蒋介石应当从金门撤出军队。但是杜勒斯仍然期望出现一种有利于美国的世界舆论气氛。3月28日,杜勒斯在国务院一次会议上表示,美国还是应当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就台湾海峡局势采取行动。他仍指望在中国拒绝联合国决议的情况下,世界舆论会转而支持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但政策设计室主任鲍伊提出不同看法,鲍伊说目前的政策可能会失去“威慑效果”,“破坏自由世界的团结”。他指出,美国人民和“自由世界”多数人民“不会认为这种行动(指美国就沿海岛的采取军事行动)是有理由的。”鲍伊强调说,让国民党从金门撤出的方针既能维持美国的威信,又能使美国从沿海岛屿问题上脱身,并赢得盟国对防御台湾的支持。会议结束前,与会的高级官员们被告知:“总统有了试图改变保卫这些岛屿的想法。”
FRUS, 1955—1957, Vol.2, pp.409415.这些情况表明,随着形势的发展,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对于如何处理这场危机的分歧也在增加,尽管表面上美国还是气势汹汹,但实际上已是骑虎难下。
1955年3月底,艾森豪威尔承认,台湾海峡危机问题是他就职以来的最棘手的问题。4月1日,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召开会议,再次讨论台湾海峡问题,到会的有国务卿杜勒斯、国防部长威尔逊、财政部长汉弗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等人。在对形势作了详细讨论以后,艾森豪威尔总结说,美国一方面要考虑维持国民党军队的士气,立即取消美国在金门、马祖问题上的支持将导致国民党军队的崩溃,并且对东亚和东南亚造成强烈冲击。另一方面,美国为防守金门、马祖而卷入同中国的全面战争也是不可取的,原因是这些岛屿的军事地位十分不利,行动的最终目标也不清楚,还得不到盟国的支持,美国国内公众舆论也将会发生分裂,甚至对国内经济也会带来严重的不利。艾森豪威尔指出,基于上述两种考虑,美国应说服蒋介石自愿撤出金门、马祖,固守台湾并等待大陆出现变化,以构成对中共政权长期的军事和心理威胁。同时,艾森豪威尔又说到,美国不能强迫蒋介石从沿海岛屿撤出。4月1日的这次会议表明,美国对台湾海峡危机的处理方针又在发生变化,在寻找从沿海岛屿的“脱身”之计时,着眼于巩固美国对台湾的控制,并在长期政策中逐步推行“两个中国”的方针。
FRUS, 1955—1957, Vol.2, pp.475476,496.
4月1日的会议虽然定下了美国处理台湾海峡危机的下一步方针,但是还未决定如何执行这一方针。此外,杜勒斯认为改变方针的时机还不成熟。4月11日杜勒斯对艾森豪威尔说:“只有在万隆会议之后,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楚些,并判断出这个地区是会有战争还是会有和平。”4月17日,艾森豪威尔政府确定由两个蒋介石信任的人——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去台湾说服蒋介石自愿从金门马祖撤军。4月20日他们两人离美飞台。这时万隆会议已经开了三天,用杜勒斯的话来说,“会议进行得似乎相当好”,因为一批亲美的国家在美国的策划下正在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
雷德福和饶伯森选择了24日到达台北,这天正是万隆会议闭幕的日子,对美国来说台湾海峡危机也应当适时结束了。他们在台北告诉蒋介石,如果同意撤出金门、马祖,美国将提供掩护;在撤出金门、马祖之后,除非中共宣布放弃用武力夺取台湾,美国将和国民党一起对从温州至汕头的海面进行封锁,美国还将在台湾部署原子武器、防空力量、空军和海军陆战队。但蒋介石对这些条件根本不感兴趣,并决意不从金门、马祖撤军。他对两位美国官员说,他很同情总统的困难,“作为盟友他不能无视总统的国内问题”,他也不想让美国政府为了“中国政府的利益”而卷入武装冲突。但是他不会撤出金门、马祖,因为如果他那样做了,“连小孩子也不会相信他的政府在保卫台湾本土时会得到美国的帮助”,而且一旦放弃金门、马祖,那样只会增加国际上要求在台湾建立托管制度的压力。蒋的这些回答表明,他不仅对美国的支持抱着怀疑的态度,而且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方针持有戒心。
FRUS, 1955—1957, Vol.2, pp.497498,510517.
在读了雷德福与饶伯森从台北发回的报告后,艾森豪威尔不快地表示,这两个人自己也没有真正理解他的观点,因此“根本就不可能取得进展”。
FRUS, 1955—1957, Vol.2, p.523.然而就在此时,从万隆传来了消息,中国政府愿意为危机的解决做出新的努力。
八、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为缓解危机所作的努力
中国政府在台湾海峡危机时期曾多次声明,解放台湾和其他沿海岛屿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国家都无权干预。但在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由于美国已经蛮横地插手台湾问题,围绕着有关沿海岛屿问题,中国政府面临着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交织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局面。因此中国政府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更加重视外交和政治活动,力争在不与美国发生全面冲突的条件下,解决东南沿海岛屿问题。
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毛泽东会见尼赫鲁时说,中印两国都需要和平以建设各自落后的经济,中国至少需要20年的和平来发展经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愿意同任何国家,甚至美国进行合作,但是美国不愿让中国和平生活。毛泽东说,中国并不害怕战争,但“如果我们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我们就会劝他不要打仗。不管怎样,这个工作,由总理(指尼赫鲁)做,比我们做容易些”。毛泽东还提议召开一次世界和平会议,与会国家可以签订和平与互不侵犯条约。毛泽东的这些话表明了中国愿意同美国改善关系的设想。
S. Gopal, Jawaharial Nehru, A Biography, Vol.2, 1947—1956,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229230.
在1954年12月,美国以中国审判美国间谍案为借口掀起新的反华浪潮之后,中国政府一方面坚持司法主权不容外国干涉的原则立场,另一方面对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访华要求做出积极反应,表示为了和平,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同意他来北京商谈有关问题。周恩来在同苏联大使尤金谈话时指出,如果中国拒绝哈马舍尔德的访华要求,中国将陷于被动,西方会通过亚洲国家继续活动,有关国家会把这个问题提到科伦坡国家的会议上去讨论,这将对中国不利,甚至会影响到中国参加即将举行的亚非国家万隆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95页。
从1955年1月6日至10日,周恩来同哈马舍尔德进行了四次会谈。在拒绝向美国的压力让步的同时,周恩来向哈马舍尔德解释了中国政府在中美关系中各个问题上的立场。哈马舍尔德离京到达日本后对美国驻日大使说,中国并不打算把释放美国人员问题和解决远东其他问题相联系,但中国也不打算关闭解决问题的大门。他说周恩来已经成功地使他了解了该问题中内政与外交方面的不同性质,他对局势的发展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哈马舍尔德1月13日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洛奇也说到,中国的灵活立场表明了具有缓和中美双边关系的意愿。
FRUS, 1955—1957, Vol.2, pp.1213,2630.。
1955年1月28日,美英试图推出“神谕行动”,由新西兰代表向安理会提出一份文件,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的某些岛屿地区发生的武装敌对表明,这样一种局势的持续有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保持”,新西兰要求安理会尽早开会讨论此事。同日,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向周恩来通报了新西兰政府的建议。周恩来当时就明确地向英国代办指出,联合国讨论沿海岛屿问题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为了防止被指责为拒绝和平调停,中苏两国协商后,决定由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递交了一份文件。这一文件指出,台湾海峡和中国沿海岛屿问题是美国的侵略行动造成的,苏联政府要求安理会开会考虑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动。31日安理会通过表决采纳了新西兰与苏联的建议,并邀请中国派代表参加有关讨论。在此同时,安理会还通过了英国的建议,即在讨论苏联建议和决议草案之前,先完成对新西兰提议的讨论。这个建议实际上是试图取消对苏联建议的讨论。2月3日中国政府正式回电联合国秘书长,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新西兰建议。中国政府只有在讨论苏联提案,并从安理会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的情况下,才会同意派代表出席安理会。中国方面采取的这种立场迫使英美两国搁置“神谕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93100页。FRUS, 1955—1957, Vol.2, pp.178179,202203.
1955年2月2日,哈马舍尔德致电周恩来,了解中国是否同意派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并且表示“存在着有助于继续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发展或许会大大超过引人注目的公开活动”。6日,周恩来复信说,他在做出正式答复后才收到秘书长的这一电报。中国政府认为新西兰提议不会有助于局势缓和,相反它只会导致干涉中国内政和“两个中国”的后果。周恩来说:“如果要缓解紧张,说服工作应指向美国。中国不会拒绝就这一问题同美国直接谈判。如果美国有一点谈判的愿望,他们就应当接受直接谈判,放弃他们的战争威胁。”周恩来还保证说,“所有缓和紧张包括台湾地区紧张的每一个真诚努力都会得到中国的支持。”有关同美国直接谈判的建议是中国政府在危机发生后做出的最重要的和平努力,但是这一建议却没有得到美国的响应。相反,美国政府还认为哈马舍尔德与周恩来的通信超越了安理会的授权。
FRUS, 1955—1957, Vol.2, pp.226228,231232.
2月6日周恩来会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重申国际上搞“两个中国”的活动是不能接受的。同时,周恩来也通过印度外交渠道向英美表明了中国希望同美国直接谈判的态度:“造成紧张局势的正是美国,因此要由美国与中国直接谈判。”此外,中国也积极支持苏联提议召开国际会议的主张,并表示在国际会议召开之前愿和美国先进行外交接触。2月6日至10日,哈马舍尔德与周恩来再次交换信件。周恩来重申拒绝可能形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并再次建议美国“坐下来与中国面对面的谈判”。尽管哈马舍尔德在向美方转达这一信息时强调“中国真的想要谈判”,艾森豪威尔政府却仍然对中国的和平努力置之不理,甚至把它看作中国的手段,以便日后宣传美国拒绝和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100页;FRUS, 1955—1957, Vol.2, pp.264267.。
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消极态度,但中国并未放弃和平努力。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探讨和平解决危机的可能。万隆会议开幕之后,为了表示中国寻求和平与缓和的真诚意愿,周恩来于4月23日公开宣布了中国在台湾海峡危机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中国政府的这种立场立即受到世界各国舆论和政府的高度赞扬,为台湾海峡危机的缓和奠定了基础。
在此同时,中国已经全力投入国内经济建设。考虑到在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获得解放的情况下,国民党对大陆的破坏骚扰已经明显收敛,中国政府决定,在东南沿海作战的军事目的已基本实现的情况下,暂时搁置原定的攻占马祖岛的行动,并逐步停止对金门等国民党所占岛屿的炮击。在中国采取了这一系列缓和紧张的行动后,台湾海峡危机开始平息下来。
美国政府对周恩来在万隆的声明起初作了完全消极的反应。国务院经艾森豪威尔批准发表了一个声明,宣称只有在国民党代表参加的情况下才能和中国谈判。这实际上是公然拒绝谈判。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这一立场立即遭到了美国国内和世界舆论的强烈批评。从台北传来的消息也表明,蒋介石这次不会听从美国的意见主动从金门、马祖撤军。在这种情况下,杜勒斯同艾森豪威尔商讨后决定改变策略,接受与中国直接谈判的建议,放弃要国民党代表参加的先决条件。但杜勒斯同时也表示,美国不会背着“台湾”同中国讨论涉及国民党利益的问题。美国的这一姿态平息了舆论的不满,也使它自己走出了危机。然而,杜勒斯并不真正准备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美国只是希望借此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停火”
FRUS, 1955—1957, Vol.2, pp.507509.。
出于对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担心,在台湾海峡危机期间,亚洲一些中立主义国家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希望以此推动中美关系及远东地区国际局势向缓和的方向发展。
台湾海峡危机在1955年1月底进入最危险阶段。2月初英联邦总理会议正好在伦敦举行。印度政府利用这一机会同各国政府协商,希望找到解决这一危机的途径。2月3日,尼赫鲁对美国驻英大使说,印度已承认新中国,因此印度不可能承认占据中国领土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具有合法性。他指出,中国担心“台湾”在美国支持下反攻大陆,并且认为“在中国被接纳进联合国之前,要说服他们到纽约去是困难的”。
FRUS, 1955—1957, Vol.2, pp.200201.
印度政府非常希望能担任危机的调解者,因此一直寻找一种中间立场,从而对双方都能发挥影响。在中国拒绝参加联合国安理会的讨论以后,尼赫鲁立即通过驻华大使赖嘉文向中国传达信息,并表示想知道“怎样一种跳出目前僵局的出路是可以被接受的”。尼赫鲁还劝说中国“将台湾问题与其他问题分开处理,并降低其重要性”,希望中国能同意在其他问题上进行谈判。
Gopal, Jawaharial Nehru, A Biography, Vol.2, 1947—1956, p.234.
在了解中国政府愿意谈判的真诚意愿之后,印度政府又试图说服美国同意谈判。1955年3月24日,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向杜勒斯提议,中美两国可建立直接和非正式的联系,并表示“第三方面”在建立这种联系时是非常有用的。梅农还表示,印度相信中国没有扩张野心,中国认为台湾是自己的合法领土,中国把与“台湾”的战争看成是内战而不是侵略扩张。然而,美国政府此时对于中美外交接触根本不感兴趣,并且蛮横地表示,美国不会同意把“台湾”“转让给一个公开敌视我们的政权”
FRUS, 1955—1957, Vol.2, p.39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112页。。
万隆会议之后,局势有所缓解。印度政府更加希望能促使台湾海峡危机得到最终解决。1955年4月30日,尼赫鲁宣布他将派外长梅农访问北京,并表示不管是否得到有关国家的斡旋请求,印度都将寻求谈判的可能性。从5月12日到20日,梅农在北京同周恩来举行了六次会谈。中国方面向他解释了有关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并向他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及台湾国民党当局分别进行谈判。5月27日,尼赫鲁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国同意梅农到华盛顿介绍他的北京之行,他表示梅农此行已经取得进展。
FRUS, 1955—1957, Vol.2, pp.536537.
1955年6月9日,梅农在赴美途中顺访伦敦,他向英国方面透露了有关调停的设想。他说中美双方都有谈判愿望,中国将同意把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作为谈判主题之一。梅农说,他将建议中美双方采取减少紧张的措施。例如,美国可以允许想要回国的留美学生回中国,中国可以允许被拘押的美军人员家属去中国探望亲人。更进一步的措施是国民党军队逐渐撤出金门、马祖。梅农还说,中国虽然反对正式停火,但会默认将目前的平静维持下去,他认为中国会释放美方人员。
FRUS, 1955—1957, Vol.2, p.588.
伦敦立即把梅农的观点电告华盛顿。然而,杜勒斯对印度的这种立场非常不满。6月10日他向艾森豪威尔建议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以示美国不能允许把美军人员的释放与中国学生回国相联系。但艾森豪威尔似乎不愿看到局势再度紧张,在留学生问题上,他对杜勒斯说,“这些中国人来这时有着一种理解,即他们将被允许回国”,他认为美国在这方面不能理直气壮。艾森豪威尔明确说:“我们应该让所有的中国人回去。”当杜勒斯提到军方怀疑有两名中国学生接触了高级机密时,艾森豪威尔反驳说,“这事不应成为障碍,也许那些情报并不像设想的那么有价值”。艾森豪威尔的这一表态为中国留学生以后回国提供了可能。
FRUS, 1955—1957, Vol.2, pp.588589.
梅农在华盛顿也几次同杜勒斯会谈,但是对于印度提出的所有建议,杜勒斯都加以拒绝。杜勒斯一面声称美国政府并不要和共产党中国打仗,一面又不忘用核战争的前景及后果来恐吓梅农。对于印度的谈判呼吁,杜勒斯则表示过早进入谈判只会造成损害,“在未出现成熟的解决办法之前最好还是等待”。他说,中国人传统上就有让时间解决问题的才能,希望中国有耐心而不要强求不成熟的解决。梅农的调停活动以美印双方不欢而散而结束,梅农在最后离开华盛顿时沮丧地说,杜勒斯实际上对他表示,“走开,你没有什么用”。
FRUS, 1955—1957, Vol.2, pp.595605,631637.
杜勒斯并不只是拒绝印度的调停努力,对于其他亚洲国家的外交活动,美国也同样采取冷淡和不予理会的态度。万隆会议时,周恩来与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建立了友好关系,周邀请阿里访华,阿里也表示巴基斯坦愿促进中美进行谈判。当阿里征求美国意见时,美国国务院立即表示反对他访问中国,并说中美谈判只有在国民党代表以平等身份参加时才能进行。阿里对于美国的这种态度十分失望。
S. M. Burke, Pakistans Foreign Policy, An Historical Analysi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80181.
1955年2月初,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曾提议,科伦坡会议五国对台湾海峡危机的解决进行“联合努力”,但印度认为,局势可能因此而复杂化。5月下旬,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应邀访问北京。毛泽东在会见他时指出,中国人民非常需要和平,战争爆发会破坏革命成果,妨碍经济建设,中国愿以和平方式同美国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问题,可以同美国签订50年甚至100年的和平条约。27日周恩来也向印尼客人介绍了关于中美会谈的可能设想,并且表示欢迎同中美两国都有友好关系的国家为会谈铺平道路。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说,印尼政府准备对中美关系进行斡旋。具体设想是,通过各方采取缓和紧张的行动创造良好气氛,为中美双边谈判提供所需的一切帮助。他还提到,中国如能在释放被押的美军人员问题上采取行动,将有助于美国舆论朝有利的方向发展。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回国后指示印尼驻美大使会见美国官员,以了解美国政府对斡旋的态度。但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帮办墨菲在听完印尼大使介绍情况后说,“只要中国仍然利用美国战俘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美国就不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中国已释放四名美军人员的行动也被说成是没有意义的,墨菲甚至把中美在谈判问题上不能取得进展的责任推在中国头上。美国国务院的这种态度当然也使印尼政府的斡旋工作难以开展。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273283页。
另一位真诚希望解决危机,改善中美关系的亚洲领导人是缅甸总理吴努。吴努在1955年2月份甚至想去台湾调停,因中国方面的反对而未成行。吴努认为中美冲突将导致灾难性后果,势必影响缅甸的重大利益。他相信缅甸能使中美双方坐到谈判桌上来。万隆会议前后,吴努多次和周恩来接触,他要求中国采取“理性”态度,对中国的和平努力表示赞赏。但是,7月初,吴努访问美国时也碰了钉子。当他向杜勒斯问到美国对中国直接谈判的要求有何反应时,杜勒斯说美国已经公开作了回答,美国将只在有关“双边的问题上”进行会谈。杜勒斯说,已经有五个调停人试图进一步探讨会谈问题,这显然是回绝缅甸的调停愿望。杜勒斯倒也不是无中生有,因为除了印度、巴基斯坦、英国提出居中帮助之外,连菲律宾外长罗慕洛、泰国的旺亲王在万隆会议后都向美国作过类似表示。
W. C. Johnstone, Burma’s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63, pp.8995.虽然亚洲中立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缓和台湾海峡危机的外交努力没有获得预期的成果,但是作为世界舆论的一部分,他们表达的和平意愿是美国政府不能忽视的,这种意愿有助于防止美国采取更为冒险的行动。他们向中美双方传达的信息对于形势的缓和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杜勒斯拒绝亚洲中立主义国家的调停努力并非偶然。美国这一时期一直对中立主义在亚洲的影响日益增长感到不满,担心它的亚洲盟国会因此动摇,从而妨碍美国在这一地区孤立中国、遏制共产主义的基本战略。正因如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亚洲国家的和平调停活动一直冷淡地加以拒绝,私下里则依靠英国与中国政府进行沟通。
1954年日内瓦会议结束以后,中英双边关系有所改进,两国建立了代办级的外交联系,贸易往来也有了进一步发展。1954年秋季以后,面对日益紧张的远东局势,英国政府不能不感到忧虑,并试图扭转这种局面。英国极不愿意看到美国为中国的两个沿海小岛冒战争风险,更何况中美军事冲突还可能因中苏同盟条约而发展为全面战争。因此,英国政府希望台湾海峡危机能尽快缓和。但为了维持自己在亚洲所剩不多的利益,英国又必须依靠美国的“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支持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亚洲战略。因此,英国政府并没有解决这一地区对抗与紧张形势的根源的打算。英国政策中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它的外交活动的空间是很有限的。
英国政府解决台湾海峡危机的设想是:美国让国民党当局同意从沿海岛屿撤出军队,在此情况下中国默认国民党占据台湾的现状,放弃以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1953年1月29日,首相丘吉尔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国让蒋介石主动从沿海岛屿撤军,这样西方就可以“在台湾海峡划出一条清楚和明确的界线”。同一天,英国驻美大使也对杜勒斯指出,如果战争爆发,英国及其他承认沿海岛屿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国家将无法支持美国,“西方联盟将会破裂”。2月初,英国让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向美国表示,只要美国表示将使国民党军队撤出所有沿海岛屿,它们就支持美国的台湾政策。
但是杜勒斯对于英国的这种设想不予理会,他利用英国害怕战争爆发的心理,一再恐吓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美国不能坐视中国加强作战准备,美国可能不得不对某些地点进行打击。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又把外交活动的努力转向中国,希望中国做出实质性让步。2月28日,艾登致电周恩来说,英国了解中国在台湾和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立场。中国政府能否公开或私下发表声明,在维持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主权要求的同时,表示不打算以武力实现这一要求。艾登表示,如果中国同意上述做法,英国愿意同美国政府进行探讨,就和平解决所有这些岛屿的问题找到有利于中国的方案。他还表示愿意同周恩来在香港会面。在同苏联协商后,周恩来3月1日复函艾登说,英国的意见只会使美国的侵略合法化,艾登如愿意讨论如何创造消除台湾地区危险局势的必要条件,欢迎他来北京会晤。
FRUS, 1955—1957, Vol.2, pp.308312,33833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102103页。
英国政府这一时期的外交活动没有取得进展。英国对于中美双方在冲突中的政治意图并不了解,此外它也缺乏影响事态发展的有效手段。尽管如此,英国没有放弃它的外交努力,伦敦一直同莫斯科、新德里保持密切的联系,希望能找到缓和局势的突破口。与此同时,英国也对美国采取了一些牵制行动。杜勒斯一直想利用“神谕行动”来加强对美国的舆论支持,为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披上合法外衣。对于英国的拖延,杜勒斯十分不满,并多次催促英国同意行动。3月下旬,艾登向杜勒斯指出,现在提出“神谕行动”将使公众认为,这是试图保证蒋介石在沿海岛屿的地位。他还说,这一行动“无助于使中国人克制敌对行动”。对于艾登的这一态度,杜勒斯极为愤怒,他立刻复电说:“我原来预期苏联会否决这个决议,但绝对没有想到这个否决会来自你!”
FRUS, 1955—1957, Vol.2, pp.397398,404405.
英美在台湾海峡危机问题上的分歧使两国关系变得紧张。由于英国在许多方面都依赖美国的支持,英国政府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立场,更主动地向美国靠拢。3月下旬艾登向美国建议,让亚洲国家领导人在万隆会议上向中国施加压力,要中国“放弃使用武力”。艾登说:“来自亚洲人的压力可能比我们在安理会说的话更能有效地威慑中国人。”4月18日,艾登在一个文件中写道:如果台湾问题使英联邦与美国的友好关系破裂,那将是悲剧性的事。“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以防止这样的事发生,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的计谋,我们决不能落入这个陷阱。”
M. Dockrill, and J. W. Young,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45—1956, UK Palgrave, Macmillancom., 1989, p.167.英国政府的这种反复当然使它不能公正地进行外交斡旋,也限制了它在这场危机中能起的作用。
在周恩来于万隆会议上公开提出中美谈判建议之后,美国政府不得不做出同意谈判的反应,英国对于局势的缓和松了一口气。5月9日,伦敦指示驻华外交官杜维廉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意见,杜维廉向周恩来表示,“英国急于抓住能使英国起作用的机会”,并询问中方是否有口信转告美国。周恩来指出,中国将在研究以后给予英国正式答复。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杜勒斯讲话中关于中美谈判“可以没有蒋介石参加这一点”,但杜勒斯说中美谈判的主题是“停火”,这是文不对题,中美之间并不存在战争。中美之间应讨论缓和紧张局势问题。
FRUS, 1955—1957, Vol.2, p.562.《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110111页。
1953年5月26日,周恩来通过杜维廉向英国作了四点答复:(1) 为了推动谈判,双方应采取一些缓和台湾地区形势的行动;(2) 双方可通过苏联、英国、印度等国政府进行外交接触;(3) 中方认为谈判的主题应是减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4) 蒋介石集团不能参加国际会议,但中国政府不拒绝,而且建议同他们直接接触
FRUS, 1955—1957, Vol.2, pp.566, 581.。为了表明中国的诚意,周恩来在5月13日向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指出:有两种解放台湾的可能途径,即作战的方法或者和平的方法,只要有可能,中国人民将努力通过和平手段来解放台湾。5月30日,中国政府宣布释放四名未被判刑的美军被俘人员。
然而中国的这些行动并没有得到美国的响应。在5、6两个月中,艾森豪威尔政府虽然口头上表示愿同中国谈判,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打算通过谈判解决远东地区的重大国际问题,他们只是试图利用缓和的气氛来迫使中国释放所有被拘押的美方人员,同时使中国不攻打沿海岛屿的局面“长久化”,自己却没有任何的谈判计划和妥协设想。
FRUS, 1955—1957, Vol.2, pp.570, 589591.
此时,台湾海峡危机虽然因中国的行动而有所缓和,但局势仍不明朗,英国对此仍然感到担忧。1955年6月20日,新任英国外交大臣麦克米伦在旧金山会见杜勒斯时说,梅农可能把事情弄糟,中国方面可能以为会形成一个明确的方案,而其一旦失望,就可能重新诉诸武力。他问杜勒斯对未来有何看法。杜勒斯说,美国可能提议同中国交换特派员,处理被拘押美国人员及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他说这样做是“让中国人有一点面子”。至于长期问题,杜勒斯说,除了等待之外美国无事可做。“也许在5年以后我们才能知道,中共真的能维持其对国家的控制还是会垮台。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要看他们是否会采纳某些行为准则,以致可以被文明社会所接纳。”
FRUS, 1955—1957, Vol.2, pp.606608.
杜勒斯的这种傲慢态度增加了英国的担心。1955年6月3日麦克米伦再次致电杜勒斯,希望美国能采取一些行动缓和紧张局势。麦克米伦指出,美国的行动将有助于抵制苏联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首脑会议上提出召开远东问题国际会议的要求,而且还能防止中国可能采取“一意孤行”的行动。
FRUS, 1955—1957, Vol.2, p.642.
英国的这一提醒对杜勒斯也许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杜勒斯当然不会忘记一年多以前由于自己同意召开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而引起的一系列政治麻烦和挫折。同时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反对与中国互派特派员的设想,认为那将不符合美国承认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原则,因此,杜勒斯放弃了原来的考虑,并在7月初决定,提高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进行的低级别会谈的层次。7月8日,杜勒斯要求英国政府向中国转达将日内瓦会谈升级为大使级会谈的口信,并明确说不要尼赫鲁在这件事上当中间人。11日,美国通过伦敦向中国发出了正式函件。这一函件说:中美双方在日内瓦进行了多次关于遣返各自要回国的平民问题的会谈,结果却令人失望。如果会谈能在更有权威的层次上进行,将有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间某些其他有争执的实际问题。函件建议双方指定大使级代表在双方同意的时间于日内瓦举行会谈
FRUS, 1955—1957, Vol.2, p.627628,641.。
麦克米伦似乎认为美国的提议太空泛,他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称,美国的设想“太僵硬”,中美之间有许多缓和紧张的问题可谈,如停止攻击商船,和平利用公海等。他认为可以进行一些相当普遍和实用的对话,而又不会损害美国对国民党局的“义务”。麦克米伦的这些建议当然也是为了英国自己的商业利益。
FRUS, 1955—1957, Vol.2, p.642.
英国新任驻华代办欧念儒于1955年7月13日向中国递交了美方的函件。15日周恩来也通过英国回复美方的建议,同意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并且讨论和解决双方之间“有所争执的某些其他的实际问题”。在此后两周中,英国还为中美双方转交过几次信件,商定了有关举行大使级会谈的日期和发表新闻公报的措辞。以1955年8月初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的举行为标志,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终于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120121页;FRUS, 1955—1957, Vol.2, pp.660,675676.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虽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它对美国的依赖,以及它仍然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有扩张和侵略野心的国家”,这种立场使它在台湾海峡危机中的外交斡旋活动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在危机前期,英国实际上试图形成一种“一中一台”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当时是中美两国都是不能接受的。但是英国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杜勒斯的冒险政策有牵制作用。万隆会议之后,中美会谈露出一线希望。英国政府继续鼓励亚洲国家进行调停,同时它也积极敦促美国采取具体行动,以便推动谈判能正式举行。此时英国并没有提出它自己的调解方案,但它的努力却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对于中美两国就日内瓦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是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美之间最严重的对抗,它极大地危及了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通过这场危机来打击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威望,遏制亚洲地区国际局势向不利于它的方向发展的趋势。然而美国的这种目标并未实现。在危机中,中国政府采取的既坚定又灵活的立场,得到了众多国家的理解与支持,扩大了外交活动范围和自己的国际影响。由于美国的蛮横干涉,中国未能完全解放东南沿海的岛屿,解决台湾问题所需要的外部条件也未能形成。但中国迫使美国政府放弃了完全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做法,迫使它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这一危机也表明,美国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障碍,中国必须通过持久不懈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探析
*
*本文原发表于由时殷弘和蔡佳禾主编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6—1958》,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现在原文标题上加了“探析”二字。
1955年春夏,在中国政府努力推动下,美国政府不得不同意在日内瓦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因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而形成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但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利益,加强针对中国的“反共”军事同盟体系,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继续奉行遏制中国的政策,继续把台湾当作反华的基地,并试图长期阻挠中国人民统一自己的国家。美国的这一政策使台湾海峡地区仍然不得安宁。
一、日趋紧张的台湾海峡局势
1. “美台”关系中的龃龉
1954年,美国同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为了防止被蒋介石拖入中国内战,美国政府同时又迫使蒋介石接受一项秘密协议,即未经同美国协商,台湾当局不得对大陆采取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一秘密协议一定程度束缚了国民党当局的行动,蒋介石为此感到非常不满。此外,美国还派出大批军事和平民顾问进入台湾,他们在台湾颐指气使、耀武扬威,在台湾民众中,包括在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中,激起了一股不满美国的怨气。
同时,美国人对蒋介石实施的独裁统治也有不满,他们试图在台湾高层人士中培养亲美力量,对台北市长吴国桢和陆军司令孙立人似乎尤其青睐。对此,蒋介石当然不能容忍。1953年吴国桢被迫出走美国。次年,吴公开指责国民党统治是特务专权和不民主,美国主要报刊竞相刊登这一消息,国民党当局的形象在美国严重受损。
1955年夏,已失去陆军司令职务的孙立人在军中搞秘密串联,蒋怀疑他要发动兵变。不久,孙及其亲信均被逮捕。为了除去这一心腹之患,国民党当局迫使孙的亲信郭庭亮承认自己是中共“间谍”,并以此为由免去孙立人职务,加以软禁。对蒋介石的这一手,美国政府非常恼火。一贯亲蒋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会见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表示他毫不怀疑孙立人的忠诚,要求“台湾”进行“公正的”调查。美国国务院还指示美外交官向外散布消息,说美国认为孙立人不可能对“自由中国”不忠,当局对其的指控是“令人无法置信的”
Department of State, U.S.A.,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 1955—1957, Vol.3, pp.6970.
。美国报刊也为孙立人鸣不平,说他受到了有反美情绪的人的迫害。
美国政府还试图让国民党当局接受“两个中国”的局面。从1956年起,美国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玩弄“两个中国”把戏。蒋介石很清楚,这一政策对国民党当局蕴藏着潜在的危险。美国还一再拒绝蒋介石的要求,不同意国民党军队制订“反攻大陆”的军事原则和具体计划
FRUS, 1955—1957, Vol.3, pp.331, 413.。
由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美国对蒋氏父子的动向很不放心。1957年1月“美联社”发消息说,蒋经国已经把中共的和谈条件通知了蒋介石,甚至编出了蒋经国已与中共领导人陈毅进行会谈的故事。美国情报人员在香港也放出“蒋经国通共”的流言,试图削弱蒋经国在台湾的地位。这使双方的关系更为紧张
黄嘉树:《国民党在台湾,1945—1988》,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第209页。。
1957年3月20日,美国顾问团的一名士兵罗伯特·雷诺开枪打死了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少校军官刘自然。雷诺声称他出于自卫,因为刘偷看其妻子洗澡并首先对他进行了攻击。但台湾报纸刊登的消息却说,刘实际上是在同雷诺进行一笔黑市交易,因发生争执而被雷诺杀死。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在向国务院的报告中也承认,要证明雷诺所说的自卫是“有些困难的”,因为雷诺开了两枪,而第二枪是在雷诺追逐刘自然跑出其住宅一段距离以后才开的。随着审判的临近,台湾舆论表达了公众对美军暴行日益强烈的情绪。4月16日,台湾警方的正式调查报告认定,雷诺杀人是“蓄意行为而非自卫”
FRUS, 1955—1957, Vol.3, pp.524525.。
但是,根据美台之间订立的有关协定,台湾司法当局无权审判此案。5月23日美国军事法庭宣判雷诺无罪开释。24日,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向美国提出抗议,并要求美方重审此案。同时刘自然的妻子也到美国“大使馆”门前绝食抗议,激起台北市民的普遍同情。大批围观者随后到美国“大使馆”前示威。下午,示威活动失去了控制,人们冲进美国“使馆”和美国新闻处,殴打里面的美国人,砸毁汽车、电话、家具等用品,甚至抢走了部分机密文件。傍晚,从香港赶回台湾的美国“大使”兰钦从机场直接到台“外交部”提出最强烈抗议。7时30分,他要求叶公超陪他返回“使馆”和美国新闻处。尽管此时已经有大批警察到场,但他们乘坐的汽车还是被扔了石头。直到晚上9时,台湾当局才动用军队平息了事态
FRUS, 1955—1957, Vol.3, pp.524535.。
美国人怀疑这是一起有预谋的反美活动。26日下午,兰钦见到蒋介石时强调说,这是一起预谋与自发相结合的事件。他指出现场有人在分发10元面额的新台币,鼓动人们参加暴乱。27日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汇报时也认为:“台北发生的暴动从一开始就是精心策划的,那个寡妇得到了官方的某种支持。政府当局最初的维护秩序的行动是不明确的,而且肯定是不积极的。”他说,“无罪释放的宣判触到了民族主义最敏感的地方,即人们最痛恨的治外法权。似乎很可能是政府允许了示威的进行,以此作为向美国施加一些压力的手段”。艾伦·杜勒斯说,有一名国民党高级官员认为可能是蒋经国挑起了这场暴乱,但他怀疑这一指控的可靠性
FRUS, 1955—1957, Vol.3, pp.538541。
台湾存在着反美情绪是毋庸置疑的。兰钦承认,与亚洲其他地方一样,在台湾也存在不信任和不喜欢西方影响的暗流。“将近有11000名美国人生活在台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开着新车,享受着各种特权,对中国人来说,他们似乎有着非常高的生活标准。这些美国人出现在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其规模绝不亚于殖民国家在其殖民地之中。”他说,“以上环境中潜在的愤怒无疑部分地要对5月24日事件负责。”在谈到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情绪时,兰钦认为这些人“看不到未来前途,并且受到‘小卒子情绪’的折磨,唯恐自己的最终命运被别人决定,或许还会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决定”。他认为,“五·二四事件”的发生与这些人要显示其独立和不满有关
FRUS, 1955—1957, Vol.3, p.536.。
“五·二四事件”使美国受到很大的震动。他们无法理解,靠美国才能生存的台湾怎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反美情绪。一些报刊认为台湾当局要负一定责任,并指责国民党“忘恩负义”。不少国会议员表示,他们要重新考虑对台援助问题。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接到报告的当天也受到震动,他说亚洲各国都可能发生类似事件,美国必须对亚洲国家有非常严肃的看法,如果他们是如此仇恨美国,美国继续留在那儿将是很不明智的
FRUS, 1955—1957, Vol.3, p.528.。
4个月后,总统特别助理、亲蒋的前众议员詹姆斯·理查兹到台湾调查这一事件。他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说,有证据表明,警察没有认真控制“暴徒”。可能蒋经国和“青年服务团”预先知道会发生有组织的抗议,但没人认为他预先知道“大使馆”会受到攻击。理查兹说:“似乎存在着的一种轻度的挫折感,它来自中国人对是否还真有机会回大陆的怀疑。”他在结论中说:台湾的士气,总的说来,现在还不太坏,“但是正在缓慢地恶化”。“岛上自然有一种潜在的反美情绪,但还没有达到危险点。”
FRUS, 1955—1957, Vol.3, pp.624629.
2. 蒋介石拒绝“第三次国共合作”
万隆会议以后,亚洲地区的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中国领导人将自己主要的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经济建设方面。为了推动国际形势进一步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使台湾问题得到早日解决,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方针。
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生活在台湾的人民是中国的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周恩来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956年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二次会议的决议说,希望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和海外的人员,站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2266,2354页。。
由于美国开始推行“两个中国”的活动,中共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也在加快形成。1956年6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说,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周恩来认为,现在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正在增长。这首先是因为目前国际形势肯定地趋向缓和,美国的干涉行为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周恩来郑重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他还提出了“爱国一家”、“既往不咎”的方针,表示欢迎一切爱国的人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功立业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24002403页。。
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想法。他说,“我们同蒋介石也是这种微妙关系。我们要同他恢复友好和合作的关系。我们过去合作过两回,为什么不能合作三回呢?但是蒋介石反对。他每天反对,我们就每天说要同他合作。”
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提出与美蒋矛盾尖锐化有一定关系。1956年秋,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势力加紧活动,他们利用蒋介石“祝寿征言”的机会,试图劝蒋退休。香港亲美分子褚定民1957年1月说只要胡适“登高一呼”,海外华侨必群起响应,台湾同胞及三军人员受外来的鼓励,必定有所表示,美国友人间对于中国人民的一致要求蒋介石退休的运动,势必重视。褚定民的文章实际上点出了美国同这件事的联系。3月,毛泽东分析说:“台湾的情况现在有变化。美国现在想搞垮蒋介石。它正在扶植一派人,想用这派人来代替蒋介石。现在我们需要帮助蒋介石反对美国。因为问题是:蒋介石好些呢,还是美国所扶植的更亲美国的势力好些?台湾像目前这样作为美国的半占领地好些呢,还是台湾成为美国完全的占领地好些?”中国领导人认为,在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问题上,蒋介石是持反对态度的。周恩来明确说道:“台湾政府反对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我们同蒋介石倒是统一战线。”
黄树嘉:《国民党在台湾》,第256260页;外交部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74页;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205页。
这一时期,中共建立了对台工作小组,由李克农和罗瑞卿负责。中共领导人还希望开辟与国民党进行对话的秘密渠道。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民主人士李济深的前卫士长、英国人马坤,请他以后去台湾时向蒋介石转达几句话。周恩来说,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最后一次谈判是在南京,那是在1946年。那次谈判破裂以后,接着就打了三年内战,至今还没有结束,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说,我们永久不再谈判。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
马坤说,现在英美势力还不愿劝蒋放下武器。周说,这不要紧,蒋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而这件事也会像你所说的那样载入历史。”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341页。
7月16日,周恩来会见了来自香港的原国民党中央社记者曹聚仁,请他向台湾方面转告中共的和谈意愿。周恩来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有国民革命北伐的成功,第二次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中国共产党要求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建议传到台湾以后,蒋介石于1957年初决定,派“立法委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希濂的哥哥宋宜山以探亲名义到北京探听情况。4月宋宜山从香港到达北京。他见到了周恩来,并且与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进行了商谈。中共提议的主要内容是: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成为中国政府管辖下的自治区,实现高度自治,台湾政府仍归蒋介石先生领导,共产党不派人去干预。而国民党可以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不许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
马齐彬等编:《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第11961197页;李松林:《蒋介石晚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4页。。
宋宜山回香港后以书面方式汇报了会谈内容,但蒋没有做出进一步反应。蒋介石本来就没有合作的诚意,在他看来,中共举行谈判的目的是要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失效,同时还想要挟美国“迫我退出金、马等外围岛屿”,最终“唾手而得台湾”
李松林:《蒋介石晚年》,第265页。
。其次,“五·二四”事件以后,美国对他和蒋经国猜忌已经很深。他与中共的秘密往来如果暴露,国民党同美国的关系将更加难以维持。其三,1957年下半年,中国大陆开展了反右派运动,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遭到政治批判,国共会谈的气氛受到影响。因此,蒋介石很快从试探的立场上退了回去。
蒋介石拒绝国共合作,但对于中美大使级会谈心存疑虑,唯恐美国政府会抛弃他。虽然中美双方在会谈中没有取得进展,但由于西方媒介认为,双方可能在“不使用武力”方面达成协议,台湾对此非常不安。11月17日,叶公超写信给杜勒斯说,如果中共和美国达成协议,这将被世界各国看成是“美国向着承认中共政权又走了一步”,这可能在国内和国际增加中共政权的威望,损害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他胡乱猜测说,中共可能会同意放弃使用武力,以便与美国公开谈判政治解决台湾问题
FRUS, 1955—1957, Vol.3, pp.175176.
。国民党的这种猜疑表明,他们同美国的关系是很不稳定的。
1957年10月,国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台北举行。蒋介石在会上说,国民党已从“改造时期”转入了“反攻复国”时期。这次大会的任务就是“决定反攻复国的总方略”。“行政院长”陈诚在大会上也说,“我们由保卫台湾进而建设台湾……更进而反攻大陆了”。他强调“一切为了达成反攻复国的任务”。大会通过的“国民党政纲”还规定“光复大陆”的中心是对大陆进行“抗暴”和“策反”鼓动,以便里应外合推翻中国共产党政权。此后,台湾当局加紧“反攻大陆”的准备,并进一步在沿海地区进行军事窜扰活动
郭传玺等编:《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史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4547页。。
3. 陷于停顿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进行。中国希望会谈能使亚洲局势继续得到缓和,为解决各种双边问题创造条件。在中方的议程表上,讨论台湾问题、争取实现两国外长直接会谈,以及建立两国经济文化联系等实质性内容被列在优先地位。为了使会议有一个良好的气氛,中国政府在会谈开始之前宣布,提前释放11名美国空军人员。这些美国军人在朝鲜战争时期因驾机进入中国进行侦察而被逮捕和判刑。
但是,美国对于中美大使级会谈持消极态度。在美国政府内部,决策者对于谈判如何进行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国务卿杜勒斯坚持美国不应同中国举行实质性的谈判,并预言除了事实上的停火之外,会谈不会有任何结果。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沃尔特·乔治认为,可以利用这一机会重新考虑对华政策,重建与中国的关系,并鼓励两国举行外长会谈。但是,在国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派持反华的立场。他们认为,总统和乔治“走得太远了”。当时担任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詹姆斯·理查兹在会谈前特意拜访了杜勒斯,他说众议员们理解他的困难处境,他们实际上是一致支持杜勒斯的立场的
FRUS, 1955—1957, Vol.3, pp.1011.。
对杜勒斯来说,举行这一谈判本是为了应付舆论的压力。在给美国谈判代表、驻捷克大使阿历克西·约翰逊的谈判指示中,杜勒斯明确规定,美国在谈判中不得涉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承认,不得涉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权利”。杜勒斯指出,美国在谈判中应当首先促使中国释放被关押的美国人,并规定实现这一目标是进入其他实质性问题谈判的前提
FRUS, 1955—1957, Vol.3, pp.526527.。
会谈在8月1日开始。双方同意首先谈判侨民回国问题,然后讨论其他有争执的实际问题。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艰苦谈判,双方终于就滞留在对方国家的人员的回国问题达成了妥协。在取得这一进展之后,美国方面采取了极为敷衍的态度,使会谈无法取得质性进展。中国驻波兰大使、中方谈判代表王炳南提出,双方可以讨论台湾问题、美国取消对华禁运和周恩来与杜勒斯直接会谈等议程。但美国方面却坚持要谈在台湾地区“双方保证互不使用武力”问题。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美国的提案作了认真研究,他在给王炳南的指示中指出:“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侵占台湾已经成了国际争端,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已影响到东南亚的和平稳定与安全,但是造成这种局势的,首先是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它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应该放弃对我国使用武力,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另一方面,从中国方面来说,台湾在历史上、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人民愿意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无权要求我们不使用武力。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不容混淆的。”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3158页。
由于双方无法就具体议程达成一致,在中方建议下,会谈转而由各方自由提出自己的观点。中方表示,两国可以讨论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而不诉诸武力问题,但中国不会放弃解放台湾的权利。但美方继续坚持其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并于11月10日提出了一个方案:要求两国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台湾地区,“除了单独和集体的防御外”,同意放弃使用武力。这是要中国在放弃台湾的权利的同时,承认美国在台湾地区有防御的“权利”,中国代表很坚定地拒绝了这一方案。
在谈判进行了一年以后,中美双方在实质性问题上仍然没有进展。为了打破僵局,周恩来在1956年8月宣布,已向美国15家新闻机构发出邀请,欢迎他们派记者到中国采访。尽管艾森豪威尔承认,阻止记者访华是要挨骂的,但出于敌视心理和阻止气氛缓和的需要,杜勒斯不顾新闻机构的抗议,蛮横地拒绝了美国记者的访华要求。国务院还威胁要吊销擅自去中国采访的记者的护照,甚至威胁要以战争时期去敌对国家的有关法律对其治罪
FRUS, 1955—1957, Vol.3, pp.417418, pp.421422.。
8月21日,王炳南提出,中美双方各自采取主动,“消除现有的阻挠两国之间贸易障碍”的议案。9月22日,王炳南又提出关于“消除干扰相互接触与文化交流的障碍”的议案。但10月4日约翰逊回答说,在美国在华人员被全部释放和就“放弃使用武力”问题达成协议之前,美国不会讨论贸易与文化交流问题。10月18日,王炳南在会谈中强烈批评美国的消极立场。他说美国政府“故意阻止大使级会谈取得进展,并且害怕中美关系得到任何改进”。
王炳南说,中国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却没有得到美方的响应,为了打破这种停滞的局面,中国方面正式要求举行两国外长会议,“讨论缓解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以及中国和美国相互放弃使用武力、人民接触和文化交流等问题”。但这一要求再次遭到美国的拒绝。1957年12月,中国方面又提出了两国司法协助问题议案,美国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和不必要的”。
FRUS, 1955—1957, Vol.3, pp.422423, pp.432, 435.
进入1957年后,中国对日内瓦会谈已不抱什么希望。3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一个东欧代表团时坦率地说,中国同美国进行谈判是“为了在外交上采取攻势。这个谈判已经搞了一年多,到目前之所以一直没有破裂,是因为双方都想把谈判破裂的责任加在对方身上”。他说,只要美国愿意,中国就陪它谈下去,它要谈多久就谈多久。周恩来在11月15日会见各国驻华大使时也指出,如果美国不从台湾撤出一切武装力量,而中国同意发表互不使用武力的共同声明,“那就等于承认台湾地位为合法,我们不能上这个当”。周对大使们说,中国可以十年、二十年地长期谈下去
《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版,第287页;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53261页。。
美国在日内瓦谈判中采取的是“拖而不断”的消极方针。周恩来的讲话迫使美国调整策略。11月下旬,助理国务卿饶伯森与杜勒斯、约翰逊大使讨论了可能接替约翰逊的谈判人选。同时,饶伯森提出了一个由一秘爱德温·马丁出席谈判,使会谈“降级”的建议。饶伯森说这是一个表示对中国不满的机会,也是对周恩来15日讲话的“回答”。他说美国不用担心这会导致中国中断会谈,而且这还能给美国在有需要时恢复大使级会谈的行动自由。杜勒斯表示他不反对“降级”,但他表示“破裂是不可取的”
FRUS, 1955—1957, Vol.3, pp.639, 641.。
饶伯森的方案得到了批准。12月12日,约翰逊对王炳南说,他已奉调担任新职,所以不能继续与王炳南的会谈,但美国政府有决心并愿意耐心地谋求解决分歧,因此希望日内瓦会谈继续进行,爱德温·马丁将被指定为美国的代表。对此,王炳南当场问道,美国政府是否故意要改变大使会谈的级别,并进而改变会谈的性质?王炳南说,中美进行的是大使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个参赞,不能代表大使,美国方面的这一做法是很不严肃的,中国不能接受。约翰逊坚持马丁是美方代表,王炳南不得不拒绝下一次的会期,谈判陷于中断
FRUS, 1955—1957, Vol.3, pp.643644, 657659;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65页。。
日内瓦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多少进展,但它是中美两国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分歧的象征。中国认为,“降级”是美国拒绝会谈的借口,是美国在台湾地区加剧紧张局势的表现。1958年1月和3月,王炳南和他的助理赖亚力曾分别致函约翰逊和马丁,敦促美国尽早指派大使级的代表,指出“使会谈长期处于有名无实的境地是不能容忍的”。4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美国“竭尽拖延的能事,力图背弃诺言,破坏协议”。声明还指出,“在全世界人民强烈要求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压力下,美国不能公然破裂中美会谈,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害怕形势的和缓将使它的冷战政策更不能得逞,因此,它不仅阻挠会谈取得任何进展,而且还企图使会谈根本失去作用。这就是四个月来美国耍尽无赖手法,使中美会谈陷于长期停顿的根源所在”。
美国政府一方面进行强词夺理地辩解,另一方面国务院在4月14日又表示“应该继续会谈下去”,并表示美方会尽快指定一位大使来担任美国代表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5942599页。
。但实际上,美国政府仍在玩弄拖延的把戏。在此同时,美国领导人不断公开发表各种反华讲话,有意使用极为敌对的语言刺激中国。美国还操纵表决机器,让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名义进入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试图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对于美国的这些敌对行为,中国方面已经越来越不能容忍。
4.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338次会议
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共潮流。蒋介石也认为自己“反攻”的时机接近了。1956年4月16日,蒋介石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试图让美国支持他“反攻大陆”的政策。他在信中一方面吹捧美国提出的“解放被奴役的人民”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批评美国说,仅靠遏制政策,是阻止不了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侵略的。蒋介石说,为了加强对中共的压力,台湾必须被给予机会,以便尽早实现对“铁幕”的突破。为了赢得美国对其武力反攻计划的支持,他在信中说:“一旦自由中国的军队在大陆沿海建立滩头阵地,全国人民极有可能起来造反。”蒋还说,苏联是不会对中国的局势进行干涉的,因为苏联不想让自己卷入一场大规模战争中去。“即使苏联选择干预对华战争,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他们的直接军事行动的范围也只会限制在黄河以北。”
FRUS, 1955—1957, Vol.3, pp.341348.
自作聪明的蒋介石很快在美国人那儿碰了钉子。美国政府认为,蒋介石自己根本没能力反攻大陆,他想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艾森豪威尔回答蒋介石说:“我不相信,以武力来解决共产党控制中国大陆这个困难问题会符合我们两国的最大得益。我们不认为,动用军事力量是解放共产党统治下人民的一种适当手段。而且我们反对发动可能使世界陷于一场会失控的大火中的行动。”
FRUS, 1955—1957, Vol.3, pp.361362.
这次通信表明,此时,艾森豪威尔对台湾当局的“反攻”计划没有兴趣。
在东欧发生政治动荡后,特别是台湾发生了“五·二四事件”后,美国政府对了于台湾当局的作用有了新的看法,这一变化对台湾海峡的局势产生了影响。
1956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部门认为,美国对台湾援助计划开支巨大。在寻找原因时,联邦预算总署的代表曾多次去台湾考察。他们发现,为了有能力对中国大陆发起反攻,国民党当局希望得到更多的军事装备。预算总署认为,应把国民党的使命限制在防守台湾、澎湖和沿海岛屿方面。他们认为,1955年通过的NSC5503号文件中提到的,“台湾”能对东亚集体防御做出贡献的规定只是这一使命的“副产品”。因此,预算总署建议,“明确告诉‘中华民国’,除了世界形势或中国大陆的条件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我们未来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计划将不会以‘中华民国’重返大陆执政的设想为前提”。
FRUS, 1955—1957, Vol.3, pp.614615.
但是这一想法遭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的反对。他们认为,NSC5503号文件为“进攻性使用”台湾军队保留了可能。他们承认总统曾在1954年9月28日下令,“在目前情况下”停止对中共领土的大规模袭击,但那并不意味着放弃在任何时候“进攻性使用”国民党军队的可能。国务院和军方认为,国民党军队是远东地区集体防御力量中的重要因素,“对中共的侧翼构成一种经常威胁”,是针对大陆的“最有价值的军事工具”,因此,他们要求继续规定国民党军队的使命应包括“做好在台湾、澎湖和沿海岛屿之外地区进行进攻性行动的准备”。
联邦预算总署认为,军方和国务院的目标是不现实的。因为尽管美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但是没有美国的干预,国民党仍然不能守住台湾和沿海岛屿。经验表明,要在亚洲其他地区利用国民党军队总有各种实际困难。“长期设想国民党军队具有超出防卫领土的基本能力和使命”,只会“分散美国的资源”。显然,双方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是否要保留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性”使命
FRUS, 1955—1957, Vol.3, pp.593594.。
这个争论被提到了1957年10月3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38次会议上进行讨论:刚从台湾考察回来的总统特别助理詹姆斯·理查兹说,他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如果大幅度改变对台政策,对“自由亚洲的任何地区,特别是对东南地区,都将是灾难性的”。理查兹说,蒋介石竭力向他陈述一种观点,即大陆人民的不满可能为今后国民党的军事行动提供机会。因此,美国应该对这一点加以考虑。理查兹说,对蒋介石“实际上是否能回到大陆去当然要另当别论,尽管如此,即使他只有十分之一的成功机会,美国就应该准备利用这一机会”
FRUS, 1955—1957, Vol.3, p.612.。
杜勒斯在会上也表示,就美国在远东的整体地位而言,改变国民党军队的使命将是一场大灾难。这并不是说必须使国民党军队维持在某种水平上,而是说美国肯定不应当改变国民党军队的使命,“特别是我们不应当以取消提及国民党返回中国大陆的可能性的方式来改变其使命。实际上,正是重返中国大陆的希望维持了台湾的士气,即使这个希望是很遥远的”。
为了说服安全委员会成员们接受他的看法,杜勒斯说,亚洲和欧洲是大不一样的。西欧国家在纵深与强度上都是牢固的,在军事和其他方面也是如此。而亚洲是另一种情况,“只有一系列的小岛和半岛将美国的地位与共产党在亚洲大陆的纵深地位分割开来,这些小岛国和半岛国保持其向往自由的原因是,他们希望共产党中国某一天会垮台……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可以设想也会在共产党中国发生,如果这种垮台到来,中国国民党军队就能得到他们想要寻找的巨大机会。”
杜勒斯知道这种“机会说”没有多少吸引力。他说:美国人可以对这种可能性保留看法,但事实上国民党人相信这种机会会出现,正是这种信念维系着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抵抗。如果改变了美国的政策,美国就摧毁了国民党人的希望,同时也就摧毁了国民党人保卫台湾自身的能力。从杜勒斯的这种推论中可以看出,他最关心的是台湾当局的“士气”和“希望”。在他看来,台湾的“士气”同“反攻大陆”的可能性是密不可分的,如果美国阻止蒋介石强调这种可能性,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会更紧张,“台湾”最终可能会以某种方式脱离美国的控制
FRUS, 1955—1957, Vol.3, pp.612613.。
艾森豪威尔在会议上表态说,他同意国务院的方案,要是消灭了国民党人最终回到大陆的希望那将是很危险的。但是,这并不是说美国要把自己内心所有的想法都告诉国民党人。艾森豪威尔表示不需要修改美国的对台政策,“当然这也不意味着美国要给他们送去大量军事物资,让他们用来入侵中国大陆”。他认为,美国可以提供一些进攻“能力有限”的两栖装备,但援助主要用于防御方面。
艾森豪威尔强调,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要守住太平洋近海岛屿链,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美国必须让蒋介石相信他最终能成功地返回大陆。但国防部长威尔逊认为,他怀疑蒋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能够回到大陆,蒋反复讲这种可能性只是要挽回面子。理查兹为蒋介石辩护说,在东南亚地区大概是没有人相信这种可能的,但蒋介石本人对这一信念是真诚的。困扰着蒋的是台湾的挫折感。因此,蒋要他转告总统,请求美国帮助训练伞兵。理查兹说,“这种训练可以构成一种明显的证明,即美国
并没有放弃
对国民党人最终返回大陆的希望”。因此,美国“应当避免让已在台湾四处弥漫的挫折感进一步加深”
FRUS, 1955—1957, Vol.3, p.616.。
安全委员会第338次会议的讨论表明,由于“五·二四事件”的发生等因素,1957下半年美国对台湾的局势深感不安。为了强化台湾当局的反共士气,确保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控制,美国政府开始比较积极地迎合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政策,并向台湾提供了一些发动军事进攻所必需的装备和训练。这项政策加剧了台湾地区的紧张形势,导致了海峡两岸军事对抗的上升。这种紧张和对抗是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生成的重要条件。
二、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与调整
1. 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新估计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反对美国的侵略和扩军政策,希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同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毛泽东在1954年12月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说:“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6187页。
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也希望同美国缓和关系,通过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1955年4月,毛泽东对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五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1956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说:“我们天天说要同世界上一切国家断交,包括美国在内,但是我们不讲时间。中国人办事,就是不讲时间的。有些人讥笑我们,说中国人总是慢慢来,我们恰好就是这一条。”毛泽东认为,美国对华实行禁运,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及不承认中国,这些都不能影响中国的发展。相反,它只会使美国处于被动地位,在世界舆论面前输了道理,失去它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于国际形势的缓和不但具有信心,而且很有耐心,他还提出了“世界讲和,长期防御”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04页、第272274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页。
苏联二十大以后,社会主义国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加之苏联长期干涉东欧各国的内政,民主德国、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了政局动荡。西欧、北美等地的一些共产党组织出现了退党的风潮。这一局面刺激了国际反共势力,他们积极地开动宣传机器,对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政治和心理攻势。
进入1957年,毛泽东对西方反共浪潮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关注。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八大”提出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论断是否符合现实。
在国际形势方面,毛泽东密切注意的是东西方的力量对比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心理优势问题。1957年1月,他说:“世界各国都不安,中国也在内。但是,我们总比他们安一点。”“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之间,究竟是谁怕谁?我说都怕。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倾向这么一个估计: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他说:“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1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354页。
显然,力量对比的变化条件也是他关注的重要问题。
1957年2月,美国政府对“国家基本安全政策”进行审核。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策计划部门认为,中国的力量和国际地位在不断上升,这不仅需要美国付出更多努力和资源来遏制中国,而且会对“一个独立的台湾的继续存在构成危害”,除非能够达成一种美国“可接受的全面解决”。这一看法遭到了杜勒斯“最强烈地反对”,他认为这意味着接受“共产党中国代表着亚洲未来潮流的观点”,他说,没有理由认为挽救台湾就必须同中共进行某种讨价还价,例如,接纳中共进入联合国。“将来,一两年或者五年后,共产党中国将处于防守地位,因此,美国和自由世界无需对中共让步,给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杜勒斯拒绝妥协的方针得到了总统的首肯
FRUS,1955—1957, Vol.3, pp.491492.。
杜勒斯僵硬的对华政策受到美国舆论的批评。6月28日杜勒斯发表了长篇讲话,为他的不承认中国、不允许中国进入联合国、不同中国进行贸易的政策辩护。杜勒斯诬蔑中国“有连续侵略的记录”,并且提出各种理由反对承认中国。针对一些认为中国的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美国承认中国是“不可避免的”观点,杜勒斯坚持说:“美国决不需要接受‘不可避免’论。我们认为,我们同我们的朋友们能够规划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不承认共产党势力占优势。”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5022511页。
美国这种蛮横无理的立场,激起了毛泽东坚定反应。他开始强调要与美国进行斗争,并对50年代中期同西方缓和的方针产生了怀疑。1957年9月,他说:“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所以这和杜勒斯的方针相同,他怕我们去闹事,不同我们建交。”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8页。
1958年6月,毛泽东指出:1954年他曾指示在日内瓦会议上和美国人接触,这与他一贯的想法不一致,“看来还是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他说,这是显示中国人民能否站起来的问题。“要利用美国的对华三原则,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
何迪:《毛泽东的美国观》,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54269页。
1957年下半年,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的估计发生了变化。11月,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乐观地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他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口方面的优势,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所证明的技术优势,西方在中东遭到了失败,以及亚、非、拉人民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等原因,“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抛得很近还是很远?照我讲——也许是我这个人有些冒险主义,我说,永远地抛下去了”。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91300页。
这种估计大概是要给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打气”,其主观意愿性是非常明显的。同时也表明,毛泽东迫切希望扭转国际斗争中社会主义阵营较为被动的局面。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经常谈论战争问题。他在1957年2月说:“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还提到了打核战争的可能,“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是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毛泽东强调:“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4、296297页。
在以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毛泽东也多次谈到了世界大战的问题。他对战争与和平的观点具有现实意义。
2. 中苏分歧的发展
从1956年起,中国的对苏政策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是由苏共二十大引发的。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全面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半月后,这一报告在西方报刊上发表,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3月17日,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进行了讨论。出席会议的中共领导人认为,苏共不同兄弟党商量就批评斯大林是对各国党的突然袭击,使他们在毫无准备的下陷入了混乱。他们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说,我们一开头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对二十大正式报告中提出的“和平过渡”问题有不同意见。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共也要议论。他一分为二地指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二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是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3月19日和24日,中共中央又召开政治局会议,深入研究了对斯大林功过事非的评价问题。会议认为,赫鲁晓夫的报告破除了苏联的一切都正确的迷信,中共不能再硬搬苏联的模式,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指出:“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持讨论和亲自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斯大林问题上表明了中共的不同态度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610页。。
中国共产党准备抛开苏联这根拐棍,但赫鲁晓夫根本不想改变苏联的大国主义、自我中心和事事正确的态度。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贺词中极少谈中共革命的成就,反而大谈苏联的政绩和在世界革命中的中心地位,他甚至认为中共的“每一个进步,每一项成就‘都是根据苏联的经验’而来的”。米高扬的贺词究竟是苏联的一贯傲慢,还是故意表示反对中国的新方针还难以断定。但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他认为米高扬是在摆“老子党”的架子。那天,毛泽东故意不出席会议,以示对苏联的抗议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606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4页。。
“八大”期间,毛泽东同米高扬详细谈了斯大林和苏共当年如何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如何打击中共的正确路线,并说,“过去我们不便说,现在就要开始讲了,甚至还要骂人了,我们的嘴巴你们是封不住的”。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版),第609页。
毛泽东的这一态度表明,他对斯大林虽然不满,但这种不满并没有因为苏联对斯大林批判而解决。相反,翻这些“老账”还有现实意义。
1956年10月,波兰政局发生动荡,苏联准备出动军队进行武装干涉。对此,毛泽东在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用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会后,他立即召见了苏联大使尤金,向他指出:“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1213页。
苏联政府在接到中国的警告后,很快改变了政策,通过谈判缓和了与波兰的关系。
不久,匈牙利又发生了政治动乱,反共势力试图推翻匈牙利共产党政权。在混乱的形势下,苏联领导人决定将苏军从匈牙利撤出。10月31日,赶到苏联讨论有关局势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奉命通知苏共,中共反对从匈牙利撤出。他说:“苏共这个决定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从这些强硬的语言中可以看到,中国对苏联的批评已经直言不讳。
1957年1月,中央临时决定派周恩来出访苏联和波、匈两国。在中苏两党会谈和一些讲话中,周恩来批评苏联兵临华沙,实行威胁,是以武力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内部事务。在斯大林问题上,周恩来再次说明了中共反对全盘否定的立场,认为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能抛开历史背景孤立地评价一个人。他还指出:“与斯大林长期共事的苏共领导人,在助长斯大林的错误问题上有一定的责任。”这实际上是对赫鲁晓夫的当面批评。
访苏以后,周恩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中苏关系现在是大敌当前,所以苏联对中苏团结态度甚殷,但非心悦诚服。”他指出,在国际形势上,苏联领导人考虑或应付具体的现实问题多,缺乏对于整个局势的全面分析和预见。“考虑和讨论世界战略和远景问题很差。”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5页。
此时,中共领导人认为自己比苏共更透彻地了解国际局势。
1957年11月初,毛泽东去苏联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公开场合,中苏两党都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强调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然而在双方会谈中,意见分歧却时常表现出来,在“和平过渡”问题上分歧尤其突出。赫鲁晓夫还试图以撤退专家来威胁中共,毛泽东却不动声色地说,中国应该学会自己走路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外语教学和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136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5859页。
。这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他的真实想法。
3. 由“共同舰队”问题引发的争论
虽然出现了理论上的分歧,1957年中苏国家关系还处于较好时期。经过谈判,中苏双方签订了“十·十五协定”,苏方承诺向中国提供新型导弹和作战飞机的技术。11月,海军司令萧劲光大将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同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讨论了中国海军的建设方针,以及苏联可能向中国提供的海军新技术等问题。1958年4月,海军向中央军委提出报告,认为为了少走弯路,应尽早获得苏联较新和较现代化的海军技术,即“可携带火箭和导弹的潜艇、快艇”的设计图纸和资料。中央军委同意了海军的要求
萧劲光:《萧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176182页。。
1957年苏联曾援助中国三座小功率长波电台。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和远航需要,中方又向苏方提出援助大功率长波电台的要求。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电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中苏合作在中国海岸建立一个大功率长波电台,由两国共同使用。苏方需用其指挥在太平洋活动的苏联潜艇部队,所需费用1100万卢布,苏方出700万,中方出400万。由于双方在由谁投资问题上发生分歧,6月上旬毛泽东批示说,电台“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但他强调钱一定要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如果苏方以高压加入,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
萧劲光:《萧劲光回忆录》(续集),第200201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16317、634页。
。长波电台问题出现,使毛泽东怀疑苏联想要控制中国。
6月28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要求苏联在中国海军建设方面给予援助。在可能的条件下,希望苏联有计划有步骤地提供核潜艇及其他新兴舰艇的设计图纸及相关部件、材料和武器的设计图纸。此时,台湾海峡的形势已较为紧张,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停了半年多,两天后中国政府向美国递交了限期恢复谈判的“最后通牒”。
苏共领导人对于中美关系的紧张当然是了解的,他们担心苏联的海军技术可能会助长中国对美国采取对抗政策,因此不愿
提供核潜艇技术。如果中国一定要,可以建立一支“共同舰队”。7月21日晚,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意见,说苏联沿海的自然条件不利于发挥核潜艇的作用,要求利用中国沿海的良好条件,“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毛泽东当场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这番话表明,毛泽东对主权问题非常敏感,他绝不允许由苏联来控制中国的海军。
22日,毛泽东怒气未消,他又将尤金招来讨论此事。毛泽东说他昨晚气得一宿没睡觉。苏联人就是不相信中国人,“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在历数苏共历史上对中共的种种不信任后,毛泽东尖锐地说:“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他还指出:“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也不行。”他还建议赫鲁晓夫来北京,把这个问题谈清楚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2333页。。
尤金将毛泽东发火的消息报告国内后,赫鲁晓夫在7月31日匆匆赶到北京。机场上没有红地毯和仪仗队,只有表情严肃的中国领导人在等待他。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先是对苏联意图作了辩解,说尤金没有传达清楚他的意思,苏联没有要搞共同舰队的想法,只是要同中国共同商量。如果不行,苏联希望中国提供一个可为苏舰加油、修理的基地。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说,中国“不搞共同舰队,一万年没有原子弹、潜艇舰队也可以”。他还很干脆地拒绝了苏军使用中国基地的要求。在以后的三天会谈中,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缺少共同语言。用随赫鲁晓夫访华的苏方中国问题专家费德林的话来说:“赫鲁晓夫的北京之行不仅没有消除苏中之间已经形成的裂痕。相反,从那时起标志着两国关系更加紧张,中苏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48158页;陈小鲁:《陈毅与中国外交》,载《环球同此凉热》,第146页;尼·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费德林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143页。
赫鲁晓夫在北京停留了四天,与毛泽东进行了四次会谈,但毛泽东没有对他提起中国将在台湾海峡地区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显然,毛泽东想看一看苏联在这次行动中会做出什么反应,而且他还要让赫鲁晓夫看一看,中国人不仅敢于同西方斗争,而且在斗争中也不是“毛手毛脚的”。
4. “八大”二次会议与外交
进入1958年,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出现了新的转折。1956年,党中央认为当时出现了过热的经济气氛,于是决定采取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周恩来和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根据中央的决定及时纠正了经济建设工作中的冒进问题。但是到了1957年,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打击了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损害了经济建设的速度。从1957年9月起,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以及南宁、成都两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反冒进”是方针性错误,并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出现高潮,一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在创造之中。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在北京进行。这次会议在政治上改变了“八大”做出的国内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的结论,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依然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还存在两个剥削和两个劳动阶级的错误观点。在经济上,会议再次批判了“反冒进”问题,提出了“大跃进”的方针。会议确立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体现了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左”倾指导思想。
在反冒进和“大跃进”的气氛下,经济建设的计划不断被修改。在1957年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在15年内赶上美国的口号,当时毛泽东也提出中国可以在15年内赶上英国。到了“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7年赶过英国,15年赶过美国”的新口号。毛泽东在会议上说我们是世界第一人口最多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发展。我们已经看出了前途。早些时候还看不清楚多快、多大规模,要多少时间可以摆脱落后状态、被动的状态,在世界上没有地位状态。我们6亿人口的大国,杜勒斯不看在眼里,总有一天我们赶上英国,赶上美国,他才知道确实有这个国家。”
裴棣:《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会议》,《中共党史资料》第29辑,第236256页。
毛泽东要改变与西方的力量对比关系的心情越来越迫切。赶超英美的时间不断缩短。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他还把1958年生产 1070 万吨钢的计划告诉了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两个多月后,他甚至提出了“七年超过美国”的设想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67、699704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368页。
。这种迅速赶超、不甘落后的精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订下这种时间表却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左”倾气氛对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产生了影响。会议的内容之一是听取和讨论邓小平作的有关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报告。毛泽东在会议上多次讲话,强调要防止大灾难,要准备发生战争和党的分裂。“八大”二次会议在积极评价《莫斯科宣言》的同时,也对南斯拉夫共产党进行了激烈批判,使刚建立不久的中南关系重新蒙上了阴影。
在1958年初,南斯拉夫共产党为准备召开代表大会而公布了一个纲领草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对这一草案进行研究认后认为,南共纲领草案的大部分内容,如实行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建立工农联盟、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实现民族平等及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等与《莫斯科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只有两三条内容与宣言所说的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南共纲领强调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党平等,但《莫斯科宣言》强调的是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一致。伍修权在给国内的报告中说,该草案许多部分反映了正确的观点,如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认为有革命的、议会的及其他斗争方式的前途,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内部矛盾等,与我党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说:“虽然我们同南共同志在一些问题上,在看法上有所不同,但是南斯拉夫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渴望和相当的干劲也是事实,而且这是最本质的问题,几乎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
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46259页。
但苏联领导人对南共强调各党平等的独立自主的政策不满,认为南共“别有用心地企图”提出同《莫斯科宣言》相违背的纲领文件,对当前国际局势、工人运动、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提出了不少是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和评语。因此赫鲁晓夫决定派代表团与会,只派大使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并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协调立场。毛泽东不仅同意中国与苏联采取同样措施,而且错误地以为南共领导“企图向全世界散布他们修正主义理论”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72173页。。
“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对南共纲领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一纲领违反了马列主义原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决议提出:南共“散布不要无产阶级革命、不要打碎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他们站在两大阵营之外的“超集团立场”是为了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决议还认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任务”。在这一决议通过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和国际上长期进行了“反修”斗争。
“八大”二次会议决议强调要根据《莫斯科宣言》精神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批判。但决议对于该宣言中另一重要内容,即争取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和平共处却几乎没有提及。“和平共处”是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对外政策总路线,中共自1954年以来对和平共处原则也有极高的评价。1957年10月《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说: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必要性现在越来越明显了,在当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情况下,如果各国之间不能学会和平共处,那就必然会招致重大的灾难。因此,实现和平共处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呼声”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6102616页;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49—1958,总论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691694页。
。对这一重要原则避而不谈,说明“八大”二次会议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它的看法。实际上这次会议对苏共的“和平过渡”等观点还进行了内部批判。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由于国际上出现了反共逆流,由于来自美苏两国的压力增加,中国面临着不利的国际环境。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与主权,为了抵制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思想,中国拉开了与苏联的距离。为了反击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也为了鼓舞世界人民的反帝精神,中国强调要对美国好战政策采取更坚定的斗争立场。同时,由于对东西方力量对比做出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并且错误地强调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的调整也出现了偏差,如在调整后的中国对外政策中,和平共处原则的地位明显降低。
三、以战争边缘对战争边缘——危机的第一阶段
第一次台海危机后,台湾海峡地区的局势有所缓和,但国民党当局对大陆沿海地区的骚扰活动从未停止,空中军事冲突也时有发生。金门一带还多次发生一定规模的炮战。1957年美国政府迎合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政策以后,国民党对大陆的军事袭击和骚扰活动明显增加,他们“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浙江”,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全构成了一定威胁。这是台湾海峡地区第二次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
中国政府在1957年实行了较大规模的军队复员计划,1958年军队总人数下降到240万,军费开支降到历史最低点
徐焰:《金门之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中共中央此时没有使用军事手段解放台湾的计划,但中央没有排除先解放金门、马祖的可能性。从1955年起,中国开始在福建和广东两省建造新的军用机场,并且加紧修筑通往福州和厦门的铁路。这些行动虽然并不涉及军事行动,但从战略上看,对国民党当局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1957年5月,美国开始把它的“斗牛士”地对地战术导弹部队派驻到台湾。这种导弹可以打到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对中国的安全进一步构成了威胁。王炳南大使奉命在日内瓦会谈中向美方提出严重抗议,他指出,美国政府必须对这一行动的后果负责,中国绝不会容忍美国的侵略
FRUS, 1955—1957, Vol.3, pp.522523.。
1. “中国人就是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炮击金门的目的
位于福建等地的可以起降喷气式军用飞机的机场在1956年以后已经完成,为了配合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解放军空军没有立即进驻这些前沿机场。由于台湾当局的空中骚扰活动不断增加,空军准备加强对国民党空中活动的打击力度。加之蒋介石不仅拒绝“第三次国共合作”,而且利用波匈事件加大了“反攻大陆”的调门。因此,毛泽东在1957年12月28日指示彭德怀,“考虑我空军1958年进入福建问题”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77页。
。1958年1月,空军上报了部队入闽的计划。这年春天,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4月27日,福建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政委叶飞上报了炮击封锁金门的作战方案,准备在适当时候对金门实施大规模的炮击封锁。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1958年春已在考虑对金门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所要等待的只是合适的时机。
1958年6月30日,中国政府发表有关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声明。声明指出,美国中断大使级会谈已经半年多了,这种情况不应该再继续下去。在回顾两年多的谈判历程与揭露美国拖延会谈的真正目的后,声明强调,中国同意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为了争取用和平方法消除美国在台湾地区的武力侵略和武力威胁。但是,中国人民绝不害怕美国的侵略,更不稀罕同美国的谈判。正在以飞跃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完全有力量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中国人民建设和统一自己祖国的伟大事业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的。声明最后告诫说:“中国政府既不能同意片面改变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水平,也不能同意用任何行政性理由使会谈继续中断。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在从今天起的十五日以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已经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6262628页。
这一声明意味着,中国可能要采取某些措施来打破僵局,回击美国对中国的敌对与挑衅。
中国政府的强硬声明引起了美国方面的震动。当天,美国国务院做出反应,表示美国“一直在积极考虑选派一位大使以及可能改变会谈地点的问题。但是,我们不打算对限期十五天的最后通牒屈服”,“暂不对举行另一次会议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在第二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感到了风暴可能到来的杜勒斯格外谨慎地说:“实际上有一项有关这个问题的备忘录已在交送的过程中,谈的是可能把这种会谈的地点从日内瓦转到华沙的问题。”但他也说,美国不受中国规定限期的“约束”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6282630页。。
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发生军事政变,亲西方的萨费尔王朝被推翻。次日新政权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这一行动对于美国的中东战略构成了沉重打击。为了防止伊拉克革命蔓延到国外,为了防止黎巴嫩亲美的夏蒙政权被反对派推翻,美国以保护侨民为借口,15日出兵在黎巴嫩登陆,占领了该国首都。西方的这一行动立即招致中东地区和世界各国舆论的强烈反对。中国也在7月16日发表声明,“强烈地谴责和抗议美国的侵略行为”。全国各地还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美国入侵黎巴嫩。
美国在出兵黎巴嫩的同时,下令其在世界各地的军队进入戒备状态。7月17日,台湾国民党军队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
7月17日,毛泽东下达了准备炮击金门的命令,同时还下达了空军作战飞机进入福建前线机场的命令,命令炮兵的任务是封锁金门及其海上航运,利用一切时机打击国民党军的运输船只。7月18日晚,毛泽东又召集军委和海空军负责人,布置军事行动。他在会上说:支援中东要有实际行动,“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而对美帝国主义则有牵制作用”。他明确指示,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准备打两三个月
转引自徐焰:《金门之战》,第205页。。
随后,彭德怀在军委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他指出:最近美英两国军队武装干涉黎巴嫩和约旦,企图镇压黎、约人民及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对阿拉伯人民的支持要有实际行动。这个行动一是空军进入福建,二是对金门打炮。为了策应美英在中东的战争行动,国民党空军也蠢蠢欲动,台湾海峡出现紧张局势。我方以实际行动打击它,既可以牵制美军在远东的兵力,又可对台湾方面进行警告。同时告诉全世界人民,美帝国主义要打仗,中国人民是不怕的
聂凤智:《战场——将军的摇篮》,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222223页。
。这些情况表明,中东危机的发展为炮击金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时机,炮击行动不仅是要打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而且要打击美国对华政策,使美国无法无视中国的存在。
解放军部队从7月19日起开始调动,24日前完成了一切作战部署。但是就在这时发生了如前所述的中苏“共同舰队”问题,赫鲁晓夫要来中国进行解释。7月27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和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写信说:“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中东解决,要有时日,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着急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526页。
推迟炮击的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是赫鲁晓夫即将来访,毛泽东不想让外界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
但空军已经到达前线机场。7月29日,解放军空军和国民党飞机发生了入闽后的第一次空战,击落击伤敌机3架。8月前半个月,双方又连续进行了三次空战,解放军空军初步取得了福建上空的制空权。在此同时,一批海军舰艇、三个炮兵师和一个坦克团也到达厦门地区
聂凤智:《战场—将军的摇篮》,第226227页;叶飞:《征战纪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47页。。
8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化问题。18日,毛泽东写信给彭德怀说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东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人。同时,他提醒说,“台湾”可能出动大编队飞机以夺回金、马制空权,我军要准备大编队击败对方。但他强调,“追击不要越过金、马线”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348页。
。8月21日,毛泽东召见负责前线指挥的福州政委叶飞,听取了有关炮击的准备工作的详细报告。
8月23日中午12时,解放军开始对金门进行大规模炮击。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今天开炮,时机选择得当。联合国大会三天前通过决议,要求美、英军队退出黎巴嫩和约旦。美国人霸占我台湾更显得无理,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湾太远打不到就打金、马。这肯定会引起国际震动,不仅美国人震动,亚洲人震动,欧洲人也震动。”他还说:“这次炮轰金门,老实说我们是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而采取的行动,就是要整美国人一下。美国欺负我们多年,有机会为什么不整它一下。”他指出,我们现在处于主动,可进可退,游刃有余。美国人在中东烧了一把火,我们在远东烧一把火,看他怎么办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475页。。
从上述毛泽东的讲话可以看出,炮击金门虽然是军事行动,但这一行动的政治目的是主要的和明确的。一方面,毛泽东要对美国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及远东地区推行反华反共政策进行一次主动还击,他要告诉杜勒斯,中国人不怕美国的战争威胁,紧张局势压不垮中国人民,它只会使人民更坚定地同帝国主义斗争。另一方面,从1957年以来,毛泽东曾多次谈论在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究竟谁怕谁”的问题。在这次危机中,他要向世界,特别是向苏联证明,“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1、342页。。
从军事目的上来看,毛泽东希望通过炮火打击和海空封锁的压力,迫使国民党军队从金门、马祖等岛屿撤退。在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要观察各方面的反应,首先是美国的反应,再确定下一步的行动。在25日的常委会上,毛泽东说:“从这几天的反应看,美国人很怕我们不仅要登陆金门、马祖,而且准备解放台湾。其实我们向金门打了几万发炮弹,是火力侦察。我们不说一定要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我们相机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他指出,美台条约没有明确规定包括金门、马祖,美国是否把这两个包袱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中国人就是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6页。
毛泽东的这些话表明,中央当时没有一定要把金门打下来的决定。但是,如果美国政府不想为了一两个小岛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蒋军又被迫撤出,那将是最好结果,不仅达到了军事目的,而且达到了政治目的。
在军事行动方面,毛泽东是非常慎重的。他密切地注视着各方面,特别是美国的反应。他多次要求部队避免打到美国人。9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两位巴西记者时说,西方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几斤钢铁几个原子弹”。他说,要在战略上蔑视帝国主义,但在战术上和每件具体工作上,却要重视它们。“帝国主义由真老虎变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变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纸老虎,这是一个事物走向反面的转化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前,老虎还可能活一个时期,还可能咬人。因此……不能大意。”
叶飞:《征战纪事》,第350357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5340页。
从8月23日到9月3日,中国海军和炮兵5次打破了国民党对金门的补给企图。4日,国民党当局向美国承认,他们无法对金门提供补给。于是美国不得不站到前台表演。
2. “谁是老子?”——美国军事干预政策的形成
第一次台海危机结束以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于美国帮助国民党防守金门、马祖的方针一直争论不休。1956年春夏,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杜勒斯认为,随着福建地区铁路和机场的建成,中共可能重新挑起危机。财政部长汉弗莱认为,美国应当利用此时台湾地区的平静,从沿海岛屿脱身。艾森豪威尔总统也希望重新进行一次讨论,明确政府的方针,以免像上一次危机时那样仓促行事。但他们的意见遭到了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的反对。杜勒斯不以为然地说,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已经有明确的政策,安委会还有许多重要的事需要考虑。雷德福认为,沿海岛屿的防御已经大大加强,他怀疑中国是否还会对金门、马祖发动进攻。他说美国国会的决议“已经吓退了中共”
FRUS, 1955—1957, Vol.3, pp.364365.。
波匈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在台海地区采取了更具冒险性的立场,1957年10月,国家安全委员会部分迎合国民党的反攻大陆政策,并对沿海岛屿政策作了补充。编号为NSC5723号的文件称:“如果总统判定对确保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防御有需要和适当时,美国军队可以被用来协助中国国民党人防守沿海岛屿,以抵御中共的进攻。”这一文件表明,为了帮助国民党控制这些岛屿,美国很可能直接干预中国内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FRUS, 1955—1957, Vol.3, pp.619623.。
对中国是否会进攻沿海岛屿的问题,美国政府进行过研究。1958年5月18日美国“国家情报估计”认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将会继续破坏国民党的意志,使台湾当局在国际上信誉扫地。但是,“只要他们相信有可能使自己卷入同美国的军事行动,他们也许不会诉诸公开的军事行动。虽然他们对沿海岛屿的态度可能变得更加好斗,但发动军事行动以夺取这些岛屿的决定,可能要以他们对美国是否会进行军事干预的估计为条件”。
FRUS, 1958—1960, Vol.19, pp.2327.
这一估计应该说具有一定的预见性。
6月底,中国要求美国恢复大使级谈判,设定的最后期限正逢中东危机发生,远东地区的气氛也高度紧张。虽然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7月15日说,美国要点面子是可以理解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恢复“推迟几天时间也无不可”。但美国方面迅速采取了行动,7月17日,杜勒斯要求有关人员立即将美国新的谈判代表人选通知王炳南,以示美国无意继续拖延
FRUS, 1958—1960, Vol.19,pp.2728, 3032;《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637页。。
7月29日,国民党两架F84战斗机被解放军空军击落,台湾当局相当恐慌。但新上任的驻台美军司令斯摩特对蒋说“克制是最明智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研究了局势后认为:没有迹象表明中共在集结兵力,其他军事行动也不表明中共在这一地区有进攻意图。杜勒斯担心国民党可能会对大陆机场进行报复性轰炸,他要求国民党当局,“未经协商”不得对大陆机场采取行动。美国对于进行中的中苏领导人会谈非常关注,他们认为这一会谈可能与中东形势有关。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行动表明,此时美国主要的关注点在中东
FRUS, 1958—1960, Vol.19, pp.3334; pp.38, note.2; pp.3537.。
蒋介石对于美国的反应十分不满。他在8月4日会见美国“大使”杜姆赖特和斯摩特时说,美国政府远在十万八千里以外,看不到他面临着“直接和紧急的现实威胁”。蒋保证会遵守条约,但要求美国表明已看到局势的严重性。他还要求美国提供“响尾蛇”导弹,提前交付 F86 战斗机,并希望美国派遣F100战斗机进驻台湾
FRUS, 1958—1960, Vol.19, pp.3940.。
8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台湾海峡形势,政府各部门都认为,中共在没有集结地面部队以前,不会对沿海岛屿发动全面进攻。他们认为,中共下一步要控制制空权,“可能的战略是封锁那些岛屿,以使那里的国民党军队困死或被迫撤出”。艾森豪威尔在会上说,即使有国会的“福摩萨决议”,美国也没有理由干涉目前的局势,除非美国认为中共的空中活动是进攻台湾的前奏
FRUS, 1958—1960, Vol.19, pp.4243.
。尽管如此,军方还是未雨绸缪,同意向台湾提供“响尾蛇”导弹,提前运交F86飞机。美国还打算增加航空母舰在这一地区的活动。
助理国务卿饶伯森8日向杜勒斯报告说,国民党军队和武器装备的三分之一部署在金门、马祖,他们肯定要阻止中共取得制空权和进行封锁,他们可能轰炸大陆机场。美国将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如果中共的封锁成功,美国要不站在一边看着国民党军队在沿海岛屿上困死,要不就采取军事行动去维持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如果美国不能提供支持,那将对国民党的士气产生重大影响,并使“台美关系”发生严重紧张。这还会对美国在远东的盟友产生严重后果,特别是韩国和越南,他们正面临着共产党的威胁
FRUS, 1958—1960, Vol.19, pp.4546.。
8月中旬,美国情报部门断定中国加强了在沿海地区的军事力量。艾森豪威尔认为,沿海岛屿并没有多少战略价值,但由于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驻扎在这岛上,“一旦将他们撤走或损失,对所有亚洲人来说那是一种信号,即抵抗共产党中国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艾森豪威尔对蒋介石将大量军队放在金门非常不满。他说,1954年政府在丹佛曾决定不对沿海岛屿承担义务,但现在美国已让局势发展到了这种地步,蒋说如果丢失这些岛屿,他就不能守住台湾。
杜勒斯认为,金门、马祖的防卫已经同台湾的防卫“形成一体”,美国可能要考虑“对沿海岛屿的攻击也就构成了对台湾的攻击”。国民党军队会因失去沿海岛屿而丧失士气。而且,失去沿海岛屿对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也构成一种士气上的打击
FRUS, 1958—1960, Vol.19, pp.5054.
。显然,艾、杜两人对金门、马祖的军事价值有不同的看法,但在政治意义上,他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对美国来说,沿海岛屿的政治意义和心理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这是美国决定进行军事干预的首要原因。
在国务院内部,负责政策计划的助理国务卿杰拉德·史密斯认为,美国面临着同中国和苏联发生全面战争的严重风险。由于军方坚持必须使用核武器打击中国大陆,而且无法进行地区性防御,政府应当重新审查对沿海岛屿的政策。他说,如果可用的军事手段将导致与中苏发生全面战争的风险,美国就不应保持目前有条件地,或正走向无条件地防守金、马的承诺。针对那种认为放弃沿海岛屿会带来严重政治后果的观点,史密斯说:“不论人们是否赞同我们的立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相信我们能守住这些岛屿。我们最近在近东的坚定行动表明我们准备使用力量保卫重大利益,因此改变政策不会被认为是软弱的信号,而是对国家利益的仔细估计。”史密斯认为,等到中国力量强大了,甚至有了核武器再改变政策,那将更加危险。他建议说服蒋介石从金、马撤军
FRUS, 1958—1960, Vol.19, pp.5759.。
然而史密斯理智的看法没有能改变他上司的观点。他们认为,沿海岛屿对于美国反共决心具有象征性意义。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伯克对艾森豪威尔说:“这些岛屿没有任何意义,它纯粹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它仅仅意味着:谁是老子?世界上谁在这个地方说了算?是‘红色中国’或者是‘国民党中国’”?在伯克看来,即使需要用核武器,美国也不能让步,“否则,我们面临着十年内失去整个世界”。
Appu K. Soman,“‘Whos Daddy’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Offshore Islands Crisis of 1958”,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Winter 1994, pp.373389; FRUS, 1958—1960, Vol.19, p.120.
正是冷战政治和霸权心态,左右了美国政府再次选择军事干涉政策。
为了应付危机,政府各部门反复策划美国的行动方案。军方在8月中旬提出,如果中国对沿海岛屿进行封锁,国民党只有45天的补给,除非美军进行干预,否则国民党无力打破封锁。军方的观点是,“无论是对付进攻还是封锁,美国有效的干涉必须是对大陆基地进行核轰炸”。最初的核打击目标是厦门周围6~8个机场,如果进攻继续,可能要深入对中国北至上海的地区进行核打击,以防共产党对台湾、冲绳等地进行核报复
FRUS, 1958—1960, Vol.19, p.56.。
8月23日,解放军开始大规模地炮击金门。美国政府再次向台湾地区增派军事力量。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和“中途岛”号奉命分别从地中海和珍珠港赶往远东。一个中队的B47轰炸机被调往关岛,这是一种可以投放原子武器的战略轰炸机。此外还有6架F100战斗机、一个“奈克”导弹营被调到台湾,还准备向台湾提供3艘大型登陆舰和其他登陆船只。参联会还命令美军太平洋总部,迅速向台湾增派其他海空力量,并准备接管台湾的对空防御。命令还要求准备为国民党船队护航,确保通往金门的补给线不被切断。如果发生危及主要沿海岛屿的大规模进攻,将准备使用美军援助国民党,包括攻击大陆的沿岸机场。命令说,最初的攻击可能使用常规武器,一旦得到总统授权就准备使用核武器
FRUS, 1958—1960, Vol.19, pp.76, 9699.
。这是一个先用常规武器,再用核武器的“逐步升级”的军事方案。
美国政府做出强硬反应的另一个原因是,饶伯森在8月20日对杜勒斯说,1955年的危机表明,美国不能说服蒋介石主动从金门、马祖撤出。从那以后,国民党已经大力加强了金门的防御。国民党还强硬地表示,不管美国是否协助防守,他们要为金门战至最后一人。艾森豪威尔在危机发生后发牢骚说,美国1954年主要关注的是台湾和澎湖,现在却有一种倾向,要使美国的防卫扩大到沿海岛屿。美国卷入这些小岛唯一的理由是要维持国民党的士气,但国民党却不顾1954年美国的军事意见,故意让它的主力部队去防守这些岛屿。他认为这些部队成了“人质”。这一看法反映了艾森豪威尔内心的无奈
FRUS, 1958—1960, Vol.19, pp.6265, 73, 98.。
8月26日,最高级别的情报——“特别国家情报估计”对中国的动机做出了判断。文件说:“共产党中国加强它在台湾海峡地区军事压力的主要目的是,考验美国和台湾当局对沿海岛屿的意图。共产党中国可能期望,加强紧张局势的后果会有利于它参与世界性决定,阻止任何承认事实上的‘两个中国’的可能,特别是如果美国不愿采取有力措施守住沿海岛屿的话,会加速国民党士气的涣散。”文件认为,由于美国承诺防卫台湾,以及中苏不愿冒世界大战的风险,半年内中共不会试图夺取台湾。
文件认为,虽然中共可能对主要的沿海岛屿发动进攻,但“它很可能在最近的将来不会试图这样做,因为它担心美国可能的干预,共产党中国可能继续对金门和马祖群岛施加军事压力,但会避免走到军事摊牌的临界点”。文件认为,根据美国的反应,中国可能采取炮击金门、在台湾海峡采取空海行动、飞越台湾,封锁对金门、马祖的供应,夺取较小的岛屿等措施。如果美国的反应使中共相信美国不会干预,中共就可能试图夺取金门、马祖。如果美国明确保证或承诺用军队保护主要的沿海岛屿,中共可能不会试图夺取这些岛屿或封锁其补给
FRUS, 1958—1960, Vol.19, pp.8182.。
在危机的初期阶段,毛泽东要考验美国的决心,“走一步,看一步”,根据美国的反应来决定下一步行动。但美国对中国的这一策略有所估计和准备。
8月29日,在白宫召开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批准了美国的军事干涉方案。这一方案规定,在中共对金门进行封锁的有限行动阶段,美国的主要反应是在“国际水域”为国民党军队提供护航等间接支持。如果中共对金门发起大规模进攻,美国军队将直接进行军事干涉。美军在开始行动时不使用核武器,打击范围也不超过当地作战区域。在这些行动无效的情况下,美国有可能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并有可能扩大打击范围。如果中共对台湾和澎湖发动攻击,军队将要求总统给予新的授权。这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总统仍没有给军方使用核武器的预先授权,即预先同意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战术核武器。
3. 美国的核威胁政策与《新港声明》
台海危机发生时,杜勒斯正好在度假的飞机上,9月1日他才回到华盛顿,他没有立即去同总统讨论局势,而是以要了解情况为由把同总统的会见推到4日。实际上,杜勒斯此时对总统没有做出使用核武器的决定不满。9月2日,他在同军方领导人的会谈时针对舆论的怀疑态度说,问题不是失去几个小岛,因为这一损失可能导致中国进一步的“侵略”。他说,在美国能严肃地对待,并绝不接受共产党每次挑战的后果之前,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打一场世界大战。海军作战部部长伯克也说,“那种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打一场世界大战的想法就是共产党不断取得胜利的原因”
FRUS, 1958—1960, Vol.19, pp.113, 119121.。
在9月3日的会议上,杜勒斯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致意见:美国“应当使用小型核武器来打击共产党的机场和炮兵”。而且,这是军方完成其任务的“唯一方法”,必须“有限地使用核武器来守住那些岛屿”。为了替这一方针提供根据,他们毫无根据地声称,中国的目标不仅是针对沿海岛屿的,也是针对台湾和其他地区的。同一天,在与国防部长麦克罗伊尔的会谈中,杜勒斯还说,美国的目的是要威慑对沿海岛屿的进攻。在这方面,更大的危险是美国的立场没有被充分表达清楚
FRUS, 1958—1960, Vol.19, pp.113, 115122, 125126.。
9月4日,杜勒斯飞往罗德岛的新港,同正在那里度假的艾森豪威尔进行会谈。他直率地对总统说,“当我们决定将这些武器包括在我们的武库之内时,我们就意识到使用这些武器会有政治和心理上的危险”。如果“在赌注已经投下,而我们因为世界舆论而不使用这些武器,我们就必须修改我们的国防体系”。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打出了最有力的一张牌:要么同意在危机中使用核武器,要么就推翻当初艾森豪威尔自己提出的“新面貌”战略。艾森豪威尔虽然担心战争扩大,但他最终还是接受杜勒斯和军方的观点。为此,他们两人还写下了一份备忘录,声称使用小型核武器将会在全世界引起公众针对美国的强烈反感,但是美国如能迅速取胜,使用核武器的后果就比不能顶住中共的政治灾难的损害要小些。同时他们还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冒更广泛使用核武器的风险,甚至冒全面战争的风险
FRUS, 1958—1960, Vol.19, p.130; Soman, “‘Whos Daddy’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Offshore Islands Crisis of 1958”.
。这次会谈充分表明,此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为实现其政治目的具有不顾一切后果的疯狂性。
会谈结束后,杜勒斯即根据总统授权发表了《新港声明》。该声明说:美国负有条约义务来帮助保卫台湾不受武装进攻。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像金门和马祖这样的有关阵地。声明还说,“中国共产党人方面现在要夺取这些阵地或其中任何阵地的任何尝试,都将粗暴地违反世界秩序所基于的原则,即任何国家都不得使用武装力量来夺取新的领土”。声明威胁说:“总统现在还没有做出判定是否要动用美国武装部队保卫台湾,一旦情况必需,总统就会毫不犹豫做出这种判定。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确保和保护金门、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日益有关。……美国已经做出军事部署,以便一旦总统做出决定就立即采取及时的和有效的行动。”这一声明实际上已明确地表示,美国将对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进行军事干涉。
《新港声明》最后表示,“美国并没有放弃希望”。声明说:在日内瓦进行的持续谈判中,美国作了长期努力希望能够获得一项,特别是在台湾地区,宣布
除了自卫以外
相互和互惠地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这样做也不会妨碍以和平方式追求各方的政策目标,这一方针是“唯一文明的和可以接受的程序”。就美国来说,它打算奉行这一方针,除非中国的行动使它别无选择
FRUS, 1958—1960, Vol.19, pp.134136.
。《新港声明》虽然语气强硬,但杜勒斯并没有公开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同时这一声明流露出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寻找出路的意图,以及希望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的暗示。
4. 毛泽东论“绞索”、“脱身”与紧张局势
8月23日以后,解放军利用炮击、控制制空权和小型舰艇的出击逐步对金门形成了封锁。虽然8月28日福建前线电台向金门广播说,“人民解放军准备在金门登陆”,其实这只是一种试探美蒋反应的手段。9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这一文件说:台湾、沿海岛屿的斗争,根据情况发展可采取一切适当有效的办法,即(1) 继续炮击,不宜进行登陆作战;
(2) 炮击打打停停,看看打打,完全保持主动;(3) 不得进入公海作战,蒋不轰大陆,我不轰金、马,蒋轰大陆,我即轰金、马,但不轰台湾;(4) 不主动攻击美军,若其入我领空领海,我坚决打击之。当天晚上,毛泽东突然提出,福建前线自9月4日起停止炮击三天,以观各方面动态
石仲泉:《周恩来的卓越奉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368373页,转引自徐焰:《金门之战》,第241页。
。从这些指示看,中共中央当时的政策的确是主动和慎重的,解放军此时没有登陆和进攻金门的打算。
9月5日,毛泽东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海峡问题作了讲话。毛泽东说:“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过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的颈吊在我们的中国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它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它的头更接近我们。我们哪一天踢它一脚,它走不掉,因为它被一根索子绞住了。”毛泽东说,蒋介石过去给我们捣乱都是从福建这个缺口来的。金、马在蒋军手里,实在讨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但是我们现在不是马上登陆金、马,只是试试美国人,吓吓美国人。但有机会就打,机会来了为什么不把金、马拿回来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41342;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980页。。
毛泽东还说,东西方“双方都怕”打仗,“但是他们怕我们比较多一点,因此战争是打不起来的”。他指出,中国反对战争,但不怕战争。“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要打就打,打完了再建设。”他说,中国要求缓和紧张局势,缓和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但也不能认为凡是紧张就有害。紧张局势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利,也有有利的一面。紧张局势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紧张局势“归根结底对于帝国主义更不利”。这些态度表明,尽管台湾海峡地区的局势日趋紧张,但中国政府并没有被美国的威胁所吓倒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43352页。。
9月6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表了关于台海地区局势的声明。声明驳斥了杜勒斯的谬论,指出要不是美国的武力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岛早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之下了。声明说,最近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大陆的骚扰和破坏更为猖獗,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军给予坚决打击。任何外来干预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声明严正指出,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大量集结武装力量,公开威胁要把它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这是对六万万中国人民严重的战争挑衅,是对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
周恩来的声明对美国的《新港声明》作了针锋相对的回答: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中国人民尤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大陆内海中存在着像金门、马祖这些沿海岛屿的直接威胁。美国的任何战争挑衅都绝对吓不倒中国人民,相反只会激起六亿中国人民与美国斗争到底的决心。
周恩来的声明指出,“中国和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国际争端和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内政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美国企图把这两件事混淆起来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完全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自己的领土,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这一立场既驳斥了美国的干涉借口,也表明了中国暂时没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打算。为了重新推动中美外交谈判,声明说:中国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按照五项原则实行和平共处,并且用和平谈判的方法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现在美国政府又表示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为了再一次进行维护和平的努力,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但声明接着也指出:“但是美国在中国台湾地区所造成的战争危险并未因此减轻”,中国“决不能丝毫放松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威胁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斗争”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6852687页。
。在这一精神指导下,中国继续对金门进行炮火和海空封锁。
对于周恩来的声明,美国政府立即做出了反应,白宫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同意迅速恢复大使级会谈,并具体表示美驻波兰大使已准备好会见王炳南大使。
9月8日,毛泽东在最后国务会议上再次谈到国际形势和金、马问题。他在分析美国要对金门、马祖进行武装干涉时说:问题是十一万国民党军队,金门九万五,马祖一万五,只要有这两堆在这个地方,美国就得关心。他说:“总而言之,你是被套住了。要解脱也可以,你得采取主动,慢慢脱身……现在我看形成了金、马的脱身政策。你那一班子实在想脱身,而且舆论也要求脱身。脱身者,就是从绞索里面脱出去。怎么脱法呢?就是这十一万人走路。”他说“台湾这些地方早一点解脱,对美国比较有利,它赖着不走,就让它套在这里,无损于大局。我们还是搞大跃进”。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0页。
毛泽东对西方舆论相当敏感,尽管此时美国还是气势汹汹,但他已经看到了美国人可能要脱身的苗头。因此,他坚持要国民党从金、马“走路”。
5. 赫鲁晓夫的台前幕后
台海危机的再度爆发使苏联感到极为不安。赫鲁晓夫对于中国没有事先把这次炮击通告他很不满意。但是大敌当前,他不想让这种不满表现出来。美国的《新港声明》发表以后,国际舆论对于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更加担心。9月5日,苏联报刊表示:美国侵略性的报复行动,可能不限于台湾海峡,对此苏联不会无动于衷,决不会袖手旁观。为了了解中国在危机中的真实目的和基本立场,苏联提出了由外长葛罗米柯秘密访华的要求。同一天,周恩来向苏联参赞苏达利柯夫表示欢迎葛罗米柯来访,并介绍了中国在这次危机中的立场、策略和已采取的行动。
周恩来说,中国炮击金门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不是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这一态度表明,中国并不指望苏联的军事支持。
由于中美两国已处于军事对峙状态,苏联如不正式表态就等于告诉世界,中苏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立场不一。6日和7日,葛罗米柯在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周恩来对中国政府的立场作了全面说明后,葛罗米柯表示苏共中央完全赞同中方的措施。针对杜勒斯的声明,周恩来说:我们只放了几个炮,我们的政府还没有说什么话,美国就露了底。国民党尽量想把美国拖下水。至于美国,它不加理睬,那它的那些亚洲傀儡国家会产生离心倾向,如参加战争,就很难说会是局部战争。周恩来说,美国还未做出进行军事干涉的最后决定,如果美国对中国发动战争,并且在作战中使用战术核武器,届时苏联可对美国发出严重警告,但不要立即加入战争。在美国使用大当量核武器,并以这一方式冒险扩大战争的情况下,苏联可以用核武器进行报复性打击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66167页;石仲泉:《周恩来的卓越奉献》,第370页;1958年9月27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件,转引自“The Cold War In Asia”, Cold War International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 ed. by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pp.226227.。
葛罗米柯还带来了一封赫鲁晓夫致美国总统的信稿,征求中方意见。7日,中方基本肯定了赫鲁晓夫的信稿。同一天,此信被送交美国政府。赫鲁晓夫在信中说,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行动令苏联感到严重不安。美国的军事示威是要阻挠中国解放台湾,保持这个中国岛屿作为它的军事基地,美国还企图阻挠中国为解放沿海岛屿而采取的合法行动。信件在谴责了美国调动舰队的措施后说,水上舰队的全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威力空前强大、作用空前迅速的核武器和火箭武器的时代”,这些军舰只能用作鸣放礼炮,或者作为“火箭的打靶目标”。赫鲁晓夫最后警告美国说,“对我国伟大的朋友、盟邦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忠于自己义务的我国,将尽一切可能同人民中国一道维护两国的安全、维护远东和平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赫鲁晓夫是在了解了中国不会主动挑起战争的方针后表示支持的,它虽然来得迟了一点,但对世界舆论还是产生了较大影响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67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6942701页。。
赫鲁晓夫要向世界表明,他是坚决站在中国一边的,对于他的这一姿态,美国方面并没有感到意外。9月16日,美国情报部门认为:苏联公开承诺支持中共,部分是要威慑美国。但这种承诺几乎肯定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估计之上,中国在“台海地区的活动不至于将美国的干预挑动到这样的规模,即要求苏联公开的军事参与”。美国情报部门确信,苏联并不想同美国打仗,如果美国的行动只使用常规武器,涉及的地区局限在台湾海峡附近,苏联可能只提供道义和物质援助。但如果美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苏联的反应可能要依美国打击的范围来决定。如果美国深入打击中国内地,也许苏联认为它有必要进行核报复
FRUS, 1958—1960, Vol.19, pp.166168, 205206.。
当然,赫鲁晓夫也想做些事来表示他愿意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葛罗米柯回国后,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应邀去克里米亚讨论台海危机。赫鲁晓夫在会见刘晓时通报了苏方为应付局势所作的准备,认为美国有可能进一步采取挑衅行动,他说“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是很危险的”。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将考虑采取一些具体步骤,来帮助中国制止美蒋侵略阴谋的实现”。他认为美蒋在台海地区的优势主要是在海空方面,“苏共中央经过讨论研究后认为,应在空军方面加强那一地区的力量,使这里的(即苏联)力量对美蒋的海军起到威慑作用”。9月22日,周恩来召集了一次会议研究赫鲁晓夫的建议。然后,中国政府以毛泽东致赫鲁晓夫信函的方式,婉拒了苏联提供空军援助的建议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6265页。。
但是,赫鲁晓夫对中国的这一立场更为不满。9月27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说:苏方已经研究了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允许敌人有这样的幻想,即如果美国或日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进攻,苏联将会袖手旁观。信件以嘲讽的口吻说:“感谢你们的高尚,你们准备承受一次打击并且不使苏联卷入。”“如果当原子弹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中国的儿女们已经付出生命的代价,而苏联,拥有不仅能阻止而且对我们共同敌人占有优势的可怕武器,却允许自己不向你们提供援助,这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共产主义工人阶级运动,都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是对世界工人阶级的犯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教导的共产主义最神圣的原则的背叛。”
1958年9月27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件,转引自“The Cold War in Asia”, Cold War International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 ed. by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pp.226227.
苏共这些情绪激烈的话表明,苏共并不真正认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具有行动自由。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行动使苏联有陷入或是卷入战争的风险,或是丧失盟国信誉的两难困境之中。尽管这封信反复强调了中苏团结和联合的重要性,强调不能给西方造成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机会。但信中的主要观点说明,赫鲁晓夫不仅对中国的行动极其不满,而且他还认为中国主动挑战美国,对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构成了威胁。
6. 中美两国在“护航”问题上的较量
8月2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下令准备为国民党提供护航,希望以此打破中共对金门的封锁。8月29日,艾森豪威尔决定,美国海军的护航只能在国际水域中进行,美国的护航舰队将前进到距中国大陆海岸3海里的海区
FRUS, 1958—1960, Vol.19, pp.76, 9699.。
早在炮击开始以前,排除美军海上干涉的可能性已在中国领导人的考虑之中。8月21日周恩来与外交部及军队领导人讨论关于中国领海宽度的文件。8月23日,他又同毛泽东讨论了这一问题。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了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这一声明是要以国际法手段将美国飞机舰只阻挡在金门水域之外。此刻正值美国海军要为国民党运输船队护航之时,美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宣称它从不承认关于12海里的任何领海要求,美国对领海的态度一直是3海里范围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63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6802681、26832684页。
。美国的这一态度表明,它的护航行动很快就要开始。
9月7日,一支由14艘军舰组成的美蒋混合编队出现在金门。美国军舰将国民党的运输舰围在当中。出于慎重,解放军没有立即对国民党的这次补给行动进行打击。对美军的这一卷入应该做出何种反应,担任前线指挥的叶飞向北京作了请示。毛泽东的回答是照打不误,当叶飞再请示说,是不是连美国军舰一起打?毛泽东说“只打蒋舰,不打美舰”。而且他还规定,如果美舰开炮,我军没有命令不得回击。在避免主动同美军发生冲突的同时,毛泽东也在观察美国的军事干预究竟会走多远
叶飞:《征战纪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353356页。。
18日,美蒋混编的运输舰队再次出现在金门外围。为了避免打到美国军舰,叶飞下令等这支编队到达金门以后再开炮。中午12时,美蒋舰队到达金门料罗湾港口。根据毛泽东的命令,解放军炮兵集中火力攻击停在港口的国民党舰只。战斗开始后,停留在3海里以外的美国军舰立即后撤,在5至12海里处徘徊观望,未发一炮。码头上的国民党运输舰和护航船只,一艘被击沉,数艘被击伤。这次战斗虽然不能阻止美国继续为国民党船只护航,但中国方面进一步了解了美国的底牌。当天,毛泽东指出,美国并不敢进攻中国,它的主要目的还是霸占中间地带
徐焰:《金门之战》,第248251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7页。。
9月11日,解放军第二次对到达金门的国民党运输船队进行炮击,美国护航舰只仍然在3海里外观望。由于运输舰船两次在料罗湾码头遭到沉重打击,连一吨物资也没送上金门,美国舆论对补给的失败议论纷纷。13日毛泽东提出了白天黑夜打零炮,“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的方针,加强了对金门及附近海域的封锁
FRUS, 1958—1960, Vol.19, pp.172174;《建国以后毛泽东文稿》第七卷,第416页。。
从9月14日起,美蒋开始改变补给方式,以大型登陆舰载运载两栖车辆至靠岸地带,然后再由两栖车辆运输物资上岸。但是,这些车辆仍然遭到解放军炮兵的打击。美国情报官员18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承认,解放军对金门的封锁是高度有效的。直到9月下旬,经过一再试验,美蒋才想出了用两栖车辆乘夜分散登陆的方法,同时还不惜代价进行空投补给。这样每天的补给量可达到125吨。虽然还不能弥补每天300吨的最低消耗,但可以延长岛上军队的生存期。美国军方估计,如果按每天补给100吨计算,国民党在金门可以维持到11月15日。
FRUS, 1958—1960, Vol.19, pp.208, 272.
9月24日以后,美国空军接过了“台湾”的空防,而国民党飞机则全力出动,并在空战中使用“响尾蛇”导弹击落解放军战机一架。美蒋试图夺回制空权,并对金门开展大规模空投补给。10月初的个别日子,对金门的补给曾达到过600吨。但10月3日,解放军空军一举击落 F46 运输机两架,迫使国民党停止白天空中补给。美蒋还准备在10月4日进行一次200吨的补给行动,因天气原因而延期。到10月5日为止,解放军对金门的封锁仍然是有效的,但由于解放军空、海军受不得出公海作战的限制,对国民党两栖车辆“渗透”上岸和敌机夜间空投也不能完全封死
FRUS, 1958—1960, Vol.19, p.503;徐焰:《金门之战》,第261页。
。国民党军队在金门的生存时间虽然有所延长,但美蒋并没有真正打破封锁。所以,在补给问题上,双方形成了一种军事上的僵局。
这一阶段的军事较量表明,中美双方继续利用军事手段来推进政治目的。在此同时,双方也意识到了危机的严重性,因此对于可能导致行动升级的措施都比较慎重。10月下旬,毛泽东曾经解释说:“在炮打金、马过程中,我们和美国人都搞边缘政策。美国集中了那么多的军舰,而且侵入我领海,给蒋介石船队护航,但又从不开炮;我们也是一万、两万发炮弹那么打,美舰护航时更大打,但只打蒋船队,不打美船队……美国人在这个战争边缘,我们在另一战争边缘,双方都在战争的边缘,都不越过边缘。”“我们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人的战争边缘政策。”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90页。
这是对该阶段的军事斗争的形象说明。
四、逐步降级——危机的第二阶段
美国避免直接卷入冲突的行为表明,它的干预在强度和时间上都是有限度的。中国的炮击行动是要侦察美国的反应,因此必然要根据美国反应做出政策调整。中美两国的这些行为表明,两国都不想为此发生全面对抗。在了解了对方的意图后,双方都会采取措施缓和危机,或寻找谈判解决的道路,或将争执中的问题推迟解决。
1.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恢复
毛泽东9月8日的讲话表明,中国虽然不打算与美国发生战争,但中国占领金门的目的没有改变。此时,为海峡两岸传过话的香港记者曹聚仁又到了北京。8日,周恩来在会见他时分析说,美国是在虚张声势,金、马的蒋军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是与岛共存亡;第二条是全师而还,好处是金、马驻军占国民党军队的三分之一,这个数字对我们不在乎,对蒋介石有作用,可以作为对美国讲话的资本;第三条是美国逼蒋撤退,这条路是很不光彩的”。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68页。
曹聚仁此时到京可能也负有传话使命,“与岛共存亡”大概就是“台湾”要他转告的口信。但周恩来此时坚持要国民党从金、马撤走的立场。此外,周的分析表明,中国并不认为美国在沿海岛屿问题上会全力支持蒋介石,中国对美国的这一分析,也有很准确的预见性。
在了解了美国的基本态度后,毛泽东准备离开北京去外地视察。临行前一天,即9月9日晚,毛泽东召集了一次会议来讨论下一阶段中国的对策。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张闻天、黄克诚、王炳南、乔冠华等人。张、王、乔都是外交部的干部,他们的到会表明,毛泽东准备将重点转移到外交方面。同时,中央也准备采取一些措施缓和紧张局势,以配合即将在华沙重新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68页。。
王炳南大使在8月底已被紧急召回国内,中国此时已在为中美谈判的恢复作准备。在9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指示王炳南说,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不要用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的民族感情。可以对美国人说,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与六亿中国人民为敌呢?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7074页。
9月10日,周恩来又接见了曹聚仁,请曹次日返香港后以最快办法转告台湾,为了宽大并给予蒋方面子,准备以七天的期限,准其在此间由蒋军舰只运送粮食至金门、马祖。但前提是决不能由美国飞机和军舰护航,否则我们一定要向蒋军舰只开炮。周恩来再次提出国共两党可以公开谈判的问题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68页。
。这一口信表明,大陆对金门的封锁将继续维持下去,与此同时也准备给国民党从金、马主动撤军搭一个下台的梯子。
美国方面也急于恢复大使级会谈,早在8月初美国驻波兰使馆的外交官就几次同中国外交官联系,要求尽早恢复会谈。王炳南刚从北京返回华沙,美国代表就催促早日开始会谈。9月13日杜勒斯指示驻波兰大使、美方首席代表贾各布·比姆说,美方的主调是世界舆论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把远东或世界拖入战争中去。因此,美国的第一项动议应是停止敌对行动,其次是“非正式停火”。同一天,毛泽东也指示说,“华沙谈判,三四天或者一周以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
FRUS, 1958—1960, Vol.19, p.18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卷,第416页。
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举行,这是双方希望缓和的信号。贾各布·比姆在发言中将台海地区紧张局势的责任推给中国,声称美国不能接受通过使用军事力量带来的领土变化。他要求中方立即停止对金门的炮击,说一旦停火实现,美国愿意转向讨论“结束挑衅性行动和消除海峡地区紧张的问题”。比姆的这一番话暗示,在中国同意停火以后,美国可以以消除挑衅行动为名,不再允许蒋介石利用金门进行骚扰活动。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国民党对金、马的占领维持下去,并要使中国接受台湾分裂的永久化。
王炳南在会谈中指出,解放台湾、澎湖包括金门、马祖是中国内政,美国无权代表台湾当局讲话,无权提出停火建议。他说,为了消除蒋介石集团对大陆港口的威胁,中国决心解放金、马等沿海岛屿。如果国民党军队主动撤退,中国将不会进行追击。他还说:“中国在收复金门、马祖这些岛屿后,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王炳南在会谈中说:“我要坦率地声明,由于蒋介石集团的生存绝对依靠美国的支持,为什么你方不能说服他们从金、马等岛撤退呢?”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7577页;FRUS, 1958—1960, Vol.19, pp.191194.
显然,中方对先解决沿海岛屿,再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作了坦率的表示,这说明了中国想以1955年的“大陈方式”解决金、马问题。
这次会谈表明,双方立场相去很远。16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估计美方在第二次会议上仍会在停火问题上纠缠,中方拟在第二次会议上提出要求美国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出其一切武装力量,停止向中国领海、领空的军事挑衅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他估计说,“关于停火和撤军的斗争,估计会进行几个回合。在三四次会议后,可看出美方究竟有无意思要将蒋军从沿海岛屿撤走”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70171页。
。通过谈判,促使美国人压蒋从金门撤出,这是中国在华沙谈判中的具体目标。
18日,双方进行了第二次会谈。美国方面拒绝从台湾地区撤出军事力量,同时再次提出所谓停火建议。中国代表王炳南也明确拒绝了美国的所谓停火建议,他指出,美方的要求是故意将中美之间的国际冲突,与将台湾和沿海岛屿从蒋介石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一纯粹的国内事务混淆起来。他说中国解放自己的领土是中国的内政,就像过去解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那样,本来是不会引起任何国际紧张局势的。台湾地区的紧张根源完全就在于美国武装侵略台湾
FRUS, 1958—1960, Vol.19, pp.208216.
。第二轮谈判表明,美国此时还没有改变其援助国民党防守金、马的政策和打算。
21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缅甸和锡兰大使时揭露说:中国政府期待通过和平谈判同蒋介石解决台湾问题。蒋军经常骚扰沿海大陆,“这个情况我们不能忍受”。他说,美国不但要中国承认其占领台、澎合法化,还要承认对沿海岛屿的侵略合法化,中国不能接受。同一天他对来访的柬埔寨经济代表团说,“美国要扩大侵略,从台湾扩大到沿海岛屿,我们决不能接受,所以要请它走。它不走,要打仗,那只好接受”。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72页。
周的这些话是要让美国知道,中国不可能同意以放弃解放自己领土的权力为条件,换取国民党不利用金门进行挑衅的方案。
9月下旬,双方又进行了第三次会谈,美国在30日的会谈中要求大陆和金、马之间“互惠性地”停止骚扰和挑衅。美国还表示,如果实现停火,有关措施还可以包括减少驻金、马的军队和装备。但中方对这种有条件的让步不感兴趣
FRUS, 1958—1960, Vol.19, p.294.。
2. 美国的政策转变
大陆对金门开始炮击以后,受到沉重打击的国民党当局非常紧张。面对金门被封锁的前景,蒋介石在8月27日致艾森豪威尔的信上说,中共要国民党“自然瘫痪和崩溃的策略比全面军事进攻更凶恶和危险”。国民党在炮击发生后立即要美国给予支持,他们一方面要美国公开声明美军将参与对金、马的防守。另一方面,他们还要求美国政府同意国民党对大陆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蒋介石想要利用这一机会扩大事端,尽可能地把美国拉入同中共的军事对抗中去
FRUS, 1958—1960, Vol.19, pp.8386, 7475, 7778.。
美国对蒋介石的目的非常了解,一些政府官员认为,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在国民党采取行动以前就使美国卷入危机。中共的军事行动还没有对“台湾”构成充分的威胁,因此不能同意“台湾”立即对大陆机场进行报复性空袭的要求。由于艾森豪威尔没有给他复信,蒋介石8月31日会见美国大使时大发雷霆,他指责美国阻止国民党军队行动是“不公正”、“不人道”,打击了台湾的士气。他威胁说,如果美国三天内不给答复,他就无法维持部队的士气。蒋介石的威胁暗示着他可能要采取单方面行动。为了安抚蒋,9月11日艾森豪威尔给他回了信,保证美国将在安全和国际威望方面支持他。但实际上,艾森豪威尔认为,蒋介石是在利用美国对他的支持
FRUS, 1958—1960, Vol.19, pp.8993,107108, 115.。
在杜勒斯发表《新港声明》以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危机政策受到了美国舆论的抨击,著名评论家李普曼说:“极为清楚的是,蒋认为机会来了,并且决心要抓住它,这将使美国陷入一场在中国大陆的战争。”前国务卿艾奇逊也指责《新港声明》说:“实际上的事实是,我们的政府因为要帮助蒋,已经最不明智地卷入了它不能控制的局势中。”参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主席西奥多·格林写信对总统说,美国的军事卷入发生“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对我们的安全没有重大关系,并且没有盟国支持的问题上”。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和约翰·肯尼迪、民主党众议院领导人山姆·雷伯恩和林登·约翰逊也都拒绝支持政府的危机政策
Soman, “‘Whos Daddy’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Offshore Islands Crisis of 1958”.。
国际舆论也反对美国的战争冒险政策。许多亚洲中立国家强烈反对美国的军事干涉政策。连日本也表示,如果美国在沿海岛屿使用核武器,日本政府可能被迫要求美军撤出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不支持美国为沿海岛屿卷入战争。英国的态度非常明确,首相麦克米伦向杜勒斯重申: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法律地位完全不同,为了帮助蒋介石保住这些小岛而战,这对英国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9月11日,面对英国舆论的批评,麦克米伦正式表态说:“我们没有为远东局势对美国承担任何义务。”
FRUS, 1958—1960, Vol.19, pp.120, 13914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737页。
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友,英国拒绝同美国站在一起,这对美国公众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杜勒斯虽然气势汹汹,但底气也不足。8月23日,金门的炮声刚刚响起时,杜勒斯似乎就清醒了一些。他承认,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美国并不处于完全可以站得住的地位”。他说要阻止中共以武力来改变领土是一回事,但是,说他们应当默认这些地区被国民党当作行动基地,以激起内部反抗,并进行针对中共政权的全面宣传,这又是另一回事。他承认,这样做会使这些岛屿成为“特权庇护所”,国民党能从那进行针对中共的政治和颠覆战,而共产党却不能进行报复。因此,美国也要考虑寻找和平的暂时解决
FRUS, 1958—1960, Vol.19, p.69.。
在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下,9月8日,杜勒斯要求其下属考虑,“能否达成这样一种暂时解决,即国民党对这些岛的法律地位被(中共)承认,但这些岛实行某种方式的非军事化”。但饶伯森坚持说非军事化不是可行的解决办法,那会使这些岛屿完全暴露在共产党人进攻之下,而且在美台之间也会产生严重分歧。饶伯森说,在要求国民党不以这些岛作为对大陆挑衅的基地方面,美国具有强有力的地位
FRUS, 1958—1960, Vol.19, p.157.
。显然,饶伯森的看法就是美国在大使级会谈中抛出的方案。
由于公众舆论明显地不支持政府的立场,艾森豪威尔试图向公众解释他的方针。8日,他发表了电视和广播演讲,声称美国决不在武力侵略面前怯懦地退却,并且把“慕尼黑谈判”搬出来为他的干涉政策辩护。但在私下里,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11日,他在会见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时说,从军事角度看,国民党军队防守金、马是很不利的。因此在他“不想在通过谈判放弃这些岛的问题上显得不愿妥协”。他承认这样做是有困难的,而且正因如此,国务卿倾向于采取比他更强硬的立场。艾森豪威尔说,他“正在试图找到一种强国也能进行妥协的途径”。当天,麦克尔罗伊告诉杜勒斯,参联会正在重新估计金门、马祖对于保卫台湾的重要性,他说,他们很可能得出这些岛屿是不需要的结论。
同一天在白宫召开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说,由于金门、马祖是不可防御的,他“准备在可预见的将来放弃金门,当然现在阶段还不能公开这么说”。在总统的明确表态下,杜勒斯也表示可以采取一些降低对抗程度的措施。他建议逐步结束国民党利用金门对大陆进行的破坏活动,并且暂停美国间谍飞机对中国的空中侦察,暂停美国军舰对国民党船队的护航
FRUS, 1958—1960, Vol.19, pp.161163.。
9月16日,针对蒋不愿从金门撤军的态度,艾森豪威尔对杜勒斯说,美国可以为蒋提供包括两栖舰船和伞兵等在内的机动能力,以满足他以后打回大陆去的愿望。但杜勒斯说,蒋介石要保住金门还有其他理由,“这些岛屿是国民党人仅剩的中国领土,他极不愿意放弃它们”。但艾森豪威尔说,“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事,否则我们将被指责使同盟瓦解,或者是引起战争,这两者都是不可接受的”。显然,盟国对这一危机的反应使艾森豪威尔非常不安,他希望能找到另一条出路
FRUS, 1958—1960, Vol.19, pp.196197.。
国务院内部对危机的前景也有不同意见。远东司的地区计划顾问格林在18日指出,中国的炮击非常有效,要打破对金门的封锁,其代价将非常高昂。他认为,由于金门的物资储备已经下降到不足一个月的需要,美国很难维持现状。如果美国主动扩大军事行动,那就迟早要动用核武器,这不仅会带来核报复问题,而且会招致世界舆论的谴责。日本也可能要求撤出驻日美军。格林认为,再拖一个月金门可能失守,因此美国必须迅速采取外交行动寻找出路,并且防止国民党自行采取军事行动
FRUS, 1958—1960, Vol.19, pp.221224.。
9月20日,台湾当局“行政院长”陈诚召见美国大使要求美国同意国民党飞机对大陆进行报复性打击。陈诚说,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补给,而是部队在长期炮击下的心理挫折。他说“台湾”的忍耐已到了极限,仅仅回击中共的炮兵阵地已没有意义,最好的策略是摧毁共产党的交通设施和机场。陈诚明确说,“台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金门撤军,它也将拒绝正式的“停火”、非军事化、中立化等诸如此类的建议,并且也不赞成将海峡危机提交到联合国去。美国已在另谋出路,台湾当局的这种态度自然得不到美国的支持。10天后,美国政府拒绝了陈诚的要求
FRUS, 1958—1960, Vol.19, pp.239240,244.。
9月下旬,对于美国是否和如何改变有关政策,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发生了意见冲突。艾森豪威尔认为,尽管补给情况有所好转,但美蒋在海峡地区的军事地位实际上是不能持久的。他说世界舆论的三分之二,美国舆论的百分之五十是反对政府的现行政策的。他希望能说服蒋介石同意从沿海岛屿撤军。但杜勒斯认为,美国的政策在西欧和东亚是得到理解和支持的。他说,最终的情况可能对美国有利,除非中共的消耗战能剥夺金门的生存能力。如果补给行动能继续成功,中共对金门的军事行动可能会逐渐停止
FRUS, 1958—1960, Vol.19, pp.266267.。
在艾森豪威尔的一再敦促下,杜勒斯开始采取行动。9月25日,他到达纽约试图让联合国介入危机。同时,他也要为美国的政策转变寻求支持。次日他向总统报告说,他已与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董事会主席约翰·麦克劳伊讨论了一起去台湾“与蒋商讨放弃哪些岛”的问题。在讨论中他谈到了如何使蒋接受让步,而又不会引起台湾局势垮台的反应。政府的妥协方针得到了洛克菲勒财团这位重要人物的支持
FRUS, 1958—1960, Vol.19, p.290.。
蒋介石意识到美国要脱身。29日,他召开记者招待会宣称,国民党当局“不容慕尼黑在远东之历史重演”,“就是战至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亦决不会放弃金门群岛的寸土尺地”。但是,他也不得不对艾森豪威尔政府要他调整政策的压力做出让步,他表示,金门是台湾的屏障,而不是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基地”
黄嘉树:《国民党在台湾》,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第313页。
。蒋介石后来说,他这样做是要帮助美国政府应付舆论。
但是美国人对此并不满意。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国民党在沿海岛屿部署大量军队不是一种完善的政策,对此美国只是默认和没有反对。在回答美国是否认为应该撤出这些军队时,杜勒斯说,“如果有了看起来是可靠的停火,我想把这么多军队放在那些岛上就是很愚蠢的”,“从军事角度看,将它们放在那儿是不明智和不慎重的”。杜勒斯还说美国的政策是灵活的,如果局势改变了,“我们的政策也会随之改变”
FRUS, 1958—1960, Vol.19, p.301.
。这一番话是公开向蒋施加压力,要他同意撤军。这表明美国处理这场危机的方针在9月底已经发生了部分变化,“脱身”已成为美国的主要动向。
3. 大陆不占领金门、马袓的决定
9月中下旬,中国政府继续奉行比较克制的政策。在这一段时间,由于担心中美会谈可能会出现不利于台湾的后果,
台湾当局
试图使危机升级。金门国民党军队对厦门市港口和居民区进行狂轰监炸,甚至炮击著名的高等学府厦门大学,造成了严重的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针对国民党的行动,参战人员中出现了在金门大打的主张。经过反复考虑,周恩来22日致信毛泽东说:在目前形势下仍以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的方针为妥。周恩来指出:海空炮火联合作战不好配合,且有触及美军的可能。“我实施对金门轰炸更不适宜,因这样做恰好给蒋介石空军以轰炸我大陆的机会。目前,美军还在控制蒋帮空军不许其轰炸我大陆,其原因是摸不透我空军回炸何地……我就以不促成蒋空军向我大陆轰炸为有利。如蒋轰炸大陆,而我只炸金门,反而示弱。”毛泽东回复说,这一意见是对的,要求“照此办理,使我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石仲泉:《周恩来的卓越奉献》,第373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73页。
。这种比较克制的反应表明,这一时期中央更倾向于不对金门发动地面和空中进攻。
9月27日,周恩来会见苏联驻华使馆代办安东诺夫时,对形势的发展作了三种估计:(1) 当条件成熟时,美国会准备让步,中美之间将找到妥协办法。如果美国保证蒋军撤退,我们可以同意让蒋撤退,可是现在条件还不成熟。(2) 双方坚持,继续拖下去,这种可能性较大。(3) 美国准备把头伸入绞索,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周恩来的这一估计表示,中国也想等美国走出下一步棋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73页。。
9月29日,毛泽东结束在外地的视察回到北京。30日他在会见新华社负责人吴冷西时说,我们不是不想拿下金门、马祖,但这个问题不单是同蒋介石有关,特别是要考虑美国的态度,切不可以鲁莽从事。在华沙的大使会谈,经过几个回合的互相侦察,大体可以判断,美国人要保台湾但不一定要保金门,而且有迹象显示美国人企图以放弃金、马换取我承认其霸占台湾。毛泽东指出,这就需要研究对策,关于占领金门的意见“恐怕不宜采纳”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8182页。。
杜勒斯9月30日讲话发表以后,在台湾引起了巨大震动,台湾当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蒋介石会后对美联社发表谈话说,杜勒斯的声明只是美国单方面的声明,他“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他说杜勒斯的讲话不知是出于外交上的原因,还是怀有其他目的,这些讲话与台湾的立场背道而驰,而且与杜自己早些时候的意见互相矛盾。蒋介石的态度表明,在撤军问题上美国与台湾有很尖锐的分歧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8242826页。。
杜勒斯30日的讲话和美台矛盾的发展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美国的政策在发生变化。从10月3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几乎天天开会研究台湾海峡局势。周恩来说,杜勒斯的谈话表明,美国想利用这个机会制造“两个中国”,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以此为条件,美国可能要台湾放弃所谓“反攻大陆”的计划,并且从金门、马祖撤退。“杜勒斯这个政策,一句话就是以金、马换台、澎”,他指出,美国的这一意图在会谈中说得比杜勒斯说的更露骨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8384页。。
刘少奇和邓小平认为,现在双方都比较了解对方意图了,美国人也知道我们并不想在最近时期解放台湾,也并不想同美国迎头相撞。公平地讲,在台湾海峡对峙中,双方都比较谨慎。他们认为军事和宣传两方面,中央的行动都是正确的。
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棋怎么走。他指出,我们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我们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能解放台湾,国民反攻大陆也不可能。蒋介石是不愿意撤出金、马的,我们也不是非登陆不可。可以设想,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怎么样?毛泽东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通过金、马保持同国民党的接触,也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主动手段。他说,这样做不会影响社会主义建设,金、马蒋军对福建也不至于造成多大危害。如果收复金、马,或者让美国人迫使蒋介石从金、马撤退,我们就少了一个对付美蒋的凭借,事实上形成“两个中国”。经过两天会议,中央决定军事上继续执行“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的方针,以打打停停、大打与小打结合的方法保持对金门的压力。中央还决定,中美大使级谈判要继续下去,但对于美国可能提出的以中国停火为条件,换取减少金、马的蒋军或从金、马撤军的方案则予以拒绝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8385页。。
10月5日,毛泽东下令停止炮击两天,并亲自起草了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这一文告表示,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原因是国民党当局过去长时期以各种方式猖狂袭击和骚扰大陆。文告提出,台、澎、金马是中国的领土,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文告警告国民党当局不要同美国合作,因为“总有一天美国人要抛弃你们的……杜勒斯9月30日的谈话,端倪已见”。文告宣布从10月6日期,暂停7天炮击,以便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9382839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8页注。
。中国这一行动使台海危机形势有所缓和。
12日,中国宣布再停止炮击两周,使金门军民得到充分补给,以利固守。1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曹聚仁。毛泽东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保住金门、马祖的方针,如蒋介石从那儿撤出,台湾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周恩来也表示,美国要用金、马换台、澎,我们根本不同它谈,台湾抗美就是立功。这次谈话表明,中共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沿海岛屿和台湾“分两步走”的打算,转而实行以后一揽子解决的方针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81182页。。
外交和军事上的僵局表明,由于难以无条件地达到目的,由于看到美国积极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中共
已经放弃
逼蒋退出金门的方针。中国政府的主要关注已经转移到如何防止美国利用危机搞“两个中国”的问题上。
4. 杜勒斯访问台湾
10月1日,蒋介石在紧张不安的气氛中召见美国大使杜姆赖特。他说台湾对杜勒斯在《新港声明》中提出重开谈判曾感到震惊,而现在又一次感到了震惊,杜勒斯关于撤军的建议严重损害了军队的士气。蒋介石说,这一切使他想起了当年因马歇尔要求谈判而带来的厄运。如果美国不想让“大陆上的那幕悲剧”在台湾重演,美国政府就应“在毫不妥协的基础上”坚定地支持“台湾”。他威胁说,否则,他将不能再控制台湾局势。说到激动之处,蒋介石要杜姆赖特转告美政府,他9月29日的谈话是台湾当局能够做出的“最大让步”,“没有任何外部压力,没有任何武器,包括原子弹”,能迫使他从沿海岛屿撤出一兵一卒
FRUS, 1958—1960, Vol.19, pp.319; 320, note 6.。
在接到了中国暂停炮击的消息后,美国政府很快下令,只要中共停止炮击,补给不受干扰,美国就停止为国民党护航。对中方暂停炮击的迅速反应表明,美国急于做出缓和姿态。尽管如此,总统艾森豪威尔仍对局势感到担心,并说美国“正在维持一种不合逻辑的立场”。他恼火地说,美国还在被迫做蒋介石要美国做的事,他正在准备告诉蒋介石应当在什么地方罢手
FRUS, 1958—1960, Vol.19, pp.335, 337.。
蒋介石对于中共停止炮击深感疑惑。6日,他对美军司令斯摩特说,彭德怀的文告是中共分裂美台关系的阴谋,美国应继续进行护航。新任“外长”黄少谷还对美国大使说,蒋要求美国不要以中共的这一行动为借口,提出金门撤军问题。他还说,如果美国停止护航,国民党当局就会陷于难以支撑的处境。但是,美国坚持宣布停止护航
FRUS, 1958—1960, Vol.19, pp.331, 338.。
华盛顿对中国的政策变化也大惑不解。10月8日,国务院开会分析形势。杜勒斯说停火是美国的胜利,但他不得不承认,美国面临严重的困境。他指出,如果维持台海地区的敌对状态,让局势拖下去并什么也不做的话,一年后如果中共重新进攻金、马,那时将没有人会支持美国的政策。蒋介石必须意识到,到时候他会没有退路。美国政府为了挽救他,同国会、同其他国家政府的关系也会紧张到接近崩溃的程度。因此美国不能允许这种危机再度发生。这次会议探讨了解决金、马问题的可行方案,如全部撤出还是减少岛上的军队,如果撤军国民党能否控制金、马,能否建立国际保证,能否从大担、二担撤军,中共能否接受有条件撤军,等等。由于意见分歧很大,杜勒斯强调“要做些事来摆脱这个棘手的问题”
FRUS, 1958—1960, Vol.19, pp.349353, 375376. 。
杜勒斯知道,要阻止危机再度发生,关键是要控制住蒋介石。10日,杜勒斯在会见台“大使”叶公超时说,形势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中共无法以炮火封锁来达到目的。现在中共面临让军事行动平息下来,或者使军事活动升级的困难抉择。两天后,他同参议院外委会主席谈话时承认:“美国并没有完全克服补给问题。”杜勒斯认为,中共试图用政治手段达到目的。他说,美国最大的困难是阻止盟国承认中共,美国不能把头埋在沙子里,以为现行的立场在两年后还会有效。他表示要去台湾与蒋介石讨论,“如何使我们的政策更能被美国人民和盟国所接受”
FRUS, 1958—1960, Vol.19, pp.359361.。
彭德怀于12日宣布再停止炮击两周以后,美国政府下令将一部分军舰撤离台海地区,局势进一步得到缓和。由于美国新闻媒体上不断出现要国民党减少在金、马驻军的报道,美台之间的相互猜疑加深了。杜勒斯13日对叶公超说,中共声明中的语言很不寻常,他对中共要国民党“固守金门”感到奇怪。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森提醒叶说,共产党要在台湾挑起反美情绪,他还试探国共之间是否会进行秘密谈判。蒋介石则怀疑,中共与美国在华沙可能达成了协议,暂停炮击只是双方的默契,意在迫使国民党从金门撤退。台湾当局还担心,杜勒斯访台会加强对国民党的压力。叶公超恳求说,在杜访台的联合声明中,不应有美国为撤军而向台湾施压的表示
FRUS, 1958—1960, Vol.19, pp.382388.。
10月13日,美国参联会主席特文宁上将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报告,军方已同杜勒斯进行了讨论,他们的一致意见是,在炮火平息下来后,从金门撤出三分之二的国民党军队是明智的。他们也讨论了沿海岛屿的“非军事化”,但这方面存在着困难,要等杜勒斯去解决。艾森豪威尔说,如果达成撤出部队而不丢失面子的一致意见,下一步是要说服蒋。“我们必须通过说服而不是施压来达到目的,否则我们将被指控背弃了原有的立场。”他说主要的问题是不能在炮火或威胁下撤军。艾森豪威尔的这一想法表明,他根本没有将中国停止炮击看作美国的胜利,在他看来,美国需要停火作为让步的条件。他担心中共可能重新进行炮击,那样将妨碍美国说服蒋撤退
FRUS, 1958—1960, Vol.19, pp.381382.。
国务院最初为杜勒斯准备的访台文件表明,美国政府试图造成“事实停火”,以此推动台海局势向“两个中国”的方向发展。有关的文件称,“实际上可以创造一种类似于朝鲜和越南停火线的形势,在那儿有密切的接触,但却没有越线的挑衅,并至少有某些感觉得到的军队减少”。在该方案中,削减金门驻军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安全措施
FRUS, 1958—1960, Vol.19, pp.399400.。
杜勒斯10月21日抵达台湾,当天即与蒋介石进行了私下交谈。他宣读了国务院准备的文件,提出了美国政府的基本想法:“要消除世界对于台湾当局是对和平威胁的担心。”蒋却重申了要反攻大陆的决心。对于美国将他看成“和平的威胁”,蒋回敬说,美国对他缺少信任,对他有很多误解,他并不要以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反攻大陆。他还一再对杜强调,他不能放弃金门
FRUS, 1958—1960, Vol.19, pp.418421.。
在次日的会谈中,杜勒斯说台湾当局的最大危险主要不是军事方面的而是政治方面的。由于世界对和平条件的渴求,所有自由国家都感到,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不仅危及和平,而且是台湾“想使这一关系危及和平”。杜勒斯又将朝鲜、印支战争与中国内战相比,声称有必要“消除‘麻烦点’”。杜勒斯说,除了韩国和南越,美国也许是“台湾”唯一的有力支持者。他说美国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阻止其他西方国家承认中国,他表示美国不能在现有环境下长期保护台湾。
杜勒斯在给蒋介石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前景后,指责国民党当局的观点基本上是军事主义的,因此需要加以改变。杜勒斯说,台湾当局如果坚持它的军事主义观点,其形象是没有吸引力的。国民党仍然有一些军事使命,如保卫台湾,维持沿海岛屿不让中共占领,以及准备与大陆的反叛分子合作。他说,相信国民党当局通过同美国的合作,能在找到发挥这些作用的方式的同时,为自己找到更重大和更能被接受的使命。他认为,国民党当局的主要使命应是维护中国文化传统,“防止中国的美德被共产党毁灭”等
FRUS, 1958—19600, Vol.19, pp.421423, pp.424426.。
毛泽东马上看出了蒋杜争吵的含意。22日他在常委会上说,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矛盾。这次杜勒斯同蒋介石吵了一顿,说明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联蒋抗美。我们暂不解放台湾,可以使蒋介石放心同美国人闹独立性。我们不登陆金门,但又不答应美国人的所谓“停火”,这更可以使美蒋吵起架来,过去一个多月中,我们的方针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现在仍然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更可以宽一些,以利于支持蒋介石抗美。会议决定要进一步利用美蒋矛盾,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了“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的方针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8889页。根据吴冷西回忆,21日下午开了常委会会议,毛泽东对杜蒋会谈的内容作了评论。但根据美国外交文件,杜蒋第一次会谈是在21日下午4时,所以吴冷西关于这次会议的时间记录可能有误,很可能是在22日开的会。。
22日,杜勒斯继续同蒋介石会谈,他要求台湾当局宣布,“反攻大陆的基础不是中华民国的武装力量和在沿海岛屿的阵地,而是6亿大陆中国人的精神和灵魂”;他还要求台湾谋求签订停战协议,并由蒋本人宣布,国民党将“不主动进行武力反攻大陆的努力”,国民党军队要避免对大陆进行袭击、挑衅以及进行空中活动;在沿海岛屿问题上,“台湾”必须表示愿意接受任何解决,只要这些岛不被交给共产党;它还必须保证不利用这些岛屿从事内战,不利用它们封锁厦门和福州港口,及将其当作“跳板”。杜勒斯本人虽然没提金门撤军,但对蒋介石来说,要其放弃武力反攻大陆,其严重性远远超过金门问题。听完杜勒斯的话后,蒋立即要求休会考虑
FRUS, 1958—1960, Vol.19, pp.424426.。
下午,由黄少谷出面同杜姆赖特会谈。显然,蒋介石还想抵抗一番。黄少谷指责美国说,“台湾”的困难来自有些国家的错误观念,他们倾向于以任何代价实现和平,尤其是这些代价由别人来付出时更是如此。在以反共陈词滥调为国民党的政策作了一通辩护后,黄少谷说台湾“已准备不反对实现事实停火”,但一个有自尊心的政府的行为,如果超过这一点就会丧失它的生存权利。他说美国的建议“其性质几乎到了动揺‘中华民国国本’的地步”,等于是要国民党自愿宣布接受“两个中国”的观念。黄少谷竭力表明,国民党绝不能容忍接受其流亡政府的地位,不能同意这一地位的永久化,他说这样做无异于“自杀”,“台湾”即使丧失外国政府的支持也不能丧失人民的支持。但是,他没有敢直接拒绝美国要蒋宣布不以武力反攻大陆这一条
FRUS, 1958—1960, Vol.19, pp.428429.。
晚上,杜和蒋讨论了金门的军事形势。蒋介石承认,金门守军的日子如同在监狱之中,中共“打打停停”的战术,使国民党军队紧张和疲劳不堪。他说,如果这样的炮击再继续三四个月,对守军将产生崩溃性影响。蒋说他无法解决金门问题,希望美国能提供帮助,否则他只能对厦门附近的运输线进行轰炸。杜勒斯说,美国现在没有办法可摧毁中共的炮兵阵地,除了使用核武器。蒋闪烁其词地说,他认为不需要使用核武器,但认为使用核武器也可以考虑。杜勒斯告诉他说,美国并没有那种只打击炮兵阵地的核武器,使用核武器将会导致数百万人死亡。蒋听了这一点才缩了回去,表示他不熟悉核武器,也不想用核武器,因为那会引起大战,并使美国卷入大规模敌对中。但在23日,蒋介石又一次向杜提出要解决中共的“打打停停”战术,说这对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影响很大。这表明,尽管有美国的援助,国民党对于守住金门仍感到没有把握
FRUS, 1958—1960, Vol.19, pp.430433.。
经过讨价还价,在23日杜勒斯离台前“美台”双方达成了妥协。蒋杜联合公报声称,国民党当局的“主要目的是要做中国人民的当之无愧的代表”,“恢复大陆人民的自由是它的神圣使命”,而实现这个使命的主要手段是实行三民主义,“而不是使用武力”。这说明,蒋介石虽然认为杜勒斯的基本观点危及国民党当局的“国本”,但是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他不得不向美国作了让步。公报没有提从金门撤出部分军队的问题,尽管台湾已经承诺将减少一万多人。公报说,“美国承认‘中华民国’是自由中国的以及广大中国人民所抱的希望和愿望的真正发言人”。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8842886页;
FRUS,1958—1960, Vol.19, pp.440442.
10月23日,杜勒斯一上飞机,美国就播发了他一周前接受英国电视台采访的消息。杜勒斯在这次采访中说,台湾与美国取得了一致意见,“不以武力打回大陆或攻击大陆,除非在与我们取得共同协议的情况下”。世界舆论迅速对此做出反应,认为蒋介石已被迫同意放弃使用武力反攻大陆。对此,蒋介石十分不满。为了挽回面子,叶公超受命对记者解释:国民党人只是在“原则上”放弃使用武力收复大陆,但是并没有放弃支持和帮助谋求推翻北平政府的反共运动的权利,也决不会放弃武力进行自卫。他还说,援助匈牙利式的叛乱并不是蒋杜公报中宣布放弃的那种咄咄逼人的使用武力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874、2915页。。
10月25日,毛泽东又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他在文告中说:“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文告指出“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他提醒台湾当局“不要过于寄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文告公布了双日不打炮、单日打炮的方针,并说这样做是有利国民党固守金门。“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针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活动,文告还要国民党当局加强团结,一致对外,“不要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
美国发表的英文版公报中“自由中国”一词用了大写F,这可能是毛泽东在25日文告中说,美国把国民党当局“封为一个小中国”的原因。30日台湾要求美国更正。《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8892890页。FRUS,1958—1960, Vol.19, pp.474475.
中国的新政策宣布后,美国于30日决定,只有当中共在双日攻击国民党补给船时,美国才为台湾提供护航,如果国民党坚持要在单日进行补给,即使他们受到攻击,美国也不护航
FRUS, 1958—1960, Vol.19, p.477.
。蒋介石虽然不愿意,但到头来还是不得不遵守中共的“条件”,只在双日给金门补给。
5. 中国对国际舆论的成功争取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不仅是一次军事和外交的较量,同时也是中美两国在争取国际舆论方面的一次较量。
在炮击金门开始后,毛泽东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希望能对国际舆论产生积极影响。8月25日,毛泽东对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现在宣传上要打外围战,等美国、蒋介石以及世界各国的动向摸清楚之后,再开始就炮打金、马问题发表评论。”他要求中国报刊的文章暂不直接联系金门打炮,而是把主要锋芒对着美国到处侵略,谴责它入侵中东,也谴责它霸占中国领土台湾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4页。。
在台湾危机引起全世界紧张关注,国际舆论对美国卷入中国内战表示反对后,毛泽东认为,由于为蒋护航,美国入侵了中国领海,中国有权自卫,但不一定马上打炮,可以先发出警告,相机行事。他说:“我们还准备另一手,通过即将在华沙恢复的中美会谈,以外交斗争配合福建前线的斗争。有武戏也有文戏。我们还有一手,就是宣传斗争。”他指示说:现在要大张旗鼓地谴责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要强调台湾及沿海岛屿是中国领土,炮打金、马是惩罚蒋军,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他还具体指出,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评论可以讲得激烈一点,当然也要适当,不要说过头话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9页。。
美国和国际舆论的反应表明,美国的干涉政策很不得人心。至9月7日,白宫收到640封公众来信,其中只有39封是支持总统防守金门的观点。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即有470封信是要求总统不要卷入这场战争。还有89封信要求让联合国讨论这一问题。这一时期盖洛普民意调查数据也表明,80%的美国公众了解台湾海峡危机的发展。其中62%反对美国防守金门、马祖,如果这意味着全面战争和使用核武器。只有28%的人支持政府的立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讽刺说,艾森豪威尔政府是要将金门变成美国的防御第一线。就连在危机第一周主张采取强硬政策的《纽约时报》,突然也改变了调子,说政府的“多米诺骨牌论”是幼稚的
Soman, “‘Whos Daddy’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Offshore Islands Crisis of 1958”.。
9月18日,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他一方面否认台海问题只涉及中国内战,另一方面又提出要实现“停火”,试图说服公众支持其政策。对此,中国领导人立即做出反应。周恩来当晚致电毛泽东说,针对美国的停火要求,中国应扩大要求美军停止挑衅和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退的活动。具体办法是:(1) 准备一个驳斥杜勒斯联大演说的外长声明;(2) 声明发表后动员各地报纸、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广泛响应;(3) 将中国的斗争策略转告苏联领导人,以便苏联和兄弟国家配合我们行动;(4) 致电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感谢他支持我们,向他解释美国的停火阴谋,说明中国解放自己领土的权利不容美国干涉。(5) 将上述内容以备忘录形式递交东欧、亚非和北欧国家政府,唤起它们注意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766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71页。
。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方案,强调了中国的方针是“主动的、攻势的、心理的”。这些行动表明,中国领导人密切注视着国际舆论,并且非常积极地注意着它的可能动向。
这一时期美国政府还试图将问题引入联合国,并且试图让中立国家出面要求中国停火。对此,9月21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锡兰、缅甸和柬埔寨外交官时指出,如果美国一定要把战争加在中国的头上,我们只能抵抗。他对印度大使指出,如果美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或者进攻中国大陆,就将导致全面战争。这些谈话增加了国际舆论对中国立场的了解,阻止了美国利用联合国、利用“停火”来扭转舆论的企图,并限制了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172176,179页。。
根据印度驻华大使的报告,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9月28在美国发表电视演说,他说蒋介石正在力图使美国卷入一场冒险战争,他预言中国将“大举报复”对中国大陆的任何进攻,在目前的联盟体系下,俄国和其他国家可能加入战争。梅农警告,沿海岛屿的危机是“极严重的”,结果可能酿成世界大战。梅农还说,对于所谓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对亚洲的安全是必要的,该地区的国家并不接受这一论点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80281页。
。梅农的话表明,中立国家反对美国的军事冒险政策。
尽管美国领导人不断努力,试图改变舆论倾向,但他们并没有成功。9月25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沿海岛屿不应当设防,美国也没有义务防御这些岛屿,“不论是对我们、对蒋介石还是对共产党人,它们都不值得打一场大战”。28日,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文章,揭露国务院收到的5000余封信件和电报中,有80%是反对政府的立场的。当时,美国新闻署的副署长沃希伯恩说道:“在金门、马祖存在着核卷入的极大风险情况下,我不相信美国公众舆论能被引导支持我们参战。”
George C. Eliades, “Once More Unto the Breach: Eisenhower, Dulles and Public Opinion During the Offshore Islands Crisis of 1958”, in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Winter 1992, pp.343367.
当10月上旬中共中央做出了暂停炮击的决定后,毛泽东再次指示宣传部门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原则,要求他们强调美国军舰云集台湾海峡是蓄意制造紧张局势,必须完全撤退。他要《人民日报》“停火”几天,准备充足弹药,一声令下就“排炮轰击”。这种“轰击”是有效果的。杜勒斯在10月10日对叶公超说,世界上存在着反对美国政策的强大舆论潮流,甚至在美国也有变化。“两三年以前,对华政策还是两党一致的事,现在已不再如此。”“我们必须对付强烈的反对,并且感到人民不想要另一场世界战争。”从这些情况看,正如一位美国史学家所说:“美国人民迫使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寻找谈判的或至少是和平的解决。”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86页;FRUS, 1958—1960, Vol.19, p.360; George C. Eliades, “Once More Unto the Breach: Eisenhower, Dulles and Public Opinion During the Offshore Islands Crisis of 1958”.
美国政府引导舆论的努力实际上是失败的。
中国政府对舆论的引导工作,同国际舆论中反对美国干涉的倾向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对此,杜勒斯自己也是承认的。在与叶公超的谈话中,杜勒斯说:共产党希望散布一种国民党当局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不和的思想,并且“正试图在美国制造一种反对蒋总统和他的政府的情绪”。在访台时,他也对蒋介石说,对台湾的“威胁”来自中共巨大的军事和宣传能力,以及自由世界舆论,这种舆论想要消除会带来全面战争风险的“这场内战”。他还和蒋介石讨论了中共的宣传对美国、欧洲及“台湾”的不同影响。伯克也说过,日本反对使用核武器的态度是“共产党鼓动的”,目的是要阻止美国使用它
FRUS, 1958—1960, Vol.19, pp.360, 415, 419, 120.。
杜勒斯承认,国共两党在国际舆论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10月16日,他对英国大使说,现在的需要是,国民党当局应该表现得更重视世界舆论。它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忽视外界的看法与发展。他说,中国在亚非国家中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一影响甚至超过了苏联。最近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影响:一些亚非国家试图让联合国来解决台湾地区的局势,但“当中共外交部长向他们在北平的代表表示了对此事的不快后,这些国家立即停止了这一努力”
FRUS, 1958—1960, Vol.19, p.408.
。把危机引入到联合国正是美国的计划,所以杜勒斯对此耿耿于怀。由此可见,在这一危机中,中国的“文戏”是唱得相当成功的。
五、结论:危机对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三方政策的影响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在10月下旬结束。从表面上看,危机之后海峡两岸军事对峙的形势依然如旧。但是,在这种表面上的维持之下,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的政策都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危机本身是各方力量互动的结果,而它的结局又对各方的政策产生了复杂的作用。
1954年,中共中央决定先解放浙、闽两省的沿海岛屿,然后再考虑解决台湾问题。这种“分两步走”的方针在第一次台海危机结束后没有改变。在1958年炮击金门之前,美国已公开地进行“两个中国”的活动。中国估计炮击后美国可能迫使国民党从金门撤军,但毛泽东在危机开始前没有将“两个中国”的问题与占领沿海岛屿问题联系起来考虑。
在危机发展过程中,毛泽东改变了“分两步走”的方针,停止封锁金门,放弃占领沿海岛屿的目标,这说明他对解决台湾问题的长期性有了新的认识,对美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活动的危害性也有了新的估计。危机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反对“两个中国”的重要性超过了占领金门、马祖的意义。毛泽东在次年4月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最初的方针是搞金门、马祖。后来看到不对头,搞金门、马祖是杜勒斯的方针,把金门、马祖送给我们,把台湾、澎湖送给他,以金、马换台、澎。我说没意见了,统统是蒋委员长的。”
石仲泉:《周恩来的卓越奉献》,第378页,注1。
在危机以后,中国开始奉行“一揽子”方针,力求在条件成熟时同时实现台、澎、金、马与祖国的统一。中国政府坚持了反对美国侵略和干涉的政策,但斗争的主要舞台开始转移到中国之外的地区。
此外,军事上的僵局也是中国改变政策的原因之一。当时,对金门的军事斗争只能做到“断而不死”,拖下去有可能拖垮国民党守军,但也可能会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10月下旬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手里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打金、马的蒋军好办,但跟手里有原子弹的美国打仗,就不是好办法。”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过,“平衡的打破优于平衡,但不要走向冒险主义”。危机中的僵局也是一种“平衡”,毛泽东不可能为两个小岛冒与美国直接对抗的风险。但是,从这一斗争的军事目的看,虽然解放军没有占领金门,但台湾当局的行动在危机后受到严重束缚,中共保护沿海地区安全的目标已基本达到。毛泽东当时说:“金门这一仗打过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他都不干涉了。”
石仲泉:《周恩来的卓越奉献》,第378页,注1:吴冷西:《忆毛主席》,第89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201页。
在这次危机中,中国不怕美国战争威胁的勇气得到了证明,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志得到了体现。世界各国人民对于美国好战的亚洲政策有了更清楚的了解,美国的反华政策进一步受到世界舆论的批评指责。从这一角度说,炮击金门的政治目的基本实现了。这场危机验证了毛泽东的“战争打不起来”的预言。
这次危机对中苏同盟造成了一定的损害。赫鲁晓夫对中国的炮击行动大为不满,在他看来,中国不仅违反了双方的同盟条约,而且使苏联陷于严重的战争风险之中。一心想同美国缓和关系的苏共领导人认为,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是危险的。赫鲁晓夫在危机中就已决定,苏联将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并要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
“艾伦·惠廷访问贾丕才记录”,见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39547页。
。苏联的这一方针使两国关系在危机后进一步恶化。这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也产生了影响,增强了中国“反对修正主义”的决心。
在这次危机中,国民党当局坚持所谓的不放弃金门“寸土尺地”的政策。因国民党自己无力守住金门,蒋介石坚持该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拖美国下水。在这个企图失败之后,蒋又以这一姿态来抵御美国压力,防止美国迫使他放弃金门。在他的坚持下,台湾当局终于顶住了高压,使美国政府内部无法就国民党从金门撤军问题形成一致意见,也使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面临较大困难。
但是,蒋介石的损失要比丢失金门更大,蒋介石最终不得不放弃了以武力“反攻大陆”的企图,对他来说,这是1949年逃台后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多年来国民党一直想借助美国的力量重新打回大陆,现在这一方针已完全失去了可行性。美国甚至公开要国民党接受“两个中国”的政策,这对国民党当局的“合法性”构成了重大威胁。虽然杜勒斯安慰蒋介石说,在发生匈牙利那样的“起义”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还会有机会,但杜勒斯也说得很清楚,在任何情况下,台湾当局“绝不能自己发动在大陆重建政权的战争”
FRUS, 1958—1960, Vol.19, p.476.。
危机以后,在美国的严厉限制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基本停止对大陆的武装挑衅行动,它在与中共的较量中越来越陷入被动,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也不断下降。而且,出于它在危机中明显暴露了将美国拖入中国内战的意图,美国舆论对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也显著减少。
这次危机对美国军事战略具有重大冲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军事战略是建立在发展和使用核武器的方针上的,该战略强调“非常规武器常规化”,试图通过核威胁和使用核武器来达到政治和军事上的目的。但是,金门危机表明,核武器在危机中的作用是有限的,美国的威慑没能阻止中国采取封锁金门的行动。在危机中,美国军事行动的方案并不是用核武器进行“大规模报复”,而是以常规武器为主,作“逐步升级”的反应。在中国停止炮击前,美国的行动并没有完全打破中国对金门的有效封锁。美军太平洋总部在危机后总结说,海军过分依赖核武器,因为已有的军事计划均设想将使用核武器。由于经费和物资都投入核武器,美国常规武器能力不足,而且缺乏使用常规武器的计划。美国历史学家A.K.索曼指出:“在这次危机以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关于核武器与常规武器没有什么不同的强词夺理的谈论结束了。”
Soman, “‘Whos Daddy’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Offshore Islands Crisis of 1958”.
美国的军事战略不得不作进一步调整,而且,美国政府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核威胁了。
艾森豪威尔政府原来一直坚持国民党军队具有某种进攻性使命,他们的理由是,如果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要求,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就会动摇,而支持蒋的反攻将有助于中共政权的崩溃。在危机中,杜勒斯不得不改变了这一他原来认定“肯定不应当改变”的政策,并且迫使蒋介石接受了不以武力反攻大陆的要求。这一变化不仅是美国对台政策的重大转折,而且表明该政策原来就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之上,它动摇了杜勒斯对华政策的可信度。有人说,这次危机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分水岭”,这一看法是相当有道理的。实际上,这次危机以后,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采取了明确的防御性姿态,而中国东南地区的安全地位因此得到了改善。
危机以后,美国政府不得不正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更多的美国人意识到,美国不承认中国的政策迟早是要变化的。为了掩人耳目,危机后杜勒斯经常谈论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经常谈论将会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其实,这正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挑衅和军事威胁政策已经遭到失败。同时,这也表明中美之间的冲突将向长期化和复杂化方向发展。
20世纪50—60年代中美关系研究述评
*
*本文原发表于由资中筠先生和陶文钊先生所编的论文集《架起理解的新桥梁——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①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韩念龙、薛谋洪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近十几年来,中美关系史的研究领域已经有新的拓展。关于20世纪50—60年代中美关系的研究同其他阶段相比开展得较迟,成果也较少。但近年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研究者们正从新的角度、以新的观点对这一敏感的时期进行探讨,这是中美关系史研究向成熟发展的重要标志。
思想解放和提倡实事求是精神是这一段中美关系史研究能够有所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近10年来中美两国的关系虽然波澜迭起,但大多数研究者能排除各种干扰,坚持科学的研究态度。此外,一批当事者回忆录的出版,通过各种渠道公开的档案资料的增多,以及中美两国学术和文化交流的发展,这些都使研究1949年后的中美关系史条件趋于成熟。两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专著的出版,为研究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基础。①
主要通过一批中青年学者的努力,已经出现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有关20世纪50—60年代中美关系史的学术成果。但从另一方面看,目前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某些重要课题的研究,还存在着不少限制因素。已有成果的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全面地回顾前一时期的研究进展,更清楚地了解已有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有待克服的困难,对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必定会有积极意义。
一、进展和成果
从朝鲜战争爆发到20世纪70年代初两国关系缓和,这一时期中美两国处于相互敌视和对抗状态,两国间的直接联系很少。但双方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都经历重大的变化,双边关系对当时的国际关系也发生过深远影响,这些都为历史学家提供了极有意义的研究空间。
1. 朝鲜战争
有关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丰富的中外文献资料,使研究者能对这一时期交战双方的政治策略、军事战略及外交联系进行较全面的探讨。在有些问题上,例如,关于中国领导人在参战前的决策,关于复杂艰巨、一波三折的谈判过程,以及美国在朝鲜战争时期的对华政策等方面,姚旭、徐焰等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纠正了国外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一些不确切看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柴成文、赵勇:《抗美援朝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姚旭:《从鸭绿江到板门店》,人民出版社,1985年;徐焰:《第一次较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张希:《彭德怀受命率师抗美援朝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第31辑;谭旌樵主编:《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在关于中国参战的战略决策方面,研究者们在中国出兵朝鲜的目的上意见一致,即认为中国出兵是在受到美国军事威胁的情况下,从保卫国家安全、支援朝鲜、保卫东方和世界和平目标出发的。中国领导人正确地估计了国际形势,从全球角度分析了美国的战略,对中国出兵后美国可能的反应也做出了大致准确的预期。
宫力:《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党史文汇》,1992年第10期;王汉鸣:《略论朝鲜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军事历史》,1984年第4期;齐学德:《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951页。
但是,也有研究者对于战争爆发前的一些事态有不同看法。郝雨凡、翟志海认为,中国事先并不清楚朝鲜方面计划,因此对战争的发生没有准备。在美国可能干预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比斯大林更为慎重。徐焰指出,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日益紧张的局势是有所了解的,虽然他们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但出于自己的体验,他们也反对阻止别国革命。斯大林根据美国未敢干涉中国革命的事实,错误地推断出美国也不会出兵干涉朝鲜。陈兼认为,做出中国不支持朝鲜军事进攻的结论还为时太早,中国领导人当时也可能低估了美国在朝鲜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
Hao Yufan and Zhai Zhihai, “Chines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 The China Quarterly, March 1990;徐焰:《出兵入朝参战决策最后确定的曲折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4期;Chen Jian,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Chinas Entry into Korean War”, Unpublished Pape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ed.by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研究也有重要进展。研究者们都指出,美国方面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坚持所谓“自愿遣返”的要求,是谈判长期僵持的症结所在,美国方面的这一无理要求造成了战争的拖延。
但是在有关谈判的具体过程方面,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涉及在谈判过程中朝中两国对“全面遣返”原则的灵活运用。《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的作者根据美国方面的材料指出,1952年5、6月间,周恩来曾经通过印度政府提出一个遣返10~11万名战俘的方案,但后来中方又否定了这一立场。徐焰在《第一次较量》一书中写道,1952年夏,中朝谈判代表团曾准备接受按一定数量进行遣返的方案,但是这一意见经中朝双方领导人协商后被否决。毛泽东认为接受此方案等于接受城下之盟。他还提到,中国方面在1951年上半年对于是否要进行谈判,随战争进程的变化在态度上有过反复。
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3》(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95298页;徐焰:《金门之战》,第284287页。
有关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美国在参战初期的战略考虑和军事目标是关注的一个焦点。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朝鲜战争刚爆发时只是一场内战,美国以反对朝鲜“侵略”为借口参与战争,是别有目的。同时他们也倾向于认为,美国最初投入这场战争时,其目的主要并不是针对中国。
一些研究者认为,美国决策者把朝鲜战争的爆发看作苏联进行全面扩张的序幕,美国担心如果中国趁机进攻台湾,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战略地位有崩溃的危险。因此,美国决心以此为契机,在远东进行“第二次划线”,并在避免同中国发生公开冲突的前提下,用武力吞并朝鲜。在中国出兵朝鲜后,美国又被迫放弃了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目标,由此美国陷进了一场“打不赢的有限战争”。这一观点强调了美国政策中的反苏性质。
肖健宁:《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剖析》,《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田金星:《论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3辑),南大—霍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合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29252页。
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在决定进行干预后最初目标是“使朝鲜半岛恢复到6月25日以前的状态”。它是在军事行动逐渐得手后才决定执行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政策的。中国参战后,美国领导人确定了在不扩大战争的前提下能打多久就打多久的方针。杜鲁门政府最后通过解除麦克阿瑟职务及国会听证会,解决了国内争论,为停战谈判找到了出路。这种观点似乎更强调美国政策中的机会主义特点。
牛军:《美国对朝鲜战争政策的演变》,《美国研究》,1991年第1期。
关于美国在朝鲜战争时期对中苏同盟的看法也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美国决策者的根本错误在于把对华政策隶属于对苏战略的需要,以反苏和反共的需要规划对华政策。但也有人认为,在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杜鲁门政府是把苏联而不是中国看成是亚洲的主要敌人。但是,随着中国在亚洲政治地位的提高,从5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在远东的遏制战略的主要目标,逐步从苏联转向了中国。美国政府这时已经了解中国独立于苏联,它公开否认这一点只是为它拒不承认中国的合法地位寻找借口。
田金星:《论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3辑,第229252页;王缉思:《1945—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后果》,
袁明和哈里·哈丁编:
《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第440470页。
2. 从日内瓦会议到日内瓦会谈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开始执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正在引起人们的兴趣。围绕着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对于从朝鲜战争结束到1955年初这一段时期的中国对美政策中的主要倾向,即究竟是实行外交缓和,还是支持革命并进行军事斗争,研究者们有一些不同见解。
贾庆国等认为,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政府采取了推动国际形势进一步缓和的对外政策,目的是加快国内经济建设步伐,完成国家的统一。因此,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了缓和方针,力争打开同美国协商解决台湾等问题的局面。中国在1954年秋炮击金门主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目的是要试探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阻止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防止台湾问题的固定化。
贾庆国:《从台湾海峡危机到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何迪:《台海危机和中国对金门、马祖政策的形成》,《美国研究》,1988年第3期。
徐焰认为,中国领导人把朝鲜、印支和台湾看作打破美国对中国威胁的三个战场。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决定加紧支援越南夺取抗法战争的胜利,同时在浙江沿海对国民党进行规模有限的打击。中国决心支持越盟尽快打败法国,争取在美国军事上直接介入印度支那之前实现停战。在印度支那停战以后,由于朝鲜半岛和越南的分裂已成定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把军事斗争的重点再度移向台湾海峡,在国际上打破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
徐焰:《五十年代中共中央在东南沿海斗争中的战略方针》,《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2期;《金门之战,1949—1959》,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175页。
陈晓鲁的观点是,中国外交是二者兼顾的。他指出,朝鲜停战后中国领导人更重视外交斗争,他们认为外交既是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手段,又是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维护和平的根本方法。在日内瓦等地进行外交斗争的同时,中国还在台湾海峡针对美蒋的挑衅采取了军事行动。
陈晓鲁:《1949—1959年的中国对美政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第229246页。
研究者们认为,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后,中国已经意识到,军事行动有其局限性,如果要打破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实现解放台湾的愿望,就必须在外交方面采取更灵活的姿态。中国在万隆会议上主动提出愿和美国谈判,就是缓和方针的新体现。
较普遍的意见是,这一时期对美国的和平共处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成果,其主要原因是美国执行顽固的反华政策。由于在朝鲜和印支的失败,美国政府更加敌视中国。美国不仅试图破坏日内瓦会议,而且企图阻止万隆会议的召开,在这一计谋失败后又试图控制会议的方向,尽可能削弱中国对亚非国家的影响。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艾森豪威尔政府最后才不得不对周恩来的呼吁做出姿态,同意和中国进行双边会谈。
Zhang Qiang,“China and Geneva Conference”, The China Quarterly, March 1992; 蔡佳禾:《从积极进攻到双重遏制——论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未发表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历史系);任东来:《美国对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反应》,沈宗美编:《理解与沟通:中美文化研究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研究表明,尽管中国当时真诚希望通过大使级会谈缓和亚洲地区国际形势,并在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采取了一些主动、灵活的步骤,但对美国政府来说,接受这一会谈只是为了摆脱危机,欺骗国际舆论、避免同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因此杜勒斯严格限制美方代表的授权,规定谈判不得涉及外交承认,不得涉及国民党的“权利”。美国还试图利用所谓“放弃使用武力”问题把会谈失败的责任推给中国。在这种政策下,中美大使级会谈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中国国内情况的演变、国际共运中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对美国政府坚持敌视政策的愤慨,在日内瓦会谈的后期中国也开始对美国采取强硬的立场。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对美政策趋向强硬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的与美国有关,有的则没有直接关系。
陈煌:《日内瓦大使级会谈的起源与进程研究》(未发表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历史系);前引贾庆国文。
3. 5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内容
近年来,随着美国外交档案的逐步开放,中国学者加强了对于50年代中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
关于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有的研究者认为,杜勒斯特别发展了一种“军事遏制政策”,美国在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海峡等地多次运用“战争边缘术”,以积极行动遏制中国,并通过集体安全体系形成对中国的军事包围。这一政策无论从过程和结局看都是不成功的。在杜勒斯任职后期,由于中国的强大,他不得不采取一定的现实主义政策和灵活态度,从“积极遏制”转向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
陆航:《杜勒斯与5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
第二种观点是,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是在杜勒斯的“和平变革”、“和平取胜”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确立的。该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分裂中国领土台湾,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一政策的目的是要维护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利益和霸权地位。美国这一政策严重破坏了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危及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霍世亮:《论5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
第三种观点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政策是以改变中共政权方向或推翻这一政权、打击中国国际威望和分裂中苏同盟为三项基本目标。由于美国政府预先就排除了同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以及当时美国亚洲政策的需要,艾森豪威尔政府实际上制定了一项比过去更为僵硬和保守的对华政策。美国决策者认为,只有明确表示反共反华决心,才能稳住亚洲局势。较弱的表示将在亚洲产生涣散人心的影响,因此必须避免。
前引蔡佳禾未发表博士学位论文,《从积极进攻到双重遏制——论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贾庆国:《5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贸易政策问题上的讨论》,《美国研究》,1990年第2期。
上述三种观点并不相互排斥,研究者们在分析美国国内政治的消极影响时,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政策中的军事性行动、意识形态和政治,以及地区性特点,各有侧重。从而也表现了他们对这一政策的主要倾向具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研究者探讨了5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王缉思认为,这一政策是从朝鲜战争爆发到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而逐渐形成的。美国之所以阻挠中国统一,既有把台湾看作遏制共产主义的前沿阵地这种军事战略考虑,也有担心中国一旦统一,美国在亚太地区组织反共亲美联盟计划无法实现的政治考虑。此外还有阻止东南亚华人转向中国及国内政治等因素。他指出美国无法公开推行这一政策是因为中国的坚决的斗争,以及国民党当局在公开和秘密场合都坚决抵制“两个中国”的方针。
王缉思:《论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起源》,《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第31933页。
4.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近年来,1958年的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也得到了众多的关注,鉴于美台关系的研究另由专题介绍,这里只介绍这一危机中有关中美两方关系的研究。
何迪强调了当时国际形势对中国决策者的影响。美国在台湾地区的所作所为,中苏两国就如何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发生的争论,以及中国领导人试图在全球性问题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等因素,使得中国的这一决策带有更多的国际色彩。他指出,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对美国缓和和让步是否明智。中国领导人这时对美国远东战略的看法有了变化,毛泽东得出了美国实际能力有限,不得不对社会主义阵营采取守势的结论。
何迪在分析中国的决策过程时指出,中方采取军事行动的原来目的就是要争取收复金、马两岛。但随着美蒋矛盾的激化,毛泽东改变了政策,他决定把两岛留在国民党手中,这一变化有助于维护国家统一。
何迪:《台海危机和中国对金门、马祖政策的形成》,《美国研究》,1988年第3期;迟爱萍:《毛泽东对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战略指导》(该文也表明,从这一时期起毛泽东对国际战略的看法常常发生变化),《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徐焰的看法是,炮击金门是中国要以军事行动促使台湾问题得到解决。他的分析还提到了中国国内形势对这一决策的影响。他指出,在“大跃进”形势下毛泽东试图以革命战争年代中那种对敌斗争的激情和组织形式动员全民,针对美国实行的“战争边缘政策”,准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自身”。徐焰分析1958年夏毛泽东的一种想法,即“紧张局势除去有害的一面外,还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斗争,以促进经济建设的大跃进”。徐焰在研究中指出,经济建设有不同于战争的特殊规律,无视这种规律而照搬过去战争时期的模式只能陷入主观主义,并留下值得惋惜的历史教训。
与何迪不同的是,徐焰在分析这一决策的发展过程时,强调了毛泽东的“走一步,看一步”方针,认为毛泽东想要根据形势的发展来决定是否夺取金门。
徐焰:《金门之战》,第221223页;徐焰:《五十年代中共中央在东南沿海斗争中的战略方针》,《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2期;
其他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在这一次危机中采取的是主动性进攻,但动机主要是政治性的。这一观点的积极意义是超越了过去简单的“惩罚”说。他们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在对美政策上改变了原来谋求改善两国关系和争取通过高层谈判解决分歧的做法,转而对美国采取强硬态度。在危机后期,中方最后提出了台湾问题和两国关系改善相联系的“一揽子”政策。然而,研究者们一般都回避了对这种“一揽子”政策做出评价。
范希周:《1958年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分析》,《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4期;郑永平、吴丹虹:《试析美国处理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政策》,《世界历史》,1990年第1期。
5. 60年代的中美关系
同关于50年代的研究相比,有关60年代中美关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资料缺少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基本原因。尽管如此,一些研究者还是大胆投入了这一段历史的研究。这些著作虽然还没有全面地论及中美关系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与变化,但是它们为今后研究提供了有用的框架。
资中筠以“缓慢的解冻”为题,分析了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美国对华舆论方面的转变过程。资中筠认为,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中苏分歧的日益明显及中国开始试制核武器等因素是这一时期美国重新审查对华政策的背景。围绕上述背景以及中国对外政策的意图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得失等问题,美国学界、新闻界和国会都出现了要求松动对华政策的意见,并最终在60年代中期形成了“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构想。她的分析不仅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产生变化的复杂背景,而且也有助于了解美国行政部门、权势集团和舆论界在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互动作用。
但是,美国发生的这种气氛变化,在中国并没有相应出现。资中筠认为,除了当时美国还坚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观点,以及试图把中国拉入核裁军谈判中去等因素外,中国当时也存在着日益拔高的支持“世界革命”的调子,并有一种认为美国的自由派比保守派更危险的看法。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后来还是逐渐注意到了美国的这种变化,以及中美关系松动的可能性。
资中筠:《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
顾宁的研究注意到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中出现的变化的迹象,以及该政策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肯尼迪政府仍然积极推行“遏制并孤立”中国的政策,在中国进入联合国等问题上,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另一方面,肯尼迪已意识到,“中国的存在和稳定是不容置疑的”,美国必须调整对华政策。顾宁认为,美国国内强大的保守势力,以及肯尼迪对苏联政策的优先考虑,还有东南亚的局势等因素,阻止了肯尼迪把对华政策调整到一种“遏制但不孤立”的方向上来。
顾宁:《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
何迪在分析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美国看法变化时指出,毛认为美国在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和平演变,并加紧争夺中间地带。毛泽东提出了“绞索”政策,即支持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他试图以局部战争来抑制全面战争。1962年以后,毛还警惕美国和苏联有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的可能性。李可、郝生章的研究披露了60年代中期在中国南方进行的以美国为假想敌的对空防御作战演习,以及这一时期中国防御政策的某些变化。
何迪:《毛泽东的美国观》,《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54269页;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6. 中美两国长期对抗的原因
在讨论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对抗的原因时,研究者们都认为,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是造成对抗的主要原因。但在分析这一对抗长期性和深层原因时,研究者们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王缉思认为这种对抗是中美两国利益与民族意志较量的结果,并有其必然性。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革命利益和国家利益同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计划已经发展成对抗性矛盾。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觉醒和革命精神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美国的实力和武力扩张的倾向也相对处于巅峰状态。因此,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美两国也可能在中国南疆附近发生军事冲突。
前引田金星:《论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新的视野——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王缉思:《1945—1955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后果》,《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
霍世亮和陆航认为,两国的对抗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因素造成的。美国政府的决策者有着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他们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具有普遍意义,应在全世界推广。加上它谋取世界霸权地位的野心,和不甘心失去它过去在中国的独占地位,美国政府便把分裂中国的政策作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长期目标,从而为正常的国家关系设置了严重障碍。他们既不理解,也不愿接受中国反抗列强干涉和侵略的立场,低估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决心。
陆航:《杜勒斯与5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霍世亮:《论5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
蔡佳禾把这一对抗同美国东亚政策的全局相联系,他认为在二次大战后,各种政治思想交织在一起影响着亚洲地区的社会发展。在中国和越南等地,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结合导致了革命的胜利。到50年代中期,这种结合又出现了另一种可能的形势,即中国和一些民族主义中立国家建立密切的经济政治联系,形成较稳定的和平共处局面。这种前景被认为会从总体上削弱西方在东亚的利益,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美国要防止亚洲国家脱离它的控制,维护它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就必须执行同中国对抗的政策,用紧张和对抗阻止中立主义的影响及其力量在亚洲的进一步蔓延。
前引蔡佳禾博士学位论文;贾庆国:《5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贸易政策问题上的讨论》,《美国研究》,1990年第2期。
二、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同其他阶段的中美关系研究相比,50—60年代的研究是较为困难的,尽管已经获得了初步的进展,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资料严重缺乏是面临的最大问题。目前中国的外交档案尚未解密,即使有一些可以利用的档案,但对大部分研究者也是可望而不可即。而美俄等国这一时期的外交档案,包括与中国有关的档案正在加快开放,供研究者利用。这样,新的重大研究成果就难免是由这些国家的史学家根据他们的材料而完成的,从而在国际学术界造成先入为主的效果。能否依据中国档案对重大历史问题提出权威和科学的论点,这是从事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中国史学家面对的一种挑战。历史学家必须继续向有关部门呼吁,使更多的历史档案供研究使用。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发掘各种历史资料,脚踏实地地推动研究进一步发展。
葛罗米柯在回忆录中提到,1958年金门危机时毛泽东同他进行过谈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对其所述加以澄清,否认毛泽东当时说过可把美军放入中国,再由苏联出兵围歼的话。《永志不忘——葛罗米柯回忆录》,伊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对外关系史研究一度处于较为滞后的状态,这一问题当然也存在于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中。总的说来,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指导思想有关,如把历史上的政策同国家威望、决策者的形象、当前的政策过于密切和不恰当地联系起来,这就很难全面地、辩证地看待这一时期的历史,突破一些过时的观点。中国对外政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明确定论,这是我们开展这方面研究的指南,而不应成为发扬实事求是精神的阻碍。中国对外政策也有许多深刻的教训有待总结,文过饰非不仅有悖于学术精神,而且对维护国家的形象也没有真正的益处。
目前,某些研究还不能超越宣传的模式,对于对美政策中可能有过的问题或失误,常常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例如,对于中国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反美统一战线政策问题,一些外交史著作就讳莫如深,这就很难了解这一时期对美政策的全貌,这种情况表明,进一步解放思想、强调求实求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执行了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无疑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但这个事实无须研究者讳言,中国在对美外交上作过妥协让步。例如,在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中,几乎没有人承认中朝方面在1953年3月下旬做出了重大让步,即实际上放弃了“全部遣返”的主张。有的学者提出中国的这一行动是给美国“下台阶”。这种解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美国并没有放弃原来在战俘问题上的主张,当时,可以不承认这是让步,但历史学家不能在几十年后还停留在当事人的地位上,理解尊重历史条件和坚持科学的批判精神这两者是可以一致起来的。
相反的一种情况是,尚未弄清楚历史事实,但由于某种需要就从主观推测得出结论,这就难免以讹传讹。例如,一些文章在谈及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时,把它看作美国50年代对华政策的核心。当时美国实行的政策是对中国进行遏制、封锁和孤立。关于和平演变中国的言论,实际上反映的是决策者的一种无奈情绪和模糊的预期。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这时对于如何才能使中国发生变化尚有很大的分歧。因此,认为这种愿望已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是难以成立的。
历史研究的主要功效应是澄清历史事实,总结经验教训,为后人“以史为鉴”提供可靠的依据。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研究应该经得起科学精神的批判。
方法论问题对于这一段时期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也许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地区性特点显著加强,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总是从亚洲甚至全球角度出发的。中国的对美政策从50年代后期起也越来越显著地具有地区性特点。但是,目前的研究往往只从双边问题看待两国关系,忽视这种关系同整个亚洲地区国际关系的相互影响。例如,过于强调台湾问题对1958年以后的中美关系的影响,但对于中美在越南和东南亚的对抗却没有给予充分重视。
此外,现有的研究对中美双方受对方政策变化的影响还缺乏分析,而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双方政策的互动作用可能是非常大的。例如,在50年代后期,中美两国都可能因对方的态度而变得更不愿意妥协。此外,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关注较多,但对于有关政策在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的变化却关注较少。实际上,后者或许更能清楚地说明这些政策的实质。因此,系统研究的方法应被更多地引入,以便尽快提高关于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水平。方法的陈旧也限制了课题的选择和资料的使用,在这些方面也还存在着很大的改进余地。一些研究中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值得忧虑。对50—6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将其归纳为一贯敌视中国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阶段,美国敌视中国的理由不全一样,表现也不一样,后果更不一样。现有的某些研究却存在着内容重复,满足于简单定性的缺陷,从而使研究缺乏应有的理性和深度,文章读来如同当年的时评。有些研究过于强调中国方面行为的合理性,以致前因与后果,前提与结论不能保持一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论证中的逻辑问题。
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研究还受到了来自“纪实文学”的挑战,一般说来,历史文学作品是在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但是近年来,一些作者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发表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也透露了一些新的史实,但由于其文学的形式而无法进行核实。然而,这一挑战所带来的真正的问题是,由于作者可能有意无意地歪曲了历史,从而有可能对读者形成某些误导。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纪实文学”作品可能还会增加,历史研究者应加强对有关课题的研究,以真实客观的研究成果作为应战。
三、对今后的研究方向的意见
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基本性质发生过多次变化,双方有过“特殊关系”,也有过战略伙伴关系,在那些阶段中,尽管两国之间有过各种矛盾和冲突,但双方的合作总占主导地位。像50—60年代这种强烈的敌对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从总体看,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双边关系的研究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在澄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找出这种对抗的原因和条件,分析对抗给两国关系和双方利益带来的后果,解释对抗缓解的原因和过程,这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一定具有借鉴的作用。
严格地说,关于50—60年代中美关系的主要线索还没有理清楚,大量的课题还有待去做,而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国外正在不断涌现。中国的史学家应责无旁贷地和更紧迫地投入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去,对一些重大国际关系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
有必要加强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后期中国对美政策的研究。虽然近年来研究者对中国外交决策者的国际战略思想作了有益的探索,为深入了解这一时期对美政策变化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帮助,但目前对于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主线仍难以做出全面的解释,对许多重要问题还缺乏基本的了解。如1957年以后中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对美政策?反美统一战线政策在60年代中期的中国外交中占据什么地位?中国从什么时候起认为美国的威胁小于苏联?60年代中期,中国的军事防御战略重点有过由南向北转移的重大调整,鉴于此时越南战争正进入高潮,中国这种调整的条件从何而来?此时中美之间是否有过重大的外交动作?等等。
本阶段国际关系领域中发生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是中苏同盟的分裂。美国外交史学中的后修正学派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中苏同盟破裂的重要因素。中苏关系的恶化有多种原因,但这种关系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发生剧变应该说是异乎寻常的。中国的国际关系史学现在还没有研究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的中、美、苏三国的互动关系。弄清楚这一问题对于认识当时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有很大意义。
对于美国50年代试图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想法,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者应该进行深入的探讨。这一研究应当结合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客观估计这种企图在当时美国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对其后果做出解释。同时也总结中国当年回应这一企图的经验教训。
关于60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研究的重点应放在这一政策与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两者的联系上面。应进一步研究老挝、越南、印度尼西亚等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坚持50年代对华政策的原因,以及这一时期美国国会、舆论界和学术界对对华政策的影响能力和方式。
双边关系中还有一些重要问题也应当引起重视,如美国这一时期对我国西藏地区的分裂干涉活动、支持国民党残余力量对云南渗透袭扰活动等。研究这些课题对于了解美国对华政策全貌,维护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都有一定意义。
50—60年代的中美关系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全部消失。但中美两国是亚太地区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它们的双边关系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两国的利益和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历史做出真实可信的解释,将有助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这是形成两国更加稳定、更加成熟的关系的基础。
肯尼迪政府与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
*
*本文原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从50年代后期起,西方认为中国和印度两国在发展模式与速度方面的竞争具有重大的意义,关系到东西方冷战的全局。肯尼迪政府认为,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可以使印度放弃中立主义政策,成为西方冷战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尽管美国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它的这一目的却未能实现。关于肯尼迪政府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扮演的角色,现有的研究大都关注美国提供援助等行动,对其动机还缺乏分析,而关于肯尼迪政府对印政策失败的原因,则缺乏深层次的论证,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
有关60年代美印关系的史学著作已有很多,历史学家大都认为,肯尼迪非常重视印度在冷战中的作用。托马斯·帕特森认为肯尼迪对中立主义的态度是摇摆的,他想要打败中立主义,使中立国家加入美国一边。(Thomas G. Paterson, “John F.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and Global Crisis,” in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1—1963, ed. by T. G. Thoma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南亚地区的史学家普遍认为,尽管肯尼迪对印度给予高度关注,但美印关系不如艾森豪威尔时代。(Garry R. Hess, “Global Expansion and Regional Balance, The Emerging Scholarship on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Pakistan,” Pacific History Review, May 1987, pp.259295)霍夫曼的研究是关于中印冲突的重要著作,但他关于印度担心美国“不可靠”的说法过于简单。(Steven A. Hoffman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1990)丹尼斯·库克斯认为,阻碍肯尼迪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立。这一看法过高估计了巴基斯坦的独立性。(Dennis Kux, India and United States: Estranged Democracies, 1945—1991,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2) M.查里注意到了美苏关系的背景,但他没有深入分析美国全球冷战政策与亚洲政策的矛盾。(M. Srinivas Chary, The Eagle and the Peacock, U. S. Foreign Policy toward India since Independence,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95)罗伯特·麦克马洪的书是研究美国南亚政策的最重要著作之一。他认为美国的错误在于要印度放弃中立,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Robert J. McMahon,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and Pakist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事实上,肯尼迪政府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角色并不局限于提供军事援助。美国积极支持印度对中国采取“前进政策”,但它对中印冲突的后果严重估计不足。南亚国际关系的互动方式非常复杂,印巴对立并不是肯尼迪政府在南亚地区失败的主要原因。迄今为止,英国和苏联因素还没有受到研究者的充分关注,正是这些因素使肯尼迪的南亚政策前后不一、逻辑混乱。
一、中印边界冲突前美国对印政策的变化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将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拉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向它们提供大量军事援助。此时,印度的对外政策以中立主义为基本原则,试图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基本平衡,防止冷战对其利益产生消极影响。印度对巴基斯坦加入西方同盟体系极为不满,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威胁了亚洲和平。而美国共和党政府对印度的中立主义立场也非常反感。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认为中立主义是“不道德”的政策,国会中的保守势力不愿意向印度提供任何援助。
(一) 共和党政府对印度重要性的新认识
1954年,中印两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边关系有所改善。1955年,苏联开始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印苏关系也有明显发展。美国对印度外交的新动向深为不安。1955年11月,中央情报局指出,苏联在东南亚、南亚和中东的活动是要扩大共产主义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对苏联工业化成果印象深刻,他们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就,而且这一制度也能有效推动他们自己国家的工业化。杜勒斯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的竞争舞台正在变化,美国与自由世界必须准备应付更为严峻的苏联经济竞争。”总统艾森豪威尔指出,如果印度与苏联结盟,这对美国来说将是一场政治、战略和心理上的灾难
Robert J. McMahon,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 pp.219221.。
美国开始关注如何才能赢得这场竞争。1956年,美国驻印大使约翰·库珀(John S. Cooper)说,苏联正在挑战西方,争取印度的友谊。印度认为美国的态度是冷淡、摇摆和不一致的。除非美国政府很快改变不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的政策,否则苏联就会填补这一真空。艾森豪威尔说,经济援助对西方来说“是一种最廉价的保险”,美国过去对印度关注不够,政府应改变只向军事盟国提供经济援助的方针,加强对印度的援助。在他看来,让印度这样的大国保持一种倾向美国的中立,对西方是很有利的
Department of States, U.S.A.,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 1955—1957, Vol.8, pp.298300; Vol.10, p.37.
。1956年8月,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在今后三年中,向印度提供价值3.6亿美元的粮食援助。11月,印度总理尼赫鲁第二次访问美国,艾森豪威尔同他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尼赫鲁不仅批评苏联在匈牙利的镇压行动,而且还批评中国的西藏政策,印度对外政策开始右转。由于农业减产、过高的国防支出以及工业原料和设备价格的上涨,印度在1957年陷入经济危机。西方的经济援助对印度来说已非常重要。
1957年,美国政府通过了NSC5703号文件。该文件认为,苏联正在南亚地区开展外交和经济攻势,印度是苏联的主要目标。美国的对印政策正面临着困境,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与美国的立场经常发生冲突。如果由于美国的经济援助而使印度的力量得到加强,印度可能成为中立主义更有力的代言人,而中立主义是与美国的利益相冲突的。但是,一个软弱和脆弱的印度最终可能比一个稳定与有影响的印度有更大的风险,“一个强大的印度在亚洲背景下可能是替代共产主义的成功典范”。这个文件表明,美国准备调整对印政策,重点是要利用印度来削弱中国的影响。为此,政府还提议建立7.5亿美元的发展基金
FRUS, 1955—1957, Vol.8, pp.2943; Burton Kaufman, Trade and Aid, Eisenhowe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53—1961,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04111.。
但政府面临着两方面的阻力。一方面,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可能改变反对中立主义的立场,国会更不愿意为中立主义国家提供援助,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威廉·诺兰(William Knowland)说:“如果世界得到一种印象,我们正在奖励中立主义,那将是非常糟糕的。”艾森豪威尔自己也很犹豫,他说如果美国真要利用印度来平衡中国,美国“可能会在这一过程中破产”。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强烈反对美国援助印度。巴基斯坦认为,美国援助印度肯定会损害作为盟国的巴基斯坦的利益。如果美国一定要这样做,那就必须以印度同意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作为条件
Robert J. McMahon,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 pp.223, 240, 260.。
11月,杜勒斯报告说,金融危机可能使印度的五年计划根本无法完成。在最近的选举中印共在经济衰退的喀拉拉邦获得了政权,印共的权力还可能扩展到更重要的孟加拉邦。杜勒斯说,这可能导致进一步的连锁反应,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可能泛滥,动乱使共产党人在整个南亚次大陆夺取权力的机会大为增加。1958年3月,美国宣布为印度的五年计划提供7500万美元的发展援助。8月,在美国的压力下,美、英、德、日等国组成了多国银行团,准备在紧急情况下向印度提供3.5亿美元的金融援助
FRUS, 1958—1960, Vol.15, pp.415421.。
自1947年以后,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一直紧张对立。美国认为这不仅浪费了西方的援助,而且不利于西方的冷战。1959年春,由于印度向从事武装叛乱的达赖集团提供帮助,中印关系开始紧张起来。4月底,在讨论西藏局势时艾森豪威尔说,“现在的形势会促进印巴两国更好的相互理解”,美国应积极促进双方和解。8月,中印两国在边界地区发生了第一次流血冲突。表面上,美国宣布不对争议地区的归属表示意见。私下里,它试图利用这一形势。12月,艾森豪威尔在新德里问尼赫鲁是否愿意同巴基斯坦一起从事反华的“共同事业”。尼赫鲁婉拒了这个建议,表示只希望在印度对付中国时,巴基斯坦不会在印度背后捅刀子
FRUS, 1958—1960, Vol.15, pp.166, 195196, 529; FRUS, 1961—1963, Vol.22, p.334; H. W. Brands, The Specter of Neutr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Third World, 1947—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38.。
20世纪50年代后期,艾森豪威尔政府虽然改变了对印度的敌视,但是美国影响印度的能力却很有限。在政治上,敌视中立主义的政策使它很难吸引亚洲不结盟国家靠拢西方。在经济上,吝于提供援助导致美国的影响力持续下降。
(二) 肯尼迪政府的南亚新政策
在1960年大选中,民主党人肯尼迪以微弱的多数当选。早在担任参议员期间,肯尼迪就强调要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与落后,他批评共和党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保守、软弱和没有主动性。在就职之前,肯尼迪已组织专家研究增加对印援助问题。在他看来,中印之间的竞争会对美国的安全和地位产生实质性影响。如果印度经济不能从停滞转向增长,不能表现出至少与中国同样的能力,“共产党人就会兵不血刃地赢得一场最大的胜利”。民主党资深政治家、外交家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今后是否会追随西方,他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正在同人口最多的专制国家进行殊死竞争”,他们中获胜的一方将成为“觉醒的亚洲人民的榜样”
McMahon,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 pp.259262.
。与其前任相比,肯尼迪政府也从冷战视角看待中印两国的竞争,但新政府更强调通过行动改变现状,更希望在南亚地区打赢冷战。
1961年3月,哈里曼以无所任大使身份访印,了解尼赫鲁对于亚洲事务的看法。哈里曼报告说,尼赫鲁对中国的“侵略态度”非常不安,相信“对世界的危险来自北京而不是莫斯科”。尼赫鲁认为苏联用武力传播共产主义的热情已经消退,莫斯科对中国的好斗政策感到担心,“中俄间的历史性冲突迟早会削弱两国现有的同盟关系”。尼赫鲁说,中国正处于“侵略意向的高峰,形势是危险的”。哈里曼表示完全同意尼赫鲁的看法,美国期待两国在东南亚事务上进行合作。
5月,副总统林登·约翰逊访问印度。约翰逊在报告中说,印度对美国新政府已有“良好的印象”。美国不应利用这种印象“使印度加入我们的范围,这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但美国可用它来加强当前的美印关系。约翰逊建议美国帮助印度实现军事现代化,敦促印巴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使印度可以把军队抽调出来威慑中国,而不是同巴基斯坦相互对峙
FRUS, 1961—1963, Vol.19, pp.3133; Dennis Kux,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190.。
副国务卿鲍尔斯(Chester Bowles)认为,美国“在亚洲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存在”。美国必须促使印度认识到,在对付这一危险时美国力量是有限的,因此印度必须采取主动行动以保证亚洲的安全。8月,鲍尔斯访问印度。他在同尼赫鲁的会谈中就印度支那问题、柏林危机、刚果危机及中国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鲍尔斯说,中国会在东南亚和南亚进行军事扩张,并暗示美国可能以军事力量解决东南亚问题。鲍尔斯还试探印度对于组织一个针对中国的“亚洲力量平衡关系”的态度
FRUS, 1961—1963, Vol.19, p.83.。
经过一番摸底,肯尼迪政府为南亚政策的调整定下了方向:美国将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印度的不结盟立场,以此换取印度加强亲美的倾向,促使印度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伙伴。美国还决心大规模地增加对印援助,防止印度在经济上进一步依靠苏联。此外,美国还希望印度能在其他国际问题上与西方配合,支持美国的立场。总之,在肯尼迪政府的全球战略中,印度已经具有一种“特殊的突出地位”
John K.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 Memoirs, New York: Ballantine Press, 1981, p.406; Gary R. Hess, “Accommodation amid Discord,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and the Third World,” Diplomatic History, Winter 1992, pp.122.。
肯尼迪政府还准备调整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它认为“阿尤布汗(Mohammed Ayub Khan)总统的对外政策很可能是在亲西方的框架中寻求更大的独立性”。因此,美国将不再增加对巴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防印巴两国进一步陷于军备竞赛,“毁掉美国的援助计划”。新政府打算拉开与巴基斯坦的距离,使今后的对印政策少受巴基斯坦的牵制。
1961年4月,国务院提议,为支持印度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今后两年美国通过多国银行团向印度提供10亿美元援助。6月,多国银行团宣布,两年内将向印度提供总计为20亿美元的援助。美国还承诺5年内向印度提供13亿美元的剩余食品援助。1962年初,美国又决定向印度提供500万美元的发展援助
FRUS, 1961—1963, Vol.19, pp.63, 190, 244345, 3536, 5152.。
尽管美国的巨额援助得到印方的高度评价,但美印的蜜月期并不长。1961年11月,尼赫鲁再次访问美国。肯尼迪原本对这次访问寄予很大希望,他认为自己能与尼赫鲁建立密切的私人信任关系。但他在会谈中发现,美印双方在解决发展中国家贫穷的迫切性、共产主义影响扩大的意义、克什米尔等问题上有很深的分歧。此外,印度在越南和东南亚问题上也不愿追随美国的方针。肯尼迪后来失望地说,与尼赫鲁的会谈是“他遇到过的最糟糕的国事访问”
Dennis Kux,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186; FRUS, 1961—1963, Vol.19, pp.128135, 139142.。
一个月后,印度不顾美国的一再阻拦,使用武力夺取了葡萄牙控制下的果阿地区。美国指责印度以武力解决国际问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发表讲话谴责印度说:联合国不能饶恕在这一事例上使用武力,因为这会为在其他冲突中使用武力铺平道路。肯尼迪也嘲讽说,印度“15年一直进行道德说教……现在说教者在走出妓院时却被逮个正着”
果阿位于印度西海岸,面积约3700平方公里。16世纪初期被葡萄牙殖民主义势力侵占。1961年印度政
府用武力强行收回这一地区。Dennis Kux,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198.
。这一时期肯尼迪政府还希望调解印巴冲突,但是尼赫鲁拒绝了美国的建议。美印两国的种种分歧表明,除了反华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共同点非常有限。
二、边界冲突时期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和援助
1961年春季,印度政府决定进一步推行“前进政策”。印度的目的是,在边界地区将印方的军事哨所不断向中国实际控制线推进,甚至推进到中方哨所的后面,以武力迫使中国接受印度划定的边界。尼赫鲁认为,印度的行动不会遭到中国的反击。一位印度历史学家指出:“根据不同的情报和外交报告,他使自己相信,中国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已越来越紧张,国内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局面。这些因素使中国不能对印度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Harish Kapur, Indias Foreign Policy, 1947—1992: Shadows and Substance, New Delhi: Saye Publication, 1994, pp.2526.
(一) 美国对印度军事冒险政策的怂恿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美国决策层自作聪明地以为中共可能接近于垮台。1962年1月,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必须小心地不过分强调中共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关键问题是力量在哪里。例如,比较中国在其他地区的力量,它在印度北部边境地区的力量就相当少”。他要求研究20世纪中国政权交替时的各种情况:什么情况下中国政府会失去“天命”?中国是否可能重新发生军阀混战和割据?等等。5月底,美国最高级别的《国家情报估计》说:“印度试图迫使中国从克什米尔的拉达克(中印边界西段)前沿阵地后退,这可能会导致边界冲突,但形势不利于发生任何军事上的升级。”显然,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问题是这种估计还间接地鼓动了印度政府。中印边界战争发生以后,美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思(John K. Galbraith)在一封给肯尼迪的信中承认,“印度人总是低估中国的意图。我们的估计可能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了他们”。
FRUS, 1961—1963, Vol.22, pp.176179; FRUS, 1961—1963, Vol.19, p.258;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mbassadors Journal,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Kennedy Yea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7, p.413.
肯尼迪政府知道,印度在中印边界地区采取的是军事冒险政策。但美国从不反对印度对中国使用武力。1961年,美国军方认为应尽快向印度出售军事装备,“对于印度加强自己以对付中共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和侵略倾向的努力,美国是表示同情的。美国准备考虑印度得到某些具有双重用途的军事装备的要求,如运输机、高纬度地区使用的直升机、雷达、舟桥和工程装备等。如果印方愿意,美国准备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优惠地提供这些装备”。
FRUS, 1961—1963, Vol.19, pp.9798, p.150.
印度此时最想得到美国的F104超音速喷气战斗机和“响尾蛇”导弹,但由于巴基斯坦的强烈反对,美国只能拒绝印度的要求。印度于是转向苏联求购同一档次的米格21战斗机。美国对印度这一动向非常不满,它与英国一起竭力阻止印度购买苏制飞机。美国建议印度以优惠条件购买美国的C130运输机,并以美国补贴的方式购买英国战斗机。但印度对英制飞机却没有兴趣。
1962年3月,副国务卿鲍尔斯再次去印度评估形势。在同印军参谋局长、积极鼓吹“前进政策”的考尔(B. M. Kaul)将军会谈时,考尔问鲍尔斯,在中国公开入侵的情况下,美国是否会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鲍尔斯回答说他个人认为美国会这样做。考尔要求美国派高级军官到印度秘密访问,通过双方协商为上述情况准备一个应急计划。显然,为了达到以武力强占中国领土的目的,印度军方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鲍尔斯的回答是误导性的。他可能使考尔得到这样的印象,即美国的保证将使印度的军事计划万无一失。鲍尔斯报告说,印度领导人对中国的“威胁”有深刻的理解,印度已解决了一些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它对抗中国决心已大为增强。他要求华盛顿认真考虑考尔的要求。
FRUS, 1961—1963, Vol.19, pp.274, 219220.
1962年夏,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8月10日,尼赫鲁对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思说,印度希望同中国谈判,谈判可能在9月后进行,但又暗示边境地区可能随时会发生交战。加尔布雷思向华盛顿报告说,尼赫鲁并不预期谈判会有结果。9月上旬,在东段边界的朵拉地区双方军队发生流血冲突后,印度决定采取代号为“来克亨”的军事行动,用武力把中国军队从东段争议地区驱赶出去。10月10日,印军又在僧崇地区挑起了冲突。就连美国的情报也认为,“可能印度自己要对这一事件负责,因为印度要把中国人从印方要求的领土上赶走”。
Steven A. Hoffman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 p.130; FRUS, 1961—1963, Vol.19, pp.321, 341.
在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后,印度多次要求美国尽快出售美制装备的零配件及运输通讯装备。10月2日,印度要求紧急购买美制C119军用运输机的零配件。4日印度又提出紧急转购加拿大订货的“驯鹿”运输机。同时,印方还提出购买250台防空雷达用于中印边界地区。美国军方不仅要求政府立即批准印度所有的要求,而且还为印度提出进一步要求做了准备。
FRUS, 1961—1963, Vol.19, pp.340343.
由于印军在僧崇地区遭到沉重打击,10月12日,考尔从前线赶回新德里汇报。他对到其家中摸底的加尔布雷思说,印度打算将中国军队赶出印度的领土,但是尼赫鲁和梅农对这一任务的困难性尚未有充分的理解。他强调“只有在美国的帮助下这一任务才可能完成”。考尔说,他“已劝告政府放弃对不结盟政策的承诺,并要求美国提供援助”。他确信“由于对共产主义的厌恶”,美国肯定会欢迎印度的要求。虽然加尔布雷思说美国希望避免卷入中印冲突,但他没有反驳考尔的估计。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 p.429.
10日以后,中印危机进一步加深。18日尼赫鲁从锡兰回国,加尔布雷思立即赶到官邸同他会谈。尼赫鲁说,印度已决定要把中国人赶走,不管需要一年、五年或者是十年的时间。印度不会使用所有力量,主要是“用地面部队保持对中国的长期压力”,而且这一措施也将扩大到西段边界地区。加尔布雷思对尼赫鲁这一方针继续表示支持。
FRUS, 1961—1963, Vol.19, pp.346347.
与在果阿问题上的立场相比,美国对印度的“前进政策”显然是全力支持的。肯尼迪政府不仅从政治上鼓动印度进行军事冒险,而且为印度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实质性的援助。但是,美国对这一军事冒险政策的结果估计不足。中央情报局原来认为“印度军队的战斗效率在自由亚洲是最高的”,但战争的结果完全出乎美国的预料。加尔布雷思后来辩解说:“我们知道那(指中印边界地区)的情况如何,我们以为印度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很明显的是,实际上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FRUS, 1958—1960, Vol.15, pp.570571; Dennis Kux,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202.
其实,正是美国的怂恿使印度有恃无恐,忘乎所以。
(二) 肯尼迪政府的应急措施
10月20日,中国军队开始自卫反击作战。22日,美国国务院指责中国“侵略”,并宣布会以同情态度考虑印度的援助要求。10月26日,加尔布雷思得到授权,宣布美国承认麦克马洪线是“一条传统的、基本上被接受的国际边界,美国完全支持印度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这表明,美国可能公开干预中印边界冲突。为了减少印度的压力,国务卿腊斯克告诉巴基斯坦的阿尤布汗总统说,中国的行动威胁了整个次大陆的安全,巴基斯坦应保持边界平静,“必须避免采取增加印度困难的行动”。肯尼迪还亲自写信给阿尤布汗,要求巴方向印度做出不采取军事行动的保证。美国还迅速向印度政府提供了有关中国的军事情报,与印度建立密切的情报交换关系。
FRUS, 1961—1963, Vol.19, pp.349, 358359; Galbraith, Ambassadors Journal, pp.386395.
10月24日,印外交部长德赛(M. J. Desai)表示,印度很快会向美国提出援助要求。26日,华盛顿表示,只要印度提出要求,美国愿意用军事援助方式(无偿援助)提供武器装备。27日,印驻美大使向肯尼迪递交了尼赫鲁的信,尼在信中正式要求美国紧急提供军事装备。但是驻印度大使要求肯尼迪在回信中不要提军援问题,因为新德里还在考虑以现金购买美国武器。此时,尼赫鲁力图避免国际舆论认为他已放弃了不结盟政策。从11月3日起,美国开始向印度紧急空运武器弹药及通讯装备,美军C130大型飞机为这批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物资起飞60架次。
FRUS, 1961—1963, Vol.19, p.352, p.384.
中国开始自卫反击作战时,古巴导弹危机已经发生。为了使华盛顿能集中精力处理导弹危机,美英两国决定在伦敦建立联合工作组,研究中印边界局势的发展。工作组的另一任务是为双方的对印长期政策进行评估。11月中旬,伦敦工作组建议,在以后数月内美国及英联邦国家为印度装备5个师的军队,这笔开支大约需要1亿美元。伦敦工作组的基本设想是,在得到这一援助后,印度在目前位置上能顶住中国的进攻。印度如果要“收复”所有被“占领”的地区,它必须调动部署在印巴边境地区的2/3的军队。伦敦工作组认为,西方的最佳方案是,在提供相当数量援助的同时向印度施加压力,促使它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在此之后,西方再考虑向印度提供长期军事援助。这一方案基本反映了英国政府的意见
FRUS, 1961—1963, Vol.19, pp.385387; FRUS, 1961—1963, Vol.22, pp.322325.伦敦工作组的建议基本来自英国政府,而英国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与周恩来总理10月底同英国前议员麦克唐纳的谈话有关。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07508页。。
11月17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卡尔·凯森(Carl Kaysen)在给肯尼迪的报告中指出,伦敦工作组提出的是初步方案,提供1亿美元援助的目的并不在于让印度获得全面的军事优势,而是要为印巴解决基本分歧创造机会。下一步援助计划要等中国的军事动机及次大陆局势变得更清楚时才能提出。凯森说现在还不能确定,把印度推得更远、向它提供更多援助、使它不能按中国的条件进行谈判、不能退回中立主义立场上去是否更符合美国利益。他强调,中印“战争拖延下去有助于美国重大政策目标的实现”。原因是如出现这种局面,中立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将会下降,印巴关系可以得到改善,中国的威望与实力会受到打击。但凯森也指出,让战争拖下去的方针也有一些不确定因素。美国是否愿意承受增加支出的负担,巴基斯坦是否会成为美国的“限制性因素”,等等。
FRUS, 1961—1963, Vol.19, pp.385387.
凯森的报告表明,美国认为中印战争是一次天赐良机,但还不能断定美国要为其目标付出多大的代价。
11月14日,印度在东段边界地区发起新的军事进攻,中国不得不进行第二阶段的自卫反击作战。中国军队在战斗中迅速和全面清除了争议地区的印军据点,而且还进入传统习惯线以南作战,印军全线溃败。震惊中的尼赫鲁几乎丧失了判断大局的能力。19日,他在未同内阁磋商的情况下两次致信肯尼迪,说“局势真正令人绝望”,呼吁美国紧急向印度派遣12个中队的超音速战斗机,并提供先进的雷达和通信设备。他请求在印度空军未完成训练之前,先由美国飞行员驾驶这些飞机作战,以保卫印度的城市。这实际上是要求美国派空军到印度与中国直接交战。尼赫鲁还要求美国提供两个中队的C47中程轰炸机,由印军驾驶轰炸中国境内基地和机场。加尔布雷思也沉不住气了,他要求肯尼迪立即让航空母舰进入印度,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
FRUS, 1961—1963, Vol.19, p.397; Michael Brecher, “NonAlignment Under Stress: The West and the IndiaChina Border War,” Pacific Affairs, Vol.52, 1979—1980, pp.612630.
尽管美国已将“企业”号航母调至孟加拉湾,但肯尼迪政府对印军的迅速失败还是深感震惊。腊斯克认为,尼赫鲁在要求“美印无限制合作,以对付中国对印度的入侵”,这实际上已是要求同美国结盟。但问题是印度“并没有真正做好准备,根据这种条件面对局势”。腊斯克说,在印度没有公开澄清它的不结盟政策之前,美国不可能考虑直接参战。为了弄清尼赫鲁的想法,肯尼迪决定先让助理国务卿哈里曼赶赴新德里。同时,紧急调遣12架C130大型运输机,为印军抢运增援和物资。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 pp.437442.
11月22日哈里曼到达印度时,中国已宣布单方面停火,并宣布将把军队撤回至1959年实际控制线。中国的行动打破了美国使战争长期拖延下去的幻想,印度不得不在事实上接受了停火。
三、中印冲突与美国的南亚战略计划
(一) 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大计划”
虽然中印两国已经停火,但是美国认为它仍有机会实施伦敦工作组的建议,使印度放弃不结盟政策。哈里曼与尼赫鲁先后会谈4次,尼赫鲁表示,中国已成为印度长期的和主要的敌人,印度将尽其所能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付中国,他要求美国为此提供援助。随同哈里曼访问的国务院情报研究司司长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指出,哈里曼访印的使命是“表示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并且向中共发出威慑信号”。但美国更想知道它能为印度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印度和巴基斯坦怎样估计中国威胁的性质……他们是否愿意调整他们的敌对关系”。美国认为,“唯一有效的防御是印巴在次大陆的联合防御”。
FRUS, 1961—1963, Vol.19, pp.414417; 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ohn F. Kennedy, New York: Doubleday Co. 1967, pp.329330.
美国想知道,在与西方结盟问题上印度能走多远。
此时,英国也向印度提供了一些轻武器和弹药。为了劝说印巴妥协,保守党政府派英联邦事务部长邓肯·桑兹(Duncan Sandys)抵印施压。桑兹对印度政府表示,争议中的边界地区是一些没有价值的荒漠,印度应同意把西段地区的大部分交给中国。印度应参加西方同盟,接受西方的核保护伞。他还说,作为得到美英军事援助的最低姿态,印度必须同意与巴基斯坦重开谈判。在桑兹和哈里曼的双重压力下,尼赫鲁不情愿地同意了与巴基斯坦谈判。
Michael Brecher, “NonAlignment Under Stress: The West and the IndiaChina Border War”, Pacific Affairs, Vol.52, 1979—1980, pp.612630.
为确保印巴实现妥协,美国也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11月25日,肯尼迪指示哈里曼说,访巴时要让阿尤布汗清楚知道美国的立场,“次大陆已经成为自由世界与共产主义进行对抗的新领域,”印度已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巴基斯坦也必须这样做,承担起它与西方的联盟义务。肯尼迪威胁说:“如果巴基斯坦在我们帮助印度对抗共产党中国时进一步靠近中国,它就会损害对整个自由世界的严肃承诺”。
Robert J. McMahon, “Choosing Sides in South Asia,” in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pp.215216.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负责南亚事务的科默尔(Robert Komer)领导的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于12月提出报告说,中印冲突带来了重要的机会,它可能导致印巴两国和解,“使一个觉醒和实力加强的印度加入对红色中国的遏制”。报告强调,美国的战略利益应该是“保持高强度的中印摩擦”,同时“防止它蔓延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科默尔的报告指出,美国对印度的“过分承诺”会带来一些问题,如国会可能不予支持、可能卷入中印战争以及巴基斯坦的反对。因此,关键问题是美国怎样才能实现这个战略“大计划”(Grand Design)。美国影响事态发展和实现其计划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持续和活跃的中国威胁才能迫使”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进行妥协。但报告承认,中国已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并正在很有策略地脱离危机。报告提出了三项建议:第一,让英国和英联邦国家出面担任主要角色;第二,给印度的防空提供某种援助;第三,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要有非常巧妙的策略。
美国希望英国走在前头,但英国的态度很消极。12月13日,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写信给肯尼迪说:“一种有意义的防御,不管是多大规模,只有在被当作印巴联合防御整个次大陆的计划才会有效。”麦克米伦指出,英美的目标是要印巴双方同意联合防御南亚次大陆,但即使他们达成了妥协,这两个国家可能也没有军事和经济能力建立真正的防御。他说,必须使印巴两国缔结地区性军事同盟条约。“那样中国人就会像俄国人一样,在进行大规模进攻前三思而行,因为他们不能确定那样做是否会引起核报复。”
FRUS, 1961—1963, Vol.19, pp.430432, 437.
英国政府为提供长期军事援助定下了三个条件: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印巴建立联合防御、印度成为西方的联盟体系的成员。
12月20日美英两国在巴哈马群岛首府拿骚举行首脑会谈。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帮办邦迪(William Bundy)在会谈中说,伦敦工作组的建议是:提供6个山地师的装备,改进印军空运能力,在现有机型的范围内帮助印度提高空战能力。工作组还建议派专家去印度了解雷达和通信设备情况,英美还可以派战斗机轮驻印度,数量是4个中队。但英方在会谈中指出,提供武器是一回事,但是“让印度将其军事计划建立在指望英美提供飞机,并向中国开火的基础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邓肯·桑兹表示,即使在西方的帮助下,印度也没有能力承担它的国防建设的代价。所以经济上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让印度进入西方防御组织的保护伞之下。美国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思承认,印度建立独立的防空体系代价是昂贵的,美英提供战斗机只是一种威慑力量而不是保护力量。这个计划比较便宜,而且较易为巴基斯坦所接受。但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认为,在西方给印度大规模军事援助、克什米尔问题不能解决、中国又撤军的情况下,向印提供防空援助对巴基斯坦会有灾难性后果。
麦克米伦似乎比美国人更敌视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他说印度在过去10多年中一直攻击西方,大肆宣扬不结盟的好处。他强调要考虑巴基斯坦的反应,“我们可能在支持找麻烦的人,而放弃支持我们的人”。麦克米伦说,中国的目的是有限的,中国没有占领印度的计划。现在中国人已经撤走,美英不要让印度退回到傲慢和对西方敬而远之的态度上去。“我们必须让他们面对克什米尔的现实。从长期看,他们依赖西方。在短期内他们可以得到西方的援助,但条件是他们解决克什米尔问题。”
FRUS, 1961—1963, Vol.19, pp.452453.
尽管肯尼迪希望援助印度,但还是听从了麦克米伦的观点。英国的方针对拿骚会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拿骚会谈决定,为了帮助印度装备6个山地师,美国和英联邦国家各自承担6000万美元紧急军事援助,防空援助问题暂时搁置。西方将放慢援助速度,以便敦促印度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如果印巴达成妥协,西方将为南亚联合防御提供长期军事援助。也就是说,除了1.2亿美元的援助外,印度只有在满足了有关条件之后,西方才会为它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在印巴两国就克什米尔问题开始谈判之前,12月26日中巴两国宣布双方在边界问题上已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中巴关系的进展明显地打乱了美国的“大计划”,华盛顿指责巴基斯坦与中国“调情”。印度政府恼羞成怒,更不愿意向巴基斯坦做出让步。在获知美英将对印度提供大规模援助后,巴基斯坦明确表示不同意美国认为中国有侵略动机的观点。它还不顾美国反对,宣布外长布托(Z. A. Bhutto)将出访中国。1963年3月,中巴两国签订了关于边界问题的协议。
FRUS, 1961—1963, Vol.19, pp.448458, 481506.
1963年上半年,印巴两国在美国的斡旋下进行了6轮谈判,双方未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取得进展。随着中印边界形势逐渐平静下来,美国不仅失去了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的兴趣,而且降低了对印度战略地位的估计。危机时期印度曾提出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要求,美国应付了一阵后也就没有下文。印度希望美国提供空中保护,但美国只提供了一些雷达设备。印度还期望美国提供先进的军工设备,最后它只得到几条二手的弹药生产线。美英提供的1.2亿美元军事援助到1965年只完成了0.9亿,剩余部分后来干脆取消了。
Stephen P. Cohen, U.S. “Weapons and South Asia: A Policy Analysis,” Pacific Affairs, Spring 1976.
(二) 美国分裂中苏谋划与其南亚政策的矛盾
美国在南亚地区无法实现其“大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处理中苏分歧的政策有关。
自1959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以后,莫斯科一直拒绝支持中国的立场。尼赫鲁对中苏分歧非常关注,试图以良好的印苏关系来促使苏联束缚中国的行动。1962年8月,印度不顾美国的反对,同苏联签订了有关购买米格飞机的协议。此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牵制中国。
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打响。两天后,肯尼迪政府因古巴导弹问题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面对全面战争的风险,赫鲁晓夫认为最好还是同中国站在一起。25日苏共《真理报》在头版刊登文章说,“中印边界问题是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遗产,中国从来没有承认过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它是被强加给中印人民的”。文章不仅没提原来的中立立场,而且还指责印度受帝国主义的唆使,挑起武装冲突。文章表示,“在反对帝国主义阴谋的斗争中,苏联完全站在兄弟般的伟大中国的一边”。苏联的变化使印度非常不安,但是新德里很快就知道,苏联发表这一“坏文章”的原因是“古巴导弹危机造成的形势和战争威胁”。
S. Nihal Singh, The Yogi and the Bear, Story of IndoSoviet Relations, Maryland: The Riverdale Company, 1986, pp.2931.
在要求美英提供军事援助的同时,印度也将这一决定通知了苏联。29日,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尼赫鲁如释重负。他告诉加尔布雷思说,苏联对印度寻求西方军事援助的行动表示理解,但苏方要求印度不要同美国形成军事同盟关系。而且,苏联稍后还会向印度提供武器。所以印度要尽可能避免刺激苏联。加尔布雷思表示理解印度的立场,他说美国并不要求印度成为西方盟国。10月31日,加尔布雷思会见印度新任驻苏大使T.N.考尔(T. N. Kaul)。考尔说在摊牌的情况下,苏联一定会支持中国,现在印度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确保苏联维持一定程度的中立,或许这还能维持苏联对印的经济援助。考尔问道:“美国现在是否继续支持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加尔布雷思立即向他做了保证
FRUS, 1961—1963, Vol.19, pp.351, 365; 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p.331; J. K. Galbraith, Ambassadors Journal, pp.387388, 394.。
尼赫鲁需要西方的军事援助,但也要保住不结盟政策这块招牌,而苏联的支持是他达到目的的先决条件。11月2日,印度外交部秘书长R.K.尼赫鲁(R. K. Nehru)对苏联驻印大使说,尼赫鲁指令他转交一封致赫鲁晓夫的信,并同大使进行谈话。R.K.尼赫鲁说,中印边界战争的发生是中共“左派教条主义基本战略的一部分”,中共左派的目的是要证明,“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印度必定要加入西方集团中去”,“他们正以行动竭力迫使印度放弃不结盟政策,使它被纳入西方集团”。这位秘书长还说,他确信中国的行动是中苏意识形态争论的延续,中共“正在把主要打击目标指向苏联及其外交政策原则”。而印度是高度评价这些原则的。
“New EastBloc Documents on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1959 & 1962,” ed. by James G. Hershberg, in New EastBloc Evidence on the Cold War in the Third World and the Collapse of Détente in the 1970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6/1997, p.264.
这番话表明,印度竭力要扩大中苏分裂,以确保它继续得到苏联支持。
印度的期望没有落空。古巴导弹危机刚一收场,赫鲁晓夫就觉得可以抛弃中国了。11月5日《真理报》重新表示,苏联在中印冲突问题上持中立立场。11月17日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司的希尔斯曼在分析中说,苏联“可能被迫要在对中国履行作为军事同盟及共产主义伙伴国家的义务,以及它殷勤培育的同印度的联系中进行选择”。苏联希望尽可能保持中立并让双方谈判。但是只要这场冲突持续下去,莫斯科可能就无法逃避这种困境,“这一冲突持续越长,它对中苏关系的分裂性影响就越持久、越强烈”。
S. Nihal Singh, The Yogi and the Bear, p.31.
在肯尼迪政府中,国务卿腊斯克对于援助印度较为消极。11月19日,他在同总统讨论中印危机时说,他怀疑印度以后会与中国进行谈判,双方可能达成某种“交易”。他认为,美国应该让英国在援印问题上起主要作用,“我们越是站到前面去,我们就越是把莫斯科推向北京”。
FRUS, 1961—1963, Vol.19, p.396. McMahon,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 p.287.
腊斯克相信,中国在印度的目标是有限的,但中印冲突是美国使中苏分裂深化的天赐良机。
23日,哈里曼在新德里对尼赫鲁说,美国并不打算要印度加入西方军事联盟。如果可能,对印度来说,最好是保持与苏联的良好关系。哈里曼回国后向肯尼迪汇报说,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会发生相当程度的、实质性的、在方式上有利于美国的变化。但美不应谋求印度与美国或西方建立形式上的总体联系。西方形式上的保证可能破坏印度实质性的努力,并且可能迫使它断绝与苏联的关系,“致使苏联与红色中国更为接近”
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pp.332, 325; FRUS, 1961—1963, Vol.19, pp.417, 426427.
。显然,美国对印政策出现了矛盾。
11月30日,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提出了题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文件,这份文件说,美国要努力避免采取“或是会减少目前及将来对中国的压力,或是会迫使中国与苏联回到密切联系中去”的行动。这一观点很快就成为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目标。12月美国决定,不再阻挠印度采购苏联米格飞机。在反驳英国的不同意见时,加尔布雷思说,莫斯科希望避免长期夹在中印之间,而米格机是让苏联继续挂在印度的鱼钩上。
FRUS, 1961—1963, Vol.22, pp.325, 437, 456.
印度购买米格机似乎已成为符合西方利益的行动,考虑到几个月前美国还拼命反对此事,这一变化极具讽刺意义。
1963年5月,国务卿腊斯克在访印后报告说,尼赫鲁将坚持不结盟政策,“这是为了在反对中国时得到苏联的帮助。如果这样做失败的话,他就会同中国讲和”。
FRUS, 1961—1963, Vol.19, p.577.
就美苏竞争而言,肯尼迪政府自然不愿看到苏联在新德里的影响扩大,但为了达到分裂中苏这一更具战略意义的目标,美国不得不接受这种扩大作为代价。然而,在苏印关系发展的前提下,美国指望印度会接受它的冷战战略是不现实的,甚至在逻辑上也是混乱的。有了苏联的支持,印度不仅可以长期与中国对抗,还可以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不做让步,同时避免对西方武器的依赖,并为自己的利益而不加入西方同盟体系。
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为其自身利益服务的。1963年5月,中央情报局局长麦考恩(John McCone)在谈到美国在南亚的目标时说:如果印度同中国联合,美国就不会有“自由的南亚”。“我们的利益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次大陆,我们将利用能帮助我们推进这个目标的国家。”麦考恩说,美国虽然不能解决印巴矛盾,但也不能让那些“自称中立的人完全落入共产党的阵营”。
FRUS, 1961—1963, Vol.19, p.480.
麦考恩的话表明,美国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是要利用印度进行冷战,而不是被印度利用为它拓展疆界。
肯尼迪的南亚政策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但此后美国在南亚的影响却走了下坡路。英国的政策是阻碍美国实现其目标的主要原因之一。英国原来对印度的中立主义政策相当宽容,而麦克米伦在拿骚的态度却很苛刻。英国很清楚,印巴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它坚持以此为长期军援的条件。这表明,财力拮据的英国根本不愿为武装印度掏钱。科默尔的小组委员会曾经认为:英国不愿承担过多义务的原因是,“它不想做任何要付大代价的事”。其实,美国也不愿意花钱帮助印度实现军事现代化。
FRUS, 1961—1963, Vol.19, pp.435, 453456.
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是复杂的,不仅印巴关系对这一地区的战略形势有着重大影响,中巴关系、印苏关系、中苏关系也对局势产生着互动影响。中国很快打赢战争,很克制地结束冲突,在关键时刻与巴基斯坦解决边界问题,这些行动都大大压缩了美国的政策空间。这一时期肯尼迪政府开始关注中苏分裂,防止中苏关系的修复被认为是最优先的目标。为此,美国不得不改变策略,容忍苏印关系的发展。然而这种变化同肯尼迪政府的南亚战略目标存在着矛盾。印度虽然没有同中国联合,但它同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美国虽然卷入很深,但它对事态发展的结果、对南亚地区的战略形势没有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
肯尼迪的对华政策与1962年的台海危机
*
*本文原发表于陶文钊和仲掌生主编的论文集《中美关系1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1961年,民主党人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入主白宫,美国政局变化对美台关系产生了冲击。1962年春,国民党当局再次图谋以武力“反攻大陆”,由此在“台湾”海峡引发了一场新的危机。台湾当局的这一行动虽然主要是针对大陆的,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针对美国民主党政府的。这场危机由于中美双方的外交沟通而得到控制,危机的过程体现了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三方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一、美台关系中的“四重危机”
1957年,肯尼迪在《外交》季刊上批评共和党的对华政策“过于僵硬”。1959年,随着极端亲国民党的共和党参议员诺兰(William Knowland)和亚历山大·史密斯(Alexander Smith)等人去职离开国会,美国朝野出现了一股要求抛弃杜勒斯(John F. Dulles)僵硬的对华政策的呼声。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人迪安·腊斯克(Dean Rusk)领导一个小组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研究,他们要求政府重新评估对华政策。1960年,两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鼓吹让台湾“公民有以投票方式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实际上是鼓吹“两个中国”的政策。东部权势集团的重要思想库“对外关系委员会”提交了一个全面的研究报告,希望找到能同中国妥协的方案。在大选中,肯尼迪曾公开批评共和党对金门、马祖的政策是冒险政策。这一切都给“美台”关系带来了不确定因素。
Arthur Waldron, “From Nonexistent to Almost Normal: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1960s”, The Diplomacy or the Crucial Decade: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During the 1960s, ed. by Diane B. Kun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219250; Christopher Matthews, Kennedy and Nixon: The Rivalry that Shaped Postwar Americ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pp.158160; James Thomson, Jr., “On the Making of U.S. China Policy, 1961—1969: 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50, AprilJune, 1972, pp.220243.
民主党新政府成立后,腊斯克当上了国务卿,史蒂文森成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另一名支持改变对华政策的开明派民主党人鲍尔斯(Chester Bowles)成了副国务卿。台湾当局对肯尼迪政府的国务院新班子充满了戒心。国民党当局“副总统”陈诚在肯尼迪宣誓任职的当天说:“今年是世界人类危机最大的一年。”
“民国”史事纪要编委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61年1月至4月)》,台北,1980年,第185186页。
肯尼迪政府刚上台不久,就因为在老挝的国民党残军问题指责台湾。国民党残余力量过去一直在缅、老、泰边境地区活动。1960年,台湾当局对他们进行空投补给,试图让他们参与老挝内战,帮助消灭老挝的中间和左派力量。台湾当局的这些措施与共和党政府的老挝政策是一致的。1961年2月,一架国民党飞机被缅甸政府军击落,仰光发生了反美示威。民主党新政府认为,国民党的这些行为可能为中国干预老挝提供借口,他们要求将这些国民党残军撤回台湾。此外,美国政府还认为“台湾”的行动损害了美国在中立主义国家中的威信。腊斯克威胁说:“美国政府决心要保护自己的名誉和信誉,如果有必要的话,会让‘中华民国’政府为此付出代价。”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U.S.A.,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以下简称FRUS), 1961—1963, Vol.22, pp.57, 1217.
蒋介石虽然不满美国的压力,但也只好同意撤军。
此后,美台之间接二连三地发生外交冲突。首先,双方在如何保住国民党当局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上发生了对立。朝鲜战争以后,美国一直以“暂缓表决”策略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当局得到联合国席位。1960年,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让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一些西方国家也指责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承认现实。肯尼迪认为,如果美国允许中国加入联合国,将导致美国国内发生严重的政治分歧,甚至会削弱美国对联合国的支持。因此美国不能抛弃国民党不管。
FRUS, 1961—1963, Vol.22, p.15.
美国政府估计在1961年的表决中,它很可能因得不到多数支持而被击败。为了应付新的局面,肯尼迪政府准备提出所谓的“继承国方案”,即认为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继承国。这是一个推行“两个中国”政策的方案,美国对“台湾”解释说,它希望中共会因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而拒绝进入联合国,以此达到保住“台湾”席位的目的。当然,美国也可以以此推卸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责任。
FRUS, 1961—1963, Vol.22, p.27.
但蒋介石不愿接受“继承国方案”。1961年4月3日,他写信给肯尼迪说,台湾当局“不可能接受所谓两个中国或者其他影响中国或者其他影响‘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代表权性质的安排”。“台湾”不能在这一问题上妥协,因为“忠奸绝不相容”。
FRUS, 1961—1963, Vol.22, p.46.
其次,“美台”之间因蒙古问题也发生了激烈争吵。国民党当局长期阻挠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1961年4月,在一些非洲国家的支持下,苏联将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与毛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宣称如果蒙古的加入被台湾当局否决,毛里塔尼亚的加入也将被苏联否决。美国希望国民党当局这一次不要再使用否决权,因为这会引起非洲各国对台湾的反感,从而使美国保住“台湾”在联合国席位的努力落空。此外,以副国务卿鲍尔斯为代表的一些官员认为,在中苏分裂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美国应该考虑在外交上承认蒙古的问题。这样做一来可向苏联及其集团显示美国欣赏他们的温和政策,二来可向“台湾”表示美国的亚洲政策可能有所变化,三来可在地处中苏之间的乌兰巴托建立一个情报“窗口”。
FRUS, 1961—1963, Vol.22, pp.9091, 105.
其三,出现了美国政府要为“台独”分子廖文毅发放签证的问题。廖文毅长期在日本进行“台独”活动,从1950年起,他就想去美国活动以寻求支持。考虑到“台湾”的反应,华盛顿一直没给他发签证。肯尼迪政府上台后,国务院在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的要求下同意给廖签证。此事通报给“台湾”后,也引起了蒋的强烈反应。
其四,国务院准备出版系列档案文集《美国外交文件》中的“1944年中国卷”。这卷档案涉及当年国民党政府的许多腐败行为,以及美国与国民党关系中的一些内幕,其中有些内容曾在1949年的《美中关系白皮书》中有所披露。该书本应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版。因为台湾方面的阻挠,共和党政府将该卷的出版搁置起来。民主党人一直对国民党卷入美国国内“谁丢失了中国”的政治争吵不满,所以重新考虑出版该书。这四个问题被当时的国务院官员詹姆斯·汤森称为“美台”关系中的“四重危机”。
James Thomson, Jr., “On the Making of U.S. China Policy, 1961—69: 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50, AprilJune, 1972, pp.220243.
在蒋介石看来,“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是肯尼迪政府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美国承认蒙古可能是其在外交上承认大陆的先兆。台湾召开了“五院联席会议”,动员民族主义情绪,试图以此向美国施加压力,阻止蒙古进入联合国。6月21日,蒋对美国驻台“大使”庄莱德(Everett Drumright)说,美国同意给廖签证是“无视友邦的利益”,是以牺牲台湾当局为代价鼓励“台独”。他还表示坚决反对“继承国方案”,如迫不得已“台湾”将退出联合国;美国如果坚持这一方针,“台湾”实际上就是被美国赶出联合国的。蒋介石说,他“怀疑尽管美国政府表示支持“台湾”,但实际上正精心改变对华政策”,如果这些不利的情况不幸发展下去,将会对“美台”关系产生“严重损害”。
FRUS, 1961—1963, Vol.22, pp.7779.
8月初,“副总统”陈诚赶到华盛顿活动。经过紧张的会谈,肯尼迪政府放弃在联合国执行“继承国方案”,代之以“重要问题方案”,继续利用联大程序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肯尼迪政府还表面上同意暂不考虑承认蒙古问题。此外,美国还表示将暂不给廖文毅发签证,并继续推迟“1944年中国卷”的出版。但是,美国的让步未能使“台湾”在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上妥协。蒋在9月写信给肯尼迪说,如果必要,“台湾”仍将在这一问题上使用否决权。
FRUS, 1961—1963, Vol.22, pp.104110, 112113, 135135.
其实,美国在蒙古进入联合国问题上决心已定。腊斯克9月17日电告庄莱德说,如果台湾当局“决心与船一起沉下去而不是妥协”的话,美国将不承担责任。如果需要,美国要向公众宣布,尽管它作了最大努力,国民党当局“还是在联合国问题上选择了政治自杀”。月底,腊斯克警告台湾“外长”沈昌焕说,“台湾”应当重新考虑否决蒙古的问题,在“让蒙古还是让北京进入”的问题上,美国别无选择。“台湾”不要幻想可以把它自己招致的失败归咎于美国。
FRUS, 1961—1963, Vol.22, pp.137138, 140141.
10月2日,蒋介石情绪激动地向庄莱德提出:如果“台湾”投否决票的话,美国将投票赞成蒙古加入的消息是否属实?美国政府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新的白皮书”?美国会由此承认蒙古并与之建交的消息是否属实?美国将因此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的消息是否属实?如果中共被接纳进联合国,美国是否认为“台湾”的地位不复存在,并将台湾看成中共的领土?
FRUS, 1961—1963, Vol.22, pp.142144, 148149, 152153.
这种激烈的争吵表明,“美台”关系此时已极度紧张。最后,在美国的全面压力下,台湾当局只得同意不否决蒙古进入联合国。蒋介石要肯尼迪本人公开保证,美国将使用否决权阻止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务院拒绝作这种保证后,蒋经国同中央情报局台北站负责人雷·克莱恩(Ray Clane)进行了秘密谈判。通过这一渠道,肯尼迪向台湾做出秘密保证,即在必须和有效时,美国将使用否决权。
FRUS, 1961—1963, Vol.22, pp.155, 160.
在以上四个问题上,国民党当局实际上在三个问题上迫使美国作了让步,而在蒙古问题上,“台湾”也得到了美国的秘密保证作为交换。
二、肯尼迪政府的“门缝”政策
肯尼迪是以“活力和革新”的口号打动美国选民的。他承诺要以更灵活的立场处理对外事务。在对苏政策上,肯尼迪比他的前任更强调同苏联缓和,更热衷于进行裁军等谈判。在对华政策方面,民主党政府一度也想有所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一些官员在新政府上台后提出过一些工作文件,有的要求在中国进入联合国与沿海岛屿问题上改变政策,有的还提出了可能改善中美关系的各种措施。
FRUS, 1961—1963, Vol.22, pp.1927;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官员赖斯(Edward Rice)在1961年春就曾提出过一份全面研究报告,为改变对华政策和显示美国灵活态度,他列举了可采取的各种措施,如发放到中国的签证,改变对华“禁运”政策,以及让中国加入军备控制谈判,等等。见James Thomson, Jr., “On the Making of U.S. Chine Policy, 1961—69: 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50, AprilJune, 1972, pp.220243.
在1961年3月3日与新西兰总理的会谈中,肯尼迪说,他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看中国问题的,他并不特别在意与中国问题有关的法理和理论。在对华问题上,“他也许是以一种较开放的思想来承担总统的职责的,并且准备在可能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创造一种不太紧张的气氛,以便可以寻找某种建设性关系”。肯尼迪指出,美国有很多像“百万人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反对改变对华政策,但只要他认为有可能的话,他就“准备着手解决这种在全国根深蒂固的和情绪强烈的反对”,美国还准备做出一些“有限的探索性姿态”。
FRUS, 1961—1963, Vol.22, pp.5455.
肯尼迪是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总统,但是在对华政策方面,他并没有真正做好变化的准备。1961年5月,国务卿腊斯克就中国问题与总统进行了长时间的私下讨论。他们认为,多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没有反映亚洲的现实。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可能有几种选择:“对‘两个中国’都承认,即所谓‘两个中国’的方案;或者悄悄地在幕后为北京和台北调解;或者稳坐不动,等待进一步的发展。”腊斯克问肯尼迪是否要求国务院探索对华政策方面的改变,但肯尼迪排除了政策上的变化。肯尼迪只是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大选,他没有得到美国人民强有力的授权,因此他必须小心谨慎,“而改变对华政策将是一场生死搏斗”。他说采取较现实的对华政策是将来的任务,不是现在的事情。如果现在就做,他会被国民党的游说集团、共和党人和一些国会议员“赶出白宫”。
FRUS, 1961—1963, Vol.22, pp.5455.
肯尼迪实际上选择的是“等待发展”的第三种方案。
肯尼迪的探索姿态十分有限,他同意在华沙大使级会谈中提出互换记者要求,以及研究是否可向遭受经济困难的中国出售粮食的问题。为了掩盖自己政治上的软弱,肯尼迪一开始就把关系继续紧张的责任推到中国头上,声称中国对改善关系没有兴趣。实际上中国政府在1961年春就在华沙主动安排过秘密会谈,并在会谈中提出过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但肯尼迪政府不敢越雷池一步,对中方的设想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FRUS, 1961—1963, Vol.22, pp.7072, 8789.
与此同时,东南亚形势的发展使肯尼迪政府加深了对中国的敌视。肯尼迪认为,共产党支持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对美国的重大挑战。他研究过毛泽东的游击战著作,还要求下属们也读这些著作。他认为东南亚是美国能否处理这一问题的试验场。1961年4月,肯尼迪政府同意举行老挝问题日内瓦会议,这表明美国不得不回到老挝“中立化”的道路上来。但军方反对停火,希望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预,他们认为美国在老挝的困境是中国造成的。就连积极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副国务卿鲍尔斯也认为,美中之间的战争可能很难避免,迟早要打。
James Fetzer, “Clining to Containment: China Policy”, in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1—1963, ed. By Thomas G. Pater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78197; FRUS, 1951—1963, Vol.24, pp.150154.
在政府内部,积极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声音是很弱的。五角大楼认为中国是最严重的威胁,他们不希望民主党政府改变政策。1961年4月,国防部长助理帮办兰斯代尔(Edward Lansdale)上校提议,中国经济已经陷入困境,美国应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此人以在东南亚进行反共“秘密战”而闻名,他在给国防部长的报告中暗示,可以同意让台湾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说,中国还没有达到“总起义的爆发点”,中国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知道自己没有成功的机会,“除非有来自外部的帮助”。兰斯代尔承认中国军队仍是“有效的”,但又说“强大的心理攻势能改变这种情况”。针对肯尼迪政府可能改变政策的倾向,兰斯代尔说:“阻止在中国内部进行试探性行动,认为第七舰队只是一种外交工具,或者对周恩来的政治谋略考虑过多,可能正是我们现在不该去做的错事。”
中央情报局是另一个主张采取强硬政策的机构。中情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在7月初返回华盛顿。他通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向肯尼迪报告说,美国最近的一系列行动使台湾当局深受震动。台湾当局对美国的动态极为敏感,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他说台湾当局现在极为紧张,“正在准备进行非常危险的冒险,包括对大陆进行自杀性登陆行动”。克莱恩预言,如果这一趋势不能扭转,美台之间会“发生严重的分裂”。
FRUS, 1961—1963, Vol.22, pp.3839.
当时蒋介石的确很紧张,但他实际上不可能采取“自杀性”行动。克莱恩这样危言耸听,显然是要对肯尼迪政府施加压力。
FRUS, 1961—1963, Vol.22, pp.8991.
邦迪与克莱恩一唱一和。他说:“使这一切如此悲哀的是实际上我们并不打算抛弃蒋,我们有一切理由去支持台湾取得真正的进步。然而我们似乎正在走向马歇尔和艾奇逊曾经走过的死胡同,并因此在国内和国外都产生很坏的政治后果。”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和艾奇逊(Dean Acheson)都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调整对华政策而被台湾和美国右翼势力攻击得一无是处。重提他们的名字,对肯尼迪来说是最明白不过的警告。克莱恩还说:“如果我们能在某些对大陆的试探行动上与蒋联合行动的话,我们就能立即重新得到他的最大支持。”台湾只有依靠美国才能生存,为什么肯尼迪政府倒过来需要蒋介石的支持?强硬派这一建议主要是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考虑上提出的,即怎样才能避免台湾和美国右翼的压力。
FRUS, 1961—1963, Vol.22, pp.8991.
国会和共和党中的亲台力量是民主党政府的另一阻力。他们反对改变对华政策的声调正在渐渐升高。肯尼迪当选总统后,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和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都警告他不要改变对华政策。1961年夏,在国民党当局的动员下,美国亲台势力大肆活动,攻击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和在蒙古问题上的立场。一些国会议员认为,政府承认蒙古可能是承认中国的第一步。他们扬言,如果肯尼迪政府不改变承认蒙古的决定,他们就要毁掉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方案。
Christopher Matthews, Kennedy and Nixon, The Rivalry That Shaped Postwar America, pp.186189; 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The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ohn F. Kennedy, New York, Dell Publisher Co., 1967, pp.306307.
亲台势力的活动使民主党政府非常头痛。
正是这些因素使肯尼迪在1961年夏向台湾做出让步,并可能进一步搁置了调整对华政策的想法。国务院在10月完成的文件稿“美国对华政策”中写道:“我们应当对大陆中国遵循这样的基本政策,以便寻求:(1) 留一条门缝以便与美国建立一种较满意的关系。(2) 降低我们相互的敌对。(3) 把这敌对的责任推到共产党中国身上去。(4) 同时,为中苏集团在亚洲的扩张建立更有效的障碍。”
FRUS, 1961—1963, Vol.22, pp.162167.
显然,肯尼迪政府执行的仍然是遏制政策。它虽然说要“留一条门缝”,但它没有计划做什么改变。
这种政策在1962年上半年起草的“基本国家安全政策”文稿中也得到了反映。这份文件认为美国应对中国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但文件说,阻止美中建立正常关系的障碍是,“中国从根本上不愿改变它现在的侵略政策”。但“美国将留一条门缝,以便有同中国扩大经济、文化和其他接触的可能”。
FRUS, 1961—1963, Vol.22, p.271.
肯尼迪政府认为它能在继续对中国进行遏制、继续对“台湾”进行公开支持的条件下,逐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实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三、肯尼迪政府对1962年台海危机的处理
在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受到盟国和舆论的普遍指责。为了防止危机的重演,杜勒斯后来去台湾见蒋介石,迫使他承诺放弃以武力‘反攻大陆’。肯尼迪上台后,国务院曾有人提出过设想,认为美国应逐渐摆脱对大陆沿海岛屿的“义务”,并让国共内战逐渐熄灭,以便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但政府内部对这一方针有不同意见。1961年7月,在中央情报局建议支持国民党对大陆的骚扰活动后,肯尼迪批准了一项允许台湾向大陆空投6~20人的小股武装的计划。这是民主党政府为平息“台湾”的不满而做出的姿态。
FRUS, 1961—1963, Vol.22, p.193.
但国民党认为这一计划的规模太小,因此没有马上付诸实施。由于大陆的经济困难和中苏关系的恶化,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的最好机会正在到来。1961年12月,蒋对“国大代表”说,1962年将是反攻成败的“决定年”。1963年元旦,蒋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声称“台湾”“对反攻作战已经有了充分准备时可以开始行动”。他还摆出一副要摆脱美国牵制的样子,让“国大”通过议案,要求修改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黄嘉树:《国民党在台湾,1949—1988》,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第333页。
1月24日,蒋介石向克莱恩提出要和美国交换意见,讨论国民党对大陆局势进行“干预的可行性、必需性和可取性”。2月下旬,蒋介石会见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时说,国民党将要进行反攻,“台湾”不要美国参加这一行动,但要求美国“策略上”的同意和秘密提供后勤支持。
FRUS, 1961—1963, Vol.22, pp.183184.
但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研究机构认为,虽然中国处于软弱的情况下,但政府早先的结论——“除非发生重大革命,国民党反攻大陆才能成功”——仍然成立。美国如同意“台湾”发动大规模登陆作战,自己必然会被卷入其中。这一进攻即使得到成功,它也只会促使中国在东南亚进行公开的军事干涉。此外,中国还可能寻求苏联的支持,造成中苏两国重新联合的局面。
这一研究报告还指出,如对大陆采取较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后果也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如果大陆不会发生人民大规模“反叛”的话,美国同样会面临前一种情况。如果国民党的行动失败,它的国际地位将更难维持,美国支持一个“独立的”台湾也更困难。如果国民党的行动导致一种既不失败也不成功的局面,这固然有引起中国动荡和消耗中国资源的好处,但也可能使中共与莫斯科缓和关系。
FRUS, 1961—1963, Vol.22, pp.183184.
总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国民党的反攻行动不管结果如何,对美国的利益都会造成损害。
3月初,肯尼迪政府决定不直接拒绝蒋的要求。同时,它提醒国民党当局要严格遵守1954年12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即对大陆的军事行动事先应同美国磋商,并需得到美国的同意。为了表示重视“台湾”的意见,肯尼迪让助理国务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访问台北。哈里曼是民主党的资深外交家,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就见过蒋介石。肯尼迪指示,哈里曼应强调美国赞赏“台湾”进行及时磋商,但也要以美国在“吉隆滩事件”中的失败为由,强调必须有充分的情报才能行动。
FRUS, 1961—1963, Vol.22, pp.191193.
肯尼迪已从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中学乖了,他不想再让亲台势力有攻击其政策的借口。
在同哈里曼的会谈中,蒋介石保证不会轻举妄动,但他避免做出只有在美国同意后才采取行动的承诺。他说:“人民和军队已经没有耐心,如果不马上采取行动,他可能会失去对他们的控制。”哈里曼向肯尼迪报告说,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是中国的事务”,“他的唯一义务就是磋商,而不是事先要得到美国的同意”。
FRUS, 1961—1963, Vol.22, pp.195196.
3月21日,蒋介石和蒋经国与克莱恩进行了会谈。他们希望得到肯尼迪的私下保证,即美国对“台湾”的秘密军事行动给予暗中支持。克莱恩对华盛顿报告说,如果美国直接拒绝“台湾”空投200~300人的行动计划,蒋会做出强烈反应。这可能导致反美示威,破坏美国在台湾的计划。国民党还可能对大陆采取“绝望的”进攻,以期将美国卷入。蒋最后甚至会辞职,这会给“美台”关系带来动荡。克莱恩也说不能全面接受蒋的要求,但他建议向“台湾”提供适当的飞机和其他的援助,理由是可以拖延“台湾”的行动时间。詹姆斯·汤森(James C. Thomson, Jr.)认为,国民党的“反攻”计划“无疑得到了他们在美国政府中的盟友的鼓励”。至少,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军方中有不少像克莱恩这样的同情者。
FRUS, 1961—1963, Vol.22, pp.198200.
3月31日,肯尼迪与他的高级助手们讨论了台湾的要求。腊斯克指责“台湾”的计划是一派胡言,他说这种计划根本不可能保密,到时候美国也逃脱不了责任。由于担心“台湾”再次发起反政府宣传,引起美国亲台势力的响应,肯尼迪政府决定采取敷衍应付的方针。政府一方面批准向“台湾”提供两架C123飞机,另一方面要台湾提供更多的情报,以证明其计划的可行性。4月中旬,“台湾”同意将对大陆的秘密进犯行动推迟到10月。但要美国保证同意在10月1日进行首次空投。美国则强调200人规模的行动必须得到美方事先批准。
FRUS, 1961—1963, Vol.22, pp.204205, 218219.
5月克莱恩再次回华盛顿传达蒋介石的意见。由于台湾当局增加税收并将大量资金用于“反攻”准备,美国政府威胁要减少援助。为此,蒋介石批评美国使用经济压力,说这会损害台湾当局的威望,会“在台湾引起不稳定和反美主义。他还指责美国官员对台湾没有同情态度,并再次要求美国提供军用飞机,以及7万至10万吨的登陆船只。
FRUS, 1961—1963, Vol.22, pp.227229.
由于台湾当局的挑衅行动不断加剧,台海地区的危机局面重新出现。5月底,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以为现在是进犯大陆的最好时机,“他下决心要大干一场了。”总参谋长罗瑞卿指出,“现在已经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怎样打的问题”。为了粉碎国民党的计划,中央下令迅速向福建地区增调军队。6月10日左右,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要驻波兰大使、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代表王炳南立即返回华沙。因为中央认为,蒋介石反共决心虽然很大,但他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关键的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周指示王炳南尽快了解美国的意图。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8590页。
解放军的调动很快引起了美国的注意。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到6月20日,中国已经向福建增调了7个师,可能还有5个师正在路上。美国政府对中国大规模集结军队的动机捉摸不透。他认为中国可能有三种动机:一是要威慑国民党当局,防止国民党对大陆发动进攻。二是可能再发动一场1958年那样的军事和政治危机,以此加剧美台紧张关系,转移国内问题。三是可能对沿海岛屿发动突然和全面的进攻。国务院认为,中国的动机主要是威慑,但也可能引发危机。中央情报局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更大,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认为,已有的情报表明,中国的航渡能力不足以发动登陆进攻。但他建议让第七舰队保持四艘航母,并将航母开到台湾附近活动。
FRUS, 1961—1963, Vol.22, pp.248249, 252253.
肯尼迪政府也希望通过外交途径了解中国的意图。6月22日,哈里曼会见了苏联大使多勃雷宁,试探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同一天,代理国务卿乔治·波尔(George W. Ball)会见英国大使,要英国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转达信息。哈里曼本来准备稍后在华沙同中国直接接触,但22日王炳南提出要求,次日同美国大使卡波特(John M. Cabot)举行私下会谈。国务院立即把有关的信息通知了卡波特。23日,王炳南在会谈中说,蒋介石集团正在准备进犯大陆,这种准备是在美国的支持和鼓励下进行的。他警告说,美国是在玩火,美国从“台湾”的行动中不会得到任何好处,美国政府要对蒋的行动负全部的责任。
在以上三个渠道的会谈中,肯尼迪政府向中国传达了同一个信息:在目前条件下,美国无意支持国民党对大陆发动进攻。美国与“台湾”有正式的谅解,没有美国政府的同意,“台湾”不能对大陆采取进攻行动。卡波特还特意对王炳南说,他是得到政府授权作这一声明的。卡波特甚至表示,如果蒋要进攻,中美可以联合起来制止他。与此同时,美方也表示,它同“台湾”有条约关系,他们将帮助国民党防御台湾和沿海岛屿。卡波特试图要王炳南保证中国不会主动进攻,王炳南经过考虑后回答说,中国“现在没有面临要以武力解决的问题,但如果发生(国民党的)进犯,整个形势的性质就会变化”。
FRUS, 1961—1963, Vol.22, pp.267275;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第8890页。
了解了中国方面的这一态度,对美国来说也是有用的,它避免了美国对中国的动机的进一步猜疑。
26日,美国媒体报道说,中美两国大使在华沙进行了秘密会谈,美国已向中国保证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交底,并把此事泄漏给媒体,从而使危机明显地降级了。
FRUS, 1961—1963, Vol.22, pp.283291.
此时,蒋介石已经骑虎难下。从1962年10月起,“台湾”以空投和小艇登陆方式向大陆派遣小股武装。这些小股武装以6~28人为一组,试图促成大陆人民“反叛”。中国公安部门在12月29日发表公报说,三个月来中国消灭了9股“美国和国民党特务”。台湾的报纸承认有172人在行动中被打死。如果以计划中平均每队20人来计算,到达大陆的国民党特务差不多已全军覆没。
国民党的窜扰活动在1963年以完全失败而告终,先后进行的28次窜扰活动无一达到目的。9月,蒋经国到美国访问。尽管他仍希望能“形成一种不引起大战就能解决中国大陆问题的方案”,但华盛顿对此已完全没有兴趣。蒋经国自己也承认,每次窜扰活动的唯一“破坏作用”就是大陆要动员上千人进行围捕。
FRUS, 1961—1963, Vol.1, Vietnam, 1962, pp.393395; Vol.22, pp.337338, 388389.
四、结论
肯尼迪政府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企图非常清楚,他们知道他的目的是要使美国卷入同中国的战争,以便自己有机会重新控制大陆。在这一方面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利益并不一致。为了避免被“台湾”拖入与中国大陆的大规模冲突,美国政府通过外交方式与中国进行了直接沟通,从而达到了控制危机的目的。正如腊斯克会见国民党驻联合国“大使”蒋廷黻时所说,美国政府的“第一义务是对它自己的人民的”。因此,美国不可能为了国民党的利益而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在重大危机到来时,肯尼迪政府采取了现实主义方针。这表明,尽管台湾当局能挑起事端,但在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措施的情况下,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制约下,它的意图是无法得逞的。
但是,这场危机的后果对肯尼迪政府来说也是复杂的。
肯尼迪政府上台后试图调整对华政策,1961年,“台湾”动用了他们的全部政治能量来阻止肯尼迪政府实现这一目标。虽然美国做出了一些让步,但“台湾”没能阻止蒙古进入联合国。因此,发动一场新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台湾当局扭转民主党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倾向。1962年3月,美国驻台“代办”高立夫(Ralph Clough)报告说,蒋介石决心要采取行动,他想渐渐把美国推到同意他进行大规模行动的方向上去。如果美国不同意的话,他会威胁单方面采取行动。高立夫说,蒋是一个精明人,“他清楚地意识到他是多么需要美国的支持。只要他还对美国政府基本上同情其目标,而且不打算改变对华政策感到满意……在今后几个月中他就不会采取单方面行动”。肯尼迪政府虽然阻止了蒋的军事冒险,但是它却不得不维持原有的对华政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政府政治上的软弱:这一时期的美国舆论调查表明,由于亚洲局势的紧张,反对改变对华政策的意见占了上风。
FRUS, 1961—1963, Vol.22, pp.202204; Leonard A. Kusnitz,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Americas China Policy, 1949—1979,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woods Press, 1984, pp.102103.
鲍尔斯等人曾建议对中国出售粮食。但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罗斯托(Walt W. Rostow)却提出“以粮食换和平”的设想,试图让中国放弃对越南和老挝人民的支持,以此作为美国同意售粮的条件。这种将人道主义措施变成谋求政治好处的方案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肯尼迪政府还考虑过迫使国民党撤离金门和马祖。但在危机时期,哈里曼认为,美国只有给“台湾”极大的利诱或施加极大压力才能达到目的,而这两者的代价都过于高昂。五角大楼在1962年6月强调,在目前条件下美国应维持原有政策。国务院也不得不承认,让蒋放弃沿海岛屿不是短期目标,此时政府不应修改政策。
FRUS, 1961—1963, Vol.22, pp.231233, 237, 264265.
英国历史学家福特(Rosemary Foot)认为,对中共的强烈反感和中苏关系的分裂是妨碍肯尼迪做出改变的重要原因。
罗斯玛丽·福特:《重新定义国内局势及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姜长斌、罗伯特·罗斯合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98333页。
肯尼迪政府对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中苏分裂——反应非常迟钝。1962年1月,国务院确认中苏分裂是“真正的”和“长期的”,但腊斯克却不愿采取具体行动,他只是将此事交“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美国当时认为,中苏在东南亚“保持着基本团结”,中苏分裂只会使中国在东南亚“采取更好战的态度”。这一届政府没有认真思考过中国为何要在越南采取强硬立场。由于麦肯锡主义的后果,美国政府中此时没有对高层决策者有影响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而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等老资格的苏联问题专家的意见,即美国与苏联合作共同对付中国,却很容易被决策者所采纳。苏联人对中国“非理性”的生动描绘也被美国决策者“接受和重复”。詹姆斯·汤森后来称这一现象为“国务院里的中国代沟”,并认为这是肯尼迪时期不能处理好对华政策的核心问题。
FRUS, 1961—1963, Vol.1, Vietnam, 1962, p.164; James Thomson, Jr., “On the Making of U.S. China Policy, 1961—69”.
肯尼迪时期也不是什么变化都没有。一批新的中国问题专家进入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1963年国务院设立了与“中国(指台湾当局)科”同级的“大陆事务科”,稍后这一机构又升格为“亚洲共产党事务处”。这种变动使美中关系逐渐摆脱了受制于“美台”关系、美日关系的处境。1963年11月23日,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在旧金山发表了一篇得到肯尼迪批准的政策讲话,认为“现在没有理由相信”中共政权“可能会被推翻”。美国“决心对可能的变化打开大门,而不会对有利于美国利益、服务于自由世界与中国人民福祉的发展关上大门”。这一讲话被认为从言辞上否定了杜勒斯的观点,为60年代后期的政策变化奠定了基础。
James Thomson, Jr., “On the Making of U.S. China Policy, 1961—69”; 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pp.350353.
总之,肯尼迪政府只提出了要为中美关系的改变提供可能,但它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事来促成这一变化的实现。一些美国学者认为:肯尼迪从一个对共和党僵硬的亚洲政策提出疑问的候选人,渐渐成了强烈地鼓吹这一政策的总统。他的对华政策与杜勒斯的政策没有什么区别。
Bevin Alexander, The Strange Connection: U.S. Intervention in China, 1944—1973, New York, Greenwoods Press, 1992, p.191; Christopher Matthews, Kennedy and Nixon, p.193.
这一政策不仅没有在台湾问题上有所突破,而且坚持将中国当作主要敌人,犯下了“以中国为代价与苏联谋求谅解”的战略错误,从而使美国在越南的卷入步步加深。这也是美国为其反华政策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冷战与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与南亚关系的变化
*
*本文原发表于陶文钊、杜瑞清和王旭主编的论文集《中美关系与东亚国际格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文化与制度有相当大的不同,但两国的关系却经受了各种考验,长期保持着友好互利的合作。中巴关系被称为“持久的协约”,它对南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也对其他大国同该地区的关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巴关系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是有关的研究大都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进行的,从历史角度进行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于中巴关系由冷淡到密切的转变仍然缺乏较为深入的了解,对于中国60年代初期的政策变化更缺乏动机层面的解释。本文试图在全面分析有关各方的南亚政策变化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国方面政策变化的原因,揭示这一时期南亚国际关系的特点。
一、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缓慢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是冷淡的。中国对于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缺乏了解,加之受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影响,中国一开始将这些国家归入西方阵营之内,视其为帝国主义的走卒。巴基斯坦是根据伊斯兰教义建立国家的,它对刚从革命中诞生的新中国政权也没有多少了解。印巴两国立国之后就为克什米尔问题发生战争,从1948年到1949的两年中,联合国先后为这一问题通过了6个决议。由于巴基斯坦认为中国可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也由于印度已在1949年底承认了中国,巴基斯坦政府在1950年1月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国的伊斯兰国家。不久后,它又宣布撤销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承认。巴基斯坦这样做的理由是很简单的,它不愿看到印度与中国形成密切的关系,而自己被一个亚洲大国晾在一边。
巴基斯坦认为,中国革命是亚洲的重大事件,巴政府批评一些国家不愿承认中国的做法。1950年6月朝鲜战争发生后,巴基斯坦认为朝鲜侵略了南方,并象征性地加入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但是,在中国加入朝鲜战争后,巴基斯坦没有在联合国投票指责中国是侵略者。而且,巴基斯坦也没有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表示异议,它还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中国得到联合国的席位。尽管如此,中巴两国正式建交还是拖了一年多的时间。中国对巴基斯坦冷淡的原因是,巴基斯坦当时同美国保持着密切关系,并在努力争取西方的援助,中国政府对此感到不悦。
此外,中国对巴基斯坦也缺乏了解。1951年11月,当巴基斯坦大使罗查(N. M. Raza)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时,毛曾以一种揶揄的口吻问他,巴基斯坦的大使是否需要由英国王室来任命。
Yaacov Vertzberger, The Enduring Entente, SinoPakistani Relations 1960—1980, New York:Praeger, 1983, pp.14.
1953年2月,美国艾森豪威尔(D. D. Eisenhower)政府上台。这届共和党政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加强了对中国的遏制。在国务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看来,巴基斯坦地处南亚与中东政策的交接处,它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由于印度反对美国的军事联盟政策,美国应当将巴基斯坦纳入西方的军事同盟中去。这年10月和11月,具有亲美意识的巴陆军司令阿尤布汗(Mohammed Ayub Khan)应邀访问美国,同美国政府讨论了两国“共同防御”问题。同年12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问了巴基斯坦,不久双方宣布美国同意向巴提供军事援助。巴基斯坦的这些行动使中国增加了对它的怀疑,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说,中国人民正在密切关注美国与巴基斯坦建立军事同盟的活动,因为巴基斯坦的东西两个部分都很接近中国的西南边疆。此时,中国正开始同印度谈判西藏问题,中印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进入了友好合作的阶段,而中巴关系却因巴基斯坦加入西方联盟而疏远。
这一时期,巴基斯坦政府声称“决心在自由世界的集体防御中扮演重要角色”。1954年5月,美国与巴基斯坦签订了“共同防御协议”。同年,为了加强对中国的遏制,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组织军事联盟,巴基斯坦成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之一。第二年巴基斯坦又加入了另一个西方军事同盟“巴格达条约组织”。
巴基斯坦采取结盟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西方的军事援助,并通过结盟取得超过印度的政治优势。对巴基斯坦参与美国领导下的军事同盟最不满的是印度。印度自独立后就执行中立的外交政策,它不愿看到冷战扩大到亚洲,更不愿意看到巴基斯坦从东、西方对立中得到好处。当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大量援助以后,印度对美国的批评就更加大声了。美国驻印大使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忧虑地指出,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的武器可能被用来对付印度,这可能会增加南亚与中东的不稳定。但是急于建立军事集团的杜勒斯没有听从鲍尔斯的意见。
到1956年为止,美国已同意向巴基斯坦提供2.0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估计完成计划需要提供4亿~5亿美元。Rashmi Jain, USPak Relations 1947—1983,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83, pp.91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1955—1957, Vol.8, South Asia, p.13.
1952年以后,中国对广大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态度有了重大的变化,中国逐渐认识到,这些国家有可能采取和平与中立的国际立场。从1954年起,谋求与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成为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方针。尽管巴政府在1954年追随美国阻挠中国得到联合国席位,但中国看到巴基斯坦对外政策中的某些特殊性,所以并没有向巴基斯坦提出抗议。1955年,在万隆会议期间,中国总理周恩来与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保格拉(Mohammad Ali Bogra)进行了两次会谈。保格拉强调,巴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不是要反对中国,它只是要保护自己不受印度的侵略,巴基斯坦不会参加美国发起的针对中国的战争。中国接受了巴的这一解释。三天后,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尽管我们原则上反对军事集团,但是中巴“达成了互相谅解”,“在集体和平与合作方面存在和谐一致的相互理解”。保格拉当场确认了周的这一说明。
John W.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191; Yaacov Vertzberger, The Enduring Entente, p.5.
1956年,中巴两国总理进行了互访,但是双边关系仍然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巴基斯坦总理回国后曾经说过:他相信在关键时候中国会对巴提供援助,但这只是他个人的印象。中巴两国之间也存在着边界划分问题,两国领土在克什米尔地区交界,这使得边界问题更为复杂。50年代中期,中国不打算立即与其他国家解决边界问题。但是,根据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耿飚的建议,中国主动放弃了对已在巴管辖下的坎巨堤地区的主权要求。该地区位于克什米尔,历史上曾经属于中国。此外,耿飚建议中国在印巴克什米尔争议问题上采取“不卷入、讲正义、讲公道”的立场。
耿飚认为,中国的这一行动表明了自己没有领土野心,使巴方对中国的政策有了新的认识。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59页。
从1955年起,苏联开始重视印度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赫鲁晓夫访问印度时,两国签订了经济合作协议。此后,苏联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苏联援印的目的也是为了冷战,赫鲁晓夫希望把印度拉到苏联一边,利用印度在亚非各国的威望,扩大苏联在亚非地区的影响。由于巴基斯坦加入了西方军事集团,苏联经常严厉批评巴的外交政策。苏联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也完全站在印度一边,这与中国在该问题上的立场是不一样的。
50年代中期。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关系也相当紧张。在阿富汗,普什图族占人口多数,他们非常关注生活在巴基斯坦并处于少数地位的普什图族的处境。阿富汗政府支持建立所谓“普什图尼斯坦”的分裂主义势力,因此民族问题使阿巴两国间经常发生争端。
“普什图尼斯坦”是指阿富汗以东、印度河以西、帕米尔以南的一片山区,这里居住着普什图等族居民。该地区根据1893年英国与阿富汗的“杜兰线”划界条约划归英属印度。1947年印巴分治,该地通过公民投票被划入巴基斯坦。但阿富汗当时支持该地的普什图族分裂势力的政治要求。
苏联自20世纪30年代就与阿富汗签订了中立与互不侵犯条约,它长期在阿富汗培养亲苏的势力。巴基斯坦认为,苏联和印度为了削弱巴基斯坦,也在背后支持“普什图尼斯坦”分裂主义的活动。
阿富汗也要求美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但是巴基斯坦反对美国援助阿富汗,理由是阿富汗政府支持分裂巴基斯坦的活动,而且同苏联关系密切。美国对于阿富汗可能过于依赖苏联的前景感到不安,但杜勒斯说,他不认为美国要加强与阿富汗的关系就需要站在喀布尔一边去反对盟友巴基斯坦。但他认为“支持阿富汗关于普什图尼斯坦的立场就是帮助分裂一个友好国家”。美国认为,苏联可能为这一分裂活动秘密提供金钱武器,这不仅损害了巴的利益,反过来还会使阿富汗进一步依赖苏联。
FRUS, 1955—1957, Vol.8, South Asia, pp.165, 172; Larry P. Goodson, Afghanistans Endless War, State Failure, Regional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Taliba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46.
尽管美国多少向阿富汗提供了一些援助,但它的犹豫和迟疑使阿富汗不得不更多地倾向苏联。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这一时期它们的南亚政策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是忽视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现实的,它们总是从冷战角度考虑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并利用南亚各国间的矛盾。
中国是印、巴、阿三国的邻国,与它们都有着未划定的漫长边界。中国对于如何在印巴之间处理好关系也颇感为难。这种因地缘政治而产生的实际利益早在50年代初期就困扰着中国,妨碍了中国与这三个国家发展合作关系。苏联同印巴两国都没有共同边界,它的南亚政策的目标相对要简单一些。因地缘政治利益不同,中苏两国在南亚政策上自然存在着分歧,只是在50年代前期和中期这一分歧没有表面化而已。
二、各国政策的调整与互动
从5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开始调整它对印度的政策。美国认为,苏联的经济援助是要将印度拉入东方集团,而它的最终目标是要控制和影响印度的政权。美国从1956年开始增加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它通过邀请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访问美国,试图增进印度领导人的亲美情绪。这一时期正好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联的国际形象与威望受到损害,尼赫鲁趁势向美国示好,拉近美印双边关系。在此以后,印度在美国南亚政策中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巴基斯坦的重要性则相对下降,美国政府开始减少计划中的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
Rashmi Jain, USPak Relations 1947—1983, p.20.
1957—1958年,巴基斯坦的政治局势出现动荡。由于党派冲突加剧和宗教因素的影响,巴基斯坦无法根据英国式的宪政体制解决其国内政治纠纷。政治局面的混乱又加剧了经济上的困难,巴基斯坦公众对于这种局面相当不满。总统伊斯坎达·米尔扎(Iskandar Mirza)担心反对党在大选中获胜,于是联合军队力量,在1958年春宣布废除宪法,解散议会,并任命了陆军司令阿尤布汗为首席军法执行官。不久,阿尤布汗宣布总统米尔扎辞职,他接管全部权力。
FRUS, 1958—1960, Vol.15,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p.668.
新政权对巴基斯坦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作了一系列改变,这些行动推动了巴的国内经济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阿尤布汗本来就具有亲美思想,他也试图在对外政策方面进一步采取追随美国的方针,扭转美国越来越重视印度的势头。1959年3月,美巴两国还签订了新的双边合作协定,美国承诺在发生外部对巴侵略的情况下美国将会采取行动,包括使用军事力量。
P. L. Bhola. PakistanChina Relations, Jaipur: RBSA Publisher, 1986, p.78.
1959年春,在发生西藏达赖集团叛乱事件以后,中印关系开始紧张。1959年夏天,中印两国又发生了边境武装冲突。印度社会上出现了反华的气氛,印度政府调整其国防政策,打算将布防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一部分军队调集到中印边境。阿尤布汗政府也开始向印度示好,表示重视同印的关系。8月,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巴基斯坦还有人批评中国,认为中国是入侵者,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承担维持克什米尔国际边界的责任。
FRUS, 1958—1960, Vol.15,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p.193; P. L. Bhola. PakistanChina Relations, p.98.
在中印关系出现紧张以后,美国政府非常兴奋,认为今后可以将印度拉入西方集团。同时他们也担心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1959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分析报告中说,中巴关系不可能发展,“巴基斯坦过去显然有同中国调情的想法,即利用中共作为对抗印度的力量”,但美国报告认为,巴基斯坦军人领导集团现在已经认识到了危险,他们已经拉大了同中国的距离。美国可以更加积极地同印度改善关系,不必过于担心受到巴的牵制。
FRUS, 1958—1960, Vol.15,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pp.718721.
但偏向印度而不引起巴基斯坦的反对是不可能的,美国不得不另辟蹊径。1959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研究部门认为,“中国力量正在迅速增长,苏联也在强化它在南亚的经济攻势,这似乎有可能在今后十年中进一步威胁到自由世界在亚洲的利益”。印巴两国的不稳定局势会导致这两国落入共产主义的影响之下。因此,研究报告建议,美国“要使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巴两国理解,对他们的安全威胁不是来自南亚,而是来自不断增强的中苏力量”。
FRUS, 1958—1960, Vol.15,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pp.2946.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艾森豪威尔政府表示要支持印巴两国进行合作,对中国进行“联合防御”。
美国的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巴基斯坦政府的赞成。阿尤布汗在1959年9月访问了印度,他的目的是要说服印度同意解决克什米尔问题。阿尤布建议,两国在南亚建立共同防御计划,减少各自在印巴边境上的军事力量,使他们可以将安全关注集中到北部边境地区。很显然,阿尤布汗是想利用印度面临军事上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推动印度按巴基斯坦的条件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不久,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到达南亚访问,阿尤布汗再次向美国提出印巴两国应共同防御以对付中国,这样就能使巴、印、阿三国的军队从相互对立中解放出来。阿尤布汗的这一建议赢得了艾森豪威尔的好感和支持,但尼赫鲁对巴方的这种计划根本没有兴趣。
FRUS, 1958—1960, Vol.15,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pp.782783.
1961年,美国民主党的肯尼迪(J. F. Kennedy)政府上台,这届政府准备在第三世界更积极地同苏联进行争夺,为此,他们更为重视印度的地位和作用。经过阿尤布汗的努力,肯尼迪同意继续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但是由于中印关系继续恶化,印度得到美国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使巴开始意识到,它依靠美国来平衡印度的力量的想法已经不容易实现了。
巴基斯坦在1959年10月曾经提出“标定”巴占克什米尔与中国新疆之间的边界的可能性,随着他们对印度的立场越来越失望,巴开始采取措施以改善它同中国的关系。1961年2月,巴基斯坦政府正式向中国提出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1961年2月,阿尤布汗在伦敦表示,巴基斯坦将在联合国支持接纳中国的议案。根据巴方向美国的通报看,巴基斯坦原来打算先解决部分有争议的地区。但稍后它觉得应当解决从阿巴边界到克什米尔印巴停火线的全部边界问题。巴基斯坦的打算是以实际控制为基础确定边界,使双方军队不会进入对方一侧,巴方准备先把法律问题,也就是边界最后划分问题搁在一边。
FRUS, 1961—1963, Vol.19, South Asia, pp.2829.1962年2月,中国认为,比较实际的方法是先对共同边界达成一个临时性的协议,同时在协议中规定,在巴印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后再签订正式条约。
显然,这是一个实际的做法,巴方也许不想因为同中国签订正式条约而受到美国的指责。
但是,中国并没有马上同意与巴谈判边界问题。中国显然对前一时期的中巴关系并不满意。从1957年起,中巴关系开始恶化,巴总理苏拉瓦底(H. S. Suhrawardy)在访问华盛顿时一面奉承美国,一面攻击中国“侵略性的扩张主义”立场,威胁了亚洲的和平与自由。巴基斯坦不仅加入“中央条约组织”,而且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采取反华反共立场,它还在西藏问题上指责中国。1959年7月,中国曾就巴在台湾和联合国问题的立场向巴方提出过抗议,7月23日,《人民日报》批评巴基斯坦的亲美政策,指出巴允许美国运用军事力量和在巴建立军事基地,这是对苏、中、印、阿富汗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严重威胁。
Anwar H. Syed, China and Pakistan: Diplomacy of An Entente Cordiale,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4, pp.7273;《人民日报》,1957年7月23日,转引自林良光等:《当代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中国对巴提出的南亚联合防御的计划更是不满。
1960年春,毛泽东曾经考虑过英、法、中、苏是否可能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性。1960年夏以后,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中印谈判又没有任何进展。这使中国不得不对世界力量的组合重新进行审视。从1962年初开始,毛泽东多次重提“中间地带”理论。他强调“中间地带国家”是各种各样的,其“性质也各不相同”。他认为,这些国家,包括英法,都受到美国的欺侮控制,“他们同美国有矛盾,日子很难混,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稍早,1961年9月,周恩来也使用了“中间地带”这个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423、48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20页。
从他们的观点变化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正在走出“两大阵营”的理论模式,试图为中国对外政策寻找新的指导方针。
1961年12月13日,中国外交部长陈毅会见巴基斯坦新任大使拉希迪说,中国愿意同巴发展友好关系,但中巴关系存在着三个障碍:巴在联合国投票中反对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巴领导人宣传搞“印巴联防”以及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不公正指责中国。陈毅说,巴参加军事集团,双方有个谅解,那就更好。陈毅的讲话表明,在“中间地带”的理论影响下,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中国已不把巴参加西方军事同盟看作发展双边关系的障碍。两天后,巴在联合国对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议案投了赞成票,而对美国阻挠中国重返连联合国的议案投了弃权票。1962年2月,中国正式表示愿意同巴基斯坦谈判解决边界问题。3月,巴方向中国提交备忘录,表示巴参加军事条约只是为了防卫而不是针对中国。5月,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军队与政府官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对巴基斯坦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在不久后召开的国民大会上,一些与会者批评西方国家没有支持巴基斯坦在国际事务上的立场,有人提出应当与意识形态不同的中国和平共处。
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8586页;P. L. Bhola, PakistanChina Relations, pp.8290.
实际上,巴政府已经对前一段亲西方的对外政策感到不满意了。尽管同西方的结盟为巴基斯坦带来了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巴基本的对外政策目标——解决克什米尔争端——却没有进展。1960年,巴方曾经将这一问题带上联合国讨论,令他们失望的是,美国等盟国并没有积极支持巴基斯坦的立场。有关的讨论也没有产生巴想见到的后果。巴舆论开始批评美国没有向印度施加足够的压力。
巴基斯坦的对外政策也受到了苏联的压力。50年代后期,美国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建立了电子情报侦察基地,美国U2型侦察机也从这里进入苏联和中国领空进行侦察。苏联先是认为这里是美国火箭基地,后来才了解它的用途。1960年5月,从白沙瓦起飞的一架U2飞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美国飞行员被俘。
这一事件使巴基斯坦面临困境。赫鲁晓夫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专门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大使拉到一起,说道:“白沙瓦在哪儿?我们已经在地图上特地把它用红线圈起来了。”当巴大使说它位于巴基斯坦北部后,阿富汗大使却故意说白沙瓦是在“被占领的巴克图尼斯坦”,这显然是普什图分裂运动的说法,但赫鲁晓夫却对阿富汗大使说,“对,它是在被占领的巴克图尼斯坦,你可以把这一点告诉你的政府。”
FRUS, 1958—1960, Vol.15,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pp.810811.
面对苏美两国的冷漠与压力,巴政府进一步意识到中巴两国具有加强合作的可能性。
中国已经敏感地察觉到了南亚国际形势中的地缘政治特点,中国开始认识到,南亚的国际局势不一定受到冷战格局的支配。1962年5月,周恩来对巴基斯坦大使拉希迪说,国家无论大小都要友好,中巴友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巴基斯坦同邻国的纠纷要直接解决,无须第三国介入和插手。”周恩来说,如果巴能降低同周围国家的紧张气氛,腾出手来搞建设,这有利于国家独立和人民幸福。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463页。
1962年10月12日,就在中印边界形势相当紧张的时候,中国和巴基斯坦宣布双方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已经进行。这一行动使印度拒绝同中国谈判的政策更显得不明智。几天后,中国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印军发起自卫反击作战,遭到打击后的印军全线溃败。尼赫鲁在惊恐之下向美国紧急求救,并要肯尼迪总统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让巴做出不利用印度困难形势的书面保证。10月27日,阿尤布汗总统对美国大使说,巴不会采取阻碍印度对华作战的行动,但是他不会接受对尼赫鲁作书面保证的要求,因为这对印度改变其军事局势毫无意义。针对西方的惊慌,阿尤布·汗指出,中国的行动不像要跨越“麦克马洪线”大举进攻印度本土,也不像要挑战印度的基本国家安全。
FRUS, 1961—1963, Vol.19, South Asia, p.353.
巴基斯坦政府对西方大规模地向印度提供紧急军事援助非常不满,认为美国夸大了中印边境地区的军事形势,在援印问题上违反了要同巴事先磋商的承诺。11月5日,阿尤布汗向美国指出,中国的行动不是大规模的入侵,从中国采取行动的时间和地点看,中国只是要打一场有限战争。印度的失败是它的对外政策造成的后果,印军的80%还部署在印巴边境地区。
FRUS, 1961—1963, Vol.19, South Asia, pp.369375.
面对巴基斯坦的强烈批评,肯尼迪政府不得不向巴保证,它会推动印度谈判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美国这一保证的目的是要换取巴接受美国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
11月20日,中国宣布在中印边境地区全面停火和撤军,中国还宣布将从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以避免发生进一步的冲突。巴基斯坦舆论对中国的自卫反击行动给予很高的评价。其实,巴舆论早就谴责印度的军事冒险行动,认为印度政府应当对这一冲突负责。
P. L. Bhola, PakistanChina Relations, pp.9192.
1962年12月28日,中巴双方宣布,两国关于边界划分的谈判已经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实际上,中巴两国在6月份已开始谈判,由于中印冲突的原因,谈判的进程明显加快了。巴方加快谈判速度并要求在此时宣布这一消息有着重要的原因。在中印边界战争发生后,美国向印度施加压力,要求印度同意与巴基斯坦谈判克什米尔问题。为得到西方的援助,尼赫鲁当时不得不同意举行谈判。巴方知道,刚刚蒙受了军事失败的尼赫鲁很难接受巴方的条件。但以中巴协议作为后盾,巴方在谈判中就会具有战略上的优势地位。如果印方拒绝巴基斯坦的条件,巴就可以此为据,阻止西方向印提供援助。从中国方面看,中国也愿意早日签订协议。周恩来认为,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进行谈判,“印度把肥沃的克什米尔给巴基斯坦,转而抢夺我们贫瘠的不毛之地”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许剑波译:《前苏东国家新披露的有关1959—1962年中印关系的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第8期,第2829页。
对中国来说,早日结束谈判可以堵住美国和印度利用巴基斯坦的路。这一方针存在着明显的地缘政治的考虑。
中巴边界协议在1963年3月正式签署,边界全线基本按传统习惯线,即沿穆士塔格—喀喇昆仑山脉的岭脊定界。根据巴基斯坦方面的资料说,中巴边界共有3400平方英里的有争议领土。经过双方谈判,巴方得到了1050平方英里的土地,其中包括750平方英里原先由中国控制的土地。中国得到了2050平方英里的土地,其中有1050平方英里是巴方原来要求的。巴方得到了喀喇昆仑山7个山口中的6个,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巴方称K2峰)的四分之三地区,而且没有失去巴方控制的土地。巴否认了印度说它丢失了大片土地给中国的指责。
P. L. Bhola, PakistanChina Relations, pp.102103. 巴方的资料显然不太精确,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方面没有披露有关中巴边界谈判的细节和领土方面的具体内容。
中国对中巴边界协议也是满意的。1962年10月26日,周恩来对来访的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说,中巴谈判的气氛是友好的,态度是积极的。巴基斯坦在边界问越上的立场是正确的。“我们认为巴基斯坦虽然属于一个侵略集团,但是巴基斯坦在与我们谈判过程上,并没有听从美英的指挥。”周还说,“印度虽然声称它不属于侵略集团,但是它却按照美国人的腔调说话。”
许剑波译:《前苏东国家新披露的有关1959—1962年中印关系的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8期,第2729页。
周的观点表明,中国的南亚政策已经实质性地突破了集团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
中巴边界位于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两国的边界协议因此具有非常复杂的战略意义。由于印度对中巴边界协议持否定立场,巴基斯坦领导人意识到,他们可以利用由此而产生的地缘政治效应。巴外交部长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1963年7月在议会中说:“现在,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攻击已不再只涉及巴基斯坦的安全和领土完整。印度对巴的攻击还涉及亚洲最大的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安全。……因此,一个屈从的巴基斯坦或一个被打败的巴基斯坦不仅是一个我们被消灭的问题,而且对其他亚洲国家,特别是亚洲最大的国家也构成了严重威胁。”阿尤布汗总统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西方舆论甚至怀疑中国与巴基斯坦达成了某种秘密协议。布托在10月份对媒体澄清说,如果印度侵略巴基斯坦,巴可以期望其他国家的帮助,在这件事上中巴之间“没有保证,也没有协议……但是有一种强有力的假设”。
Khalid G. Sayeed, “Pakistan and China,The Scope and Limits of Convergent Policies” in Policies toward China: 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 ed. By A. M. Halpern,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65, p.246.
从1958年至1962年,中、巴、美、印各方都进行了政策调整。这些调整的结果是,中印关系走向恶化,肯尼迪政府试图加强它在南亚的影响,采取利用印度来遏制中国的政策。与此同时,美巴关系有所疏远,中国开始与巴基斯坦形成互利的双边关系。尽管美国政府加大了对这一地区的“投资”,但南亚的现实离它的目的还有很远的距离。
三、冷战和地缘政治——谁更优先
进入1963年,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合作也有了迅速发展,两国在这一年中还签署了贸易协议和航空协议。前者使双方相互获得了最惠国待遇,中国成为巴基斯坦棉花的主要出口市场。后者建立了上海—广州—达卡—卡拉奇的空中航线,对中国来说,这是同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第一条商业航线,它不仅具有商业价值,而且也具有突破美国封锁的政治意义。美国政府对这个协议公开表示不满,肯尼迪总统对巴
基斯坦驻美
大使说,美国相信中国的威胁是巨大的,无论是从现时还是从潜在的角度看都一样,印度的垮台不符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巴基斯坦的利益。肯尼迪强调:“共产党中国必须在整个亚洲受到遏制。”他还指责巴基斯坦很少考虑美国的这种关注。巴大使辩解说,中巴航空协议只是出于商业考虑,因为英国政府阻止巴基斯坦飞行香港的航线。在阻挠不成的情况下,美国下令暂停为达卡机场扩建而提供的430万美元的援助项目。
FRUS, 1961—1963, Vol.19, South Asia, pp.618619; P. L. Bhola, PakistanChina Relations, p.114
中印边界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内部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美国应当向印度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以防止印度完全投入苏联怀抱。美国不必在意巴基斯坦的反对。强烈主张这一观点的人有美国驻印大使、总统的密友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南亚事务官员罗伯特·科默尔(Robert Komer)。另一种意见认为,美国不能忽视与巴基斯坦的联盟关系,不能把巴逼到中国一边去。支持这一观点的有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近东及南亚事务助理国务卿菲利普斯·塔尔博特(Phillips Talbot)。这两种意见看起来有一定的分歧,但实际上都是从冷战的视角思考问题的,他们的区别只在于美国应当更注重防范中国还是更注重对付苏联。肯尼迪处于两种意见之间,一时也无法做出决断。
Robert J. McMahon, The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and Pakist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4, pp.298299.
1963年11月,肯尼迪被暗杀。巴基斯坦外长布托到华盛顿参加葬礼。继任的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在会见布托时警告说,拟议中的周恩来对巴基斯坦的访问会在美国引起严重的“公共关系”问题,而且还会在国会引起不利的反应,危害到以后美国对巴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布托为巴基斯坦的对华政策进行了辩解,他说巴因为印度军事力量增强而被逼到了墙角,改善对华关系只是一种保护措施。但是,约翰逊完全不能理解巴方的地缘政治考虑,认为这种政策冒犯了美国的利益。布托本来要向新总统转达阿尤布汗的一个极为机密的口信,即巴保证“绝对不会背弃”同美国的联盟,然而,面对强硬而冷淡的约翰逊,布托不得不放弃转达口信的打算,因为那很可能会被美国看作是软弱无力的自我辩白。
Robert J. McMahon, The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 pp.306307.
12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Taylor)到印度和巴基斯坦访问。泰勒南亚之行的主要目的是要稳定印巴两国同美国的关系,减少它们对美国可靠性的怀疑。泰勒在巴基斯坦说,美国将给印度提供它所需要的援助,巴没有必要担心印度的威胁。中国才是南亚真正的威胁。他再次指责巴准备接待周恩来访问,并且用此事可能影响援助来威胁阿尤布汗总统。阿尤布汗说,美国不应对中巴关系纠缠不放,巴的动机“只是与一个潜在的敌人关系正常化”。他还反驳说,美国自己也同苏联保持关系,并接受苏联官员到华盛顿访问。
FRUS, 1961—1963, Vol.19. South Asia, p.718.
对于印巴军事合作问题,阿尤布汗认为,印度很可能在今后同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印度只要一个“环印度洋”,而把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留给中国。他认为印度不会参加集体和共同的防御计划。此时的阿尤布汗已经决心加强同中国的关系,他对美国的调解作用也不抱什么希望了。
由于美国在越南面临着越来越麻烦的局势,泰勒此行的另一目的是要了解巴印两国对越南问题的看法,以及美国能否在越南得到他们的军事支持。泰勒提出,巴基斯坦应继续承担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义务。美国还试图将第七舰队的舰只派驻到印度洋地区,泰勒希望巴参加“印度洋特遣部队”的计划。他说,这是一个“没有核心任务”的安排,它未来可能要面对印度洋东西南北各个地区的紧急情况。但是阿尤布汗对这一没有明确目标的计划表示怀疑,认为为什么该计划应当知道和在哪里作战。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要试探巴的态度,而访问的结果是令泰勒失望的。
FRUS, 1961—1963, Vol.19, South Asia, pp.710713.
泰勒访印后表示,美国军方批准了一个为期5年、每年向印度提供 5000 万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但是泰勒也认为,美国必须为此附加条件,以保证印度有继续发展经济的能力,并且愿意同美国“合作遏制中国”。他建议在印度制订出5年军事计划后,美国才最后确定援助计划。但在以后的时间中,约翰逊政府对印度的表现越来越失望,因为印度不仅拒绝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让步,而且它也不愿在印巴“联合防御”方面进行合作。
FRUS, 1961—1963, Vol.19, South Asia, pp.45, 1415.
印度需要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它虽然没有公开批评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的行动,但是,它一直强调美国不能依靠武力解决问题。既然印度不可能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全面支持美国,美国政府向印度提供援助的热情也就大大降低了。
Ramesh Thakur, Peacekeeping in Vietnam, Canada, India, Poland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Edmonton Alta: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Press, 1984, pp.211212.
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在继续调整。1963年9月,毛泽东指出,美苏两国在国际上“到处碰钉子”;“中间地带有两个”,它们同美苏“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1964年1月,毛泽东还指责美苏“想统治全世界”。他还有了“中间地带”具有既反美也反苏的性质的看法,这一看法是新的发展,它表明中国非常需要巴基斯坦这样的地缘性的盟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6509页。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领导人频频出访亚非国家。1964年2月,周恩来在拉瓦尔品第对阿尤布汗说:“世界在变化,力量在改组,我们要冷眼观局势,在外交中多交换看法。”周恩来说,无视亚非新兴国家的独立意志,企图抹杀它们的地位是必然要碰壁的。周恩来的访巴公报还声明,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继续持中立的立场,但中国接受了巴基斯坦在这一问题上的提法,即强调要“根据印巴两国保证过的、符合克什米尔人民愿望”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一立场表明,中巴两国在战略上有了更紧密的合作。显然,毛泽东关于“大分裂、大动荡、大改组”的观点,要“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观点,以及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已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这些思想成为中国对外政策首先在南亚地区突破意识形态束缚,把地缘政治摆在主要位置上来考虑的深层原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621623页。
为了能够在战略上与中美两国都具有稳定的关系,巴方一直试图调解中美关系。阿尤布汗总统后来说,他曾经应美国的要求,与到访的周恩来长时间地讨论了中美关系,并且扮演中间调解的角色。但是美国政府却对此加以否认。然而美国的报刊报道,美国政府曾经要巴、英、法三个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捎话给中国说,美国不会在东南亚对中国让步。显然,这一时期巴政府的确为缓解中美关系作过努力。
P. L. Bhola, PakistanChina Relations, p.116.
阿尤布汗本来应邀在1965年4月访问华盛顿。在此之前,即3月,中国政府也邀请他访问北京。阿尤布·汗在同刘少奇、周恩来会谈时说,美国想让印度在军事和经济上成为对抗中国的力量。美国还向巴施加压力,因为巴是美国这一战略的障碍。中国领导人向他保证:如果印度入侵巴基斯坦的领土,中国将坚定地支持巴基斯坦。毛泽东也会见了阿尤布汗,毛泽东说,中国和巴基斯坦可以相互信任,因为我们都不会损害对方。他指出,美苏正在达成某种谅解,以便实施针对中国的遏制政策。毛泽东说,在南亚“我们将同意你,而不是同意夏斯特里”(L. B. Shastri,当时的印度政府总理)。外交部长陈毅也对随访的巴方记者说,中国将会同侵略者战斗,“如果我们的朋友被消灭了,我们怎么能存在下去?”这句话的地缘政治考虑也是非常明显的,他似乎在回应1963年7月布托的讲话。
G. W. Choudhury, India, Bangladesh, and the Major Powers, Politics of Divided Subcontinent, London: The Free Press, 1975, pp.183185.本书作者G. W. Choudhury利用巴基斯坦外交部的资料进行了研究,此书是研究中巴关系的重要著作;John W.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196.
1965年4月1日,周恩来在出访途中在卡拉奇与阿尤布汗进行了会谈,周恩来请阿尤布汗捎话给美国政府,表明中国支持越南的坚定决心。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15、723页。
显然,中国政府不仅没有阻止巴基斯坦同美国保持关系,而且愿意利用这一关系同美国进行沟通。阿尤布汗在4月上旬还去了苏联访问,而且受到了热情接待。约翰逊总统对巴基斯坦与中、苏加强关系,以及印巴关系的紧张非常恼火,他推迟了阿尤布汗的访问。这就使得巴基斯坦对美国更为不满。
巴印两国关于克什米尔的谈判一直没有取得进展。对此,巴基斯坦政府非常失望。1965年,巴基斯坦试图帮助印控克什米尔人民“起义”,希望以此方式推动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一些巴基斯坦“自由战士”进入了巴印克什米尔停火线印方一侧,导致印控地区出现了骚乱与冲突。印方则进行镇压,逮捕了印控区的一些穆斯林领袖。双方在边界上的小规模冲突也不断发生。4月,小股巴基斯坦军队越过边界并开展游击行动。虽然双方在6月份签订协议,承诺和平解决冲突,但是协议没有真正被遵守。8月,随着更多的巴军进入印控克什米尔,两国的军事冲突加剧了。美苏对战争的前景非常担心,他们怀疑中国会对局势进行干预,认为中国的影响可能因此而增加。
Shinn TahirRheli,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The Evolution of An Influence Relationship, New York: Preaedger, 1982, pp.1921.
9月4日,陈毅到达卡拉奇。他向布托外长指出,中国愿意尽最大努力支持巴基斯坦。两天后,印度军队大举进攻,印军直接越过两国的国际边界进入巴基斯坦本土作战,巴基斯坦的安全面临严重的威胁。面对巴方的求援,美国政府非但没有给这个盟国以支持,而且宣布停止向巴印两国提供军事援助。它只是表示愿意支持联合国采取调解行动。苏联一方面支持印度的立场,另一方面表示愿意帮助两国实现和平,苏联总理柯西金邀请印、巴领导人去塔什干会谈。只有中国表示完全站在巴基斯坦一边。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印度对巴基斯坦进行赤裸裸的侵略。同一天,周恩来会见巴驻华大使说,中国正在观察局势的发展,并考虑在必要时采取什么措施。他要求巴方做出两点保证:(1) 巴基斯坦不会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屈从于任何有利于印度的解决方案;(2) 巴基斯坦也不会屈从于美苏两国和联合国为达成这种解决而施加的压力。阿尤布汗很快向中国做出了这些保障。8日,中国向印度递交照会,要求它撤除在中国—锡金边界中国境内的工事,立即停止军事入侵行动,否则就要对严重后果负责。
G. W. Choudhury, India, Pakistan, Bangladesh, and the Major Powers, p.189.
美苏两国的“中立”鼓舞了印度,印军毫无顾忌地在巴基斯坦迅速推进。9月12日,巴政府告知中国,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中国的“军事干预可能是必需的”。与此同时,印度政府对中国的警告却不加理睬。印度还说,它只准备有条件地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决议。9月15日,中国向印度发出强烈抗议,指责印度在中国—锡金边界违反停火协议修建大批工事,而且印军还不断越境侵扰中国牧民,掠夺中国牧民的羊群等财物。中国要求印军在三天内撤除所有工事,同时归还抢走的财物。这份被视为“最后通牒”的抗议立即震动了世界,国际舆论猜测中国将在中印边境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政府不得不做出军事上的反应,向南亚增派军队。同时它也加快了在联合国的调解行动,印度政府虽然否认它在中锡边界有越界行动,但它又表示愿意对中国的指责进行调查,说如果有军事设施可以拆除。在中国的压力下,印度在19日不得不告诉美国,它愿意接受联合国的决议,立即结束与巴基斯坦的冲突。
FRUS, 1964—1968, Vol.25, South Asia, p.422.
鉴于联合国的调解行动需要时间,中国在9月17日宣布将把“最后通牒”的时间延长三天。外交部原来只准备延长一天,毛泽东亲自干预,认为延期一天太短,可改为“三天之内”。中国领导人在这些时间里密切关注着局势发展,同时也准备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美国密切关注中国的动向,五角大楼认为,中国在中印边界没有增加军事力量,中国还有后勤方面的困难。美国军方还认为,越南战争已使得中国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因此中国不会在南亚采取大规模的行动。22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宣布同意接受停火,印军将从巴基斯坦及巴控克什米尔撤军。第二次印巴战争结束了。
FRUS, 1964—1968, Vol.25, South Asia, pp.392395, 4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461页。
中国的行动对这场战争的结束有着直接和重要影响。经过这场战争的考验,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更加牢固,两国在南亚国际关系中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准同盟的关系。
四、结论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的目标是将南亚纳入冷战格局中去。到50年代末,美苏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出现了竞争与缓和并存的局面。但中美关系却依然紧张,中国被认为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威胁,美国希望构筑针对中国的南亚“联合防御计划”。到1965年,美国甚至认为美苏两国在南亚的利益是重叠的,它具有平行的政策和路线。约翰逊政府甚至愿意让苏联为印度提供援助,认为这可以使美国卸掉一些包袱,并可以免遭巴基斯坦批评。
Selig S. Harrison, “Troubled India and Her Neighbors,”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965.
美国的南亚政策是以冷战考虑为出发点的,但结果遭到了南亚地缘政治现实的无情嘲弄,约翰逊政府在印巴两国都得不到信任。这表明它已走入了地缘政治与冷战思维纠缠在一起的迷宫之中。
苏共20大以后,苏联一直想把印度纳入其全球战略,以此抵消中苏分裂而产生的战略和政治方面的损失。苏联以为它拉拢印度就占有了南亚地区的最大优势。苏联对巴基斯坦的敌视,以及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表明,它宁可看到美苏控制南亚的局面,也不愿看到中国安全地位的改善。苏联政策的这一倾向为它树立起一个持久的敌人——巴基斯坦,它后来在阿富汗的失败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
中国在60年代前期大幅度地调整了南亚政策。中国与印巴两国接壤,中国的国家利益要求南亚地区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原希望维持边界地区的安定,并在印巴之间保持中立。在美国与印度相互利用,苏联还支持印度采取沙文主义对华政策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有同巴基斯坦站在一起。中国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和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特点,成功地恢复了南亚地区的力量平衡。
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对外政策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国家安全方面过高估计了外部的威胁,致使后来出现了“四面出击”的问题。但是,就南亚局部而言,中国却较早摆脱了冷战思维的模式。中国领导人以“中间地带”理论为基础,建构了一种代价不大但效果持久的政策,不仅有效捍卫了自己的利益,而且限制了美苏在南亚国际关系中的影响。
下篇
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下篇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道德原则
*
*本文原发表在沈宗美先生主编的《理解与沟通——中美文化研究论文集》一书中,该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
美国政治家很少像欧洲政治家那样,常常直言不讳地宣布,其对外政策只是建立在现实政治(Realpolitik)或现实物质利益之上的。相反,历届美国总统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他们对外政策中的道德原则。新闻界律津乐道地对此加以评论解释,学术界也不断对这些原则进行探讨辩论。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强烈的道德色彩可以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鲜明特点。今天,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正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对它对外政策中的道德原则的意义作进一步的探讨,无疑有助于我们对这个超级大国的对外政策有更多的了解。
本文论及的道德原则是指那些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形成与实施产生过或试图产生过指导性作用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一般由一组基本价值观念所构成。而这些价值观念的来源是复杂和广泛的。它们可能来自宗教信念或哲学思想,可能来自社会伦理或文化传统,也可能来自民族或地缘观念。应该说道德原则与实际利益有密切的关系。实际利益要求变化时,旧的道德原则会淡化,新的道德原则会萌发。当然也有一些道德原则始终发挥着作用。而一些淡化的原则,在条件得到满足时也可能重新被人们所重视。
目前,强调道德原则已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要素。在探讨这种强调的实际作用之前,弄清这一现象的起源是十分必要的。
一、强调道德原则的历史原因
进入17世纪后,欧洲新教徒在向北美洲迁徙时,抱有寻求宗教信仰自由与经济出路的双重目的。马克斯·韦伯曾详细论述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赢利精神是如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赚钱获利,对新教徒来说,不仅是为了满足物质上的需要,而且其本身就是符合新教伦理道德的。新教的这祌世俗特点,为它的伦理观念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提供了有利条件。早在美国建国之前,北美殖民地社会生活中一直充满着强烈的宗教色彩,这种色彩当然也反映在政治生活中。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1776年说到,移民们定居美洲是上帝的辉煌计划的开始,它意在启发全人类,并要解放那些尚在受奴役的人民。当独立革命发生时,美国人相信,创立新国家是上帝的旨意,他们脱离英国而独立完全是正义的。在立国之初,“使命”这一宗教概念就已深深地印刻在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中。他们相信,作为上帝的选民,他们负有拯救旧世界的光荣使命。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命观念虽然发生了一些演变,如在19世纪中期,它派生成为一种“天定命运论”,为美国的扩张主义提供支持。但作为一种基本价值,它却长期影响着美国对外政策。它使美国人在领土扩张,在输出美国的社会生活方式或价值体时都有一种自以为是的使命感。E. M. Burns, The American Idea of Mission: Concepts of National Purpose and Destiny,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7, p.11; Arthur A. Ekirch Jr., Ideas, Ideal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A History of Their Growth and Interaction,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6, pp.22, 3839;被认为是民主派的美国革命时期领导人托马斯·杰弗逊同样认为美国制度应该扩大到整个南北美洲大陆,Frederick Merk, Manifest Destiny and Mission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1966, p.9.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对独立前后的美国思想界有重大影响。洛克强调人的自然权利,他认为人在组成国家时交出了自己在立法、司法等方面的某些权利,但他为自己保留了生活、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从这点出发,洛克反对强大的专制政府。对过去深受欧洲各国封建统治压迫和剥削,现在又对英国殖民地政策深为不满的北美洲人来说,洛克的思想无疑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北美逐渐演变为人们有权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的原则,成为统治者的权利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的原则,这些原则成为独立革命时期发动群众的强大思想武器。独立战争的胜利使美国人相信,他们已经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自然权利,因此他们也可以以此来衡量旧世界。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常识》中写道:“旧世界遍地盛行压迫”,自由到处遭受迫害,他要美国人把北美洲变成自由人类的庇护所。正是源于这种对建立在“自然权利”之上的原则的坚定信念,在文化方面本来一无所有的美国人,才能具有一种自己代表人类未来希望的想法,才会有那种要输出自己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不灭的热情。美国人当时同情法国大革命,支持欧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出于这种原因。Roger Burlingam, The American Conscience, 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57, p.121;托马斯·潘恩著:《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7页。
移民们冒着生命危险渡过了大西洋,经过他们胼手胝足、生生不息的辛勤劳动,一片荒芜的土地逐渐发展成具有较高生活水平的地区。这种巨大的社会进步,对于建国时期的每一个美国人来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巨大的进步和巨大的潜力使他们感到,北美社会的飞速发展不仅来自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而且来自他们道德和精神方面的优越。康马杰(H. S. Commager)说过:“对于美国人来说,他的国家的道德优越是不需证明的。”H.S. Commager, The America Mi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p.11.乔治·华盛顿要求他的国人表现出真正的美德,从而成为全人类的榜样的那种想法,正是这种优越感的典型表现。
自我优越、自以为是的另一种表现是对旧大陆的蔑视。一个在1790年访问美国的欧洲人观察道:“美国人相信,除了他们自己以外,世界上没有人是有智慧的,欧洲人的聪明、想象力和才华已经衰退了。”H.S. Commager, The America Mi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p.11.至于旧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在美国人看来是既肮脏又可怜,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甚至说“印第安人也比欧洲人幸福”,因为欧洲社会“已被分为两个阶级,即狼和羊”,他认为弱肉强食是欧洲的“真实图景”。Thomas Jofferson, The Life and Select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ed. by A. Kock and W. Pede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p.412.如果把这些话与他对美国社会的热情称颂联系起来,那么美国人当时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就基本上很明了了。
独立之初的美国人是从道德角度来看外部世界以及他们自己国家的,也是从同样的角度来看待这两者关系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做法如何能长期延续下来,因此有必要了解一些美国人的文化心理。康马杰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指出过,美国人不喜欢理论和思辨,“他躲避那些深奥难懂的政治哲学和行为哲学就像健康人躲避吃药一样”。但是,美国人能简化那些有用的哲学思想。美国人几乎一致相信一种把上帝和莱布尼茨(G.W.Leibnitz)的名言——一切事物都被普遍和必然法则所统治——撮到一起的观点。他们相信,存在着普遍的宇宙进程。上帝的存在就体现在自然和普遍道德秩序的每一个合理的创造之中,他们把自己的道德习惯与天地万物的道德结构联系起来,承认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道德法则的普遍的束缚力量。这种简单但实用的文化心理,使道德在美国社会生活中起到了极为重要和普遍的作用。这已经成为美国的传统,即用自己的道德标准衡量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并企图让别人也接受这种衡量的后果。H. S. Commager, The American Mind, pp.2830.莱布尼茨的思想是通过自然神论被引入美国文化中的,与欧洲的某些自然神论不同,美国的自然神论者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见 Harvey Wish, Society and Thought in Early America, New York, David Mckay Co.,1950, pp.143145.无疑,别人是很难或者说是无法接受这种后果的,因此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中,美国人感到既然他们不能使别人接受这种看法,他们就宁愿“孤立”。但到了20世纪,随着美国力量和地位的上升,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迫使别人接受了。
二、道德原则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
在对外政策中强调道德原则,不仅仅是出于政治文化心理。应该指出,这样做对美国是有高度实用价值的。托克维尔(A. de Tocqueville)曾经在他著名的《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对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很困难的,因为外交活动要求保密和私下交易,而这一点在民主制国家是难以真正做到的。托克维尔说,这是民主制国家的“天然缺陷”。Kenneth W. Thompson,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6667.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难以保密是实,但也易于在公开方面做文章,强调道德原则,在外交中常常是一种名利兼收的好办法。
首先,强调道德原则是协调解决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矛盾和冲突的重要途径。在美国,各种力量的竞争是其社会行为的基本方式,因此社会也需要具有一种将竞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机制,以求得社会的基本稳定。美国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经常发生辩论,其实这是利益冲突在理论层次上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通德原则就是一种防止冲突扩大,调整利益分配的机制。要使冲突各方妥协,其方案就必须包含超越物质利益的高尚道德性。19世纪早期,对于美国是否要全力插手拉丁美洲事务,将欧洲在拉美的势力范围全部剪除,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论。最后美国政府发表了“门罗宣言”,在维护拉丁美洲独立和自由的华丽语言之下,它既表示了要排斥欧洲势力的决心,又小心地避免与欧洲势力马上进行直接对抗。这使美国能集中力量开发西部地区,并把向拉美地区的扩张作为长久之计来处理。又如19世纪末期在对华政策中提出的“门户开放”问题,从理论上看,它强调的是“机会平等”这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原则。但实际上,这一方针既迎合了当时东部扩张主义势力立即投入与其他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要求,又满足了中部和西部势力扩大海外贸易但不愿增加军费的愿望。
“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原则中宣扬的独立、自由、机会平等和自由竞争等价值,都是美国人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对这些原则的强调和小心地利益权衡结合在一起,使在这些原则指导下产生的对外政策得到了各方面的长期拥护,因而也维护了整个统治阶级的团结。美国对外事务权势集团的核心人物,曾经为从杜鲁门到里根总统服务过的保罗·尼采(Paul Nitze)就认为:“伦理和道德的主要任务是,对非常复杂的个人-集团结构的各个部分间,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价值体系各个部分间的潜在冲突的解决,提出指导的路线。”Paul Nitze, Recovery of Ethics, in Moral Dimens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ed. by K. W. Thompson,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1984, pp.5556. 他的意思是清楚的:不同的集团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又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与之相联系,道德原则的任务是要解决多种利益间和各种价值间的冲突。
道德原则在对外政策领域中的第二个重要作用是动员舆论,争取盟友,压倒对手。尽管美国人已经形成了一种自以为是的文化心理,但这并不能使别的国家和民族相信,美国在国际社会中总是扮演着英雄和救世主的角色。为了实现政策目的,自我标榜便成为不可缺乏的一环。从立国初期起,自由、民主、独立、和平之类的语言不绝于各届政府的对外政策文件之中,其高峰当推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说他们是自我标榜并不意味着提出这些方针的人是出于虚伪的目的。然而提出这些方针也不是出于理想主义热情。在这些方针中大张旗鼓地宣扬种种道德原则,并把这些原则的实现同战胜法西斯主义国家联系起来,同打败战争发动者联系起来,大大提高了美国在战争中的形象和领导地位,为它在战后世界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铺平了道路。人们得到的印象是,美国不仅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而且还高举真理与美德的旗帜。尽管事后那些道德原则在碰到具体问题时往往化为乌有,但总体的形象与社会舆论已经形成,在具体问题上违背原则而造成的损害总是局部的和有限的。
约翰 · 杜勒斯(J. F. Dulles)曾经说过,总有一些道德概念是各国都可理解的,可以以此作为国际行动的共同标准,美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如不涉及这些标准,可能就得不到盟国的支持,结果会导致混乱和最终的失败。在50年代中期,国际上出现过一股和平中立、和平共处的潮流,这种形势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军事同盟政策。为了扭转潮流,杜勒斯反复不断地强调“共产主义威胁”没有减少,他攻击中立是一个“陈旧”、“不道德和近视的”概念,说中立原则“妄称一个国家获得自身安全的最好办法是不关心其他国家的命运”。在杜勒斯看来,“西方最大的危险是认为来自东方的威胁已经减退,这样盟国之间会发生争吵,集体防御安排将被看成过时,中立就会受到尊重”。John Gaddis. Strategic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32145;约翰·杜勒斯:《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 231233 页。很明显,强调反共,强调集体安全,把“中立”说成“不道德”,都是为了维持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体系,防止这些盟国脱离美国的控制。在这时候,道德原则常常成为美国迫使盟国就范的鞭子。
进入20世纪,美国充当世界事务“领袖”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这种愿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似乎成了现实,美国的各种利益已经遍布全球各地。但是要说服有“孤立主义”传统的美国人长期承担维护海外利益的巨大代价,支持统治阶级的全球政策却不太容易。因此大战结束后,美国立即将对外政策的核心转到对苏联的冷战方面,声称美国的全球战略是为了对付苏联的扩张。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曾评论说,从杜鲁门政府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建立一座反共产主义的堤坝上”。Stanley Hoffmann, Primacy or World Ord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any, 1980, p.13.反共意识形态成为全球冷战战略最有力的支柱。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美国遭到越南战争的惨败才有所改变。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里根政府上台,反共意识形态重新得到强调。我们也许可以从新保守派代表人物诺曼·波多雷茨(Norman Podhoretze)的一段话中,了解到为何这面旗帜被反复竖起的原因。波多雷茨认为,由于“一般美国人对伊朗、阿富汗的考虑已经被他们的自我经济考虑模糊了,在一种真正的遏制政策被确立之前,‘共产主义’这个词应该重新被引入美国对外政策的词汇表。只有那样美国人民才会认识到,与苏联的冲突是一场为自己和反共的斗争”。R. A. Melanson, “Paul H. Nitze to Norman Podhoretze: The Tradition of AntiCommunist Containment”, in Traditions and Values: American Diplomacy, 1945 to Present. ed. by K. W. Thompson,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4, pp.173175.这位保守派理论家的观点流露出这样一种含义:如果不把美苏冲突涂上意识形态色彩,美国人民就不会支持政府的对外政策。里根也的确曾把苏联称为“邪恶的帝国”。“邪恶”一词显然是针对美国公众的文化心理设计出来的。
波多雷茨在谈及美国人民对增加军费的态度时,也谈到了强调道德的意义。他指出美国人民生性不愿建立一支常规军,除非是为了打仗。美国人民不能忍受这样的想法,即他们与对手的竞争“只是为了维持均势”。因为这样做时双方的道德地位似乎是相同的。Ibid.这里人们不难得出这样一种推论:美国人民只有在面临道德上势不两立的敌人时,才会支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如果政府试图说服人民接受增加军费的计划,那就必须使人民相信,这是出于道德原则的考虑和需要。如果说在18和19世纪促使美国人为扩张和海外利益奔波的,是赋予他们“天定命运”的上帝,到了20世纪,似乎只有“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魔鬼”才能驱使美国人民为“全球利益”操心了。道德原则成为动员舆论、获取国内公众支持的一种工具,在这里表现得是相当清楚的。
三、对外政策中道德原则的构成与变化
历届美国政府在制定和调整美国对外政策时,总忘不了要建立起与新政策相适应的道德原则。这些原则有的能发挥重大影响,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指导对外政策发展,有的则昙花一现,在本届政府任内就被悄悄“遗忘”。成败的原因自然在于对道德原则的选择得当与否。这里,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新提出的某一种道德原则是否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它牵涉到政策制定人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能力。另一方面是这种原则所体现的价值是否正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在以上两个方面都有满意结果时,这一原则才会有成功的可能。
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道德原则是由多种基本价值形成的。这些基本价值大致可分为三类,在不同的条件下,人们关注的重心是不同的。
第一类是与安全有关的价值,如和平、生存、实力、自卫、稳定、独立,等等。这些价值观念,抽象地看,在人们心目中并没有什么变化,但从历史角度看,它们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与美国对外政策会形成一种互动关系。
立国初期,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所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便是这个新生的共和国的安全问题。当时美国只拥有东部十三州,人口稀少,联邦政府的财力与权力都十分有限。此时,在世界各地扩张建立殖民地仍是欧洲列强的重要政策。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并不甘心,法国和西班牙在边界上虎视眈眈。尽管面临这种不利局面,美国政府并没有倾全力去增加军费,扩军备战。当时美国的政治家们充分利用了欧洲列强间的均势,以及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满足于一种相对安全的国际地位。虽然当时国内有亲法和亲英两种势力,但他们都支持这一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麦迪逊(James Madison)等人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指出,维持人们的自由和国家的团结,而不是花大量的钱去建设一支大规模的军队,是美利坚合众国安全问题的关键。Paul A. Varg,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Baltimore, Penuin Books, 1963, p.304. 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满足于相对安全地位的政策,使美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保持了和平的环境(其间发生的第二次英美战争只是短暂的插曲),而且有助于它稳定地开发国内经济。如果美国在立国之初便卷入列强的角逐,势必会严重地影响它的自身安全与经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拥有强大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超级大国。与建国之初相比,应该说其安全地位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那种满足于相对安全地位的观念却总是受到谋求绝对安全地位的观念的挑战。进入80年代,美国的国防开支高达二千多亿美元。但里根政府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仍然受到美国公众的支持。这种状况表明,尽管有着世界上最庞大和最先进的武器库,美国人的安全感反而下降了,他们长期生活在核恐怖的阴影之下,离罗斯福提出的“无虞恐惧”的自由相去甚远。与两个世纪前相比,美国人在安全方面的价值变化是不难看到的。
第二类价值涉及自由、民主、公正、正义、平等、人权等方面。美国人高度重视这些价值,并且视这些价值为美国社会的精神支柱,出于我们上一节中分析过的那些原因,美国人还希望这些价值在其他国家得到同样的理解,起到同样的作用。这种愿望也许不难理解,但是把这种愿望变成行动,使之成为对外政策的一部分,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国际社会中引起争论和对抗,因为对任何社会来说,人们的价值观念并非是通过“进口”就可以根本改变的,人们是“通过母亲的乳汁”建立起自己的基本价值观的。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倾向于认为,美国应以自己的榜样行为使别国追随自己。乔治·华盛顿希望他的国人成为一个总是尊奉崇高的正义和仁爱精神的民族,为人类树立高尚和崭新的典范。随着美国国力的逐渐强大,华盛顿的这些话似乎已经逐渐被人淡忘了。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宣称,美国有权使用武力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的内部事务,在那儿建立起符合美国标准的秩序和稳定。威尔逊在为其武装干涉墨西哥革命的决定辩护时说,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墨西哥人尽快获得民主和自由。虽然威尔逊承认榜样能起更好的作用,但他坚持说必要时美国可以使用武力。其实罗斯福、威尔逊的行动只是要维护美国在拉美的霸权而已。但这种以道德名义进行的干涉不仅损害了有关道德价值的名誉,而且也给美国自身造成了损害。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指出:以道德名义进行的种种干涉既不反映美国“自身的道德意识,也不代表任何一般的社会舆论”,而只是“屈从于少数有影响人的压力”George Kennan,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64, Winter 1985/86, pp.205214.。那些价值上自我冲突的对外政策折磨着美国人的良心,久而久之,它已降低了人们对以自由和民主为核心的这一价值体系的信仰程度。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在1979年公开承认,美国人民对于政府、教会、学校、新闻媒介等机构越来越不信任。卡特认为美国存在着某种信仰危机,这是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吉米·卡特著:《忠于信仰》,卢君甫等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第141142页。此书的书名也反映了卡特对信仰问题的重视。80年代发生的“伊朗门事件”加强了美国人的这种情绪。《华盛顿邮报》1987年4月报道的民意测验表明,“美国的政治空气比越南战争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充满了怀疑和失去信心”,“美国人对他们国家的方向,对于包括里根总统在内的领导人的活动越来越持否定态度”。民意测验还表明,美国人民认为,“对国家的未来失去控制是由华尔街到白宫这一系列机构造成的”。Washington Post, April 22, 1987, p.1. 当然,海湾战争的胜利和苏联的崩溃使美国人“信心”有所回升,但这种回升能否持续还是令人怀疑的。美国人对这一类价值的“信心”的上下升降对美国对外政策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第三类价值涉及美国人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关系,如合作、相互依赖、中立和世界秩序等。
当大批欧洲新教徒远涉重洋抵达北美时,他们怀有一种逃避感,他们是为了逃避旧世界的宗教迫害和经济困苦来寻找新的出路的。对新生活的憧憬和对旧世界的憎恶,逐渐使美国人形成了一种两个半球不同的观念。这种想法认为东西半球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价值和传统,因此在立国之初,美国人普遍赞成欧洲国家不应干预美洲的事务,美国也不应卷入欧洲国家的事务中去,这种观念也被称为“孤立主义”。被看作“孤立主义”宣言的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指出,美国人民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与欧洲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那样会把美国的和平繁荣陷入欧洲人的野心、争夺、利益关系、好恶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乔治·华盛顿著:《华盛顿选集》,聂崇信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25页。可以看出,18世纪末期美国的“孤立主义”思想是建立在自我优越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蔑视上的,它是一种“孤芳自赏”的道德原则。同时它也反映了这样一种看法,美国人应更多关心自己的事情,西半球可以单独得到和平与繁荣,实质上它表现了美国人当时对外部世界的冷漠态度。
“孤立主义”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在19世纪起过重要的作用。进入20世纪,由于它已不符合美国参加世界性竞争、充当世界领导者的目标,“孤立主义”的影响逐渐下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它还“复兴”过一阵,此后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已微乎其微了。但是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它并没有死去,它悄然隐伏在美国人的政治文化中。当美国在越南遭到失败时,“孤立主义”影响曾一度上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George S. McGoven)就提出过“美国回家吧”的口号。80年代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当代大部分美国人对外部世界持不关心的态度。他们不相信世界各国必须相互依赖,不相信美国能领导世界走向公正和稳定,也不相信能够找到关于世界经济、环境污染、能源紧张及第三世界经济等问题的出路。James M. McComick,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American Values, Ithaca. Illinois, F. E. Peacock Press, 1985, pp.298312. W. Schneider, “Conservatism, not Interrentionism”, in Eagal Defiant, U. S.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80s, ed. by K. A. Oye Boston, Little Brown, 1983, pp.3347. 这里反映出一种深刻的厌烦情绪,美国人对发挥“世界领导作用”正越来越不感兴趣。
应当指出,人们观念中各种价值的地位变化是复杂的、不确定的,而且常常由于某些重大事件的发生而反复。上文指出的三种变化——安全感的下降,对美国典范作用信心的下降,以及对“领导”外部世界的兴趣的下降——也很难说已成为必然趋势。但是透过这些不确定的变化,也许可以增加对美国对外政策未来发展的了解。
四、美国未来政策中的道德原则问题
价值的变化必然会影响道德原则的作用和地位,当一些原则显得过时不能指导对外政策,人们就希望形成一些新的道德原则来取代旧的。美国上层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共识”被越南战争的失败打破了,他们在80年代重建这种“共识”的尝试一直没有成功。不成功的原因可能是人们对世界形势的发展还有很大的分歧。
自由派思想家代表人物斯坦利·霍夫曼在80年代初认为,“我们已从建立在一国开明利益基础上的优势时代,转变到了强制性的谈判与妥协时代”。但是,里根总统的对外政策顾问、学术界著名的持保守主义观点的人物罗伯特·塔克(Robert W. Tucker)教授则指出,“这是个熟悉的世界,总的说来,超级大国全面竞争的利害关系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面对这种几乎完全不同形势估计,新的道德原则显然是难以形成的,里根勉强使“反共主义”继续成为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上文已指出公众对此是有不满的。Stanley Hoffman, Dead E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w Cold War, Cambridge. Mass., BaIlinger Pub. Co., 1983, p.1; Robert W. Tucker, The Purpos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1, p.30.对这一时期对外政策的辩论见Kenneth W·Thompson, Ethics, Functionalism and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risis in Values,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还可参见另一重要著作Foreign Policy and Domestic Consensus, ed.by Kenneth Thompson and R. A. Melanson,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冷战的结束使人们对形势的估计趋向一致。霍夫曼于1991年出版的《沧桑巨变》外交政策论文集中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塔克在同一书中也承认,从50年前美国放弃“孤立主义”以来,世界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指出:“欧洲分裂的结束发出了二次大战以来统治世界政治的巨大冲突结束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能否重建“共识”,形成一些指导对外政策的新的道德原则呢?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Stanley Hoffmann, “A New World and Its Troubles”, in SeaChange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World Transformed, ed.by Nicholas X, Rizopoulo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1, pp.274292; Robert W. Tucker, “1989 and All That”, in SeaChange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World Transformed, ed. by Nicholas X, Rizopoulo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1, pp.204237.
《对外政策》杂志主编查尔斯·迈纳斯(Charles.W. Mayners)认为,由于冷战的结束,“美国对外政策将比它的敌人失去得更多,它将失去1945年以来指导国家航船的六分仪”。迈纳斯说的这个“六分仪”不是别的,正是美国的反共主义。今天已很少人认为它还能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最基本的指导原则。霍夫曼说得很清楚,曾经指导过美国对外政策的三个原则——美国例外主义、反共主义和世界经济自由主义现在都帮不上什么忙了。Charles William Mayners, “America without the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Vol, 79, Summer, 1990. pp.325; Stanley Hoffmann, “A New World and Its Troubles”, in SeaChange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World Transformed, pp.274292.
新的道德原则必须既能适应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又能突出地强调美国制度和价值前景。塔克指出,美国之所以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长期冷战,除了要捍卫通常意义上的安全与经济利益之外,还要“维持和推行美国的自由制度和价值”。他认为维持均势利益和推行自由利益之间的紧密联系,是“深深扎根于美国人意识中的信念”。Robert Tucker, “1989 and All That”, in SeaChange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World Transformed, pp.204237
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立塔克所说的“联系”。美国面临的国际问题不少,但正如迈纳斯所说,“在恐怖主义、第三世界激进主义或日本上升的经济理论等问题上寻找一种新的安全威胁是没有说服力的”。也就是说公众很难真正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对美国的威胁。也有人认为可以用“输出民主”、“保卫西方文明”来代替反共主义作为新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些提法似乎与美国的安全没有联系,而且“输出民主”的手段,譬如是否能使用武力等,又会引起极大的分歧。Mayners, “American without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Vol, 79.Summer, 1990, pp.325.
已经有一些人认为,美国会继续担当世界领导人的角色,但同时应发挥一种更为“温和”的作用,如只充当一名维持秩序的世界警察。但塔克认为,对美国来说这种变化是不可取,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人的最终目的中包含着“总有一天美国要使世界得到自由”的信念,而世界警察的功能中是不包含这种信念的。依靠“戒律”维持秩序是对国务活动持传统观念的一种信念,“它不是曾经推动过美国的那种信念”。Tucker, “1989 and All That”, in SeaChange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World Transformed, pp.204237.
霍夫曼强调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用援助交换发展中国家保护环境,重视健康和人权等问题。他提议由美、欧、日建立一个“指导集团”,进行一种“多中心指导的新试验”。但“指导集团”内部的关系是什么呢?在美国历史中,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处的先例是不多的。
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没有别的国家能取代美国的地位,因此美国“注定要领导”世界。但是似乎所有人都已承认,美国的领导力量已大为削弱,这种削弱主要并不是由于日本或德国的崛起,而是日趋严重的美国国内问题。前助理国务卿罗伯特·霍迈茨(Robert D. Hormats)最近撰文说,当世界上如此之多的国家和人民把更好的生活质量作为压倒性的目标时,这样一个美国,它的城市在某些方面与第三世界贫民窟别无两样,它的已经庞大的下层社会继续落在社会其他人后面,它“能够维持世界领导权所需要的道德上的权威吗?”Stanley Hoffmann, “A New World and Its Troubles”, in SeaChange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World Transformed, pp.274292; Joseph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1990; Roberts D. Hormats, “The Roots of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70, Summer 1991,p.138.霍迈茨的问题表明,在道德权威方面,仅仅拥有“自由”的权威是远不够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不管美国人自己是否满意美国在道德方面的形象,美国所追求的有效的领导作用,还有赖于其他国家对其道德形象的判断。
1992是选举年,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的“把美国放在第一位”的口号已赢得了一些美国人的支持,也许这只是经济衰退导致的短暂现象。但是如果美国不能用长远的目光解决它面临的国际与国内问题,那么“孤立主义”的阴影就不会散去,因为这种原则是一种美国人很难拒绝的诱惑,一种政治文化的诱惑。
二十世纪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优先选择
*
*本文原发表于《美国研究》,1991年第1期。
①约瑟夫·格罗姆等:《环太平洋——美国的新边疆》;劳伦斯·伊格尔伯格:《欧洲和太平洋之间的美国》。两文均刊登在《太平洋的挑战》一书中,时事出版社,1986年,第2132页。
当20世纪到来时,美国刚刚跨过太平洋,开始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在东亚打了三场大规模的战争,在成为东亚地区主要大国的过程中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另一方面,美国在东亚也拥有越来越大的利益。1983年美国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贸易达到了1360亿美元,第一次以260亿的差额超过了与欧洲的贸易额。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投资增长率也超过了别的地区。一位加利福尼亚政治家说,“从经济上说,太阳正在从西边升起”。前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告诉人们,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心正在转移到太平洋盆地。也许,越洋而来的美国人更能感受到亚洲太平洋地区在半个多世纪里发生的巨大变化。①
当20世纪即将结束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地区仍将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对于该地区国际关系如何变化,和平与稳定的环境能否维持,这种乐观估计就不容易建立了。
亚洲国家对于维持本地区的繁荣与和平自然是责无旁贷的,但是历史、地缘、文化、利益等各种压力也许使它们只能作有限的选择。作为外来力量,而又深深卷入这一地区事务的美国或许会有更大的选择余地。经验已经表明,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过多次机会对它的亚洲利益进行战略优先选择,各种选择对亚洲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试图归纳20世纪美国在东亚的几种战略优先次序,分析影响美国做出不同选择的原因,比较东亚国家在其战略优先次序中的地位变化,以及不同的优先选择给美国带来的各种后果。在这里战略优先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范围内具有多种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它必须对这些利益进行选择和排列,确保列于优先地位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放弃排在较低地位的战略目标,虽然后者在完整性、时间和程度上会受到影响。
一、美国东亚战略优先的四次调整
20世纪初,美国在东亚面临着三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第一,如何按照“门户开放”原则维持中国的“完整”,防止列强瓜分和垄断中国市场,为美国扩大在华经济利益提供必要的条件。第二,在殖民地争夺战争经常发生的时代,如何确保刚刚从西班牙手中夺来的领地菲律宾的安全;第三,如何防止美国同本地区唯一的军事大国日本的利益冲突不断扩大,维持美日之间协调与和平的关系。20世纪头10年美国的东亚政策提供了第一种战略优先次序的模式。1901年12月,西奥多·罗斯福在他的国情咨文中指出,由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和利益正迅速增长,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事都同美国有强烈的利害关系。他认为美国提倡的是包含全部意义的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整个帝国”有同其他大国一样平等的待遇。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美国试图阻止俄国独占中国东北(“满洲”)的企图。但是美国的种种外交行动没有使俄国停止不前。因此当日俄战争爆发时,西奥多·罗斯福说,“我对日本的胜利感到极其愉快,因为日本在为我们打仗”。但是日本在战场上的胜利,特别是对马海战的胜利,使西奥多·罗斯福不得不重新认识日本。罗斯福看到一个在军事上和工业上都迅速崛起的日本,拥有强大的海军,还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认为如果美国冒犯了日本,它就会立即被夺走菲律宾和夏威夷。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不得不放弃“满洲”的“国际化”方针,允许日本取得“满洲”南部的优势,他寄希望日本在解决亚洲大陆事务以前“不会看上菲律宾”。A Complic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Prepared under Direction on the Joint Committee on Printing of the House and Senate, New York, pp.66766677; E.E. Morison ed., The letter Theodore Roosevelt, Cambridge, Mass, 19511954, Vol.4, pp.724, 12021205, 12301231.
尽管罗斯福对日本采取了低姿态,但是日本仍然在中国东北阻止美国参与铁路建设,不断挤占美国商品的市场。更加严重的是,1906年以后美国西部又发生了多起排日事件,使两国关系更为紧张。1907年夏,欧美舆论界广为流传着美日之间可能发生战争的谣言,西奥多·罗斯福一方面把美国的主力舰队调入太平洋作为对日本的威慑;一方面寻找摆脱这场危机的办法。8月份他抱怨公众对防卫菲律宾不感兴趣,说菲律宾是使美日局势紧张的“全部原因”,并认为应立即考虑允许菲律宾独立。不久美国找到了一种既能保住菲律宾,又能继续保持日美正常关系的方法。1907年11月国务卿鲁特告诉日本方面说,美国从一开始就理解日本的政策是宁愿把日本移民的方向转移到亚洲大陆去而不是到美国来。因此两国根据不同理由,愿意实现这一同样结果。在美国的这一“理解”之下,日本开始实行“自愿限制”政策。E. E. Morison ed., 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Vol.4, pp.761762; P.C. Jessup. Elihu Root, New York, 1938, p.29.
1908年日本新内阁实行“弃名求实”的外交方针,力求使各国逐渐承认日本在“满洲”具有“特殊地位”。11月美日达成了“鲁特—高平协议”,双方保证不侵犯对方在太平洋的领地。但在有关中国的条款中,文件说两国决心运用一切可用的和平手段支持中国的独立和完整,以及各国在这个帝国中的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实际上谈判过程表明,双方已取得默契:将“中国”理解为“中国本部”,即不包括蒙古和“满洲”等地,而用“帝国”一词专指包括这些地区的全部中国。总之,“鲁特—高平协议”使美国得到了日本不侵犯菲律宾及遵守“门户开放”的保证,而日本则使美国默认了它在中国东北的“优势地位”。协议签字后,罗斯福高兴地说:“没有别的事比同日本的协议给了我更多的欢乐。”在不久后给美国国会的咨文里,他又轻松地提到,美国应用一代人的时间来考虑,是让菲律宾独立还是让它继续处在美国的保护之下。他似乎完全忘记了一年前曾说过要立即让菲律宾独立的话。 T. Bailey, “The RootTakahira Agreement of 1908”, Pacific Historic Review, 1940, Vol.9, p.25; R. A. Esthus, Theodore Roosevelt and Japan, Seattle, 1966, pp.273278;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一书第一辑中,这一协议的该条款把“在这个帝国”译为“在华”,这一翻译不能反映美日双方使用该词的含意。
西奥多·罗斯福的东亚政策构成了这样一种战略优先次序:占据最高地位的是维护菲律宾的安全,尽管他一度想尽快让其独立,但美国这一时期的备战活动表明,为了维护它自己的大国地位,美国不能一枪不放就抛弃菲律宾。占据第二位的是维持与日本的友好关系。西奥多·罗斯福向日本软硬兼施地表明,只要日本不向南扩张,美国会在东亚大陆给日本补偿。维护在中国的“门户开放”处于最低地位。“满洲”地区的“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美国在东亚的第二次战略优先选择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行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秩序设想的产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战略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发现,这一长期受到忽视的国家正是自己的可靠盟国。罗斯福1942年春对蒋介石说,中国在未来不仅要在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繁荣,而且还要在维持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方面发挥适当作用。9月,罗斯福以蒋的政治顾问约翰·拉铁摩尔的名义告诉蒋介石:在西太平洋地区,从法属印度支那到日本,主要的有关大国将是中国和美国。在这场战争之后,必须考虑由中国、美国、英国和俄国作为世界的四个“大警察”。FRUS. 1942, China, pp.44, 185187.
罗斯福把中国提到四大国之一,是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中国将在战后世界一切重大问题上支持美国,霍普金斯在设计战后国际组织时,坚持应设立由四大国代表的委员会,而不是英国提出的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由七八个成员组成的机构。因为那样美国“会被多数票压倒”。至于中国这一票肯定会投给美国,宋美龄刚刚向他保证过,“中国将在和平会议上同美国站在一道,这是由于中国信任罗斯福和他的政策,并愿意出于这种信任而预先做出承诺。”R.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New York, 1950, pp.718, 716.
罗斯福政府重视中国战略地位的第二个考虑是,中国将是最终打败日本的主要力量。1943年罗斯福指出,美国不能指望浪费时间,一个岛一个岛慢慢越过广阔的太平洋,直到最后打败日本,直通东京的道路比比皆是,美国对所有道路都会加以考虑。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支持了蒋介石组织缅甸战役,盟军在孟加拉湾登陆的作战计划。在德黑兰,他向斯大林介绍了从中国攻击日本的可能。罗斯福也重视中国在战后对日本的遏制作用,他对蒋介石建议的战后在辽东半岛和台湾建立军事基地,以阻止日本再度侵略的计划“印象深刻”。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79, pp.426427; Shewr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p.773779, 788; FRUS, 1942, China, pp.185187.
第三方面的考虑是,中国可以参加对亚洲太平洋地区殖民地的托管工作。罗斯福曾向蒋介石表示,战后这些殖民地不应恢复从前的政权。1942年8月,美国战后对外政策顾问委员会所属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建议,战后东南亚地区应建立托管制度,使殖民地逐渐独立,参加托管工作的应是美、苏、中、澳和新西兰等国。最后,中国还可以作为抗衡苏联的一支力量。为了说服英国接受“四大国”概念,罗斯福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由于中国同俄国存在着严重的政策冲突,它将全毫无疑义地站在我们一边”。G.R. Hess, The United States Emergence as a Southeast Asia Powers, 1940—1950, New York, 1987, pp.6669; Sherwook, Roosevelt and Hopkins, p.718.
东南亚地区在美国战后政策中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罗斯福政府认为,战后世界将结束帝国主义,东南亚是“非殖民化”政策的主要目标。在美国看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采取托管制度。国务卿赫尔后来缩小了托管范围,但坚持战后殖民地应确立“门户开放”原则。此外美国还试图在这一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建立军事基地,赫尔曾表示过印度支那对战后的亚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英国一直反对美国用“非殖民化”政策削弱其战后地位。为了让美国同意恢复印支的法国殖民统治,英国外交部官员认为应说服法国在印支接受美国基地,以此换取美国的妥协立场。G. R. Hess, The United States Emergence as a Southeast Asia Powers, pp.67, 69, 79.
在太平洋战争进行的4年之中,中国在美国的东亚战略优先次序中占据了最高地位。东南亚地位没有下降,而日本已成为敌国,战后日本将处于盟国的严格控制下,其政治、经济制度都要改变,军事机器、军工企业将消灭,开罗会议通过的文件表明,日本在战后将长期处于很低的地位。
但是战争的结束比预计的要快,而罗斯福也在胜利到来前就离开了历史舞台。苏联在战争中力量和影响急剧扩大的趋向,使美国认为西方必须以更大的实力来抗衡苏联。但是东亚事态的发展使美国不得不重新确定它在这一地区的战略优先次序。1947年至1949年,杜鲁门政府在东亚地区选择了第三种战略优先模式。
由于对付苏联的需要,杜鲁门政府更加依赖蒋介石和国民党,希望以此确保中国站在美国一边。但这只是助长了蒋依靠军事手段解决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分歧的决心。马歇尔在中国“调停”一年,未能阻止中国内战的爆发。国民党的腐败和经济上的混乱表明,它的政治前途极其危险。美国已看到这样的前景,国民党无法打败共产党,这个政府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处境已全面恶化,中国共产党可能取得全国政权,利用国民党政权维持远东的安全与稳定已不再可能。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148156页。
杜鲁门政府在东亚地区必须找到新的战略支点,这一支点不仅要有遏制苏联的作用,还要有抗衡中国的力量。当“遏制”苏联这一概念被美国政府接受后,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在乔治·凯南指导下对世界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进行了排列。遏制政策的设计者们认为,保护这些地区应构成“最优先的具体目标”。1947年秋,国务院确认全世界只有5个工业和军事力量中心,它们是美国、英国、苏联、德国及中欧,名列最后的是亚洲的日本。凯南等人认为德国和日本此时并没有军事上的危险,威胁来自内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这有可能使它们落入苏联控制下。10月凯南向其上司提出警告,麦克阿瑟的政策可能鼓励共产党对日本的渗透。很快,按照“开罗会议”和“波茨坦会议”文件制订的对日惩罚性措施逐渐被放弃,新政策要求美国长期在日本保持军事基地,恢复日本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把日本作为军事大国永远消灭的思想正在转变”。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1985, pp.8488, 104.
对美国来说更为严重的是日本的经济问题。东京盟军司令部在1947年决定,美国应努力使日本的经济同亚洲及远东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但是,美国又担心日本可能会依赖中国大陆或俄国的资源和市场,以致日本无法在政治上同美国结成同盟。1948年杜鲁门任命银行家约瑟夫·道奇去指导日本的经济方针。道奇认为应把美国的援助用于推动日本同远东国家的贸易发展上,他认为东南亚可以为日本提供市场和原料。1949年国防部动员局主任C. E.威尔逊去日本调查经济发展前景。调查的结果是,台湾地区、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是日本可能得到原料的地区。这些思想都反映了这样一种方针,即日本的发展不必依靠大陆市场和资源,日本与东南亚经济一体化可以解决它们面临的不同的困难。William S. Borden, The Pacific Alliance: United Stat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and Japanese Trade Recovery, 1974—1955,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pp.110122. 890. Ooc/5250, Box 5528; 894.00/2.2050, Box 5650. RG59, National Archives,Washington, DC.
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民族主义力量的兴起,1945年美国战略情报局认为,美国应促使欧洲国家实行开明的政策来维持他们的殖民地,以此来阻止苏联刺激殖民地叛乱。情报局还认为,由于需要欧洲国家的帮助来抗衡苏联,因此美国应避免采取任何削弱其在亚洲殖民地地位的政策。由于美国已经占领了日本在西南太平洋的所有岛屿,它的战略安全问题已经解决。同时,美国的经济力量在当时已占绝对优势,它也不再需要“门户开放”政策作为扩张的途径了。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完全放弃了“非殖民化”政策,并把阻止这一地区脱离西方影响作为自己主要的战略目标。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认为,苏联试图不让西方得到东南亚的资源,“如果东南亚也被共产主义席卷,我们将遭到重大政治挫败”,其影响会遍及世界所有地区。G. R. Hess, United States Emergence as a Southeast Asia Power, pp.125126,154156.从1947年至1949年,新的战略优先次序已经形成。扶植日本,同其结成密切的盟国关系成为美国东亚政策中的最高优先权。确保东南亚与西方的联系,阻止这一地区激进民族主义取得政权是具有第二优先地位的战略目标。遏制中共政权的“扩张”处于前二者之下,虽然在宣传上它似乎被放在很主要的地位。
1970年前后,美国的东亚政策再次进行调整。从而形成了第四次战略优先选择。面对苏联战略核力量赶上美国,以及苏联在全世界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尼克松政府意识到,美国陷在亚洲严重影响了它的全球战略主动权。同中国改善关系,从越南脱身成为新政府上台后的当务之急。改善同中国关系的主要理由是,中国可以成为抗衡苏联的主要力量,使苏联东西两面受到牵制,这样苏联在同美国打交道时难以坚持强硬立场。1971年10月,基辛格说“我们对中国采取主动行动得到的最大好处,也许是针对苏联的有利影响”。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1979, pp.756766.
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另一好处就是能够更快地从越南脱身。美国已经无法打赢这场战争,但美国力图缩小由此带来的损失,按照尼克松的说法,美国结束这场战争的方式将会决定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他认为如果结束得好就能维持美国在欧亚两大洲的地位。通过改善同中国及苏联的关系,基辛格认为他已成功地把河内“孤立起来”,并使美国在结束越南战争时,“取得了行动自由”。由于中国主要担心苏联的扩张,美国也努力运用它同中国的新关系稳定整个东南亚的局势。1973年基辛格在北京对周恩来说,中美双方在印度支那有平行的利益,“美国仓促撤出东南亚将酿成一场灾难”。他认为周恩来同意了他的看法,而中国也确实在70年代初改善了同泰国、马来亚、菲律宾等国的关系。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p.969, 1077, 1087, 1197: Richard Nixon, Memories of R. Nixon, New York, 1978. p.742;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Upheaval, Boston, 1982, p.60.
中国战略地位的上升,也构成对日本的某种微妙平衡。尼克松上台时,面临着来自日本的两种压力,一是美日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对日贸易在20年后第一次发生了赤字,这表明日本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大国,日本经济开始对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构成挑战。二是日本在收复冲绳问题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军方认为,冲绳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这不仅由于它能支持越南战争,也由于它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占有重要地位。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p.321, 340. Walter Lafeber, “Decline of Relations during the Vietnam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The Post War World, ed. by Akira Ireya and Warren I. Cohen,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9, pp.97110.即便如此,美国最终还是不得不将冲绳还给日本。面对一个经济日趋强大,政治上已表现出独立愿望的日本,美国也有必要建立一定的平衡力量。尽管中国地位有所上升,但日本仍然是主要盟国,美国没有把它对日本的“忠诚”转移到中国去。美国由于在东南亚的失败,以及它力量上的限制,在70年代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东南亚的战略地位,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大为减少,并要求日本对东南亚的开发与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第四种战略优先次序中,日本失去绝对优势,但仍然占有最高优先地位。中国地位显著变化,从敌人转变为战略上的伙伴关系。东南亚地区虽然不再具有过去那种重要性,但仍然被看作是忠实可靠的盟友,而东南亚本身的重要性决定了美国仍把它放在高于中国的地位。
二、影响战略调整的地区性因素
20世纪美国的东亚政策尽管有许多变化,但基本上都可纳入以上四种战略优先次序的模式。西奥多·罗斯福建立的第一种优先次序影响了以后30年的美国东亚政策。从“蓝辛—石井协议”到“史汀生主义”,基本上都没有越出这一模式。第二种战略优先次序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就被放弃了。第三种战略优先次序维持得较长,到20世纪60年代末宣告破产。第四种次序维持到目前,但在80年代已经有过调整,主要是降低中国的地位。
在这几种次序下,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的战略地位都发生过变化,它们时升时降,似乎没有规律。但是仔细分析,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有意义的现象。在这四种次序之下,中国除了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处于一种最高优先地位之外,在其余情况下都排在东南亚与日本之下。中国在20世纪有两次上升的机会。一次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另一次是70年代初苏联实力对美构成全面挑战的时候。这两个时期都是美国的世界利益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候,在前一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打一场两洋战争,在后一情况下,美国在欧洲、中东及非洲都面临严重局势。生死存亡之际,中国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罗斯福全力要让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尼克松认为中国是世界五大经济力量中的一员。美国完全清楚,中国在当时只是一个潜在的世界大国,正如罗斯福所说,他完全认识到中国目前的软弱,但他是在“考虑遥远的未来”,他认为最好还是把4亿中国人民作为朋友,而不是使他们可能成为敌人。作为一种潜在的、长期的战略利益,中国可以弥补美国在近期和现实利益上遭受的损失。
但是,当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所受到的压力下降,它的现实和近期战略环境有了积极改变,中国在其东亚的战略优先地位就难免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的战略地位下降过一次。进入80年代,苏联对美国压力大大减轻,中国的地位又相对下降,国务卿舒尔茨认为,从东亚和太平洋新出现的实际情况看,中国的地位不如日本重要,美国政府把在太平洋盆地的战略重点放在日本。其实从1947年以后起,美国从未把它的重点从日本移开过,舒尔茨的这种强调只是表明美国重估了中国的地位。班宁·加瑞特等:《从尼克松到里根,中国在美国战略中地位的变化》,刊登于《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1988年,第76104页。
除了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之外,日本在美国的战略优先次序中一直维持一种较高的优先地位,甚至最高的优先地位。普遍的解释是美日之间有着大量的共同利益,其实,构成优先地位的并非单纯是共同利益,竞争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1940年以前,日本在东亚的扩张使美国无法忽视这个竞争对手,美国只有通过妥协和竞争两种策略才能维持和日本的关系。从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后期,日本不具备现实的竞争能力,但它是五个军事和工业力量中心之一,也就是说它具有潜在的、可以迅速恢复的竞争能力,美国不能承受失去日本这一力量的后果。这种潜在的实力使它得以占据优先地位。进入70年代,日本的经济力量对美国构成了挑战,日本经济影响在东亚迅速扩大。尼克松在1972年这样对周恩来说:“如果我们没有同日本的防御安排,我们在与它有关的问题上就发挥不了影响。”密切的合作是控制和竞争的一种方法。一位美国参议员比尔·布莱德雷说过“你要让日本在世界上承担更多的对外政策责任,但要使它与美国合作,关键是让它承担责任而不用使它重新武装”。较高地位并非一定是共同利益的产物。R. Nixon, Memories of R. Nixon, p.567; Gordon Laurer and R.F. Wylie, ed., Destinies Shared: US.Japan Relation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135.
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并没有严重下降过。作为西方和美国传统的势力范围,这似乎是正常的。但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却常常被美国人自己扭曲。西奥多·罗斯福对菲律宾的态度只是扭曲的一种表现方式。1953年3月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印度支那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具有最高优先地位,在某些方面比朝鲜更重要,这种看法就更是一种扭曲。为越南打一仗是一种扭曲,认为日本现在的扩张不损害美国的利益也是一种扭曲。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说,美国对东南亚的误解会导致美国在政策上犯两种不同的错误,它可能导致一种侵犯性和干涉主义的努力,想要按美国人认为合适的方法塑造东南亚各国社会,不承认它们不可能被外部力量操纵。或者它也可能导致一种迟疑不决的立场。这一立场不能充分促进美国的利益以应付日本的挑战。看来,战略地位的稳定也并不一定能确保战略利益的稳定。东南亚地区也许是过分地紧跟了美国的战略,因而难以纠正美国对这一地区的“误解”。Memo of Conversation at White House, March 24. 1953, Dulles Papers. WH Memo Series, Box l; AWF; Lawrence B. Kranse, U.S. Economic Policy towar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Meeting the Japanese Challenge,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p.2629.
三、影响战略调整的全球性因素
战略优先地位的选择会受到世界形势变化的影响,但是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往往是那些最基本的因素。经济考虑是一种重要的因素,但现实的经济利益往往要超过那些潜在的经济利益。不管美国商人如何想象中国市场的未来前景,基本的事实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额几乎是一成不变地落在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额之下。中国也很少向美国提供大宗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而形成对照的是东南亚。美国开始只拥有菲律宾,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却迅速增加。当时美国从东南亚进口所需橡胶的90%,所需锡的75%,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美国石油资本在20世纪20年代投资印度尼西亚石油开采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在印尼的石油生产占印尼石油总产的27%,并拥有一家炼油厂。美国与东南亚经济的结合已相当紧密,1938年美国购买菲律宾全部出口的77.2%,这一数字在马来亚为30%,在印度尼西亚为13.6%,这种密切的经济关系使美国与这一地区相互依赖程度大大提高,也正因如此美国不能向日本的“南进”政策让步。战后日美经济关系的发展也构成了日本地位不断提高的基本原因。P. A. Varg, “The Myth of the China Market, 1890—1914”,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Vol.73, 1968; G.R. Hess, United States Emergence as a Southeast Asian Powers, pp.920.
从地理上看,美国是一个两洋国家,对美国来说,欧洲及大西洋的战略地位远远高于亚洲的战略地位(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变化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是优先解决大西洋问题。因为正像美国海军总部委员会在1907年春说的那样,“我们过去没有,在最近的将来也不会有充分的舰只同时控制两个地区(两大洋)以对付欧洲和日本的进攻,或者两者中一个的进攻”。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非常明显。1940年,日军向南洋进逼,此时美国舰队已集中于太平洋,但它就像1908年一样也是一种威慑工具。考虑到大西洋更为紧急的情况,罗斯福不得不承认,必须同日本谋求妥协,“想缔结一项联合公约,以维护太平洋的和平”。要不是日本不肯罢休,美日妥协是很可能出现的。W.R. Braisted, The U.S. Navy in the Pacific, 1897—1904, Austin, Texas, 1958.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2, pp.234236.战后遏制苏联的需要是美国重新确定战略优先次序的主要原因,中国地位的变化都与美国遏制苏联的成功与否有关。一度美国认为自己能够打“两个半战争”。结果越南战争粉碎了这个估计,美国不得不回到“一个半战争”战略上去,寻找同中国的和解。
意识形态也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对华政策白皮书认为,美国不能影响中国是由于中国的内战、分裂和落后。但1949年以后,尽管中国在统一和强大方面的进步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但意识形态的因素使美国长期敌视中国。1970年前后这一情况才有所变化,但是这一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直到1983年,美国国防部仍把中国列在“潜在敌人”的“P类”国家,严格控制对华技术转让。1983年后中国虽然进入了非盟国友好国家的“V类”,但是仍然得不到同等待遇。80年代中国地位的再度下降,也与这一时期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回升有关,而日本与东南亚当然不受这一因素的影响。L. Sullivan Jr. and D. S. Hollard, The Trad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China Policy for Next Decade, The Atlantic Councils Committee, 1984, p.294;兰德公司:《如何处理战略三角关系》,刊登于《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1988年,第2627页。
四、对美国未来东亚战略优先的思考
在以上几种战略优先次序下,美国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主要战略目标,但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可观。但不同次序还是有不同的收获和代价。在太平洋战争前,美国维护了在东南亚的利益,但相当大程度上损失了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和机会,尽管美国把对日和平维持了多年,但是最终没能逃过一场恶战。这一战略次序的缺陷是明显的,它的有效性依赖于日本自我限制不向东南亚扩张,一旦日本抛弃这种限制,这一次序就解体了。战时设计的优先次序几乎没有起作用就放弃了。40年代末形成的战略优先次序使日本及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美国影响下,但是美国先后打了朝鲜与越南两场战争。这两场战争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是要保卫日本和东南亚。但日本对越南战争却持批评态度。在这一次序下日本经济与西方经济形成了一体化,但同时也构成了对美国经济地位的挑战。Welter Lafeber, “Decline Relations During Vietnam War”, in The United and Japan in The Post War World, pp.101102.
在70年代形成的战略优先次序下,美国在东亚地区付出的代价显然最低。东亚地区各种力量形成了阻止苏联势力扩张的强有力的阵线,东亚本身保持了稳定与和平的局面,并出现了普遍的繁荣。与过去的情况相比,或者与中东及欧洲相比,美国在东亚的政策可谓是低代价、高效益。当然问题也是存在的。在这一战略优先次序下,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正渐渐被日本的影响替代。目前,美国对东南亚的贸易、投资、援助和贷款都明显低于日本,日本的政治影响也会随着其经济作用的扩大而上升。美国也不会放弃目前的方针,斯卡拉皮诺认为,美国自己不打算在东南亚承受过重的和不相称的负担份额,它将同日本合作以解决在东南亚面临的复杂关系。这肯定是一条充满困难的道路。郭昭烈:《日本和东盟》,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3956页;R. L. Scalapino, “Formulating an American Agenda for Asia”, in USJapan Relations, Agenda for the Future, ed., by R. A. Mors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9, p.12.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它维持东亚利益的主要支柱,过去如此,今后一个时期也将如此,但是从以上归纳的几种战略优先次序来看,军事力量的作用已逐渐缩小。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已在世界上名列榜首,经济因素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已越来越重大。东亚各国已越来越明显地把经济合作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而将它们间的意识形态及各种其他分歧搁置起来,希望时间的流逝和利益上的相互依赖会减少那些分歧的影响。在这种趋势下,美国要是不能改进它的经济竞争地位,不能根据东亚的情况调整有关政策,继续让自身经济利益服从政治或安全方面的过高要求,那么,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也许会进一步下降。同样如此,美国在进行新的战略优先选择时,如果缺乏长远计划,过分强调军事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因素,那么这种战略优先次序很可能给东亚和美国自身都带来严重的后果。今天一些美国人已经认识到,在亚洲“现在经济因素超越了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考虑,不久以前还没有达到这一程度”,他们也意识到“经济民族主义在高涨”。但他们似乎依然认为,经济安全还远不如军事安全重要。他们看到日本把经济安全作为全面安全的重点,同时不发展“戴高乐式的”军事力量就感到十分放心,而对中国有一支力量有限的军队总是耿耿于怀。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太平洋的地区主义,前景与问题》,刊登于《新趋势与新思维》,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1989年,第3753页。
意识到新局面正在出现,但又不愿面对这种现实,这就是美国今天的困惑。它将影响新的东亚战略优先选择。
在远景与渐进之间
——美国的和平崛起及其对外部资源的利用*
*本文原发表于《国际观察》,2004年第4期。
①Robert E. Gallman,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ed. by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55.
美国经济在19世纪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尤其是在美国内战以后,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主要工业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美国的工业和农业产值都已居世界首位,它的经济总量超过了英、法、德三大国的总和。经济上的能力给了美国逐渐主导一战以后国际事务的巨大支持。但是经济能力本身并不能直接形成一套持久的国际秩序。①
在19世纪末期,美国国内一度出现很强的实行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要求。在强大的经济能力的支撑下,美国的军事力量开始扩大,1898年它与西班牙的战争被公认是一场帝国主义的战争。尽管打赢了这场战争,而且美国也从战争中得到了殖民地战利品,但是美国却没有沿着武力扩张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相反,在一次大战期间,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政府提出了战后国际秩序的不同主张,这一主张对战前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国际秩序形成了巨大的挑战。虽然威尔逊的政策当时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支持,但是此后20世纪国际新秩序的形成同他的这些设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首先要分析外部资源的利用在美国崛起过程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其次要分析20世纪初期美国利用外部资源的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最后本文将分析这些变化对美国该时期的对外政策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对于“帝国主义”的概念采取比较狭隘的定义,仅指近代以来用武力征服或以少量军队加上经济压迫来统治世界的历史进程,它在20世纪初期达到了高峰,并在此之后渐渐衰落。有关帝国主义的定义见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邓正来主编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1372页。
一、美国的土地扩张和移民政策
19世纪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扩张的世纪,大规模的土地扩张和快速的人口增长构成了其经济发展的基础。美国在1803年以1500万美元从法国购买了大路易斯安那地区,这次扩张使美国的国土面积几乎增加了一倍。1819年美国又从西班牙手中买下了面积达72000平方英里的佛罗里达地区。40年代,美国通过扩张和战争得到了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及俄勒冈等地,使美国成为领土上横跨两洋的国家。稍后,美国还从俄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并吞并夏威夷诸岛,国土总面积达到了300万平方英里以上。Gallman,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pp.1213.
19世纪美国的对外扩张主要是利用有利的国际时机,从传统的殖民大国如法国、英国及俄国手上购买土地。其次是利用战争后的有利局面强买土地,如从西班牙和墨西哥得到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最后是在亲美国的移民发动叛乱控制有关地区后,让他们以合法方式并入美国,如得克萨斯和夏威夷。美国的大陆扩张表现出资本对土地的贪婪性,而且包含着一定的帝国主义扩张的成分,但从美国治理这些地方的方式看,它基本上是通过建立美式民主制度而不是通过殖民主义实行统治。
通过扩张得到的土地资源对美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联邦政府本来就拥有英国殖民时代已得到的中西部土地,而且也拥有后来扩张所得到的土地。它从一开始就制定了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化政策。1785年美国通过土地法令,要求对公共土地进行测量,将这些土地划成6平方英里的基本单位,以便将土地出售给个人。在最早完成划分的俄亥俄州,这些基本单位又被细分成640英亩的地块拍卖。当时的价格为每英亩1美元。1795年国会将最低地价定为每英亩2美元。同时,国会还制定了土地购买的贷款和拍卖制度。进入19世纪,国家对购地条件不断放松。1832年最低地价降到每英亩40美分,最小地块降为60英亩,以方便不断增加的普通定居者购买。1850年代,政府拥有的土地达到了12亿英亩,为了更快地卖地,它还将质量较差的土地价格大幅降低,按当时的市场价格,这类土地每英亩只值十几美分。1862年通过的“宅地法”规定,在一地居住了5年时间的定居者可以得到160英亩的免费土地,他们只需要出50美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家庭农场。联邦政府还以各种方式赠送土地,如为退伍军人免费提供土地,向各州提供公共土地,向州立大学提供免费土地,甚至向铁路公司提供免费土地,鼓励他们向更广袤的地区建筑铁路。Jeremy Atack, etc., “Northern Agriculture and the Westward Movement”,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ed. by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pp.292296; Richard Sylla, “Experimental Federalism: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Government, 1789—1914”,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ed. by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pp.494495.
通过这些措施,美国的土地资源很快转变为财富,大批土地被投入经济开发过程,并产生了巨大的利益。从1850到1860年,伊利诺伊州的农业用地增加900万英亩,艾奥瓦州增加了700多万英亩。这一时期全美新增加的农业用地超过1亿英亩,新建立了60万个农场。Jeremy Atack, etc., “Northern Agriculture and the Westward Movement”,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pp. 298299.应当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当时只有非常有限的财政来源。关税、酒烟专卖税和出售土地的收入是它的三项主要收入。尽管政府很“穷”,但是联邦政府始终坚持以低价出售土地的政策,而不是利用垄断性的地位来获取土地收入。从历史角度看,这种让利于民的政策是极富远见的方针,因为迅速的土地私有化进程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而且也为州和地方政府征收财产税提供了基础。实际上,它成为一种政府和公民双双得利的资源。
19世纪是美国农业生产率迅速增长、单位产量不断提高的时期。农场主的收入明显多于其他劳动者。土地资源的意义当然不止于提供了美国农业的发展必要条件,其实它还是美国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如进行矿山的开发和铁路的建设。它是美国人口增长、技术发展和资本积累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从独立成功到1909年,美国的土地增加了3.5倍,而从1774年到1909年,美国的资本总量增加了388倍。土地资源对资本总量增加的间接作用是不可忽视的。Gallman,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pp.1213.
1898年,美国在对西班牙的战争中不仅以武力夺取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而且在菲律宾建立了直接的殖民地统治,它还将古巴变成了它的保护国。但是在这一战争后,美国基本上放弃了直接占有外部土地,转向间接地利用外部土地。对外贸易的统计表明,在美国的出口当中,农产品等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增长率在下降,这些产品的出口在1918年达到顶峰,而在技术密集基础上的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在同一时期则迅速增长。Peter H. Lindert, “U.S. Foreign Trade and Trade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3, p. 407.
作为一个前殖民地国家,土地是美国大陆扩张的主要目标。但是由于北美大陆人口稀少。美国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直接占有大量土地,但是无须进行殖民主义统治。通过有关法律规定,美国新得到的领地在定居人口达到一定数量时,就可以建立议会,并逐渐过渡为一个新州。这种政策推动了各领地争相招揽移民,以便早日建成州一级的政府机构。
美国在其崛起过程中利用的另一种重要的外部资源是人口。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海外移民是美国经济在19世纪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由于土地迅速增加,这一时期美国的劳动力更为缺乏,19世纪前期,西部的土地的增加,贩运非洲奴隶的禁止以及北方的制造业都需要大量劳力,这些因素为美国带来巨大的移民需求。
据不完全统计,从1790年到1920年的美国全部人口增长中,来自海外的移民增长份额占了25%。从1819年到1920年的100年当中,有3370万移民进入美国。这一时期移民的年增长率为4.9%,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最高峰时,每年进入美国的海外移民达到了100万人以上。从东部到西部,从农村到城市,外来移民不仅弥补了美国劳动力紧缺的不利因素,为美国废除丑恶的奴隶制度准备了条件,而且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Michael R. Hain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920”,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pp.187, 198.
19世纪移民前往美国的原因基本上是经济性的。统计数字表明,移民数量的高峰和低谷与美国经济的长期性波动有密切的关联性。自由移民在很长时间内是美国的一种基本政策。这种波动表明美国较好的经济条件对移民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它也表明海外移民的到来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统计表明,美国农业、铁路和制造业如果没有移民劳动大军的加入,其发展时间就会大大推迟。
大部分的海外移民来自欧洲,他们在19世纪远渡重洋到美国,不仅需要支付较高的旅费和初期的生活费用,还必须受过基本的教育,并拥有一定的劳动技能。他们的到来减少了美国经济过程中的工资费用,增加了土地和住房方面的租金收入。统计表明,在1850到1860年,外国出生的人拥有的不动产比美国本土出生的人所拥有的不动产少一半。历史学家们认为,在19世纪进入美国的移民有2000多万,因此加大了美国经济上的不平等。Clayne Pope, “Inequal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pp.116117.
美国长期执行自由的移民政策,虽然曾经发生过多次“老移民”排斥和歧视“新移民”的风潮,但是这类事件在1880年以前并没有影响美国联邦政府的自由移民政策。然而,生活水平已经明显上升的美国工人已不再能容忍移民无限制的涌入,他们害怕新移民会不断降低其收入。激烈的竞争使这一时期的美国人普遍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将早已在美国发酵的种族主义当作抵御不安全感的思想武器。在这些人的压力下,1882年,美国通过了第一个限止自由移民的法案“排华法”,这一法案的通过不仅反映了美国对亚洲移民的歧视进一步加深,而且它是美国经济结构变化的产物,说明了它对廉价的体力劳动者的需求已经明显减少。
188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禁止输入合同工人的法案典型地表明了这种排斥是出于经济的目的。到20世纪初期,随着美国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组织的工会力量增强,产业工人和其他行业的社会活动对政治的影响扩大了,对亚洲移民的排斥,特别是中国移民达到了新的高潮。1917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限制自由移民的法案,自由移民的政策终于结束。James Foremanpeck, A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since 1850, New Jersey, Barnes and Nolbe Books, Totowa, 1983, pp.152154.
二、从引入资本到输出资本
与欧洲一些国家相比,美国的工业化开始得较晚一些。从殖民地时代开始,美国就一直利用外部资本来加快自己的发展。美国的储蓄率在19世纪早期平均约6.5%,到19世纪末期这一比率曾经接近20%。虽然在独立后美国发展主要依靠的是本国资本,从1799年到1900年1个世纪中,美国总体上的资本增加量几乎达到600亿美元,而外部资本只占这个增量中的5%,也就是30亿美元左右。因此,有的经济史学家认为,外部资本对于美国的崛起没有多少意义。Lance E. Davis and Robert J. Cull,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s, Domestic Capital Market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820—1914”,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p.734.
但如果不是仅从数字本身来观察的话,人们对外部资本的作用就会有不同的认识。首先,在某些特殊阶段,外部资本可能在美国净资本形成中占较高的比例,如19世纪上半期的西部开发,中期的战后重建以及铁路大开发时期就是这样。在这些时期,美国经济的多种有利发展条件对资本构成了爆炸性的需求,但是美国自身储蓄率的增长并不能满足这种需求。外部资本因此起到了弥补差距的作用。例如,当年美国政府购买大路易斯安那地区的资本就是向欧洲市场借来的。此外,在某些特殊的投资领域中,外部资本的风险投资作用也会起到难以估计的先导作用。特别是在19世纪前期和中期,美国还远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它也缺少成熟的金融机构,美国储蓄人和投资人的投资方式还较为原始,在这种条件下,来自欧洲的投资者的经验和引导就有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美国各级政府为引进外部资本做出了很大努力。19世纪初期的联邦政府虽然并不愿意发行政府债券,但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它也不得已地靠借债应付巨大的开支。但美国的一些州政府较早地利用外国资本来推动经济发展,解决道路、运河建设和土地开发等方面的资本短缺。Susan Previant Lee and Peter Passell, A New Economic View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W. W. Noton & Company, 1979, pp.307310.在1840年后,许多州政府因财政困难而推迟还债,这在欧洲资本市场造成了严重的信用问题。一些州的议会改写他们的宪章,以限制州政府的借贷能力。
但联邦政府在这一时期开始向欧洲贷款,以支付因取得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等地而产生的联邦费用。此外,联邦政府在内战和重建时期也借下了大量的欧洲资本。同时,美国各地的城市和地方政府成为外国资本的主要吸纳者,他们将这些资本引入本地的农业、运输和城市基本建设方面。为了较快地得到外国资本,许多地方政府还在国际市场上竞相以高成本借贷。从1865年到1914年,英国市场为美国公共债务提供了16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1880年以前投入的。可以说,美国这一时期的城市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靠外部资本支持的。Lance E. Davis and Robert J. Cull,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s, Domestic Capital Market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820—1914”,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p.752.
从1830年到1839年,美国得到净外部投资近1.7亿美元,这在当时等于人均得到了12美元的外部资金。在1850年代,大量外资进入美国公私债券领域,其中相当部分进入铁路债券。从1860年到1869年,从外部进入美国的净资本达到了7.61亿美元,人均分摊到了21美元。1868年,一家刊物指出:“有7亿美元的美国联邦债券是在外国人手上,……财政部长麦克库伦估计,不算铁路股票,外国在美国的投资约为8.5亿美元,而所有的外国人手中的美国证券总额达到了9.38亿美元。”考虑到当时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不超过15亿美元,外部资本对联邦政府债券的投资就相当可观了。Lance E. Davis and Robert J. Cull,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s, Domestic Capital Market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820—1914”,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pp.738739.
外国投资的另一高峰是1882年到1896年,在这15年中,外部资本的净流入总额为17亿美元,这些外资的大部分投入了私人企业,其中大部分购买了美国铁路公司的股票证券。这一时期的外部资本对于美国铁路高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856年,美国第一家铁路公司的股票在阿姆斯特丹股票市场上市,4年后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的美国铁路公司就达到了7家。铁路、船运和交通等基本设施的大量投入对于美国在19世纪后期20世纪早期的高速增长具有重大意义,它与充沛的土地资源一起构成了这一发展的主要条件。Lance E. Davis and Robert J. Cull,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s, Domestic Capital Market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820—1914”,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p.751. Susan Previant Lee and Peter Passell, A New Economic View of American History, p.267.另一得到外国资本的领域是美国的采矿业。从1865年到1914年,大约有1亿多美元的英国资本投入到了这一领域,这大约占投入采矿业的所有外资的一半。统计表明,从1815年到1914年,外部资本为1500家到2000家美国矿业公司提供了财政支持。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外资投入到美国的土地开发和农业领域,1883年资料表明,得克萨斯一地有500万头牲畜是外国人投资饲养的。
美国在19世纪中期以前缺乏成熟的资本市场,投资人对于将他们的资本用于远离自己的地方感到不安,储蓄者也只愿将资本交给有着个人关系的投资者。这是一种前现代的资本活动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欧洲资本的进入显然有助于美国资本在储蓄人视野之外的经济活动中形成。在19世纪晚期随着美国国内资本的增加,美国自身的资本市场才逐渐改进和成熟起来。这一时期美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完善的银行,并且发展了各种非银行中介金融机构,如各种保险公司、抵押贷款公司和证券交易机构等。这些机构推动了美国资本的加速积累和流动。一位经济史学家说:“内战后经济的大规模增长和结构变化带来了巨大的需求,而正是制度创新使得美国资本市场能够对此做出反应。”Stuart Bruchey, The Wealth of the Nati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8, pp.104108.
在19世纪大部分的时间内,美国一直是国际社会中最大的债务人。但到了一战前,尽管美国仍有大量的外国投资,但是美国资本的流出已经大于流入。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投资在1900年总额为9.1亿美元,1908年这一数字上升为25.8亿美元。而在1914年则达到了48.2亿美元。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919年,美国对外投资总额已经达到了122亿美元。大量和高速增长的美国资本输出表明,美国对国外资本的需求已经大为减少,它对外部资源的利用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直接取得外部土地和劳动力的意义已经降低,而对外投资成为美国利用外部资源的更有效和更主要的方式。
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在加拿大、欧洲和墨西哥,1914年,这三地分别占的比例是21.6%、23.3%和22.1%。进入20世纪后,美国在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的直接投资虽然增加较快,但是这两地同期得到的直接投资只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4%。这种情况说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干预对于资本输出未必有很大的作用,投资人主要考虑的是获利的可能而不是这种投资能否得到美国军事或政治力量的庇护。从美国资本的投资领域看,它在欧洲的投资主要是商业和制造业。在加拿大的投资领域分布得较为平均,但在中南美则重点投入采矿和铁路建设。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是利用当地资源,如南美的水果资源、东南亚的橡胶资源等。还有一部分对外投资是为了推动美国产品的出口。Rarry Eichengreen, “U.S. Foreign Financial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3, pp.476, 468469; Lance E. Davis and Robert J. Cull,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s, Domestic Capital Market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820—1914”,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pp.788792.
内战后,美国的储蓄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率逐步上升,在1899年到1908年期间,它的年储蓄率达到了29%。从1894年到1903年的年净投资率则为19%。这些储蓄中相当大的部分投入了美国国内的经济过程,在20世纪的很长时间里,海外投资只占美国投资总额的一小部分。当时的储蓄率比对外投资率增长得更快,这表明资本输出的增长是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较自然的变化。Robert Gallman,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pp.3940.在美国进入20世纪时,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国内经济结构和制度变革所产生的巨大能量,这种变革使美国得以在更深层次上利用已有的国内资源,同时将外部资源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这种发展道路为美国的下一步崛起奠定了基础。W. Elliot Brownlee, Dynamics of Ascent,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pp.357358.
三、美国利用外部资源方式转变的原因
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对外部资源的利用方式发生了变化。它是美国经济与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反映,是美国初步迈入现代化社会的表现,同时也是美国适应世界经济更紧密地整合的措施。
经过19世纪的快速发展,美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美国从一个世界主要的农业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1870年,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占43%,到190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65%。美国不仅在钢铁、制造、采矿等传统工业领域中超过了欧洲工业国家,而且在电器、化学和石油等新兴工业领域中异军突起,展示出了强大的发展势头和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农业经济在美国经济整体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了,依靠大量土地投入和劳力投入的粗放型农业模式已经无利可图,农业的生产率只是在机械化和集约化的推动下才继续提高。Stuart Bruchey, The Wealth of The Nati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 & Row,1988, p.100; Jeremy Atack, Fred Gateman, and William N. Parker, “The Farm, the Farmer, and the Market”,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pp.272284.
美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建立在新技术和新产业基础上的,它具有后发国家的优势。同时,美国工业经济的规模生产也非常突出。这一时期,美国出现了公司合并浪潮,许多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以托拉斯和康采恩方式组成的企业大量涌现。1901年,占公司总数1%的企业生产了美国所有工业制成品的40%。Neil A. Wynn, From Progressivism to Prosperity, World War I and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Publisher, 1986, p.3.合并与联合帮助美国企业降低了产品成本,增加了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占有率,并加强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工业的发展使美国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入制造、交通及建筑业,以及转入城市服务业,到1900年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的劳动力仍然在农业领域工作。Robert Margo, “The Labor For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pp.214216.这一数字也反映了美国此时的经济结构性变化。
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美国的人口构成相对年轻,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明显提高。虽然工人阶级的处境还是不好,但他们已经强大到可以争取分享经济发展的利益。农民的地位不如过去,但是城市化的加速减轻了农业收入相对减少的压力。一个由专业人员、城市白领、农场主和小企业主构成的中产阶级在稳定地发展,甚至一些技术工人已经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美国人的收入已经达到世界前列,他们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城市化和教育的普及化为下层阶层向上流动提供了机会,这次变革弥补了美国国内因“边疆消失”而放慢的平面流动机会。Stuary M. Blumin,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U.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p.849.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逐渐采取了抑制垄断、允许建立工会、加强了各类劳工立法、开征累进所得税和建立联邦储备制度等改革性措施。这些变化有力地推动了中产阶级的扩大,帮助了美国以较快的速度向现代化社会的方向发展。
从1873年到1896年,西方一些主要工业国家发生了较长时期的萧条,而短时期的恢复并不能改变经济不景气的状况。这种周期性危机使得对外投资变得更具有吸引力。经济界和金融界越来越依靠政府来推动它们的利益。长期萧条以前的20年里,欧美国家之间的贸易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已经得到了扩大。但是在萧条导致商品价格下跌后,各国不得不转向采取关税保护政策。德、法、俄三国在1879年到1902年的十多年中两次提高了关税。而本来关税就高的美国当然也不会落后,它在1890年和1897年也两次增加关税。工业大国的这种行为表明,工业品的增产速度明显地超过了它的消费速度。这种保护主义风潮的后果是,贸易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工业国家间相互的贸易相对减少,而他们向非工业国家的出口则明显增加。在19世纪50年代,英国出口总值的20%输往美国,而到19世纪末,它的出口中只有6%是输往美国的。Tony Smith, The Pattern of Imperialism,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nd the Lateindustrializing World since 1815,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38.保护本国市场其实只是当时大国贸易战的一方面,更激烈的竞争是争夺世界非工业化地区的市场,这种形势使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对欧美有了更大的吸引力。
美国在19世纪后半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欧洲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国家建立了共和制,有的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继续维持专制制度的国家明显减少。工业化在所有国家都迅速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后果正在对更多的社会阶层产生影响。这些变化使很多美国人感到,他们与欧洲的差别正在消失,双方的制度已越来越接近。当时有位历史学家乐观地指出:“在政治和审美趣味对立的下面,已经不再有老欧洲和新欧洲之分,只有一个共同的、受经济驱动的形成中的新世界。”Daniel T. Rodgers, 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52.
在对外政策方面,如果说欧洲国家中普遍出现了通过扩张而获得安全的要求,这种扩张要求就来自于工业大国内政治联盟的需要。这一联盟中的各集团都指望通过对外扩张、加强军备或构建自成一体的经济而得到各自的利益。这些集团当中既有经济团体,也有官僚机构,它们都是以保护国家生存的普遍利益为借口的。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31.
此时的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政界、企业、军队、媒体及传教集团中都有要求对外扩张的庞大势力。这些势力将欧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扩张政策看作是美国进入国际政治的正常途径,希望美国加快速度走上这条道路。他们以传播文明为名,宣传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让普通美国人相信这是保护美国安全的最好办法。在他们看来,如果不进行对外扩张,美国将失去进入亚洲市场的机会,甚至失去在加勒比和南美洲地区的优势。这些集团要求政府扩大军备开支,加强与其他大国的世界性竞争。美西战争正是这样一种帝国主义思潮下进行的。
但是美国也存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对于美国在世界中的作用有着不同的看法。随着美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美国国内对于如何处理战后问题发生了争论。虽然同欧洲有千丝万缕的文化与历史联系,但美国经历过殖民统治的历史使一般美国人在观念深处不赞同殖民主义制度。他们相信这种制度是反民主的,如果美国自己也走上这一道路,美国的民主制度就会面临危险。纽约的一家报纸说:“除非我们放弃民主制度的基本观念,否则我们就不能拥有殖民地、附属国和臣民。”他们借用林肯的话说,帝国主义就是“为了他人,由他人来统治他人的政治制度”。
美西战争以后,麦金莱政府做出了吞并菲律宾和波多黎各的决定。但是国内反对美国走上帝国主义扩张道路的声音却越来越响。由于传统上的反殖民主义的原因,美国社会和公众对以国家与军事力量去控制一个外部社会是非常反感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乔治·霍尔说:“自从新教徒在普利茅斯登岸以来,我们面临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将不得不从一个建立在独立宣言基础上的,受到华盛顿教导指引的共和国,转变成一个庸俗的、联邦制的帝国。”Frank Ninkovic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mperialism,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p.45.对美国反帝国主义思潮的长期性作用,历史学家了解得还不太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的影响决不只限于美西战争时期。
这一争论反映了在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后,美国社会对于未来如何参与国际政治,如何获取及利用外部资源有着深刻分歧。麦金莱总统在1901年指出:孤立已不再可能,也不再可取。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于世界其他国家之外。美国人意识到,由于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世界市场已经形成,传统的不参加欧洲大国竞争、只维护美国在美洲的霸权地位的政策已无法维持。Frank Ninkovich, The Wilsonian Century, U. 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0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99, p.25.显然,美国的制度与欧洲制度仍然有着重要的区别,美国国内那种公开而充分的政策辩论在当时的欧洲是难以开展的。此外,欧美各国当时仍然面临着贫穷、阶级冲突、城市犯罪等各种社会问题,但美国明显地比欧洲更注重以国内资源和改革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19世纪后期,通过对外扩张来保护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是工业国家中很普遍的想法。尽管当时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从事扩张和侵略的国家实际反而会因此受到安全上的损害,但许多工业化大国仍然以扩张主义作为推进国家利益的理由。美国在美西战争前后也表现出扩张主义的倾向,但是美国并没有将武力扩张和夺取外部领土看作是它走向世界的唯一出路。公众反对殖民主义的呼声对政府形成非扩张的方针有很大的影响。
在此同时,美国的对外扩张也受到其他大国的坚决抵制。从1902年起,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就试图利用日本抑制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垄断性统治,并借此为美国扩大在中国的利益。但是,在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在中国的垄断行为比沙俄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日本还表现出向太平洋地区扩张的强烈愿望,这使得老罗斯福非常不安。由于担心菲律宾的安全受到影响,他不得不对日本违反门户开放政策的行为妥协。当初美国占有菲律宾是为了扩张主义利益,现在反倒成了心病。Raymond A. Esthus, Theodore Roosevelt and Japa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1967, pp.190191. 而菲律宾人民的反抗也表明,美国不可能担当一种所谓传播文明的角色。老罗斯福在1907年说,美国将不得不准备让这些岛取得或多或少的独立。5年后,他干脆承认,美国保留菲律宾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利益了。只有10年的时间,不仅过去喧嚣一时的扩张主义在美国公众中已失去了吸引力,而且它的积极鼓吹者对此也失去了信心。
四、对外新政策和新秩序
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在不久后产生了积极影响。1909年,曾担任驻菲律宾首任总督的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成为总统。他认为,现代文明已经创立了一种安排,发达工业国家可以在世界中进行合作。这一年,他的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hase Knox)说:“现在时代的潮流明显是趋向国际团结。”他努力推行金元外交,试图说服日本政府放弃独占政策,允许美国财团在“满洲”(中国东北)地区修筑新的铁路。塔夫脱在评论自己的方针时说:他“努力要把日本在中国的政策提高到美国的水平,……这样总比把美国的政策降低到他们的水平要强”。Ninkovic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mperialism, p.75.尽管塔夫脱的“金元外交”只是鼓吹工业化大国之间的合作,但他还是在迷信武力的日本当局面前碰了壁。然而,美国已开始转变方针,它不愿再进行传统的殖民主义扩张,它更倾向寻找以商业方式获取外部资源的新途径。
到了伍德罗·威尔逊时代,美国的态度有了进一步变化。虽然继续在拉美维持着霸权主义的政策,但威尔逊从自由主义立场上渐渐意识到,欧洲的大国外交是竞争性民族主义的产物。他认为,现代人正在使世界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虽然商业上的进程对此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虽然有经济上的相互联系,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共同感,各国外交仍不能超越受利益驱动的那种生意上的逻辑,就像“金元外交”那种性质的关系。“唯一能使世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同样沉默的、有全能力量的人的舆论。”Frank Ninkovich, Modernity and Power, A History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58.
大多数新兴的工业国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都不能摆脱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的诱惑。经济衰退使主要工业大国间的贸易相对减少,同时他们对非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则迅速增长,这些国家开始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常常感到不安。德国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1882年不情愿地认为,由于德国越来依赖外贸,占有殖民地就成为保护德国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19世纪90年代,德国统治集团将扩张主义看作是维持国内团结和扩大殖民统治的最好方式。没有民主传统的德国中产阶级被这一集团的利诱拉下了水。Tony Smith, The Pattern of Imperialism, p.38.
刚刚进入工业化的日本统治集团认为,世界上一些落后的地区不仅容易征服,而且这些地区有着丰富的资源。如果日本不去占领,这些地区很快就会落入到竞争对手的控制下。这种理论对缺乏经济和军事资源的日本来说具有特别强大的诱惑力。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3.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就开始了它的对外扩张进程,它先后夺得琉球、台湾、辽东半岛及朝鲜半岛等地。它的殖民地从无到有,在20多年中扩大到100万平方英里。虽然日本战胜了中国和俄国这样的传统大国,但是它同德、英、美等主要工业大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而且,它的政治权力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为一个骄横跋扈的军人集团所把持。结果,日本离民主改革的目标和国家安全的目标都越来越远了。
美国一直在努力寻找能适应时代变化的对外新政策。进入20世纪,由于具有了资源和竞争能力两方面的优势,美国国内关于贸易政策的辩论日渐激烈起来,随着辩论的展开,自由贸易的原则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工业集团认识到,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对美国经济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现存的帝国主义秩序对美国的竞争地位构成了不利的障碍。这一辩论不仅有利于克服国内的政治障碍,而且有利于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当世界各地的联系已达到密不可分的程度,自由贸易原则必然代表着一种面向未来的取向。它的鼓吹者也自然会由此而受益。
塔夫脱的共和党政府已经在改变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调,但国会中仍有强大的保护主义势力。到1912年大选时,威尔逊提出了“新自由”的竞选纲领,他以“有竞争力的关税”这一口号来表达自由贸易的立场。在这一年大选中,强调保护主义的进步党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输掉了选举,而赞成自由贸易原则的民主党人则在参众两院都获得了多数。1913年,在威尔逊领导下,国会通过了大规模减少关税的改革法案。Michael J. Hiscox,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57.
美国虽然没有将帝国主义扩张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但是它的新方针并不是很快形成的。美国在这一时期一直有同其他列强加强合作的倾向,这种倾向有时表现为对列强的扩张进行温和的抑制,有时也表现出向它们的垄断地位进行妥协。其实,这种合作既是它自己的某种扩张愿望的谨慎表现,也是它为参与大国政治寻找合适方法的尝试,这种方针还减少了外部世界对它崛起的阻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威尔逊开始把反对列强军事竞争和大国外交放在对外政策的首位。虽然英法被美国看作是民主国家,但威尔逊仍然小心地挑战它们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方针。他曾明确提出,应当以集体安全代替过时的均势外交。如果将世界的未来委托给一种“跨国结构与民族主义思想的易燃结合物”,自由国际主义将不可能维持生存。“任何争议,不管涉及多小和多有限的问题,如果发展到战争的地步,都可能再点燃烧遍世界的大火。”Ninkovich, Modernity and Power, A History of the Domino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4456.
困境中的英法两国表面上接受了他的“十四点计划”,但心中仍打算在赢得战争后再来保卫自己的帝国。威尔逊的政策在战后不能被其他大国接受,正说明了他的对外政策已经具备了新的原则,英法意日等国的拒绝是因为这一政策中包含了颠覆其殖民帝国的危险。而在美国国内,一些原来支持威尔逊的进步主义力量则因为他的妥协而失望地离他而去。对于威尔逊的失败可以有多种解释,而根本的问题是,美国对传统国际秩序的挑战,无论是原则上还是方法上都是渐进性的。在当时,威尔逊政府既没有能力,也缺乏国内的政治支持来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Frank Ninkovich, The Wilsonian Century: U.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66.但从本质上看,这是美国在推动国际秩序发生渐进性变革,是它既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又要在价值观念上领导其他大国的精明之处。
美国在20世纪早期提出的一些方针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潮流的,并且或迟或早地产生了世界性的重大影响,这些方针包含了20世纪新秩序的主要原则: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民族自决、大国合作以及集体安全等。这些原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确立起来,而美国在该世纪初期已开始尝试它们。与此相反的是,其他一些工业大国执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并没有为它们带来想象中的贸易和安全利益,两次世界大战及其结果最终表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国际秩序是无法维持的。
本文的结论是,美国在19世纪末改变了对外部资源的利用方式,它较自觉地意识到了对外部资源的利用只具有相对意义,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充分的资源使它可以在利用国际资源和国内资源两个方面保持平衡。在此同时,美国经济和社会也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的是,美国维持和发展了早期的反对殖民主义的价值观念,它在尝试了扩张主义方式以后又基本摒弃了这种道路,从这一角度看,它也保持了物质进步与文化价值的新的平衡。这一时期美国在参与国际政治和经济进程中敏锐地看到了世界潮流的发展方向,但它也遵循了渐进地改变现存秩序的方针,在远见性和渐进性之间适当地保持了平衡。正是这些变化和平衡使美国在20世纪中能够和平的崛起,成为主导性的世界大国。
退向未来
——保守主义思潮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
*本文原发表于《美国研究》,1996年第1期。文章标题受两篇美国学者的论文的标题启发,他们是米尔斯海默的《退到未来,冷战后欧洲的动荡》(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0, pp.556)和格雷的《退回将来,威尔逊主义的危险》 (John Gray, “Backward into the Future, The Perils of Wilsonianism”), National Review, March 29, 1993, pp.2732.
1994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可能是20世纪美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共和党人在国会处于少数地位的40年后,重新夺回了多数控制权。大批年轻的共和党候选人击败了经验老辣的民主党对手而当选,所有争取重新当选的共和党议员无一落选。此外,共和党人还新控制了十几个州的州长席位和州议会多数。
在这次选举前夕,共和党议员在华盛顿国会山推出一项名为《与美利坚的契约》的纲领。这是一份充满着保守主义色彩的文件,它在联邦预算、税收、福利、政府改革、医疗保健等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全面迎合保守势力的要求,在各种有争议的社会问题上,强调必须以保守主义的个人责任、家庭观念等价值为解决的指针。一些候选人甚至使用极端保守主义的言论煽动选民的情绪。正是这种强烈地诉诸保守主义的策略,使共和党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得以大获全胜。共和党的这场胜利是多数人始料不及的,甚至研究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也未能做出预言。Alonzo L. Hamby, Liberalism and Its Challengers, From F. D. R. to Bus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389395.
共和党人的这次胜利发生在克林顿击败小布什,上台执政还不到两年之后,而且是在美国经济稳定增长、对外政策取得一定成果之时。因此,在这次胜利的背后,可以说是存在着一些深层的原因。保守主义为什么能对选民产生新的吸引力?在对外政策领域中自由主义的影响为何会减退?保守主义在对外事务中有哪些新的观点?这些观点形成了哪些政策要求?本文将就这些问题深入地展开分析,并力图揭示保守主义思潮对美国未来对外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本文论及的“保守主义”一词,是指当代美国社会中大体上同自由主义对立的一种基本思想倾向。它以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原罪说为哲学基础,吸收古典自由主义中关于个人自由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思想,强调通过维护传统、历史连续性和稳定性来解决当代会面临的问题。文中提及的“保守主义势力”泛指美国社会中以保守主义为思想武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
一、保守主义为何来势凶猛
保守主义思潮的盛行反映了自由主义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自由主义在美国政治领域中有着长期传统,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60年代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全盛时期,它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美国公众的价值观念,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以权利平等为核心的政策。在这些政策的干预和影响下,美国在种族平等、女性权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取得了程度不同的进展。
但是,美国社会中的结构性冲突和特殊性矛盾未能由此而解。相反,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这30年里逐渐变得尖锐起来。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造成了“劫贫济富”的分化后果,中产阶级的收入长期停滞不动,新一代美国人的收入可能永远也赶不上其父辈。在种族问题上,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紧张和对抗情绪日趋加强和公开。犯罪问题持续恶化,公众的安全感进一步丧失。一位作者写道:“美国人与暴力有关的问题不是那种偶然的恐怖主义事件,而是数百万公民今天正经历着的日常生活中的恐怖。”James Petras and Morris Morley, Empire or Republic? American Global Power and Domestic Decay, New York , Routledge, 1995, pp.6375; Adan Walinsky, “The Crisis of Public Order”, Atlantic Monthly, Feb. 1995, p.39.
除此之外,公共教育制度的破产,滥用和贩卖毒品,文化产品中的色情和暴力倾向,家庭观念下降以及政府官员和公众道德水准的下降等问题也始终困扰着美国中产阶级。美国人“在国内问题上的信心感正在消失,没有人还相信美国会很快见到一个新的时代”。“整个美国弥漫着一种不断滋长的情绪:未来比过去更糟糕。”美国《外交政策》的主编查尔斯·梅恩斯 (Charles Maynes)如是说。Charles Maynes, “The New Pessimism”, Foreign Policy, Fall 1995, pp.3749.
面对各种互为因果、日趋严重而又长期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美国公众,尤其是中产阶级对自己的未来日益不安。他们对政府无力提出有效的政策深感失望,并对那些在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政策逐渐产生了怀疑。
自由主义者力图适应社会变化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正如一位批评者指出的:“自由主义在选举中的每次挫败都导致了对它进行新一轮的界定,但是每次新的界定都使自由主义变得更加不对选民的口味。”进入90年代,“人们普遍地认为,自由主义已经认同于一些几乎得不到多数人支持的文化态度及少数人的利益”。民主党人在 1992年大选中打着变革的旗号获胜,然而他们却无法从自由主义哲学中找到变革的方向,恢复选民对自由主义的信心。David Brooks, “Whats Left of Liberalism?” Commentary, June 1995, pp.6365; Alonzo L. Hamby, Liberalism and Its Challengers, From F. D. R. to Bush, p.395.
自由主义的这一状况使保守主义思想得以大行其道。保守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的种种社会政策,不但不能赢得对贫困的战争,反而要对越来越严重的目无法纪和暴力现象负责。他们强调,只有抛弃自由主义方针,并且按照保守主义的思想来构筑新的解决方案,美国才能重现 50年代的繁荣与稳定。这些主张对高度失望的白人中产阶级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们需要对眼前的问题有一种全面的解释,对未来的前途有一种可寄托的希望。可以说,美国中产阶级对现实的不满是保守主义得以盛行的主要因素。
保守主义的胜利不会是一种短暂现象。在80年代,共和党人曾在三次总统大选中获胜,但保守主义并没有能够取代自由主义获得主流地位。一位保守主义评论家在中期选举后指出:“至少在政治领域,自由派现在已失去了确定什么是主流或者什么是可尊敬的权力。”Norman Podhoretz, “Comes to counter revolution”, Commentary, January 1995, pp.4650; Arch Puddinton, “What to Do about Affirmative Action”, Commentary, June 1995, pp.2128; Harles Maynes, “The New Pessimism”, Foreign Policy, Fall 1995, pp.3749.事实上,保守主义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社会领域中也正在取得过去不可想象的进展。在60年代代表着种族平等观念的“肯定性行动”,现在已被解释为“对白人的歧视”,一度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现在被看作是敌视男性的行动,社会福利被认为是贫困的根源,等等。自由主义者现在已不得不承认,美国“正在度过它历史上最保守的时期”。
但是,保守主义的胜利未必就意味选民一定信任共和党。实际上,公众对两党政治早已失望,民意调查表明,公众认为:“整个政治制度已经破产,它被操纵在那些听不进去人意见和无法解决我们问题的局内人的手中。”他们普遍感到,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同样地“完全不了解公众的需要和关注”。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将军在他的自传中评论说,美国选民在 1992年抛弃了一位共和党总统,1994年又把一个民主党的国会拉下了台,“与其说他们在寻找一个不同的政党,毋宁说他们是在这个国家中寻找一种不同的精神”。James Petras and Morris Morley, Empire or Republic? pp.112113;《参考消息》,1995年10月10日。保守主义是否就是美国选民需要的那种精神呢?这是大可怀疑的。但毋庸置疑的是,保守主义已借助公众的强烈不满和迫切的求变情绪,重新获得了失去多年的主流地位。
二、自由主义在对外政策领域中的危机
自由主义的危机不仅表现在它无力解决众多的美国国内问题,而且同样表现在美国的对外事务方面。
冷战期间,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在对外政策领域中的分歧相对来说是较小的。在反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中,自由主义找到了表达美国价值观念及理想主义的空间。保守主义也在谴责共产主义“邪恶”,主张美国拥有军事优势方面得到了满足。他们在强调军事联盟和“集体安全政策”,防止第三世界“丢失给共产主义”等方面持有相同的观点。在越南战争失败之后,对外政策方面的两党“共识”开始破裂,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缓和与裁军、推进人权,是否支持第三世界右翼专制政权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冷战结束后,由于保守主义难以适应苏联突然崩溃后的世界形势,自由主义在对外政策领域中就迅速获得了主流地位。自由主义认为,由于共产主义的失败,任何别的意识形态都不可能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构成挑战。因此美国应把推进民主、维护人权和扩大自由市场体系作为对外政策新的指导思想。但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变化和发展却并不像自由主义者设想的那样简单。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新的国际问题与各种冲突已使自由主义思想陷于混乱与矛盾之中。
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一种真正的和平的国际秩序只有在全世界建立民主制度后才能出现,因此,美国应该为要求建立宪法民主制度的国家提供“支持”和“保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pp.318; Moton H. Halperin, “Guaranteeing Democracy”, Foreign Policy, Fall 1993, pp.105122. 这种观点为美国在世界各地推进西方民主制度和进行干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但是几年之后,人们发现关于西方民主制度的乐观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相反,在前苏联和巴尔干地区专制与无政府行为正在横行,中国并没有发生西方希望的那种变化,中东的政治地图也依然如故,非洲的一些地区甚至在发生国家权力解体。
面对各种国际冲突,自由主义者即使还没有放弃他们的观点,但也已经对如何推进民主产生了怀疑。是消极地宣扬民主自由,还是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积极进行干预? 如果推进民主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世界和平,而为了建立民主却要造成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这岂不是本末倒置吗?在后冷战时期,如何去判定一个国家是否具有民主也同样使自由主义者感到困惑。在中东地区,一些宗教极端主义力量可以通过选举合法取得政权,美国能否接受这样的民主政权?在民族主义盛行的今天,据有统治地位的民族是否会凭借投票实行一种“多数人的暴政”?
冷战后另一种自由主义的重要观点是,美国应该根据“被统治者的同意”的原则去支持民族自决运动。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任何政权的合法性都必须建立在这一政权能够获得被统治者认可的基础之上。寻求民族分离意味着该民族人民对原国家的否定,因此这种否定本身就具有要求民主的内涵。
但是,支持自决的自由主义观点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美国能够支持所有的民族分离运动吗?如果给予肯定回答,如何对待那种“根据血缘和土地来界定国家的、专制主义版本的民族主义”?这样一个独立了的民族国家是否会真正尊重其公民的权利?让所有国家都建立在单一民族基础上是否可能?它的后果又能否与自由主义希望见到的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相匹配?如果给予否定的回答,自由主义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定一个民族是否可以获得自决?一个分离后的民族主义国家会如何对待它自己的少数民族?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著名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指出: “民族主义重新造成了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因此威胁着国内的自由主义纲领和对外的全球主义观点。”Stanley Hoffmann, “The Crisi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5, pp.159177.
在国际范围内促进和保护人权是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第三个基本观点。苏联的垮台一度使自由主义者乐观地预言,美国不必再为了反苏的需要而支持右翼专制政权,保护和促进人权将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对外政策。但他们现在已经发现,首先,在一种“以国家为中心、主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人权的命运主要依赖国家的政治而不是国际的政治,“国际人权进步仍深受结构性力量的限制”。其次,他们也看到民族主义的复兴对建立保护人权制度构成新的威胁,“民族自决很难保证国际承认的人权会得到保护”。一些民族将会看到新的种族压迫替代老的种族压迫。第三,自由主义的另一目标,即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将进一步削弱许多国家中本来就缺乏的社会服务。私有化可能造成更不公平的财富和资源分配,从而破坏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人权。Jack Donnelly, “Human Right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World Policy Journal, Spring 1992, pp.249276.
一些激进的人权运动人士现在还认为,政府对一些国家乱贴民主标签,而且对有些国家违反人权公开谴责,对另一些所谓的民主国家违反人权则悄悄放过。这种双重标准的行为使人权运动人士认为,促进人权与政府推进民主制度的政策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此他们“反对使人权运动政治化”,声称人权运动“不愿意同在全球推进民主的十字军及民族自决运动联结在一起”。Aryeh Neier, “Asias Unacceptable Standard”, Foreign Policy, Fall 1993, pp.4251.
上述对自由主义矛盾的分析是在该理论本身的框架中进行的,笔者在这里有意地避免了引用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对自由主义对外政策的批判,目的是要更清楚地揭示自由主义在这一领域中的深刻困境。如同霍夫曼所说,在当前形势下,主权、民主、民族自决及人权“是四个冲突的准则和自由派完全混乱的根源”。正因如此,霍夫曼认为,“在确立优先次序和战略时,自由派政治家在寻找线索时很少能从自由主义哲学中得到帮助”。Stanley Hoffmann, “The Crisi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5, pp.159177.
三、对外政策领域中的保守主义观点
面对理论与现实两方面的困境,自由主义对外政策明显地表现出缺乏内在的一致性和解决问题的针对性。这使得保守主义在对外政策领域中影响重新增长。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些传统的分野被打破,有人抱怨说:昨天的鸽子今天变成了鹰,而昨天的鹰却变成了鸽子。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保守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似乎正在互换立场。但是,如果循着他们的哲学思路去分析,人们还是可以找到保守主义的许多重要观点的。
“最低限度主义”认为,美国应当放弃按照自己想象改造世界的那种自由主义目标。现在,美国并不面临重大和直接威胁,因此可以最低限度地承担有关的国际义务,集中力量解决迫切的国内问题。他们还希望美国放弃现有的联盟,回到一种“正常”国家的状态中去。他们反对干预主义的方针,认为除了在西半球之外,美国最好在世界上维持一种类似19世纪后期英国的“光辉孤立”那样的方针。Ronald Steel, “The Domestic Core of Foreign Policy”, The Atlantic Monthly, July 1995, pp.8590.这种观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美国公众的看法,但是,它也常常被“国际主义者”认为是一种“新孤立主义”的观点。
与此相反的观点是“里根式的国际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正是里根总统提出的理想主义目标和对美国实力的强调,加速了苏联的崩溃,使美国在战略和意识形态两方面都扩大了在世界上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美国可以利用它的政治军事优势,无限期地抵制某个全球性竞争者的挑战,抵制回到多极结构,保持现有的一极霸主地位。美国也不应当成为一个像别的大国那样的“正常”的国家,这种观点认为,“力量平衡”的战略不能防止孤立主义影响的扩大,共和党目前在对外干预问题上表现软弱,缺乏领导世界的坚强决心。Robert Kagan, “A Retreat from Power”, Commentary, July 1995, pp.1925; Zalmay Khalilzad, “Losing the Mo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after the Cold Wa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1995, pp.87108.
“原教旨保守主义”强调遵循传统。他们认为美国的力量并不在于美国的价值观,也不在于美国的财富,而是在于美国人民愿意为某种事业而牺牲。他们对美国对外政策权势集团相当反感,对总统在对外政策中的决定性地位也不满意,主张让国会在对外决策中起更大的作用。从这一角度看,“原教旨保守主义”具有平民主义的倾向,但它主要反映的是国会要求在对外政策领域中扮演更积极角色的愿望。在具体政策方面,这种观点要求加强军事力量,对结盟和多边主义都没有兴趣。Angelo M. Codevilla, “The Fundamentals of American Security”, Orbis, Summer 1994, pp.395408.
“保守的国际主义”认为,美国在对外政策中必须坚持民主理想,但将政治秩序建立在民主自由的普遍主义文明基础上是一种自由派的幻想。意识形态冲突只是出现在启蒙时代以后,而战争却像人类本身一样古老。这一观点认为,坚持国际主义对外政策的重要方法是保持世界的力量平衡。在对外干预问题上这一观点称自己“既不亲也不反”,但他们否认“低代价”的军事干预能解决问题,认为美国不干则已,要干就必须全力以赴。这种较保守的国际主义观点强调,美国应继续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在军事力量削弱的情况下,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必然受到影响。John Gray, “Backward into the Future, the Perils of Wilsonianism”; Peter W. Rodman, “Bills world”, National Review, Nov. 15, 1993, pp.3440; Peter W. “Rodman, Interven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ational Review, March 29, 1993, pp.2829.这一观点一定程度反映了新生代保守势力的观点。
近一年来,影响有所增强的是一种可称为“返回冷战秩序”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一个“多数国家同美国没有共同价值”,却尊重美国力量的世界里,美国“只能通过保卫自己的利益去追求它的理想”。这种观点虽然承认不同文化可以有“共处模式”,但它也认为由于各国价值不同,联合国不能成为美国全球性国务活动的工具。这一观点强调,一种建立在同盟基础之上,在过去50年里行之有效的,类似于冷战时期的世界秩序应是美国目标。在它看来,美国不需要冷战时期那样大的军事力量,但也不能允许军事力量过快下降。Harvey Sicherman, “Winning the Peace”, Orbis, Fall 1994, pp.523544; Paul W. Schroeder, “The New World Order: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1994, pp.2540.这些立场反映了共和党内较传统的国际主义势力的看法。
还有一些观点也属于保守阵营,如“新保守派”,他们认为美国应坚定地把推进民主作为对外政策的目标,为此可以施加经济制裁或者军事干预,这种观点被认为具有普遍主义倾向。此外还有“就业机会第一”的观点,这种观点强调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应具有最优先地位,但它有着保护主义倾向,把其他国家的经济竞争看作是对美国的主要威胁,认为政府必须保护本国的就业机会。Peter W. Rodman, “Bills world”, pp.3440.这些观点虽然对保守势力中某些人会产生吸引力,但由于这些观点背后的哲学理念是非保守主义的,所以它们不可能成为保守主义主流。
四、保守主义势力的基本政策要求
不同的保守主义派别由于视角和重点不同,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一些观点甚至大相径庭。但是将他们的不同视角作为多个扇面重叠起来,从中还是可以发现他们相互妥协的基础和共同的要求。由于这些要求不仅牢固地建立在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而且还反映着保守势力较为重大和普遍的利益,在未来数年里,这些要求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势必产生深远的影响。
增加军事开支、加强美国军事力量是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的最优先的要求。保守主义强调个人责任,这一基本价值包含着对自身力量的高度重视。面对极不稳定的国际形势,保守主义自然地回到了霍布斯的理论上,认为国际关系的状态就是“丛林里的状态”。人类的良知、国际法或更权威的机构都是无用的,这里只有弱肉强食的法则。最保守的共和党人、下届总统的竞选者之一菲尔·格拉姆(Phil Gram)参议员认为,如果狮子和羊不得不在一个世界里相处,“对美国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成为一头狮子”。这句话现在正挂在这位参议员的办公室的墙上。David Frwn, “The Righter Than Newt”, 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5, pp.8195.
与几年前相比,美国要求增加国防费用的呼声现在已明显加强。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奥布斯》(Orbis)杂志最近刊登的文章声称,美国“军队在 21世纪的战场上将发现自己使用的是过时的武器”,“现有的力量结构对于完成这一战略(同时打赢两场地区性战争)来说太小了”,“防御预算太少甚至不能支持现有的结构”。D. S. Zakheim, “A TopDown Plan for the Pentagon”, Orbis, Spring 1995, pp.173189; John R. Brinkerhoff, “The Late, Great Arsenal of Democracy”, Orbis, Spring 1995, pp.225236.这些夸张的语言显然是在为增加国防费用制造声势。
保守主义的这一要求已形成了政治气候。共和党提出的《与美利坚的契约》就明确要求增加国防开支,还要求恢复弹道导弹防御计划项目。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争相表态同意增加军费,以此显示自己立场强硬。芝加哥外交委员会进行的民意调查也表明,尽管仍有一半人认为军费应维持在现有水平上,但在公众和领导人这两部分人当中,要求增加军费的人数在增多,要求削减军费的人在减少。John D. Reilly, “The Public Mood at MidDecade”,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5, pp.7695.
巩固同盟关系,建立美国优势下的地区力量平衡,是保守主义的另一优先要求。
保守主义在哲学上对人性持悲观态度,这种理念对保守主义看待外部世界的视角具有重大影响。近两年来,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乐观情绪已经消逝,面对众多的种族和宗教冲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人口爆炸、资源匮乏、移民浪潮等问题,美国保守势力对世界未来产生了强烈的悲观情绪,其典型就是登载在《大西洋月刊》上的卡普兰(Robert Kaplan)、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和马修·康纳利(Matthew Connelly)等人的文章。这些作者搜集和罗列发生在第三世界的种种混乱与暴力现象,预言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繁荣与安全必然遭到冲击和破坏。Robert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The Atlantic Monthly, Feb.1994, pp.4479; Matthew Connelly and Paul Kennedy, “Must It Be the Rest Against West?” The Atlantic Monthly, Dec. 1994, pp.6184.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查尔斯·梅恩斯指出:“从传统看,悲观主义是富人和想保持现状的人所选择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为保守势力重新回到现实主义国际思想的轨道提供了桥梁,因为现实主义对世界的未来同样持悲观主义的看法。在另一位总统竞选者、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鲍勃·多尔(Bob Dole)开列的美国未来最重要的对外政策中,“防止一个大国单独支配欧洲”、“在东亚地区保持力量平衡”这两条占有最优先的地位,它们所反映的“力量均衡”思想正是经典的现实主义原则。Charles Maynes, “The New Pessimism”, Foreign Policy, Fall 1995, pp.3541; Bob Dole, “Shaping Americas Global Future”,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5, pp.2943.
美国对外政策研究所是华盛顿一家最积极反映保守主义要求的对外政策研究机构。该所总裁哈维·西奇曼(Harvey Sicherman)认为:“今天美国越来越面临两种选择:通过联合国采取无效的行动或者单干。但这是一种自己套上的紧身衣,最有效的行动方式仍是丘吉尔设想的地区联盟,也就是说北约和我们的亚洲安全体系。”维持和加强现有军事联盟体系是为了继续在欧洲、东亚和中东的地区保持力量平衡。通过力量平衡来保持地区稳定,对付西方面临的“共同的危险”。Harvey Sicherman, “Winning the Peace”, Orbis, Fall 1994, pp.523544.
美国保守主义势力的另一基本要求是,除非发生威胁美国重大利益的形势,对于今后发生的一般种族和宗教冲突及第三世界中的混乱,美国应避免进行军事干预。
从保守主义哲学来看,各国间的普遍和平与公正是一种可怀疑的目标。西方民主制度是多少世纪发展的产物,第三世界国家根本不可能具有民主,它们只是要夺得西方的物质享受而已。保守主义甚至不认为多元主义和宽容是民族和谐的基础。施瓦茨(B. Schwarz)在讨论美国白人与其他种族关系时坦率地说:“美国的巩固和稳定并非因为多样性受欢迎,而是因为占优势地位的美国文化被强加于其他人。”Garry Wills, The Convenient States, in William F. Buckley Jr. ed., American Conservative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70, pp.737; Benjamin Schwarz, “The Diversity Myth: American Leading Export”, Atlantic Monthly, May 1995, pp.5767.保守主义强调个人责任,实际上是将穷人的贫困和绝望处境完全归咎于其自身因素。保守主义的这种看法,同样表现在他们对国际政治的思考中。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各种冲突和影响这些国家的生存发展的严重问题,保守势力冷漠地认为,美国不值得为这些问题进行军事干预,这些问题不会对现有的国际秩序造成重大影响。所以不应该让美国人的生命在索马里、海地和卢旺达这样的地方“去冒险或去丧失”。在他们看来,“西非或南亚的污染和人口过剩对美国的利益最多也是边缘性的”,卢旺达和索马里的问题“对美国的利益至多也只有微小的影响”。保守主义还要求进一步减少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发展援助,多尔已明确宣布,“美国援助项目的改革和削减是国内福利改革的海外版”。Bob Dole, “Shaping American Global Future”,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5, pp.2943.从保守主义的角度看,穷国的问题和穷人的问题差不多是一样的。
保守主义势力当然不反对一切军事干预活动。在涉及美国重大战略利益的问题上,保守主义可能比自由主义更倾向于使用武力。保守主义势力认为,美国可以对各种国际问题保持有限的卷入,而不是充当和平与安全的保证人。但美国必须“组织盟国在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地区抑制最危险的动乱根源”。西奇曼也说:“美国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们肯定能够对付最重要的问题。”John Gray, “Backward into the Future: The Perils of Wilsonianism”, National Review, March 29, 1993, pp.2732; Harvey Sicherman, “Winning the Peace”, Orbis, Fall 1994, pp.523544.高度重视“秩序”的保守主义当然知道如何将它“强加”给别的国家。
保守主义另一项基本的要求是减少多边活动,保留行动自由。
冷战结束后,对外政策权势集团认为,为了能够长期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应该与盟国保持更密切的合作,给盟国更多的发言权。同时,为了在对外行动中得到美国公众的支持,美国应当更多地利用联合国和其他地区性组织以增加道义上的力量。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教授肯尼思·奥耶(Kenneth Oye)指出:“为了在促进全球稳定和和平的同时减轻领导者的经济负担,美国可能最好明确地改用一种形式很复杂的多边战略。”Kenneth A. Oye, “Beyond Postwar Order and New World Ord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in K. A. Oye etc. ed., Eagle In a New Worl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2, p.27.
克林顿上台后,民主党的政策曾经鲜明地表现出这种多边主义轨迹。但是,保守主义势力拒绝这种方针。从保守主义哲学的角度看,个人自由是最重要的“天条”,每个人是自己利益最好的判断者,无数个人判断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正常和自然的状态。保守主义“深深地怀疑任何基于集体之上的理论和政策,认为那些是自由主义的参照点”。Frank S. Meyer, “The Recrudescent American Conservatism”, in American Conservative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8183.但是保守主义并不反对联盟政策,因为结盟只是一种“自愿的合作”。在他们看来,多边主义有可能为了别国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一些保守主义者批评说,克林顿政府不是把多边主义看作工具,而是更多地把它看作哲学上的目的。保守势力攻击多边主义把美国军队置于联合国指挥下,让“美国人的鲜血和财富为别人的利益、而不是为美国自己的利益去抛洒”。鲍勃·多尔认为无论是联合国还是世界贸易组织都不能保护美国的利益,“转包美国对外政策和转让美国主权在国内会鼓励孤立主义,在国外会使美国的对手胆大妄为”。他们强调美国应按照自己利益采取行动,
多边体制只是一种分摊经济负担的手段。Peter W. Rodman, “Bills world”, National Review, Nov. 15, 1993, pp.3440; Bob Dole, “Shaping American Global Future”,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5, pp.2943.
在对外经济方面,保守主义的基本要求是扩大国际自由贸易,敲开其他国家的市场,确保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
保守主义的基本经济思想是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反对国家控制和干预经济过程。因此,保守势力支持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世界贸易组织,要求扩大和深化国际自由贸易。但他们又认为,由于其他国家控制本国市场和保护本国产品,美国在贸易竞争方面必须采取强硬立场,他们要求政府利用各种手段迫使这些国家遵守“公平贸易”原则,向美国的产品、服务和资金全面开放市场。
前些年,美国保守势力对日本在其产品大量涌入美国的同时,顽固保护本国的农产品、服务业等市场十分不满,要求政府敲打日本。但这两年由于日本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不景气现象,保守主义势力从战略和双方经济已高度相互依存的实际考虑,发出了对盟国要“区别对待”的信号。Ibid.
将现在的保守主义要求与冷战时期的保守主义对外政策主张相比,两者之间的异同还是很明显的。迈耶(Frank S. Meyer)在60年代曾这样归纳保守主义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基本观点: “美国保守派将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种以救世主自居,并且是对西方和美国的基本生存的武力威胁。他们相信,我们的整个外交和军事政策必须基于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出于反对模糊的国际主义和对共产主义‘软化’的空想,以及反对代表自由派思想和行动的联合国价值,他们把保卫西方和美国看作是最具压倒性和迫切性的公共政策。”Frank Meyer, “The Recrudescent American Conservatism”, in American Conservative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83.
与过去相比,当代保守主义要求中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有所弱化,保守势力现在不可能再像冷战时代那样去树立一个势不两立的新敌人,他们更关心的是维护美国现实和具体的利益。冷战时期保守势力将一切国际冲突都视为共产主义的挑战,他们主张对所有的冲突都要做出针锋相对的反应。而当代保守势力却不愿轻易卷入任何非战略性国际冲突中去。此外,解决当前国际问题的迫切性对保守派来说也已大为缓解,他们的目光更多地集中在国内问题上。
但是,在“保卫西方和盟国”这样的重大目标上,在加强美国军事力量,反对“模糊的国际主义”及多边主义倾向上,保守主义似乎还是在几十年一贯地坚持自己的信条。
五、保守主义要求对政策的影响和限度
冷战结束已有五年了,保守势力对布什和克林顿两届政府的一个主要的不满是,他们均提不出一个目标明确、手段可靠的全面战略。持保守主义观点的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冷战结束时就说过,保持冷战秩序、两极体系和适度的美苏紧张是最符合美国和西方利益的。尽管已经做不到这一切,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应当放弃维持现有秩序的所有努力”。五年之后,这种看法终于赢得了保守势力的广泛赞同。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0, pp.556.
在未来的岁月里,保守主义势力会努力推动一种以维持地区联盟和保持地区力量平衡为核心的战略。基辛格认为,力量平衡是美国“实现历史性目标的先决条件”。退役中将、赫德森 (Hudson)研究所国家安全研究部主任奥德姆(W. E. Odom)指出,美国最重要的利益是在欧洲、东亚、中东及加勒比地区保持稳定繁荣,而稳定只能建立在“地区力量平衡之上”。美国如在欧洲做到了这一点,“在俄国建立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努力即使完全失败,一种新的国际体系仍可实现”。他承认这是一种建立在现实主义理论上的“美国的体系”,目的是要将“民主国家联结在一个军事安全的屋顶之下和在一个更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中”。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p.83; William E. Odom, “How to Create a True World Order”, Orbis, Spring 1995, pp.155172.目前,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已在朝这一方向调整。
保守主义势力实际上是要重新启用冷战时期的国家基本战略。这一战略虽然不再具有过去那种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其目标相当明确,即以军事联系加强和维持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从这一角度看,冷战时期的战略与新战略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在手段方面,它们都强调美国的军事优势、维持西方联盟和保持力量均衡。只是前者具有全球性特点,后者则偏重于地区性问题。前者指向明确的敌人,后者则偏重于预防挑战者的兴起。
随着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现实主义学派也重新得到了它过去有过的显赫地位。当代现实主义者更注意扩大相对力量优势和利益的相对获得,承认各国之间可能进行有限的合作。但他们依然认为,“世界仍旧像过去一样,国际政治将继续存在于一个无政府、竞争和自助的领域之中”。因此,根据威胁界定利益,利用平衡维持现状仍是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如何同其他大国“共处和互动”对美国来说只是一个未来的课题。Chrestopher Layne, “The Myth of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4, pp.549; 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all 1993, pp.4479;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94/1995, pp.549.
在地缘政治方面,冷战后初期美国对德国与日本的恐惧已暂时减轻,新的疑虑对象是俄国和中国。理论家们认为,大国迅速的兴衰期往往就是国际体系最不稳定的时期。目前,美国对于中俄两国力量的兴衰变化的担心超过对德国和日本两国的担心。在未来的地缘政治天平上,德日两国即是平衡俄中两国的主要砝码,又是天平上被平衡的另一端。米尔斯海默曾指出,如果俄国重新要扩张和推翻现存秩序,“我们就回到冷战去”。如果它能实行维持现状的政策,“苏联的力量就能起到平衡德国的作用。”William E. Odom, “How to Create a True World Order”, Orbis, Spring 1995, pp.155172.从基本战略目标和手段、政治理论和地缘政治等各个方面来看,保守主义就是要先退到自己熟悉的道路上,在那儿等待“难以认识”的未来的到来。
但是,保守主义的这些要求会受到各种力量的限制,这种力量可能来自自由主义的挑战,也可能来自保守主义阵营内部,更可能来自国内外政治经济状况的现实。
首先,美国的军事预算从下一个财政年度将重现回升的趋势,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必然要兑现他们在《与美利坚的契约》中许下的诺言,增加军事开支。但是美国的经济力量毕竟大不如前,加之共和党的首要目标是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要达到这一目标本来就很困难,如果军事开支过大,就会招致自由主义势力的责难,并引起选民的反感。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军事力量的增加将是有限的。
其次,维持地区联盟和力量平衡战略也将受多种因素的限制。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不大可能再找到一种对其重大战略利益真正构成威胁的力量。威胁的不确定性可能使该战略的全面效果受到影响。因此,自由主义势力会对这一战略的前瞻性和灵活性方面提出批评。在理想主义色彩强烈的美国,即使是在后冷战时期,这种以现实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战略仍将受到左右两翼的抨击,认为它是向现实政治让步,抛弃美国外交的道义责任。
第三,盟国,尤其是德国和日本,能否在冷战后长期受美国的束缚也是一个重要的变数,尽管它们认为现有秩序仍有利可图。英、法两国也可能采取它们自己的平衡政策,以免欧洲的重心偏向德国。在保守主义思想指导下,美国同其主要盟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势必继续给联盟关系带来麻烦。
第四,保守主义势力虽然不愿意在非重大利益问题上进行军事干预,但是一旦危机发生,他们将受到左右政治力量的挑战。对危机的反应过分或反应不足都可能导致新孤立主义情绪的上升。另一方面,在后冷战时期如何界定美国的战略利益将更为困难。巴尔干、北非和东欧地区对美国来说都是利益不大,但又不能弃之不顾的地区。因此,保守主义势力也很难对这些地区的冲突长期地持消极态度。
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形势仍处于变动之中,美国的自由主义势力愿意对捉摸不透的未来做出动态的调整,而保守主义势力则宁可以经验和传统为依托,形成可靠的反应基础。与自由主义相比,保守主义的政策将更稳定一些,也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便如此,面对一个变动中的世界,美国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仍将是一种中期性和过渡性的政策。
保守主义回潮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
*本文原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7期。发表时英文注释全部译为中文,现保持发表时的原样。
保守主义思想在美国已经重新崛起,并已在许多领域里取代自由主义成为主流,这一状况势必影响美国今后的对华政策。本文将探讨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问题上的一些基本看法,着重分析保守主义势力对于对华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估计这一影响的程度。
战后,美国保守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对于对华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一种僵硬的对华遏制政策在这一背景下最终形成。美国对华政策在60年代后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时正是自由主义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处于高峰时期。美国在越南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处境,将社会主义国家看作是“铁板一块”的保守主义观点已被事实抛弃,一度影响极大的国民党的游说活动无人理睬,亲台势力的影响急剧缩小。这表明对华遏制的政策已经彻底失败。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自由主义关于“缓和”的思想得到美国公众的支持,而保守主义则强调必须建立以抗衡苏联为基础的战略方针。双方在构筑新的对华政策问题上找到了合作的基点。
1989年以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自由主义以扩大民主、推进人权和促进市场经济为号召,一度在美国对外政策领域中起主导作用。在对华政策方面,自由主义势力宣称中国已不再具有平衡苏联的价值,因此美国可以在人权、安全及台湾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试图使中国按他们的设想变化。这种观点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并对双边关系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然而,自由主义思想却不能对解决新出现的各种国际问题提供明确的指导思想,以致后冷战时期美国缺乏一种全面而有效的对外政策。由于国内问题的困扰,保守主义目前已代替自由主义成为美国政治领域中的主流思想,共和党也在40年后第一次取代民主党控制了国会。共和党人正在重新审视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亲台势力的影响也随着保守势力的上升而回潮。这一系列变化不定的因素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复杂的作用,使这一政策的走向显得更为扑朔迷离。
一、保守主义势力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基本看法
当前,尽管保守主义思想盛行,但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还没有出现意见一致的保守主义观点。在深入探讨各种不同的保守主义观点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目前在中国问题上保守主义势力的基本视角。
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和重构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通过这一方式来保证和加强美国的国家利益。保守主义势力认为,冷战后一些大国力量的急剧上升或衰落可能对现存的世界秩序造成威胁。由于近年来中国综合力量迅速增强,美国保守主义势力普遍地怀疑中国是一种未来的威胁。
美国保守主义反对将对外政策建立在民主或人权等普遍主义的价值基础上,而主要从战略角度来构筑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保守势力认为,维持建立在强权与优势之上的和平与稳定是当前的迫切需要。由于冷战已经结束,刺激中美缓和与友好的因素已不复存在。保守势力希望形成一种以力量平衡为特点的亚洲战略,中国是这一战略要平衡的主要对象。威廉·奥德姆:《怎样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全球》1995年春季号,第155173页。
保守主义认为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因素,因此相对自由主义势力来说,保守主义思想比较尊重主权原则。但是,保守势力又具有较强烈的道德主义色彩,他们往往倾向于拒绝同所谓的“敌对反应”国家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希望用制裁和施压等手段来迫使这些国家屈服。1989年以来,保守主义势力的这种倾向也表现在他们的对华政策考虑中。
保守势力基本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对华政策思想,它们对于未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势必将产生较大影响。第一种类型是想阻止中国力量的不断增强,并以抑制、威慑和排斥中国为主要特点。第二种类型的保守观点虽然也怀疑中国未来的作用,但他们主要的目的是想影响中国未来的国际行为,这种观点以试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为特点。
尽管在新闻媒介中曾经出现过一些要求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文章,民主党政府的高级官员温斯顿·洛德也公开提到过美国将来“可能”对中国进行“遏制”,但是在保守势力的对外政策研究圈里,还未见到有人认真提出要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政策建议。这可能同保守主义具有现实主义倾向和强调战略的思想有关。
保守主义主要关注的是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国际秩序可能造成的影响。这种倾向使保守势力认为,今后中国必然会在国际政治中扮演更活跃的角色。美国保守势力既不会改变他们对未来的悲观看法,也不会相信中国对外政策的和平性质,因此,他们必然要怀疑中国的发展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和挑战。在这一方面保守势力的各种观点并没有太大的分歧。他们争论的是所谓威胁和挑战的程度,以及如何去控制和影响中国的国际行为。应当记住的另一点是,当前被美国保守主义势力怀疑的对象,并非只有中国一家,俄国、德国、日本及伊斯兰激进主义都是“榜上有名”的。
二、保守势力关于台湾问题的看法和影响
保守主义思潮的上升带来了亲台势力政治影响的重新扩大。亲台势力是美国保守势力中一股极端保守而且相当活跃的力量,50年代这股力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起过非常恶劣的作用,到了60年代后期他们的影响逐渐消失。进入80年代后期,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亲台势力重新开始活动起来,他们积极支持“台独”和国民党当局进行的“两个中国”的活动。李登辉实现“私人”访美表明,对这一势力的影响和能力不可低估。
与50年代一样,亲台势力在国会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是著名的亲台人物,他在担任此职后第一个会见的就是台湾驻美代表。在他的支持下,参议院外委会去年3月曾通过决议,要求让台湾进入联合国。这位先生也许可以像50年代的共和党人威廉·诺兰那样被称为“来自台湾的参议员”,不同的只是他多半当不上共和党参议院领袖。此外,阿拉斯加州参议员穆尔科斯基、纽约州参议员达马托、众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基尔曼等人也同亲台势力有密切关系。甚至保守势力最有权势的领袖人物、众议院议长金里奇也受到亲台帮的影响,一度声称美国可能承认台湾。克林顿政府“提升”美台关系,允许李登辉访美,都与亲台势力在国会的活动有密切关系。众议院外委会已在修改“对台关系法”,试图进一步加强对台湾当局的军事支持,长期保持中国的分裂局面。戴维·香博:《美国与中国,一场新的冷战?》,《当代历史》,1995年9月,第241247页。
尽管亲台势力对美国政界的影响正在卷土重来,但美国政界对这一势力过去扮演过的角色也不会完全忘记,当年正是这一势力影响的过分膨胀,使美国对华政策在一段时间内根本无法改变。保守势力认为台湾的重要性在上升,但他们也意识到台湾的分量不可能超过中国大陆。因此,保守势力主要和直接的目的是要遏阻海峡两岸趋向统一的势头,而不是公开否定“一个中国”的原则。
保守势力中的主流派在台湾问题上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在谈论承认台湾之后,金里奇曾同基辛格进行过一次会谈,接着就收回了他的讲话。用洛德的话来说,这位共和党领袖“显然是在讲这些话时并不认真,或者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或者他已经改变了想法”。S·墨菲:《好坏兼有的关系,采访温斯顿·洛德》,《当代历史》,1995年9月,第 248257 页。 这一情况表明,主流派认识到完全改变六届政府已实行了25年的对华政策势必引起严重后果,对他们构思中的美国冷战后的基本战略将会产生巨大冲击。在这一点上,他们同亲台势力有重大分歧。
保守势力虽然反对中国统一,希望长期保持台湾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但是出于维持世界秩序的考虑,他们又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台湾独立”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就连拉萨特也指出,美国“不能允许台湾独立运动控制台湾的公共政策”。沃尔德伦也担心,“台独”势力如不顾美国的呼吁和其他人的反对,贸然宣布“全面独立”,肯定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基辛格在同金里奇会谈后,写文章警告台湾当局要三思而行,不要迫使美国最终抛弃台湾。同时他也批评亲台势力说,“有一种学派认为中国只是吓唬人并且最终是要让步的,这是不顾后果的观点,是用国家的命运来进行挑战和威胁”。《华盛顿邮报》,1995年7月26日。
李登辉访美所发生的事态表明,台湾当局和美国亲台势力推行“两个中国”的企图虽然能够在一段时间里影响公众舆论,能够使中美关系发生一时的倒退,但不可能使美国对华政策发生根本性改变,他们的政治能量仍然是有限度的。克林顿政府和保守势力的主流派都不可能从美国对台政策的角度来制定对华政策和亚太政策。
三、对保守主义势力影响程度的估计
1996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从目前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势头来看,以保守主义为号召的共和党候选人获胜的可能性会稍大一些。即使克林顿能够保住他的总统宝座,他的对外政策也必然会受到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的影响。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趋向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保守势力的观点而不是自由派的观点将在这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
无论哪个政党上台,下届美国政府必然会实行对中国进行平衡的战略方针。美国将在西太平洋地区继续进行前沿部署,维持冷战时期形成的联盟关系,并动员和利用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力量,以确保战略上的相对优势。这是根据保守主义思想形成的战略,其基本属性是防御性的,目的是要阻止中国力量的增长对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形成威胁。克林顿政府对亚洲战略的新调整表明,这一战略方针已在执行之中。詹姆斯·凯利:《美国在东亚的安全政策:与侵蚀斗争并寻找新的平衡》,《华盛顿季刊》,1995年秋季号,第2135页。
在外交层面上,平衡战略可能与前述的第一种类型的对华政策观点结合,构成一种强势的、在国际事务中抑制中国影响的政策,也可能与第二种类型的观点构成一种温和的、承认中国能够起一定积极作用的政策。如果保守势力作第一种选择,美国会更粗暴地向中国施加压力,动辄对中国使用“制裁”手段,冲突和紧张将成为双边关系的特点。但他们也会进行必要的妥协,以免关系全面恶化。如果作第二种类型的选择,美国会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和多边体制中主动寻求同中国合作,以合作为手段影响中国的行为,必要时以有限的“制裁”作为影响完全失效的补充。
对华政策是美国全球政策尤其是亚太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对全球性政策的辩论有较清晰答案之前,美国对华政策不可能很快稳定下来。从这场辩论的发展轨迹看,一种弱意识形态的、国内考虑优先的、维持现有战略地位的政策方向,正随着保守主义思想的回潮而占上风。J·麦克利斯特:《信号不清的灯塔》,《时代》,1995年11月27日。 在这种政策环境下,美国对华政策可能更接近于第二种类型的选择。
保守主义思想对国际关系中的力量变化比较敏感,因此保守势力会更加关注亚太地区的军备问题,并会竭力推行阻止中国取得军事力量相对优势的政策。同时,保守势力还会要求进一步采取措施,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更严格地实施对常规武器输出的国际监督和控制,并会要求尽早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这类安全问题上,保守势力在要求中国进行合作的同时,也将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尽可能地把中国绑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商定的行为框架内。
出于对维持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考虑,保守势力不会鼓励“台湾独立”,但由于亲台势力及其影响的存在,保守势力将保持同台湾当局的密切关系,支持李登辉集团的统治地位。为了保持两岸的分裂局面,他们可能向台湾提供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并可能以某种方式进一步承诺保证台湾的安全。然而,由于保守主义思想总的说来不赞成在非重大战略利益地区进行军事干预,在目前条件下,保守势力不会承诺在台湾问题上进行军事干预。
保守主义反对将美国对外政策建立在民主和人权等普遍主义的价值基础上,因此,对保守势力来说,对华政策中的人权问题的重要性就相对小一些。尽管如此,在香港、西藏和人权等问题上,保守势力中总有人会继续兴风作浪,制造麻烦,以期获得政治上的好处,并增加同中国打交道的筹码。
不论1996年大选的结果如何,美国国会中的保守势力都会谋求在对外事务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同白宫竞争决定对外政策的权力。在保守主义势头不减的条件下,国会与白宫都由共和党人控制会比较有利于对华政策的平稳执行,一位共和党总统对于国会保守势力的影响力相对要强一些,而民主党总统则会受到保守势力尤其是亲台势力的更大的牵制。
保守势力的对华政策选择也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美国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有其特定的含义,无论保守势力选择强势的还是温和的政策,未来的对华政策同遏制政策都有性质上的区别。从总体上看,美国保守势力无意也无力对中国实行一种全面的、长期的和僵硬的对抗性政策。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相当严重,将注意力和资源主要用于解决国内问题是保守势力最优先的考虑。奉行一种长期和全面的对抗政策不仅使这种优先考虑无从谈起,可能还会使这些问题更趋严重。
美国能否推行一种强势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同美国能否充分动员盟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支持密不可分。近年来,在中国复关问题上,在煽动“中国威胁论”问题上美国霸主的影响力还是清晰可见的。但是,它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的影响又是有限的。由于保守势力对于多边性国际体制的效率持怀疑态度,共和党政府如果上台将主要利用双边联系扩大影响力,东盟国家将是美国争取的重要对象。可以预见,美国的大部分盟国和东盟各国都不会对美国言听计从。
对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未必能促使保守主义势力采取较积极的对华政策,但是这一因素在阻止中美关系滑向更消极方面会起一定的重要作用。海外利润是美国大企业集团利润的主要组成部分,考虑到保守势力同大企业集团的密切关系,同中国有经济往来的美国大企业会为维持中美关系而施加影响。
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处于过渡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将在同中国的互动中不断地调整。因此,中国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中国的和平与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是阻止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消极与对抗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对中美关系产生着深层的影响。从许多角度来看,它们是减少美国保守势力对中国的怀疑和偏见的最有力的因素。因此,在坚持重大原则的同时,努力办好中国自己的事,继续执行加强合作、增加信任、减少麻烦、不搞对抗的方针,是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
当代国际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因地缘产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将使一个地区中的各个国家的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能较好地处理同亚太各国的关系,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就能保持较大的活动空间。如果中国能同有关国家和平解决南沙群岛的领土争端,保守主义的平衡中国的战略就会难以为继。
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回潮使20世纪90年代成为中美关系的考验期。在这一段时间内,双方利益冲突的最大限度正在凸显出来,为维护这些利益而能付出的代价的最大限度也会表现出来。美国保守势力如能理性地对待这些限度,就可以避免重大的危机,中美之间更为广阔和稳定的合作前景也会清楚地展现出来。
摆动中的回归
——保守主义思潮对G.W.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
*本文原发表于任晓和沈丁立主编的论文集《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由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
保守主义是当代美国最强大的一股思潮,它正在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对外政策等各领域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美国保守主义思潮已相当关注,但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仍有待加强。目前,对美国保守主义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要求和战略观点的变化可能还研究得不充分,对保守主义内部不同派别的主张和分歧也缺乏深入了解。尽管人们非常关注这一思潮的政治影响,但对于这种思潮的影响程度缺乏全面与冷静的估计。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经将保守主义定义为:在既有的体制受到根本性攻击时,一种被用来为这种体制辩护的思想体系。亨廷顿说:“当社会的基础受到威胁时,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提醒人们某些制度的必要性,以及使其存在下去的可取性。”从亨廷顿的定义看,一般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是一种与社会革命相对立,甚至很可能与社会改革也相抵触的思潮。当前美国的保守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应当有所区别,根据亨廷顿的定义和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大家詹姆斯·伯纳姆的观点,当代保守主义作家约翰·奥沙利文说:“当代保守主义的功能已经很清楚,即对西方文明体制,尤其是对以最杰出的美国方式体现的制度的辩护,抵制一系列以自由主义名义对它进行的根本性攻击,以及抵制那些称自己为自由派的人的言论与行动。”John OSullivan, “Safe for Democracy, and a Nation, The Idea of this Country Post9/11”, National Review, December 17, 2001, pp,4244.奥沙利文的定义虽然比较宽泛,但是它基本上涉及了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的两个最基本的特点:强烈反对各种自由主义思想,以保护西方文明为最根本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借用这一定义,并以此为基础对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要求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保守主义思潮在美国重新崛起的原因
战后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潮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前期,它的发展也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早期的保守主义曾因为麦卡锡主义猖獗而一度招摇过市,但此时它还没有成熟的政治与经济观点而不能形成气候。Michael Lind, Up From Conservatism: Why the Right is Wrong for Americ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6, pp.4955.
由于70年代出现了经济滞胀和越南战争失败等重大政治挫折,美国公众开始反思30年代以来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政治方向。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思潮中还出现了种种颓废与极端的要求,这些要求一定程度要对当时美国社会上价值混乱、风气衰败、犯罪率上升等问题负责。从70年代中期开始至80年代的保守主义的重新崛起正是借助了这种不满。美国公众开始对自由主义的一些极端形式表示不满。例如,原来关心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自由派基督教教会的影响下降,而保守的南方浸礼会转而关心政治,并开始与美国宗教界主流教会竞争影响力。Mark Gerson, The Neoconservative Vision,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Culture Wars, New York: Madison Books, 1996, pp.319320; Corwin F. Smidt, In God We Trust, Religio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Life,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01, pp.2630.
保守主义思想在里根时代形成了第一次高潮。但是,里根政府虽然在对外政策方面博得了保守派的欢心,但其供应学派的经济政策却带来了严重财政赤字和巨额的政府债务,加之保守主义势力内部也有种种分歧,因此他们还不能帮助共和党牢固控制国会和白宫。1989年以后,尽管乔治·H.W.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中仍有不少保守分子,但这届政府与右翼保守势力的要求有严重政治分歧。因此右翼保守势力在1992年宁可接受民主党上台也不支持老布什重新当选。在他们看来,老布什根本算不上是保守主义者,在税收和社会等国内政策方面,在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他的政府已经背叛了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www.liberairianism.org/primerintro.html
在90年代中期,保守主义的各派势力进行了新的整合,尤其是宗教右翼势力与共和党权势集团达成了相互支持的共识,宗教右翼在南部和中部地区成为共和党的核心支持力量。此外,新保守主义的影响也不断发展,并且开始成为保守主义思潮中的主流。正是在各派保守主义势力的全力支持下,共和党人在1994年中期选举时成功控制了国会两院,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共和党人第一次能主导美国立法机构。1995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5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太大太强,它已经对普通公民的权力与自由构成了威胁”。这种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观点反映了美国公众对大政府和高税收的普遍不满。但是这一时期美国经济表现良好,加之在1996年大选中,右翼保守势力对帕特里克·布坎南的“右翼民粹主义”又过分容忍,这使得共和党人未能夺回白宮。
但是,新的整合是有成效的。自由主义学者迈克尔·林德认为,以中西部为基础的保守势力为东北部的天主教——犹太教思想库提供财政援助,后者则教导南方的浸礼会教徒们在阳光地带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因此这些力量形成了一种互利的“三角交易”关系。在2000年大选中,保守主义势力终于通过一致行动将乔治·W.布什送进白宫,这次大选也证明了保守主义思潮已经构成为强大的政治实力。Michael Lind, Up From Conservatism, pp.7596.
9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思潮强化主要是国内因素造成的,它是对80年代保守主义思潮复兴的延续。当代美国保守主义势力主要关心的是国内问题,对社会道德、学校教育、福利政策、政府规模、种族关系与多元文化等问题,保守主义势力都有自己的理论与政策要求。他们希望自己的观点能为政府和社会公众所接受,在不断打击30年代以来形成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政策的同时,以所谓美国传统价值观念来约束未来的发展方向。
然而,保守主义势力的主张不仅是反对自由主义的极端要求,实际上他们在社会政策等方面具有一种开历史倒车的要求。保守主义势力的各种国内政治主张实际上将加强不同社会阶层的分裂与对立,减少中下层收入者和弱势群体从政府得到的福利帮助,削弱50年代以来民权运动取得的成果,加强基督—犹太教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制止文化多元主义的发展倾向。David Frum, Dead Ri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pp.128132.
80年代末期,冷战的结束强化了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潮。保守主义势力一贯强烈地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冷战以苏联崩溃而告结束,这使保守势力认为其保守价值观是绝对正确的,他们也由此认为,各种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观点,如福利主义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都不应存在下去。同时他们也在文化和教育等领域中向自由主义思想发起“文化战争”,试图从更深入的层次巩固保守主义的胜利。
全球化趋势的加快符合保守主义对贸易与投资自由的要求。但是也有一些保守主义势力对全球化的某些后果深深不满。他们认为全球化带来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这些新移民不愿归化美国的主流文化,有的还不接受英语而使用本民族语言,这对美国的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造成了威胁。同时,他们还认为,全球化造成了美国资本和就业机会外流,大量国外制造品进入美国市场,这些观点在美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层中也有很大影响。此外,美国人的不安全感也因毒品贩卖、国际犯罪、环境污染等问题的不断严重而加深。保守主义的这些观点迎合和吸引人们的关注。
“9·11”事件的发生也为保守主义思潮扩大影响增加了新的动力和可能。冷战结束后,保守主义势力一直在寻找可能对美国构成实际或潜在威胁的新的外部力量。他们认为,未来的世界是非常不稳定的,美国仍然面临着“无赖国家”挑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势力等各种危险。“9·11”事件似乎表明保守主义不能忽视美国安全的思想是正确的,世界上存在着广泛的敌视美国的力量,他们或是出于意识形态与宗教文化原因仇恨美国,或者纯粹是妒忌美国的财富与地位。“9·11”事件造成了严重的生命与财产损失,它显著地加强了普通美国人的不安全感与民族主义情绪,使他们认为尽管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处于一个充满危险与邪恶的世界中,只有依靠实力才能保护自己的安全。
从政治角度看,9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思潮的强化态势削弱了共和党内的温和力量,改变了该党内部的力量平衡。从艾森豪威尔时期开始,执行保守的财政与经济政策、强调自由贸易、走“国际主义”路线的温和力量在共和党中占有主流地位。但1992年老布什在大选中的失败表明,共和党要赢得大选必须在南方各州得到保守势力的支持。共和党主流派已经不能拒绝保守阵营内各种强硬势力的要求,他们必须在社会、经济和对外事务方面一定程度地满足这些势力的政策主张。保守主义对当代美国政治的影响已如此之大,今后数年它可能会增强到70年前孤立主义对美国影响的程度。
二、保守主义思潮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基本要求
从1992年开始,美国经济经历了连续9年的中速增长,这种增长使美国的GDP规模从6万多亿美元增加到9万亿美元,从而为21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及改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90年代以来美国军事开支不断增加,它的国防开支早已超过其他6个军事大国军事开支的总和。在此同时,美国从80年代开始的对军事与国防科技进行大规模投入的结果已经逐渐表现出来,海湾战争的结局表明军事技术领域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美国利用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领域的技术领先加强了指挥、通讯、控制、信息等方面的能力,进一步扩大了它与其他军事大国的差距。
冷战的结束使保守主义势力在对外政策领域一度失去方向。80年代后期,新保守主义过于强硬的反苏立场已使他们失去了一些影响。在90年代初期,保守主义思想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影响明显下降,而自由主义的思想却在上升。保守主义势力一度无法形成全面和长期的政策思想和建议,对于采取较为克制的对外政策还是确立意识形态方面更为扩张性的政策目标,新保守主义内部存在若干分歧。这种情况到90年代中期才有所改变。John Ehrman, The Rise of Neoconservalism, Intellrvtuals and Foreign Affairs 1945—199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75185.
进入90年代末期,由于同克林顿政府产生越来越尖锐的分歧,美国保守主义势力在对外政策方面最基本的要求是加强美国的军事力量,加强美国在世界上的力量优势,在需要时坚决使用这种力量。从这一原则出发,保守主义势力强烈抨击民主党政府在90年代忽视美国的军事力量建设,军费的短缺使军事装备的更新与加强受到阻碍。尽管克林顿政府也不断增加国防开支,但是保守势力认为,“90年代美国的军事采购经费减少了将近一半,其下降率是整个军事预算下降率的两倍,1998年的支出是20年来最低的”。Richard Lowry, “Bombing at the Pentagon, Don Rumsfelds agony”, National Review, Sep.3, 2001, pp.3638.增加国防预算,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等都是他们在这一原则下的政策要求。在保守主义势力的推动下,布什政府迅速增加国防预算,并且推动“国家导弹防御计划”,追求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在“9·11”事件之后,美国人的安全感更为脆弱,他们把增加安全费用视为当然。在他们看来,如果美国“不愿显得那么专横的话,我们就会因为迎合那些妒忌的家伙而很快丢失领导权”。2002年美国的国防预算猛增480亿美元,总额达3780亿美元,其增幅为20年来之最高,其总额接近历史最高水平。www.cato.org/dailys/020502.html
保守主义势力的第二个基本要求是利用冷战后形成的国际力量不平衡局面,建立美国在世界上的单极霸权。他们希望美国在对外关系上,尤其是在军事力量的使用上保持最大程度的行动自由,不受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制约。最早鼓吹单极霸权和强调军事力量的是查尔斯·克劳塞默尔,他是保守主义势力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代言人。在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战争基本结束后,克劳塞默尔其至高呼“北约死了,北约万岁!”在他看来,北约已经没有军事意义,随着俄美关系的改善,这个昔日的同盟现在只是一个跨大西洋的俱乐部而已。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America and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1990/91, p.24; Charles Krauthammcr, “ReImaginng NATO”, Washington Post, May 24, 2002.保守主义的这一要求与他们过去强调结盟,防止战略对手联合而形成力量优势的传统大不相同。
美国保守主义势力一贯不喜欢国际多边组织,冷战结束后,单边主义倾向已成为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保守主义势力认为,美国根本就无须在乎别国对美国的看法。两位重量级的强硬保守派罗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尔说:“美国与那些表示反对它霸权的国家争论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美国的‘傲慢’。这是美国多种形式的实力的不可避免的现实。那些认为国际上的愤怒会由于较为克制的美国对外政策而消除的人只是处在快乐的幻想中。”在保守主义势力的推动下,布什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单边主义政策。对此不满的共和党国际主义派系认为,今天的单边主义势力同20世纪早期孤立主义势力实际是一对双胞胎。Joseph S, Nye, “Seven Tests, Between Concert and Unilateralism”,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2001/2002, pp.513; Michael Hirsh, “Bush and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Sep/Oct 2002, pp.143.保守主义势力的第三个要求是确立起美国霸权地位正当性的理由,以此作为凝聚美国人民意志,构建新的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在这一原则之下,保守势力一方面竭力鼓吹美国国际行动的正义性,另一方面还试图确认美国在国际上的新的敌人。从保守主义的视角来看,冷战结束不能改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世界上总是存在着敌视美国的“邪恶”势力,那些拒绝认同美国价值观、拒绝接受美国霸权的国家都是实际或潜在的威胁。从90年代中期起,一些强烈敌视中国的保守势力越来越明显地把矛头指向中国,保守主义评论家卡根和克里斯托尔曾多次撰文提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威胁。Ibid; Walter A, McDougall, “Editors Column”, Orbis, Winter 2002, pp.110.从保守主义的标准来看,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制度、军事能力及未来潜力等方面都符合美国的敌人标准。但是也有一些保守势力认为,一些“无赖国家”因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的重大战略利益构成直接挑战,因此这些国家应是美国的主要敌人。“9·11”事件表明,认定中国是美国威胁的设想是没有根据的,但保守势力还是认为,这一事件证明了世界上的确存在着仇恨、嫉妒甚至要毁灭美国的力量,因此他们对世界未来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
保守主义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第四个基本要求是维持世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经济秩序,在这一秩序下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这一原则是美国保守主义的一贯要求,也是保守主义中的主流力量最重要的政策指导思想。美国保守主义势力与大型跨国公司有密切的关系,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正是当代跨国公司的生存方式。但是,保守主义势力中的一些平民主义力量也在挑战这一要求,他们认为这会导致美国就业机会的减少等问题。但与此同时,G.W.布什政府已经批准了对农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提高美国钢铁进口关税,虽然这些行动主要是出于共和党的政治和选举战略考虑,但它们已经受到强硬保守主义势力的批评。从这一角度看,美国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并不必然地产生非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
G.W.布什政府还在努力整合保守主义势力的各项要求,努力制定与这些原则相适应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人们已经看到,布什政府决定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和退出反导条约、对美国军事体系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将伊拉克问题与反恐问题联系在—起、拒绝批准“京都协定书”和拒绝加入“国际刑事法庭”、提出所谓的“邪恶轴心”概念、承诺将“尽一切可能保护”台湾,等等,都是在不同方面满足保守主义势力的要求。在保守主义思想的主导下,美国正在加强对全球军事战略地位的控制(包括技术和地缘的),其自行其是的倾向非常严重,越来越不尊重其他国家,包括它的盟国的重要利益。它已经表示将把“预防性打击”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原则,打击那些威胁美国安全的国家和力量。所有这些行动都旨在加强美国的独霸地位,它的一些行动势必会对未来国际关系造成一些复杂和消极的后果。
三、保守主义思潮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新看法
当代保守主义正在对美国对外政策和当代国际关系造成长期和重大影响。保守主义势力在共和党政府尚未上台时就准备提出有关未来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和军事改革等方面的建议,如传统基金会、凯托研究所、新美国世纪项目等新老保守主义思想库都早就有所行动。
确定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是保守主义势力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涉及美国21世纪长期战略的制定。在“9·11”事件发生以前,美国保守主义势力把矛头指向中国,国防—军工势力集团与新老保守主义在这方面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他们认定中国是美国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要求G.W.布什政府改变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战略,保守派国际政治理论家、“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主要提倡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任何大国都必然要谋求地区霸权地位,因此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使它拥有与美国“同一等级”的竞争地位,中国将谋求亚太地区的霸权并对美国的霸权构成挑战。近年来政治影响力上升的米尔斯海默建议,美国在亚太地区应当进一步加强同日本和印度的关系,与他们形成新的军事联盟体系,共同对中国构成战略“包围”。米尔斯海默还认为,美国政府应当改变对华政策,从支持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转向阻止中国加入,而美国现行政策却在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s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1, pp.400406.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将近年来美国保守主义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思想理论化和系统化。它对布什政府亚太地区战略的形成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他要求改变对华经济政策的想法受到了美国企业界的强烈抵制,保守主义力量中的温和派也对这一观点持有异议。Geoge Gilboy and Eric Heginbotham, “Getting Realism”, National Interest, No.69, Fall 2002.
长期以来,新保守主义势力在中东政策方面是以积极支持以色列而著称的,他们的亲以立场不仅得到老保守主义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宗教右翼力量的大力支持。Corwin F. Smidt, In God We Trust, Religio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Life, p.126.但是在“9·11”事件之前,保守主义势力并不认为以色列的安全问题和中东问题是美国安全战略方面最重大的问题。“9·11”事件的发生使得保守主义势力的议程发生了重大变化。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进行的恐怖攻击表明,尽管美国具有极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但这个超级大国在国家安全方面依然存在着严重的脆弱性。以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的战略思考受到了巨大冲击。威廉·克里斯托尔在参议院作证时说,美国的“对外政策和战略已发生根本的变化”,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国家安全战略问题,他们的对外政策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摆动。www.newamericancentury.org/foreignrelations020702.htm
2002年2月,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诺曼·波德霍雷茨提出:“美国已收到宣战书,我们也正在走向战争。但是这场战争的敌人是谁?”在他看来,美国的敌人不仅是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也不仅是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这个敌人不是“一般抽象的恐怖主义,而是好战的伊斯兰”。波德霍雷茨进一步强调:虽然并非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忽视这一简单的真相是虚伪的,伊斯兰教已经成为当代恐怖主义的肥沃温床”。他希望美国将反恐战争的矛头最终指向伊斯兰极端势力,消除它在中东和世界各地的影响。
新保守主义希望这场反恐战争会产生重大的成果。波德霍雷茨说:“所有的战争都有人们在参战时预计不到的或不想看到的后果,但那些大的战争会有比这更大的后果:它们不可避免地会以重新塑造世界而告终。如果布什总统认真地追求这样的结束,9月11日的战争正是这样的一场大战争,在此过程中他在国内能够得到必要的政治支持。”这个结果到底是什么呢?波德霍雷茨引用另一位保守主义作家的文章说:“开始中东的转变,它能为一个不自由的地区的人民带来很多好处,最终它将使我们在国内享有极大的安全。”Norman Podhoretz, “How to Win World War IV”, Commentary, February 2002, pp.1929.
新保守主义力量中的后起之秀、有影响的中东问题专家丹尼尔·派普斯一年来不断发表文章,他的矛头不仅指向“好战的伊斯兰”,而且强调沙特阿拉伯要对“9·11”事件负责。他认为“瓦哈比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这一思想统治下的沙特向恐怖组织提供了人力、金钱和武器的支持。派普斯早在1998年就强调宗教激进主义是美国的“新敌人”,他批评布什政府没有明确反恐战争的对象究竟是谁,这就如同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同法西斯主义作战一样。Daniel Pipes, “Make the Saudis Pay for Terror”, New York Post, April 15,2002; Daniel Pipes, “Sue the Saudis”, New York Post, Feb.18, 2002; Daniel Pipes, “A Deadly Erro”, Jan21, 2002.
反映新保守主义观点的《评论》杂志和传统基金会的《美国遗产》在2002年都发表了保守派学者维克多·汉森的长篇文章。这位军事史专家认为,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主义”政权既专制又腐败,沙特政府“是恐怖活动积极的教唆犯,是中东地区最恶毒的反以色列国家。‘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分子从沙特得到贿赂金钱,没有这些钱他们本来不可能有效行动。”如果没有拥有石油财富的“瓦哈比主义”的支持,那些试图摧毁西方的恐怖活动将会很快消失。汉森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对沙特的政策,断绝现有的合作关系,为推动海湾地区的政治变革做好准备。在汉森看来,数千年来东西方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过,美国人不仅不用怀疑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正义性,而且应当充分认识和利用西方在力量和道义上的优势。Victor Davis Hanson, “Our Enemies, the Saudis”, Commentary, JulyAugust 2002, pp.2328; Victor Davis Hanson, “The Longest War”, American Heritage, Feb/march 2002, pp.3648.
老保守主义的态度与新保守主义是一致的,早在2001年11月,在得知“9·11”事件中劫持四架美国飞机的19名恐怖分子中有15人来自沙特阿拉伯后,老保守主义的喉舌《国民评论》就发表文章说,如果世界要摆脱恐怖主义的威胁,就要使“瓦哈比主义”遭到“明确无误和不可挽回的失败”。《国民评论》是美国最早对沙特阿拉伯政权表示出敌视态度的刊物,此后这份刊物一直表现出对伊斯兰世界的强烈敌视。Stephen Schwartz, “Liberation, Not Containment”, National Review, Nov.19, 2001.
保守主义影响下的其他媒体,如《华尔街日报》、《新闻周刊》以及《华盛顿邮报》也刊登了大量要求全面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文章。克劳塞默尔说“伊斯兰坏家伙”是美国最直接的威胁,美国必须打击伊拉克和伊朗等“邪恶轴心”国家。《新闻周刊》的文章说:“我们不会谋求在中东建立民主,至少现在不会这样做,我们首先谋求的可以被称为民主的前提条件……法制、个人权利、私有财产权、独立的法庭、宗教与国家的分离……我们不会设想在西方花了几百年时间的事情在中东一夜之间就会发生。”National Review; Charles Krauthammer,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 2002; Norman Podhoretz, “How to Win World War IV”, Commentary, February, 2002, pp.1929.
在“9·11”事件之后,基督教右翼领导人也激烈攻击伊斯兰教构成对美国的威胁。富兰克林·格兰姆,美国新教主要领袖比利·格兰姆的儿子,宣称伊斯兰“是非常邪恶和恶毒的宗教”。“基督教联盟”建立人帕特·罗伯森认为,说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是“欺骗性的”。为了使伊斯兰“妖魔化”,美国有的宗教右翼领导人甚至攻击先知穆罕默德是“恐怖主义者”。“9 · 11”事件发生后,美国公众中出现反伊斯兰情绪,为了平息这一情绪,安抚美国的穆斯林,布什总统曾访问一所美国的清真寺,表示伊斯兰教是“和平的”,那些从事恐怖活动的人违背了伊斯兰教义,见 “Bush and the Islamhater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8, 2002.
新老保守主义已经要求布什政府改变对外政策。“美国新世纪项目”是代表新保守主义要求的主要思想库,该组织的主席威廉·克里斯托分别在国会众参两院作证,说由于沙特已经牵连在“9·11”事件中,美国应当重新考虑与它的关系。这位新保守主义思想的领袖人物指出,美国的安全战略不应建立在沙特今后会采取温和及适应美国要求的政策之上,美国可以利用“后萨达姆”政权下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减少沙特在石油供应和油价方面的影响,迫使这个政权进行全面改革。www.newamericancentury.org/saud052302.htm与保守主义在“9·11”事件以前的观点相比,它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些思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摆动。
四、保守主义思潮中的政策分歧与限制因素
保守主义势力对G.W.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都有重大影响,在他们的推动下,布什政府确定将军事打击伊拉克作为反恐战争的第二阶段。在第三阶段中,保守主义势力还会要求将反恐斗争扩大到中东和整个伊斯兰世界,试图全力消除伊斯兰极端主义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同时也使未来的中东局势更有利于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与这种新的要求相吻合的发展是,最近美国保守主义媒体上敌视中国的声音已经降低。
尽管保守主义势力在反恐问题上具有大体一致的意见,但应该看到他们内部仍然有着种种分歧,这些分歧使共和党政府难以在短期内提出全面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虽然布什总统已经提出以“预防性打击”为核心内容的安全战略,但是这一战略并没有明确提出恐怖的威胁根源来自何种意识形态,这一战略还回避提出美国的地缘战略目标。显然,保守主义阵营内的不同派别在使用军事力量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没有实质性分歧,但他们在反恐战略的根本目标方面还有众多分歧。
以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为代表的军方和军工集团原准备对美国军事体系作深刻的改革,布什政府制订了重组军事结构和指挥系统的详细计划,并打算对未来美军武器系统作全面的评估。由于“9·11”事件的发生,美国军方不得不投入一场反恐战争。但是以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为核心的恐怖主义势力并不是美国军方和军工集团理想的敌人,因为这个敌人既没有大规模的军事目标可供打击,也没有强大的经济军事潜力以构成美军得到更多军费的理由。今后,甚至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充当“基地”等组织的庇护所,因此,对美军来说,对付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难免会有一种空有“屠龙之技”的感觉。兰德公司专家和米尔斯海默等人认为,反对恐怖主义主要是一场精神和思想方面的斗争,美国不宜宣称自己在进行“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它只是在“同恐怖主义斗争”,他们也不愿将所有的恐怖主义组织都视为美国的敌人,认为美国不必把所有发生恐怖活动的地区都当作美国反恐的前线。www.rand.org/publications/mr/mr1620/;http://globetrotter.Berkeley.edu/peple2/mearsheimer/mearsheimercon0.html.这种思想表明,这个集团不太情愿将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看作是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
保守势力虽然都赞成增加国防费用,但是他们也知道,美国不可能长期维持如此之高的国防预算比率。因此,美国必须对现有的军事和武器体系进行调整,重组和消除那些任务重叠的机构,改变过时的军事战略,提早淘汰低效的武器系统。这种对国防资源进行改组的调整必然影响到各国集团的利益再分配,引起他们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军队和军工集团中的某些势力对拉姆斯菲尔德主持的战略与政策调整已有不满,而反恐战争使这种调整变得更加复杂。在老保守主义势力看来,布什总统对拉姆斯菲尔德支持力度不够,没有提出全面的军事战略,而且一味做“减法”——放弃一些已经订购的装备和拒绝增加军队数量是“不实际的”。而支持“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ism)的凯托研究所则强调,布什应当坚持他的改革原则,放弃一些已经失去意义的重武器系统,如陆军的“十字军火炮系统”,以腾出经费采购更为先进的其他装备。Richard Lowry, “Bombing the Pentagon, Don Rumsfelds Agony”, Nantional Review, Sep. 3, 2001.
尽管反恐斗争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突出,美国军方和新保守主义势力中有一些人仍坚持从“能力”角度看待中国的所谓威胁,他们认为美国不应长期推迟与中国的“竞争”,顽固地要将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敌人。但是这种态度引起了不满,保守主义势力中有更多的人要求采取现实主义方针,保持同中国合作以便使美国全力对付恐怖主义威胁,属于新保守主义阵营的《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文章说,小布什政府中军事机构的影响过大,它们虽然制定了具有核心思想的亚洲政策,但那是一种错误的核心,这种政策试图“追求一种旨在孤立中国的新俾斯麦主义”,该文作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方针,布什政府应采取现实主义的政策,在亚洲继续推动已经为亚洲国家所接受的民主化进程和经济一体化进程。Ramesh Ponnur, “Get Realis”, National Review, Dec. 31, 2002. pp.1719; Gary Schmitt, “Our Ambivalent China Policy”, Weekly Standard, July 15, 2002; George Gelboy and Eric Heginbotham, “Getting Realism”, National Interest, Fall 2002.
在如何打击“邪恶国家”方面,保守主义也有分歧。新老保守主义和军方保守势力已经非常明确要开动战争机器,推翻萨达姆政权。《国民评论》杂志早在去年10月就提出了这一要求,它甚至提出肢解伊拉克的主张。Richard Lowry, “End Iraq”, National Review, Oct. 15, 2001.但是对于保守势力内部尤其是共和党的温和派来说,不顾国际舆论与盟国反应的仓促行动是不可取的,美国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证据可以把萨达姆政权与“9·11”事件联系起来。温和派并不反对推翻萨达姆政权,但是认为美国应当更加耐心地等待时机,以免对伊战争破坏反恐战争的全局部署。同时,保守势力对于如何处理“后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局面也有争论。同样,他们在如何与朝鲜政府打交道方面也缺乏一致意见。
更为有分歧的是,保守主义势力还不能对反恐战争的未来前景形成一致意见。新老保守主义和宗教右翼希望将矛头指向沙特和“瓦哈比主义”,至少也要明确指向中东地区激进的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他们希望以此构建美国21世纪的安全战略,并树立起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道义理念。但是温和派并不打算推行一种在中东追求全面变革的政策,担心这会演变为无法完成的复杂任务。保守主义势力中的石油和军工集团与沙特政权有着太密切的利益关系,沙特阿拉伯在最近10年中仅军火就采购了3000亿美元。因此,这两个集团不打算直接打击沙特阿拉伯政权,以免影响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既得利益。他们仅希望打击“萨拉非主义”,这也是沙特政府早已认定的敌人:一种反对伊斯兰本国统治者的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Michael Hirsh, “Bush and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Sep/Oct 2002, pp.1943; Victor Davis Hanson, “Our Enemies, the Saudis”, Commentary, JulyAugust 2002, pp.2328.目前这些辩论还在进行,它反映了保守主义各派在确认主要战略对手的问题上还不能真正形成一致意见。当然,在美国军界中也存在着反对“瓦哈比主义”的呼声,他们可能推动政府的政策向这一方向变化。
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是以保护和维持西方文明为根本宗旨的。在最近20年中,他们一直同国内的自由主义力量就文化多元主义,世界的多样性、道德与家庭、社会福利等问题进行政治辩论。在他们看来,美国文化与价值观念在国内与国际上都受到了严重挑战。保守主义已经确认,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中,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正在对美国的安全以及它的价值观进行挑战。美国保守主义势力正在将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尤其是这一意识形态中的极端势力,看作西方文明的主要敌人。他们希望对从南亚到中亚、从西亚到北非的广大地区进行多种方式的军事和政治干预,以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David PryceJones, “The New Cold War, Familiar Battle Lines, Unfortunately”, National Review, Nov. 5, 2001.
保守主义虽然没有直接鼓吹“文明的冲突”,他们深知在当前世界中公然拒绝和歧视其他文明是不能被接受的,但他们的政策要求很可能会间接地推动这种冲突的发展。当然,这种冲突也是一些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所希望看到的,他们正在克什米亚、车臣等地努力挑起这种宗教与文明的冲突。而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潮也在为这种冲突火上加油,他们的要求一旦成为政策,必定会加深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也许,这种后果将对当代国际关系造成长期和难以预计的复杂影响。
在可以预期的未来,G.W.布什政府仍将深受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应看到美国毕竟是一个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中还存在着对保守主义势力的种种限制。除了保守主义势力自身的分歧外,美国政治中自由主义思想是保守主义思潮的主要限制,自由主义力量正在重整旗鼓,希望借助“9·11”事件后公众要求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外关系的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一些自由主义评论家强调,较为宽容的文化和对外政策是成功打击恐怖主义的途径,较为强大有力的政府是保障公民安全的基本条件。
保守主义思潮的强化是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条件引起的。美国公众,特别是中产阶级,目前对共和党的经济政策并不看好。如果布什政府不能扭转美国经济低迷的局面,那就会对美国政治产生复杂的冲击。由于安然公司等大公司发生了一系列的腐败丑闻,这会使选民对共和党增加怀疑,因为共和党与美国大公司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最近天主教会内也发生了一系列丑闻,这种局面可能也不利于共和党候选人参与中期选举。美国选民很可能倾向于选出共和党控制白宮,民主党控制国会的局面,他们可能不愿意看到共和党影响过大的情况。如果国会控制权易手,保守主义思潮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影响也会进一步受到限制。
在国际方面,欧洲各国在对伊拉克问题上与美国的冲突表明,盟国已经对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和独霸政策相当不满。欧洲盟国虽然不能阻止美国做它想要做的事,但从长远看,美国也很难忽视欧洲国家的声音。从全球地缘政治角度看,中、俄、印等大国与美国的关系仍将是复杂的,美国可以在一地、一事上不顾这些国家的重大利益,但它无法长期忽视这些国家的基本利益。因此,随着反恐政策的进一步形成与推进,在大国合作与协调方面,保守主义思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向现实主义回归,并影响到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Philip Gordon, “Reforging the Atlantic Allianc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2002.
在多边体制中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
*
*本文原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①Economics, October 18, 1997.
一、全球化与多极化趋势下的复杂国际环境
随着信息、通讯和交通技术日益迅速地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在悄悄地影响着每个国家和世界上多数人的生活。今天,信息、资本、技术、商品和人才正以过去不可想象的规模和速度在世界上流动,从而把全球经济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过去的10年里,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是产出的两倍,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是产出的3倍,国际股票买卖的增长速度是产出的10倍。①
今天一家大公司要是不能把自己的长远发展同世界市场相联系,那么这家公司的前途注定是暗淡的。
全球化为各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结构性提升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但是,这一进程的前景与限度、利益与弊端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和风险已经相当清楚: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缺乏竞争力,它们的民族工业可能因外国产品的长驱直入而破产。在发达国家中,由于资本流向劳动力低廉的国家,国内工人的工资水平将下降,就业将更加困难。由于多国公司具有强大和灵活的能力,单个国家很难对其实行有效的管理。由于规模巨大的金融活动可以轻易地跨越国界进行,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这类活动的巨大风险。
全球性经济问题表明,无论是要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还是要避免随之而来的风险,国际社会都必须通过更加深入的合作找到出路。全球化使中国同世界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1996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由20世纪70年代末的13%上升到30%以上,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的对外依存度。《瞭望》,1997年第34期,第21页。对于全球化经济环境的挑战,中国政府已在通过国际多边体制做出反应。从80年代起,中国已经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进行合作。进入90年代,中国参加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的活动,并正在争取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可以相提并论的是,当前国际政治中出现了力量多极化趋势,这是冷战结束后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的事实。虽然,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还能维持其优势和霸权地位,但是欧洲、中国、日本和俄罗斯无疑会在21世纪中拉近与美国的距离,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将会逐渐下降。
目前,国内很多人认为,多极化是一种对我国有利的发展趋势。其实,多极化的趋势并不意味着未来的国际秩序必然比现在的秩序更稳定。国际关系史表明,多极体系像两极体系一样有可能引起频繁的动荡和纷争,直至引发战争。19世纪的欧洲国际关系表明,多极体系是很不稳定的,国家之间改变结盟和战略关系是常有的现象,为此还经常引起地区性战争。在20世纪初期和30年代,由于恶性竞争,多极体系最后又“极化”为两极体系,并带来两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后果。一些专家指出:在多极体系下,大国可能无情地在全球等级体制中相互争夺优势地位。在这里虽然不一定有国家谋求统治世界,但所有国家都不想处于屈从地位——“因为没有一个大国愿同比它弱的国家平等相处,他们只想同比其强的国家平等”。因此,这些专家认为,找到一种维持多极世界和平的机制将是严重挑战。与单边或双边方式相比,多边方式将是制止大国竞争的较好方式。Charles W. Kegley , Jr., and Gregory A. Raymond, “GreatPower Relations: Paths to Pea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Global Agenda,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ed. by C. W. Kegley, Jr. and E. R. Wittkopf,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95, pp.154165.
多极化对中国的国际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多极化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际环境肯定得到改善。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在多极体系中仍将属于较弱的一极,中国在很长时间内必须集中力量进行国内建设,同任何大国发生对抗都不符合中国的基本利益。在多极体系中,中国的行动自由虽然会有所增加,但是该体系的不稳定性完全可能抵消这种自由所带来的好处。利用多极体系与某个国家联合,同第三方抗衡也是行不通的,钱其琛副总理1997年12月在吉隆坡指出:冷战时期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安全观念和体制已被证明不能营造和平。在新的形势下,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更是有悖于时代的潮流。要争取持久的和平,就必须培育新型的安全观念,寻求维护和平的新方式。《钱其琛阐述新安全观》,《人民日报》,1997年12月16日。
多极化是21世纪的长期趋势,大国之间或者说各极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是保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本条件。有效的多边外交和多边国际体制将是这种良性互动关系的基本表现形式,反过来,这也会推动以合作与协调为基本特性的新型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
近几年的发展表明,邓小平在1989年以后为中国外交政策做出的一系列指示是正确的。他不仅引导中国度过了苏联解体的动荡期,而且为积极利用外部环境提供了指导方针。十多年来经济的迅速增长、大量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引进、对外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表明,中国社会总体稳定,改革与开放没有受到大的干扰。因此,对中国来说,现存的国际秩序有着相当有利的一面,中国可以继续利用这种有利性发展经济,中国所需要的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与现存国际秩序并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在全世界的经济利益将进一步扩大,对中东和中亚等地的石油需求会不断增加,香港回归后对港人在世界各地的利益要加以保护;各种类型的动乱,世界各地的地区性冲突一定程度上都会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会威胁到中国的战略安全。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各种资源的紧张会损害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因此,中国应当根据邓小平提出的“有所作为”的设想,适应国际环境中不断出现的变化,进一步参与现有的国际多边体制,加强同其他大国的协调,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发挥与自己地位与国力相适应的作用。
当然,现存国际秩序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公正与不合理的因素,中国可以在承认其有利性和参与的进程中,团结中小国家对它进行渐进的结构性改革。历史表明,在现有体制之外的批判与对立并不能推动它向公正与合理方向变化。
二、在多边体制中维护和推进国家利益
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问题使单个国家的经济决策权受到了影响,政府保护本国利益、保持经济上的有利地位变得相当复杂和困难。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国家的作用被削弱了。
在关于经济全球化和技术革命对国家功能会造成多大影响的讨论中,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这将侵蚀传统的国家管辖权,但是,占主流地位的看法是:“国家没有消失,政府正在分散为职能明确的部门……与国外的同行建立关系,创造牢固的关系网络,构成新的、跨政府的秩序。”“我们并不面临国家的结束,而只是面临建立在地域主权上的和相互排斥性司法权之上的政治和经济统治效率的下降。……应给国际制度真正的权力,以进行监测、控制甚至征税。”“民族国家将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中生存下去,但它将是发生巨大变化的民族国家,尤其是在国内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外经济政策、对国际商务的控制,以及可能的战争行为这些方面发生变化。”AnneMarie Slaughter, “The Real New World Order”, ForeignAffairs, Sep./Oct. 1997, pp.183197; Stephen J. Kobrin, “Electronic Cash and the End of National Markets”, Foreign Policy, Summer 1997, pp.6567; Peter F. Druncher,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NationState”, Foreign Affairs, Sep./Oct. 1997, pp.159171.
可以肯定,国家实施其职能的领域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动和转移,部分传统的直接治理正在向间接治理转变。因此,积极地开展多边外交是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职能变化的一种途径,因为多边体制正是权力移入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在一个高度复杂的世界中,权宜之计的和单边主义的利益考虑不可能提供必要的合作层次”。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Regimes, ed. by S. D. Krasner,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121.1997年,通过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多边谈判,各国先后在信息产业、电信产业两个领域中达成了贸易自由化协议,并且就金融服务业的开放达成了协议。这些进展表明,多边体制的决策作用已经不可忽视。
国际多边体制理论的主要倡导者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多边体制为解决当代国际问题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机制。作为一种中介安排,多边国际体制有助于世界各国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它通过提供谈判的规则、规范、原则和程序,使各成员更容易意识到它们共同的利益,克服阻止达成一致的障碍,实现互惠的目标。Robert O. Keohane,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Regimes, ed. by Stephen Krasn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and London, 1983.
本文所指的国际多边体制包括全球性、地区性和专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各种多边国际协约和具有连续性的跨政府国际会议。各种多边体制操作程序虽然不同,但它们都有两个共同的基本特性,一是它们使各国走到一起,为解决共同的问题做出集体的或联合的(有时是非正式的)决定。二是它们包括一套实施已有决定的机制。Charles Hauss, Beyond Confrontation: Transforming the New World Order, Praeger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1996.
近年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表明,多边外交所涉及的范围正在迅速扩大。国际多边体制正从安全和裁军等传统的高级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环境保护和资源短缺等低级政治领域;从邮政和航海等技术领域发展到人权、人口、难民、司法等社会领域;从较具体的问题性合作扩大到较全面的地区性合作。这些扩展导致了多边外交功能的加强,使一些传统的双边外交问题也被纳入多边外交的范围之内。如传统的贸易优惠总是双边互惠问题,但是现在却以贸易自由化方式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这类多边机制中进行讨论。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中国决策层已经相当重视多边外交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他们完全认识到,传统的双边外交不能完全解决当代世界各种错综复杂、交叉关联,甚至互为因果的问题。
从世界上最初的国际多边组织——国际电报联盟与万国邮政联盟建立起,政府间国际组织已经从20世纪初期的200余个发展到1990年的4000多个。中国已经参加了其中的1000多个国际组织的活动。John Spanier and Robert L. Wendzel, Games Nations Play,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Washington DC., 1996, pp.6061, 94;新华社,华盛顿1997年10月24日电。尽管中国已经参加了许多国际组织,但由于对多边体制的理论研究滞后,有些部门对它的作用和意义仍然存在着误解和低估,有些人对参与多边体制的长期意义认识不足。这种状况不利于中国对外政策适应正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不利于中国积极大胆地利用多边机制,维护和推进中国的国家利益。
第一种较为普遍观念是,多边体制会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甚至会超越或取代民族国家,使国家丧失独立地位。实际上,多边体制的基本功能是“协调各方的行为,在某些问题领域中获得各方都想要的结果”。在多边体制中,国家对主权的部分让渡是建立在互惠和自愿基础上的。对“欧洲联盟”所作的新研究表明,没有任何重大的原因能证明多边体制会导致世界政府的出现,并使传统的民族国家消失。“最近的潮流表明,似乎最有可能的模式是一种多层系统,在这一系统中超国家的制度与国家制度同时存在,次国家的制度将以大致与现在同样的方式同全国政府合作。”Charles Hauss, Beyond Confrontation: Transforming the New World Order, Praeger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1996.
第二种观念是,强调多边体制会使人们对全球文化产生错误的幻想,从而削弱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动摇对本国发展模式的信心。其实,共性不可能否定个性,“与整体的认同可能与多种多样的政府结构是并行不悖的,这种认同能够同各种差异共存,甚至共荣,而这些差异目前却以它现存的方式危害着许多国家”。Charles Hauss, Beyond Confrontation: Transforming the New World Order, Praeger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1996.多边体制存在的本身,是世界多样性得到确认的证明,它是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找一致性。
另一种误解多边国际体制的观念是,多边体制往往沦为争论不休的讲坛,对于实际问题不能提供解决方案。的确,由于各国利益的复杂性,多边体制常常不能迅速解决一些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但是,让各国的利益要求都得到充分表达,正是国际关系走向成熟的表现。在多边体制中进行深入的讨论,很可能是兼顾各方利益的必要前提。从另一方面看,即使是一个效率很高的全国政府也不可能解决它面临的所有国内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多边体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是正常现象,因为有的国际问题并不是多边体制能够解决的。
最后,有一种普遍的担心是,多边体制通常是由西方大国占主导地位,中国积极参与其活动只会更多地受这些国家的约束,被它们“套住”而丧失行动自由。作为当代国际秩序的一部分,现有的多边体制的运作一般有利于体制的决策者和主导者。“在那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国际组织的决定通常反映力量关系和这些组织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国的目标。”John Spanier and Robert L. Wendzel, Games Nations Play, p.94.从国际法角度看,首先,国际规则和规范对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它们对西方发达国家同样有约束性。其次,成员国参加多边体制是一种自愿选择,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上,多边机制并不能剥夺成员国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其三,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出现更多的多边体制,它们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有待形成,现存的多边体制也会因为各种因素而需要修改,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和影响,完全有可能在多边体制中参与决策和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多边体制维护自身的利益,维护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
三、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多边体制
1997年《中美联合声明》确定,中美两国将共同努力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战略伙伴关系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亚太地区及全世界的稳定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这样一种双边关系,为什么要提出在多边体制中推进它的形成呢?在多边体制中推动这一关系的基本条件是否具备呢?中美之间有一部分的合作,如军备控制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基本上就是在多边体制中进行的。但应该看到的是,多边体制对双边关系的积极意义还远远不止这些。
首先,中美两国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两国虽然具有很多共同的或平行的利益,但也存在着不少分歧和利益冲突。1949年后的中美关系历程表明,国内政治因素是损害两国合作的重要原因。特别是由于美国国内存在着党派、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各种政治斗争,对华政策常常成为政治攻击的对象,两国的互利合作往往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牺牲品。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国家之间达成协议的要求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领导人对协议是否符合其利益的认识的影响。而这种认识又受到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和其他没有被“约束—选择”方式包含的因素的影响。在多边体制的中介作用下,中美两国政府能够将双边问题纳入多边谈判和多边协议之中,这种多边性质的协议有助于降低双方的“交易成本”,有利于避免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减轻政府领导人在国内政治方面的压力。Robert O. Keohane,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Regimes, ed. by Stephen Krasn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and London, 1983.
其次,由于各种原因,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非常有限,双方对另一方的政策目标都有不确定感,都认为对方的行为缺乏可预期性,对于对方能否严肃履行已达成的协议也存在一定怀疑。例如,中国认为美国可能出于政治动机阻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美国则认为中国的长期目标可能是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这类不确定性和知觉错误必然会影响两国的长期战略合作。多边体制理论认为,多边外交比双边外交有较多的公开性,各方较易于进行充分的信息交换,进行高质量的沟通,潜在的“欺骗者”将受到较多国家的监督。多边体制是“具有连续性的游戏”,它涉及许多问题,“一个体制涉及的或与之相关的问题越多,单个问题相对于整体的重要性就越小,在某一个问题上因欺骗而产生的严重性也越低”,而且其他国家对“欺骗者”报复的机也会增加。因此多边体制有助于降低双边关系中的不确定性,超越官僚机构带来的封闭性,加强信任与合作关系。Ibid.
对多边体制的第三种需要来自双边因素之外。按照中美两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两国将是世界上综合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因此,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必然波及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1997年《中美联合声明》提出:“中美两国通过增进合作,对付国际上的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还指出: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于共同承担责任,努力实现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是重要的”。 《中美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7年11 月30 日根据这种精神,中美双边的战略关系实际上将成为更为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将涉及约束破坏秩序的行为者的问题。
根据“约束—选择”理论模式,加入多边体制的国家是从自己的长远目标出发,经过利益比较,愿意把自己同其他成员国的关系建立在稳定和互利基础上。多边体制并不排弃进一步谈判,以便使规则适应情况的变化。因此,尽管体制中力量较强的成员国对其他成员国的选择具有约束性,但是成员国仍可能在自愿基础上参加这一体制。Robert O. Keohane,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Regimes, ed. by Stephen Krasn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and London, 1983.这里,可以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作为案例来分析。该体制在确认了在2010年实行地区性贸易自由化这一约束性原则后,在实现目标的方式上,该体制具有让成员自愿确定时间表的灵活性。这使得所有的成员既能根据自身的条件逐步实现自由化,同时也能确保贸易自由化这一原则最终得到实现。这种既有约束性又有灵活性的规则,不仅满足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成员的利益要求,而且吸引了更多的国家希望加入该体制。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在多边国际体制中,约束性和自愿性是可以得到充分统一的。如果在多边体制中推动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中美双方就能以较低的代价实现其战略目标。通过多边体制的决策过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就能最大限度地同其他国家的利益保持一致。同时,多边体制还能为实现中美两国共同的战略目标提供合法性基础,使多边体制的约束性可以为双边关系的战略目标服务,使国际秩序中的强制性约束需求降到最低点。
在多边体制中推进建设性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美国方面也要有同样的考虑。应该说,种种全球性问题已使中美两国在加强多边体制的作用方面具有较多的共同利益,但是对美国来说,与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其意义不只是解决那些具体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美国充分意识到全球化和多极化正在给美国外交带来巨大冲击,民主党政府上台后,多边外交成为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方面。美国政府对外交机构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合并改组;设立了新的副国务卿职位,专门负责协调打击毒品和国际犯罪、环境保护、难民和人口,以及人权、民主和劳工等全球性事务;国务院还招募了大批国际金融、环境科学和法律执行等专业的人员加入外交官队伍。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不久前说:美国政府正努力通过与非国家行为者——多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结成联盟,以增进“应付跨国威胁的能力”,使美国可以“同时与许多组织和机构进行多重的多边工作”。Strobe Talbott, “Globalization and Diplomacy: A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 Foreign Policy, Fall 1997, pp.6983.
在此同时,美国的主流派已经明确认识到,鼓吹“中国威胁论”对美国来说不会有益处。他们认为,中国和它的邻国的未来安全有赖于中国成为它亲自参与形成的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正因如此,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斯坦利·罗斯1997年10月在香港说:美国在亚洲一贯承诺支持多边合作,支持亚洲安全对话。中国“作为迅速发展、开放和非侵略国家的兴起,拥护走国际规则的道路将对亚洲和世界具有最深远的影响”。他说,美国一直在寻找机会与中国就共同的责任进行战略对话。美国希望看到中国与形成中的世界体系一体化,并帮助这一体系的形成。A. J. Nathan and R. S.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W. W. 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1997, p.231; USIA, East Asia/Pacific Wireless File, Oct. 16, 1997, pp.1618.
克林顿总统本人也认为,美国和中国在国际多边事务中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克林顿在江泽民访美前夕发表的对华政策讲话中说:中国在21世纪将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扩大合作的领域,坦率地对待双方的分歧,就能促进美国的利益。克林顿高度评价了两国在联合国和裁军领域等多边体制中的合作,他说:“建立一个和平、繁荣和稳定的世界,关系到美国的根本利益。如果中国加入这一过程,不仅遵守国际行为准则,而且帮助制订和实施这些准则,我们的任务会容易得多。”新华社,华盛顿1997年10月24日电。他承认在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打击国际有组织犯罪、推进更自由和公平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环境和大气保护这些“涉及美国根本利益”的领域中,美国必须同中国合作。
美国方面的观点表明,美国一方面需要中国的合作,从而推动全球化和多极化条件下的国际新秩序的形成,另一方面美国又想按照它的愿望将中国纳入这一秩序中。这两种愿望其实存在着一定的自相矛盾。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虽然美国在建立这一秩序的过程中会起重大作用,但未来的新秩序不能由美国一家来决定,在建立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完全可以在同其他国家合作的同时,努力贯彻自己的观念和目标。这是中国同美国求同存异,在多边体制中推动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形成的基础。
四、亚太地区多边安全体制:中美建设性
战略伙伴关系的支柱
中美两国是21世纪的主要大国,两国在国际多边体制中进行充分合作可以消除国际关系中许多不稳定因素,并且有助于形成互利的国际环境。两国进行多边合作的领域可以包括经济和贸易、防扩散和军售、地区安全、国际维和、国际执法、环境保护和打击国际犯罪等很多方面。这些合作是符合双方利益的,而且通过这种合作,中国还可以进一步要求美国取消对华制裁,放宽对华出口控制,认真履行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诺言等。
中美两国也是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一方面两国在该地区都有高度密集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台湾等问题上又存在着较严重的分歧。双方如果不能在这一地区找到共同的战略利益,两国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进程就会遇到严重障碍。双方如果能在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的基本理念和方式上达成共识,并以地区性多边安全体制作为一种载体表达这种共同利益,双方就能求同存异,建立起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支柱。
亚太地区的经济变化对全球经济体系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这种变化也会影响21世纪的国际安全结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发展迅速,但是政治与安全合作却比较滞后。亚太地区国家能否使现有的安全体系适应和赶上变化了的经济环境,将“主要取决于该地区的国家是否意识到需要进行调整,以及他们如何对因经济变化而产生的安全挑战做出反应”。这些挑战包括各国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对资源和市场的竞争,国家内部变化带来的问题,以及像人口非法流动、非法贸易、国际毒品走私和犯罪等新问题。R. B. Zoellick, “Economics and Security in the Changing AsiaPacific”, Survival, Winter 1997—98, pp.2949.
此外,其一亚太地区各国之间还普遍存在着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和领海争议,因此在安全问题上相互信任度较低。其二,在朝鲜半岛还存在着冷战的遗留问题,这一潜在的“热点”威胁着地区和平。其三,以军事同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行为还时有发生。这些问题不利于地区性合作的深化,使本来应投入经济发展的资源被转移到军备领域。上述这些经济和安全领域中的挑战和冲突,有些是潜在的,有些已在上升之中,它们突出地表明了建立地区性多边安全机制具有紧迫性。
中国政府早在1955年就提出过建立亚洲和平公约,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为亚洲各国的和平共处而提出的设想。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现状基本上是稳定的。在江泽民访美成功之后,建立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条件更趋成熟。一种新的安全合作机制不仅将为本地区提供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同时它还会逐渐替代过时的以军事同盟为核心的安全方式,创造各方都能接受的并使美国军队最终撤离亚洲的条件。
中美在建立地区性安全机制方面可以进行充分合作,这种合作应该以维持地区国际关系现状为基本理念。“只有各国都接受现状,认为战争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将对其他领域产生严重影响,安全领域中的国际体制才可能形成。” 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Regimes, ed. by S. D. Krasner, p.12; Robert Jervis,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Regime, pp.173194.中美两国能够从维持地区现状上得到重要的利益,中国在过去20年中没有大战的威胁,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实现了香港的顺利回归,台湾问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如果这种趋势保持下去,中国的经济实力必将继续增长,国际地位和影响也将不断加强。当然,美国也可以在该地区稳定地获取不断增长的经济利益,它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变化。
台湾问题是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进程中的障碍,也是建立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时必然要遇到的难题。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努力用和平方式实现统一,但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中国政府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是相当明确的,但“台独”和国际反华势力却一直歪曲中国的政策。从“台独”势力和台湾当局对中美关系具有一定破坏能力来看,中国政府对现有和平统一方针的措辞可以进一步明确,在保留使用武力的权利方面做出更清楚的规定,争取台湾同胞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统一方针有更完全的了解。基欧汉说过:“在合作发生时,每一方在改变自己的行为时,都是以其他方也改变行为作为条件的。”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Westview Press, Boulder, San Francisco, 1989, p.189.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明确承诺支持海峡两岸最终统一的情况下,在台湾当局明确放弃“台独”的条件下,中国政府可以允许台湾以某种准成员方式进入地区性多边安全体制。
中美两国在建立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方面已经开始合作,已经进行了两轮会议的朝鲜半岛四方会谈即是例证。这一会谈表明,中美两国在建立地区性安全机制方面不仅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能起到互补的作用。两国的这一合作对于消除亚太地区的冷战遗留问题,加强和平与发展的地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2050年的中国、东亚与世界
——基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分析
*
*本文原发表于《人民论坛》2013年03上总第21期。
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中国人民建成富强、民主、和谐与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如果以2050年为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时间节点,要实现以上目标,任务是极为艰巨的。为此,中国仍然需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需要一个公正和良性互动的国际秩序。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世界各国的竞争可能进一步加剧;随着各国的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的进一步纠缠,今后的国际关系可能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如果应对不力,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不但不能完成,中国和平发展的未来战略空间还可能被进一步压缩。因此,中国必须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主动地抓住战略机遇,塑造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利的国际新秩序,开创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一、1949年之前国际秩序的发展历程
历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辉煌文明与领先国际地位的民族。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中华文明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具有广泛与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将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看作一种若干“同心圆”的扩散,还是将其看作一种“朝贡体系”,两千多年来中国的不同朝代虽有强盛衰弱之别,有统一分裂之变,但直至欧洲国家开始殖民扩张之前,中华帝国在亚洲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却是无可替代的。
明朝初年,国土不算广袤,军力不算强盛,但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制定了开明的对外政策。结果,“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爪哇、大琉球、三佛齐、渤尼、彭亨、百花、苏门答剌、西洋邦哈剌等凡三十国”。参见《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四。永乐年间,朝廷派遣郑和为正使率庞大船队出访西洋。据在南京发现的下西洋副使太监洪保的寿藏铭记载,这些远航“风飘海舶,远迩必通。所至披靡,孰有不从。群星共北,众流趋东”。《洪保“寿藏铭”揭开郑和下西洋谜中谜》,《扬子晚报》,2010年10月29日。这里虽有宣扬帝国威望的夸张之辞,但明王朝当时的主导地位亦可见一斑。这是中国经历的“1.0版”国际秩序。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它是一个等级制的秩序。中国高居塔顶之上,并用国家实力和儒家学说维持这一秩序。明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拒绝与世界其他国家往来,这种措施使传统中国“失去了调整自身、适应世界历史变迁的持续性的机遇”。陈支平:《以世界史视野看清代的历史地位》,《北京日报》,2012年9月11日。中国与工业化进程中的欧洲国家的实力差距不断扩大。西方列强从17世纪中期起将“2.0版”国际新秩序强行推行到世界各地。在欧洲,该秩序是文明与历史的进步,但到了亚洲等地区,它的丑陋就暴露无遗。在工业化的同时,西方国家推行殖民化政策,亚洲国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不同程度地丧失了主权与领土。西方的文化和市场原则被肆意利用,以维持不平等关系。这其实是一种弱肉强食的秩序。在自由贸易的借口下,连鸦片贸易都成了西方商人的合法行当。由于制度和生产力落后,中华帝国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不断下降。1840年以后,拒绝改革的清政府使中国丧失了世界大国的地位,甚至耻辱地失去了大片国土与权利。中国在这一秩序下毫无尊严和地位,西方的理由是亚洲国家不具备“文明国家”的法律体系,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还不能享有一个主权国家的平等权利。
在“2.0版”国际秩序下,中国实质性的收获是开始了解来自西方的各种政治和经济思想,开始学习现代国际关系的各种规则,并且以很大的代价体会了大国“秘密外交”等各种潜规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孙中山提出了以民权、民族和民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思想,并且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中国决心通过自我革新来摆脱不平等的地位,追求新的、公正的国际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3.0版”国际秩序仍然是实力基础上的秩序,美苏两国拥有其他国家不能企及的巨大军事和经济力量。战后的美国经济一度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45%以上,这为它掌控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19世纪末期,欧美社会出现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普通公众与工人阶级反对战争与殖民主义对外政策,这迫使统治阶层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美国的国际主义外交方针战胜了孤立主义思想,为美国构思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可能。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不仅依靠庞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且也建立在它坚实的软力量基础上。美国在规划战后国际秩序时,设计了一整套国际制度,由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及世界银行等构成,后来还增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多个军事同盟组织。依靠这些国际制度和一些国际法准则,美国形成了一种以操控国际制度为特点的霸权。它用自己的价值观构成国际规范,并以此确定相关国际组织的规则和目标。有了这些合法手段,对于违反其目标和利益的国家,美国便可采取各种强制性措施,甚至发动战争进行打击。
与美国相比,苏联战后的国际影响力明显要小。苏联不能将自己的观念与准则转化为国际规范和规则,更无法主导战后出现的大批国际组织。俄罗斯帝国是殖民主义“2.0版”国际秩序的获益者,同时它又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落后者。正因如此,列宁曾经试图从自身做起,摆脱殖民主义秩序,但最终并未实现这一目标。斯大林在掌权后成为玩弄大国“秘密外交”和“势力范围”的高手,这一度为苏联在二战前后的国际政治中扩大了利益,但这也是苏联始终不能摆脱扩张主义传统,并最终解体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在国际秩序中逐渐崭露头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3.0版”的国际秩序已经形成,中国很难确定自己在这一秩序中的位置。虽然殖民主义的国际秩序在第二次大战后已经崩溃,中国的国家主权也大体恢复,但中国的最终统一尚未完成,国际环境相当恶劣。中国面临重建经济和现代化的艰巨任务,但美苏冷战使中国不得不在两个阵营中选边站队,参与对抗。两个主要大国都曾经以中国为敌,当时中国领导人也对国家安全形势发生过严重错误的估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卷入两场地区性战争,同两个主要大国有过多次战争危机,在周边地区还不得不应对一些局部性军事冲突。中国基本不能适应现存国际秩序,因此也不可能从这一秩序中获得利益。由于经济增长率低和人口翻番,从1950年至1973年,中国人均GDP的增长率仅为2.86%,低于世界同期水平。萧国亮:《从世界经济史的视域看中国的长远发展及其地位变迁》,《中国经济》,2010年第8期。中国的民族复兴事业在这一时期受到较大的挫折。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议,中国对外政策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开始了解西方和其他国家的经济管理经验,借鉴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重视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国门逐渐打开后,中国还借助国际市场来推动现代化建设,在全球化进程中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的大循环。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9740亿美元。从1979年至2010年,中国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104833.8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到2010年翻了四番多,达到5.88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8%增加到9.3%。到了2011年,中国的GDP位居世界第二。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9月6日。
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是在现存国际秩序下进行的。1971年,中国重新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先后加入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组织等主要国际组织。在经济管理制度方面,中国逐步地实现了同国际经济体制的接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9月6日。这些组织、公约和国际法包涵了现存国际秩序中几乎所有的规范、规则及重大议程。中国是发挥联合国作用的支持者,是自由贸易和主权平等原则的维护者。中国在海外直接投资快速上升,至2011年底,海外直接投资总存量达到3660亿美元,成功地利用国际市场解决了部分资源的匮乏。冯迪凡:《中企遭遇欧盟严密安全审查》,《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2月1日。
在安全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派出两万多名军事人员参与安理会批准的30项国际维和行动。中国政府积极参加反恐、防扩散及军控领域的国际合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大体上适应了战后国际秩序,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一秩序的支持力量。在此背景下,中国与现存秩序的主导国——美国形成了密切的双边关系,两国在战略、经济、文化等几十个领域开展着广泛的合作。这种合作支撑着国际局势得以保持基本稳定,阻止了冷战的再度发生。
但是,以上的情况并不意味着中国完全接受美国主导下的战后国际秩序,中国对这一秩序的不满一直是公开的。中国不能接受美国长期阻止大陆与台湾实现和平统一;不能接受西方国家维持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它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在多个领域中对发展中国家实施不公正的措施不满,这些不公正行为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不能接受西方国家以自己的人权标准干预不同历史和文明背景国家的内政,为此,中国长期同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着尖锐的斗争。那种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对美政策软弱的看法是相当片面的,中国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核心利益去换取经济利益或其他国家的“好评”。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既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也是这一秩序的受害者。叶自成、蒋立群:《新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变迁》,《党的文献》,2011年第6期。但总体看来,这一秩序对中国还是利大于弊。中国在最近30多年中逐渐适应了这一国际秩序,并始终为改革这一秩序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方面而抗争。这种看似矛盾冲突的状态其实是有着深刻背景的。
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将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要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各种有益经验,要学习当今世界一切国家的先进文化。但中国不可能因此否定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可能短期内改变落后的经济结构。中国在坚持与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方针的同时开展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以确保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
其次,战后的国际秩序以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价值观为基础,虽然它存在着诸多的不公正与不合理之处,但是它同前一阶段“2.0版”的国际秩序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为他们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保留了一定的空间。同时,西方也需要中国的合作,西方国家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中也获得巨大利益。西方国家面临着多种棘手的挑战,如果拒绝与中国合作,其自身的安全与经济利益会受到严重损害。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所说,美国公开将亚洲组织起来遏制中国,或者建立民主国家集团发动意识形态进攻,这些举动均不可能成功。亨利·基辛格:《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14页。
三、中国在构建21世纪国际新秩序中的国际诉求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漫长道路上,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未来的30年是一个更为关键的时期,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低潮期,科学技术的推进作用可能不如前一时期那样显著。国际竞争因此变得更为激烈,国际秩序面临重大调整,国际环境将更难预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表现出对发达国家不利的转向。西方发达国家对未来的变化忐忑不安,它们正在谋求变化中的先发制人。发达国家甚至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动向相当敏感和焦虑。因此,中国不仅要弄清楚自己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具体目标,更要明确告诉其他国家中国未来的国际诉求。朝着富强、民主、法治和公正方向发展的中国,完全可以用坦荡的胸怀去面对世界,在与世界的积极互动中追求自己正义的目标。
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不可能是实现了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是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标志,是这一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在未来的30多年中要努力排除妨碍和平统一的国际与国内障碍,确保国家的最终统一。这一问题的国际障碍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的干预,但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这类干预的力度必定会逐步削弱。应当看到,国际上的障碍虽然复杂,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与国内即台湾内部存在的障碍是难以分割的。近年来,“台独”势力的气焰受到了打击,但是影响统一的鸿沟尚未填平。大陆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加诸台湾的打算,更无意降低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两岸的经济差距有望在未来消除,而政治制度方面的障碍还会长期存在。不断加强的文化经济交流有助于两岸心理防线的消解,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助于不同制度的对接。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解决表明,国家的统一并不以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同一化为条件。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通过法理和法律途径的创新,通过对两岸民众权利和利益的保障,两岸同胞必将形成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两岸的和平统一定能够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另一重要标志是,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地位显著上升,成为东亚和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家之一。要取得这一地位,首先有赖于中国军事力量在未来30年的稳步增长,有赖于国防现代化的顺利完成。2050年,中国将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大国之一,在第一岛链地区有可靠的海洋优势,在第二岛链地区有强大的维护和平与国际航行安全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还应拥有能快速部署到印度洋以西地区的军事能力,能对波斯湾及红海地区局部性、低烈度的国际冲突予以威慑和打击。其次,中国要有能力把自己倡议的新安全观转化为有效的政策,在东亚地区建立多边合作的安全机制,并对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将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同时,实现地区各国共同安全的目标。平等合作而不是以对抗求安全的思想将在东亚地区获得普遍认同,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诉诸武力来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将成为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基本特点。
中国在地区事务中追求的目标是合作共赢。中国在东亚并不谋求霸权和垄断性的地位,不排除美国、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愿意同其他有能力的国家合作,共同主导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冷战时期的遗产——军事同盟可能仍然存在,但它的作用已经大打折扣,东亚国家对共同安全的需求大于对同盟体系的需求。将中国排除在地区安全体系以外,利用军事政治同盟包围和孤立中国,是中国不能接受的。在这一地区违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穷兵黩武、抱住冷战思维不放的行为同样也是中国不能接受的。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带来稳定与友好的周边关系,中国将保持并增进同俄罗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俄关系在21世纪仍然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在经济与安全领域中的合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双方在构建21世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中也将有多领域的合作。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中国有望在互谅互让基础上解决同印度的领土争端问题,解决同其他国家的海洋领土及专属经济区划分等问题。但是,解决领土及专属经济区的争议问题并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必须完成的工作。中国不会奉行扩张主义政策,中国可以等待其他国家的妥协意愿。中国将尊重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以换取印度尊重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中印两国将高度重视军备控制,以防止陷入“安全困境”中。中国将提升与其他南亚、中亚国家的关系,上海合作组织可以适度增加成员国,它不仅是打击这一地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主要工具,也是各成员国间加强安全与经济合作的工具。中国要加强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支持它的国家安全与现代化进程。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有重大影响力。到2050年,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应当高于20%,这个比重是衡量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自公元元年到19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始终占世界经济的20%以上。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只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0%左右。[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1页,图表B20;《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2011占世界份额10%》,《解放日报》,2012年6月4日。未来30多年中国的经济虽然将继续增长,但年平均增长率会下降到6%左右。在实现以上目标的同时,中国要大幅度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使中等收入阶层人口占到55%以上。要实现以上两个目标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中国未来必须加大经济改革力度,尽早完成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体制改革,提高在国际分工方面的地位,以确保持续增长的空间。参见北青网,http://house.ifeng.com/news/detail_2011_12/16/11369857_0.shtml,2011年12月16日。
保持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国参与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中国已经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同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更加完善和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中国国内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也是今后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需要。中国要加快完成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在30年后应是国际结算和国际储备的主要货币之一,从而成为中国影响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中国要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合作,并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帮助,努力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要推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集团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更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共同构建真正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为21世纪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做出贡献。
确保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保证。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今后几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能源建设任务重大。”江泽民:《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确定中国能源战略,必须认真思考能源国际合作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因为能源问题发动战争;20世纪后半叶,能源问题是中东战争背后的重要因素;同时,石油供需的不平衡还引起国际油价反复大幅度波动。研究表明,今后30年仍然是油气资源大体供求平衡的阶段,特别是全球性的“页岩气革命”,能明显缓解国际能源的供求关系。张国生、梁坤、武娜:《未来十年世界石油供需格局判断》,湖北省人民政府政研网,2012年12月27日,http://www.hbzyw.gov.cn/News.aspx?id=10591;刘增洁、梁伟:《最新世界能源供需预测》,《国土资源情报》,2009年第10期,http://news.chemnet.com/item/20100420A327132.html。
当前,中国石油进口已经达到需求量的50%以上,未来30年是中国能源需求继续快速增长的阶段,中国油气资源的短缺必然使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提高。但是,从世界石油供需总量平衡角度看,中国不必因“石油资源短缺”而陷于“石油供应恐慌”。“页岩气革命”将蔓延到中国,明显缓和中国的油气短缺问题。中国在这一阶段完全有可能以国际合作为基本方针解决油气问题。与此同时,要认真从技术和经济两个角度为未来使用可再生能源做好准备。能源的国际合作必然要采取多样化的策略,但中东及波斯湾的油气将继续占较高比例,对于这一点需要有战略准备。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否成功,还要看中国在国际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中能否起到积极作用。正如“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xj.xkihuanet.com/20121V19/c_113722546.htm。自冷战结束至21世纪中叶,是孕育“4.0版”国际新秩序的阶段,也是中国参与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不断加强的年代。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实际上一直在尝试国际秩序的改革,以确保它们在新的国际秩序继续占有优势地位。[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体系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它们以保护人权和实现民主为由,频繁地干预发展中国家内政,甚至使用武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诚然,维护和平和尊重人权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原则。但是,西方能否以保护人权为由而将尊重国家主权、不使用武力和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弃如敝履呢?其实,《联合国宪章》序言中强调,为保护人类和尊重人权,最重要的方法是“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接受原则,确立方法,以保证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用是发愤立志,务当同心协力,以竟厥功”。《联合国宪章(序言)》,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这些重要思想因为冷战中的对抗而被忽视,因为西方的自私而被冷落。在重构21世纪新秩序时,世界各国应当重温宪章中的这些思想和原则。
中国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十八大报告对这些精神还作了深入的解释:“平等互信,就是要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主权,共享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构建未来的国际新秩序首先就是价值与观念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是未来新秩序的基础,是超越将世界各国人为分成对立集团、以意识形态对抗为标志的“3.0版”国际秩序的重要观念,是对《联合国宪章》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是对所有人民、文明和国家都负责任的思想创新。
要实现以上目标,中国还要在国内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体制,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进一步尊重和维护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必定是在与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中推进的。“国内秩序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内部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有效组织会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力。”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组》,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45页。“十八大”已经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且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中国在人权建设的道路上正在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到21世纪中期,以上价值体系应得到公众普遍认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得以完成。同时,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将广泛传播,西方对中国歪曲诋毁的空间将逐渐缩小。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只有更自信地高举人权的旗帜,才能揭穿西方某些国家以人权为幌子而行霸权的真面目,才能在建构21世纪国际秩序中发挥强有力的主导作用。
保持中美和平合作、实现中美共赢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的重要目标。冷战结束后,中美间的合作关系维持了大体的稳定发展,但是其中的坎坷曲折也非常突出,这是国际结构调整的必然表现。美国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必定会挑战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中国的所得必然是美国的所失。因此,阻碍两国合作、压制中国的发展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经常性选项。当然,战略性的互疑也不完全是单方面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美国的打压,中国社会精英中也存在对美国的怀疑心理,认为美国因其霸权需要不会接受中国崛起。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2年。
21世纪的中美合作事关世界全局,是维持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基本因素。当前,两国在几十个领域进行着密切的合作,经贸和金融领域的数据非常可观。在各种国际多边制度中,中美两国也进行着广泛的合作,如在军控与防止核扩散等国际安全问题、多数地区性国际问题以及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方面,双方都有着积极的互动。美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中美合作的意义,“在广泛的全球问题系列中,包括多边制度的未来、全球金融体系、核未来、网络安全、外层空间、气候变化、全球资源短缺及亚洲安全—美中关系都将是问题解决或失败的一个主要推动者”。Atlantic Council: Envision on 2030, US Strategy for a Post-Western World, A Report of Strategic Foresight Initiative at Brent Scowcroft Center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inciple drafter: Robert A. Manning, http://www.acus.org/files/publication_pdfs/403/Envisioning2030_web.pdf.pdf, p.32.因此,中美两国在未来形成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是有其基础的。
同时,中美之间的矛盾是多样和深刻的,这些矛盾既来自当下,也会来自今后出现的问题。美国在台湾、意识形态输出和中国周边局势等问题上不会轻易改变现有损害中国利益的政策,但双方已有的管控措施会阻止这些矛盾转化成严重危机。中国的和平发展及改革的深入将会逐渐削减美国压力的效果,中国今后要继续敦促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自我控制,并联合其他国家抵制美国可能的霸权行为。
从长远的视角看,中美两国可能面临来自海洋、空间和网络等领域的竞争,中国在相关领域的进展将被看作挑战美国霸权的“证据”,成为一些美国人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理由。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是高度关联的,因此,双方都要学会应对这种平行四边形般的互动。中国既要争取对方主张合作的力量,抵制主张对抗的力量,也要避免简单的两分法可能造成的事与愿违的结果。中国要不拘一格地进行策略与方法调整,加强对外事务的开放透明和民间互动,使用对方能够理解的方法去沟通。中国有必要主动拓宽两国利益的交汇点,敢于寻找长期战略合作的机会。
“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十八大”的这一精神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指引下,努力奋斗,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宏伟目标。
后记
后记
对于这一论文集的出版,我首先要感谢“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基金”的慷慨赞助和南京大学出版社的精心编辑出版,尤其是要感谢石斌教授的盛情推荐。没有他们的努力付出,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根本是不可能的。
这一论文集的编辑出版,正值我办理退休手续之际,虽然教书和研究工作并未停止,但是有这么一本文集的出版,理当借此机会回顾一下自己的学术生涯。“文革”结束后,我于1977年考入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攻读历史学专业。四年后因兴趣使然,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师从专攻美国外交史的王明中先生。1984年底获得学位后留校工作,参与筹建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1986年我又考上本校著名国际关系史大家王绳组先生的博士研究生。王先生受“兰克学派”熏陶,不仅治学严谨,而且学术上高瞻远瞩,见微知著。他的这种治学态度让我受益终生。读博期间,我还得到过本系吴世民老师和卢明华老师的悉心指导。南大国际关系史学科的优秀学术传统使我获益良多,对各位老师的恩情实在是无以为报,只能将此传统铭记于心,并以此教导自己的学生。
在南大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决定将这些文章汇编列入《学人文丛》出版后,我也是第一次去重新审读这些过往的文章。开始时不免有些惶恐,这些多年前的作品今日是否会误导后人?青年时代的写作是否会谬误多多不堪收录?细细读完之后还是松了一口气,虽然这些文章不免有所差池,总体上还能经得起时间检验,大概不至于违背了师长们经常叮嘱的“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教导。我的研究工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冷板凳”不仅是物质贫乏之冷,也是环境蹉跎之冷,正是靠着内心对学术的热情才能坚守过来。
这一论文集中收录了我已往三十年来的部分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亚洲冷战史研究和美国对外政策研究两个部分。这些成果均发表于各类学术刊物、会议论文集和几本编年史性质的书籍中。对于当下的读者来说,即使有因特网的帮助,这些文章可能也已不好找了,因为文集中的有些论文成稿于我使用电脑写作之前,当年没有电子文档的存储。现在,这些旧稿能结集出版,可以给后进学子一个交代,也算是为已往的学术活动做一总结。它可以激励自己,保持终身学习的态度。检视这些旧作,不能不想起几位扶持过自己的前辈师长,他们是陶文钊先生、资中筠先生、刘同舜先生、汪熙先生、姚春龄先生等,正是有了他们的指引和教诲,我在学术道路上才少走了不少弯路。
这一论文集几乎完全是按照当年原样进行编辑排版,只是根据目前论文集的体例要求,为少数几篇论文增加了分节标题,删节了个别文章中过多的标题和篇幅,订正了一些当年写作和印刷时错字。在此书的编辑过程中,南大出版社的编辑官欣欣仔细校对编辑了全稿,对此我要深表感谢。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同事曹强老师和多位中心的同学为旧稿的电子化出了力,在此也一并感谢。
蔡佳禾记于南大鼓楼校区
2018年岁未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简介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是由“南京大学郑钢基金·亚太发展研究基金”定向全额资助的一个对大亚太地区进行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的机构。它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
该中心是国内首家以“发展”为关键词命名的综合性地区研究机构,秉持“立足中国、面向亚太、辐射全球”的开放理念,旨在探讨亚太及全球“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诸领域的重要议题,彰显“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崭新的全球价值观。
“中心”定期主办“钟山论坛”(亚太发展年度论坛)、“励学讲堂”等学术论坛,旨在推动国内外学界、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中心”主办的出版物有《南大亚太论丛》、《南大亚太译丛》等系列丛书,《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成果。此外还有《工作论文》、《调研报告》、《工作通讯》等多种非正式刊物。
通信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163号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圣达楼460室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210023)
电子邮箱:zsforum@nju.edu.cn
电话、传真:02589681655
中心网址:https://www.capds.nju.edu.cn
微信公众号:CAPDNJU
已经读完最后一章啦!
90%的人强烈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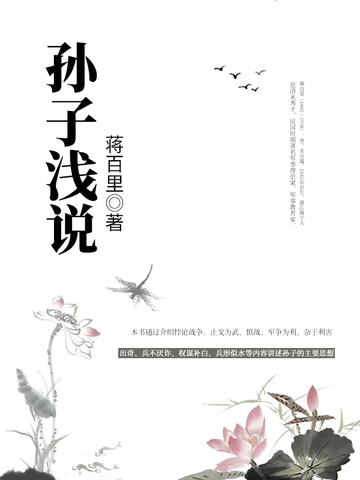
孙子浅说
孙子浅说
- 书名:
- 孙子浅说
- 作者:
- 蒋百里
- 本章字数:
- 240
统读十三篇,以主德始,以妙算终,此孙子之微言大义也。其每篇标题之字,亦不过如“学而”、“雍也”之类,勿庸刻舟求剑。他本《计篇》、《形篇》、《势篇》有作《始计篇》、《军形篇》、《军势篇》者,殊未当也。《势篇》之首以奇正虚实对举,而下文专论奇正,颇似制艺中上全下偏体裁。若欲与《虚实篇》对待标题,则即题为“奇正篇”亦可也。然古人决不如此板滞,亦“学而”、“雍也”之意而已。世儒见“九变”、“九地”两“九”字对举,遂指“九变”为九地之变。胶柱鼓瑟,滞碍甚多,均辞而辟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