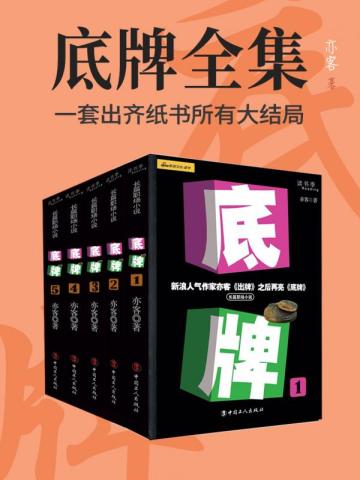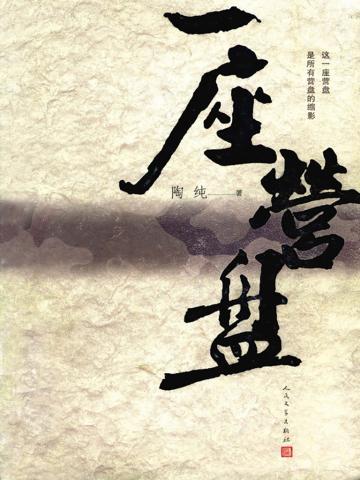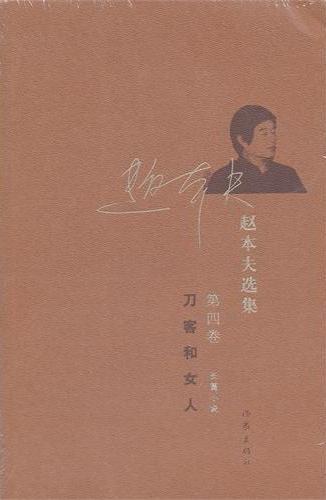外地来青云县城的人一般都不会迷路或者搞不清方向,因为这座始建于北魏黄兴年间的古老县城打小就长得十分方正,即使在没有卫星导航的年代依然很容易分清它的主要道路。它东西向的几条街道全部叫某某路,且均为“永字辈”的,由北至南依次为永昌路、永盛路、永平路、永安路、永和路;南北向的则全部叫某某街,且均是“崇字辈”的,由西至东分别为崇仁街、崇义街、崇礼街、崇智街、崇信街。最西边的崇仁街依着已经上了年岁的铁路干线,最东边的崇信街傍着才修没几年的高速公路。铁路干线和高速公路宛如两条长长的孔武有力的臂膀一般,把这个小小的县城牢牢地劫持住了,整个形势又如同两根硬棍绑着一个硕大的老鳖盖一样,而鳖盖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给人一种亘古不动的感觉,包括无处不在的毒热而憋闷的盛夏空气。
一切还都是老样子,喧嚣而繁杂,油腻而世俗,人眼所见之处似乎全都散发着扑鼻的咸咸的卤味,如同煮了上千年的老鹅汤,黄乎乎的油花子下面全是酱油色的混汁,且这混汁永远都不思进取和自以为是,丝毫也不在意它给别人造成的印象是好是坏。清明节前后鲜嫩杨柳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清新气息给人们的感官所造成的愉快冲击在这里是绝对没有的,即使有那么一星半点的意思,那也是极其稀罕的,更是不容易被人捕捉和察觉到的。
在任何地方呆久了都会让人心生厌倦,并且希望尽快逃离,这里尤甚,除非生活在这里的人已经过度成熟或者已然老去,对什么都不再好奇。那些已经过度成熟或者已然老去的人,经常会用他们那略显疲惫和懒散的神情顽固地看待眼前的一切,且佯装淡定和超然地以为世间的一切也不过如此,如此而已,并没有什么值得他们关注、激动和骄傲的新意,万事万物都只是在无聊地循环往复罢了。是的,如果一个人连厌倦的情绪都不会产生的话,那么他确实已经过度成熟或者已然老去。
永平路和崇礼街仿佛一个巨大的份量适中的十字架,规整地镶嵌在整个青云县城的正中,中规中矩,不偏不倚,像一个大家庭里面的长子一般稳重厚道,任劳任怨,默默地履行着县城主骨架的神圣职责。这个巨大的十字架把整个县城大致均等地划分为北关、南河、静安和梅山四个街道办事处,显示了一定要把一碗水端平的老家长意识。
两岸芳草萋萋、绿树如茵的,能够把雄浑和柔美两种意象巧妙地融为一体的,颇有几分浑厚气势的青龙河作为青云县的母亲河,就像是披挂在巨人右肩膀上一条不可或缺的厚厚护肩一样,从东北至西南,从左上方缓缓地流淌过整个县城的外围。而和青龙河同源同向共出却又略小一号,且以清秀妩媚、小巧别致和婀娜多姿为靓点的玉龙河,则只能称作姨妈河了。这条姨妈河是在县城的东北角与她的亲姐姐青龙河分道扬镳的,它就好比是佐罗先生挥剑在青云大地上潇洒地划了个反“Z”字,轻挑而又干练地流过小半个县城的东南部分。用蜿蜒的腰身缓缓地揽过古老的县城,这两条姊妹河又一路并行着,彼此时远时近地向着西南方向七八里远的留仙湖逛去,到那里去滋养鱼虾、抚育莲藕和生发香稻,去孕育和培养着另外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
既有让人倍感亲切的母亲河,定然少不了威严的神态里里又带着几分慈爱父亲山,否则便是明显的不平衡了,让人感觉不甚舒服,于是沿着永平路走到尽头就是本县的父亲山梅花山了。据说是因为周代的一个什么王被封在青云这片领地之后,他在这座山的南坡精心饲养了一群梅花鹿,所以千百年来这座山就被称作梅花山了。此山并不高大巍峨,气象万千,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在海西省很常见的小丘陵,就像一个长满了绿毛的大馍馍一样稳稳当当地盘踞在县城的东边,颇有在饥馑年代能让人好好地吃上一顿热乎饭的特殊气势。这种山向来是不能吸引大部分人的注意力的,因为它实在是太普通太平凡了,而且还没有什么较为有趣的传说附身加持,历史上有名的文人墨客也没给它留下点什么过硬的谈资,除非是已然喜欢上它的人才会对它一往情深,念念不忘。
就在当年青云王闲来无事养鹿的地方,如今坐落着本县的最高学府鹿苑中学,这也是张桂卿的母校。在母校刚上高一的时候,他还曾经搜肠刮肚地绞尽脑汁地写过一篇《梅花山赋》,来赞美和讴歌这座朴实无华的其貌不扬的父亲山呢,只是现在他连当年那篇文章的一个字皮都不曾记得了,说来不免有点小小的遗憾。后来的真切而又实在的生活,已经把他身上许许多多的小情小调和小资小派消磨得不见一点踪影了,全没了以前那种无知者无畏和无鬼者无愧的质朴情怀。尽管那些曾经疯长不休的并且一直折磨着他的行为和思绪,是在一种非常贫困潦倒的求学生活的基础上不屈不挠地顽强产生的,但是也依然抵挡不了悠悠岁月那无情的侵蚀和风化,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刀枪不入的,是能够屹立万年而不倒的,是可以流放百世而不变形的。
这天恰好是7月1日,正逢周日,热浪包裹中的小县城沉稳娴熟地上演着它一贯热衷于奉献的纷杂和吵闹,使身在其中的人谁也摆脱不了眼下这种胶着而持久的境况。八天前刚刚从省城同州大学毕业的桂卿是到县城来闲逛的,此刻都他刚从永平路西段路北的购物中心金碧大厦里面出来,手里捏着一件在一楼大厅花15块钱买的销价处理的白色短袖衬衫,一种他从前极少穿过的夏装。他很自然地留恋着大厦里面的股股冷气,带着重新走进酷热环境里的坚毅神情,快步走到门口存车处,去推那架他虽然动手修理过无数遍,却依然时刻担心它会不打招呼就擅自罢工的破旧自行车。当他把车子像划船一般推到路边,正考虑是往西走继续到火车站附近再逛逛,还是往东走回家的时候,突然不经意地发现从西边来了一位骑自行车的姑娘。
这位看似寻常无奇,而实际上却颇为耐人寻味的姑娘都头后扎着一个纺锤形的马尾辫子,这辫子中间饱满,一头圆润,一头溜尖,煞是好看。她前额的刘海显得非常自然飘逸,恰到好处,只有几丝头发脱离了整体在额前飘忽舞动。一双纯净无暇的几乎是会说话的大眼睛,在两帘修长睫毛的映托下折射着夺人心魄的美丽光泽。那双眼睛虽然背着西边太阳的强光,却没有一丝的幽暗和阴冷,里面流露出的欢欣光泽似乎可以和日光竞相映照地面上这条略显弯曲的街道。她的五官十分精致且比例特别协调,肤色适中,身材匀称,上身穿着一件杏黄色的短袖小衫,下身着一条浅蓝色带白碎花的长裙,宛如冬末春初深山里一株亮洁明艳的腊梅花,只是碰巧开在了这炎炎的夏季。
以桂卿的拙眼看来,这位姑娘美得简直是无以复加了,几乎符合了他心目中对年轻漂亮女孩的全部审美要求:天然形成的清纯可爱,浑身上下毫无半点腻歪人的脂粉气,身材方面整体略微偏瘦,没有任何油腻意味的俊秀脸庞带着盈盈的笑意。那一瞬间,姑娘那张熠熠生辉且神采飞扬的脸庞仿佛古希腊最著名的雕塑掷铁饼者、断臂维纳斯、雅典娜神像和胜利女神一样牢牢地凝固在了他的脑海里,而这一系列的绝美雕塑所综合形成的朦胧幻影,又随着自行车的移动转眼就滑向了不远的东边,一个他既可望又可即的黄金距离。
这种女孩天生就给人以美丽善良和温柔贤惠的类似感觉,即使别人目不转睛地较为粗俗无礼地看着她,都不会感觉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当然也丝毫不会有什么过于罪恶和内疚的感觉。桂卿自然不是那种随便看到个漂亮女人就走不动路的所谓风流人物,也不是什么道貌岸然、衣冠禽兽的所谓伪君子,更不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世外脱俗之人,他只是一个刚大学毕业的普通而又平凡的山区农村青年而已,身上甚至还带着些许的愚钝、粗鄙和懦弱的气质,他只是凭着自己朴素而天然的审美眼光和对美丽异性的天然感觉,去痴痴地追视着这个骑车的姑娘而已。一种相当震撼的强烈感觉俘获了他的心,并使他不能多想什么了。
“要是能娶到这样的姑娘当媳妇的话,我这一辈子真是死而无憾了!”他呆呆地想道,突然就有了一种鬼迷心窍的奇异感觉,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句话对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火热的目光能够传递声音的话,那么他的那双眼睛肯定已经把他这句滚烫的心里话在第一时间告诉了那位姑娘,并且还加上了若干的着重号、感叹号和下划线,以希望这位在他眼里像仙子一般存在的人物能倾听得真切、完全、深刻。那位姑娘似乎也感觉到了有一双火辣辣的年轻异性的眼睛在紧紧地注视着她,痴迷地追随着她,并且她还在经过对方身边的那一刻,略微调皮地侧颈转头,轻轻地扫视了对方一眼,随即便在自己脸上展现了一抹天使般的笑容。也许,这种毫无顾忌地凝视她的不甚礼貌的眼光对她来说已经见过得太多太多了,所以她对此也早就不以为然和不当回事了,但她这次还是因为率真的天性和本能的善良,没有让对方感觉出她所回应的笑容里面带有任何的鄙视和嘲笑之意。那种回应就像一个富裕而优雅的乡绅,随手拿出一个白面饼子递给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乞丐一样,给得从容,给得随意,给得自然,这个温馨而文明的举动既满足了别人的渴求,也满足了自己的心理追求。
这个轻盈灵动的偶然从街头出现的年轻女子,仿佛一颗从蔚蓝天际悄然划过长空的耀眼流星,具有无限多的光明和正能量,蕴含着巨大的吸引力并且强烈地吸引着桂卿的心,他那颗不知从何时开始就已经在砰然跳动的心,如同突然得了罕见的心脏病一样。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望着她靓丽多姿的背影,整个人都迎着落日的强光……
这是每个年轻男人都会经历过无数次的寻常场景,说来并没有什么过去稀奇之处,尽管心中有着太多的不舍和留恋,有着海量天真而热烈的幻想,但是在人家与他擦肩而过之后,他的思路还是很快就回到了模糊而又柔软的现实当中。流星就是流星,尽管它出现在天空的那一刻美丽得无以复加,但是毕竟不可能永远地照耀着漆黑的夜空。于是,他在亲手把自己心中那份对那个漂亮女孩的炽热渴望杀死之后,决定一直往东去,骑到永平路的尽头,然后使劲蹬着自己的小车子爬坡越过梅花山的北麓,出城之后再走过一大段丘陵山区的小路,回家。
有点怅然若失和意犹未尽的他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往东行着,行了大约有几百米的距离,就在快到永平路和崇礼街交叉路口时,他突然看见前面的人群躁动不已、古古怪怪的,这个猛然出现的情况只是让他感觉到有一片斑驳陆离的色差明显的衣服在来回地乱窜,而其他的更加明确的意识他就没有了。他惊讶地看见有的人正从远一点的地方往前面快步地小跑着,有的人则在大声地叫喊着什么,话语很不连贯。他在刹那间猛然记起,刚才隐约听到了一阵异常刺耳的急刹车的声音,也许根本就不用往别的方面多想,那一定是不幸出车祸了。于是,他也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车速,带着一种万一需要自己挺身而出,就立马跑过去参加救人性命这项高尚活动的慷慨之情。当然了,这其中也夹杂着些许看热闹的好奇心理。总而言之,他迅速地凑了过去,或者说是被吸引了过去,腿脚越来越快,年轻的他根本就抵抗不了这个下意识的本能动作。
位于十字路口东北角的,就是朴实平静、绿树成荫、带着些许威严气息的县政府,在那座外墙贴着白色瓷砖的方方正正的建筑物的前面,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这个院子此刻正向南张着一张暗绿色的大口,痛快淋漓地吸纳着未经过滤的炎热暑气,引得从此经过的路人不禁感觉到了偶然出现的丝丝凉意,心神因而也跟着安定了不少。
大约在路口的西南位置,围观的人群是里三层外三层,他不时听到有妇女的声音在说:“毁了,这个闺女看样子碰得不轻……”
“怎么回事呀,正骑得好好的,就撞了过来……”
“是啊,大睁两眼的,就能碰上,可能喝酒了呗……”
桂卿向来不太喜欢跟在别人的身后去看热闹,一来怕自己光顾着看闲情了,车子被孬种下三滥给偷了都不知道,二来也不喜欢和别人挤在一处,他觉得那样会显得自己和鸭子伸脖子去抢食一样,不仅表现得很没意思,而且还白白地折损了他身上那团原本就不够坚实和丰厚的人文气节。人都是容易自视甚高的,以为自己在很多事情上的看法和见解与众不同,别具一格,他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当大体上能够听到前边那些较为嘈杂的话语时,他心里在突然之间就感觉有些莫名的难受,不管被撞的人是谁都会让人觉得心疼不已都,想想看,车祸能有什么好结果呢?都是非伤即死的事情,这件事搁谁身上都将是天大的灾难。就算是不小心出的事吧,那开车人的心里肯定也不好受啊。
当想到被撞的人是个年轻的女孩这一点时,他的心冷不丁地往下猛然一沉,同时有些啰嗦地默念道:“哎呀,不会那么巧就是刚才骑车子的那个小姑娘吧?”于是,他急急忙忙地往前赶去,到了地方后就把车子随随便便地锁在路旁,接着就往人群中钻去来,也顾不了什么讲究了,也不怕在匆忙当中会碰着别人了,仿佛出事的人就是他的姐姐或妹妹一般,而且还是感情相当好的姐姐或妹妹。
到了跟前他仔细一看果不其然,正所谓怕什么偏偏就来什么,躲什么恰恰就遇见什么,前面就是一起让人感觉十分意外的看起来后果也较为可怕的交通事故。一辆黑色的小轿车,他也不认得具体是什么牌子,看样子应该是单位的公车,正车头朝南,斜着身子死皮耷拉脸地停在路口西南边靠路沿石的地方。在路沿石连着人行道的位置,摆着一辆前轮已经严重变形的车把已经大幅度扭曲的自行车。没错,就是那个刚才骑着车子的时候还欣然回应给他一个美丽笑容的姑娘,正一动不动地躺在人行道的地砖上呢。她的头部紧挨着一个暗红色的油漆剥落的老旧消防栓,脸朝向马路那边,黑色的头发半散开,下面有一滩十分骇人的暗红色血迹,有一小部分血还正顺着地砖的缝隙往靠近路面的一侧缓缓地流淌。她穿着一双灰白色的皮鞋,那双皮鞋看起来非常的雅致秀气,通过肉色的短丝袜连着她那匀称紧致的小腿。那双小腿不长不短,不胖不瘦,不黑不白,是典型的少女的腿,要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越是美好和珍贵的东西,在被天灾或人祸无情毁掉的时候就越是令人感到悲伤和动容,更何况现在被毁掉的还是这样一个鲜活明朗、楚楚动人、美艳娇羞的女孩子,是这样一个刚刚还十分友好和善地对着桂卿笑靥满面的女孩子,被如此快速而又如此残酷地毁掉,这就越发让他感觉难以面对和接受了。此情此景恐怕任谁看见了都会立即感觉郁郁不欢和悲戚难言的,更何况是桂卿这样一个本来就容易多愁善感,甚至是在很多情况下会突然变得愁肠百结的人,一个遇事总是习惯于往坏的方向考虑的人,所以他心中的伤感和悲恸就可想而知了。
好在这姑娘的鞋子还在她的脚上象征性地穿着,并没有掉下来。桂卿记得好像有人曾经说过,在车祸中只要人的鞋子不掉,一般是不会死的,如果鞋子掉了,那八成是没什么指望了。看着这姑娘现在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可怜样子,脸色也变得灰白了不少,他估计情况应该不是太好,尽管她的鞋子没掉。他当然知道,鞋子的说法只不过是就一般情况而言是这样的,甚至多少还有点迷信的味道,并不意味着绝对如此,所以他还是更加相信自己眼睛和直觉,即这姑娘可能真的不行了,或者她在被碰完之后就已经不行了,现在就算华佗再世也是无力回天了。
这姑娘如果真的死了的话,那么眼下的死相还不是太难看,桂卿本能地以为着,像没脑子的机械人一样。一想到这里,他又恨不能赶紧抽自己一个大嘴巴子,自己凭什么要想到人家会死啊?这真是天大的罪过啊,且罪不容赦,本身的动机就不好。一时间,他甚至都怀疑自己是否还有点最起码的人性吗,居然直接就想到了对方的死,这种想法是万万不能被原谅的。于是,他马上就在心里强迫自己默默地诚心诚意地祈祷起来,尽管他也知道这样做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甚至还有点愚蠢和可笑的意味在里边:“如果这世间真有什么神仙和异人的话,求求你们大慈大悲,发发善心,赶快显显灵吧,你们怎么能忍心眼睁睁地看着这么一个如花朵一样的姑娘惨遭横祸,意外地死在这般热闹繁华的十字街头呢?她还没有别过生她养她的爹娘,还没有别过喜欢她爱惜她的亲戚朋友,也许还没有好好地谈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终身难忘的恋爱,没拥有过一段宝贵异常且甜蜜无比的爱情呢。”
他心里顿时翻腾起一阵无比强烈的酸痛和悲伤,咸咸的温热的泪水默然涌到了眼角,他只消稍微微地闭一下眼,那些泪水就会山呼海啸般地夺眶而出。他已经没心情去看那个撞人的司机了,他宁愿那个已然闯下大祸的男人不在这个世界上,甚至当初压根就没被生下来,而只是不幸胎死腹中了。据围观的那些人断断续续地说,闯祸的司机应该是喝了不少酒,说话明显带着一股子酒气,只是还没达到烂醉如泥和不可收拾的恶劣程度,并且这厮当时在看明白大体的情况之后也及时拨打了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现在这个众人都以为是可恶至极的家伙倒是没跑,还在车子东边继续打电话呢,但是他的声音已经完全变了,腔调尖利得像个智商不高的女人一样。他话都说不成个了,脸色也变得蜡黄而发黑,两个鬓角附近全是豆大的汗珠子,大约也是吓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真是怎么也想不到的冤业啊,不早一步也不晚一步,偏偏赶到那个时间和地点就出了这个事。从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桂卿大概也知道了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就是那个司机为了躲一个夹着个熊眼闯红灯的骑三轮车的死老头,不小心把方向打过了,再加上他喝了酒,大脑不怎么听指挥,就把正常骑车的女孩给撞翻了。这个路口的红绿灯是整个小县城为数不多的几处红绿灯之一,大家并没有因为它的稀缺性而多么稀罕和重视它,相反,还有不少人却据此欺负起它的兵少将寡来,根本就不把它当回事,想怎么闯就怎么闯,就和在自己家里一样。那个懵懵懂懂地胡乱骑三轮车的老头子大约连红绿灯是干啥用的都不知道,就这么惹出一大摊子事来。现在那个让人恨之入骨的既可怜又可气的死老头已经悄悄地走远了,并没有留下来看热闹,这种人即使因为好奇而留下来围观这场事故,估计也不会认为这跟事和他有什么关系的。
很快,县中医院的急救医生到了,随后县交警队也来人了。两个穿白大褂的比较年轻的男医生简单地翻看了一下姑娘的眼睑,程序性地摸了一下她的脉搏,拿听诊器又听了一下她的心脏,就没再说什么,便指挥着穿绿衣服的两个随车人员把那个姑娘抬上担架搬到车里,往医院缓缓地奔去,警报声也没有开。交警们则忙着把肇事司机控制起来并进行简单的询问,同时开始疏散越聚越多的人群,拍照并测量现场,询问路人等。看得出来,虽然医生和交警经常遇到这一类的事故,但是这次他们的心情还是显得非常压抑和沉闷的,其表情也都显得特别凝重,很多时候他们的无情之举恰恰显示了他们的有情有爱。
那辆黑色的小轿车斜着停在路边,如犯了弥天大错而自己也受了重伤的孩子一般,其前窗玻璃右上角被撞裂了一个大坑,右前大灯附近也破烂不堪,可见当时的撞击力度有多大。人群久久没有散去,大家都还沉浸在对交通事故的愕然、迷惑和惋惜之中,有那后来的人则忙着向早来的人打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仿佛错过了一件天大的稀罕事情。有几个妇女则唏嘘不已,眼睛里面还流出些许泪滴,也许这样的意外又使她们想起来更多伤心的往事吧。
对于死亡或者说尸体一类的看起来比较恐怖的事情,桂卿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已经成功地破除了对它的天然恐惧感了,他所具备的直面死亡时所表现出来的和他的实际年龄不怎么相配的勇气,说起来和县城的一段铁路有着很大的关系。顺着永和路往西穿过一个低低矮矮的铁路涵洞之后,再南行几里路就是位于粮满镇黄石村他二姨家,这个铁路涵洞是附近百姓往来铁路两边的必经之道。那时他大约12岁左右,有一回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二姨家玩,在快到这个黑黝黝潮乎乎的涵洞时,老远看着三五个人在铁道上来回晃悠着,就很好奇地跑上去看看,结果发现原来是一个穿土黄色西装、套黑色裤子、带金丝边眼镜的男青年卧轨自杀了。那个人的身子在铁道西边,头颅在铁轨里面,面色蜡黄蜡黄,血迹隐藏在脏兮兮的石子里面很不明显,头和身子之间隔着一条铁轨,铁轨上面靠中间的部分寒光闪闪。很奇怪,当时围观的几个大人竟然没有制止他这个小孩接近那个可怕的现场,这就导致小小年纪的他突然就直面了那种特别恐怖的场面,以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脑子里面都会毫无预兆地蹦出那个无名卧轨者的可怕影像,且挥之不去反复萦绕,让他苦恼不已却又无计可施。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再不愉快的事情时间长了也会逐渐淡漠,更何况念头想法这些东西也不是想躲就能躲掉的,既然躲无可躲且藏无可藏,倒不如索性接受。于是,对于这类的事情他倒是很早就能够坦然面对了,就像面对任何司空见惯的成长的烦恼一样,这也算是坏事变好事吧。
其实再小的时候,他和很多村里的小孩子一样,对死亡还是充满深深的恐惧的。每每村子里有人去世,他总喜欢去听喇叭,看吊孝、行路祭、泼汤子等事情,但是对于那些个黑漆漆或者红幽幽的棺材却总是感到恐慌不已,觉得那就是一个暂时打盹的一个活物,他生怕走得近了会被突然醒来的活物吸进里面。而且那些一动不动的棺材看起来都是很厚很厚的,活人一旦被封在里面,恐怕就是喊破喉咙也没人听得见。每每想到这里,他就会感到无比的害怕,继而就会想到如果棺材被被埋进黄土里,那可更是暗无天日了,就算真有那休克假死的人被误埋了,恐怕也没办法把棺材从里面砸烂并进而跑出来,因此只能白白地被憋死。由此看来,把刚刚咽气的人停几天再入殓还是很有道理的,得给死人几天时间,让活着的人确定死者是真的死了再处理也不晚。死亡应该需要一个适度长短的过程,而不是瞬间就能完成的事情,就像考大学一样,得从小学、初中、高中学起。
当地农村骂人最狠的话莫过于说谁谁是“火车切的”和“大刀贼剁的”,这个“火车切的”他算是真真正正见识过了,毕竟那个已经魂归西天的男人的死相还算体面,不是太过离谱。按理说,有了以往的那种梦魇一般都独特经历,县城街里路口的这次交通事故就不会对他的心理产生什么太大的负面影响,但事实却并不是那么回事。当他准备离开事故现场像往常那样骑车子回家的时候,却发觉自己的意识竟然莫名其妙地有些恍惚,同时所有的感觉都不再真切了:身后落日的余晖,路边高大的法桐,向东一直延伸到梅花山北麓的永平路,全部变得有些不真实起来,一切都如同浸泡在了厚厚的水里面,此情此景仿佛在某年某月某日已经发生过了一样,他搞不清楚自己是在回忆一种重复过多次的梦境,还是本身就在梦里呆着,一种无论他怎么努力也逃不脱的十分可怕的梦。作为一个在县城东部山区长大的农村孩子,这条回家的路他曾经走了无数遍,可是这回他走起来却觉得忐忑不安,惴惴不平,好像有无数的颇为重要的心事都事先商量好了一样齐刷刷地涌上了他的心头,把他那原本容量就十分有限的心脏快要撑破了一般。小小的心里既然装不下这么多无头无脑的事情,这些没有正常出路的事情自然就继续往他脑袋里面涌去,直到脑袋里面也装不下了,便又从耳朵和眼睛里溢出来,搞得他越发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现如今又身处何地了。
在这些颇显复杂而沉重的混乱感觉里面,最主要的一种就是,他老是觉得那个姑娘在和他并排骑着车子一路向东,并且和他一直都有说有笑的,看起来无拘无束无所畏惧的,就像是认识多年的红颜知己那样。不管他说什么或者想什么,说得恰当不恰当,想得合适不合适,她似乎都能心领神会,一点就通,可以非常流畅而自然地和他进行一番完美无瑕的沟通和交流,并且还始终都带着一种较为醇厚质朴的欣赏和怜惜的意味在里面。在丝丝缕缕的朦胧和迷蒙之中,他偏偏又体验到了阵阵清清爽爽的奇妙感觉,这其中竟然还混合着些许的甜意和畅快。有一种类似热天里每个人都想得到的那种彻头彻尾的凉爽,冷天里每个人都想得到的那种真真正正的温暖的东西,一层一层地把他和她严密结实地环绕起来,同时也把他们两个和周围的喧嚣环境完全隔离开来。一个从未真正恋爱过的年轻人突然间找到了恋爱的神奇感觉,那种十分异样的最大幅度的躁动情绪焦灼地流淌在他的每一寸血管里,且迅速地遍布了他的全身,融进了他的每一个细胞里面,特别是神经细胞,特别是那些负责幸福和美好感觉的神经细胞。
就这样,他带着这个姑娘回家了。